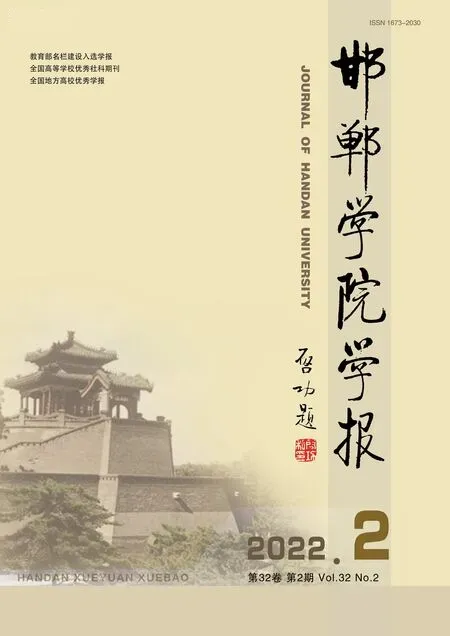論有機整體美學觀是馬克思主義生態美學的重要觀點
張子程
(內蒙古師范大學 文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如果說傳統美學是圍繞人,以人為中心的美學,那么馬克思主義生態美學則將審美視野擴展到了整個生態系統中,將整個生態系統作為自己美學關照的對象,如此就不會將馬克思主義生態美學僅拘泥于傳統美學“以人為中心”的視域內,而是將人——社會——自然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納入到美學研究的范圍,從中發現新的審美議題,從而解決傳統美學所沒有或無法發現的新問題。
一
從人類思想歷史看,應該先有“整體”的思想觀念,之后才有“有機整體”的說法。所以,“有機整體觀”有一個歷史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并非是人類早期就能達到的一種認知水平;而整體觀的思想早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如早期的哲學家們多數將“物質性的本原”看成是世界的根本,也就是說,他們常把某一種或某幾種物質看成是世界萬物的始基,認為萬物均由它或它們構成。例如古希臘米利都學派創始人泰勒斯(Thales)認為“水”是萬物的本原。阿那克西曼德(Anaksimandros)認為萬物的始基是“無限者”,“因為一切都生自無限者,一切都滅入無限者。”[1]16阿那克西美尼(Anaksimenes)將“氣”看成是萬物的基質,認為“我們的靈魂是氣,這氣使我們結成整體,整個世界也是一樣,由氣息和氣包圍著。”[1]18畢達哥拉斯學派則把“數”作為萬物的本原,“認為數目的元素就是萬物的元素,認為整個的天是一個和諧,一個數目。”[1]19他們所講的這個數目其實就是“一”,也即“萬物的本原是一”[1]20。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認為世界在本質上是“一團永恒的活火”,“一切轉為火,火又轉為一切。”[1]21。德謨克利特(Demokritos)堅持一切事物的本質都是原子和虛空,也就是說,原子和虛空構成了整個世界。這種探索世界本原的哲學觀點所采取的認知路線都是把世界萬物還原為某一種或某幾種實體,并以此作為世界萬物的根本,由此形成物質整體世界。恩格斯曾說,古希臘時代的哲學,“在自己的萌芽時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現象的無限多樣性的統一看作不言而喻的”。[2]35
中國古代的整體觀在哲學中也曾占有重要的地位。如《黃帝內經》認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素問·寶命全形論》)人由天地之氣形成,天地是人的父母,因此,人能適應天地的變化并且能對天地的變化做出反應;因為從本質上講天地人三者均由“氣”構成,這就是一種最素樸的整體觀。《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辭傳》),把“生”看成是天地的習性,也是天地最重要的一條法則。《禮記·中庸》從人的本性出發,認為人性是由天賦予的,個人的本性與其他人與物的本性是相同的,因此人可以參與到天地的變化之中,并與天地并立而存。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雛形,內含著天地萬物統一的哲學思想觀念,“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二十二章》)并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三十章》)。在中國古代,最能集中反映中國人“整體”思想觀點的是“天人合一”。可以說“天人合一”是集儒道自然觀之大成,中國古代許多哲學家、文藝家、思想家均持有這樣的觀點。可以說,“天人合一”在中國古代自然哲學中占有主流思想的地位,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而“有機整體”的觀念在西方美學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但柏拉圖的有機整體思想主要表現在國家政治思想方面,在美學方面則較少,不過也有一些零星的觀點,如在《理想國》中記載了蘇格拉底與格羅康的一段對話就表現了柏拉圖有機整體的思想萌芽,“蘇:對于有眼睛能看的人來說,最美的境界是不是心靈的優美與身體的優美諧和一致,融成一個整體?格:那當然是最美的。”[3]64有機整體思想等發展到亞里士多德時就表現得較為豐富一些,并且成為亞里士多德思想的一大特色,如他認為,“無論是活的動物,還是任何由部分組成的整體,若要顯得美,就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即不僅本體各部分的排列要適當,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體積,因為美取決于體積和順序。因此,動物的個體太小了不美(在極短暫的觀看瞬間里,該物的形象會變得模糊不清),太大了也不美(觀看者不能將它一覽而盡,故而看不到它的整體和全貌——假如觀看一個長一千里的動物便會出現這種情況)。所以,就像軀體和動物應有一定的長度一樣——以能被不費事地一覽全貌為宜,情節也應有適當的長度——以能被不費事地記住為宜。”[4]74-75“適當”“適宜”是判定美的事物的最基本的標準。因為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一個事物若要美,除了它的各個部分應有一定的適當的排列,在體積上也要大小適宜,因為美取決于事物的體積和順序。無論是藝術還是其他事物,若要美就必須展現出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美與不美,藝術作品與現實事物,分別就在于美的東西和藝術作品里,原來零散的因素結合成為統一體。”[5]39
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看法,也有完整性、統一性這樣的要求,“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經過‘裝飾’的語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別被用于劇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動,而不是敘述,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疏泄。”[4]6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亞里士多德“有機整體論”的思想觀點還是較為明確的。他的這一思想既是對當時文藝實踐的一大總結,也是進行文藝評論的一把標尺,這為后來文藝理論的發展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貴的文學遺產。再如新柏拉圖主義奠基人普羅提諾(Plottinus)(204-270 年)在《九章集》(Enneades)中認為的那樣,“美就奠定在這種統一性之上,使部分和全體都是美的。當美照亮某種自然而勻稱的統一體時,也照亮了整體。打個比方說,整個房子是由所有部分組成的,房子的美會通過某種自然品質賦予每一塊石頭。”[6]13-14古羅馬時期希臘修辭學家朗吉弩斯(Casius Longinus)(213-273 年)在《論崇高》(On Sublimity)第40 章中說,“文章要靠布局才能達到高度的雄偉,正如人體要靠四肢五官的配合才能顯得美。整體中任何一部分如果割裂開來孤立看待,是沒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但是所有各部分綜合在一起,就形成一個完美的整體。”[5]48
西方及至近代始,持有“有機整體”思想的哲學家、思想家、文藝家仍然有很多,他們各自分別提出了自己的有機整體思想,如美國當代著名學者、歷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他的《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ecological Ideas)一書中指出,“懷特海堅持認為,大自然的各個不同部分就如同一個生物機體內部一樣是如此緊密地相互依賴、如此嚴密地編織成一張惟一的存在之網,以致沒有哪部分能夠被單獨抽出來而不改變其自身特征和整體特征。一切事物都與其他事物鉤連在一起——不是像機器內部那樣表面上機械地聯在一起,而是從本質上融為一體,如同人身體內各部分一樣。”[7]370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將自然視為一個類似于生物一樣的有機整體,而組成這個有機整體的各個部分并非如機器那樣只是一種簡單的機械性的關聯,而是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如同人體那樣的在本質上相互聯結的整體,這就是一種完整的有機整體論思想。
中國古代有關“有機整體”的思想觀念似乎較西方更為豐富一些。在老子的《道德經》中他曾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道生萬物,萬物則由陰陽二氣相互交蕩構成。因此,天地生生萬物自成,天地渾然自成為一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道德經·第三十九章》)老子在這里連用了幾個“一”字,這個“一”其實是突出了“道”的特點,有“整一”之意。如此,在老子看來,天地萬物均在“道”也就是“一”的自然而然的統攝下運行,在陰陽二氣相磨互蕩下而“道生之,德畜之”(《道德經·第五十一章》),萬物生生不息,維持著世界的和諧與統一。萬物統攝于“道”,而人是其中之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經·第二十五章》)這是一種極為素樸的有機整體論思想。莊子以老子思想為基礎形成了以“和”為中心的獨特的美學思想,進而與老子一起成為道家思想重要的代表人物。莊子的哲學與美學思想重“生”,認為“生”乃天地之大德,因此建立了一個以“生”為主要秩序的畸形怪誕的形象世界,從而構成了中華美學史上一幅獨特的生態美學景觀。莊子認為天地萬物因“生生”而成其態,統一而結構為姿態萬千、光華燦爛的世界。這均源于“道”的至廣至大。無論是“以人合天”,還是“以天合人”,都是“物我同一”的結果。由老子到莊子,道家的“有機整體”思想日漸成熟,并為后人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開創了廣闊的前景。日本著名學者理論物理學家湯川秀樹(Yukawa Hideki)對此問題頗有見地,他說:“對于東方人來說,自身和世界是同一事物。東方人幾乎是不自覺地相信,在人和自然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和諧。”[8]37
二
進入20 世紀以后,隨著生態科學的逐步建立與發展,有機整體觀念不再以自發的、素樸的、零散的形式發生作用,而是以科學的、系統的、自覺的形式產生作用,并且“生態”一詞也溢出生態學科的界限逐漸滲透進其他學科領域,從而使“有機整體”這一古老的思想觀念重新煥發出生機,并對其他學科發揮著巨大的影響作用。因此,有機整體觀無論從思想深度上還是從影響廣度上已非過去素樸的有機整體思想所能相比的了。
下面,我們就對現代有機整體觀進行簡單的梳理:
在講到“現代有機整體觀”時,我們就不能不提美國生態學家和環保主義先驅阿爾多·李奧帕德。通過與大自然的多年接觸,他悉心地觀察大地上動植 物的生長、變異、繁盛,及土地自身的命運,明確地提出了“土地倫理”的問題。他認為人不應以征服者的姿態對待大地及大地上的生命,而應以謙和的態度對待自然,因為他堅信“征服者最終都將禍及自身”。在其著作《沙郡年記》和論文《西南地區自然保護的基本原則》中,他提出人們應盡力弄懂生命體和其周圍環境之間各種復雜的關系,并知道其中隱藏著的自然規律。同時,他要人們認識到自然其實是一個由不同的生命器官組成的有機整體,并借此將人類的一切行為納入到維護自然的倫理規范中。他還告訴我們,若要土地予以倫理的對待,人們必將土地視為一個統一的和完整的有機整體,并且除了從經濟得失考量外,也應從倫理及美學的視角去思考,這樣就能夠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了,“想要促進倫理規范的發展過程,一個關鍵步驟就是:停止將正當的土地使用視為純粹的經濟問題。除了從經濟利害關系的角度來考量外,我們也應該從倫理和美學的角度來考慮每個問題。當一件事情傾向于保護生物群落的完整、穩定和美感時,這便是一件適當的事情,反之則是不適當的。”[9]285人與自然的矛盾在人,人的因素占了主導地位,人的因素不改變就很難處理好人與自然的矛盾關系。因此,阿爾多·李奧帕德勸告人們只有把土地當成朋友,與土地和諧共處,才能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當然,阿爾多·李奧帕德也明智地指出這種和諧相處其實也存在著競爭,但其中的合作占主導作用。“自然資源的保護是要達到一種人和土地和諧共存的狀態。這里的土地是指地球表面、其上和其內的一切事物。和土地和諧共存就好像和朋友和諧共處一樣;你不能砍去他的左手,只珍惜他的右手。換句話說,你不能憎惡掠食者,只喜愛獵物:不能蹂躪山脈,只保存水域;不能破壞農地,只建造森林。土地是一個有機體,其中的各個部分和我們一樣,彼此競爭,也彼此合作。競爭和合作一樣,都是內在運作的一部分。你可以小心翼翼地調節這些部分,但是你不能廢除它們。”[9]212-213
無論是競爭還是合作都屬于土地的一部分,因為土地是一個有機整體。阿爾多·李奧帕德的有機整體自然觀相較于古代素樸的整體觀和有機自然論無疑是進步的。美國環境倫理學教授卡洛琳·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認為,“生態學的前提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都是和其它東西聯系在一起的。它強調自然界相互作用過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部分都與其它部分以及整體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生態共同體的每一部分、每一小生境(niche)都與周圍的生態系統處于動態聯系之中。處于任何一個特定的小生境的有機體,都影響和受影響于整個由有生命的和非生命環境組成的網。作為一種自然哲學,生態學扎根于有機論——認為宇宙是有機的整體,它的生長發展在于其內部力量,它是結構和功能的統一整體。”[10]110然而無論是阿爾多·李奧帕德、卡洛琳·麥茜特,還有其他生態學家、環境倫理學家或環境哲學家,盡管他們的有機整體自然觀相較于古代素樸的有機整體觀有很大的進步,但他們的有機整體自然觀是建立在直觀自然的基礎上,未能徹底擺脫機械自然觀的束縛,因此,他們的自然觀并沒有走向真正的全面的科學的自然觀。原因在于,現代有機整體論盡管把自然界理解為一個統一的和相互包含、彼此影響的存在,但其觀點因忽視或缺失了人的實踐性,就把人的因素排除掉了,這樣的自然就成了一個“無人”的自然。由于將人的實踐因素被排除在了自然之外,因而其所謂的有機整體自然觀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有機整體思想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并非現代社會才出現的一種思想觀點,而這一思想等發展到馬恩生活的時代時就已十分成熟了。馬恩正是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有機整體自然思想,因而馬克思主義生態美學倡導的就是一種以實踐為基礎的有機整體論,這就為馬克思主義生態美學的建立奠定了最為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三
馬克思主義生態美學要堅持或主張什么樣的有機整體思想或理論,這是需要我們討論的重點問題,恩格斯的觀點最具代表性。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舉例說,“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別的地方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競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在這些地方剝奪了森林,也就剝奪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存器。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樅樹林濫用個精光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里的山區畜牧業的根基挖掉;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競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來。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不知道和這含粉的塊莖一起他們也把瘰疬癥傳播過來了。因此我們必須在每一步都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決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個人,——相反,我們連同肉、血和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2]305耕地與樹木,樅樹與牧畜業,栽種馬鈴薯與傳播疾病,它們各自之間在表面上似乎沒有多大的關聯性,但自然界因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局部自然環境的改變會給其它自然因素或整個自然生態環境帶來巨大的變化。這樣就促使人們認識到,在看待或處理自然事物之間的關系時不能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而應深入自然事物背后去發現其潛在的本質聯系,研究自然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自然秩序中發現和認識自然規律,而不是從眼前的或局部的現象去裁定所謂的人類能夠戰勝自然的所謂勝利,因此,恩格斯告誡人們,“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在第一線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線和第三線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它常常把第一個結果重新消除。”[2]304-305正因為如此,人類在與自然界打交道的過程中要學會理解和掌握自然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去從事改造自然的生產實踐。這樣我們就可以提前預知或認識到我們在干涉自然過程中可能會引起的或近或遠的后果,并且隨著人類認知自然的手段愈來愈科學和先進,這種認識就會更加明顯和一致,那就是所謂的人與自然等的對立是十分荒謬的和不可能的事實。恩格斯的上述觀點明確地告知我們,人類就在自然中并屬于自然界。人類的強大在于認識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去正確地運用自然規律從事實踐。所以說,人類如果陶醉于對自然的勝利就會遭到自然界的無情報復。在此情形下,人類就應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會影響到自然的慣常行程,并且想到干涉自然可能得到的最為嚴重的后果。恩格斯認為人與自然是一致的,同屬于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世界,因此,那些將人與自然,甚至將人的靈魂與肉體割裂開來的觀點是極為錯誤的。這就是恩格斯對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最為深刻的認知,其集中地體現了恩格斯的有機整體自然觀,這為馬克思主義生態美學提供了基于現實的最為本質的理論指導。可以說,馬恩在自然觀上的一致性最大限度地保證了馬克思主義生態美學理論指導思想方面的有效性。
對于整個自然而言,其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其中的各個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進而構成事物的運動,維持著世界的運轉與變化。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和我們相接觸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而我們在這里所理解的物體,是指所有的物質的存在,從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們承認以太粒子的存在的話。這些物體的互相聯系這一事實就包括了,它們是相互作用著的,并且物體的這種相互作用正是運動。”[2]125對于我們人類來說,與自然界是難以分開的,無論是肉體的存有還是精神的存在都離不開同自然的交往。正如馬克思在《手稿》中曾指出的那樣,“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56-57
除人類外,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體與自然界的關系都莫不如此,因為地球就是一個由生物和其環境構成的有機整體。生物通過與自然生態環境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因果互依、環環相扣的生物鏈體。在這個鏈體中的每一類生物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形成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系之網。人類的審美正是產生于整個自然生態系統中人與自然有機整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則是借助于人類的實踐能力完成的,而人類的實踐為美的產生提供了決定性的前提條件。沒有實踐,物的世界就不可能在人類面前轉化為美的世界,其他動物之所以無法對物的世界產生美,原因就在于此。所以說,自然生態美的產生,無法脫離開人與自然所構成的這種有機整體關系,并以這個有機整體為前提,才能形成對自然的生態審美關系。若脫離開有機整體這個大的前提條件,對自然的審美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了。正是在這個大的前提下,人類的審美實踐才能順利地展開。對此,我們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說明:
首先,人類審美器官及審美能力的形成離不開實踐條件下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第一,人類審美器官的形成離不開人類的生產實踐。在自然人化的過程中,人類的感覺器官慢慢地擺脫了其他動物那種原始單純的自然能力而具有了社會性。人的視覺不再拘泥于自然的本能“直觀”,人的聽覺也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僅與生存關聯密切的物的聲音的獲得,而是可以直接地從事物的感性樣態或聲音就能感覺到其與人及人類社會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并且形成了一種超越實際功利的對待事物的態度,即審美態度,也正是有了這種審美的態度才拉開了人與物之間的距離,為人類自由地對待物留下了充足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其實就是人類自由創造的空間,因為它超越了實際功利的那種短促的時間關系模式,為自由對待對象留下了足夠的時空。如,買來面包就得吃掉它以滿足人的饑餓感,但畫個面包則可留著去慢慢地欣賞。另外,人自身自然的人化、社會化也是造成人的感覺器官由原生的動物式的純自然感覺器官變成人的感覺器官的最直接的原因。人的外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內在自然的人化是同步進行的。外在自然的人化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人的內在自然的人化同樣是人的本質力量通過作用于自然對象之后又反作用于人本身進而造成的最為現實的結果。所以,自然人化可以說是人類實踐的一種雙向作用的結果,既指向人之外的自然,又指向人自身的自然。前者的結果就是將原生自然納入到了人類社會活動的范圍,使自然具有了社會性;后者則將最初的具有動物性的人的器官及感覺納入到了社會意義的范圍內,從而使人的感覺器官變成了審美的器官,使人的感覺具有了審美的屬性。原因在于,“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11]87有了能夠審美的感覺器官,人類才能使生冷冰硬的自然變成人的審美對象,也才能在對象中肯定自己,同時也確證了人與動物之間的差別,證明了人的存在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存在,也是一種能夠審美的存在。如果缺失了實踐性,人類就不可能進入審美的世界,正因如此,馬克思才說,“人的眼睛與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與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11]86因為“眼睛成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對象成為社會的、人的、由人并為了人創造出來的對象一樣。因此,感覺在自己的實踐中直接成為理論家。”[11]86也就是說,人的眼睛和耳朵之所以與其他動物有很大的差別,原因在于人自身自然的“人化”與社會化,而這一切均源自人類實踐創造才能的形成。第二,實踐為人類審美能力的形成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人類審美能力的產生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的。人類能夠進行審美,首先得具備一定的審美能力,而審美能力的產生正是在不斷地改造自然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人類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創造智慧和才能不斷地對象化,使自然事物按照人的意圖和計劃發生變化,最終實現人的目的。人類正是在這樣反反復復改造自然的實踐中,通過認識自然對象、熟悉自然對象、親近自然對象,并與自然對象建立起情感關系而逐步培養起了自己的審美能力。
其次,人在“生態審美模式”下才可順利地完成對自然的審美。從大的范圍講,人類的自然審美需在“生態審美模式”下才可順利地進行。西方傳統美學在涉及到自然審美問題時,一般采用“藝術審美模式”進行;然而這種所謂的“藝術審美模式”當用在對自然對象時就不太恰當了,因為“藝術審美模式”一般是把審美對象當作一個孤立的事件加以看待:一是審美主體要與審美客體保持適當的“距離”(物理的或心理的),最典型的就是立普斯的所謂的“距離產生美感”說;二是審美主體要將審美客體從其所在的環境中分別出來,使其“孤立”為一個或幾個審美對象;三是審美主體要使審美對象始終保持一種確定的形式;四是審美主體重點關注的是審美對象的外在形式而非其內容;五是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總會間隔一層文化屏障,若要完全徹底地領悟審美對象的美,必須突破文化的屏障才能完成;六是若要完成審美,審美主體或審美對象總要保持在一種靜止的狀態中,否則審美就難以順利地完成。因此,所謂的“藝術審美模式”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具有形而上學特征的審美模式,這種審美模式如果用在對自然對象的審美上,必然為人們帶來極大的困擾。與藝術審美相比,自然審美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在具體的審美過程中,審美對象因與整體自然融為一體而很難從中剝離出來。即使通過審美主體的主觀努力將審美對象從整體自然中分別出來,審美對象也因脫離生態自然而失去其自身固有的審美特質,如黑格爾在講到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時曾說,“只有作為有機體的一部分,手才獲得它的地位”[12]156,在自然生態審美中,對象若脫離了自身所屬的有機整體也必然會失去其本有的美學特質。如大自然中漂亮的野花野草,若將其采摘插入花瓶后就會失去其本有的野性之美,反到成了工藝美的一部分。因為它原有的那種略帶土腥味的芬芳,花葉上閃耀的露珠,在風中搖曳的迷人姿態美就徹底地喪失了。因此自然作為人類的審美對象,其與整體生態自然密不可分,也正是因為有了整個大自然的支撐才使自然審美對象具有了不可復制的審美特征;如果喪失了整體生態自然,所謂的自然美就喪失了其獨特的審美特征了。對此,加拿大環境美學家艾倫·卡爾松曾做過十分詳細的研究。他認為,在自然美的欣賞中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對象模式,另一種是景觀模式。“對象模式并沒有將自然物體轉變成為藝術對象。它可能簡單地將自然物體從周圍環境中實際上或想象上予以移出罷了。”[13]26“如此欣賞的自然物體便成為‘現成品’或‘實物藝術’。自然物體被理所當然地賦予藝術品的資格,并且,它們如同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的小便器——杜尚賦予其藝術品的資格,并稱之為《噴泉》(Fountain,1917)——那樣成為藝術作品。”[13]26這種對象模式在實際的欣賞中,其實并沒有將自然物體轉變為藝術對象,但當從自然環境中實際上或在想象中被移出后,它們就變成藝術對象了,就如同小便器被當成了藝術品,乃是由于將它從其自處的物理環境中,即廁所中被移出,這樣小便器的實用價值被消除了,而其藝術價值展現了出來。因此,當我們欣賞的自然對象在想象中被我們從其自處的生境中移出后,就已喪失了原有的性質或特點,而我們欣賞到的自然美實際上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原生自然美,而變成了藝術的對象,即藝術美了。這就說明,真正的自然審美與藝術審美其實有著很大的不同。藝術審美關注的對象多以獨立的形式出現,盡量減少與周圍環境的瓜葛,因此它可以獨立不依,并且有章可循;而自然審美對象則與周圍的生態環境密不可分,它雖自由,但難以獨木成林,如此,它所呈現出的美的性質與特點與藝術美相比就難以把握了。第二,在自然審美活動過程中,審美主體往往不需要“審美距離”作為其開展審美活動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沒有審美距離才是自然審美活動最為突出的特點。自然審美就在自然中,這無疑是自然美學一個十分重要的美學特征。相反,藝術審美則需要一個恰當的心理“距離”。正如美學家布洛(Edward Bullough)所認為的那樣,“一切藝術都要求一種距離極限和一種心理距離,只有在極限之外和距離之內審美欣賞才有可能:這是藝術的一個普遍特征的心理學概括……”[14]384。藝術欣賞需要一定的“心理距離”,但自然美的欣賞并不基于這種個人的心理事實,而要從一種更廣泛的意義上去理解。所以,自然美的欣賞并不在乎某種類似藝術那樣的框架,比起藝術欣賞來它顯得更加自由、輕松和從容,因為藝術欣賞要復雜的多。對藝術欣賞來說,既需要心理因素的介入,更需文化等的參與,否則很難順利地完成。因此,藝術欣賞必須在一定的“水平”上才能進行,它不能像欣賞自然美那樣,只要依存于自然本身的存在狀態和性質便可進行,原因在于人和自然之間“無距離”,因為人與自然之間無任何的“阻隔”,無論是心理的還是物理的距離都不需要。第三,自然審美對象總處在變動不居之中,無固定的樣態。自然審美對象作為整個自然生態環境中的一部分,時時處處受整體自然生態環境變化的影響;可以說,“變”是自然審美的一個最大特點。諸如,云的變幻莫測,水的湍流激蕩,山的云蒸霞蔚,湖海的波濤洶涌等等,可謂“千里之山不能盡奇,百里之水豈能盡秀”[15]57。自然事物變動不居,美的姿態更是萬萬千千,“真山水之云氣,四時不同:春融冶,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畫見其大象,而不為斬刻之形,則云氣之態度活矣。真山水之煙嵐,四時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凈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15]35-38“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十數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15]39又說,“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不同也。……春山煙云綿聯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凈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15]39-42中國古代山水畫家,對自然變化中所呈現出的美的獨特價值的揭示,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審美文化中最具啟發性的自然審美思想了;同理,西方美學中也有人主張自然審美多在變化,如達芬奇在舉光的例子時說,“瞧一瞧光,注意它的美。眨一眨眼再去看它,這時你所見到的原先并不在那里,而原先在那里的已經見不到了。”[5]69-70自然的變化引動審美的變化,使自然審美 呈現永無止境的美景。第四,自然審美是一種全方位的審美體驗。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然審美要受整體自然生態環境的制約與影響。因為自然審美活動不可能在人工的環境內發生,需在自然的生境中進行。在自然審美活動過程中,審美會受到整體自然因素,如冷熱、陰晴、風雨等的影響。也就是說,在審美時,除了視聽感覺的主要參與外,還要有嗅、味、觸覺的介入,因此,自然審美是一種能激發人全身心各個要素參與的活動。對此,中國古代詩人在游歷自然山水,登高望遠時有很深的體會。詩人往往通過觸興起情,寄情托志而獲得強烈的美感,“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劉勰《文心雕龍· 神思》)詩人能有這樣的感受與詩人全方位的審美體驗密切相關。自然審美除了美以其外在的形式給人以美的感受外,更能以豐富的內容撼動人的心靈,激發并養育人的審美內涵。自然審美由形式而引發的內在美有時十分深刻,如竹子除了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外,人們往往會借其外在形象比喻人的內在品德,喻指道德高尚的人謙虛內斂而人格端直,不會無事生非而污濁他人;蘭花形象清雅高潔,清香四溢,人若如蘭則德高雅趣,淡泊寧靜,與世無爭。所以,對自然的審美由外而內則是一種全方位的美感體驗。第五,審美主體在欣賞美的對象時,無需借助文化因素就能輕松地與之建立起一種直接的審美關系。因此,對自然的審美,多是在輕松自由、簡單快樂、無拘無束的情形下進行。因為“人直接地就是自然”(馬克思語)在此情形下,可以說任何人都能在自然中完成沒有任何“距離感”的審美。在自然中,人就不像在對藝術的審美時那樣需借助某種“文化”才能完成。如,要想欣賞文學的美最起碼得識字,還要懂的文學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風土人情,民族文化,方言俚語等等;若要欣賞繪畫美就得懂得色彩、線條等繪畫語言以及其他文化要素等;相反,對自然美的欣賞則不必過多地受文化因素的影響。比如一位地理學家在大自然中也許不如一位兒童對自然美的欣賞來的更快、更直接和更快樂;因為地理學家在欣賞自然美時常常會不自覺地勾連起地理學知識來看待自然,而忽視自然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美的東西,因而不像兒童那樣輕松地對待大自然,進而引起對自然的美感。明代李贄提出“童心說”。假如我們用“童心”去看待世界看待自然,那么就會花有花姿,鳥有鳥語,自然界便是一個童話般的美的世界了。
總之,有機整體自然美學觀并不孤立地看待自然中美的事物,而是把自然審美看成是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在而生發的一種美感,可以說其是有機整體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脫離有機整體去孤立地看待自然中的美,那么這種所謂的自然之美就會失去生機而成為一種美的標本,即一個自然物如果與周圍自然生態環境無任何關系也就很難觸發起人們的審美情趣。人們無論是對自然中美的欣賞還是認知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整個生態環境的影響;而自然中美的存在與顯現也絕不可能脫離開人與人類社會。因此,在自然有機整體背景下進行的審美,其實就是人與自然之間,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一種無聲的交流與對話,更是一種人——自然——社會之間的精神交往。正因為如此,人類在自然審美過程中,不應將自然審美對象與整體生態環境剝離開來,使其“孤立”為一種審美對象,那樣的話也就背離了自然生態審美的原初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