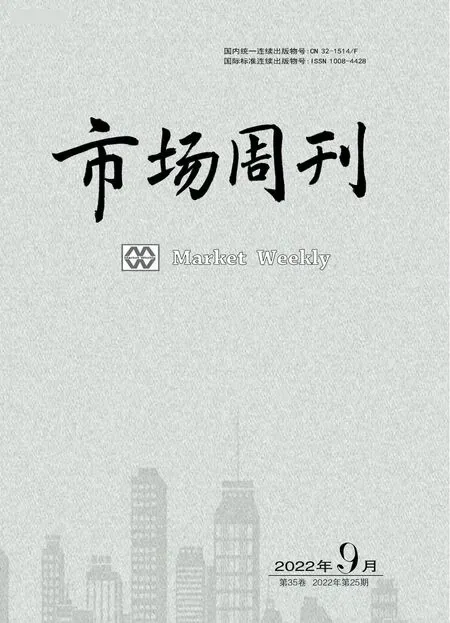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的適用思考
徐博聞
(南京財經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
一、 立法背景與目的
2015 年,我國首次將對欺詐、脅迫、惡意串通、口頭遺囑或者贈予這五類事項的證明標準在立法上提升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對證明標準的提高具體適用的規定卻未予以細化,由此不免引發實踐中證明標準的適用混亂。
權威注釋書中提到,該證明標準提升一方面回應了實體法上對特殊事項的規定;另一方面旨在借鑒比較法的經驗,構建多層次的證明標準體系。 由于欺詐、脅迫、惡意串通的主張一經成立,會產生實體法上法律行為被撤銷或者無效的法律后果,因此需要對此類事項慎重對待,保護被主張權利人的利益不受損害,故提高權利主張者的證明責任,維持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 而口頭遺囑或者贈予由于其沒有物質載體予以固定,極易偽造,故提高證明標準以保護贈予人、被繼承人的財產權益。 相比起被贈予人、繼承者可能無法獲得財產的損失,立法者更傾向對財產擁有者的保護,以此維護交易秩序的穩定。
二、 域外制度考察與啟示
在大陸法系中,對一般事項法官認為事實具有高度蓋然性從而達成“內心確信”,要求法官在窮盡并運用現有證據后,認定有高程度可能性成立的待證事實為真實。 由于客觀的證據標準難以適應所有案件,為達客觀真實,從而賦予裁判者更多的自由裁量權,使其更加注重挖掘事實真相,但對某些特殊事項證明標準也存在適當降低。 因此,在大陸法系中,高度蓋然性實際上已逐步成為法官形成“內心確信”的輔助工具。 而英美法系通常采用優勢證明標準。 若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就認定其所主張的事實存在。在美國,證明標準共分為九個梯級等級,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居于最高地位,適用于刑事訴訟,一般民事案件適用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對特殊的民事案件會提高證明標準到“明晰可信”標準,有學者為了方便與我國民事訴訟中“排除合理懷疑”的規定進行比較,將之稱為“近似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從比較法的視角看,兩大法系的民事訴訟程序并不拘泥于單一的證明標準,對特殊事項的證明標準都存在一定的提高或降低,構建了多層次、多元化的證明體系。 層次化證明標準體系建構有利于應對不同程度的民商事案件,以此達到公平效率的裁判要求。 但證明標準并不是隨意提高或者降低,其必須依據法律的明文規定,否則會造成實踐中適用的混亂。
三、 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的適用困境
我國民事訴訟制度雖然深深根植于大陸法系,但一般民事案件采用“高度可能性”的證明程度是低于大陸法系的“內心確信”而又明顯高于英美法系的優勢證據標準的。 由于英美法系中的優勢證據本身程度就遠低于我國的高度蓋然性標準,所以其對特殊事項將證明標準提高不會對當事人造成太大的負擔。而我國民事訴訟一般案件適用的高度可能性與大陸法系的“內心確信”的發現案件真實的內核近似,已屬于較高證明標準,在此基礎之上引入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這樣一種糅合,是否符合我國國情,由此產生實踐中的一系列問題,需要我們引起重視。
(一)與高度可能性的適用混淆
在對特殊事項適用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前,一般案件適用高度可能性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較高的證明標準,很多法官一直將高度可能性作為民事訴訟慣用的證明標準。 對新證明標準,由于其證明程度更高,且立法未將其與高度可能性加以細致區分,故一些法官在對待特殊事實上,一時之間難以轉變,仍適用高度蓋然性的思維,憑感覺、經驗認定,這就使得提高證明標準的規定形同虛設。 再者,在高度可能性之上設置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使之成為最高的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從高度可能性到排除合理懷疑增加的灰色區間難免會帶來法官的恣意裁判。
此外,筆者還發現,受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影響,此前,司法實踐中將高度可能性標準適用為“蓋然性占優”的案例屢見不鮮,即在事實真偽不明時,認定證據占優勢方主張的事實存在,存在將高度可能性降低執行的趨勢。 在此降低執行的語境下,也許對排除合理懷疑的適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之前對特殊事項的折扣執行,以達到對欺詐、脅迫、惡意串通事項的嚴格審查,但就其在學術和司法實踐中帶來的新混亂,仍應予以重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高度可能性尚未完全規范化適用的情形下,貿然加入排除合理懷疑的新證明標準,且官方解釋沒有規定具體的適用細則,這無疑會造成二者的適用混亂。
(二)與刑事訴訟中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界定不清
在初步理解高度可能性的適用時,又引入更高的證明標準,無疑會產生對二者的界定不清。 眾所周知,排除合理懷疑源于英美法系的刑事定罪證明標準,是一項保障被告人基本權利的憲法性要求。 我國首先將該標準適用于刑事訴訟中,要求達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程度。 而以處分權為核心的民事訴訟加入該證明標準,其證明程度是否與刑事訴訟一致,或者說能夠否借鑒刑事訴訟法中排除合理懷疑的內涵,筆者認為,基于兩大訴訟法不同的價值追求,二者不應相同。 刑事訴訟基于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價值目標,為避免嚴苛的刑罰被濫用,故設定最高的證明標準以加大檢控方的舉證難度,從而平衡控辯雙方不平等的訴訟地位,起到控權的效果。 而民事訴訟基于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核心,更注重解決糾紛以及當事人權益的平等,以此達到公正效率的裁判結果。 雙方當事人處于平等的對抗地位,所以不存在要將法律的砝碼向誰傾斜的情況。 因此,將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適用于民事訴訟難免造成兩種證明標準的適用混淆。
(三)實體法上的適用困境
注釋書中指出,排除合理懷疑標準適應了實體法中的相關規則,“欺詐、脅迫和惡意串通的事實,在實體法立法上使用‘足以"‘顯失公平"的表述,反映立法者對此類特殊事實拔高證明標準的意圖”。 該觀點筆者認為值得商榷。 霍海紅教授指出,此處并非證據法上“如何證明事實”的問題,而是實體法上“如何解釋規則”的問題。 至于當事人如何通過證據證明或使法官做出這種判斷或解釋,則是另一個問題。 在民事實體法上并未有直接規定的情況下,程序法進而加以規定,可能會造成實體法上的適用困境。 由于欺詐、脅迫、惡意串通的事由在實體法上規定了具體的構成要件,符合構成要件方能產生合同關系變動的法律后果,無疑是鼓勵誠實信用的社會風氣,杜絕這系列事項的發生,而提高這系列事項的若再加之甚高的證明標準,使得證明主體很難舉證成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實體法上的法律效果實現,不利于實體與程序之契合。
(四)加大權利主張者的舉證困難
眾所周知,證明標準越高,真偽不明的概率越大,民事訴訟中采用過高的證明標準,有損案件的公正裁判與審理。 如前文所述,即便是適用高度可能證明標準,對五類特殊事項的證明在實踐中尚存在難度,更不用說要達到比高度可能性要求更高的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實踐中,欺詐、脅迫、惡意串通的事項通常以口頭形式做出意思表示,被害人難以收集證據,這是最直觀的問題。 而口頭遺囑規定了必須在緊急情況下行使,且擁有兩個及以上無利害關系的見證人。 在被繼承人生命垂危時找到與其毫無利害關系的見證者本就不易,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更是難上加難。 這使得原本能夠認定的事實舉證困難大大提高而無法認定,一方面阻礙了對受害人的有效救濟,另一方面也可能助長欺詐、脅迫、惡意串通等行為的實施,成為一些不良行為的“法律保護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既有的平衡,很難說這與當初維護民商事交易安全穩定的立法目的不是背道而馳。
(五)法官的適用困境
在提高證明標準的語境下,如何發揮法官的自由心證,“排除合理懷疑”何為合理懷疑? 法律缺乏細致規定,以至于排除合理懷疑在民事訴訟中的界定尚處于模糊狀態,且法官自由心證帶有主觀局限,司法實踐中存在不確定性,可能導致同類型的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出現參差不齊的情況。 筆者在裁判文書網高級檢索中檢索“民事案件”及“判決結果中含排除合理懷疑”字樣的,總共檢索出10 余篇判決,其中能夠達到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只有2 例,發現多以“提供的證據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或不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主張事實被法院不予采納。 筆者發現,實踐中法官對五類特殊事項的認定多呈保守狀態,裁判結果存在否定化的傾向,以及相關裁判就未能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說理部分較為薄弱,未從證據、事實、適用法律、自由裁量四個方面進行充分說理。 筆者認為,這在一定程序上侵犯了雙方的訴訟權益,加強法官在裁判文書中的說理義務對規范化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至關重要,法官的自由心證是一個內化過程,當事人無法明確感知,只有通過法官的釋明以及裁判文書的說理部分予以表現。 尤其對特殊事項的認定,在極高證明標準的適用下,更要強化對法官心證的公開,這不僅僅是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也是對法官自由心證的一種監督和約束。
綜上所述,基于排除合理懷疑的抽象性特征,從法律解釋上進行指導和規范顯得尤為重要。 加強其本土化適用,必須深入其所存背景,不能脫離我國司法現實,從立法和司法上同時進行,尋找破解困境的具體方案。
四、 適用設想與完善建議
完善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的適用,從字面上下定義顯然無法滿足當下司法實踐的需求,所以不應局限于立法層面的修改,更要重視在執行環節的具體操作。
(一)明確該證明標準處于何種層次
首先,將其與刑事訴訟證明標準進行區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內涵,即“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有學者指出,排除合理懷疑在刑事訴訟中并非直接作為證明標準而存在,它是“證據確實充分的具體衡量標準”,二者共同構成我國刑事訴訟有罪認定的證明標準。 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對排除合理懷疑的概念進行定義,闡釋其具體內涵,此舉對其適用有指導性意義。
其次,將其與高度可能性進行界定。 只有法律規定的特殊事項才能提高證明標準,對一般的民商事案件仍應適用高度可能性證明標準,不能任意提高證明標準。 對特殊事項的審理,可以在達到高度可能性的基礎上,進而綜合全案的證據事實驗證是否存在不符合邏輯經驗的疑點。 若現有證據的證明未達到高度可能性,則法官也無須再向主張者提出合理懷疑。
(二)頒布相關民事指導案例
頒布相關指導案例對民事訴訟中特殊事項的證明標準適用予以規范。 民事指導案例對司法實現的操作具有現實性意義,但從近年來頒布的指導案例來看,對指導民事訴訟中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規范化適用的案例較少。 鑒于五類特殊事項近年來頻發,筆者認為,歸納實踐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件進行解讀,頒布指導性案例對排除合理懷疑的適用進行類型化解析以明確具體的操作過程,是很有必要的。該舉措有利于彌補排除合理懷疑適用的司法局限性,使得法官處理類似案件時,在同類法律適用和事實認定問題上能夠有所參考,一方面能夠打破一些法官對排除合理懷疑的模糊理解,抑制實踐中將排除合理懷疑標準折扣執行為高度可能性標準的行為;另一方面也為法官說理提供了素材,法官可以通過借鑒指導案例的說理來進行裁判文書中的說理論證,以此落實排除合理懷疑在民事訴訟中的規范適用。
(三)強化裁判文書中法官說理義務
強化法官在裁判文書中的說理義務,加強對法官自由心證的公開。 證明標準的提高,要求法官以更加審慎的態度對待涉及特殊事項的案件,在綜合有關事實、審查相關證據后,法官若認為原告所提主張的事實未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應在裁判說理部分進行詳細解釋,而非一筆帶過,對主要事實的存疑或是間接證據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的懷疑,應進行詳細說理和論證,防止法官裁量權的濫用。 讓當事人了解法官自由心證的過程,增加對判決結果的接受性,減少案件上訴的可能性,從而提高民事司法的效率。
為了將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落到實處,筆者認為對五類特殊事項的裁判文書說理部分宜從證據、事實、適用法律以及法官裁量四個方面規范化詳盡。 首先,對證據部分,證據是裁判正當性的基礎,對已采納的證據應充分說明采納理由;其次,對事實部分,筆者認為,對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可以結合相關證據倒推該事實,重點說明法官形成“內心確信”的理由,未達到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應綜合全案事實證據倒推,若存在合理疑點的,應重點解釋該疑點在何處以及無法排除疑點的理由;最后,結合本案的證據以及事實,對法律的適用,應列舉具體法條說明法理,對五類特殊事項的審理,應在判決說理部分明確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九條,以杜絕實踐中存在將高度可能性標準錯用于特殊事項的情形。
(四)細化現有實體法規則
筆者認為,構建層次化的證明標準體系,對一些特殊事項提高證明標準并非不可行,重點在如何強化其可操作性。 針對特定的案件情形細化實體法規則,而不是一味地提高或者降低證明標準其實更符合我國國情。 欺詐、脅迫、惡意串通的事項在實體法上規定了明確的構成要素。 以欺詐為例,一是欺詐的故意;二是欺詐的行為;三是被欺詐人因欺詐而產生錯誤認識;四是被欺詐人因錯誤而為意思表示。在司法實踐中,承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可以根據這些構成要件搜集證據,加以證明,達到相應的證明標準即可,一旦對方當事人提出一個合理懷疑的事實,使待證事實處在真偽不明的狀況時,則可認定待證事實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而在消費欺詐、脅迫的案件中,由于消費者與經營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出于對消費者利益的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對實施欺詐的經營者采取懲罰性賠償的制裁。 對消費者主張的欺詐宜采取更低的證明標準為妥,可以采用事實推定或者表見證明的方式減輕消費者的舉證負擔。 此時倘若機械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消費者將難維權,此舉會使得保護消費者的立法目的落空。 而在涉及欺詐、脅迫等特殊事實的身份訴訟中,采取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并非不可行。 在當前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前提下,一些證據搜集可以通過科技鑒定來實現,可以說大大減輕了舉證人的舉證負擔,因而對這些鑒定報告等可以采用較高的證明標準。
對口頭遺囑,《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了“危急情況下”“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有見證能力的見證人”的適用條件。 但在實際生活中卻難以同時滿足。 筆者認為,將證明標準提高對繼承人可期待利益和被繼承人的財產利益平衡所做出的取舍,看似維護了被繼承人的財產權益,實則打破了法律關系的穩定性。 有學者指出,僅憑借抽象的高證明標準而忽略客觀載體或形式要求,將使得法官不敢認定口頭遺囑的事實。 所以對口頭遺囑或者贈予的事項,筆者認為宜細化實體法的證據規則而非一味提高證明標準,就主張的事實仍需考慮各地的風俗習慣,充分發揮法官的主觀能動性,不能一概而論。 嚴格把握高度蓋然性標準才能破除證明標準適用混亂的現象。
五、 結語
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民事訴訟法適用至今,依舊存在現實的適用困境。 為了加強其在我國的本土化適用,首先在立法上要明確其所處層次;其次要加強司法實踐中的可操作性,頒布有關民事指導案例進一步打消法官的適用疑慮,強化法官在裁判文書的說理義務,在一定程度上將法官自由心證的過程外化,規范法官裁判路徑;最后要細化實體法規則,強化對特殊事項的實際操作,實現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規范化適用,從而構建合理的以及多層次、多元化的證明標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