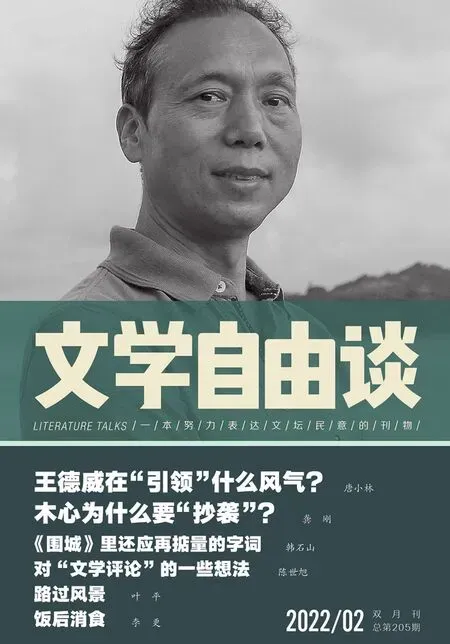短章一束
2022-11-10 21:00:27郭建勛
文學自由談
2022年2期
□郭建勛
一只貓的誄
有一年,我寫過一個《賦得貓》,扯到西方關于貓是邪靈的傳說。自以為寫得好。這是作家的通病,總以為自己寫的最好,別人的是狗屎。就得這樣,沒這么點自我激勵,這作還沒法兒寫。那么個苦差事。
過了些年,到今天重讀《賦得貓》,我卻覺得沒什么好,但也沒什么不好。過去的文章就像過往的人和事,好不好,都在那里。知道這一點并非易事。
寫文章,原本是記錄,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事,或那點兒心情,如此而已。好不好,皆是附麗。
一切沒那么重要,如一只死去的貓。
我說死去的貓是有天晚上散步時碰到的。那是一只小貓,在草叢里,很絕望地呼號,聲音卻大得像頭牛。一只很小很小的貓,估計出生也就半個月的樣子,一掌可握。是這樣的,它在我的掌中蜷伏而憩,鼻息均勻。
我動了惻隱之心。好像也不是動了惻隱之心,覺得不救它,它就死了。——其實,就是動了惻隱之心。
我帶回來了,還買了瓶純牛奶給它喝。我平時很少喝純牛奶。可見我真動了惻隱之心。發現自己這一點還是有點小殘酷的,有些人有些事我均視之如煙云,卻會對只貓動惻隱之心。
這似乎是我們,不,是我的病。
我把貓放在工作室,還囑咐保安,請他給貓喂奶。保安很愿意的樣子。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對我很客氣。我走了幾步又回過頭,看見他蹲下去服侍小貓。天地一片惻隱,像彌漫著郁金香。
回家的路上,我還想,把它喂大,在以后的日子里,也許是個伴,可以放到車上,哪去跟哪。……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