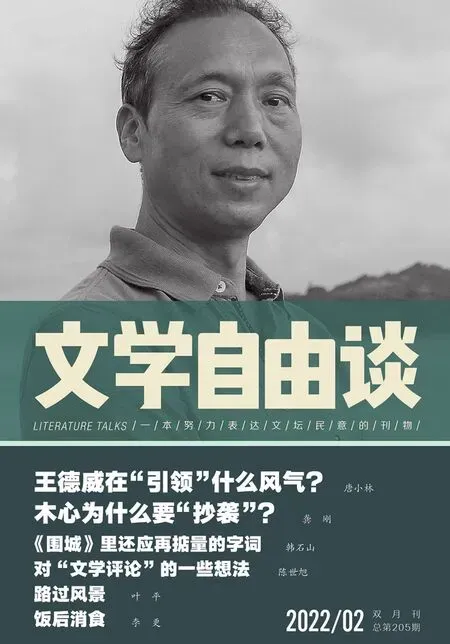理論的遮蔽和有限
2022-11-10 21:00:27楊光祖
文學自由談
2022年2期
關鍵詞:理論
□楊光祖
劉東主編的兩套叢書——“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和“人文與社會譯叢”影響巨大。我也買了其中的很多冊,啟我甚多。但劉東本人似乎不擅著述,買了他的近十冊著作,除了不斷自我印證,確實沒有說出多少讓我有興趣的東西。不過,他關于理論的一段話,我倒比較認可。他在《用書鋪成的路》中說:“當今的學者差不多都不信宗教而改信理論了,各個理論群落,其內部的以沫相濡和對外的同仇敵愾,幾乎構成了二十世紀整個學術史的縮影。”這點確是點中了學界要害。所以他說:“在這種情況下,我更主張注重心智而不是理論。不是說不喜歡理論,但要用理論去開拓心智,而不是把理論本身弄成了目的。尤其是現在大多數理論都托生于或總結于歐洲經驗,憑什么就它們中總有一款適合我們自己呢?”
近年來,我參加一些當代文學會議,總有一些時髦的學者,振振有詞地談后現代、后人類、后全球之類,還有一些自己也“原創”了自以為不凡的理論,在會上大講特講,顧盼自雄,不可一世。但所舉作品卻上不得臺面,也就明白他連基本的藝術鑒賞水平都沒有。
猶記有一次會議,我略講了一點私見,就是所有的理論,都必須化作自己的慧眼,成為自己的血肉。文藝批評靠的還是審美直覺,不是生搬硬套所謂理論。結果,惹得一位理論家反駁起來,說我講的都是常識,他們搞理論的不是不會批評,是瞧不起當代文學,沒有必要出手云云。我聽了也就一笑,覺得他太敏感,也太脆弱。……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當代陜西(2022年5期)2022-04-19 12:10:18
新世紀智能(數學備考)(2021年9期)2021-11-24 01:14:28
湘潮(上半月)(2021年4期)2021-07-20 08:05:28
汕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年4期)2020-12-14 07:05:00
讀與寫·教育教學版(2017年10期)2017-11-10 22:28:57
大電機技術(2017年3期)2017-06-05 09:36:02
區域經濟評論(2016年2期)2016-05-17 05:06:43
學習月刊(2015年21期)2015-07-11 01:51:44
社會生活探索(2013年0期)2013-10-24 03:44:40
阜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1期)2013-08-21 12:4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