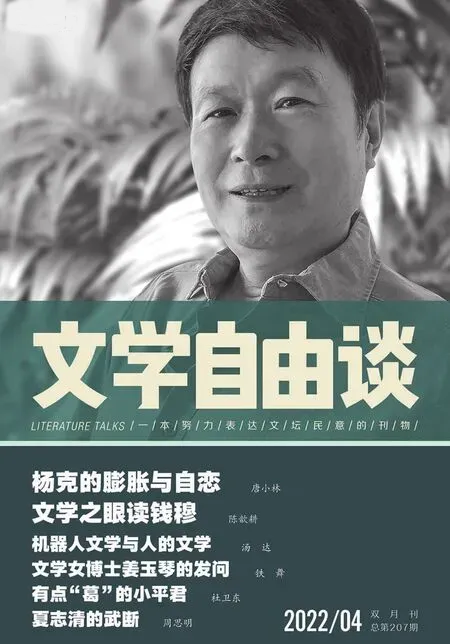一地雞毛
□朱孝兵
1.重復(fù)
不管多牛的作家,看看其自選集,就知道有幾斤幾兩了。
許多作家的自選集,看一篇代表作,讓人眼前一亮,尤其讓某些詞語鮮活起來的創(chuàng)造性表達(dá)或某種比喻通感類的修辭,一下就寫到人心坎兒去了,讓人不由得“拍案而起”,擊節(jié)而贊,閱讀的快感指數(shù)飆升。但是,再翻一翻其他篇什,就會感到失望——這個詞語,那個修辭,甚至某個細(xì)節(jié),又毫無二致地出現(xiàn)了;不單是語言,甚至某些小說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套路,都讓人感覺是在重復(fù)自己。這就讓人感到非常婉惜。
寫作方面的創(chuàng)造,不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作家重復(fù)自己,不是江郎才盡,就是對藝術(shù)性創(chuàng)造存在誤解。
也許,這就是“藝”跟“技”的區(qū)別:即便是王羲之,也創(chuàng)作不了第二幅《蘭亭序》;而庖丁切割第一萬零一頭牛,仍然是手起刀落,游刃有余。
2.郵票與文學(xué)
自從福克納將郵票與其家鄉(xiāng)聯(lián)系起來之后,我們許多作家都將之照搬過來,把這枚“郵票”貼在自己家鄉(xiāng)的大地上,強(qiáng)調(diào)自己作品的地域性。甚至有些作家還說,相比起福克納的家鄉(xiāng)奧克斯福,他的家鄉(xiāng)“比郵票還小”。
我想,我們可能太習(xí)慣去沾光,而沒有想明白人家為什么會發(fā)光。
威廉·福克納的那句話是這樣說的:“我的像郵票那樣大小的故鄉(xiāng)是值得好好描寫的,而且,即使寫一輩子,我也寫不盡那里的人和事。”他為什么用了“郵票”這個喻體,而沒說“火柴盒大小的故鄉(xiāng)”“硬幣大小的故鄉(xiāng)”“芝麻粒大小的故鄉(xiāng)”等等?是的,這樣一比較,我們才恍然大悟:郵票意同信函,它代表了情感與思想的交流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