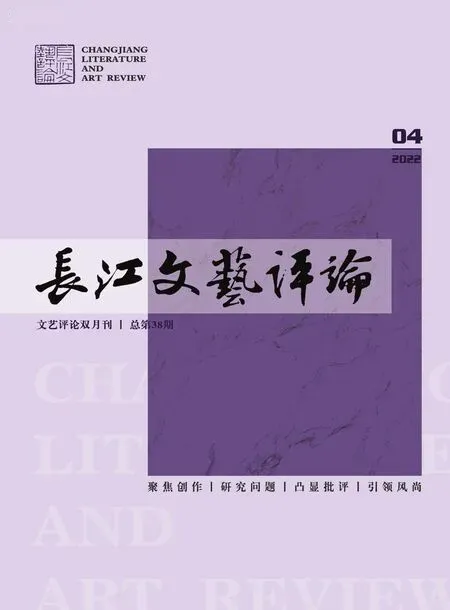中國城市文學研究的新拓展
——讀李洪華《20世紀中國作家的都市體驗與文學想象》
◆張 檸
城市古已有之,而且歷史悠久綿長。城市文學,則是晚近的事。中世紀歷史學家在描述“城市文學”的時候,用了“fabliaux”(粗俗幽默故事詩)這個詞,并解釋說是“充滿活力、純樸幽默且篇幅短小的諷刺詩”。中國翻譯家王佐良,將它譯為“中古歐洲大陸市井故事”。俄羅斯理論家M·巴赫金認為,直到中世紀中后期(13世紀前后),城市才具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性”,“城市獲得發展,并且在城市里形成了自己的文學。”M·巴赫金所說的“Фабльо”(fabliaux,故事短詩),就是新興的“城市文學”的代表,它以滑稽、諷刺、戲仿的方式“對付一切陋習和虛偽”。城市文學的主角,就是中世紀城市底層文學中三個最重要的角色類型:“傻瓜”“小丑”“騙子”。這種說法有些極端,其實就是“普通市民”的意思。這些普通市民的活動背景,不再是宮廷和城堡要塞,不再是鄉村和田野山川,更不是教堂和墓地,而是集市、街道、廣場、劇場、工場、居室。這些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民群眾,甚至比普通的人還要“低”一點,屬于加拿大文論家弗萊所說的“低模仿人物”和“諷刺性人物”。弗萊指出,是城市的市民新文化,把“低模仿人物”引進了文學,使得歐洲虛構文學的重心不斷下移(從神移向英雄和首領,再移向普通的市民),經過文藝復興直到今天,這些人物形象一直主宰著文學。
中國古典城市,按照年鑒學派史學家布羅代爾的分類,屬于“東方型帝王都城”。它帶有“政治城堡”或“軍事要塞”性質,它不是有機發展的“城市”,也沒有“市民階級”這個說法。就局部形態學的特征而言,有些古典小說也不乏“城市文化”特質,比如,反農耕價值,違背封建禮教,商業氣息濃厚,風格艷俗等;也有一定的“城市文學”的屬性,比如沈既濟的《任氏傳》中,就充滿了市民生活的細節和情感。但毫無疑問,這類古典小說中的城市故事,都帶有局部性和偶然性特征。故事的主角與其說是市民,不如說是臣民。借用美國社會學家凡勃侖的術語,古典城市中的臣民,其生活實踐或者故事情節展開,其實是在執行“替代性消費”任務,或者說在從事有限自由性質的“替代性表演”。毫無疑問,這不是城市學家芒福德所說的“身份等級制”向“社會契約制”過渡的現代“自治性城市”。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城市”和“市民階層”,應該是晚清以后的事,相應的“城市文學”應該是“新文化運動”之后的事。
1926年7月21日,魯迅在為俄羅斯詩人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漢譯本所寫的后記中寫道:“從一九〇四年發表了最初的象征詩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稱為現代都會詩人的第一人了。他之為都會詩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詩底幻想的眼,照見都會中的日常生活,將那朦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里,使它蘇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塵囂的市街中,發見詩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長者,是在取卑俗,熱鬧,雜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寫實的詩歌。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
魯迅在道出中國文學中“城市文學”匱乏之實情的同時,精辟地指出了“城市文學”的內在精神和存在真相。“城市文學”的材料是“日常的、庸俗的、喧囂的”“卑俗,熱鬧,雜沓的”,卻要求詩人用“詩底幻想的眼”去觀照,還要將“精氣”吹入那些庸常的日常事象之中,使之“蘇生”出“神秘底寫實的詩歌”。按照魯迅所說的這種要求,有些文學作品實在是不能作為“城市文學”的例證,比如《海上花列傳》,比如“鴛鴦蝴蝶派”作家群,還有一些迎合市民低級趣味的通俗文學。但符合魯迅所說的那種現代城市文學精神的文學實踐,事實上已經開始,除了“魯郭茅巴老曹”和“左聯”作家群之外,與上海這座中國最早的現代大都會相應的“城市文學”,也可以說成績斐然,涌現了大批優秀作家: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曾虛白、張依萍、黑嬰、徐訏、葉靈鳳、張愛玲、蘇青、無名氏等。這些作家,與其說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傳人,不如說是薄伽丘、喬叟、笛福、簡·奧斯汀的傳人。
然而,這種誕生于近現代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學”卻很短命,持續時間只有幾十年,隨即就中斷了。當代文學的“前27年”,“城市文學”逐漸缺席乃至有絕跡的苗頭。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的《我們夫婦之間》《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紅豆》等小說,都是描寫城市生活的,但它們伴隨著對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被改造,《上海的早晨》和《霓虹燈下的哨兵》更是這種改造過程的直接呈現。這種城市經驗、城市感受、城市精神在文學中消失的情形,直至20世紀80年代才約略有改觀。
中國城市演變史的深層,潛藏著一種宿命式的“建城—毀城—建城”歷史循環模式,自商代以來概莫例外。其本質是農耕文化對城邦文化(商業文化)的價值否定,它視“城市”為暫時的手段,“鄉村”為永恒的目的;鄉村農耕生活可以培養美德情操,城市則是一個罪惡與腐敗的淵藪。此種判斷不僅印證于中國古代的城市建造與布局上,也體現在王朝交替時刻的毀城沖動上。管理者對城市不信任,敘述者也將城市妖魔化。顧炎武也認為:“人聚于鄉而治,聚于城而亂。”“聚于鄉則土地辟,田野治。”“聚于城則徭役繁,獄訟多。”價值觀念左右話語方式,話語方式左右實踐行為。所以才有“建城—毀城—建城”的歷史循環,同時催生著大量魯迅所說的“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
以上是我這些年來對城市文化與城市文學的一些粗淺觀察。2020年上半年,我把這些想法寫成了一篇論文,名字叫《城市的形與神及其書寫傳統》。沒過多久,我收到李洪華的大作《20世紀中國作家的都市體驗與文學想象》電子稿。我被他這一體大慮周的鴻篇巨制震驚了。全書12章近30萬字,從現代作家寫到當代作家,對20世紀中國作家作品中的都市想象之例證如數家珍。在閱讀其作品時,我發現,我們許多觀點不謀而合。譬如在他看來,“都市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象征”,而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型正是與這一社會經濟發展同步進行的“文學的現代化”。又如他對以魯迅、沈從文為代表的鄉土作家在文學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其情感的矛盾與經驗的不適的觀察,即一方面他們將城市看作自身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又在情感上對這一基礎持保留甚或拒絕的態度。在這一點上魯迅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在李洪華的鉤沉中,魯迅晚年定居上海之后,曾多次表露出對北京的眷戀:“北平并不蕭條,倒好,因為我也視它如故鄉的,有時感情比真的故鄉還要好,還要留戀,因為那里有許多使我記念的經歷存留著。”可這終究是回憶中北京給他的感受,初到北京時的觀感即截然相反:“途中彌見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覽。”此種反差,正如他在《朝花夕拾·小引》里所言:“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這種無論到哪里都感到不適的經驗,非獨魯迅一人所有,沈從文大概也是這樣,舉凡這些,在作者的這部書里都有深刻的剖析。不過,李洪華并未將這種“不適”的觀察局限在作家自傳的意義上,而是將它上升到了文學現代化過程中作家轉型的艱難一點。這種描述,我以為既是一種事實判斷,也隱在地包含了某種價值判斷,亦即作者對社會現代化與文學現代化的雙重肯定。正是在這一價值導向下,李洪華從現代都市與現代文學的關聯性、鄉土作家的轉型問題、新興都市作家的寫作方式、政治視角與現代主義視閾內的城市文學等幾個方面,論述了20世紀中國城市文學發生與發展期間的諸多問題。
李洪華這部專著分為兩大部分,《導言》與第一章《都市文化表征與現代文學生成》是全書的“綱”,從第二章到第十二章為全書的“目”。“綱”是立論,為“目”中所及的作家打下了一種方法論的基礎,“目”則是立論的延伸與具體,涉及的作家既有魯迅、老舍、張愛玲、沈從文、茅盾、徐訏及新感覺派、象征派、現代詩派與九葉派等諸多現代作家,也涵蓋了“新時期”以來的一些成就卓著的作家,如王安憶、馮驥才、池莉、陸文夫、范小青、蘇童、葉兆言、賈平凹、葉廣芩和王朔。這一部分不是簡單的作家論,其論述也根據時間與對象做出了富有新意的安排,如討論魯迅、老舍、張愛玲時,作者是揀選了在他們生命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城市加以論述,對沈從文、茅盾則是從其“鄉下人”的視角與不同的政治取向加以分析的。至于新感覺派、象征派、九葉派這些帶有現代主義或者“純文學”色彩的文學流派,作者主要關心的是這些城市文學的發生學問題。
總的來看,我以為這部著作主要有三大優點,即立論價值的明晰、兼容并蓄的擇取、細致入微的分析。我有理由相信,李洪華的這部關于“城市文學”的專著,是中國城市文學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優秀成果,它將為中國城市文學研究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