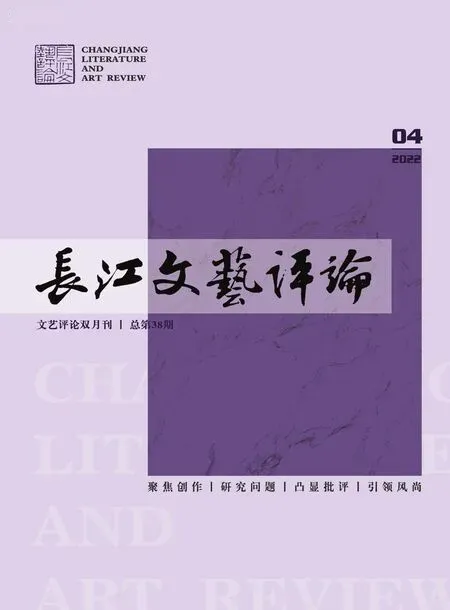藝術(shù)家為何瘋狂?
——關于藝術(shù)自律論的學術(shù)對話
◆馮黎明 姚思宇
塞爾維亞藝術(shù)家格拉迪米爾·斯穆賈、伊萬娜·斯穆賈父女編寫了一套很特別的西方藝術(shù)史,叫做《瘋狂藝術(shù)史》,這部書以漫畫的形式講述了歷史上那些著名的藝術(shù)家們的“瘋狂”故事。對于學界的思想者來說,藝術(shù)家的瘋狂當然好玩,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藝術(shù)家們的瘋狂乃是近代以來的“藝術(shù)自律論”的一個最為重要的表征,其中潛藏著深刻的思想意蘊和歷史內(nèi)涵。這些故事把所謂“藝術(shù)是一種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的事物”的普遍觀念演繹得淋漓盡致,大大地強化了人們關于藝術(shù)自律性的信念。最近十余年以來,馮黎明先生對“藝術(shù)自律”問題作出了大量的研究,這些研究分別涉及藝術(shù)自律論的意涵、藝術(shù)自律論生成的機制、藝術(shù)自律論演變的歷史、藝術(shù)自律論在當代審美文化場域中的影響,等等。一般說來,現(xiàn)代藝術(shù)理論界大都認可藝術(shù)自律論是審美現(xiàn)代性的啟動機制,是現(xiàn)代藝術(shù)體制建構(gòu)的合法化依據(jù),還是現(xiàn)代藝術(shù)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行動的指導性規(guī)劃。我們甚至可以說,驅(qū)動了從浪漫主義到先鋒主義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史的那臺思想引擎,就是“藝術(shù)自律論”,因此關于藝術(shù)自律論的研究對于理解和評價我們的當代藝術(shù)以至于理解和評價全部現(xiàn)代審美文化,有著一種“指南性”的功能。
在當代藝術(shù)理論界,“藝術(shù)自律論”是一個相對比較“老派”的話題,而您對于這個話題卻持續(xù)地研究了大概有十多年,您在找尋審美現(xiàn)代性的“文化DNA”,您想用關于藝術(shù)自律論的詮釋來解開審美現(xiàn)代性之謎。在您的論說中,自從唯美主義運動到當代藝術(shù)界,藝術(shù)活動、藝術(shù)家、藝術(shù)作品等等都被理所當然地視為一種極其獨特的存在,而我們的藝術(shù)體制、藝術(shù)觀念以及藝術(shù)消費行為都以認定這種“藝術(shù)的獨特性”為必須的前提。在您的論說中,藝術(shù)自律論為現(xiàn)代藝術(shù)體制設置了一道基礎性的啟動程序,那就是所謂“藝術(shù)的個人獨創(chuàng)性”信念。現(xiàn)代藝術(shù)場以“個人獨創(chuàng)性”信念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的“習性”以至于結(jié)構(gòu),比如審美倫理化的職業(yè)生活方式、反同質(zhì)化的意義生產(chǎn)機制,“震驚性”的藝術(shù)品出場方式等等。在閱讀您關于藝術(shù)自律論的文章之前,我對于藝術(shù)的獨特性持一種“無原則”的信任,相信康德的先驗哲學的論斷,即藝術(shù)是天才的活動,而在您的論說中,所謂藝術(shù)的獨特性只不過是我們“選擇性”認可的一種觀念而已,這一觀念不是來自藝術(shù)的“天才性”,而是某種特定的社會歷史事件的結(jié)果。
藝術(shù)自律(Autonomy of Art)這個詞組中的autonomy的本意是“自治”“自主”。“藝術(shù)自律論”是康德以來的近代藝術(shù)哲學對于藝術(shù)在人類社會實踐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中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特質(zhì)的描述。實際上,將藝術(shù)視為一種特殊的存在的觀念早在希臘時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智者們的論述里,比如柏拉圖就把詩人當成一種天生的怪物。羅馬時代的普林尼在《自然史》一書中記載了亞歷山大大帝時代的藝術(shù)家帕拉西烏斯、宙克西斯等人超凡的繪畫技藝。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瓦薩里,就是最早提出“文藝復興”(The renassance)這一術(shù)語的那位學者、建筑家,他在《藝苑名人傳》中把從喬托到米開朗基羅的一大批藝術(shù)家描寫為一群“天縱之才”,也就是后來被布克哈特稱之為“杰出人士”的一群藝術(shù)天才。這些人身上有著一種非凡的情感、觀察力、想象力、表達技藝,他們表現(xiàn)出一種難以理喻的“神秘性”,浪漫主義尤其推崇這種神秘性。西方學界習慣于用“天才”一詞稱呼藝術(shù)家,其原因就在于藝術(shù)家具有世俗理性無法解釋的一種特殊性,康德、叔本華等人都曾經(jīng)把“天才”當作一個學術(shù)問題予以辨析。弗洛伊德雖然不用“天才”概念解釋藝術(shù)家身上迥異于常人的“怪癖”,但是他同樣認可藝術(shù)家跟“俗人”的差異,只不過他將其解釋為早年特殊生活經(jīng)歷的后果,即兒時被壓抑而未得以實現(xiàn)的俄狄浦斯情結(jié)在成年時期通過“白日夢”的方式加以轉(zhuǎn)移性的表達。浪漫主義時代,藝術(shù)家的這種似乎與生俱來的超凡脫俗得到了審美文化界不遺余力的頌揚,藝術(shù)天才們好像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一樣被人們頂禮膜拜。在康德的論說中,“美的藝術(shù)”也就是天才的藝術(shù),它是一種能夠把“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關聯(lián)起來的“形式游戲”,還能夠為人類建構(gòu)一種終極的倫理即審美倫理。就像康德哲學被人們稱為哲學界的哥白尼革命一樣,康德的美學同樣開創(chuàng)了一個“藝術(shù)自律”的時代。康德美學的真意在于為人類設定一個倫理規(guī)劃,這就是“審美倫理”,而唯美主義運動則將這個“審美倫理”投入到藝術(shù)家們的生活實踐。唯美主義者堅決相信藝術(shù)跟世俗的生活世界相互隔絕,或者說藝術(shù)絕對地超越我們的世俗生活世界。所以唯美主義者們故意表現(xiàn)出一種所謂“波西米亞式生活”,他們以“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身體行為表明藝術(shù)在人類社會實踐中具有一種非同凡響的自主性和超然性,因為依照審美倫理生活的藝術(shù)家是不受世俗理性的道德規(guī)約的。唯美主義運動開啟了審美現(xiàn)代性之門,而開啟此門的鑰匙就是那把藝術(shù)和生活世界隔離開來的“藝術(shù)自律論”。
您在《藝術(shù)自律:一個現(xiàn)代性概念的理論旅行》一文中描述了藝術(shù)自律論從文藝復興時代“美的藝術(shù)”概念的初現(xiàn)端倪,到先鋒藝術(shù)時代的“自我指涉”這樣一段歷史。在您的描述中,“美的藝術(shù)”概念的出現(xiàn)是近代藝術(shù)走向“自律性”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據(jù)我的了解,“美的藝術(shù)”這一說法或者類似的說法,最早出現(xiàn)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阿爾貝蒂的《論繪畫》(1436年)一書中。在此之前,藝術(shù)一直被當成一種“手藝”,地位并不高。阿爾貝蒂寫了三本書,即《論繪畫》《論建筑》《論雕刻》,其用意在于提高藝術(shù)的社會地位。在這幾本書中,阿爾貝蒂堅持藝術(shù)再現(xiàn)自然的觀點,但是他認為藝術(shù)要再現(xiàn)的是自然中的“美”而非其他。阿爾貝蒂關于藝術(shù)是對自然中的美的表現(xiàn)的觀點,發(fā)展到啟蒙時代就演變成為了一個明確的口號,即“美的藝術(shù)”。波蘭學者符·塔達基維奇在《六個概念的歷史》(1980年)中認為,“美的藝術(shù)”最早出自于16世紀的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達·赫蘭達。阿爾貝蒂雖然沒有直接使用“美的藝術(shù)”這樣一個術(shù)語,但是他關于藝術(shù)是對于美的表現(xiàn)的說法,表達的其實就是“美的藝術(shù)”的意思。1746年法國學者夏爾·巴托出版《歸結(jié)為同一原理的美的藝術(shù)》,提出用“美的藝術(shù)”(藝術(shù)是對于美的模仿)作為基本概念界定藝術(shù)的普遍規(guī)定性。以審美定義藝術(shù),這里體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讓藝術(shù)得到一個獨立身份的訴求。從希臘到文藝復興,藝術(shù)一直沒有獲得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地位,而自從有了“美的藝術(shù)”這一說法,藝術(shù)就開始走上了所謂“自立門戶”的道路。尤其是在康德從本體論意義上對于藝術(shù)的審美本質(zhì)進行論證之后,藝術(shù)自律論有了一個合法化的依據(jù),于是“美”便成為了現(xiàn)代藝術(shù)把自己從蕓蕓眾生的世俗生活世界“隔離”出來的一件有效的證明文件。在現(xiàn)代審美文化領域里,我們一般認為比如像儀式的藝術(shù)、娛樂的藝術(shù)、政治的藝術(shù)等等都不是真正的藝術(shù),只有“美的藝術(shù)”才是真正的藝術(shù),因為美的藝術(shù)憑借著生產(chǎn)和傳播“美”的特別授權(quán)而獨立于人類的其他社會實踐。不過有些現(xiàn)代理論家對此不以為然,比如理查德·沃林,他評述超現(xiàn)實主義時在彼得·比格爾關于先鋒派的理論之上提出了一個術(shù)語——“非審美化的自主性藝術(shù)”。那么這種藝術(shù)的存在或者出現(xiàn),是不是否定了美的藝術(shù)和藝術(shù)自律之間的邏輯關聯(lián)呢?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既然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自律性源自于“美的藝術(shù)”,那么非審美的自律性藝術(shù)又如何理解呢?比如像本雅明說到的那種“震驚”效應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它似乎并不將審美當作基本功能,但是它又最大限度地彰顯一種“與眾不同”的姿態(tài),這種藝術(shù)的“脫俗”氣質(zhì)跟過去那種以審美性的“靈韻”為表征的自律性藝術(shù)在“與世隔絕”這一點上異質(zhì)同構(gòu)。其實這一現(xiàn)象就說明,藝術(shù)自律并非一種本體論的先驗規(guī)定性,而只是一種社會性或歷史性的選擇。這就是說,現(xiàn)代性工程的展開產(chǎn)生了藝術(shù)自律性的要求,而美的藝術(shù)只是給予了這一要求得以實現(xiàn)的觀念條件而已。倘若沒有美的藝術(shù)充作自律性藝術(shù)的合法化依據(jù),啟蒙時代的人們也會找出一種別的什么說法來為藝術(shù)的自律性加蓋證明圖章的,就像形式主義詩學用“文學性”來為文學設定一個本體論的基石一樣。在我看來,是文藝復興時期市民社會的崛起和蔓延導致了歐洲的審美文化界去尋覓藝術(shù)的獨立自主,只不過他們將這一尋覓的眼光對準了“美”而非其它。這里的原因大概是,藝術(shù)家們在創(chuàng)造美的形式方面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能力,所以藝術(shù)和美的結(jié)合就意味著藝術(shù)家這一社會身份在生活世界里具備了僅僅屬于他們特有的一種稟賦和技能,這對于藝術(shù)家社會身份的自主性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雅克·朗西埃看來,審美并非藝術(shù)的先驗規(guī)定性,美的藝術(shù)只是藝術(shù)史的一個階段。朗西埃把藝術(shù)史區(qū)分為三種“辨識體制”,即“影像/倫理體制”“詩學/再現(xiàn)體制”和“美學體制”。也就是說,美的藝術(shù)是現(xiàn)代藝術(shù)的體制特性而非本體論屬性。阿蘭·巴迪歐的《非美學手冊》(1998年)開篇就宣稱,藝術(shù)是真理的生產(chǎn)者。巴迪歐反對把藝術(shù)限制在美學的范疇之中,主張藝術(shù)有著比美學更大的功能,即一切真理都是在藝術(shù)中生成的。早在海德格爾那里,藝術(shù)就不再受限于所謂“美的藝術(shù)”,海德格爾說藝術(shù)是真理自身的顯現(xiàn)。這些新近的觀點切不可以看作是藝術(shù)自律論的逆轉(zhuǎn),恰恰相反,這些看法乃是藝術(shù)自律論走向了一種激進的境界。如果說康德美學、唯美主義、形式主義、先鋒藝術(shù)、審美批判理論等等以自律論為引擎將藝術(shù)推進至與世隔絕的地步從而導致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自戀”“叛逆”和“傲慢”,那么讓自律性藝術(shù)超越美學而受尊為“創(chuàng)世之神”則是海德格爾、巴迪歐、朗西埃等人對于藝術(shù)自律論的一次加強版升級。阿多諾等人要用自律性藝術(shù)為現(xiàn)代人提供一種普世性的審美倫理,引導全人類進入審美主義的自由世界,而巴迪歐則從自律性藝術(shù)與世俗世界的隔離中將藝術(shù)設定為意義世界的創(chuàng)始之源。當巴迪歐說藝術(shù)是真理的生產(chǎn)者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或許是“美的藝術(shù)”的終結(jié),但同時也看到了藝術(shù)自律論的“強化版”或者“升級版”。
您曾經(jīng)多次講到,相比起美的藝術(shù)如何為自律性藝術(shù)現(xiàn)身江湖型塑身段,更需要我們?nèi)パ芯克伎嫉膯栴}應該是:催生了藝術(shù)自律這一“歷史的必然要求”的那些社會、文化和歷史的條件是什么?我在閱讀現(xiàn)代藝術(shù)史的時候有這樣的感覺:從康德到法蘭克福學派,多數(shù)學者都是在呼吁、主張或者論證藝術(shù)的自律屬性,而在法蘭克福學派之后,對于藝術(shù)自律問題的社會學、歷史學研究占據(jù)了學界的主流地位。1968年的新左派文化運動失敗后,西方思想文化界發(fā)生了一場社會學轉(zhuǎn)向,即社會學的田野考察、結(jié)構(gòu)分析和歷史主義逐漸成為人文學術(shù)的知識學依據(jù)和思想資源,比如哈貝馬斯的轉(zhuǎn)型就是一個典型。康德用無功利性、形式游戲、天才等等論證了藝術(shù)跟純粹理性、實踐理性的差異從而賦予藝術(shù)以自洽性、自主性,唯美主義從自律性藝術(shù)中找到了藝術(shù)家的職業(yè)倫理即審美倫理并且將其投之于一種生活實踐,形式主義藝術(shù)哲學在康德的形式游戲概念的基礎上論證了藝術(shù)作品的形式自主性,審美批判理論則將形式自主性和審美倫理結(jié)合制訂了一份具有“解放”和“救贖”功能的審美主義普世價值的規(guī)劃。1968年后,這些建立在自律性藝術(shù)基礎之上的“宣言”走向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彼得·比格爾、布爾迪厄等人從社會學角度對于藝術(shù)自律論的歷史主義考察,即:把藝術(shù)自律論視為一個社會歷史現(xiàn)象辨析其生成、建構(gòu)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歷史語境。彼得·比格爾在《先鋒派理論》(1974年)中圍繞“藝術(shù)體制”概念解釋了藝術(shù)自律與“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關系問題。在比格爾看來,藝術(shù)自律是一個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范疇,它表明了藝術(shù)跟實際生活脫節(jié)的一種藝術(shù)體制的特性。比格爾認為古典時代歐洲藝術(shù)的“供養(yǎng)人體制”的解體是自律論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布爾迪厄?qū)τ诒雀駹柕恼撌龇浅2粷M,在《藝術(shù)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jié)構(gòu)》(1992年)一書中,布爾迪厄用他的“建構(gòu)論”方法對于藝術(shù)自律論在19世紀的形成做了精彩的描述。在布爾迪厄看來,現(xiàn)代藝術(shù)走向自律性是一系列的結(jié)構(gòu)運動的后果,藝術(shù)跟世俗生活世界的區(qū)隔是一種文化資本交換、增值的策略。布爾迪厄反對比格爾那種決定論的解釋,他認為藝術(shù)跟社會的關系絕非簡單的一種“脫節(jié)”,藝術(shù)場是一個復雜的結(jié)構(gòu)體,其中心是所謂“純藝術(shù)”,而其邊沿則是跟商業(yè)世界相關聯(lián)的所謂“非自律性”的商業(yè)藝術(shù)。尼克拉斯·盧曼從“社會系統(tǒng)分化”理論角度論述藝術(shù)的自主性只是一種社會系統(tǒng)功能性分化的現(xiàn)象,藝術(shù)的自主性是系統(tǒng)分化的結(jié)果,它是流動性、功能性的,不能將其處理為一種固化的先驗規(guī)定性。近幾十年來,把藝術(shù)自律論視為一種社會歷史現(xiàn)象給予客觀的考察分析的學理形態(tài)占據(jù)了主要地位,學人們更感興趣的是關于藝術(shù)自律論何以產(chǎn)生、何以延續(xù)的研究。在這一問題上,您在十多年前就做過關于藝術(shù)自律與“市民社會”關系的討論,但是在這一問題上,至少國內(nèi)學界還少見深入研究的成果。
一般說來,現(xiàn)代社會學用“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元對應模型描述我們的社會空間。這個二元對應的結(jié)構(gòu)模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催生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之后逐漸成型。當代學界大都把現(xiàn)代性工程的啟動設定在啟蒙時代,而我認為,啟蒙本身乃是“國家—市民社會”二元結(jié)構(gòu)構(gòu)型的結(jié)果,因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分立、對應、互動等導致了啟蒙運動的展開。就這個話題來說,啟蒙時代出現(xiàn)的兩個現(xiàn)象可以讓我們認識到“藝術(shù)自律”得以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原因:其一是所謂“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建構(gòu)帶來了中產(chǎn)階級文化,其二是所謂“社會實踐場域的結(jié)構(gòu)性分解”帶來了審美文化的自主性。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論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類型》(1962年)中提出,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二元對應產(chǎn)生了一個現(xiàn)代性的社會空間,即所謂“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是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一個“理想類型”化的空間結(jié)構(gòu)體,它在政治領域里建構(gòu)起所謂“公共政治”或者“廣場政治”,而在文化領域里則孕育出一種超越了貴族主義的宮廷文化和底層社會的江湖文化的一種“中產(chǎn)階級文化”。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斯梅爾的《中產(chǎn)階級文化的起源》(1994年)通過分析18世紀英國的“哈利法克斯商業(yè)精英”的文化生活發(fā)現(xiàn),中產(chǎn)階級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所謂“文雅”,這一論說應和了啟蒙時代英國經(jīng)驗主義美學對于“美”的解釋。問題的關鍵在于,由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孕育出來的這種中產(chǎn)階級文化,它需要一種既不同于宮廷趣味的貴族文化又不同于江湖化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的文化形態(tài),這種文化以“脫俗”的姿態(tài)展現(xiàn)了資產(chǎn)階級個人在公共空間中的存在,成為他們社會身份自我確證的敘事文本。由此我們就看到了自律性藝術(shù)在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里如何孕育成型并得到普遍認可的機制。進而在197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多數(shù)學者都把藝術(shù)自律視為一個“市民社會的范疇”,1972年德國祖爾坎普出版社(Suhr Kamp)出版過一部《藝術(shù)自律:一個市民社會范疇的形成與批判》。我們再來看現(xiàn)代性工程如何在“人類社會實踐場域的結(jié)構(gòu)性分解”的意義上造就了自律性藝術(shù)的出場。幾年前,我?guī)е鴰孜磺嗄杲處熀筒┦可黄鹱隽艘黄P于純粹現(xiàn)代性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把現(xiàn)代性定義為“人類社會實踐場域的結(jié)構(gòu)性分解”,報告認為以分工為啟動機制的社會系統(tǒng)分化運動將社會實踐界分為諸多相互區(qū)隔的“場域”,其中每一個場域都必須要具有自洽性和自主性的存在依據(jù),必須論證其開展社會行動的合法性,必須“自立門戶”“自謀生路”,否則現(xiàn)代性就會在生活世界的“戶籍名錄”中刪除其名稱。“上帝死了”,這意味著古典時代那個為眾生賦予意義和價值的同一性秩序消解了,“人為自己立法”,藝術(shù)也必須走出從屬于一元論和決定論的“神性”或“德性”的技藝形態(tài),去找尋或自證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身份。對此“歷史的必然要求”心知肚明的啟蒙思想家們跟浪漫主義文藝一道提出“美的藝術(shù)”“天才”“個人獨創(chuàng)性”“絕對音樂”等等口號,意在為藝術(shù)進入現(xiàn)代生活世界提供自主性和獨立性存在的依據(jù),康德美學關于藝術(shù)的本體論論證就是這一思想訴求的巔峰表現(xiàn)。哈貝馬斯把“自律性的藝術(shù)”列為現(xiàn)代性工程的三大項目之一,其原因就在于他深信藝術(shù)自律和現(xiàn)代性工程之間的共生關系。
藝術(shù)自律的哲學論證起于康德,然后在19世紀分別沿著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兩條路線演進,前者把“審美倫理”付之于生活實踐從而為藝術(shù)這一職業(yè)提供了倫理依據(jù),后者則探索一種“形式自主性”的藝術(shù)作品從而為藝術(shù)品的“非世俗化”存在提供價值坐標。經(jīng)歷了19世紀“雙線并行”的發(fā)展,藝術(shù)自律論形成了兩個堅實的基礎,即審美倫理和形式主義。進入20世紀以后,批判理論與先鋒藝術(shù)繼續(xù)在審美倫理和形式主義這兩條路徑上前行。法蘭克福學派將審美倫理從唯美主義的“藝術(shù)家生活倫理”擴展提升為普遍倫理,認為審美化生存是深陷現(xiàn)代性之隱憂的人類獲得自由解放的唯一方式,好像我們只要依循著自律性藝術(shù)所表達的那種倫理理想生活就可以得到終極的救贖。與批判理論的審美救世方案相比較,先鋒藝術(shù)似乎更加青睞于形式自主性帶來的游戲性自由。“純粹造型”“無物象繪畫”“自我指涉”等先鋒主義的主張,引導現(xiàn)代藝術(shù)日益走向一種“放縱”或者“迷狂”式的形式游戲,這種形式游戲使得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通過藝術(shù)活動完成了對世俗世界的抵抗或者逃逸。您把康德之前的藝術(shù)觀念史稱作自律性藝術(shù)的“史前史”,這就是說,自康德美學起,藝術(shù)自律論進入了“合法化”“自覺化”的進程。《判斷力批判》和黑格爾的《美學》相比,似乎前者對于藝術(shù)問題的論述遠不及后者系統(tǒng)、細致,但是正如您所言,黑格爾美學像是古典美學的總結(jié)而康德美學則更像是現(xiàn)代美學的打開。康德美學的重要意義不在于對具體的藝術(shù)問題的詮釋,而在于通過判斷力的分析建立了一條借道自主性藝術(shù)而達成審美倫理的路線。唯美主義運動的口號“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致力于把藝術(shù)從“他律”狀態(tài)下解放出來,讓藝術(shù)本身成為目的。這樣一來,審美就不僅是一種“感性的完滿”,而且是一種有價值的人生狀態(tài)。唯美主義者“傲慢”且“自戀”地把審美設置為藝術(shù)家職業(yè)的倫理定性,他們陶醉于“波西米亞式生活”之中,視蕓蕓眾生為村夫俗子。亨利·穆爾熱(Henry Murger)的小說《波西米亞人的生活剪影》(1851年)以及普契尼以之為藍本改編的歌劇,至今還很有影響,其中幾位青年藝術(shù)家放蕩不羈的生活故事,以所謂“審美主義人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19世紀中后期興起的形式主義藝術(shù)理論當然沒有唯美主義運動那種轟轟烈烈的氣度,比如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希爾德布蘭特的造型理論、瓦雷里的“純詩論”、羅杰·弗萊的“純形式”等等,都是在各自的領域里展現(xiàn)出一種“形式自主性”或者“形式本體論”的主張,但是這些“書齋化”的理論卻為理解和評價藝術(shù)品的構(gòu)成、意義和功能提供了一套“自律性”的理論系統(tǒng)。19世紀的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把康德的藝術(shù)哲學轉(zhuǎn)化成為了藝術(shù)自律論的兩道打開程序,即審美倫理和形式本體。到20世紀的批判理論和先鋒藝術(shù),審美倫理變成了普遍倫理、終極倫理,而形式本體則推進至形式自由。
你對于康德以后藝術(shù)自律論的演變的描述非常清晰。我覺得19世紀是一段極為重要的歷史,這段歷史制造了兩個東西讓自律性藝術(shù)直接出現(xiàn)在文化廣場的前臺,其一是“美學人”,其二是“純粹造型”。威廉·岡特在《美的歷險》(1945年)一書的結(jié)語中說,“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運動的后果就是一種新人類的生成,這就是所謂“美學人”。“美學人”過著藝術(shù)化的日子,他們把自己的生活處理成為一場“形式游戲”,所以他們超越了現(xiàn)實世界的道德規(guī)約,無拘無束甚至放浪形骸。“美學人”在批判理論筆下是一位救世之神,在20世紀的新左派文化運動中是令人向往的自由人,在先鋒藝術(shù)中是叛逆的革命者……連福柯都說他最心儀的生命狀態(tài)就是美學化的生活。沃爾夫?qū)ろf爾施在《重構(gòu)美學》(1997年)中引用盧克·費里的《人類美學》描述“審美化”浪潮中主體生命形式變成了所謂“美學人”,這讓我們看到,當初由“逃離現(xiàn)實”的自律性藝術(shù)制造出來的這個“美學人”,現(xiàn)在似乎要走出象牙塔回到現(xiàn)實世界了。如果說自律性藝術(shù)通過唯美主義運動制造了“美學人”,從而啟動了先鋒藝術(shù)的“叛逆美學”和“逃逸美學”,那么形式主義藝術(shù)理論則通過抽象藝術(shù)擬訂出“純粹造型”的藝術(shù)生產(chǎn)原理,從而把藝術(shù)徹底地變成了形式游戲的主體即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世之作。格林伯格認為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就是形式主義的勝利,而阿多諾則將先鋒藝術(shù)的“新異性形式”和審美倫理關聯(lián)起來,給自律性藝術(shù)輸入了“救贖”的功能性編程。20世紀的批判理論和先鋒藝術(shù),是藝術(shù)自律論全面接管了審美文化場的領導權(quán)之后實施的兩道治理程序,這兩道程序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現(xiàn)代藝術(shù)體制的立法依據(jù)也必須由此兩道程序發(fā)出命令。在我看來,批判理論和先鋒藝術(shù)是審美現(xiàn)代性的典范形態(tài),也是藝術(shù)自律論的歷史歸宿,它們分別在理論和藝術(shù)實踐兩種活動中將藝術(shù)自律論營造的那些“理想類型”釋放了出來,比如“審美倫理”“形式游戲”“美學人”“純粹造型”等等。
我有些困惑的是,波普藝術(shù)登場之后,現(xiàn)代藝術(shù)場的走向跟藝術(shù)的自律性似乎有些不相契合。西班牙學者加塞特早在1925年就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藝術(shù)中出現(xiàn)了一種“非人化”的傾向,這一傾向讓“物”自我出場,盡可能地遮蔽人的情感、觀念等。到20世紀中期,也就是波普藝術(shù)、現(xiàn)成品藝術(shù)、觀念藝術(shù)、裝置藝術(shù)、行為藝術(shù)等新奇的藝術(shù)潮流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臺的時代,面對著“平凡物的變形”“人人都是藝術(shù)家”“哲學對藝術(shù)的剝奪”等奇思妙想,藝術(shù)理論界頓時失去了定力,不知道如何才能界定藝術(shù)品的屬性。藝術(shù)自律論的本意是要把藝術(shù)從日常生活經(jīng)驗中隔離出來成為一種“特異性”的存在,這一思想訴求自然會清晰地劃撥出藝術(shù)的存在屬性和存在邊界,因為藝術(shù)自律論要做的就是在藝術(shù)和日常生活物品、日常生活經(jīng)驗之間建造“隔離墻”。但是波普之后的現(xiàn)代藝術(shù)似乎越來越多地釋放出“回歸日常生活”的意思,藝術(shù)好像放棄了自律論賦予的那種自戀和傲慢,跨越“隔離墻”,跟商業(yè)世界握手言歡。面對著這些“新潮藝術(shù)”,自律論還能夠顯現(xiàn)闡釋的有效性嗎?
的確是這樣。20世紀的先鋒藝術(shù)體現(xiàn)出一種典型的“自反性”的特點,它不允許任何現(xiàn)存的東西成為具有規(guī)定性功能的經(jīng)典,所以就有藝術(shù)流派的交替登場各領風騷的現(xiàn)象。要說到對于藝術(shù)自律論的最大挑戰(zhàn),那還是要數(shù)“現(xiàn)成品藝術(shù)”,因為這類所謂“藝術(shù)”意欲解構(gòu)藝術(shù)自律論的核心概念,比如藝術(shù)的個人獨創(chuàng)性、藝術(shù)對于世俗事物的超越等等。從杜尚的《泉》(1917年)到安迪·沃霍爾的《布洛利盒子》(1964年),自戀而且傲慢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好像越來越不拒絕功利主義的商業(yè)世界了。阿瑟·丹托稱這一現(xiàn)象叫做“平凡物的變形”(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他用“藝術(shù)界”概念來解釋所謂“現(xiàn)成品藝術(shù)”。那個時候的理論界被這些古怪的東西嚇壞了,批評家們挖空心思地想出各種各樣的概念術(shù)語來解釋這些東西,比如“語境論”“慣例論”等等,有人干脆聲稱,藝術(shù)行將終結(jié),討論這些新潮現(xiàn)象毫無意義。關于現(xiàn)成品藝術(shù),我在《論“藝術(shù)家生活”》一文中嘗試著做過一個解釋:藝術(shù)自律論的一個重要的后果就是藝術(shù)家身份和生活被提升到了“創(chuàng)世之神”的地位,這一地位使得藝術(shù)家成為了決定事物是否具有藝術(shù)品屬性的“立法者”。杜尚把小便池拿去展覽和沃霍爾把肥皂粉盒子拿去展覽是兩個重要的“藝術(shù)事件”,在其中發(fā)生的“平凡物變形”的實質(zhì)在于“平凡物的變性”,即由日常生活物品“變性”為藝術(shù)品。這場“平凡物變性”事件的啟動機制乃是藝術(shù)家的身份行動,倘若不是由藝術(shù)家來執(zhí)行這場行動,那么平凡物體是不會發(fā)生“變性”的,所以現(xiàn)成品藝術(shù)的“平凡物變形”實際上是具有獨立身份的藝術(shù)家施行的一場“創(chuàng)世”行動,這是一次“藝術(shù)的誕生”事件,從自律性藝術(shù)中獲得了超凡身份的藝術(shù)家執(zhí)行并完成了這一行動。如果換了我們這些凡夫俗子,那么無論我們怎么頓足捶胸呼天搶地,也無法對平凡物體“施法”并引導其“變性”。由此可見,像現(xiàn)成品藝術(shù)這類“非人化”的東西何以具有藝術(shù)屬性的問題,仍然可以在藝術(shù)自律論的理論模型中得到合理的解釋。其實從藝術(shù)家的身份獨立性角度來看,先鋒藝術(shù)幾乎可以視為一場藝術(shù)家的身份政治運動。各種流派的先鋒藝術(shù)背后總是有一個藝術(shù)家的“面孔”在宣示著藝術(shù)行動的“造物”功能,這個藝術(shù)家或者是在創(chuàng)造世間所無的“純粹造型”以之顯示真正的“存在者”,或者是在以放蕩不羈的身體行為表達人性的“應然”狀態(tài),總之先鋒藝術(shù)家是在通過一種“新異性”的行動來確證藝術(shù)家身份的“神圣性”。
您的意思是,平凡物變形一類的“藝術(shù)事件”是藝術(shù)自律論發(fā)展至一種激進狀態(tài)的產(chǎn)物,這種激進化的自律論使得藝術(shù)家職業(yè)以及藝術(shù)家生活甚至藝術(shù)家身體,都“與眾不同”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它們可以“無中生有”地創(chuàng)造“新物種”,或者賦予事物以全新的屬性。這個解釋的視點跟語境論、慣例論等對于現(xiàn)成品藝術(shù)的解釋不一樣,您的著眼點是藝術(shù)家的社會身份在物品的傳播過程中導致了物品性質(zhì)的改變。關于20世紀先鋒藝術(shù),還有一個比較困惑的問題,即:抽象藝術(shù)很明顯屬于一種形式自主性的藝術(shù),但是在抽象藝術(shù)興起不久,歐洲藝術(shù)界就出現(xiàn)了一種所謂“無形式”(也有人稱為“反形式”)的藝術(shù)傾向,比如超現(xiàn)實主義,后來的行動繪畫、現(xiàn)成品、大地藝術(shù)等,都表現(xiàn)出一種拋棄形式的意味,再比如超級寫實,尤其是裝置藝術(shù),根本就不屑于去營造抽象藝術(shù)賴以立本的“新異性形式”,它們似乎跟現(xiàn)代哲學對于主體性形而上學的批判相呼應,極力要“回到物自身”,拒絕現(xiàn)代性的“幾何學理性主義”加之于“物”的秩序化,讓“物”以其最原始的形態(tài)展現(xiàn)出來。這種對于“新異性形式”的揚棄,后來被學界稱之為“無形式”(informe或者formless)的東西,好像是在挑戰(zhàn)自律性藝術(shù)對于形式自主性的主張,但是這類藝術(shù)又構(gòu)成了先鋒藝術(shù)的重要部類。1996年,巴黎蓬皮杜藝術(shù)中心舉辦了一場名為“無形:用戶指南”(Formless:A User’s Guide)的展覽,極大地吸引了學界的關注。這種“無形式”的藝術(shù),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消解了自律性藝術(shù)對于形式自主性的自信。那么,無形式到底是自律性藝術(shù)的極端化,還是自律性藝術(shù)的終結(jié)呢?
這個問題說來就有些復雜了。“形式”這個詞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柏拉圖的“eidos”,另一個是亞里斯多德“四因說”中的“形式因”(forme)。柏拉圖的eidos有“觀看”的意思,后來演變?yōu)閕dea,即“理念”。所以“理念”也可以解讀為“共相”,而這個“共相”乃是形而上學的源頭,它是形而上學尋找超越于個別事物之上的“本質(zhì)”的目的所在。西方知識學從一開始就走上了這條形式化思維的形而上學之路,后來的“形式化知識”“形式化方法”“形式化科學”等等,都是形而上學的結(jié)果,啟蒙時代興起的主體論哲學將古典的宇宙論形而上學改造成為“主體性形而上學”。海德格爾認為現(xiàn)代性的起源就是這個“主體性形而上學”,它給現(xiàn)代世界帶來了“虛無主義”。胡塞爾曾經(jīng)在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的意義上思考“形式本體論”,不過胡塞爾的“形式本體論”屬于本體論的“形式化”,而現(xiàn)代藝術(shù)中的形式本體論則應該理解為藝術(shù)形式的“本體化”。其實在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知識學體制中,胡塞爾討論的那種形式本體論幾乎就可以看作是本質(zhì)主義的先導性思維范式。現(xiàn)代性批判理論中出現(xiàn)過很多對于現(xiàn)代知識的形式化的批評,比如喬治·巴塔耶就認為,宇宙本來是無形式的,類似于蜘蛛或者唾液。先鋒藝術(shù)中還真有人把巴塔耶的看法搬到藝術(shù)活動中來,比如拿一些令人作嘔的物體去展覽。在我看來,像超級寫實藝術(shù)這樣的東西,其實就是在執(zhí)行現(xiàn)代性批判理論對于主體性形而上學“秩序化”物自身的批判性反思,超級寫實主義是一種“回到物自身”的藝術(shù),它要揭去形式化知識加之于存在之上的“幾何學理性主義”面罩,恢復我們原初的“物感”。我們再來說說亞里斯多德四因說中的“形式”。Forme指的是形狀、外觀,對應于所謂“內(nèi)容”,是內(nèi)容的表現(xiàn)方式,內(nèi)容是主體而形式是載體,形式從屬于內(nèi)容。自亞里斯多德到古典主義,西方美學的主體是所謂“規(guī)范美學”,而由比如“三一律”這樣的規(guī)范美學生成了在詩學和藝術(shù)學領域占據(jù)主流地位的“內(nèi)容—形式二元等級秩序”,這一等級秩序一直延續(xù)到黑格爾的“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在內(nèi)容—形式二元等級秩序中,作為“技藝”的藝術(shù)因其在制作炫美“外觀”方面的能力被認定為表達真理的一種手段,雖然只是“手段”但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于是“制作外表形式的手藝”便成為了藝術(shù)家安身立命養(yǎng)家糊口的獨門絕技。“形式”的從屬地位恰當?shù)伢w現(xiàn)了古典時代藝術(shù)的非自律性地位,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樣式主義”藝術(shù)的出現(xiàn)。在樣式主義中,色調(diào)和光影開始嘗試背離物象,這里隱含著“形式獨立”的意思。康德美學在藝術(shù)自律論的前提下將藝術(shù)描述為一種“形式游戲”,從此以后,“形式”便堅決地走上了奔向自由的道路。我把這條道路區(qū)分為三段:第一段是啟蒙時代關于形式本體論的論證,即以形式游戲為藝術(shù)之本質(zhì)屬性,這種論證在康德美學中得以完成。第二段是19世紀中期后出現(xiàn)的形式自主論,集中表現(xiàn)為各種形式主義的藝術(shù)理論或者詩學關于形式的“自我表現(xiàn)”的主張。第三段是抽象藝術(shù)之后形成的形式自由論,這種觀念把形式視作具有“造物”功能的創(chuàng)世之神。就像“語言工具論”在20世紀演化至結(jié)構(gòu)主義的“句法關系”決定語義一樣,先鋒藝術(shù)(尤其是二戰(zhàn)后的先鋒藝術(shù))“放肆地”展現(xiàn)著“形式賦予物以存在性”的信念。當我們想到藝術(shù)家在形式世界中的特權(quán)地位的時候,就可以在“形式自由論”中間看到近代以來藝術(shù)自律論的“狂妄野心”了。
弗里德里克·杰姆遜曾經(jīng)說道,現(xiàn)代主義不是想用藝術(shù)做某一件事情,而是要藝術(shù)做一切事情。他的意思就是您說的自律性藝術(shù)的“自信”和“自戀”讓先鋒藝術(shù)產(chǎn)生了“創(chuàng)世之神”的自我幻覺,由此先鋒藝術(shù)把“形式游戲”特權(quán)提升成為了“造物主”的終極權(quán)力。信奉“純粹造型”的抽象藝術(shù)是要置形式于首要位置從而把藝術(shù)品屬性和意義的確定權(quán)交給形式,而波普之后的先鋒藝術(shù)則是要用絕對自由的形式來制造一個全新的“存在”。“無形式”的后期先鋒藝術(shù),現(xiàn)成品、行動繪畫、超級寫實、裝置等等,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律性藝術(shù)憑借自主性的形式游戲給予“物”以意義性的秩序這一行動的退隱,是“物”和“身體”的“無序化”的原始性呈現(xiàn),但其實這背后潛藏著藝術(shù)家身份的“造物”功能,因為這些無序化的原始之物乃是藝術(shù)家“制造”出來的。讓“物自體”和“原始身體”本然地敞開——這是只有“造物主”才能建立的一樁不世之功!這里可以見出自律性藝術(shù)是怎樣從逃離世界到拯救世界、再到創(chuàng)造世界的“大歷史”。您把先鋒藝術(shù)理解為一場藝術(shù)家的身份政治行動,大概就是想要設定藝術(shù)的自律性這一近代藝術(shù)的啟點、并在此維度上解釋所謂“無形式”現(xiàn)象吧。自律性藝術(shù)把自己從宗教中解放出來,獲得了自由,而這自由最終又把藝術(shù)變成了宗教,把藝術(shù)家變成了上帝。
你的描述很準確也很生動。的確如此,自律性藝術(shù)在形式問題上已經(jīng)走火入魔了,早先的藝術(shù)自律論只是想讓美的形式擺脫非藝術(shù)性的東西的約束,然后獲得了獨立身份的自律性藝術(shù)又要求形式獨占藝術(shù)品屬性和意義的決定權(quán)力,當這一些都拿到手之后,自律性藝術(shù)像一個貪婪的征服者,還想要把全部存在的存在性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于是就有了后期先鋒藝術(shù)的那種頤指氣使的王者風范。其實這里邊我們可以梳理出一份藝術(shù)史演進的模式,我將其稱之為“知世—救世—創(chuàng)世”的模式。從希臘到啟蒙時代的藝術(shù)屬于第一階段,即知世型藝術(shù)的階段。這一階段的藝術(shù)在社會實踐中的位置和功能被規(guī)定為表現(xiàn)真理的手段,即表現(xiàn)那神性和德性宣喻出來的真理的一種工具。這時的藝術(shù)不具備獨立自主的本質(zhì),它只是“手工藝”,但是它畢竟服務于真理的表達,所以藝術(shù)的最高價值仍然在于為“知世”提供美的外觀形式,越是有助于人類的“知世”活動越具有意義,所以“寫實”成為了古典藝術(shù)的最高價值。知世型藝術(shù)發(fā)展到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動搖,因為“美的藝術(shù)”的出現(xiàn)意味著自律性藝術(shù)行將蒞臨人間。文藝復興到啟蒙是知世型藝術(shù)的終結(jié)期,自律性藝術(shù)的登臺開啟了一種新的藝術(shù)范式,即“救世型藝術(shù)”。救世型藝術(shù)高舉自律性的大旗,希圖以審美倫理和形式主義拯救人類世界。從唯美主義到先鋒藝術(shù),從席勒到阿多諾,救世型藝術(shù)以審美現(xiàn)代性對抗啟蒙現(xiàn)代性,用審美倫理和形式游戲展開批判和救贖,開拓出一條通往自由之路。救世型藝術(shù)跟知世型藝術(shù)的最鮮明差異在于,救世型藝術(shù)以“解放敘事”為其特性,而不再把知世性藝術(shù)的那種真理敘事當作藝術(shù)的在世之道。大概自波普藝術(shù)問世起,藝術(shù)史開始向第三階段轉(zhuǎn)型,即“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的階段。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的最大特點在于將藝術(shù)視為一種“造物”行動,而且是一種“無中生有”的造物行動。事實上我們現(xiàn)在正在經(jīng)歷一場由救世型藝術(shù)向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轉(zhuǎn)型的“代際變革”,當前的藝術(shù)越來越失去了救世的熱情,反而是熱衷于設計和制作奇異性的物品,熱衷于激發(fā)人類的“新物感”。關于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我想說的有這樣幾點:第一,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既不像知世型藝術(shù)那樣模仿自然,也不像救世型藝術(shù)那樣放飛情感,只是想象、設計并制作一種能夠給人類提供“新物感”的人造物體,一種帶有“異托邦”內(nèi)涵的、具備某種功能性的器物;第二,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是自律性藝術(shù)的進化結(jié)果,它借助于藝術(shù)“外于世界”以至于“高于世界”的地位而實現(xiàn)“藝術(shù)創(chuàng)世”的偉大理想,因此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呈現(xiàn)”另一方面又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呈現(xiàn)”;第三,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以“造物”為職業(yè)工作內(nèi)容,因此設計在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設計藝術(shù)作為一種“創(chuàng)世”的規(guī)劃,擔任著為“造物”提供智能依據(jù)的任務,因此設計藝術(shù)將會在最近的將來成為最重要的藝術(shù)形態(tài);第四,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跟高新技術(shù)發(fā)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不再像救世型藝術(shù)那樣拒絕技術(shù),而是充分利用高新技術(shù)的“造物”功能實現(xiàn)創(chuàng)世的想象,它跟技術(shù)“合謀”起來“造物”,比如“元宇宙”,其實就是藝術(shù)的想象力和技術(shù)的制造力合謀的結(jié)果,當AI技術(shù)、生物工程技術(shù)、3D打印技術(shù)等被某種超越性的想象力引導“無中生有”地制作出能夠為我們提供“新物感”體驗的物品之時,人類藝術(shù)史就真正進入了“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階段。
您的描述讓我們感到正置身于一個偉大的轉(zhuǎn)型時代,心里充滿對于新藝術(shù)降臨人世間的期待。我感到自從“現(xiàn)成品藝術(shù)”登臺,現(xiàn)代人就執(zhí)著地通過藝術(shù)尋找那種“新物感”,但是這種對于新感覺的體驗可能要在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中才能完整地獲得。同時我也有種想法,即: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并非全部執(zhí)行了藝術(shù)自律的理想,它在一些方面推進了自律性藝術(shù)而在另一些方面卻剪切了自律性藝術(shù),比如您所談到的藝術(shù)與技術(shù)“合謀”就超越了救世型藝術(shù)對技術(shù)的鄙視和拒絕。還有就是,現(xiàn)在初現(xiàn)端倪的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比如許燎原的設計藝術(shù))基本上不再把“藝術(shù)的個人獨創(chuàng)性”和“無功利性”當成絕對價值。事實上,結(jié)構(gòu)語言學的普及就暗示著20世紀的知識界不再像浪漫主義那樣著迷于個人獨創(chuàng)性,后來出現(xiàn)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互文性”理論,更是直接否定了作為個體的作者的意義決定權(quán)。不過自律性藝術(shù)主張的“形式本體論”仍然延續(xù)在現(xiàn)代知識界,結(jié)構(gòu)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都信奉“句法結(jié)構(gòu)決定語義”的觀念。先鋒藝術(shù)中的那種激進的“形式自由”,在設計藝術(shù)中有所收斂,畢竟設計藝術(shù)要充分考慮“物”的生成條件對于形式的限制。另外,救世型藝術(shù)賴以維持其“脫俗”身份的審美無功利性,也受到了諸如舒斯特曼的“生活論美學”的非議。自從波普藝術(shù)開始,藝術(shù)跟商業(yè)世界的關系就越來越曖昧,“審美孤立”或者“審美靜觀”似乎成了一個逐漸遠去的神話。鑒于這些情況,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藝術(shù)自律論視為救世型藝術(shù)這個歷史階段的一種體制性的主流觀念,而進入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的歷史階段則意味著藝術(shù)自律論的終結(jié)?我記得您在《藝術(shù)自律與藝術(shù)終結(jié)》中提出過,所謂“藝術(shù)終結(jié)”,既不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的終結(jié)也不是“哲學對藝術(shù)的剝奪”,而是“自律性藝術(shù)體制的終結(jié)”。自律性藝術(shù)體制在救世型藝術(shù)階段的體制化為創(chuàng)世型藝術(shù)的登臺提供了很多條件,但是它更為重要的歷史功能是終結(jié)了救世型藝術(shù),尤其是終結(jié)了自律性藝術(shù)體制。還有一個問題:您好幾次談到中國近現(xiàn)代藝術(shù)中的自律性缺位,您認為這是多重原因造成的。盡管在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藝術(shù)中可以見出一些自律性的初步表達,但是這些東西很難占據(jù)主流地位。那么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知世—救世—創(chuàng)世”是一種西方藝術(shù)史的演進范式,它并不適合解釋中國藝術(shù)史。
中國藝術(shù)的自律性缺位是一個不爭事實。古典時代的藝術(shù)都不可能具有自律性,中國古典藝術(shù)從屬于德性化的倫理而西方古典藝術(shù)從屬于神性化的真理。近代西方藝術(shù)的自律化由諸多的原因引發(fā),比如市民社會的出現(xiàn)、形而上學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工程的展開,等等,這些元素在中國近代社會中均未有現(xiàn)身,所以自律性藝術(shù)的缺位可以理解。我認為細究起來,應該還有這樣一些原因可以解釋中國藝術(shù)的自律性缺位的現(xiàn)象:第一,從最直接的歷史情況來看,近代以來的悲情歷史,即李澤厚先生所論說的“救亡壓倒啟蒙”這一歷史境況,乃是中國藝術(shù)自律性缺位的首要原因。在“救亡壓倒啟蒙”的悲情歷史中,象牙塔化的自律性藝術(shù)不可能有生存的條件,社會革命的藝術(shù)敘事才是中國社會所需要的;中國知識界向往的是一種“審美國家主義”的藝術(shù),這種藝術(shù)具有引領社會革命和歷史進步的功能。第二,中國屬于后發(fā)現(xiàn)代性民族,全能主義的王朝體制很難形成“市民社會與國家”這樣的二元化共同體模式,因此市民社會的發(fā)展也是先天不足,市民社會的先天不足就不可能有以“人類社會實踐的結(jié)構(gòu)性分解”為特征的現(xiàn)代性工程,因此就沒有形成自律性藝術(shù)生長的社會土壤。不過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情況下或許會有市民社會的短期登場,這一情況可能會在藝術(shù)場里引發(fā)一些自律性愿景,比如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初期就出現(xiàn)過以騰固、邵洵美等人領銜的“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運動。第三,從中國知識傳統(tǒng)來看,中國藝術(shù)的自律性缺位乃是形式化的分析性思維的必然結(jié)果。漢語的文字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不完全形式化”的符號系統(tǒng),這種“書寫性”的符號系統(tǒng)的辨義機制是“字形狀物”,它用訴諸自然物表象的線性圖案引發(fā)有關意義的視覺聯(lián)想,所以漢語思維不可能走到“形式化”進而形而上學化的地步,這就決定了中國藝術(shù)不會生出所謂“形式本體論”。美國學者郝大維、安樂哲在《期望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思維是一種跟西方的分析性、因果性思維全然相異的兼容性、關聯(lián)性的思維。中國思維方式不會將事物分解開來凸顯其本體意義上的所謂本質(zhì),而是將其置于多重關聯(lián)中比較其“異同”。這樣的思維傳統(tǒng)中,藝術(shù)的本質(zhì)不會被置于“隔離”狀態(tài)來思考,藝術(shù)的區(qū)隔性特征也難以得到張揚。第四,在辨析中國藝術(shù)的自律性缺位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到,跟西方一樣,中國古代同樣存在著“審美倫理”,而且“審美倫理”也被當成一種藝術(shù)性的決定要素,比如莊子講的“解衣盤礴”的故事,還有《論語》中孔子與學生談及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那段話,都體現(xiàn)了一種審美化的價值想象。但是,中國藝術(shù)史上始終沒有過用“審美”為藝術(shù)品定性的想法。因此,在古典中國,藝術(shù)一直沒有獲得單一而純粹的自律性的本質(zhì),它只能存在于各種事物的“兼性”狀態(tài)。我們說自律性藝術(shù)的大廈是憑借著“審美倫理”和“形式主義”這兩道山墻跟世俗世界隔離開來,倘若缺了“形式主義”,自律性藝術(shù)大廈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建造起來的。盡管中國古代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些帶有形式主義傾向的想法,比如嵇康的“聲無哀樂論”、石濤的“一畫論”等,但是這些說法很難抵消那種出自于語言特性的思維方式的歷史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