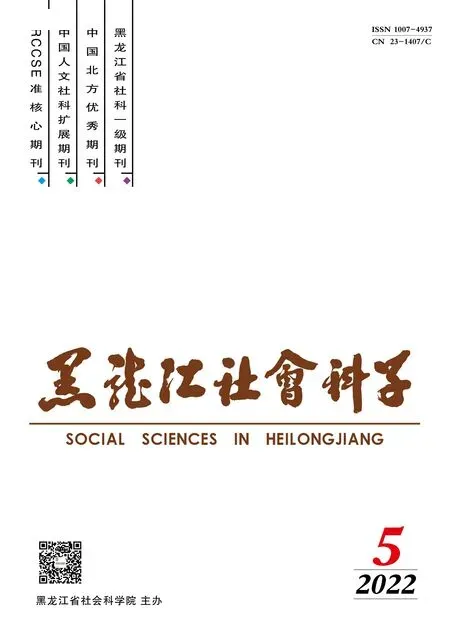金代佛教緣起與發展的內外因素
——以12世紀女真對外關系為背景
王 俊 錚
(阿穆爾國立大學a.宗教學與歷史教研室;b.考古學與人類學實驗室,俄羅斯 布拉戈維申斯克 675027)
女真人最初信仰薩滿教,史載:“‘珊蠻’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變通如神。”[1]卷3,21與其他北方民族所信奉的薩滿教并無二致,女真薩滿教也是建立在萬物有靈觀念基礎之上,以自然界、神靈為崇拜對象的原始宗教。文獻所見,女真薩滿教有祛病除害、為人求子、詛咒仇家等功用[2]。有學者有見地地提出,薩滿教中的某些觀念,如神靈崇拜等,“為女真人提供了最初的宗教體驗,從而為女真人接受佛教奠定了經驗基礎。”[3]哈爾濱市阿城區金上京遺址附近的亞溝鎮金代早期摩崖石刻(關于這一石刻的年代與性質,尚有爭議。鳥居龍藏認為反映的是金太祖阿骨打與其皇后的形象[4];張連峰認為是女真王公崖墓墓主人的形象[5];趙評春認為是金上京護國林神像[6]。而李秀蓮等則認為當為蒙元時期蒙古人形象[7]。筆者從學界主流觀點,暫將其年代認定為金代早期),便反映了這一時期女真人的某種神秘的神靈偶像崇拜觀念。
女真人在金政權建立前后,以較為開放和積極的姿態與兩宋以及遼、西夏、高麗、回鶻等政權、族群進行了密切的互動,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施加了重要的外部影響,終致金代形成“胡俗奉佛尤謹”[8]31的繁盛局面。本文即以女真對外關系為歷史背景和視角,對金代佛教的歷史緣起與發展作一探究。
一、金代建國以前東北地區的佛教傳統——渤海與遼代佛教論略
《金史》卷1《世紀》載:“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麗不肯從”[9]2,說明在金代建國以前,女真先民上層就已有人信仰佛教。但阿古乃“好佛”可能是受了高麗佛教的影響,而松花江、黑龍江流域的女真佛教當以渤海佛教為遠源,以遼代佛教為近源。
《金史·世紀》開篇說:“金之先,出靺鞨氏。”[9]1這里的“靺鞨氏”,其主體顯然應是散居于黑龍江中下游、松花江中下游和牡丹江下游的黑水靺鞨。《金史·世紀》又載:“始祖居完顏部仆干水之涯。”[9]2“仆干水”即今牡丹江,“仆干水之涯”則大致為牡丹江中游流域的海林、寧安一帶。至獻祖綏可時期,“乃徙居海古水……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矣”(《金史·世紀》)[9]3,即從牡丹江流域遷徙到海古水(今哈爾濱市阿城區東北海溝河)附近,并定居在安出虎水(今阿什河)之畔。然其后世仍常活動于牡丹江流域,如昭祖石魯在征服女真諸部時,“還經仆燕水。……行至姑里甸,得疾。”(《金史·世紀》)[9]2“仆燕水”即“仆干水”,“姑里甸”應是“胡里改”的音轉,均指今牡丹江。
由此可見,女真完顏部先祖主要活動在牡丹江流域,而該流域在渤海時期作為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百余年之久。渤海佛教繁盛,上京地區佛寺林立。20世紀上半葉,俄羅斯學者包諾索夫,日本學者鳥山喜一、原田淑人等人初步探查了上京城內佛寺遺存的情況[包括東京城第一至第四寺址(2、6、4、5號佛寺)、白廟子寺址(7號佛寺)、土臺子南方寺址(3號佛寺)、土臺子北方寺址(塔址)、土臺子寺址、土臺子內部堂址等][10]。20世紀60年代,中朝聯合考古隊的調查則確認了9座佛寺址,并對8、9兩號佛寺遺址進行了發掘[11]。此外,20世紀40年代至今,在上京城遺址內白廟子村、土臺子村等處還多次出土舍利函,并發現有寺廟遺跡[12]。如此看來,渤海上京城內外佛寺數量當在10座以上,可以說,渤海時期牡丹江流域的佛教是十分繁盛的。
除此之外,在松花江流域的樺甸蘇密城遺址發現有大量渤海陶佛殘件和銅坐佛等[13],在農安遼塔及萬金塔村遺址中發現了疑似渤海時期的佛造像、方形石塔和鐵塔等[14]。樺甸蘇密城、農安分別為渤海長嶺府、扶余府府治故址,在渤海佛教廣泛傳布的背景下,可以推知地方府州城內同樣應該存在頗具規模的佛教寺院和信仰群體。
可見早在渤海時期,佛教在金源故地內就已廣泛傳播。雖然目前尚無文獻證據能夠直接證明女真人的佛教信仰直接承自渤海,但考古發掘提供了佐證材料。1977年,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隊在對大烏蘇里島(即黑瞎子島)上的科爾薩科沃女真墓地進行發掘時,在一座墓葬中出土了1件青銅鎏金佛(菩薩)造像,發掘者認定為渤海時期[15]。也就是說,金代建國以前,佛教很可能就已傳入女真人中。
契丹貴族信仰佛教始于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時期。阿保機在建國前后,曾俘獲了大量信奉佛教的漢人。唐天復二年(902)“九月,城龍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開教寺”(《遼史》卷1《太祖紀上》)[16]2,即于龍化州創建了見于史籍的第一座契丹佛寺——開教寺。在阿保機即可汗位的第三年(909)“夏四月乙卯,詔左仆射韓知古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紀功德”(《遼史·太祖紀上》)[16]4。至繼可汗位第六年,阿保機在征討中“以所獲僧崇文等五十人歸西樓(后稱上京臨潢府),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遼史·太祖紀上》)[16]6。神冊三年(918)五月,阿保機又“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遼史·太祖紀上》)[16]13。佛寺逐漸成為契丹城市中重要的景觀建筑和宗教活動場所。近年考古工作者對遼上京西山坡佛寺遺址進行了發掘,顯示該佛寺由多組東向院落組成,總體上是塔殿并重的格局[17]。太祖以后遼代諸帝,皆對佛教極為尊崇,帝后及貴族常常親赴佛寺禮拜、飯僧。圣宗、興宗、道宗三朝時期,佛教逐漸向契丹內地發展,遂臻于極盛。
遼代東北地區則相繼出現了龍化州開教寺、上京天雄寺、宜州(今義縣)奉國寺、興中府延昌寺(今朝陽北塔)、鳳凰山天慶寺、興城覺華島海云寺等一批著名寺院;上京、中京附近還開鑿有規模浩大的石窟寺:上京附近存有前昭廟石窟、后昭廟石窟、洞山石窟和三山屯石窟,中京附近有福峰山石窟、靈峰院千佛洞等遺跡[18]。
遼代金源故地的行政建制主要包括東京道轄下黃龍府、五國部,上京道轄下長春州、泰州等。目前在上述區域發現了農安遼塔、塔虎城遼代塔基[19]、城四家子古城遼晚期寺廟遺址、礎倫浩特佛教道場等遼代佛教遺跡。位于吉林省白城市的城四家子古城(遼代長春州),系目前已知東北地區遼金時期州城級別城址中面積最大的一個。在對該古城城內建筑基址的發掘中,于早期地層發現大量泥塑佛像殘塊以及迦陵頻伽構件,同時還出土了帶有“大安八年”“大安九年”“興教院”“施主”“施瓦”等墨書文字的綠釉瓦。墨書文字表明該建筑應為一座佛寺,其營建年代不晚于1092—1093年之間[20]。
而遼代泰州治所、今泰來縣塔子城(綽爾城)遺址,則曾出土有遼代“大安七年”建塔題名殘碑,記載了“建辦塔事”的史實[21]。近年王禹浪教授等人在對位于內蒙古興安盟扎賚特旗嫩江右岸綽爾河流域的礎倫浩特遺址進行考古調查時,也發現了類似文物。這處遺址屬遼代泰州轄境,研究者認定遺址內博格達山最初為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出生地都庵山[22],而后成為一處北方民族集宗教(佛教、喇嘛教、薩滿教)、祭祀神祇(敬天、禮地、祭祖)、陵園為一體的重要場所,具備古代國家意識形態禮儀空間構造格局和多元族群與宗教文化交融的鮮明特點。其中,在可能系佛教道場的遺址發現了“大安四年”題刻[23]。城四家子古城、塔子城、礎倫浩特遺址都出土有遼代大安年間的佛教遺物,似可推測在遼代晚期,長春州、泰州一帶可能出現過一次佛教興盛和佛寺營建的浪潮。
二、女真在對外戰爭中對遼、宋佛教資源的繼承
隨著女真對遼、宋戰爭的持續,其控制地域不斷擴大,完全突破了金源故地這一地理空間,東北南部、西部以及華北等地逐步并入版圖。這一過程中,遼、宋豐厚的佛教資源被女真人所繼承,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量遼、宋寺院為金代佛教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間依托。例如,2020年發掘清理的遼上京西山坡佛寺5座建筑基址,顯示均歷經遼金兩代多次營建:軸線上的3座殿址在遼時期體量更大、規格更高,至金代體量變小;兩側的廊廡建筑在金代明顯呈向院落內部擴建之勢,致使院落內部空間整體縮小。上述情形反映了從遼代上京的都城佛寺到金代臨潢府的地方佛寺的演變情況[24]。又如,2000年對前郭爾羅斯縣塔虎城進行了系統發掘,根據出土遺物(絕大多數為金代,其次為元代)和地層關系可以斷定,塔虎城始建于金代,為金代肇州治所,但也是遼代出河店的所在地[25]。如此,該城東北墻外50米處的遼代塔基當早于該城的修建時間,而后金代在此營建州城,遼代佛塔則應得以沿用。遼代著名的奉國寺在金代也得以改擴建。根據金明昌三年(1192)所立《宜州大奉國寺續裝兩洞賢圣題名記》石碑[26],可知遼末金初之際,奉國寺僧通敏清慧大師捷公于該寺大雄寶殿殿前東西相對之兩廡鑿洞,并內置120尊賢圣像;金天眷三年(1140),寺主義擢與尚座義顯、都和義謙又于兩廡續置42尊賢圣像。而金代今朝陽地區的大部分寺院均系沿用遼代,如鳳凰山華嚴寺、天慶寺,興中州大觀音閣、崇福寺,龍山縣石柱山寺,惠和縣十方講院等[27]。此外,遼代在燕京(南京析津府)營建的寺院,如圣恩寺、報先寺、三覺寺等,在金代也都繼續發揮著講經布道、弘揚佛法的道場功能[3]。《松漠紀聞》云:“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建院”[8]31,而其中必然大多為遼代始建。同理,在女真占領北宋大片領土后,大量佛寺也必然被其所沿用。
第二,遼、宋龐大的佛教僧侶集團和信眾被納入金代國家管理體制之下。如金中都天宮院法師即緣,受戒于遼大安六年,圓寂于金天會十四年(1136),《中都天宮院法師幢記》云其“俗年七十六,僧夏四十六”[28]。也就是說,即緣在遼代傳法25年,入金后繼續傳法21年。而宋金戰爭期間,有不少宋地僧侶進入金源地區。《三朝北盟會編》引《宣和錄》云:“初,內侍承宣使鄧珪傳宣河北為虜所得,降之……又請珪家屬及官吏、士人、僧道、醫卜千余人……”[1]卷77,584-585洪皓《松漠紀聞》云:“己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其闕”[8]30,“己酉歲”系南宋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1129),可知這一時期有中原僧人在宋金交戰中被擄掠至金上京。而前文提及之《宜州大奉國寺續裝兩洞賢圣題名記》,作者為張邵,正是于建炎三年出使金國。史載其先被“拘之燕山僧寺”,后徙拘金上京會寧府:“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29]而其返程途中經過宜州,遂受邀為續修大奉國寺洞龕撰著了碑文[30]。洪皓與張邵同滯留金境,又一同歸宋,必然相識,洪皓所說之“中華僧”應該就是張邵使金的同行者。
第三,金人在對遼、特別是宋財富和文化典籍的劫掠中,收獲了大量佛教典籍。例如,史載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31];次年二月“初四日,虜索藏經、道經書板出城”[32]。大量佛教典籍輸入金境,客觀上促進了金代佛教的傳播和發展。
遼、宋繁盛的佛教文化為金代佛教涂繪了以禪宗、密教、華嚴宗等為信仰主體的底色,也為佛教繼續向東北腹地乃至更加遙遠的東北亞極邊地區傳播提供了原動力。
本研究以2018年教育部最新公布的黑龍江省81所高校為研究對象,通過拜訪形式填寫問卷。在正式發放問卷之前,首先對5所高校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和高年級學生進行了訪談,了解高校創新能力與績效的構成,在此基礎上設計、開發了調研問卷。然后,在與相關高校師生和專家的多次深入探討后,對問卷進行修正,確定最終問卷。向黑龍江省高校的中、高層教學管理人員和高年級學生分別發放了81份配對問卷,并成功回收81份有效問卷。在這些高校中,公辦院校64所,約占79%;民辦院校17所,約占21%。
三、金夏佛教文化往來——以迦陵頻伽形象的傳布為中心
西夏最初奉行盟遼抗金的政策,隨著遼的逐漸敗亡,西夏開始謀求與金建立友好關系。這種友好關系始于西夏元德六年(1124),在此后的80多年間,兩國雖有一些小的摩擦,但總體關系良好,這從兩國頻繁的交聘活動即可見一斑(《金史》卷134《西夏傳》:“自天會議和,八十余年來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9]2867。直到西夏襄宗篡位,才依附日漸強大的蒙古,轉而與金進行了長達10余年的戰爭[33]。
西夏早年與遼之間有著密切的佛教文化往來,主要表現為:遼的《契丹藏》、私人刊刻的佛經典籍和佛教繪畫、造像,以及遼的華嚴思想、顯密圓通思想、禪宗與八塔信仰等對西夏佛教產生了重要影響,而遼也通過西夏獲得了回鶻高僧為自己所用[34][35]。
而在金夏睦鄰友好時期,除了政治、經濟上的往來外,文化與宗教上的交往也很密切,主要表現之一是西夏對金佛教典籍的引入。《金史》卷60《交聘表上》載,西夏天盛六年(1154)“九月辛亥朔,夏使謝恩,切請市儒、釋書”[9]1408。此外,金代曾于解州天寧寺雕造漢文大藏經《趙城藏》,經版完工于大定十三年(1173),于大定二十年運抵京師中都;由于西夏對購買域外佛教典籍(如宋《開寶藏》、遼《契丹藏》等)始終懷有濃厚興趣,推測其應該也購有《趙城藏》[34]。
不過,因文獻記載有限,學術界一般認為,“相比之下,金朝卻絕少從西夏輸入佛教方面的東西”[34]。但通過對近年在西夏王陵、金代高等級建筑遺址中發現的迦陵頻伽構件的梳理,似乎能夠為還原金夏佛教往來的歷史面相提供新的線索。
大約在北魏時期,迦陵頻伽以印度本土的鳥形象傳入中國,之后與中原傳統的人首鳥身仙靈形象結合,并在唐代廣泛流行,進入裝飾領域。遼、宋時期繼續流行唐代樣式的迦陵頻伽,一般作為小件裝飾物或建筑外觀的裝飾紋樣出現,如耳飾、銅鏡、佛塔磚雕、經幢刻紋等。
以迦陵頻伽作為高等級建筑的構件裝飾以西夏為最。考古人員在對西夏王陵三號陵區月城、內城的東神門和東南角闕進行清理時,即出土有泥質灰陶、紅陶的迦陵頻伽雕塑脊飾[36]。西夏迦陵頻伽構件具有鮮明的風格一致性,西夏人將這種佛教圣靈形象運用于王陵的營建,是為了向世人昭告西夏君主即是佛陀;這也反映出阿彌陀佛凈土信仰在西夏境內的廣泛傳播,并受到了統治階級的認可[37]。西夏王陵三號陵是9座西夏王陵中最為高大宏偉的,再考慮到其基本處于整個陵區的中心位置,學術界多傾向于認定該陵系元昊陵[38]。如果排除后世修葺增建的可能,三號陵區出土迦陵頻伽構件的年代當在元昊去世的1048年前后。
而迦陵頻伽構件也見于遼代晚期和金代東北地區的建筑遺址中。前文提及,在城四家子古城城內建筑基址早期地層中發現了一件迦陵頻伽構件。這件器物頭部殘缺;上身為人形,雙手合掌于胸前,手部殘;下身為鳥形,下肢呈鳥爪狀彎屈置于下身兩側;底座為圓筒形。發掘者指出:“出土的迦陵頻伽雖層位較晚,但從陶質、陶色上看,亦應為早期建筑所使用。”[20]這里所說的早期建筑,時間為遼代晚期。不過,這件迦陵頻伽構件與建筑基址晚期(金中期)地層出土的灰陶鳳鳥、垂獸的質地特征并無明顯差別,且其出土層位較晚,尚不能排除制作于金代的可能。

圖1 1992年金上京遺址出土的灰陶迦陵頻伽殘件
位于安圖縣二道白河鎮附近的金代神廟遺址,其編號為JZ1的建筑臺基東側出土了一件灰陶迦陵頻伽。根據2016年在JZ1室內出土的“癸丑”“金”“於”等字樣的玉冊殘塊再結合文獻記載,可以基本斷定該神廟當為始建于大定十二年、用于祭祀長白山的“興國靈應王廟”[41]。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發現了一件迦陵頻伽構件。根據太子城的地理位置、出土文物品級以及相關文獻記載,研究者推測其為《金史》中記載的始建于金章宗時期的夏捺缽所在地泰和宮[42]。北京大房山金陵編號為2001FJL的宮殿建筑遺址群發現了7件琉璃陶迦陵頻伽和2件灰陶迦陵頻伽[43]。大房山金陵始建于海陵王時期,后經世宗、章宗、衛紹王、宣宗五世60余年的營建。
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考古學家在對遠東濱海地區尼古拉耶夫斯科耶女真時期古城內城正門遺址進行發掘時也發現了灰陶迦陵頻伽(下頁圖2)。該城門為覆瓦建筑,設3個門道[44];內城內建有高級別的覆瓦建筑群,為古城官署區。
通過上述梳理可知,大約在11世紀中葉以后,今寧夏及東北地區松花江流域等地都出現了迦陵頻伽形象的建筑構件。不過從年代上來看,東北地區目前所見之迦陵頻伽構件的年代大致為金中期的世宗、章宗時期,顯然晚于西夏元昊時期。盡管材料仍顯單薄,但筆者推測,至遲在遼代晚期,西夏建筑中的這一佛教裝飾元素就已經開始影響東北地區了;迨至金代中期,金夏關系不斷發展,佛教文化往來增多,迦陵頻伽作為高等級建筑構件的裝飾元素遂逐漸出現在了京城皇家禮儀性建筑、祭祀長白山神廟、夏捺缽皇家行宮、皇家陵寢等重要建筑中。我們雖不能將這種可能存在的關聯性歸結為純粹的佛教信仰的傳布,但至少反映了一種佛教審美的表現形式從西夏向金的播遷。
四、高麗、回鶻、粟特等周邊政權和民族對金代佛教發展的影響
前文提及,在金朝建立之前,女真始祖函普之兄阿古乃可能受高麗影響而信奉佛教,但金麗兩國佛教文化往來情況史籍卻語焉不詳。不過之前遼麗佛教文化往來十分密切:遼曾多次將《契丹藏》賞賜給高麗;遼道宗時期,高麗亦曾向遼進貢佛經[45]。金朝建立后,高麗于天會四年奉表稱藩,約定處理雙方關系的基本原則是“一依事遼舊制”(《金史》卷135《高麗傳》[9]2885。《金史紀事本末》卷14《高麗賓服》亦云:“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于金”[46])。據此推測,金麗之間的佛教文化往來應該也保持了遼麗時期確立的傳統。

圖2 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尼古拉耶夫斯科耶女真時期古城出土的灰陶迦陵頻伽(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濱海國立博物館藏)
在女真人與內亞族群的交往中,亦可覓得有關佛教文化傳播方面的蛛絲馬跡。回鶻汗國為黠戛斯攻滅后,回鶻人四處流散,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口向西、南遷徙,在河西走廊、吐魯番盆地和中亞相繼建立了甘州回鶻、高昌回鶻和喀拉汗王朝三個政權;又有約30萬人投唐,散居在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州)、天德軍(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烏加河東岸)等地[47]。隨著遼金相繼控制燕云一帶,云州、朔州一帶的回鶻人也成了遼金轄境內的居民。據學者研究,金代回鶻人主要分布在咸平府(今遼寧開原)、遼東、原遼上京及中京地區、燕京、秦川以及陰山以北汪古部等地[48]。《松漠紀聞》云:“女真破陜,悉徙之燕山”[8]15,可見確有部分回鶻人被遷徙至燕山一帶。回鶻人遷至東北地區在考古學上也得到了印證。俄羅斯學者通過對9—10世紀之際黑龍江沿岸地區女真先人遺存的考察,認為如東南歐—哈扎爾式、中央亞細亞—中亞式的平板鏤孔腰帶飾件以及斯基泰—西伯利亞藝術風格的器物等,反映出了古代突厥語族文化成分,且主要為回鶻文化,其次為黠戛斯文化;回鶻人在女真人的民族構成上亦可能在某一階段起過某種程度的作用[15][49]。
佛教是回鶻人的重要信仰之一。《松漠紀聞》有云:“(回鶻)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8]15另,元好問所撰《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曰:“(金)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50]學界對所謂“回鶻人梵唄之所”究竟為何爭議頗大,有景教教堂[48]、摩尼教禮拜之所[51]、佛寺[3]等說法。筆者贊同佛寺之說:既然“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尊像”與金太宗所見“佛陀變現”相合,則“尊像”必為佛像,“梵唄之所”當為佛寺。這則有趣的紀聞為回鶻與女真間的佛教文化交往提供了珍貴的信息。
而在早年,回鶻高僧曾受到西夏王室的禮遇,還被作為禮物贈與遼代皇室。《遼史》卷22《道宗紀二》云,咸雍三年(1067)“冬十一月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16]267。而遼代回鶻后族述律氏也對佛教十分尊崇,極大地促進了佛教在宮廷貴族中的傳播[52][34]。遼時期回鶻佛教勢力所產生的影響力,也必然成為后起的金代佛教傳播的因子。但由于文獻闕如,已很難對此作出更多的還原和解讀。
另據俄羅斯學者推斷,粟特文化可能也對女真人產生過一定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女真人物質文化的某些元素上,如帶紐的輪制器蓋、加筑器嘴的一些輪制容器、“令牌”式的青銅制品、中亞式的佛教紋飾等。至10世紀,在南西伯利亞、東蒙古高原等地的回鶻人中仍活動著不少粟特人,其許多文化元素完全有可能通過回鶻人或契丹人傳入黑龍江流域[15][53]。而除祆教外,佛教亦是粟特人的重要宗教信仰之一[54]。如若上述推斷確然,那么金代佛教或許也受到了粟特人的影響。
渤海和遼時期,涵蓋松花江中下游、嫩江下游的金源地區就已經出現了繁盛的佛教信仰,為金代佛教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女真人崛起及建國后,隨著疆域的不斷擴大和族群的不斷擴容,遼、北宋的佛教遺產幾為女真人所全盤接收,西夏、回鶻、高麗等政權、民族的佛教元素也隨之進入金國境內,僧侶、信眾、佛經與藝術等不斷進入或傳入東北腹地,乃至更加遙遠的東北亞極邊地區,佛教在金代遂得以持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