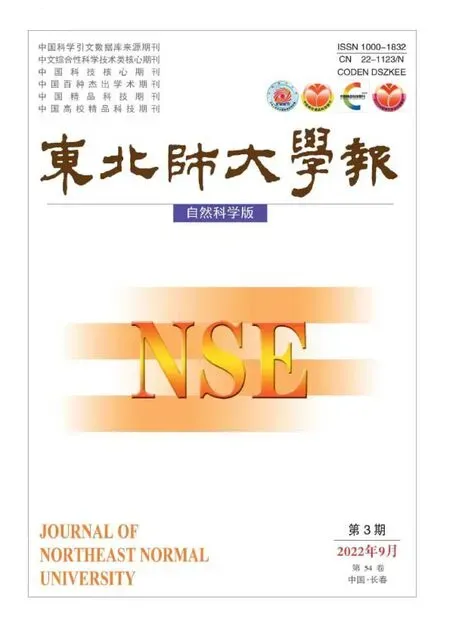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物種分化研究
張 雪,張立世,尚偉平,嚴蓉飛,姜云壘,李 時
(1.吉林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8;2.吉林農業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8)
隔離是物種分化的條件之一.一般而言,新物種的形成,先是不同種群間由于某種原因發生了地理隔離,而后各種群內的基因型和表型受到選擇壓力的影響而朝著不同的方向發生適應性進化,最終出現生殖隔離形成新的物種.但對于分布區域距離較近的物種而言,性別隔離則可能是促進其發生分化的主要原因.
物種形成是一個復雜而又漫長的過程[1].傳統的理論認為,地理隔離是物種形成的前提,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地理隔離并不是影響物種形成的唯一因素,尤其是對于擴散能力較強的鳥類而言,即使是在有基因流存在的情況下也能發生分化[2].近年來,研究者們已通過分子鐘推測出古氣候的變化也是驅動物種分化的一個因素,例如:由于更新世冰期-間冰期的氣候波動以及冰期避難所的存在,導致不同避難所內的動物種群發生了獨立的進化,進而形成了新的物種[3].有研究[4]表明,分布于北方地區的鳥類更易受到第四紀冰期的影響而被隔離在不同的破碎化地理分布區內發生分化.此外,生態因子也是驅動物種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沒有明顯的地理屏障存在的條件下,生活在不同環境中的同一物種的不同種群,由于對不同環境條件的適應而產生了遺傳分歧,甚至出現生殖隔離形成新的物種[5-6].然而,對于分化時間未超過200萬年的年輕物種,在發生二次接觸時,可能會發生雜交并產生可育后代[7],也可能將特定性狀不對稱地從一個物種向另一個物種滲透[8-10].
歷史上,栗斑腹鹀(Emberizajankowskii)曾是一種常見鳥類[11-12],主要分布區包括中國、俄羅斯和朝鮮[12-13].在過去50年間,由于棲息地喪失和破碎化等原因導致栗斑腹鹀個體數量劇減,已于2010年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列為瀕危物種[14],現存栗斑腹鹀種群主要分布于我國內蒙古的中東部地區.
三道眉草鹀(E.cioides)和栗斑腹鹀同為鹀屬鳥類,已有研究[15-16]表明二者為形態相似的近緣物種,且在栗斑腹鹀分布區內為同域分布物種.然而,驅動二者發生物種分化的主要原因,以及第四紀冰期是否對二者物種分化產生了影響仍不清楚.為此,本文通過分子鐘追溯了二者的分化時間,進而推測了驅動二者間發生物種分化的歷史原因;同時,通過形態特征和鳴聲特征研究了性別隔離對其物種分化的影響,研究結果將有助于更深入地認識和了解生物演化的過程,并為第四紀冰期在物種分化中的作用提供更為廣泛的科學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野外采樣和數據收集
2012—2019年每年的4—7月,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通遼市和赤峰市等地,對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繁殖情況進行調查,并采集形態數據、鳴聲數據和血液樣本.
在繁殖期內,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雄鳥常站在樹梢進行警戒,利用便攜式數字錄音機(TASCAM HD-P2)配以強指向話筒(Sennheiser MKH416 P48)對其進行錄音,收集兩種鳥的鳴聲數據.為避免對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繁殖產生過大影響,待雛鳥7~8日齡時,利用霧網捕捉成鳥,在翼下肱靜脈采集成鳥和雛鳥的血液樣本,每巢采集3~5只雛鳥.將采集到的血液樣本(10~20 μL/只)與1 mL無水乙醇混合于1.5 mL已滅菌的離心管中,于-20℃冰箱或液氮中保存,帶回實驗室后保存于-80℃冰箱中.繁殖期結束后,利用霧網捕捉成鳥,并用電子秤和數顯游標卡尺對捕獲成鳥的體重、體長、頭喙長、喙長、喙寬、喙高、頭長、頭高、頭寬、尾長、翅長、跗跖長、爪長和中趾長,共14個主要形態參數進行測量,收集形態數據.
收集完形態數據和血液樣本后,將成鳥原地放飛,并將雛鳥重新放回到所在巢中.根據后續的跟蹤觀察,采集血樣和形態測量均未造成雛鳥或成鳥的死亡.
2012—2019年,共采集到234份栗斑腹鹀血液樣本和60份三道眉草鹀血液樣本.2017—2019年,一共錄制到131只栗斑腹鹀的1 254個鳴聲和77只三道眉草鹀的759個鳴聲.共對79只栗斑腹鹀和20只三道眉草鹀成鳥的主要身體指標進行了測量.
1.2 鳴聲和形態數據分析
首先,利用SPSS中非參數檢驗的1-樣本K-S(Kolmogorov-Smirnov)檢驗,檢測所用形態數據和鳴聲數據是否符合正態分布.
對所有個體的形態數據進行雙尾T檢驗(2-TailedtTest),判別其性別二態性.因為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在繁殖期內主要是雄鳥站在枝頭鳴唱、鳴叫和報警,因此錄制的鳴聲均為雄鳥鳴聲.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均為雄鳥的鳴聲數據,因此,未對鳴聲數據進行性別二態性檢測.
如研究數據參數符合正態分布,則利用獨立樣本T檢驗(Independent Samples Test)判定不同物種間各形態和聲信號參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根據給出的Levene方差齊性檢驗結果判斷方差是否相等.如方差相等(P>0.05),則依據假設方差相等時的顯著值判斷;如果方差不相等(P<0.05),則依據假設方差不相等時的顯著值判斷.
如研究數據不符合正態分布,則利用非參數檢驗中的兩獨立樣本檢驗進行檢測.
選取61只錄音效果好(栗斑腹鹀30只,三道眉草鹀31只),且每只個體均具有10條以上可用聲波數據的樣本進行統計分析.鳴聲數據的非參數檢驗結果顯示,所有的鳴聲數據均符合正態分布(P>0.05).
選擇2018—2019年記錄的14個形態參數的個體用于后續研究,包括栗斑腹鹀51只(雌性26只、雄性25只),三道眉草鹀19只(雌性12只、雄性7只).各形態參數的1-樣本K-S正態分布檢驗結果表明,栗斑腹鹀各形態參數中,除頭喙長和中趾長外,其余各形態參數均符合正態分布(P>0.05);三道眉草鹀各形態參數均符合正態分布(P>0.05).
利用SPSS 19.0軟件對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主要形態和鳴聲特征參數進行聚類分析,并構建聚類圖.
1.3 DNA提取和線粒體ND2基因擴增
利用AxyPrep血液基因組DNA試劑盒和苯酚-氯仿法,對234份栗斑腹鹀和60份三道眉草鹀血液的全基因組進行提取,并參考文獻[17]給出的引物和方法進行PCR擴增.
所有的PCR擴增產物均用1%的瓊脂糖凝膠,在裝有1×TAE緩沖液的電泳槽中進行電泳檢測,所用標志物(Marker)為DL 2000.擴增所得樣本送生物公司進行測序.
1.4 遺傳距離和系統發育分析
測序所得序列用BioEdit version 7.2.5和Editseq version 5.0軟件進行編輯.用Clustal X ver.1.8軟件對測序所得的線粒體ND2基因進行比對,并對比對后的序列輔以人工校正,截取起始密碼子(AUG)和終止密碼子(UAA,UGA,UAG)之間的序列用于后續的數據分析.
分別利用PHYML軟件中的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PAUP* ver.4.0b10軟件中的鄰接法(neighbor joining,NJ)和最大簡約法(maximum parsimony,MP),以及MrBayes ver.3.1.2軟件中的貝葉斯法(Bayesian inference,BI)重建基于線粒體ND2單倍型序列的ML,MP,NJ和BI系統發育樹.利用PopArt1.7軟件構建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單倍型網格圖.
1.5 物種分化時間
基于線粒體ND2基因序列,用BEAST version 1.6.2軟件估算兩個物種最近的共同祖先時間.ND2的突變率參考文獻[17]關于黃鹀和白頭鹀的研究,采用每百萬年2%的突變率.應用jModeltest 2.1.10軟件計算所得的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單倍型的最優堿基替代模型為TIM2+I,而在Bayesi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Utility Version(BEAUti)v1.6.2平臺中并沒有TIM模型,因此,本文采用與最優模型最相似的堿基替代模型.估算分析共運行3次,每次運行100萬次,采樣頻率為1 000次/代,開始的10%作為“老化(burn-in)”結果舍棄.最終的結果在TRACER version1.5平臺中合并后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鳴聲分化
基于物種間鳴聲數據的持續時間、最高頻率、最低頻率和時間間隔4個參數的分析發現,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鳴聲間除持續時間外,均不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三道眉草鹀鳴唱語句持續時間更長(見表1),說明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在語句結構上存在差異,需進一步研究揭示二者語句結構上的差異.

表1 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鳴聲特征(平均值±標準差)
基于不同區域栗斑腹鹀種群間鳴聲數據的持續時間、最高頻率、最低頻率和時間間隔4個參數的分析發現,查干套力皋和嘎亥圖兩地分布的栗斑腹鹀個體除時間間隔外,均不具有顯著差異(見表2).

表2 查干套力皋栗斑腹鹀和嘎亥圖栗斑腹鹀鳴聲特征(平均值±標準差)
利用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鳴聲數據進行聚類分析,結果見圖1.由圖1可見,61只個體樣本聚成了2個主要分枝(A和B),然而聚類分析并沒有將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完全分開,在分枝A中,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聚在了一起.

紅色為三道眉草鹀,藍色為栗斑腹鹀
2.2 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形態分化
基于物種間形態數據的分析發現,栗斑腹鹀的翅長、跗趾長、體長、體重、頭喙長和尾長在雌、雄間存在顯著差異,其他形態參數雌雄間無顯著差異(見表3);三道眉草鹀的翅長、體長和尾長在雌、雄間存在顯著差異,其他形態參數雌、雄間無顯著差異(見表3).二者在主要形態參數上均表現為雄性個體較雌性個體略大.

表3 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外部形態特征比較(平均值±標準差)
分別對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沒有性別差異的形態參數、雌性形態參數和雄性形態參數進行聚類分析,三種方法得到了一致的聚類圖.其中,依據二者雌性形態參數構建的聚類圖(見圖2),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聚在了一起.

紅色為三道眉草鹀個體,藍色為栗斑腹鹀
2.3 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系統發育樹和分化時間
通過4種方法重建的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系統發育樹獲得了一致的拓撲結構,由其中的 ML進化樹(見圖3)可見,多數的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單倍型被分為兩大進化枝,且具有高的節點支持率(ML:76.2%,MP:100%,NJ:100%,BI:0.9).然而,被聚入到三道眉草鹀進化枝中的單倍型Hap29為兩個物種的共享單倍型,包含了4只栗斑腹鹀和21只三道眉草鹀個體.使用PopArt平臺制作的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單倍型網絡圖(見圖4)顯示,兩個物種間存在51次堿基改變.

紅色為三道眉草鹀個體,藍色為栗斑腹鹀

圖4 ND2基因序列單倍型網絡圖
從每巢中選擇一只雛鳥,估算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遺傳多樣性,結果(見表4)表明,栗斑腹鹀的單倍型多樣性(h=0.94,標準差=0.01)和核苷酸多樣性(π=0.006 2,標準差=0.000 1)均高于三道眉草鹀(h=0.52,標準差=0.11;π=0.000 8,標準差=0.000 2).

表4 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線粒體ND2基因遺傳多樣性
對兩個物種的最近共同祖先時間的計算結果表明,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最近共同祖先生活在136萬年前(95%置信區間(HPD)=1.05~1.70).實驗結果中所有參數的有效樣本量(ESS值)都超過了500,其中TMRCA平臺的ESS值達到了7 902.從計算結果來看,栗斑腹鹀所有單倍型的最近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2萬年前(95%置信區間=0.15~0.31),三道眉草鹀所有單倍型的最近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5萬年前(95%置信區間=0.08~0.23).
3 討論
3.1 鳴聲分化
鳴聲是鳥類重要的通訊手段,包含著豐富的信息,在吸引和穩定配偶關系、保衛領域、育雛等環節發揮著重要作用,具有物種特異性[18].本文對內蒙古扎魯特旗區域內,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兩個物種鳴聲參數的分析結果表明,二者間除持續時間外,其他聲學參數均不具有顯著性差異(見表1).已有研究[19]表明,鳴聲差異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生境類型、地理差異和學習行為等.三道眉草鹀具有學習栗斑腹鹀鳴聲的能力[18],通過本文利用鳴聲參數構建的聚類圖可見,61只個體聚成了2個主要分枝(A和B),但是在A分支中,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聚在了一起,聚類分析并未將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完全分開.因此,二者間鳴聲的相似性可能是由于三道眉草鹀的學習所致.對不同區域內生活的栗斑腹鹀的鳴聲特征進行分析后發現,在查干套力皋和嘎亥圖地區分布的栗斑腹鹀鳴聲參數中,只有時間間隔存在顯著差異(見表2),推測可能是由于地理差異導致的不同區域的栗斑腹鹀間出現了鳴聲分化.有研究表明,很多鳥類都具有鳴聲微地理變異,如:楊曉菁等[20]對武漢地區的白頭鵯進行的鳴聲研究表明,相隔2.5 km的兩個種群就能產生完全不同的鳴唱特征,地理距離越近鳴唱特征越相似.關于栗斑腹鹀不同種群間鳴聲特征是否存在微地理變異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3.2 形態分化
多數鳥類的形態和鳴聲一樣,具有物種特異性,這在鳥類分類學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喙高具有顯著差異,三道眉草鹀的喙要比栗斑腹鹀高(見表3),這可能是由于二者食物來源的差異所導致的.Haavie等[21]對西叢鴉(Aphelocomacalifornica)和西叢鴉落基山亞種(A.c.woodhouseii)進行的研究發現,這兩個最近分化的物種,由于食物資源的不同,在喙形上表現出明顯的不同,西叢鴉有更重的鉤狀喙,而西叢鴉落基山亞種的喙則較窄、較長,因此認為鳥喙的大小和形狀反映了鳥類食物資源的差異[22].此外,栗斑腹鹀在體型上也較三道眉草鹀略小一些.兩個物種的雄性個體都較雌性個體略大,這可能是性選擇的結果,雌性更偏愛體型較大的雄性[19,23-24].
鳥類的尾,作為飛行特性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輔助飛行的作用,可以很好地提高鳥類在飛行時的穩定性.尾羽這一功能的進化促進了鳥類的多樣化,使它們能夠更廣泛的飛行,從而開發更大范圍的生態位[25].本文的研究表明,三道眉草鹀的尾長要長于栗斑腹鹀,同時三道眉草鹀的翅長也要長于栗斑腹鹀(見表3),表明三道眉草鹀可能具有更好的飛行能力和適應性.然而,利用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形態參數構建的聚類圖同樣未將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完全分開(見圖2),表明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間尚未出現完全的形態分化,二者間仍具有相似的形態特征.
3.3 分子分化
分子進化的中性理論認為,DNA中的大部分突變是中性或者近中性的,并不會改變生物的表型,也不會對生物的適合度產生影響或影響很小.因此,DNA中同義突變的累積會遠高于非同義突變,而同義突變一般不會導致表型改變[26].這一結果表明,僅僅依據表型特征對物種分化進行研究是不全面的,可能會忽略掉DNA中存在的大量并未引起表型改變的遺傳變異.本研究利用線粒體數據重建了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系統發育樹,發現大部分個體都被歸入到了正確的分類群中.但Hap29單倍型為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共有的單倍型.盡管單倍型網格圖顯示兩個物種在歷史上出現了快速分化,二者間存在51次堿基改變[27],但仍不能否定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間可能由于較近的分化時間和不完全的表型分化而在同域分布區內發生過雜交漸滲.之前的研究表明,一些物種間由于分化尚不完全,在接觸區內常常會發生種間雜交并產生可育后代[7],即便物種分化時間達到1 700萬年,也可能誕生可遺傳的后代[28].
研究[27]表明,第四紀冰期-間冰期旋回的氣候變化對物種形成、分布區演變、種群分化、遺傳格局等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許多新物種的形成以及種群分化都發生在這一時期.本文參考Irwin等[17]關于黃鹀和白頭鹀的研究,以2%每百萬年作為ND2基因的突變率,用BEAST version 1.6.2平臺估算了兩個物種的最近共同祖先時間,結果表明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最近共同祖先生活在136萬年前(95%置信區間=1.05~1.70).這一時期,中國正處于“鄱陽冰期—鄱陽-大姑間冰期—大姑冰期”的轉換時期[29],氣候的波動和溫度的下降可能迫使這兩個物種的祖先被隔離在不同的冰期避難所中,并在不同的冰期避難所內發生了獨立的進化,進而形成新的物種.
本文的研究表明,栗斑腹鹀和三道眉草鹀的分化時間未超過200萬年,為典型的年輕物種[4],這也可以解釋二者間在形態特征和鳴聲特征上尚未發生完全分化的原因.在內蒙古繁殖分布區內的栗斑腹鹀所有單倍型的最近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23萬年前(95%置信區間=0.15~0.31),三道眉草鹀所有單倍型最近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5萬年前(95%置信區間=0.08~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