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身體的影像建構與意義生產
——再讀電影《大路》
喬潔瓊 孫 磊
《大路》是孫瑜20世紀30年代電影的代表作,“集合了全聯華的男星和當今中國銀壇最負盛名的小鳥陳燕燕,甜姐兒黎莉莉”,有“二十明星主演/四支特制新曲/全部配音歌唱”,因此,《大路》的公映被譽為“民國廿四年第一大事件”,放映一時到處客滿。甚至有人說沒有看過《大路》就是“沒有看過電影”。《大路》“啟發了觀眾的一種民族意識……從這里,顯然地國產片轉上了一個新動向。這就是從現實主義的階段更進一層的大步走入了反帝的陣線了”。《大路》不僅表現了抗日的熱情,更重要的在于“進一步把抗日的斗爭與中國工人階級聯系起來,將工人階級描寫為抗日斗爭的中心力量”,“是一部歌頌工人階級的愛國主義詩篇”。《大路》作為一部左翼電影的典型代表,塑造了“工人”這一具有政治意味的“現代身體”。
什么是中國的現代身體?約翰·奧尼爾認為身體與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們通過社會來思考身體,通過身體來思考社會、影響社會”。中國現代身體產生于革命、啟蒙、救國等現代性議題下。所謂中國的現代性,可以理解為,“新的時間和歷史的直線演進意識緊密相關,這種意識本身來自中國人對達爾文進化概念的接受,……在這個新的時間表里,‘今’和‘古’成了對立的價值標準,新的重點落在了‘今’上,‘今’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時刻,它將和過去斷裂,并連續上一個輝煌的未來”。現代身體是在新舊交替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政治性身體,本身代表了“今”的諸多特征,并融入了政治性、階級性、社會性等范疇。
《大路》中的“筑路工人”就是新舊歷史時期產生的“新民”,其健康美是在晚清以來提倡的軍國民運動、新文化運動、新生活運動對身體進行改造的歷史背景下建構起來的銀幕形象。《大路》中的筑路工人也體現了當時最時尚最先鋒的意識。影片將現代身體以時尚的面容進入電影產業,通過“凝視”這一觀看機制,工人“主體”形象得以建構和傳播。同時,這個身體的呈現又指向了未來,與社會主義工農兵電影的身體美學一脈相承。
一、政治與現代身體的影像建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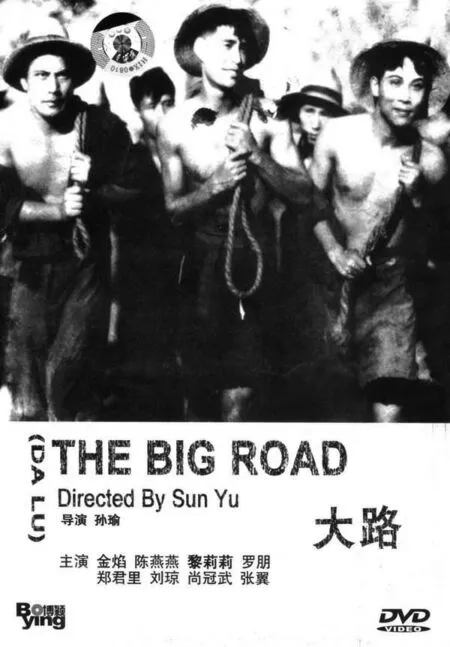
圖1.電影《大路》封套
中國現代身體建構的過程是中國由傳統儒家倫理社會向現代民族國家蛻變一種政治表征,是新舊交替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角力的結果。直到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才開始把目光聚焦到從來不認為是問題的身體上。梁啟超在《新民論》中說:“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孫中山呼吁中國應將身體視為國富種存的根本基礎。1917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中認為西方列強的強大首先在于國民身體強健,中國人要擺脫東亞病夫的面貌,必須從強身健體開始。在中國近現代歷史背景下,“現代身體”作為一種“行動綱領”上升到救亡圖存的高度,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工人階級作為先進的領導階級的觀念被召喚和建構。“工人”由一個職業稱謂逐漸變成一個具有政治色彩的詞匯,而“工人身體”從形象到敘事都需要建構起一整套話語來取代由傳統倫理綱常規定下的“封建身體”,進而適合新的政治觀念和文化邏輯。如果說中國“傳統身體”是在農業社會基礎上形成的,受家庭的“托管”,服務于封建社會的倫理秩序,現代政治觀念中的身體則走出家庭,交付于“國家”,“傾向于以國家主義來統整人民的心智與身體”。約翰·奧尼爾認為,“每一個政治共同體都必須以某種符號性的方式表達其有關信念。”從這一意義上來看,中國20世紀30年代左翼電影呈現的“工人身體”不僅僅是一個具有階級屬性的勞動者的身體,而是與國家未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具有詢喚功能的政治符號。
從20世紀20到30年代,中國電影的銀幕形象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反映出的是潛在的國家政治走向的變化。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國產電影的男性“身體”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家庭、婚姻、愛情為主題的身體敘事。這類影片常常描寫跨越階級的愛情,迎合當時小市民的觀賞心理,銀幕上的男性形象整體呈現出陰柔羸弱的氣質,充滿了憂傷哀怨的情調。以金焰主演電影為例,《野玫瑰》中的畫家江波,《桃花泣血記》中為情所困的少爺,《銀漢雙星》中的明星等。另一類則是被主流社會放逐的男性身體,如土匪、俠客等。風靡一時的武俠神怪片,其角色雖陽剛豪放,卻缺乏現代意識和時代精神。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銀幕形象依然寄宿在傳統的倫理綱常體系之下。
九一八事變之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重,救亡圖存成為擺在國人面前的首要任務。中國影壇集體“左轉”,在此氛圍下,“身體”被推到一個關涉民族存亡的重要位置,中國電影中呈現出明顯的“身體轉向”。此時,中國電影開始踐行民初以來知識分子的身體主張,“體育救國”多次出現在電影創作領域。孫瑜的一系列電影所呈現出的身體敘事,就是當時社會政治在身體上的反映。他曾說:“強身不見得就可以救國,但是救國家的國民,身體必須是強健的”,“我們研究提倡體育,在強身的條件以外,還必須養成一種新的精神:純潔、誠懇、堅忍、奮斗、勇敢、求進、切實、公正,還有那最要緊而我們最缺乏的團結精神!”《野玫瑰》《小玩意》等片中的孩子軍形象就是清末民初“軍國民運動”的縮影,《體育皇后》中的林櫻是當時提倡現代健康美的反映,《大路》更是將身體政治推向極致。
“民族危機有助于化減舊有道德和倫常體系對身體的壟斷和支配,但也在這個過程中賦予身體許多新的政治使命。”《大路》徹底擺脫和拋棄了傳統的倫理綱常體系下的“中國身體”,代之以新時代工人階級的身體形象。影片強化了筑路工人身體的國家屬性和民族屬性,他們不屬于某一個家庭,而是屬于國家和民族。他們筑路是為了國家,而國家也是他們最后的保護,這樣影片就將“身體”和“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了。《大路》作為金焰塑造的第一個為國捐軀的勞動者形象,一掃之前銀幕小生的淫邪氣質,為影壇吹來一股清新健康之風。金焰從扮演大少爺、明星、大學生到筑路工人,不僅影片中角色的身體進行著政治的蛻變,作為演員的金焰也同樣交付了自己的“私人”身體,從傳統的家庭倫理“身體”轉向了共有的“身體”。為了拍攝《大路》,金焰無暇照顧即將臨盆的妻子。在影片公映前夕,金焰領唱影片的主題曲《大路歌》《開路先鋒》,而他與王人美的孩子生下八天,不幸夭折。金焰與片中角色同時將身體交付與國家和民族。
影片通過新舊身體的二元對比建構了新的工人階級身體。在《大路》中,正、反兩派的身體對立通過空間進行了呈現。工人勞動的場景是開闊的外景空間,采用自然光,男演員較少化妝痕跡,這使得影片呈現出粗獷、奔放、大氣的視覺效果和紀錄片一般的真實感。他們修筑的是一條軍事公路,這條路是為了抵抗敵國炮火蹂躪而建,工人的動作與抗日救亡緊密聯系在一起,使得這一空間變成了富有政治意味的場域。“道路”也因為工人身體的“展演”而產生了普遍性意義。“筑路工人”代表著新的權力話語載體,這在之前的電影中從未出現過。作為“工人階級”的身份表征,他們身體的屬性具有公共性,屬于國家和民族,而非家庭,這正是“現代身體”的重要政治表征。同時,工人是以“群像”形式出現,這賦予工人以社會意義。他們之間的關系不是傳統的倫理關系,而是具有現代意味的“同志”關系,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漢奸。他們是鄉紳地主,家庭的構成有老爺、管家、夫人、小妾、丫鬟、護院,這是中國傳統的倫理綱常結構中的家庭。作為反派,電影賦予其落后性和反動性。值得注意的是,庭院后面的地窖,是封建社會鄉紳家庭的標配,是為了懲罰那些挑戰傳統禮教、倫常和夫權的叛逆者,通過對身體殘酷的刑罰,來迫使這些叛逆者踐行禮教、遵守權威。工人們被漢奸、劣紳關押在地窖之中,地窖變成了一個愛國者與漢奸的斗爭空間。封建鄉紳代表的不僅僅是舊秩序、舊權力,還代表一種賣國勢力站在了國家和民族的對立面。“現代身體”與“傳統身體”在影片中通過空間這一載體得以建構,空間作為“權力的眼睛”建構著身體,身體也決定著空間的建構,并“通過空間的建構來凸顯自身的價值”。
因此,《大路》中建構的身體高度符號化并具有超越性。影片放映后,有評論就指出“作品前半部分看到的勞動者的生活,使我們覺得這不過是一種誘人的憧憬和熱情,而絕不是現階段的勞動者的實際生活。……作品所表現的勞動者的生活,是編劇者的理想化的社會的幻覺。”影片中強調的“工人身體”并非現實中受剝削與壓迫的真實的“工人身體”,而是被賦予了階級、救亡等政治色彩,是具有革命、啟蒙意義上的現代身體。《大路》中勞動者不再是《春蠶》中的受壓迫的弱者形象,而是與力量,健康、生命、精力聯系起來的先進階級形象,這個形象承載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影片通過景別、造型、運動等表現手法,強化了符號的象征意義,如影片以工人們赤膊干活開場,伴隨著激昂的歌聲,“聯華”男星集體上陣,呈現在銀幕上的是荷爾蒙爆棚的健壯的男性身體。在烈日的照射下,他們裸露著的肌膚閃爍著健康的光芒,散發著雄性陽剛的魅力。這一場景奠定了影片的總基調:陽剛、樂觀、質樸、正氣。開篇中工人們身體的光澤、姿勢、動作都不是自然意義上的,而是具有德勒茲所謂的“超驗形式的呈現瞬間”,這一瞬間不只是單純的運動,而是指向了永恒。在《大路》中,導演孫瑜通過多次的重復強化了工人身體的“特殊瞬間影像”。除影片開頭部分赤膊干活之外,他們身體前傾,吃力地拉動著沉重的石磙,大路在他們腳下延伸……最后工人們壯烈犧牲的場景,也被高度抽象化,這完全超越了影片中的其他運動瞬間,仿佛定格在那里,具有永恒的意義。馬克思說,勞動者通過勞動創造了社會財富,并在對象化的本質活動中升華了自身。《大路》因此完成了現代身體的影像構建。
二、凝視與現代身體的意義生產
《大路》中的現代身體既然是一種政治表征,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那么這種工人形象如何實現意義生產并進入歷史場域?換言之,作為現代身體的“工人”的觀念是如何與公共空間相連接進而進入歷史的維度并指向未來?在未經歷過工業革命,整體仍處于農業社會的中國現實來講,“工人階級”不僅是一個新生的勞動階級,也是一個具有革命和啟蒙意義的新興詞匯。“工人階級”這一主體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和領導者的形象還未被建構起來,其政治符號意指仍未形成。借用拉康的鏡像理論,“鏡像階段是個體生命史、主體形成的階段,……而主體不等于自我,是自我形成過程中建構性產物。”彼時,民眾對工人階級這一主體及其認知仍處于拉康所謂的“嬰兒階段”,不僅工人階級無法確認自身的形象,民眾也無法在現實中找到政治意義的對應物。觀眾作為一個“先驗的主體”還未形成,因而不能與銀幕形象實現“認同”。因此,當孫瑜運用“高爾基式革命浪漫主義”將筑路工人以一種全新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工人形象”呈現在銀幕上時,這一現代身體卻超出了當時觀眾的“期待視野”。這一現代身體卻超出了當時觀眾的“期待視野”。當時觀眾認識并理解的工人形象是苦難、悲慘、深受蹂躪的。影片被認為沒有“忠實描寫筑路工人的生活”,是“非現實的”,認為《大路》用一種熱情把黑暗的現實詩意化了,因此“形式與內容不調和”。觀眾通過“凝視”影片形象,建構起一種對理想身體的想象。他們的凝視對象是“非現實”和“不可見”的。工人的“現代身體”在現實中處于缺席狀態,也就是麥茨所謂的“想象的能指”,“觀眾通過自己在場去指認這種缺席”。因此,具有政治符號意味的工人身體需要經歷一個自我對象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自我確認的過程,這也是現代身體意義生產的過程。《大路》中全新的工人身體通過“凝視”這一觀影機制進入形象的建構與認同中。與好萊塢電影通過劇中人物視角來體驗故事,刻意切斷觀眾與銀幕空間的做法不同,《大路》打破封閉空間,讓觀眾直接進入故事,觀眾不僅能夠達到“缺席”,還能夠獲得一種反身性自我建構。
《大路》將“工人身體”納入消費主義語境中,通過摩登女性的凝視突出了“現代性”。《大路》中“凝視”包含著復雜的層次,除上述的直接凝視外,還具有鮮明的性別視角。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與電影敘事》中指出,人們的觀看實際上是被男權主宰,女性作為客體被展示與被觀看,承受著男性的凝視,迎合著男性的欲望。好萊塢電影中的女性是欲望的對象,也是情節框架內被動的客體,因為在好萊塢電影中情節大多由男性推進,女性形象承擔著片中男性與觀眾“凝視”的功能,輔助男性完成敘事。縱觀中國早期電影莫不如此。《申報》中的電影宣傳基本上站在男性消費的角度上,“肉感”“刺激”等描述女性肉體來獲得宣傳效果。“肉感之能達到精神上的興奮,精神上的刺激是毋庸諱言的,所以,浪漫肉感、誘惑刺激、豐滿的臀、乳峰肉感的號召性標語在營業不振時尤其要作為生意的依傍,以‘肉感’為生意經來標榜,是舶來片的妙招,也是早期民族電影的法寶。”除了電影的女性身體被男性作為欲望對象進行了消費之外,早期中國電影的女性在敘事框架中,也常常作為附庸被動跟隨敘事進程。即便一些為女性量身打造的影片,如《桃花泣血記》《戀愛與義務》《一剪梅》《野草閑花》等,依然是將女性塑造成被凝視的“客體”,呈現出一種典型的男權視角。
作為一部男性主創的電影,《大路》卻反轉了以上的論述,“混雜”了女性與男性的觀看視角,將“身體”功能復雜化。影片既有“女性展示,男性凝視”,又有“女性凝視,男性展示”。女性凝視具有崇拜性,如丁香和茉莉對男性的“點評”:“我愛金哥的勇敢!他總在微笑,他永遠向前,從沒說過這事難辦!我愛老張的鐵臂!他不大說話……”勇敢、鐵臂、聰明、粗笨等男性特質成為青年女性的新寵,與之前太太小姐的審美趣味迥異。她們在評價這些男性的時候,眼睛看向畫外上方,這一視線也高于觀眾,她們的凝視具有崇拜性和公共性,指向了一個并非現實的對象,使筑路工人成為一種象征符號承載了人們憧憬和向往。影片通過丁香和茉莉這兩個摩登女性,使本身并不具有消費特征的工人身體具有消費性,從一個現實職業變成了富有政治含義的藝術符號,從而成功進入公眾視野。當時評論認為,本片的不足在于,丁香和茉莉是“擦粉燙發”階級的女性,是一種“編劇者理想之女性,而不是現實的勞動階級的女性”。然而,換一個視角不難發現,如果沒有這兩個“摩登女性”架起工人形象進入大眾的橋梁,《大路》很可能會成為像《春蠶》一樣叫好不叫座的電影。因此本片成為年度“不得不看”的電影之一,就在于其對電影時尚本性的充分利用和挖掘,進一步促進了影像的意義生產。“民國時期時尚的興起,標志著一種總體上的進步感,時尚是一種媒介,通過它,人們能跟上自己所選擇的民眾團體”,聯華公司正是將新型的意識形態通過時尚引領的方式確立了“新派”電影公司的身份。而《大路》成功將一種個人的審美與公共空間相連接,將新型的工人身體通過時尚、大眾媒介轉化為一種新的共同意識,賦予工人身體以“生產性”。在都市消費環境語境與明星效應下,通過多重“凝視”,使個人選擇和社會趨向緊密結合在一起。在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環境下,丁香、茉莉和工人們的覺醒以及她們的民族主義意識通過大眾媒介變成了時尚的一部分,通過跟隨這些新的偶像,大眾也重新定義了什么是現代身體并逐步構建起自己的身體形象。
《大路》的“凝視”也賦予女性身體現代意味。傳統倫理觀告誡人們:“非禮勿視”,而影院的放映環境卻將男性身體放大,這一方面賦予女性觀看男性身體的合法性,賦予她們性別平等的權力;另一方面,它也構建一個公共的話語空間,通過電影的放映、觀看、評價等一系列機制將婦女解放這一現代觀念隱藏其中。再如觀看男人洗澡段落突出了女性的主導性和控制性。茉莉和丁香“俯視”著男人們,空間上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讓她們得到一種超越封建倫理的居高臨下的精神快感。眾所周知,當時電影中的女性大多是被動的弱者,在大部分影片中面臨著被拋棄、墮落、死亡的命運,而《大路》滿足了她們主宰世界的幻想。本片的敘事框架并非僅僅由男性構建與推進,女性既是男性的欣賞者、觀看者。隨著故事的推進,她們成了男性的“拯救者”。影片后半部分,丁香和茉莉主導了敘事的進程。當她們勇闖虎穴,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拯救了男人,她們不再是柔弱的代名詞,而是象征著女性意識的覺醒。
三、現代身體的主體召喚
《大路》所創造的“現代身體”以一種“新人”的形象出現在早期中國電影中,其所召喚的工人“主體”的建立仍處于起步階段,但對中國電影的人物譜系開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應該說《大路》中所塑造的工人身體進入了歷史的維度,體現了工人階級這一具有先進意識的領導階級是如何成長為歷史主體的。阿爾都塞指出,所有意識形態的功能在于把具體的個人‘構成’為主體”。20世紀30年代的工人作為一個個體是存在的,但不具有“主體性”。銀幕上的工人形象與真正的工人之間是一種“想象性關系”,而這種想象關系由于缺乏國家意識形態的整體構架,其位置與合法性受到質疑。觀眾會根據現實中的工人形象的標準去評價電影中的人物,覺得電影人物脫離了現實。具有進步思想的孫瑜在電影中的工人階級還處于襁褓之中的時候,就在《大路》中將工人這一具有未來指向的形象進行表達,突出描寫了工人的反抗意識和主體意識的覺醒。片頭曲《開路先鋒》唱到:“前途沒有路/人類不相同/是誰阻礙了我們的進路/障礙重重/大家莫嘆行路難/嘆息無用/我們要引發地下埋藏的炸藥/對準了它/轟轟轟/看嶺塌山崩/炸倒了山峰/大路好開工/挺起了心胸/團結不要松/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歌曲中的道路、障礙、炸藥、山峰等意象都具有十分明顯的隱喻色彩,障礙就是指漢奸、鄉紳、日本侵略者。面對這些阻礙我們進路的障礙,工人應主動團結起來進行反抗。工人不是一個個體,而是一個階級,這就是“我們”。從“我”到“我們”,從被欺壓到團結起來反抗的敘事意味著工人主體意識的覺醒。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構架下,工人無法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合法位置,因此,影片只能提供一種想象性解決,即以工人以身殉國作為結局,正是這種身份不定、前途不明的“主體”的必然命運。
新中國建立后,以工農兵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一份整體性想象圖景”,工人作為“主體”成功被賦予了合法的位置,也接受了現存位置的合法敘事。因此,如果說《大路》生產了一個“現代身體”,那么“工農兵”電影則將“工人”身體的生產轉向主體認同,將工人成功從“個體”傳喚為電影的“主體”,同時也是國家的“主人”。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大路》所創造的工人形象指向了未來,與工農兵電影的身體美學一脈相承。
1949年后的中國電影是以“工農兵”文藝思想為指導進行創作的。工人作為“社會主義新人”以全新的面目出現在新中國的銀幕上。如《橋》講述了東北某鐵路工人為了支持解放戰爭,接受了搶修松花江鐵橋的任務,工人們克服了一系列困難,將大橋修復。《橋》中的工人同《大路》中的一樣,他們的身體屬性都具有公共性和政治性,都是以一種“新人”面貌出現,同時他們的身體都具有“生產性”。不同的是,《大路》的工人在斗爭中死亡,結局彌漫著一股悲壯之美,而《橋》的工人取得了勝利,洋溢著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豪情。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大路》上映于1934年,此時國家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前途生死未卜,工人階級力量薄弱,而工人主體尚未建立,人們是在消費主義語境中理解工人及其身份意義。而《橋》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故事片,站在回溯歷史的視角去講述故事。在這一過程中,工人已經從邊緣人成為國家主人,“主體性”已經建構。或者說觀眾是在一種建設新中國的語境中理解工人及其身份。此時的身體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體制化話語,“生產和建構著想象界與現實界的身體和身體話語”。因此,《大路》中的身體由于缺乏主體的認同主要以“消費性”為主,而《橋》則是一種已經建構起主體的“生產性”身體。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人主體性的建構。
在20世紀30年代“革命與啟蒙”的左翼話語之下,《大路》的產生具有重要的譜系意義。“電影只不過是一個主體的映像”,從《大路》到新中國電影,這個映像呈現了主體的生成過程,讓我們在鏡像中,看到了工人主體形象的流變。《大路》中工人們修筑的公路遍布祖國大陸,并不斷向遠處延伸,這些影像象征著工人的地位與位置。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大路》召喚出了作為現代身體的工人主體,并將這一主體納入歷史的網絡,預示著未來工農兵電影的方向。
結語
《大路》是20世紀30年代一部獨特的左翼電影,編導孫瑜所創造的工人群像在中國電影史上首次賦予工人身體以現代屬性。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影片通過新舊對比建構了工人的現代身體,通過電影的觀看機制實現了現代身體的建構與意義生產。在時尚風潮的引領下,影片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階級意識、女性意識等現代性議題逐漸得以傳播。應該說,《大路》有意識地將具有政治意味的工人身體的“展演”帶入公眾視野,將工人階級從被壓迫者塑造為救亡主體進入歷史的維度,與建國后中國電影中的工人形象具有一脈相承的譜系性。
【注釋】
1孫瑜全力修筑“大路”[J].聯華畫報,1934(5):1.
2廣告[N].申報,1934.12.25(27).
3廣告[N].申報,1935.01.05(33).
4轉引自袁慶豐.左翼電影的模式及其時代性—二讀《大路》[J].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19(4):15.
5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中國電影發展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343.
6[加]約翰·奧尼爾.身體五態:重塑關系形態[M].李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4.
7[美]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M].毛尖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54.
8黃金鱗.政治·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6.
9[加]約翰·奧尼爾.身體五態:重塑關系形態[M].李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51.
10黃金鱗.政治·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2.
11同10,191.
那既然這些活動都交給學生來自主管理、自主參與了,那中隊輔導員們是不是就無事可做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中隊輔導員除了要在活動中適時地給予隊員必要的幫助外,還應該在每次活動前設立合理的評價機制。當然這個評價機制應該是多渠道的,并非僅僅包含輔導員對隊員的評價,還包含個人自評、隊員互評、學校和家長評價等。如此多渠道的評價模式,必能激勵和促進隊員更積極、更主動地參與活動,提高隊員的評價能力和自我改進能力。
12光洲.大路·評一[A].陳播.三十年代左翼評論文選[C].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168.
13[法]德勒茲.電影1:運動-影像[M].謝強,馬月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6:8.
14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83.
15孫瑜.銀海泛舟[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112.
16同12,165.
17流冰.大路·評二[A].陳播.三十年代左翼評論文選[C].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168.
18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88.
20同12,165.
21[美]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M].李恭忠,李里峰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36
22陳越選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361
23史靜.主體的生成機制——“十七年電影”內外的身體話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9
24[美]尼克·布朗.電影理論史評[M].徐建生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