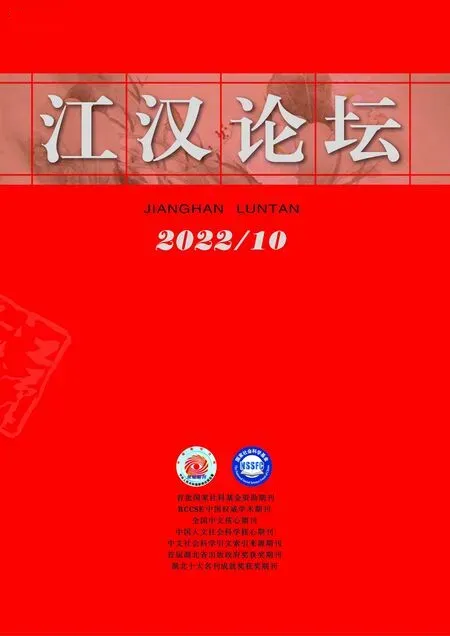德國啟蒙悲劇詩學的激情與教化
盧白羽
德國早期啟蒙運動領軍人物高特舍德曾發表過一篇題為《不能將戲劇、尤其是悲劇從秩序良好的城邦里驅趕出去》的演講。顯然,這一題目是在回應柏拉圖《理想國》將戲劇以及戲劇詩人從理想國家里驅逐出去的著名提議。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認為,戲劇在舞臺上呈現激烈情感的宣泄,迎合并助長了觀眾身上本該加以克制的非理性的感性部分,撼動理性對情感的絕對統治,從而破壞個人對自身的統治秩序,進而破壞整個國家的統治秩序。據說亞里士多德提出悲劇的凈化情感功能,就是在回應他的老師對悲劇的攻訐。自此之后,如何處理悲劇激發觀眾情感,成為西方悲劇詩學的焦點問題。
戲劇因其公共性與直觀性,是啟蒙時代向大眾傳播啟蒙思想最有力的媒介,因而成為最受重視的文學體裁。然而戲劇(尤其悲劇)激發觀眾激烈的情感,似乎威脅到理性的澄明狀態,成為啟蒙思想家不得不面對的難題。啟蒙時期悲劇詩學討論的焦點在于悲劇在觀眾身上引發的情感是否具有道德認知與教化功能。悲劇詩學首先關注的不是悲劇作為藝術品本身的審美價值,而是其對接受者的影響。詩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論證受眾如何通過文學藝術成為更好的人,并以此為標準來衡量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在將藝術自律奉為金科玉律的現代人看來,這種“效果美學”乃文學他律的過時理論。歌德就認為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根本不關心道德教化。道德與文學無關,乃是宗教與哲學要關心的問題。不過在阿倫特看來,詩人希望通過文學作品對社會施加影響,恰恰表達了詩人對這個世界的愛。詩人以作品積極介入這個世界,乃是致力于建構藝術家與同時代人的共同生活世界。看來,詩學議題并不僅僅涉及文藝學、道德哲學,甚至也牽連政治哲學。柏拉圖的問題應該得到嚴肅回應。
一、理性主義悲劇詩學教化觀及挑戰
理性主義哲學家高特舍德自信可以駁倒那些指責悲劇煽動卑劣情感、敗壞人心的異議,證明悲劇是啟發民智、對人民施行道德和公民教育最有效的途徑。他認為首先應當正本清源,明確悲劇典范。悲劇應該是“富有教育意義的道德詩篇……一篇譬喻性質的寓言,意在(闡明)一則重要道理。”文學的本質是寓言,以感性形式向觀眾傳授一則道德真理。詩人應當按照演繹法,從一則道德真理出發,鋪陳出悲劇情節。悲劇訴諸感官,激發感情,只是為了更好地達到倫理認知目的。
不過,理性主義哲學雖認定有效道德判斷只可能基于理性的判斷與認識,卻也承認情感仍然在倫理生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情感既能夠阻礙理性道德真理發揮效用,也能賦予它強大的說服力。悲劇利用精彩情節迎合觀眾的感性激情,實際上是借此“誘惑”將觀眾引向道德真理。文學引起的審美愉悅不過是一種引導和勸服觀眾接受真理的修辭手段。悲劇將美德刻畫為美,邪惡刻畫為丑,從而引導和培養觀眾對他們無法在理性上認知的善惡產生情感上的親近與憎惡,從而實現教化目的。可以看出,高特舍德在傳統修辭學意義上理解情感的教化功能,即通過操控受眾的情感來影響其判斷力。早期啟蒙詩學仍然沿用傳統修辭學情感學說的認知框架。悲劇情感只是在理性認知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接受真理的替代手段。悲劇的審美效果歸根到底并非不可替代,也不具有獨立價值。
與高特舍德同時期的法國人杜博提出的感覺主義美學將情感從倫理規定中解脫了出來。杜博認為,精神的無所作為會產生無聊,這對精神而言是最大的痛苦。激情是含有巨大能量的感知,它奪走靈魂的無所作為,因此,即便是令人痛苦的激情也能給靈魂帶來愉悅。悲劇快感源于此,杜博還強調,這一愉悅感與道德判斷無關。所有藝術門類都只對人的感官感知產生影響,并不與道德價值領域發生直接關聯,也不涉及理性判斷。藝術的首要目的不是為了傳播倫理道德知識,而是為了激蕩人的情感而產生愉悅感。悲劇作家的首要任務就是以精準的心理刻畫呈現激情的真實狀態。
杜博的感覺論,尤其是他提出情感具有獨立于道德的審美價值,是尼可萊論文《論悲劇》的指導思想。18世紀中期正是感覺論哲學在德國方興未艾,與理性主義哲學激烈交鋒之時。德語區啟蒙運動也出現了人類科學轉向。如何定位情感,成為構建現代個體的重要議題。敏銳捕捉到新動向的尼可萊希望用感覺主義美學理論來匡正悲劇詩學。尼可萊宣稱,悲劇無需考慮道德教化,只需激發觀眾的激情。如果觀眾的精神能夠在劇烈的悲劇情感震蕩之中感受到愉悅,悲劇的目的便已實現。尼可萊指出,高特舍德將悲劇視為道德說教的工具,是造成德國悲劇品質低劣的根源。悲劇作家不要期待通過刻畫美德的崇高與惡人遭受報應讓觀眾熱愛美德、厭棄邪惡,反而要利用觀眾原有的道德稟賦來激發他們相應的情感。
為證明悲劇無法完成教化作用,尼可萊區分了悲劇人物感受到的激情和觀眾感受到的激情。傳統修辭學的情感學說完全沒有區分這兩類情感,修辭學效果學說的根基恰恰在于情感的可傳遞性。如果沒有18世紀上半葉美學與心理學對于情感認知功能的強烈興趣,尼可萊的這一區分是難以想象的。而只有區分了這兩類情感,對悲劇情感的理解才能脫離傳統悲劇詩學的窠臼。尼可萊觀察到,悲劇人物的情感并不能原封不動地轉移到觀眾靈魂的感性部分。觀眾被悲劇激蕩起來的情感與悲劇人物的情感并不相同。因此,尼可萊得出結論說悲劇不可能用來改善觀眾具體的激情。比如觀眾不可能通過觀看《美狄亞》學會克制自己的嫉妒與復仇之心。
尼可萊的論文為他的兩位好友——此時已在德國哲學界與文學界嶄露頭角的門德爾松與萊辛——提供了討論悲劇情感的契機。三位朋友都意識到,悲劇情感的引發絕非為了以感性方式闡明道德道理,也不是借情感進行勸服的修辭學策略,而是一種植根于感性認識能力的靈魂活動。門德爾松和萊辛躍躍欲試,希望運用“前沿學術成果”重新闡發悲劇情感現象。三位朋友的通信后來成為啟蒙悲劇詩學的經典文本《關于悲劇的通信》。
二、情感與認知
作為理性主義哲學家的門德爾松最關注的是悲劇情感的認知功能。
萊布尼茨按照觀念呈現的清晰程度,將靈魂獲取的認識劃分為唯有通過理智才能獲得的“清楚認識”和僅有感官和想象力參與的認識活動所能獲得的“明白卻模糊的認識”。沃爾夫承續這一認知框架,區分了靈魂的上層與下層力量。感性情感屬于下層靈魂力量,愉快的情感是對善的不清楚認識,不愉快的情感是對惡的不清楚認識。可見,情感具有認知功能,是對善惡的模糊表象。然而,要保證倫理行為為善,就必須保證對善有清楚明白的認識,這一點卻只有靈魂的上層力量也即理智可以達到。靈魂的感性部分(情感與想象力)是有缺陷的認知力,并不能成為道德原則的牢靠根基。
門德爾松認為,觀眾在觀劇過程中沉浸在戲劇營造出來的幻覺里,會接受戲劇詩人建構的虛擬世界的邏輯,包括其道德判斷。此時,靈魂的上層力量會自動停止運轉,只讓靈魂的下層力量來發揮判斷功能。悲劇激發觀眾產生的悲劇情感,是觀眾的靈魂下層力量對戲劇人物所做的道德情感判斷,被門德爾松稱之為“戲劇倫理”。問題在于,虛構世界里的邏輯很可能是錯誤的,只是被詩人巧妙地掩飾了起來。如果未經理性推理驗證,靈魂下層力量很有可能會被詩人虛構出來的虛假道德迷惑。因此,觀劇時道德感覺作出的道德判斷和(現實生活中)理性推理得出的道德判斷并不一定一致。一旦戲劇結束、幻覺消失,理性(靈魂上層力量)自動重新掌舵,道德感覺會自動服從理性的判斷。按照理性主義哲學認識論,正確的道德觀只可能建立在理性推理的抽象符號認識的基礎上。但悲劇能感動觀眾、激發觀眾激情的前提卻是:放棄理性判斷,完全沉浸在幻覺營造起來的戲劇世界里。可見,在門德爾松看來,通過悲劇來培養觀眾形成正確的道德觀非但沒有必要,而且根本無法現實。
就悲劇應當激發情感而并非闡明道德道理而言,萊辛完全贊同兩位朋友的立場。然而萊辛從通信一開始就堅持悲劇激發激情并非悲劇的最終目的。悲劇的最終目的仍然是道德教化,并且是以悲劇情感為手段。不過,萊辛對悲劇情感作出了嚴格的界定。
首先,萊辛區分了悲劇激蕩觀眾心靈的不同層面:悲劇人物的激情轉移到觀眾身上的次生情感與悲劇在觀眾身上激發的悲劇情感。前者是悲劇快感的來源(觀賞劇中人物令人不快的悲慘遭遇也會激發愉悅感)。萊辛使用共振琴弦的比喻闡釋了這一現象:正如一根琴弦的劇烈震蕩會造成另一根琴弦的共振,任何情感的劇烈震蕩都能傳遞到我們身上,令我們感覺愉悅。這種愉悅的根源在于靈魂的任何運動都使我們意識到自身的“現實”,即產生自我意識。接著,萊辛區分了這種“共情”與他視為唯一悲劇情感的“同情”。觀眾不可能同樣強烈地感受到悲劇人物所感受到的激情,因為觀眾缺乏悲劇人物產生激情的前提條件。萊辛甚至認為“共情”就強度而言根本算不得情感。在這個意義上,審美愉悅與悲劇教化功能完全無關。萊辛在認同尼可萊對悲劇情感區分的同時,也將悲劇快感排斥在他的關注點之外,客觀上杜絕了同情這一悲劇情感陷入重情主義式自我陶醉的危險。
萊辛在通信里多次提到,觀眾感受到的激烈情感是對悲劇人物不幸遭遇的情感反應。而在悲劇激發的眾多激情中,萊辛認為只有同情具有道德教化作用,因此他宣稱同情乃是悲劇應該激發的唯一激情。至于為何同情本身就具有道德性,萊辛給出的理由是:“最富同情心的人是最好的人……誰使我們具有同情心,誰就使我們變得更好、更有美德。而激起我們同情心的悲劇也就會使我們變得更好、更有美德……”這其實并非通常意義的論證。不過很明顯的是,當萊辛將同情直接等同于美德時,他并不是從理性主義認識論出發來定義美德的。蘇格蘭道德感學派對人自發的自然本性給予了更多信賴,認為它并不低于理性的判斷和推理能力。相反,理性反倒是實現道德感決斷的手段。就同情本身蘊含道德因素而言,萊辛的同情觀更接近道德感學派。
萊辛信賴同情作為情感的判斷即為正確的道德判斷,認定只要培養人皆有之的同情心,人自然就會向善,甚至不要理性的匡正,“同情直接教化人,無須我們自己參與;它既教化有頭腦的人,也教化傻瓜”。即便詩人誘惑我們對錯誤對象產生同情,即門德爾松所謂的虛假的戲劇倫理,也無損同情本身的道德性。萊辛甚至提出,悲劇訓練產生同情的能力,培養出觀眾同情的“習性”,就已經改善了我們的道德稟賦。在德國理性主義啟蒙哲學語境下,“習性”指的是通過不斷反復與刻意訓練,將有意識的理性認識轉換到無意識層面,從而實現理性對身體以及情感實施更有效的操控。萊辛認為同情本身也可以進行訓練而形成習性,從而轉化為道德稟賦,成為道德性格的一部分。可見在他看來,同情具有與理性同樣的道德可靠性。
門德爾松對此顯然無法認同。在“悲劇通信”結尾,他仍然追問,如果沒有理性的檢驗,我們如何保證同情的對象是真正的而非虛假的善?兩位朋友對于情感是否具有認知功能,從而是否可以成為美德這一問題,最終也未能達成一致。
然而戲劇作家萊辛似乎并不愿在作為情感的同情是否具有認知功能這個哲學問題上繼續糾纏下去。反倒是門德爾松的一句玩笑引發了萊辛的強烈反應:門德爾松要求萊辛向驚嘆這一“美德之母”道歉,因為萊辛竟然認為驚嘆不能算激情,不過是同情的間歇,目的是使得同情可以持久。兩人關于“驚嘆還是同情”的爭論貫穿整個通信。實際上,取同情舍驚嘆,才是萊辛對于悲劇以及悲劇理論的真正興趣所在。
按照萊辛的定義,觀眾悲劇激情的對象是悲劇人物的不幸本身,那么同情或驚嘆的差異就在于悲劇應該塑造什么樣品格的主人公這一問題上。簡單來說,如果悲劇主角絲毫不以自己的不幸為苦,則會激發觀眾的驚嘆;如果主角哀嘆自己的不幸,則會激發同情。門德爾松與萊辛關于驚嘆與同情孰高孰低的爭執折射出,在18世紀中期不僅認知結構的等級體系出現了松動,生活世界與價值世界的等級體系也開始出現震蕩。
三、驚嘆抑或同情
門德爾松與萊辛對驚嘆與同情價值高低的分歧,其源頭需要追溯到萊辛同情觀的另一個理論來源:門德爾松在《關于感覺的通信》里對“同情”的定義以及在《致萊比錫萊辛碩士的公開信》里對盧梭“同情說”的批判。
在完成于“通信”之前的美學著作《關于感覺的通信》里,門德爾松其實對同情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認為同情是一種混合了愉快與不快的情感,是悲劇情感里唯一產生愉悅的痛苦情感。愉快是源于因對象的完善而產生的愛,不快則是看到被愛對象無辜遭受不幸。不幸更烘托出被愛對象的完善,增加了愉快感的程度。理性認知力越發達、文明程度越高,就越能更好地意識到對象的完善,從而體驗到更多的愉悅。
盧梭的同情則與對象的完善程度無關,針對的是“弱者、罪人和整個人類”,是一種前理性與前文明的自然情感。一切智識與文化上的進步和文明的成就并不增強、反而削弱了同情這唯一的自然美德。與理智相對的同情成為盧梭批判社會的武器。自然的、真正的人,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是這個自私自利的文明社會的明鑒。
門德爾松認為,盧梭將同情定義為“因別的造物的脆弱而產生的不快”,誤解了同情的真正結構。萊辛認同門德爾松從理性主義完善學說出發對同情的定義:同情必定基于對同情對象蘊含的偉大完善,因而同情并非徹底的前理性情感,而是以能夠識別完善的認識能力為前提。然而這卻并非萊辛同情觀的核心。萊辛和盧梭一樣,認為同情的關鍵在于對同情對象展露出來的脆弱所抱有的不忍之心。它并不是理性認知的成就,而是源于前理性的自然情感。事實上,萊辛將同情視為最根本的美德、是一切社會美德之來源的說法,就取自門德爾松在《公開信》里對盧梭同情觀的總結。
同情與驚嘆都是觀眾對悲劇人物的不幸遭遇的激烈情感反應。如果說引發同情的契機是悲劇人物暴露出來的脆弱,那么引發驚嘆的契機就在于悲劇人物對人性脆弱的克服。在門德爾松看來,驚嘆的發生,不僅基于對象的完善,并且這一完善還超出了自然天性的界限,通常表現為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同情的對象則以深陷困頓為苦,顯露出人的軟弱。就道德完善程度而言,驚嘆的對象要高于同情的對象,因此驚嘆是比同情更高的悲劇情感。
門德爾松堅持“驚嘆”作為更好的悲劇效果,也有其思想史背景。他多次提到,最能體現悲劇人物非凡品質的是,悲劇英雄在面對厄運時仍然保持內心的從容。這種心緒狀態類似于斯多葛主義的道德理想“不動情”。它表明心靈只依靠理性的判斷力,不受任何外部偶然因素的干擾。在查爾斯·泰勒看來,這種將意志主宰激情視為德性的新理解,是世俗化過程中人類中心主義轉向的一個明顯標志。門德爾松視為超凡美德之標志的“視死如歸”等品質,代表著意志“對身體以及產生于身體和靈魂之結合的事物領域(特別是激情),實施至高無上的控制”。然而,門德爾松宣揚的“不動情”有著迥異于傳統斯多葛主義的人類學前提。斯多葛主義視激情為錯誤的意見,18世紀的道德理想則十分重視激情的作用,更強調意志對激情的完全把控。歸根到底,門德爾松推崇的真正美德是道德意志的自決與自由。只有在感官欲求與理性道德決斷的劇烈沖突中,悲劇主人公方能顯出他抵擋外界加諸自身影響、貫徹理性道德主張的強大意志力,彰顯出道德主體的自主與自律。英雄悲劇也因此成為體現啟蒙道德主體之自主性的理想藝術媒介。
相比之下,同情則是截然相反的美德。如果說意志對激情的絕對把控外顯為“不動情”,那么同情的“動情”,恰恰顯示出心靈還會因外界因素而產生干擾理性判斷的情感,尚不具備對身體的絕對把控。斯多葛主義哲學蔑視同情或憐憫,正是因為它反映了主體能動者意志掌控力的薄弱。在斯多葛式哲學家看來,因不忍心同胞受苦而心生同情,不如內心毫無情感波動的扶貧救弱。萊辛對于意志自由一向并無太高評價,在“通信”中更是將它貶稱為“固執”,并宣稱,一切引發驚嘆、顯示出克服普通人性的英雄主義品質都應當排除出悲劇之外。他用半揶揄的口吻說道,門德爾松的確對人性(的軟弱)了如指掌,深知如此克服了人性軟弱而彰顯道德意志絕對自主狀態的道德楷模乃是“麻木的英雄”,他們早已超出人性范圍,是“美麗的怪物”而不再是“好人”了。
針對門德爾松提倡自塞內卡至高乃依的英雄悲劇傳統,萊辛提出以古希臘悲劇作為典范。古希臘悲劇讓所有英雄人物都卸下英雄軀殼,哀嘆自己的不幸。悲劇主人公的堅毅性格只應使他不至于不體面地毀于不幸。悲劇應該著力刻畫的,恰恰是一個仿佛在某一刻有能力對抗命運,卻在下一刻再度陷入痛苦、對人性的脆弱有著切膚之痛感受的英雄。
四、萊辛的“同情—恐懼”詩學
在距通信十年后的《拉奧孔》里,萊辛通過分析索福克勒斯的悲劇《菲羅克忒忒斯》,詳細論述了悲劇應當塑造什么樣的英雄人物來觸發觀眾的同情。
《拉奧孔》第四章處理的問題是詩(文學)為什么可以表現肉體痛苦。溫克爾曼在《論希臘繪畫和雕刻作品的摹仿》中將拉奧孔與菲羅克忒忒斯(以下簡稱菲氏)相提并論,認為兩者都默默忍受著痛苦,顯示出靈魂的偉大與沉靜。萊辛指出,索福克勒斯筆下的菲氏非但不像溫克爾曼所說的那樣默默忍受劇痛,反而因不堪忍受疼痛而發出長時間嚎叫。
偉大的靈魂能否表達肉體痛苦?這一問題實際上延續了“悲劇通信”時期他與門德爾松的爭論。在《拉奧孔》里,萊辛論述道:希臘人認為,因身體的極端痛苦而發出哀號,可以與偉大的心靈相容。古人從不因自己作為凡人而有的人性局限(最為鮮明地體現在身體上)而羞慚。從效果美學來看,只有英雄也虛弱到表達出自己承受的痛苦,才會引發觀眾對他的關切,激發觀眾的同情。
菲氏寧可繼續忍受痛苦而不改其決斷,表現出“堅韌”這一斯多葛哲學美德。然而,萊辛認為堅韌美德并不適用于任何與被動承受相關的方面。“痛苦的表現往往并不出于自由意志,而真正的勇敢只有在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動上才可以見出”。如果將自由意志理解為心靈對身體與激情的把控,萊辛顯然認為其把控不應該是絕對的。必須承認身體作為物質,在受到外物刺激時會產生相應的反應,靈魂只能被動接受而無法主動掌控這一反應。文明對情感的規訓與壓抑,尤其對于那些受外界觸發的情感的扼制,在萊辛看來反而是一種“野蠻”。身體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應當允許身體順從自然的要求,在承受外界施加的痛苦時發出哀怨。
他的哀怨是人的哀怨,他的行為卻是英雄的行為。二者結合在一起,才形成一個有人情味的英雄。他既不軟弱,也不剛硬,而是在服從自然的要求時軟弱,服從原則和職責的要求時剛硬。他是智慧所能造就的最高產物,也是藝術所能摹仿的最高對象。
意志應該使人按照道德律令行動,但在遵守道德原則的同時卻沒有必要強制壓抑人被動而天然的情感流露。“有人情味的英雄”甚至超越了藝術門類的界限,被萊辛視為一切藝術門類所能摹仿的最高審美對象,同時也是最高的倫理理想。
可見,萊辛提倡同情詩學的根源,乃是要提倡一種完全不同于強調理性靈魂對身體與情感實施絕對把控的二元對立人性觀。萊辛提倡的人性觀既承認理性按照道德原則控制身體與情感,也承認身體同時屬于自然,具有無法被精神滲透的屬性。每個個體受到自身稟賦、所處時代,乃至人作為有限造物的類屬局限,永遠無法擺脫“心的自私自利狀態”,不可能達到“因美德自身的緣故而去熱愛美德的心靈純凈狀態”。人的這一局限性,不僅是萊辛詩學思考的出發點,也是他晚年宗教哲學、政治哲學思考的出發點。正是基于對自然天性的重視,萊辛重新發現了“恐懼”這一悲劇情感。以至于有研究認為,《漢堡劇評》時期萊辛的悲劇詩學應該稱之為“同情-恐懼”詩學。
亞里士多德提出,唯有擔心某種厄運會降臨到自己頭上從而心生恐懼的人,才會在看到與自己相似的人遭受類似厄運的時候對他產生同情。因此,恐懼又可以被理解為是對自己的同情。在“悲劇通信”時期,萊辛認為恐懼由同情衍生而來,在《漢堡劇評》里,萊辛開始強調“恐懼”的獨立作用,恐懼成了同情的內核:強烈的同情必然包含恐懼,恐懼卻并不必然包含同情。甚至當悲劇構建的幻覺消失之后,觀眾心中對悲劇人物的同情也立即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對類似厄運可能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的“自私的”恐懼。
萊辛以人類科學知識重新闡釋了亞里士多德的情感學說。他將“恐懼”理解為一種自我保存的“欲望”,是值得被認真對待的激情。如果悲劇想要收到良好的教化效果,就必須將人對自我保存的天然欲求考慮進來。這是萊辛對他自己早期同情觀的重大修正。一方面,萊辛并不認為人可以崇高到否認或輕視自我保存意志的地步;另一方面,萊辛也不認為人性本惡,就是無節制追求自身利益。同情不僅是對過分強大的自愛的修正,正常的自愛也是同情的必要補充。只有將同情與恐懼視為兩種不可分割、相互交融、相互關聯的情感,對他人利益的關切與自我保存的欲望、愛他人與愛自己才能同時成為可能。
五、結語
在現代乃至后現代主義眼中,啟蒙時期儼然成為以理性之名壓抑乃至扭曲感性的新“黑暗中世紀”。然而恰恰是啟蒙運動開始探索理性與情感的邊界與交融,啟蒙時代的悲劇詩學即是這一探索活動的印記。如何看待悲劇激發的激情?為了影響觀眾固有的情感稟賦,為實現悲劇這一體裁的特有目的,悲劇又應該滿足何種前提條件?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體現出啟蒙時代不同評論家對情感的不同感知與體認。
靈魂的自主性與意志的自由,是理性主義道德哲學的根基。觀眾在觀看悲劇時不由自主產生的劇烈情感對這一根基構成巨大威脅。當高特舍德的理性主義解決方案被推翻之后,門德爾松與萊辛提出了崇高美學與同情詩學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方案。
席勒的《論激情》看似追隨萊辛,批判法國古典英雄悲劇的冷漠,推崇古希臘悲劇允許表現英雄對痛苦的敏感,從而給予天性更多的空間。然而,呈現悲劇人物承受痛苦的狀態,喚起觀眾的同情,不過是為了更好地展現意志在巨大苦難面前堅持自由與自主,最終以感性形式體現“道德不受自然法則約束的獨立性”。悲劇美學沿著門德爾松提出的心靈與身體的二元對立的模式,在悲劇呈現道德主體的“不動情”、宣示“神一般的靈魂戰勝其身體的內心勝利”之中,看到悲劇的崇高道德目的。同情則被斥為“膚淺的看法”,“憐憫……是一種有限的消極的平凡感情……是小鄉鎮婦女們特別容易感受到的”。萊辛的同情詩學及其對人性界限的洞見逐漸被悲劇舞臺上慷慨赴死的英雄所遮蔽。
①⑥⑦⑧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Ausgewaehlte Werke,hg.von J.Birke u.P.M.Mitchell,Berlin,1968ff,Bd.IX/2,pp.492-500,p.494,p.317,p.495.
②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01—407頁。
③參見歌德:《亞里士多德〈詩學〉補遺》,《歌德論文學藝術》,范大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9—553頁。
④參見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王凌云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
⑤關于高特舍德的戲劇改革詳參王建:《德國近代戲劇的興起——從巴洛克到啟蒙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175頁。
⑨⑩ 參見Gert Ueding/Bernd Steinbrink,Grundriss der Rhetorik,5.Aufl.(Stuttgart,2011),p.281,pp.281-283.
?參見Elisabeth Décultot,Lessing und Du Bos,Zur Funktion des Empfindungsvermoegens in der Kunst,in Lessing und die Sinne,hg.von Kosenina und Stockhorst,Hannover,2016,pp.81-92.
?關于18世紀啟蒙文學的“人類科學”轉向,參見金雯:《啟蒙與情感:18世紀思想與文學中的“人類科學”》,《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萊辛等:《關于悲劇的通信》,朱雁冰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45、77—79、79、19—20、38、97—98、191、34—35、28、35—36、71頁。
?參見萊布尼茨:《對知識、真理和觀念的默思》,《萊布尼茨認識論文集》,段德智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91頁。
?參見Christian Wolff,Gesammelte Werke,hg.u.bearb.v.Jean Ecole u.a.,Hildesheim,1965ff,Abt.I.,Bd.2,p.23.
?參見弗蘭西斯·哈奇森:《道德哲學體系》(上),江暢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8頁。
?參見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77頁。
?Mendelssohn,Sendschreiben,in:Gesammelte Schriften,Jubilaeumsausgabe,hg.von Alexander Altmann u.a.,Berlin:Frommann,1929ff,p.86.
?參見查爾斯·泰勒:《世俗時代》,張容南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36頁。
???萊辛:《拉奧孔》,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9、30頁。
?萊辛:《論人類的教育》,劉小楓選編:《人類的教育:萊辛政治哲學文學》,朱雁冰譯,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頁。
?參見Jutta Golawski-Braungart,Furcht Oder Schrecken:Lessing,Corneille und Aristotles,in:Euphorion,1999,93,p.417.
?參見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227頁。
?參見萊辛:《漢堡評劇》,張黎譯,華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頁。
?席勒:《論激情》,張玉書譯,《席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頁。
?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