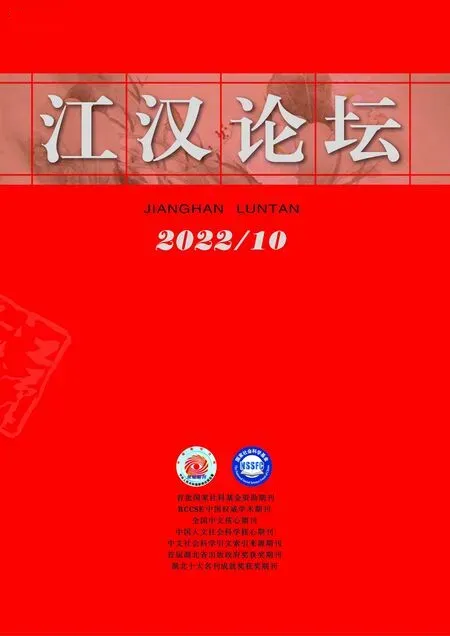從機器發現視角探討人機共生關系
——兼論赫伯特·西蒙機器發現觀
李寧寧 宋 榮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1916-2001),又名司馬賀,他被稱為“文藝復興式”的學者,原因是他在人工智能、科學哲學、認知心理學、管理學等多個領域享有盛名,同時他也是我國首批外籍院士之一,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情誼。機器發現(machine discovery)是西蒙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在70年代末開始廣泛應用于天文學、醫學、化學等眾多領域。西蒙擅長用數學、計算機科學等現代科學來科學化、步驟化地研究社會科學和哲學,而機器發現就是這樣一種研究工具。機器發現用計算機程序模擬科學發現中科學家的思維過程,不僅讓科學發現成為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也為探究人類思維打開了新思路,更為探討人機共生關系提供了新視角。
一、機器發現:讓科學發現成為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
機器發現觸及到了科學哲學界沉寂百年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問題。科學發現有無邏輯的問題一直是科學方法論和認識論的核心問題。從亞里士多德的歸納—演繹模式,到培根的歸納主義模式和笛卡爾的演繹主義模式,再到皮爾士的溯因推理模式,學者們都在尋找獲得科學知識的可靠方法,認為存在某些規則可以使自然的規律有跡可循。但是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陸續有哲學家如惠威爾(William Whewell)、席勒(F.C.S.Schiller)、亨佩爾(Carl G.Hempel)等試圖將科學發現驅逐出科學哲學的研究范圍。他們從科學發現和科學驗證的區別著手,認為科學驗證才應該被科學地研究,而科學發現本身帶有神秘主義色彩,應該逐出科學哲學討論范圍。他們的觀點也得到了眾多邏輯經驗主義者如石里克(Moritz Schlick)、卡爾納普(Paul R.Carnap)等的支持,后者合力將科學發現推入社會學、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于是,之后的一百多年里科學哲學關注的核心問題發生了轉移,從科學發現邏輯問題轉變成科學理論的檢驗和驗證問題,而科學發現甚至被排擠出哲學范疇。
直到20世紀70年代,漢森等學者開始為科學發現的合法地位辯護,探索規范性發現理論的可能性。漢森借助理論滲透(theory-loaded)理論提出探討“科學理論的起源應該與檢驗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強調發現模式的重要作用。西蒙則在漢森發現哲學的基礎上,從啟發式搜索和經驗觀察(或者說驗證)兩個角度論證了科學發現的邏輯性以及科學發現作為認識論研究對象的合法性。他將關注點放在描述和解釋科學發現上,認為如果成功地對發現作出可信的解釋,那么“解釋本身將構成對規范理論的最大的近似”。西蒙極力將科學發現納入科學哲學的研究范疇,將機器發現作為科學發現的計算機思維模式,成功地用計算機模擬了歷史上經典的科學定律。至此,科學發現有了標準化、可操作的建模方案。
西蒙的研究主要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將科學發現看作是問題解決的特例,第二步則是利用機器發現程序重現歷史上具體的科學發現。
西蒙認為“科學發現就是問題解決”,即科學發現的機制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一般機制的特例而被包含在內,也就是說可以從問題解決理論中推導出來。西蒙的這個看法隱含著一個假設,即不區分庫恩所謂的正常科學和革命科學,也沒有高創造性工作和低創造性工作之分,它們本質上都是一致的,都是逐步解決問題的過程,亦即“在大問題空間中搜索未完全定義的目標對象”。科學發現具有問題解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體現在科學發現的方法與普通問題解決的方法都依賴啟發式法,“一種最小化努力的概念”,由此得到的結果雖然不是最精準的,卻是在使用腦力成本最小、工作量最少的情況下得到的性價比最高的決策。啟發式法是人類問題解決的核心環節,而機器發現也正是利用了這一方法才實現對科學發現的重現。特殊性體現在科學發現呈現出的社會性、連續性、累積性、創造性中。將科學發現置于這樣一種關系中不僅可以利用人類在問題解決中積累的大量的知識,還能夠滿足我們對節儉(parsimony)的渴望,最大限度地降低發現工作被視為人類特殊能力的程度。
在計算機出現之前,科學發現有無邏輯更多地停留在思辨階段,而計算機的使用則讓發現研究有了具體的實現手段和標準,科學哲學家可以借以測試他們的理論并觀察機器的行為。就像達文波特(Thomas H.Davenport)指出的那樣,人類的某種智能行為一旦被拆解成明確的步驟、規則和算法,它就不再專屬于人類了。而作為高級人類智能的科學發現就在這樣的拆解中具備了被計算機占領的條件。諸多經驗證據表明計算機模擬已經是建立科學發現過程的計算理論的有力工具,當然反過來這又能更好地理解人類科學家的發現過程。
科學發現回歸科學哲學研究領域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科學發現如何成為一個可以被研究的問題。西蒙從計算機的角度回答了這一問題,他用機器發現的重大成功詮釋科學發現的標準化、理論化,去除了科學發現的神秘光環,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科學發現的新視角。機器發現不僅引領了科學方法論的變革,也讓人類對思維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
二、機器發現:從機器視角探索人類思維
機器的本質即是對人類勞動能力的延展。傳統機器作為生產工具承載了人類的意志和功能,是人的勞動器官的延伸;而智能機器除了具備傳統機器的工具性之外還具有了主體性,即將人的思維和智力也外化在了機器上。所以從機器視角探究人類思維的奧秘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人與機器的關聯。
西蒙將人類思維和計算機都置于物理符號系統假說之中,認為既然兩者都是物理符號,那么計算機就可以用于探究和模擬人類思維。當我們談論使用計算機來模擬人類思維時,更多地是指在計算機的幫助下,模仿人類在解決各種問題時大腦中實際發生的思維過程,也就是說機器發現的前提是要剖析人類的發現過程和思維模式,然后將此過程用計算機進行模擬或重現。
對于機器模擬人類思維過程的問題,我們可以將其分解為兩個問題進行探討,一是人類思維的本質是什么?二是計算機何以可能模擬人類思維?
西蒙認為人類思維是一個有層次結構、連續執行的符號操作過程。人類通過遺傳和與世界交互,獲得有效地指導思維過程的程序,即人類思維通過程序的形式被有效地表達出來,或者說,人類思維的本質即程序。當然,西蒙的這一看法遭到了德雷福斯等諸多學者的批評,引發了關于機器思維和人類思維本質的熱烈討論。目前對人類思維的解釋主要有三種,即符號解釋、神經解釋和具身解釋。符號解釋從功能模擬出發,主張用符號表征世界包括人類思維,這樣便于用計算機進行運算和操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發現中大部分都是隱性知識在起作用,而隱性知識無法通過明確的推論獲得,也無法明確表述。很多科學家無法解釋自己是如何獲得科學發現的,于是總是訴諸“靈感”或者“頓悟”,那么對于這些無法言明的思維過程應該如何形式化才能被計算機所捕捉和模擬?這些問題導致機器發現在形式化難題、意向性難題中掙扎。神經解釋從結構模擬出發,用神經網絡模型來代替計算機隱喻,雖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符號解釋的機械主義傾向,但是人腦的神經網絡錯綜復雜很難精確地被模擬,并且在高層次認知問題上功效式微。科學發現過程中神經網絡的具體工作模式是怎樣的,哪些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等依然是需要不斷被探究的問題。具身解釋與前兩種解釋最大的不同在于看重身體對思維形成的參與過程,主張用“肉身化的主體”替代笛卡爾派的“意識主體”,把身體當作為經驗的主體,不同的身體傾向于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
關于人類思維的這三種解釋,無論哪一種都讓我們離對其本質的了解更近一步。就像西蒙說的,我們對思維的無知并不在于采用何種解釋方式,而是沒有找到解釋之間的聯系,比如我們不知道思維的基本符號過程是如何在大腦中生理性地完成的,那么未來我們可以探尋的一個方向則是,信息加工理論假設的符號是包裹在神經現象之中的,而計算機則是研究這一方向的強大工具。
對于第二個問題,計算機何以可能模擬人類思維?綜合西蒙的觀點可歸納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計算機的程序語言與人類思維過程都是對符號和符號結構的操作,二者都被置于物理符號系統框架內,只要是能被符號所表示的就能夠被計算機運算,從而程序語言就可直接模擬和刻劃人類思維過程并對其進行科學化探討;第二,人類的思維過程是一個動態過程,科學家也曾尋求像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數學模型方法進行建模,但是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數學模型,再加上人類的思維和行動也并不需要數學化,而信息處理語言以符號結構而不是數字作為變量就恰好迎合了這一點。西蒙以物理符號系統假說為基礎的認知心理學帶領我們認識人類的思維,最終用計算機程序語言精準表達出來,首次實現了人類思維的科學化研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從符號系統的角度來尋找對人的智能行為的解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別是在問題解決、概念理解和長期記憶方面,符號操作模型占據主導地位;第三,既然人類思維和計算機執行程序,本質上是同一的,則計算機就完全可以模擬人類思維。
機器發現在從機器的視角探索人類思維的過程中涉及兩個重要的哲學問題,即機器思維和人類思維的問題,而正是機器思維問題的出現才讓我們更加迫切地想去了解人類思維的本質。機器發現對于思維的探索本身并不是一個理論思辨的過程,而是實踐的過程。機器發現從具體的科學史案例出發剖析人類的發現過程和思維模式,然后將此過程用計算機進行模擬或重現。這一研究方法雖然出現了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是這并不能遮蓋它作為一個新的研究方法的重大的影響力,它讓人類思維變得可操縱、可模擬,縮小了人與機器的差異,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加速了智能革命的進程。
三、機器發現:加速人機共生進程
(一)人機關系的演化
在西方,古希臘以降,人是萬物的尺度、人類中心論、人是目的等都將人放在了世界的中心,人類擁有主動權來操縱自然滿足物欲,技術和機器作為不可或缺的媒介用來縮小人類力量有限性和欲望無限性之間的差距。機器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機械化、自動化、智能化的過程,機器與人的關系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變化。
最初的機器誕生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用機械技藝代替人的手工勞動,將勞動者的手解放出來。馬克思已經看到機器開始從手工勞動時期的器官性工具轉向本身變成能工巧匠,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了自己的靈魂。馬克思對機器的研究并沒有停留于機器本身,而是將機器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視角來進一步研究,從相對剩余價值、固定資本、異化勞動三種視角來看待機器,這也就是馬克思視域中的人機關系。
計算機誕生之后,利克萊德(J.C.Licklider)在諾伯特·維納的人機交互和圖靈機器智能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機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的概念,認為計算機與人類大腦是一種耦合性關系而不是替代性關系,人和計算機能夠合作進行決策和控制復雜情況,而無需依賴預先確定的程序。達文波特則進一步提出人機共生是機器和人互相增強的發展趨勢,人機共同工作,是一種合作伙伴的關系。所以,本文認為現在以及未來的人機關系更多是以人機共生為主要模式,而人機共生最顯著的特點是人變得機器化,機器變得人性化。
人類的機器化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類身體的機器化。人不再只是血肉之軀,而是將機械裝置納入身體之中從而實現身體功能的延伸。比如通過腦機結合、芯片植入等手段,人在未來也可能輕松具備目前計算機所擁有的運算速度、精確性以及存儲共享能力。另一方面是人類思維的機器化。隨著機器滲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模式開始程序化,甚至人類思維的形成也離不開技術和機器的參與。但是也有學者指出,隨著計算機接手更多的任務,人類自身的各種技能將加速退化,而成為智能體系的“旁觀者”。但本文認為這些退化的技能正是科技在為人類核心技能作選擇,科技進步本身就是要解放人類,而不是讓所有技能都集于人類自身。
機器的人性化是指機器作為科學和技術的物化形式,不斷迎合人類的需求,開始朝著情感交互的方向發展。未來的機器可能不再是單純的人工物,而是具備人格化特征,社會機器人(social robots)的出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社會機器人主要是指機器人不再只是“工具”角色,而更多的是“社會伙伴”角色,它們的工作領域已經進入如教育、醫療、商業等復雜的社會環境之中。
從最初作為延展人手功能的石器,到今天作為延展人腦功能的人工智能,在機器完成了高強度、重復性、危險的工作之后,當情感性、智能性、類人性已悄然滲入機器之中,進而轉入到人類核心價值的科學發現這一最高智能領域時,人機共生關系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二)機器發現爭論焦點的轉移推進了人機共生關系的探討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機器發現爭論的焦點從存在性走向了關系性,其中人機關系的探討則最為熱烈。20世紀70—90年代,BACON等機器發現程序的出現和應用將機器發現主要討論的問題集中在存在性問題上,即機器發現是否可以作為科學發現的計算機存在方式。而無論是邏輯實證主義者否定科學發現的邏輯,還是西克森特米哈伊(M.Csikszentmihalyi)等心理學家否定機器發現的創造性,亦或是布蘭尼根(A.Brannigan)認為發現和學習被機器發現混淆,都不過是從不同角度否定機器發現存在的合理性。
針對存在性爭論,西蒙等學者從多個角度進行了辯護。第一,從科學發現的表現形式來看,存在多種科學發現的形式,比如發現新事物、創建新理論、歸納新規律、表征新問題等,而機器發現則可以看作是利用新儀器對發現的表征和描述方式的創新。還必須明確的是能稱之為發現的都是從已知的組件中生成的,是歷史的累積的過程,而不是憑空的、飛躍式出現的。第二,從機器發現的本質看,計算機程序和物理學、化學中的那些理論具有完全相同的邏輯結構,都是差分方程或微分方程,而且對于所研究的系統的任一現有狀況,這種理論都能預見到其以后的情況。第三,從經驗上看,BACON等程序實實在在地再現了歷史上的發明的符號方法,且與人類科學家們使用的方法相似。第四,從創造性角度看,很多學者認為機器只不過是執行人類的程序設定,毫無創造性可言,或者認為創造性是人類社會文化進化的產物,無法進行復制,但是隨著人工智能的不斷發展,已經出現了很多能夠自我創造的程序和產品,比如深度學習就是機器自我管理和控制的過程。西蒙則將創造性看作一種問題解決和識別的能力,那么機器發現只不過是用計算機手段進行問題解決,人類和機器的創造力都是依賴于解決問題和識別問題的能力。第五,從發現和學習的關系來看,西蒙認為它們在人工智能領域中的區別通常是不明顯的,也就是說許多機器學習系統同時也是發現系統,機器學習領域中的大量的研究工作實際上就是面向機器發現,它們一定程度上是等價的。機器發現的存在性受到非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的壁壘,隨著技術的不斷突破和成熟,學界對存在性問題的爭論將日漸式微。
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機器發現技術的提升和應用日益增多,爭論熱點開始向人機共生關系轉移,主要代表人物有瑪格麗特·博登(Margaret A.Boden)、安德烈·萊溫斯塔姆(Andrzej Lewenstam)、勞爾·瓦爾德斯·佩雷斯(Raúl E.Valdés-Pérez)。博登談及了機器發現與同行評審的關系問題,她認為同行的預選和評價并不都是科學的,而是社會化的,經常會涉及到科學分歧和不確定性,所以機器發現的評估無法建立,只有人類的評估才能被接受。西蒙針對博登的這一觀點進行了三點反駁:第一,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已經相信計算機的判斷更精確;第二,人的標準也會隨著社會等不同影響而發生變化,機器程序設定出來的東西對人類的審美標準也會有影響;第三,機器進入我們的社會已經對我們的品味和我們的價值判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難說所有這些變化都是人類機器發明家和建造者的思想和意圖,所以,機器已經成為談判者協會的一員。萊溫斯塔姆則從人與機器的伙伴關系角度提出,計算機從工具設備變為合作伙伴,提升了經驗資源和工作效率,增加了我們進行科學發現的機會。但是計算機采用的“理性”方法與科學家在實際中采用的“直覺”方法是不同的,這可能會使機器發現愿景難以實現。西蒙則不認為人類的“直覺”方法與機器的“理性”方是不同的,相反,機器發現的全部可能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在計算機程序中加入類似于易犯錯誤的人類直覺和人類狡猾(cunning)的能力。瓦爾德斯在談及人機協作問題時,肯定了計算機在創造性科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認為社會因素的影響會拖慢其實現的進程,尤其是科學家們排斥計算機作為創造性的合作者。許多科學發現系統的構建者在非正式報告中敘述,他們在科學發現實踐中插入計算機程序遇到了阻力甚至敵意。但是瓦爾德斯和西蒙都始終相信對機器發現的抵制最終會過去,因為科學不再被人類中心主義地視為人類的創造和財產。
隨著對人機關系的熱烈探討,越來越多哲學家、心理學家認同機器的伙伴型關系,這已經呈現出人機共生關系的雛形,只不過礙于技術的滯后性,人機相互增強的手段還并未得到充分開發。從人機關系史的演變中我們可以看到,機器一直都是推動人類增強的關鍵力量,從最初的機械增強到現在的智能增強,從人類主體化到人類客體化,機器在增強人類的同時,自身也在人類的需求和改進中不斷升級,從輔助走向共生。但與此同時,機器作為一把雙刃劍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異化現象,這不禁讓我們重新審思人機共生時代人的本質問題。
四、人機共生時代對人的本質的審思
當腦機接口這些侵入型技術讓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進行融合而模糊了人機界限時,當人失去主動權而淪為智能體系中的“附庸”時,我們該如何界定人的本質?本文認為這個問題應放在馬克思關系總和論中去探討。
隨著社會演變和科技的發展,人的進化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生物進化過程,而是生物進化和技術進化雙重作用下的結果。機器從嵌入人類肢體到嵌入人類大腦,人類的后人類(posthuman)時代已經在路上,所以我們已經不能單從構成性上或者肉體性上談論人的本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所以,人的本質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在實踐中產生,也會隨著實踐的深入而改變。福山也主張將人的本質納入關系總和論中,認為人的本質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并不是由基因完全決定的。
審思人類本質的前提需要先明確人的主體性地位。人工智能將類人智能主體帶到我們面前,人在向著客體化方向發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類人智能主體替代了人的主體性地位。由于人腦的精密性、復雜性、整體性等特點,現在的任何一種技術形式都無法全部把握人類智能,即使是人機共生時代都還只是局部強化,人的主體地位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并不會發生改變。人在面對技術變革時應更多地表現出積極和主動的姿態,找到合理的角色定位。達文波特認為人機共生中人類的角色應該是超越(step up)、避讓(step aside)、參與(step in)、專精(step narrowly)、開創(step forword)。找到人的角色定位才能更好地幫助人們找到人本身的意義。另外,人作為一個有限理性的主體,人腦的構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并不能解決人在現實世界遇見的復雜問題,所以需要通過技術等手段來增強人類理性,而人工智能作為當代最重要的技術在提升人類理性方面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的本質是在社會關系中得以彰顯的。人機共生時代,人將從單調、繁雜的勞動中脫離出來,機器和人各司其職,而人從事更多復歸本性之事。馬克思認為隨著機器使用規模的擴大,會出現“機器排擠人”的現象,會出現勞動力過剩、工作滿意度下降等嚴重的社會問題。與馬克思的看法相反,西蒙認為不會出現“機器排擠人”的現象。他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中就技術改革帶來的變化提出兩個不變的因素:第一,自動化和充分就業并存;第二,人力資源質量上的恒定性。也就是說我們不必擔心技術性失業和被機器人取代,因為在他看來,崗位的總量不會減少只是會結構性調整。機器的應用會造成程序化崗位減少而非程序化崗位增加,而且還會出現新的崗位,就業額與生產水平會保持一致。
人機共生時代審視人的本質還需要撥開技術異化的迷霧。技術是人類本質力量的顯現,機器發現作為模擬智能的一種尚未成熟的、顛覆性的技術形式,在對科學進程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潛藏著技術異化帶來的危險。機器發現試圖讓我們將科學發現的主動權轉讓給機器,由機器主導科學發展的方向和進程,然而未來機器做出的行為很可能是不可控的。新技術和新算法帶來的對倫理的突破性力量遠遠大于倫理對技術的束縛力量,比如已經出現的算法“黑箱”、數據隱私、主體自由意志和責任歸屬等問題。隨著社會信息化越來越成熟,就像弗洛瑞迪(Luciano Floridi)認為的那樣,人們對技術的依賴和技術對共同價值的影響都在不斷增加,而技術的影響變得越來越不透明,這才是人們惶恐的地方。技術帶來的挑戰僅用技術是無法解決的,探討技術化社會治理異化困境的出路,還需要回到技術與社會的邏輯中來。于是,拉瓦扎(Andrea Lavazza)等倫理學家試圖從技術的限制出發制定規約,但是這并不足以消除問題。無論怎樣,技術的發展都應該在倫理的框架之中,都應該以推動社會發展和人類幸福為宗旨,這也是在人機共生時代審思人的本質的意義所在。
五、結語
計算機科學一直追求技術的進步,如今機器發現已經找到了機器涉足科學發現這一人類最高智能的方法。機器發現不僅讓科學發現成為了一個可以被研究的問題,還深入探究人類的思維過程,并試圖用計算機剖析展現出來。這不僅是方法論的變革,還是認識論的巨大轉變。
在人機共生步步趨近的時代背景下,從機器發現的視角探討人機共生的問題,不僅能夠豐富科學發現理論,科學化探討人類思維,還可以從人與機器的共生關系中思考人的本質和未來技術發展的方向。
①N.R.Hanson,Patterns of Discovery: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p.4.
②P.Langley,H.A.Simon,G.L.Bradshaw,J.M.Zytkow,Scientific Discovery:Computational Explorations of the Creative Processes.,MIT Press,1987,p.7.
③H.A.Simon,P.W.Langley,G.L.Bradshaw,Scientific Discovery as Problem Solving,Syntheses,1981,47(1),pp.1-27.
④H.A.Simon,Machine Discovery,Foundations of Science,1995,1(2),pp.171-200.
⑤W.Kool,et al.,Decision Making and the Avoidance of Cognitive Demand,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10,139(4),pp.665-82.
⑥??[美]托馬斯·達文波特,茱莉婭·柯爾比:《人機共生》,李盼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9—240頁。
⑦A.Newell,H.A.Simon,Computer Science as Empirical Inquiry:Symbols and Search,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76,19(3),pp.113-126.
⑧⑩H.A.Simon,Models of Discovery and Other Topics in the Methods of Sc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268-288.
⑨D.Casasanto,Different Bodies,Different Minds:The Body Specificity of Language and Thought,Journal of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1,20(6),pp.378-383.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頁。
?J.C.R.Licklider,Man-Computer Symbiosis,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1960,1(1),pp.4-11.
?P.Dumouchel,L.Damiano,Living with Robots,M.De-Bevoise(tra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M.Csikszentmihalyi,Society,Culture,Person:A 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in R.J.Sternberg(ed.),The Nature of Creativ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325-339.
?A.Brannigan,The Social Basis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M.A.Boden,Comments on Simon’s Paper on Machine Discovery,Foundations of Science,1995,1(2),pp.201-224.
??H.A.Simon,Machine Discovery:Replay to Comments,Foundations of Science,1995,1(2),pp.225-232.

?R.E.Valdés-Pérez,Machine Discovery Praxis,Foundations of Science,1995,1(2),pp.219-224.
?參見[美]弗朗西斯·福山:《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黃立志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頁。
?[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陳高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頁。
? [美]赫伯特·西蒙:《人類活動中的理性》,胡懷國、馮科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111頁。
?[美]赫伯特·西蒙:《管理決策新科學》,李柱流、湯俊澄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1頁。
?L.Floridi,Mature Information Societies—A Matter of Expectations,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2016,29(1),pp.1-4.
?A.Lavazza,Freedom of Thought and Mental Integrity:The Moral Requirements for Any Neural Prosthesis,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2018,12,p.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