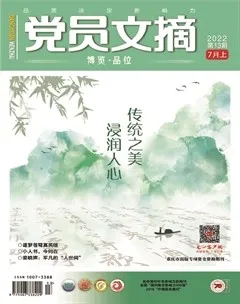“社恐”與“社牛”:社會變遷中的怕與愛
仇廣宇
“有一段時間,我根本不想要別人看到我,也不想跟外人說話。我連出門買奶茶都要穿戴好口罩、圍巾和帽子,全副武裝,要點什么飲料也是提前在手機備忘錄上寫好。”25歲的留學生Sammi這樣形容她人生中最“社恐”時的狀態。
“社恐”是“社交恐懼癥”的簡稱。如今,“社恐”已經不僅僅是心理學上的名詞,它早已變得更加泛化,成為網絡上的年輕人對自己逃避社交的一種狀態的調侃。
與“社恐”這個現象相對的是,從2021年夏天開始,一個名為“社牛”的互聯網新詞流行起來。
“社牛”和“社恐”仿佛當今社會的一體兩面,它鏡像般地折射出當今的社會生活。在80后到00后的中青年人中間,之所以會有 “社恐”和“社牛”現象,與經濟、社會的變遷密切相關。
1991年出生的山東姑娘張澤澤是名公務員。2022年2月底,她在網上敘述了自己12年的“社恐”體驗,得到了不少人的回復和共鳴。
從張澤澤的個案中,可以窺見“社恐”的年輕人究竟在害怕什么。在日常社交中,最困擾她的其實只有兩件事:一是參加單位組織的知識競賽和演講比賽時,需要拋頭露面;二是她的生活中充滿了那些必須出席的酒局、飯局,在這種場合她會如坐針氈。
生活在北京的新媒體平面設計師、38歲的阿莊也有著類似的煩惱,他在二次元世界里有多種多樣的愛好,卻不喜歡聚會,最多只和關系緊密的老友吃飯。他自稱,在生活中最讓他有“社恐”感的一件事,就是和一些中年男性共處一個空間——盡管從年齡上看,他自己也算人到中年。“他們的話題充滿了炫耀、油膩、自以為是的感覺,我很討厭這種氛圍。”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王水雄用“文化墮距”這個社會學上的概念,來概括年輕人中的“社恐”現象,尤其是他們在職場中對傳統“酒局文化”的反叛與恐懼。
“文化墮距”指的是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和科技的發展速度在前,文化習慣和社會傳統跟不上,造成二者相割裂的現象。“酒局文化”就是一個例子。對80后、90后甚至00后而言,他們多數成長于獨生子女家庭,交流的方式也與上一輩有很大不同,“酒局文化”原本在他們中間已經慢慢消淡。當這些青年人出了校園步入職場,會發現社會中還是存在著他們原本的生活經驗中接觸不多的“酒局文化”,這就造成了他們內心和外部世界的矛盾。
雖然“社恐”已經上升為心理問題,甚至為此去醫院開過藥,但很多人還是看不出張澤澤內心的恐懼。她在生活中是個活潑、健談,富有親和力的女性,哪怕和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聊天,或者電話聯系業務,對她而言都不是什么難事,“這種一對一交流反而是我很擅長的。”只要不用去公開場合展示自己,她簡直是“社牛”一樣的存在。阿莊也有自己“社牛”的一面,在為數不多的熟人面前,他就會像被噴了“社牛噴霧”一樣好起來,可以聊天,搞怪,講冷笑話,毫無顧忌。
杭州的自媒體創作者、95后唐雪也是“社恐”人士。幾年前,她開始制作視頻,在公眾號上寫文章,講述自己如何突破這種心理障礙。在她建的幾個交流群里,自認為“社恐”的年輕人爭相留下自己的經歷,天南海北的網友們和陌生人分享工作狀態、玩游戲和讀書的心得,也會有人向她傾訴“一個人待著內耗嚴重”“長時間獨處的孤獨”。通過網上交流后,有人反饋說“感覺自己(癥狀)減輕多了”。在這種交流中,唐雪幫助了別人,也治愈了自己。

從聊天記錄看,這些“社恐”在網上其實都是“話癆”,語言還很流暢甚至俏皮。可以說,在這些微信、QQ群組,抱團取暖的豆瓣小組中,他們盡情釋放著“社牛”的一面。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鄭丹丹對“社恐”現象一直有觀察。她注意到,一些人在高度競爭的職場上遇到心理困難后,會選擇一種“退縮”行為保護自己,主動退出社會競爭,不讓他人評價自己,這就引發了一系列現象。
鄭丹丹舉了一個例子,作為70后,在她成長的那個年代,如果一個女性不結婚也不愛社交,那她面對的不僅僅是社會壓力,更重要的是,在現實中她的生活會受到嚴重的影響,比如扛煤球、安裝燈泡這些粗活,對單身女性而言都會造成生活難題。但是現在,有了各種社會服務類軟件和社交軟件,此類事項幾乎都可以外包,當人們發現這些生活瑣事通過技術手段能夠解決,就會對不愛社交的人有了更多的寬容。
鄭丹丹覺得,如今人們能夠大聲說出自己是“社恐”是件好事,給自己貼上泛化了的“社恐”標簽,反而是社會進步給個人帶來的一種解脫和自由。
拒絕無效社交,作為互聯網原住民的95后甚至00后,其實表現得比80后和90后更適應,更加自洽。
“社恐”狀態對他們而言其實是家常便飯。他們甚至可以自己創造一些喜歡的場景:通過電子游戲、二次元活動等,自由自在地創造屬于自己的語言,不用理會上一代的要求與規則。
Sammi覺得自己從小內向,是天生的“社恐”,在成長過程中為了良好的教育環境又經常轉學,出國留學等,身邊的伙伴總是不斷變化,無法形成穩定的朋友關系。她身邊的很多同齡人也有類似的問題。成年后,她開發了一些拓展社交圈子的辦法。比如,她成功組織了幾個并不相熟的女孩進行“劇本殺”活動,參與者的反應都非常熱烈。
像著名科幻電影《她》中描寫的,未來世界中人類和AI談戀愛,和真人難牽手的故事,也正在“社恐”人群中發生著。
設計師阿莊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目前單身的他對戀愛這件事是積極的,也接觸過幾個姑娘,但他一直懶得見面,只喜歡“網聊”。
如何在這種虛擬交往中注入現實性,防止人們在現實和虛擬的情感之間來回切換,造成更大的不適應?王水雄建議,最好還是要在這些活動中進行一些“情感攝入”,想辦法為他們注入真實的情感能量,把他們和人類的真實情感聯系起來。
一些年輕人確實也在真實交流中逐漸走出“社恐”。過去的Sammi,會用“社恐”作為面具去抵擋長輩的“社交飯局”,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她發現這種飯局也有好處,它是一種真正的交流信息的過程,漸漸不再排斥這種場合。
張澤澤也開始努力克服自己的“社恐”,事實上她不是完全不能適應社交,她剛工作時曾經到基層鄉鎮鍛煉,當時與人的溝通能力提高了很多。
(摘自七一網 七一客戶端/《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