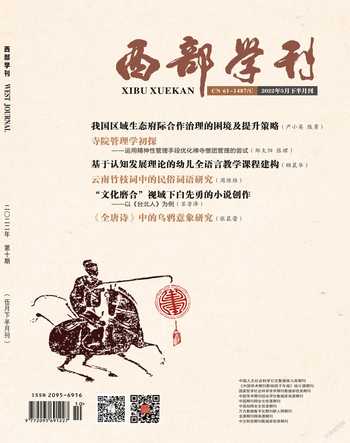試論孫中山對舊道德的繼承與發展
摘要:孫中山在傳統道德思想遭遇新舊交替的困境時,從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四個方面對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思想進行了重釋,并注入了新的時代內容,以此重新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地位。孫中山肯定了對新文化的積極發展與宣揚,但反對絕對否定和全盤抨擊舊道德的偏激行為;主張辯證地、有選擇地繼承傳統道德觀念,秉持開放的態度,將傳統文化中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思想與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道德觀念相比較,糅合并創新。
關鍵詞:孫中山;道德;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B82-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10-0138-04
孫中山認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傳統道德的基本要素,也正是當時新舊文化潮流沖突的核心所在。隨著“新文化”的入侵,社會上悄然衍生一出股弘揚新文化、排斥舊文化的勢力群體,使得傳統文化陷入了是否被西方文化淘汰,抑或是否抵抗新文化的困局之中。孫中山作為一位先進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對此局面他表示,我們要正確地審視、接納、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并不贊同對舊道德完全摒棄的做法,而是主張采取一種中立的、辯證的態度。對待我們的傳統文化,也就是所謂的舊道德要冷靜、客觀地去分析,理性地去考量其本身價值以及是否具有存在的時代意義,如若我們固有的舊文化是好的,就應該要保存下來,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注入新的國人精神,使得中華傳統道德思想在文化的長河中繼續熠熠生輝,萬代傳揚。
一、將道德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
道德思想在孫中山思想中占據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民族主義則是他的近代道德思想中的精髓所在。他將道德問題與民族主義聯系起來,試圖從哲學的角度,借助道德的力量,喚醒國民民族意識。他將道德問題看作是“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的關鍵問題[1],是維護社會穩定、維系人類發展的基本精神要素。
孫中山曾說:“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但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緣故,起初的原因都是由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 國家才能長治久安。”[2]242顯而易見,道德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思維意識,更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靈魂,是人類社會共同的生存標準。在談到道德對人和社會行為的影響時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2]25,充分肯定了道德作用在民族發展以及國家強盛進程中的力量。所以,我們想要恢復民族地位,就要先恢復民族主義,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道德精神。而我們國人對道德理解還停留在個人、家庭以及宗族的淺顯層面。對此,孫中山提出應該將國民的濃厚的宗族意識和家庭觀念推淺極深至家國歸屬感和民族存亡意識之中,在如同一盤散沙的各個宗族之間,締造出相互聯結的民族紐帶,從而使各個散落的宗族變成一個龐大的團結的中華民族團體。“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2]243簡而言之,就是要將固有的舊道德恢復重建,作為恢復固有民族地位的精神支撐。
二、對舊道德的重釋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一書中具體分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范疇。孫中山指出:“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2]243這四種范疇,是最深入人心的四種傳統道德基本觀念。孫中山對中國傳統道德的繼承和重釋,就主要體現在這四個方面,下面逐一對這四個方面進行解釋:
(一)關于忠孝道德
何為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致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于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2]244正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181在內事父,竭己盡孝;在外事君,致身盡忠。古人云:事君如事父,也就是說,一個人首先要從孝敬父母做起,把對父母的孝推廣到對君主和國家盡孝盡忠,演變為對君主和國家的忠。至此,忠和孝便被看作是一個整體,形成其獨特的忠孝道德觀念,一脈相承。
但是由于當時社會形態已經發展到了民權時代,與以往的封建制度大不相同,廢除了君主制度,沒有了君主。對于大多數普通中國群眾而言也就是沒有了效行“忠”的對象,既然對象沒有了,便認為“忠”也就自然而然應該被丟掉。對此,孫中山認為,雖然君主制度不存在了,但是國還在,家還在,民還在,我們可以從忠于君轉化為忠于國,忠于家,忠于民,甚至忠于我們職守與責任,對一件事至死不渝,排除萬難,犧牲自我也要做成功,就是忠。仍成就精忠報國的雄心壯志;延續赤膽忠心的真純凜然;繼承忠貞不渝的堅定操守,都不失為國人的家國浪漫與情懷。“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忠于人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2]244至此,便將“忠”從封建的君臣關系和單一的父子關系轉變為人民同國家之間、人民同人民之間的多元關系。
孝的道德傳統,從“人之行,莫大于孝”[4]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再到“百善孝為先”[6]。從古至今,孝道在國人的傳統中都是尤為重要的。“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2]244不難看出,在孫中山心中,中國人亙古至今的孝道在世界各個國家都是佼佼者,既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孝道,那又怎么能夠隨意摒棄呢?這是一種由心而生的民族自豪感與文化自信心,是實現民族復興,實行國民建設事業中必不可少的道德精神支撐。回望至今,家庭的建設、家風的塑造與傳承仍然至關重要,家是最小的國,國是最大的家,孝道正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基礎。“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才自然可以強盛。”[2]244
(二)關于仁愛道德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關于仁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孔子認為,最簡單來說仁就是“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3]174是“克己復禮”[3]174,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3]93也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3]93。因為有周禮的禮數限制,孔子的仁愛是有層次有遠近有差別的愛,而墨子的兼愛則是一種普世的愛。墨子認為愛是解決消除禍患,戰亂的原因,所以“天下之人皆相愛”。“兼相愛,交相利”[7]134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如果我們能夠待人之國如待己之國,待人之家如待己之家,待人之身如待己之身,人與人之間就會彼此相愛,互相得利。通過“兼愛”將“愛己”推及”愛人”,將“利己”推及為“利人”真正做到“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7]375。也正是這種大愛,使得孫中山對墨子推崇備至。在早年在西方游歷時,西方文化中的博愛的思想,對孫中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把它與中國傳統的道德思想融合到一起。孫中山將儒家的“仁愛”與西方的“博愛”等同起來,認為這種愛尤其與墨子的無差等的愛更為相近。于此,便創新了一種集“博愛”與“兼愛”于一身的新型仁愛道德。
通過前人對”仁愛“的解讀,孫中山認為,在不同的朝代,對仁愛都有不同的詮釋與定義,無數的文人、學者都在對其進行修改、完善和更新,以追求一種最符合社會要求的好的仁愛道德。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有仁愛的,并且努力去實行仁愛,想要做到愛民愛物,只不過沒有真正地落實到千家萬戶中去,沒有落實到人民真正的需求當中去,缺乏一定的實踐性和實效性。立眼當代,自西方新文化傳輸以來,我們便深刻意識到,中西方文明之間的落差與參差,以至于許多人認為中國的仁愛道德沒有外國的道德好,視外國人在中國設立了學校,開辦了醫院,通過教育濟人民的行徑為實行仁愛的好方法。面對這種情景,孫中山提出,要想最好地發揮仁愛道德的作用,恢復民族精神,并不是不加思考地照搬照抄西方國家的做法,直接摒棄傳統的舊仁愛道德,而是只需要去學西方國家把仁愛實行起來的方式即可,將這些仁愛的道德理論結合時代要求和社會背景真正付諸于實踐,付諸于民生,付諸于民情,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廢除傳統守舊的舊式私塾等。將仁愛的種子播種到關懷國計民生,追求民主政治,實行教育立國的土壤之中,讓仁愛在中華民族的國土上繼續扎根,滋養這四萬萬群眾。仁愛還是中國的好道德,是中國固有的精神。由此可見,孫中山對于仁愛二字更注重的是真操實干,講的是政府的利民服務,認為如果我們能把這樣的仁愛恢復并且注重實踐,就是固有的好道德。仁愛之路延續了千百年,先祖們一朝朝地革新,一代代地傳承,薪火相傳到我們這一輩,更是要在傳統道德的繼承中探索出一條創新的路徑。
(三)關于信義道德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鄰國和對于朋友,都是講信義的。”[2]245孫中山認為信義道德自來是扎根在中國人骨子里的,言行舉止之間講求信義,是人有修為、重品行的表現。人有信義,方可立身天地之間,正是由于中國人將履行信義看作是一個人安身立命乃至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條件,所以關于信義道德,中國人要比外國人做得好得多。
孫中山以兩個例子為證:其一在商業交易方面,中國人與中國人交易,只以口頭信用,即可了事。外國人與中國人交易,來訂一批貨,也只要計入賬本,便可了事。但是如果是中國人去跟外國人訂貨,就要擬一份詳細的合同來說明。少有沒立合同的情況,中國商人也會按照說好的條件去做,不會因為價格利潤等變動而反悔推辭,寧損利益不損信義。因為國人與國人之間都有著十分濃厚的信義感,本著“人無信則不立”的信念。正因為信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著重提出的道德標準,所以以信義為重,乃是商人中的誠賈、廉賈的本色。久而久之,很多外國商人都會夸贊中國人一句話比合同更具有信用力。不難看出,孫中山對于信義的理解,包含但不局限于先秦諸子百家對于信的傳統觀念,更是強調突出了近代商業上的一種契約精神,恰恰這種精神是被各國商人所贊譽不絕的,這種契約精神也可以用我們的一句古話來解釋:一言九鼎。因而可知,舊的信義道德不僅不能被替代,還更應該繼續傳承下去,信義道德以及新注入的契約精神將成為國人的嶄新的民族標簽,中國商人也是有信義道德的誠信商人。
其二在對待藩屬國態度方面。中國疆土遼闊,物產豐足,自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強大的秦王朝后,東方巨龍一直雄霸亞洲。漢唐盛世時期,國家版圖更是急劇擴大。元朝和大清乾隆時期,總面積更是達到1300萬平方公里以上。周邊前來進貢交好的國家接踵而至,但是中央王朝對待藩屬國多是采取懷柔的方式。“至于講到信義,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2]245-246孫中山更是主張將信義看作是判定一個人是否可交的衡量標準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友好往來的基本交往準則。
(四)關于和平道德
“中國更有了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2]246在孫中山看來,維護和平與行忠、奉孝、施仁愛、守信義是同等重要的德行。而且中國人骨子里也是以和為貴,崇尚和平的,并不傾向于使用戰爭武力手段去解決問題。道德思想不僅是一個國家民族存在的基石,更是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友好相處的基礎,是實現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關于民族主義的一次演講中,孫中山提出:“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2]253在和平道德的基礎上,治國平天下,完成恢復民族主義的宏偉目標,實現“大同社會”和持久和平的美好藍圖。“大同”社會是孫中山的和平道德思想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8]。正如國家由我們四萬萬人民做主,四萬萬人民皆為皇帝的道理一樣,在孫中山看來,這就是大同世界的完美寫照。對比中西方對于戰爭的態度便可知道,西方從前是提倡以武力解決問題的,用古人的話講就是“霸道”。最近這些年才因為害怕戰爭,為了避免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勉強采取和平手段。但是中國崇尚和平是出于國民天性,是自然而然的。這種道德,不是用武力壓迫,打壓人民,使人畏懼。而是“為政以德”[3]14,以德治國,以德服人,用愛去感化人民,以仁愛之心去愛人民,待百姓,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王道”思想。“這種特別好的道德,便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以后對于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發揚光大,然后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2]247
三、如何看待舊道德與新文化
孫中山對新文化的積極發展與宣揚是秉持非常熱忱的態度的,不過對于新文化運動中絕對否定和全盤抨擊舊道德的偏激行為,也表達了十分的不滿。“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2]243在這里,孫中山使用了“壓迫”“入侵”和“橫行”這類帶有負面意義的詞匯,就可以充分證明,孫中山對于此類不加解釋、不問情由、不考慮現實與實際情況,便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全面否定傳統文化的風向,表現出不滿甚至是排斥的情緒[9]。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亙古不滅,無論是作為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精神紐帶,還是以豐富的精神養料滋養當代國人的精神世界,道德思想作為傳統文化的基建都具有無可湮滅的跨時空的價值與意義。不論是所謂的舊道德,還是取西之用的新文化,都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都不應該被隨意取締,否定,拋棄。任何不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傳統道德為支撐,沒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加持的“新文化”都是空虛的,經不起時間和實踐的推敲。
沒有繼承,又何談創新。固有的道德在發展的進程中,與西方的新文明互相沖突,互相比較,更應該互相汲取。孫中山根據當時的時代要求,在晚年的演講中,對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進行了全面闡述和價值分析,字里行間表露的是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但是,孫中山對于中國“固有的舊道德”并不是毫無批判地盲目推崇,在對舊道德的重釋中擴大了“忠孝”的可實行范圍,剔除了“仁愛”中的封建階級成分,在“信義”中加注契約精神,讓“和平”締造大同社會,繼承與創新并進。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舊的道德,只注重原有意思已然不能滿足當代人民對道德主義的需求,我們需要借助西方優秀文化來更深層次地挖掘固有道德的時代內涵,賦予豐富的精神價值。
辯證地、有選擇地繼承傳統道德觀念,同時秉持開放的態度,將傳統文化中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思想與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道德觀念相比較、糅合、創新。在創新與繼承的過程中,既不沉浸在文明古國的光環中自尊自大,因循守舊,也不崇洋媚外,盲目引進[10]。展現的是泱泱大國對于異國文化包容與兼容性,通過對舊道德的推陳出新,對西方文化取精去糟,揚長避短,形成一套嶄新的中西結合、古為今用的獨特的道德思想體系。至此,無論是孫中山對于本民族的文化自信,還是他在面對新舊交替時的辯證性思維,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體現出的透過表象看實質的文化內涵,由表及里的哲學素養,都值得當今的我們細細品味,時時警醒。
參考文獻:
[1]趙曉華.簡論孫中山的和平觀[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
[2]孫中山.孫中山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孔丘.論語[M].楊伯峻,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4]孔子.孝經[M].徐艷華,譯注.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33.
[5]孟軻.孟子[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7:1-21.
[6]王永彬.圍爐夜話[M].北京:中華書局,2016:120.
[7]墨子[M].方勇,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8]禮記·禮運[M].賈太宏,譯注.北京:西苑出版社,2016:264.
[9]曾慶榴.舊道德的重塑與道統傳承——孫中山晚年重釋中國傳統道德之意蘊[J].粵海風,2014(6).
[10]江中孝.從孫中山的“國粹”觀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J].廣東社會科學,2003(1).
作者簡介:閆雪(1997—),女,漢族,山東濟寧人,單位為黑龍江大學,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
(責任編輯: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