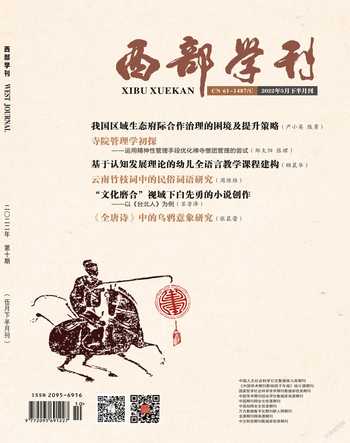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思政教育的研究
摘要:1931年后,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加劇,為了抗日救國,國民政府推行“黨化教育”,遭到懷著抗日救國理想的大批知識分子的抵制,他們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尋求真理。在延安,中共通過三方面的思政教育:(一)傳授抗戰救國知識和馬列主義;(二)引導知識分子參與勞動實踐;(三)確定文藝發展方向。完成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為日后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思政教育
中圖分類號:D2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10-0009-04
一、緒論
從1935年10月19日到1948年3月23日,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這段時期也被稱作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時期。延安坐落于中國的西北一角,位于陜西省北部,地處黃河中游,黃土高原的中南地區。與國統區和淪陷區的其他城市相比,這片區域形成了更為民主、平等的氛圍。眾多知識分子不惜克服重重險阻前往延安,到達他們理想中的革命圣地。他們在這里延續革命熱情,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成為了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一部分。
在中西方語境之中,知識分子的含義有所不同。西方語境中的知識分子從事獨立的研究、教學、出版等工作,是其所在領域的權威,不受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是能夠站在獨立視角針砭時弊的知識群體。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多數不愿抽身政壇之外,他們的前身被稱作“士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希望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朝廷任職,具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這些特質被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繼承了下來。民國時期中國內憂外患的局勢,
喚醒了知識分子的愛國意識,他們所追求的不僅僅是撰稿寫作,而是希望引領中國發展的步伐,肩負救亡圖存的使命,將自己的前途和命運與國家的前景緊緊聯系在一起。
此外,國民政府的“黨化教育”政策由于僵化呆板,嚴重不符合實際,不為知識分子所接受,眾多知識分子迫切希望尋找到新的主義和路線。在1935年的瓦窯堡會議中,毛澤東提出團結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政策的改變為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創造了條件,前往延安的知識分子絡繹不絕,在1940年達到了4萬人之多。中國共產黨采取傳授理論知識、引導知識分子參與勞動和工農大眾結合,明確文化文藝工作方向的方式,團結知識分子,將他們納入到了黨主導的革命話語體系之中,為日后抗戰勝利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礎。
二、迷茫與抗爭——知識分子前往延安的原因
(一)知識分子的個人選擇
黨史研究專家蕭一平先生對知識分子前往延安的原因有這樣的解釋:“當年從國統區去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很多是沖著延安有發展的空間和舞臺去的,他們在國統區目睹和親身體會了國民黨的貪污腐敗以及對人民的傷害,國統區已經沒有適合他們生存的空間和機會了,而延安作為當時的革命圣地、全國抗戰模范區,那里人際關系平等,到處是抗戰的歌聲,還有抗大陜公等高校吸納青年,這些都對國統區的青年產生了很強的吸引力。”[1]
深究知識分子們的身世背景,可以發現他們前往延安具有各自不同的動機。前往延安的知識分子可分為三類,分別是叛逆者、逃亡者和追求者[2]3。叛逆者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響頗深,他們中的有些人在前往延安之前就對馬克思主義有所了解,他們的種種言行為舊的社會所不容,故走上反叛的道路,前往延安尋找新的可能,代表人物有丁寧、艾思奇和范文瀾等人;逃亡者主要是出生在東北的知識分子,他們因故土淪喪撤到關內,隨著日寇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深,曾流亡到重慶、桂林、成都的東北知識分子紛紛聚集到延安,形成了延安的東北作家群,代表人物有雷家、蕭軍和舒群等人;追求者沒有與舊社會的強烈沖突,也沒有喪失故土的慘痛經歷,他們前往延安更多是出于生計和發展需要,或為個人理想的選擇,代表人物有冼星海、何其芳等人。作為叛逆者和逃亡者的知識分子斷絕了回歸原有社會的可能,他們將個人的命運與延安的事業緊密捆綁在了一起,因此他們在各領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他們決定了延安知識分子成就的高度,追隨者多為青年學生,雖在成就上略遜一籌,但人數眾多,他們決定了延安知識分子的廣度。
(二)國民政府失敗的“黨化教育”
除知識分子的個人選擇外,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也極大地影響了知識分子的去向。國民政府一直在向全社會和文化界推廣所謂“黨化教育”(“三民主義”教育),希望借助宣揚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理論團結民眾,凝聚人心。為此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和教育部先后于1928年頒布了《大學規程》和《各級學校增加黨義課程暫行條例》,對黨義教育進行了嚴格的規定。
國民政府對“黨化教育”不可謂不重視,但在文化界“黨化教育”遭到了許多左翼人士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抵制,均認為“黨化教育”是國民黨禁錮思想自由的工具。
在學校中,“黨化教育”僅流于形式,學生們普遍對黨義課感到枯燥乏味,將黨義課稱為“黨八股”和“黨雜碎”,黨義課教師被視為國民黨的宣傳工具,在校內地位尷尬,常遭到學生轟趕,在教學上只管教授不管效果。
意識形態的宣傳往往需要政治和經濟保持良好的耦合關系才能實現。國民政府在面對日本侵略時,展現出了足夠的強硬態度,以滿足人民的訴求,但在對內宣傳方面卻陷入失敗。加上清黨之后,國民黨內有理想、有信仰的黨員受到清洗,投機分子和土豪劣紳趁機混入黨內,許多國民黨人已經拋棄了他們的信仰。因此當國民政府試圖通過獨裁手段向知識分子灌輸“黨化教育”的內容時,知識分子們因其內容空洞、禁錮思想與現實嚴重不符而感到厭惡和反感。
(三)中共的宣傳和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轉變
自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國共產黨專注于土地革命,工作重心逐漸從城市轉變為農村,對于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城市,共產黨抓住了文化和思想領域,將抗戰救國、民族解放和馬列主義思想相結合,引導以學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自發學習理論知識,并號召他們參與反日游行和請愿活動。0C0CDFD3-C445-4C64-96AD-7EBED4D8224F
左翼學者潛心翻譯馬列著作,建立起詩社、讀書會等組織,以此為掩護,傳播馬列思想,再加上共產黨外圍組織社聯、左聯的助力,馬列思想逐漸成為流傳在學生之間的進步思想,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一文,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是愿意為工農服務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因此要保護革命的知識分子[3]。1939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撰寫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提出應該對愿意抗日救國且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和培養,讓他們到戰爭中得到鍛煉,如有他們具備入黨的條件,可吸收他們入黨[4]。
為突破國民政府的封鎖,便于吸收各地的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在各地的組織積極介紹知識分子到延安學習和工作。當時前往延安共有四種方式:一是通過處在南京、武漢、西安、重慶、太原、長沙、桂林、蘭州、迪化等地辦事處和通訊處;二是通過陜西、河南、四川等地下黨組織;三是通過各地黨的負責人如羅世文、劉子久介紹;四是通過一些群眾團體或名人引薦[5]。
三、教育與改造——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抗日軍政大學對第四期4269名學員的成分進行了統計,發現成分為“學生”的學員共計2465人,占總人數的57.7%;在對657名教職工的統計中,成分為“學生”的有200人,占30.4%;知識分子有70人,占10.7%[6]30。可見,知識分子和學生在延安高校已占有相當比重。而延安知識分子群體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進入到政黨政治及其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之間;二是與工農大眾打成一片[2]4。他們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特點,源自于黨組織和民主政府對他們的教育和改造。
(一)教授抗戰救國知識和馬列主義理論
中國共產黨以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等17所院校為場所,教授抗戰救國知識和馬列主義理論,促進了知識分子在思想觀念上的轉變。
1.抗戰救國知識
為適應抗日的需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提出優先教授抗日救國知識的教育政策,指出院校設立課程應“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原則”,并提出要擴大增強各干部學校,培養抗日干部。
延安高校實行“準軍事化”管理,學校的組織結構參照軍隊編制,新入學的學生按照身份或學習程度分配到不同的“大隊”“支隊”或“隊”,每個“大隊”設有大隊長和政委。學生每天早上6點隨著起床號一起出操跑步唱軍歌,晚上10點隨著熄燈號一起休息。
在課程設置上,延安的高校也充分體現了“抗日優先”的理念。抗日軍政大學以培養軍事干部為主,預科科目有抗日民眾運動、戰略學、游擊戰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八路軍戰術、政治常識、政治工作、社會科學;本科有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中國革命史、戰略、戰術、射擊學、地形學、建城學、技術兵種等。陜北公學以培養政工干部為主,在教育內容上注重如下四個方面:第一,抗戰的基本理論;第二,抗戰的政策及方法;第三,指揮民眾武裝斗爭進行戰斗的基本知識;第四,對于目前時局的認識[6]59。陜北公學的課程可分為普通班和高級班兩類。普通班設有4門課程:“社會科學概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戰爭和民眾運動。高級班設有中國革命運動史、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世界革命運動史、科學社會主義、三民主義研究、世界政治等課程。”[6]59
這些高校的學生們畢業之后,多數會分配至八路軍、新四軍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中直接參與抗日斗爭,以陜北公學為例,1937年8月至1941年8月,80%以上的畢業生奔赴敵后從事抗戰工作,或是直接參與指揮游擊戰爭;僅有20%的畢業生留在了陜甘寧邊區和大后方。可以說,延安的高校將眾多的知識分子培養成了抗日的骨干力量,為中國最終取得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2.馬列主義理論
1939年7月2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了《關于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提出教育知識青年的重點在于傳授馬列主義理論,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將知識青年改造為愿意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服務的無產階級戰士[6]42。為達到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兩種方式,一是領導干部帶頭講課;二是發揚民主作風,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黨中央的領導干部常參與到學習之中,并親自為學生講課或作報告。毛澤東為學生們講過《中國憲政運動》和《青年運動方向》;周恩來講過《大后方的抗日形勢》和《平江慘案情況》;朱德講過《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發展》和《根據地經濟》;董必武講過《正統觀和六法全書的批判》;張聞天講過《新民主主義文化》等內容。黨中央領導們所講的內容多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客觀實際的結合。學生們在聽講的過程中,不僅獲得了這些寶貴的實踐經驗,也逐漸習得了如何把理論運用于實際的方法。
延安高校非常重視發揚民主精神,規定教師與學生地位平等,學生可以給老師提意見。師生之間互相學習,共同進步;在學習組織上,各分隊的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集體討論和思考,加深對理論的理解,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時班與班、隊與隊之間還會采取舉辦學習競賽的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效率。
(二)引導知識分子參與勞動實踐
中國共產黨引導知識分子參與勞動實踐,一方面是由于陜甘寧邊區長期受國民政府封鎖,需要知識分子參與生產勞動,以緩解物質條件不足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出于改造知識分子的考慮。
對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而言,勞動實踐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為了解決住宿問題,抗大學生在兩個星期內挖了175個窯洞,并修筑了長達3000米的抗大公路[6]27。在日常生活中,延安的學子和教職工要參與整治環境衛生,打掃操場,伙房幫廚,搖轆轤從井底取水,協助買賣采運等勞動[7]。
1939年初,國民黨反動派加強了對革命根據地的封鎖,延安的物質條件日益匱乏。1939年4月20日羅瑞卿帶領抗大全體教職工以班、排、隊為單位帶著自制的農具開展向荒山禿嶺進軍、向荒山要糧的運動。在運動開展過程中,班與班、排與排、隊與隊之間開展了勞動競賽。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抗大的生產運動取得了不錯的成就,所開辟的荒地共收獲了谷子、土豆等糧食100余萬斤[8]94-95。0C0CDFD3-C445-4C64-96AD-7EBED4D8224F
除開荒種地之外,延安的知識分子還要生產一些日用品和輕工業品,如自制若干粉筆、墨水、肥皂、紙張、襪子和綁腿等日用品;開辦被服廠、制鞋廠和縫紉廠從事制鞋、縫紉、紡線、彈棉花等生產活動[8]95-94。生產所得均交給學校或政府部門用于日常使用和支援抗日前線。
對于生產運動,許光達曾這樣評價道:“生產運動不僅解決了經濟的困難,鍛煉了身體,特別是改造了我們的思想意識,尊重勞動,使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統一起來。”[9]中國共產黨通過讓知識分子參與勞動,讓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尊重和關注勞動,培養了知識分子與群眾同甘共苦、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達到教育與改造知識分子的目的。
(三)確定文藝發展方向
毛澤東于1942年5月23日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重點確立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針,探討了怎么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問題,要求文藝工作者在從事文化生產活動時,從創作觀念、作品形式、作品題材和作品語言都要從資產階級的立場轉變為無產階級的立場。
從文學創作題材上看,延安的知識分子更專注于描寫普通群眾的生活,描寫農民反抗壓迫的革命歷程,力圖創造普通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表現形式。在《人民文藝叢書》收錄的177部作品中,描寫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與軍隊生活的101部;寫農村土地改革、減租、復仇清算等各類階級斗爭的,反對迷信、文盲、不衛生、婚姻不自主等封建現象的41部;寫工農業生產的16部;寫陜北土地革命時期革命歷史故事的7部;其他如寫干部作風等題材的有12部。這些作品現實性、政治性較強,展現了延安生活的風貌,也體現了延安知識分子在經過改造之后的創作傾向[10]349-350。
延安的戲劇也貼近普通民眾的審美。1943年魯迅藝術學院派出27個秧歌隊在延安等革命根據地開展新秧歌運動。這些戲劇反映了農民的日常生活,展現了舊新時代交替之際,農民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如《兄妹開荒》《夫妻識字》《慣匪周子山》《牛永貴掛彩》等劇目,既具備娛樂性,為人民大眾所喜愛,同時又自帶革命啟蒙的性質,讓觀眾感受到革命給民眾生活帶來的改變[10]478。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視黨校對黨員干部的黨性教育。近百年來,黨校黨性教育隨著黨的發展壯大逐漸走向科學化和制度化。分析不同歷史時期黨校黨性教育的特點,為把握黨校黨性教育的歷史脈絡、推動黨校黨性教育向縱深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中國共產黨在規范文藝創作的問題上,以出臺文藝政策的方式主導文化創作的方向,將知識分子納入到了黨的話語體系之中,自覺創造出人民大眾喜歡的作品,起到了統一思想,凝心聚力的作用。
結論
國民黨失敗的“黨化教育”因其虛偽且不符合現實情況的原因沒能被知識分子所接受。相比于國民黨政府在籠絡知識分子上的無能,中國共產黨人充分發揮了強大的宣傳和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向知識分子普及抗戰和馬列理論知識,引導知識分子參與勞動,用黨的文藝方針引領延安的文藝創作方向,達到了改造和團結知識分子的目的,為擊敗日本侵略者,促進中華民族的解放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參考文獻:
[1]楊軍紅.抗戰初期青年知識分子赴延安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15.
[2]朱鴻召.延河邊的文人們[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
[3]張遠新,吳素霞,張正光.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0.
[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9.
[5]任文.我要去延安[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117-118.
[6]曲士培.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高等教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7]劉大年.我親歷的抗日戰爭與研究[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38.
[8]任文.延安時期的日常生活[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9]許光達.“抗大”在國防教育上的貢獻[N].新中華報,1939-05-30(4).
[10]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作者簡介:戴銘志(1995—),男,漢族,廣東深圳人,單位為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研究方向為黨史。
(責任編輯:趙良)0C0CDFD3-C445-4C64-96AD-7EBED4D8224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