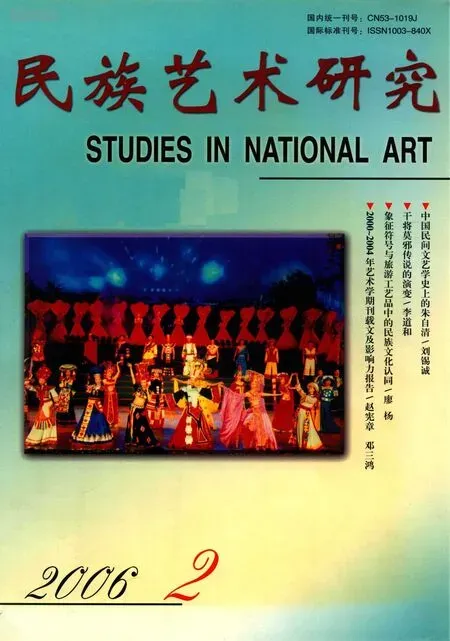梅蘭芳的戲曲美學觀
李志遠
在當前的學界或戲曲界,梅蘭芳作為一個語匯應該說有著兩種所指:一是指作為乾旦演員的梅蘭芳本尊;一是作為京劇甚或說戲曲的藝術符號,這無論是曹禺先生所言的“梅蘭芳三個字已經成了美的化身”①轉引自寧殿弼:《梅蘭芳改革京劇的藝術理論概觀》,《戲曲藝術》1996年第2期,第22頁。,還是戲曲學界在談論世界三大戲劇觀時把梅蘭芳作為中國戲曲藝術的代表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相并列,都可于中察知。本文所言梅蘭芳是就第一種所指而言,即是立足學習作為乾旦演員的梅蘭芳所留存下來的相關資料,于中探討作為優秀戲曲表演藝術家的梅蘭芳,秉持著什么樣的美學觀進行戲曲創作及其對今天的戲曲美學建構的啟示。
梅蘭芳對戲曲藝術具有美的本質有著清醒認知,如他在《國劇學會宣言》中直稱“愈信國劇本體,固有美善之質”②梅蘭芳:《國劇學會宣言》,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頁。,而在國劇傳習所授課時也講到“中國戲曲,處處離不掉美,同是一種動作,但有些就引不起觀者快感,就是因為不夠美的成分”③梅蘭芳:《在國劇傳習所之一課》,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頁。。正是因為他在進行具體的戲曲作品創作時,無時無刻不按照內心所總結出的戲曲美學原則進行美的創造,如他稱,“中國的古典歌舞劇,和其他藝術形式一樣,是有其美學基礎的。忽略了這一點,就會失去藝術上的光彩”④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頁。;他在講解戲曲化妝時提出了明確的美學理論主張,即“根據‘為美’的原則,找出學理的一種技巧”⑤梅蘭芳:《國劇化裝術之一部》,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頁。;在談到如何從現實生活中汲取表演素材時稱“要什么,不要什么,這里牽涉到一個美學的問題”⑥梅蘭芳:《中國戲曲的表演藝術》,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400頁。。這一“美學基礎”“為美原則”“一個美學的問題”,顯然就是梅蘭芳戲曲創作的核心美學觀,并且將其運用于戲曲創作的每一部分。
依據今日留存下來的、較為易見的梅蘭芳有關戲曲美學的文字表述,對其戲曲美學觀進行歸納,筆者認為約略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戲曲藝術之飽蘊內神的外形美
戲曲作為舞臺表演藝術顯然要注重唱念做打等手法的視聽美感,即從外在創作手法上就要形成吸引觀眾的強有力元素,對此,梅蘭芳應該說有著清醒認知,如他曾說,“在舞臺上的一切動作,都要顧及姿態上的美”,正是基于這種美學創作見解,他在每部作品的舞臺創作上都極力追求作品的外在形式美。如他闡釋《宇宙鋒》趙艷蓉的表演身段稱,“趙女在‘三笑’以后,有一個身段,是雙手把趙高胡子捧住,用蘭花式的指法,假做抽出幾根胡須,一面向外還有表情。這個身段和表情,雖說是帶一點滑稽意味,可是一定要做得輕松,過于強調了,就會損害到美的條件。”①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頁。關于《貴妃醉酒》的舞臺身段,他說,“高力士跪在下面,也應該向后坐下,使一矮坐的身段,跟上面楊妃做的,一高一矮地對照著,才顯得格外美觀”,而劇中的打嘴巴“以前是用手打的,總覺得不美觀,近來改為用水袖打,兩次的打法不一樣,打裴是用袖正打,打高是用袖反打”,總之是要舞臺上“顯出舞蹈上美的姿態”②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57、265、266頁。。在人物化裝上,他強調說,“除去由化裝上可看出劇中人的個性外,同時盡量往‘美’上追求,并且這種美是立體式的美,圖案式的美”③梅蘭芳:《國劇化裝術之一部》,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頁。,因而在對待時裝戲《童女斬蛇》中寄娥的裝扮,力求“要使觀眾覺得和日常生活里接觸到的人差不多,但比她們更鮮明,更美”④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頁。,再加上他對戲曲表演中手勢的重視,特別是古裝新戲裝扮的精益求精,都可以看出梅蘭芳對戲曲藝術外形美的重視。正是由此,有學者稱“梅蘭芳戲曲美學體系明顯的特點是很強調外部形式美”⑤寧殿弼:《梅蘭芳改革京劇的藝術理論概觀》,《戲曲藝術》1996年第2期,第22頁。。
當然,梅蘭芳注重戲曲藝術的外形美,并不像其在訪問蘇聯時一些人所評價的戲曲僅注重了外在形式而忽視了內容,如他創作的時裝新戲就多是取材于現實生活,而《抗金兵》《生死恨》的創作也與時事相關。事實上梅蘭芳所注重的外形美是以飽蘊內神主導的,如他稱《童女斬蛇》的創作“是從內到外來表演的,用心里的勁頭指揮動作”⑥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頁。;告誡青年演員“內心與形體動作的統一,這是非常重要的,更需要耐心體會”⑦梅蘭芳:《對小朋友們提出幾點要求》,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頁。;并稱戲曲傳授一定要“親傳”,否則“終必至于襲貌遺神”⑧梅蘭芳:《國劇學會宣言》,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頁。。這些言論無不表明他注重的是有著內在精神的外形,而不是單純追求舞臺上的外在造型,且他對舍神取形的戲曲創作有著清醒認識,如他明確表示“身段假使沒有內心表演,就會流為形式主義”⑨梅蘭芳:《看日本歌舞伎劇團的演出》,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47頁。。
二、注重戲曲創作手法與人物形象的契合
無論戲曲作品要表達什么樣的主旨,顯然是要通過在舞臺上塑造出富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形象得以實現的,這就需要采用恰切的創作手法使得人物形象圓滿和立體,對于此,梅蘭芳所言“演員的任務是把劇本所規定的人物在舞臺上表演出來”①梅蘭芳:《對小朋友們提出幾點要求》,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頁。,應該說是闡釋得非常清楚的。但具體如何在舞臺上把人物表演出來呢,顯然是需要采用最為恰切的創作手法,就演員而言就是用最為適合人物形象塑造的唱念做打等表演技巧,以把人物形神兼備地呈現于舞臺上。如他所說,“劇中人的性格和身份是靠演員的唱、念、做、表四種工具表達出來的”,所以人物“一出場的念白、動作、神態,先由尺寸上”來展現“她們的性格”②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84頁。。梅蘭芳多次談及杜麗娘形象塑造與身段改換,可視作此觀點的最好注腳,如他稱在唱“和春光暗流轉”時的三個下蹲動作,“是一個刻畫得比較尖銳的老身段”,后來一則因自己年齡大的原因,認為“再做這一類的身段有點過火”,二則認為“在入夢之前,過于露骨的身段,對一個像杜麗娘那樣身份的女子還是不大適宜”,于是就“改成轉到桌子的大邊,微微地斜倚著桌子,有些情思睡昏昏的嬌慵姿態,最后輕輕地一抖袖,就結束了這一句的動作”③梅蘭芳:《談杜麗娘》,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70頁。這種立足于人物身份、內心、性格以選用舞臺創作手法的見解,幾乎成為梅蘭芳人物創作的核心遵循。他曾多次有著相近的表述,如:“假戲真唱要設身處地地琢磨每一個劇中人的身份性格。”④梅蘭芳:《對京劇表演藝術的一點體會》,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頁。“演員在表演時都知道,要通過歌唱舞蹈來傳達角色的感情,至于如何做得恰到好處,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⑤梅蘭芳:《談表演藝術》,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頁。“我從小就喜歡跟人家討論劇情、研究人物性格,總想把我演的戲里每一個角色的內心情感通過藝術提煉,用表情和動作表達出來。”⑥梅蘭芳:《不抄近路是我學戲的竅門》,《中國戲劇》1995年第7期,第11頁。“演正德這個角色,偏重佻達,固然會令人生厭,過于堂皇華貴,也不合適,應該從華貴中帶點故意模仿舊社會里少年軍官的習氣,才符合這個好色貪玩的風流天子的性格。”⑦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頁。對于演員表演的好壞,他也多是從是否能夠采用恰切的表演手法成功塑造出劇本規定的人物為依據。如他評價賈洪林,稱其“盡管嗓子不好,對于體會劇中人的身份、性格,是有他獨到之處的”,“他扮演任何角色,都情態逼真,處處合理”⑧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223頁。。
當然,在達到創作手法與人物形象塑造契合的目的后,一定要追求創作手法給觀眾的最大美感,這既是與梅蘭芳注重外形美的美學觀緊密相連,也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人物形象的審美效能。他作為乾旦演員,曾多次強調旦行要注意行當美,稱“唱旦角更應處處合乎‘美’的條件”⑨梅蘭芳:《旦角的化裝術》,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頁。,“現在最通行的一種毛病,就是旦角站立時,都把重心移于后邊腳上,這種姿勢最不美而且最費力”①梅蘭芳:《劇舞筆記》,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頁。。他還用他的表演實例予以述明,如他說《貴妃醉酒》中楊貴妃醉酒后的三個臥魚身段本來是沒有目的的,他進行了多次深思與修改,就是要“給觀眾一種真實的感覺”②梅蘭芳:《談表演藝術》,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頁。,即要達到做出來的“身段得相真,得好看”③梅蘭芳:《在國劇傳習所之一課》,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5頁。;對于《黛玉葬花》之所以沒有采用旗裝、京白,就是因為會使舞臺上的賈寶玉“未免顯得俗氣,更不能表現林黛玉的絕世聰明”,而采用古裝裝扮“一則可以盡量發揮林黛玉的才華,二則可以在葬花時表演種種姿勢”,且扮演出來的舞臺上的林黛玉,“大家都很滿意,認為理想中的林黛玉,應該是這個樣子”④梅蘭芳:《四十年戲劇生活》,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頁。;而對《思凡》中色空的扮相,則并不是據“正青春被師父削去了頭發”這句唱詞而扮作光頭尼姑,就是因為舞臺創作手法的選用“處處要照顧到美的條件。像這種一個人演的獨幕歌舞劇,要拿真實的尼姑姿態出現在臺上,那末臉上當然不可能擦粉抹胭脂、畫眉點嘴唇。這就跟種種美的身段、唱腔、表情都不能夠調和融洽了”⑤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頁。。正是因為梅蘭芳注意創作手法與人物形象的契合,他不僅強調要“根據傳統技巧的表現原則來創造適合于現代人物的新唱腔、新格式、新手段”,認為“光從唱詞字面上去表演,就會流于膚淺以至歪曲,必須從劇情里去分析人物思想感情的來龍去脈,處處想著角色的身份,進行創造”⑥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頁。,不要“為了搬用傳統技巧,而不顧人物性格、環境,就會走上為運用而運用、生搬硬湊的形式主義道路”⑦梅蘭芳:《運用傳統技巧刻劃現代人物——從〈梁秋燕〉談到現代戲的表演》,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186頁。。
如果我們再稍加注意的話,甚至可以看出梅蘭芳對創作手法與人物形象契合的關注,甚至不僅僅局限于唱念做打等舞臺表演元素,而是擴展到演員自身是否適合劇中人物形象的創作,如他在《虹霓關》中頭本扮東方氏,而在二本中改扮丫鬟,這是他的首創。為何如此呢?他稱,“這是因為我的個性,對二本里的東方氏這類的角色,太不相近,演了也準不會像樣的原故。”⑧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頁。當然,如再進一步追尋梅蘭芳為何會有如此的美學見解,可能與他所認為的,“戲曲演員,當扎扮好了,走到舞臺上的時候,他已經不是普通的人,而變成一件‘藝術品’了”⑨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三、注重舞臺表演的劇情規定性
戲曲劇本是戲曲舞臺創作的最終遵循,所有的人物形象、場景展現以及主旨表達等,無不是依據戲曲劇本的設定展開,這就需要舞臺表演要緊扣劇本所設定的劇情進行。正是基于此,梅蘭芳特別注重劇情對表演的內在要求,力求舞臺創作能夠較好地完成劇情的立體呈現,以較美的形態實現潘之恒所言“顯陳跡于乍見,幻滅影于重光”⑩。
梅蘭芳對舞臺表演要達到劇情規定性的要求,他在不同的文章中分別從不同方面予以闡釋。如:就舞蹈而言,他說,“中國戲曲的表演方法,是把舞蹈動作融化在生活里,人物登場,一舉一動都是舞蹈化的,其中個別場子如‘劍舞’‘羽舞’‘拂塵舞’雖然著重在舞蹈,但仍然是為劇情服務的”①梅蘭芳:《我的電影生活》,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七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頁。。就表演身段而言,在有人問他演《汾河灣》唱完“等你回來我好做一做夫人”后的極美妙身段是怎么做出來的時,他說“那時的動作只是隨意而為而已,只是符合劇情,是不會重復的”,并稱身段要符合人物內心、恰到佳處,就要“不斷分析劇情”②梅蘭芳:《說戲》,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42頁。。就念白而言,他說,“不論是韻白或京白”,都應該“根據劇情,運用輕重緩急、抑揚頓挫的技巧”,否則就“如同小孩背書,索然無味”③梅蘭芳:《中國戲曲的表演藝術》,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91頁。。就表演道具而言,他以《斷橋》中青蛇是否要背劍上場為例說,劍“拔出來是容易的,插回去就難了。要不插回去,老讓青蛇背上插著一把劍,這多么難看。其實《斷橋》出場,就換了打扮,武裝已經解除,何必再帶武器,所以不插劍的方式,對于劇情比較合理”④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頁。,于是就不讓青蛇背劍上場。就舞臺表演所采用的耍戲法而言,他稱贊《封神榜》表現狐貍精吃掉妲己采用的耍戲法,因為它“沒有離開劇情”,而批評《歐陽德》的耍戲法則正是因其與劇情沒有關系⑤梅蘭芳:《贛湘鄂旅行演出手記》,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55頁。。就突破戲曲表演常規而言,他認為只要是符合劇情都是可以的,如他說,“演老派青衣的不常露手,而我們演柳迎春可以常常露手,因為有許多動作是必須要用手的。當年有位時小福老先生,演柳迎春就時常露手,當時有人叫他為‘露手青衣’。柳迎春有許多做派是需要露手的,時老先生這樣做是合乎劇情的。保守派稱他為‘露手青衣’,是一種諷刺性的外號,這是不對的”⑥梅蘭芳:《旦角表演及〈穆桂英掛帥〉的形象塑造——一九六○年五月在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09—410頁。。就劇作表演成規的修改而言,也是依據劇情進行的,如認為《奇雙會》中趙寵與桂枝斗趣若如一貫的以開玩笑終場,就“失去了桂枝救父的悲痛心情”,于是在桂枝掩口一笑轉身朝下場門走時,又增加了桂枝“又回轉身來,看了看手中狀子,做出啼哭的樣子,然后才走了進去”這一身段,這樣就更符合劇情規定⑦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60頁。。他對《龍鳳呈祥》中趙云、孫尚香上下場的重新安排,是因為這樣“對劇情是比較合理的”⑧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頁。。
一如他要求創作手法契合人物形象之后還要注意外形美,在強調舞臺表演要符合劇情規定性的基礎上,他提出,“要在吻合劇情的主要原則下,緊緊地掌握到藝術上‘美’的條件”“除了很切合劇情地扮演那個劇中人之外,還有把優美的舞蹈加以體現”⑨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303頁。。顯然,就此所表述的美學觀而論,依據劇情規定進行舞臺表演是基本的美學要求,而能夠以更為優美的外形呈現劇情則是相對較高的美學要求。
四、注重戲曲舞臺創作的適度與整一
戲曲作為綜合性極強的藝術形式,內在地要求戲曲作品各方面的恰適與整一,而不能單獨凸顯某一個方面,即使對于演員個體而言在舞臺表演時也須如此,否則就會出現賣弄某一技巧的嫌疑。對戲曲創作的此種特點,梅蘭芳顯然有著獨到的認識,并從此內在特點出發,總結出在戲曲創作時要遵循表演的適度與整一的美學原則。
適度美表現在密切相關的兩個方面:一是就戲曲作品創作而言,即要演員表演不能出現“灑狗血”的過火現象。如他說,“京劇有一定的繩墨,工夫要深,一舉一動都得按規矩,不然就要脫格,哪怕是一個寫實的動作,寫實也有程度的限制,超出限度,就覺得刺眼,不調和”①子岡:《梅蘭芳抵平記》,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三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頁。,“我對于舞臺上的藝術,一向是采取平衡發展的方式,不主張強調出某一部分的特點來的”②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頁。,身段“只要做得好看,合乎曲文,恰到好處,不犯‘過與不及’的兩種毛病,又不違背劇中人的身份,夠得上這幾種條件的,就全是好演員”③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頁。。批評一些演員“只顧為了吐字清楚齜牙咧嘴,矯揉造作,就會有損舞臺形象,給觀眾以過火的感覺”④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56頁。。批評有演員把《玉堂春》中王金龍與劉秉義的對手戲“演成對立的地位,好像當場要開火的樣子”,就“犯了過火的毛病”⑤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頁。。同時也要求舞美不能過度,他說,“我見過有些劇團,遇有八員將的場面,為了增加威嚴火熾,讓八員將都戴翎子狐貍尾,其實八員將中至多有二員翎子尾就夠了,‘整齊美’超過了飽和點就不美了。”⑥梅蘭芳:《談戲曲舞臺美術》,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三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頁。二是觀眾的審美感受,即戲曲創作要讓觀眾感受到一種“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紅,著粉則太白”的美。關于此,他在評價日本歌舞伎時有著明確表述,他說浮世又平扮演《傾城返魂香》中的弁慶,在表演上有著“內在的節奏”“極精確的格局”,“所以才使觀眾有一種‘適度感’”,并說“表演藝術能使觀眾有‘適度感’,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⑦梅蘭芳:《看日本歌舞伎劇團的演出》,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348頁。。可能正是為了實現戲曲創作給觀眾以“適度美”,梅蘭芳先生才更為注重戲曲舞臺表演的“適度”和內在的“分寸”,甚至告誡青年演員,“假使火候不到,寧可板一點,切不可扭捏過火,過火的毛病,比呆板要嚴重得多”⑧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頁。。之所以“嚴重得多”,顯然是此類表演嚴重違背了梅蘭芳的戲曲美學觀。
戲曲創作講求“一棵菜”。如余叔巖就說:“戲要演得‘整’,一場,一節,乃至一個身段,都要像‘一棵菜’那么整齊才有精神。”⑨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頁。就戲曲演員表演而言,既強調多位演員在舞臺表演上的緊密配合,也強調單個演員表演的完整,以及樂隊與演員之間的配合。如梅蘭芳在談及《穆桂英掛帥》“坐帳”一場中四員大將的盔頭時稱,“比武的幾個人,身份職位并沒有規定相同,應該有理由一個人一種打扮。‘坐帳’一場四員將都扎靠已經表示了身份大致相同,盔頭還是差開來戴比較好些。這一類型戲的服飾安排,應該是在整齊一律當中,要求每人有特點。‘整齊美’表現在幾員將一律都扎靠,‘特點美’表現不同的靠色、不同的盔頭。”①梅蘭芳:《談戲曲舞臺美術》,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三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頁。這里雖然意在說明四員大將要從靠色、盔頭上有所區別,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前提是四員大將都扎靠,即首先是有“整齊美”的存在,然后再注意“特點美”,“整齊美”與“特點美”在作品內的共同呈現,正是“一棵菜”創作原則的遵循,亦是整一美學觀的實踐,更是為了配合適度美學觀的實現。再如梅蘭芳談群戲的舞臺創作稱:“群戲就是集體制作,每個角色都要演得有分量……戲扣子要扣緊,不能有絲毫松懈……要嚴絲合縫,否則戲就瘟了,就索然無味,集體創造的群戲就無法達到很高的境界。”②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頁。由此可以看出,這就是說演員在舞臺上的表演配合要整一,只有這樣,作品才能達到很高的境界,給觀眾以美的享受;就每位演員的表演而言,亦要達到各種創作手法的相互諧和、完整如一。如他稱演員“必須吐字準確,氣口熨貼,面部還要保持形象的‘美’,然后配合動作表情,唱出曲情、味兒,使觀眾看了聽了之后,回味無窮,經久難忘”③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56頁。;稱贊譚鑫培、楊小樓的演出“從來是演某一出戲就給人以完整的精彩的一出戲,一個完整的感染力極強的人物形象”④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63頁。;批評以前的“觀眾只注意一腔一調一舉一動,每到一個所謂‘俏頭’的過節,觀眾經常報以彩聲”;稱揚現在的觀眾“從整體上欣賞”⑤梅蘭芳:《勞動人民使我的藝術創造有了新的生命——慶祝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76、277頁。表演藝術。對演員與樂隊之間的配合,梅蘭芳也有明確的表述,他說:“有了好演員,還要有好樂隊的伴奏……主要的是打的、拉的和唱的都應該了解劇中人在特定環境中是有些什么情感,把它充分而恰當地表達出來,這樣,才是一出完整無暇(瑕)的真正好戲。”⑥梅蘭芳:《創造性地運用傳統程式》,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頁。可以看出,一出真正的好戲,梅蘭芳認為不僅是有好演員的好表演,還要有好樂隊的好伴奏,雙方緊密配合,完好地完成劇情設定的情感與人物形象。對梅蘭芳的整一戲曲美學觀,學界已有關注并予以總結,如劉禎就稱:“梅蘭芳的‘完整’理論,追求的是藝術完整,不是表演的一招一式,不是唱念,不是身段,但又是包涵了唱念和身段的藝術整體。”⑦劉禎:《論梅蘭芳表演理論及體系——〈舞臺生活四十年〉個案研究》,《民族藝術研究》2015年第1期,第79頁。
五、追求戲曲表演的平淡、自然
人的審美無疑會受到閱歷、年齡等變化的影響而發生改變,梅蘭芳亦是如此,他晚年對戲曲美學的追求與他早年相較,已經由追求新穎、炫奇轉變為追求平淡、自然。關于此,梅蘭芳在多篇談戲的文章中都有述及,如他在《中國戲曲的表演藝術》中說:
我早期的唱腔是當時流行的青衣的傳統唱法,比較簡單樸素。自開始排演古裝新戲,自己就琢磨比較新穎的唱腔來配合新穎的裝束。當然這是和先后伴奏的幾位琴師如茹萊卿、徐蘭沅、王少卿等的辛勤勞動分不開的。從初期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一直到四本《太真外傳》為止,我覺得在唱腔方面已經繁復多樣,似乎不能再向這方面發展了,所以后來排演的《抗金兵》《生死恨》,在唱腔設計上就走向了平正通達的一路,不以追求新奇為目的了。我在去年為國慶十周年獻禮排演《穆桂英掛帥》一劇,唱腔設計更以沉著簡練為主,聽上去好像比以前所排新戲的腔調簡單些,但實質上并不簡單,也就是說這出戲的唱腔和唱法,更多地注重表達劇中人復雜的思想感情方面。①梅蘭芳:《中國戲曲的表演藝術》,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二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93頁。
可見,梅蘭芳早期在唱腔的美學追求上,因為那時的青衣唱腔整體上“比較簡單樸素”,他為了實現青衣唱腔美學的突破,于是就以“新穎”“新奇”“繁復多樣”為唱腔設計的美學標準,同時還配合以“新穎”的裝扮。這時他的戲曲美學追求鮮明地表現在一個“新”字上。但到他演藝日益成熟之后,他卻不再以求“新”“花巧”②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頁。為美學旨歸,而是追求以“平正通達”的形式進行基于劇情的人物形象立體塑造。另如他在《舞臺生活四十年》中說:“在民國初年,新腔之風雖未盛行,但我排演新戲時,總想琢磨些新穎動聽的腔調”,只是后來他漸漸覺得,“有些炫奇取勝的唱腔,雖然收效于一時,但終歸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本身是不協調的,同時,風格也是不高的”③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256頁。。可見,梅蘭芳之所以認為唱腔不能再向“繁復多樣”的新穎、炫奇一路發展,是因為他認為這種戲曲美學的風格不高,只能收效于一時。于是,他開始在戲曲創作中以平淡、自然為戲曲美學的遵循,對此他有著明確表述:“我覺得演劇的要訣,由絢麗歸于平淡,方是學到功深。譬如運一腔,做一身段,教臺下觀眾注意,并不是一件難事,但是一定要耐人尋味,好像吃橄欖,有回味,越到后來越甜,才能夠抓得住觀眾”④梅蘭芳:《綴玉軒回憶錄》,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頁。;“我認為:一些生活細節的描寫,要準確而又自然,不能被程式束縛,同時要理解到細致不等于繁瑣,緊湊不等于趕落”⑤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306頁。;“我的中心主張,在唱念做工表情方面,屬于舞臺上的基本工作,全部吸收了進去。我覺得最需要的是‘自然’,最忌的是‘矜持’。在我演出的技術上,似乎有了一個新的境界”⑥梅蘭芳:《拍了〈生死恨〉以后的感想》,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頁。。從這些表述中不難看出,他不但把表演的“歸于平淡”“自然”視為表演功力深化的表征和“新的境界”,而且最終是要通過以看似平淡無奇的創作手法創作出“耐人尋味”的作品。
如果再進一步追尋梅蘭芳所追求的平淡、自然之戲曲美學觀是一種什么的藝術境界,也許從他評價“譚老的藝術,晚年已入化境,程式和生活融為一體,難于捉摸”⑦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71頁。中可以窺知一二,亦可從稱贊梅雨田胡琴藝術是“渾脫綿密,天衣無縫”⑧梅蘭芳:《綴玉軒回憶錄》,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頁。的評語中略知其概。
結 語
以上僅是從梅蘭芳有關戲曲美學的表述中進行的梳理、勾勒與歸納,同時為了敘述的方便把其戲曲美學觀劃分為五個方面。就其戲曲美學觀的形成來看,除在其演藝生涯中有著從追求外在表演手法的新奇到平淡通達的變化外,其他幾個方面皆是緊密相連于一體的,無論是講求創作手法的新奇,還是追求創作手法的自然,皆不是脫離劇情、人物內心情感體驗的單純炫技,如他稱所編古裝新戲中,“‘劍舞’‘羽舞’‘拂塵舞’雖然著重在舞蹈,但仍然是為劇情服務的”①梅蘭芳:《我的電影生活》,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七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頁。,在民國初年琢磨的新腔調也是為了“加強表現劇中的人物”②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五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頁。,且他從小“就喜歡追究劇中人的性格和身份,盡量想法把它表演出來”③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載梅蘭芳著、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四卷),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頁。。可以說,正是因為梅蘭芳立足于自己多層位、多側面的戲曲美學觀,依據劇本及劇本所設定的劇情、人物,使得他在走上戲曲舞臺成為“藝術品”的同時,也創作出了一系列令觀眾視聽適度而內心又回味無窮的戲曲作品。既然事實已經證實他的戲曲美學觀對戲曲表演創作是行之有效的,顯然其對當今青年戲曲演員的美學觀形成與建立有著重要的效法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