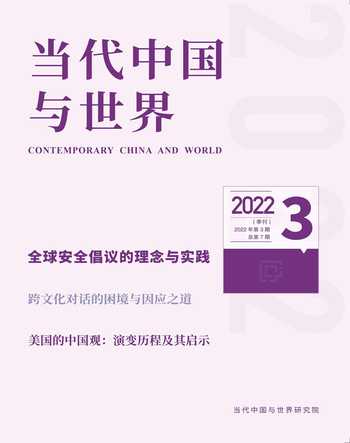美國的中國觀:演變歷程及其啟示
王棟 陳涵
【關鍵詞】美國;中國觀;中美關系;舊接觸共識;新接觸共識
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哈羅德·伊羅生(Harold Isaacs)曾經這樣形容美國的中國觀:“我們對中國人的認知是其兼具聰慧和無知、活力和可鄙、保守和極端、達觀冷靜和突發暴力。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總是在同情與反感,家長式的愛護與惱怒,鐘情與敵視,熱愛與憎恨之間徘徊。”美國對中國情感的雙重性貫穿中美交往的漫長歷史,在近代、冷戰和后冷戰時期交織并存,并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以多樣的形式呈現。
近代,隨著中國國力的衰退,美國在對華商貿、傳教和援助時將中國看作需要經濟擴張的對象和可供改造的弱國。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視中國為站隊在蘇聯陣營中的敵人。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破冰進程開啟后,美國開始將中國看作對抗蘇聯的“準盟友”,并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形成了對華接觸的新認知框架。后冷戰時期,克林頓、小布什兩任政府在遏制和接觸之間搖擺,但總體延續了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所確立的接觸路線。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兩國實力差距逐漸縮小,美國精英對華疑慮逐步上升,負面認知不斷加劇,中國開始被美視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對其霸權地位構成威脅,從奧巴馬到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逐漸成為美國戰略界的共識。
一、近代美國的中國觀在中美開啟交
往歷程之前,美國的中國觀受歐洲思想影響頗深,總體對中國持贊譽態度。第一批美國人來華后,在異國制度、倫理沖擊之下改變了以往從歐洲思想家著述中積淀的對華友好認知。鴉片戰爭后,中國的貧弱更讓美國人的情感從仰慕轉變為輕蔑。近現代以來,隨著中國有識之士救亡圖存運動的興起和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的涌現,美國的這種輕蔑感又發展成為同情感,將中國看作是需要被保護的對象,并以“恩賜者”的身份自居。
(一)清朝中晚期:從“羨慕”到“失望”
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航中國,正式開啟了中美之間的交往歷程。此時的中國正在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治之下。清朝中晚期是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的交變期,既面臨著內部性的破朽和革新,又遭到西方工業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沖擊,被李鴻章稱為“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國力由盛轉衰影響著這一時期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對中國的情感在清朝中晚期經歷了從“羨慕”再到“失望”的轉變。
在“中國皇后號”抵達中國之前,美國人主要通過傳入美國的中國商品和歐洲思想家的著作了解中國。精美的絲織品、瓷器和茶葉貿易,以及伏爾泰、萊布尼茨等歐洲思想家筆下對中國文明的肯定性敘述錨定了美國對中國的正面印象。伏爾泰曾經在《道德論》中提出中國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對中國的官僚體系大加贊揚。包括本杰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杰斐遜在內的一批美國開國元勛都對中國的社會體系和制度運作頗為向往。富蘭克林甚至曾考慮派使者前往中國,讓“年輕的美利堅民族”可以學習中國法律。在美國人眼中,這一時期的中國官僚體系成熟、軍事力量強盛、生產力強大,是值得效仿的對象。然而,正如費正清所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這一時期的中國觀,是“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并被“日后通商口岸那些對哲學不感興趣的商人和領事的誹謗而粗暴地粉碎了。”
在“中國皇后號”來華后,美國人首次親身進入中國的環境氛圍當中,兩種世界秩序相撞,中美之間殊異的秩序觀、價值觀給美國人帶來直接沖擊。基辛格在《論中國》評論道,“中國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它從未長期地與另一國在平等的基礎上交往過……和美國一樣,中國認為自己發揮了一種特殊作用,但它從未宣揚過美國式的普世觀并借此在世界各地傳播自己的一套價值觀,而是僅把注意力放在駕馭近鄰的蠻夷上。”西方以主權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朝貢體系觀大相徑庭,在清朝統治者看來,不論是以馬戛爾尼為代表的英國人,還是以美商為代表的美國人,都是未開化的“蠻夷”,是需要被“天朝上國”教化的對象。這一時期,美國認知中國的主體是美國商人和傳教士,他們均對清朝統治者的秩序觀感到不滿。美國商人在親身經歷了廣州十三行的官員對其盤剝后,產生了深刻的落差感。禁教政策也使來華傳教士對中國產生憤恨情緒。早在1832年10月,由美國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載文稱,中國人的主要特征是“自私”“驕矜和傲慢”,并且“以劣等民族看待外國人”。但這一時期,出于傳教和經濟利益獲取的需要,美國傳教士和商人對中國的態度總體上是順從的。例如,美國學者雅克·當斯(Jacques Downs)就曾經提及,“美國人……由于貿易而懦弱地向中國更加嚴酷的專制屈服。……致力于在世界各地謀生的美國人會愿意服從《防夷新規八條》,按照中國的方式來尋求機會。”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戰敗扭轉了美國人對中國的正面看法。中國國力的衰弱、在條約談判時的故步自封都讓美國意識到中國的落后性,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也從朝貢體系下的大國印象轉向了羸弱之國的認知,并以“黃禍論”為借口為對華擴張尋找合法依據。“黃禍論”同時也影響了美國的排華浪潮。1849年淘金熱的興起和鐵路修筑擴展了美國對勞動力的需求,《蒲安臣條約》簽訂后,一批中國勞動力來到美國尋求工作,參與到美國的鐵路和礦工工作當中。然而,在輕視中國的總基調影響下,大量華工被歧視,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這一時期,美國對華負面的中國觀折射出其經濟擴張和塑造中國的意圖。出于開拓市場的需要,美國商人團體致力于游說美國政府,將中國納入條約體系中,從而為其提供貿易的制度性便利,進而增強了美國對華政策當中的擴張性。而“天定命運”觀和“山巔之城”的新教文化則支配著美國傳教士的傳教邏輯,使其將中國看作“異教之國”,企圖將之納入其所宣揚的新教觀當中,改造在傳教士看來“愚昧”的國家。
(二)二十世紀上半期:從“蔑視”到“同情”
直到20世紀初期,美國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才有所轉變。受中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等救亡圖存的變革運動影響,許多美國政要開始對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的興起抱以同情和敬意。這一時期,部分中國人吸收了美西方的民主思想,并將之運用于中國體制改革中,譬如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便受到了林肯思想的影響。孫中山還將林肯提出的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譯為“民治、民有、民享”。因此,當時相當一部分美國精英開始認為,有必要對向積極學習美國、逐步靠近美國的中國予以援助。
在清政府衰亡之初,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仍舊保持輕蔑。孔華潤(Warren Cohen)觀察到,隨著美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蓬勃開展,“到19世紀末,當美國已利用它巨大的能量并成為一個偉大的工業強國以后,某些美國領導人及許多美國人民都希望看到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來行動。”美國的戰略視野拓展到了全球,并且日漸關注其在亞洲可攫取的利益。鑒于美國人認為清政府軟弱無能,加之美國國內的擴張主義思潮、種族主義思潮泛濫,諸多美國政要在晚清時期持負面中國觀。譬如,美國時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將中國看作是衰落中的國家,認為同處亞洲地區的日本比中國更值得尊重。
隨著中國一批有識之士民族意識的覺醒,美國人在與中國互動的過程當中也逐漸意識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帝國主義擴張不僅撼動了中國傳統的專制統治秩序,也使中國卷入西方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中,主權和國際法等各種西方國際體系概念涌入知識界,催動了中國人現代國家意識的形成和民族意識的覺醒,鄉紳、學生、新聞記者和商人開始關切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合法權益。從義和團運動,到辛亥革命運動,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的涌動喚起美國對中國的同情心。西奧多·羅斯福曾經抨擊美國嚴酷的移民政策給中國帶來傷害,其在1905年12月的國情咨文中曾經提到,“在實施排華政策的過程中,美國對中國及其人民極不公正。”與此同時,美國民眾對中國人好感度增強,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傳教士對中國看法的影響。這一時期,美國傳教士將中國看作一個“被救贖”的對象,其長期居住在中國,對中國遭受的苦難有更深體察,返美后時常號召美國民眾為在華傳教事業捐款。民意的轉變和教會的支持也影響了威爾遜政府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秉持理想主義傳統的威爾遜認為,中國正在向現代化邁進,有必要擴大美國的援助以幫助中國人民實現獨立和現代化的愿望。然而,鑒于美國在中國利益范圍的狹小,中國始終處于美國外交政策議題的邊緣位置。
“七·七”事變發生之后,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大舉入侵客觀上損害了美國在東亞的利益,中國首次成為美國政治中的重要討論對象。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表現喚起了美國對中國的同情乃至敬佩。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麥克斯韋爾·漢米爾頓贊揚中國“在戰爭中做出了許多英勇的事情”,認為“一種真正的民族主義精神在中國興起了……在與西方的接觸中,中國的精神得到了復興”。然而,受經濟大蕭條的爆發影響,美國孤立主義思潮興起,以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為代表的“不承認主義”主導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盡管美國政府認為日本侵華損害了美國自19世紀末開始在中國實行的“門戶開放”政策,但“不承認主義”對日本行為的實質干預非常有限。1944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國正式加入太平洋戰場,開始對日作戰,才對中國展開大力援助。由此,在抗日戰爭中,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與其實際行動之間產生了張力。一方面,美國民眾和政府一致性地對中國抗日行動抱以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在東亞的利益判斷影響了美國援助中國的實際行動,使其在中日之間保持了微妙的中立。
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美國政府和公眾對中國持同情態度。但與此同時,在對華政策的實際執行層面,美國政府又受到兩股力量的撕扯牽拉。一方面,部分以史汀生為代表的孤立主義者在中日之間保持著微妙的平衡;另一方面,以威爾遜為代表的理想主義者認為,一個強大的獨立的中國更加符合美國的利益。這一時期美國情感上憐憫中國,但其本質仍舊將中國看作一個可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弱國,是以恩賜和庇蔭的居高臨下心態看待中美之間的合作。
二、冷戰期間美國的中國觀
二戰結束后,世界秩序經歷重構,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極格局確立。這一時期,美國的中國觀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冷戰思維,而中美蘇戰略大三角的成型則驅動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以中美關系正常化為時間節點,美國在冷戰期間的中國觀總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從新中國成立到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前,美國對中國的看法總體呈負面,從意識形態出發,視中國為“威脅”和“敵人”;二是從中美關系正常化到冷戰結束,這一時期美國將中國視作對抗蘇聯的“準盟友”,并期望中國實現朝向“現代化”的改革。
(一)新中國成立后至中美關系正常化前:從“期待”到“仇恨”
受冷戰意識形態影響,美國在新中國成立后對華敵意上升。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抗美援朝”更使美國確信中國正在從“一個美國人民傳統上以輕蔑、憐憫及同情態度對待的國家”,轉變為美國“最害怕的敵人之一”。該認知主導了美國政府的對華遏制戰略,一直到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前,兩國關系長期處于敵對狀態。
自抗戰后期至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國民黨敗退臺灣,美國的中國觀持續搖擺動蕩,在支持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問題上舉棋不定。1944年,美國專門派遣美軍觀察組(也稱迪克西使團)進駐延安,考察國共兩黨的關系。在見證了國民黨消極抗戰的行徑和腐敗無能的作風后,美國對國民黨日漸失望。例如使團成員之一謝偉思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官員抱持負面看法,其在1944年發回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提及:“可以說現在的國民黨是軟弱的、無能的、抗拒合作的。”相比之下,使團對共產黨的認知顯得更為正面。使團成員曾經在1945年制作了一部反映延安生活的電影,并在片段中表示,“中國共產黨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簡樸。他們的精力、活力和真誠與腐化的國民黨形成鮮明對比。”包括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特朗在內的部分美國進步人士都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引領建設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然而,美蘇冷戰開始、國共內戰爆發后,美國越來越擔心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結盟威脅美國,美國決策層中的親共聲音逐漸被削弱。1947年,曾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阿爾伯特·魏德邁在華調查后發布報告,認為“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將對美國有害”,主張美國應該扶植國民黨。
國共內戰后期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方面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已是大勢所趨,在對華路線上又陷入了新一輪搖擺。為了擺脫國民黨失敗對美國威望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國務院首任政策規劃司司長、遏制戰略的提出者喬治·凱南于1948年9月開始主持重新審議對華政策,認為“中國革命發展的結果是由于中國內在原因所致,非美國力量所能逆轉”,并主張“視情況決定承認誰的問題”。1949年8月,由“艾奇遜小組”編寫的長達1054頁的《中美關系白皮書》發布,稱國民黨垮臺是因自身腐敗無能所致,與美國對華援助無關。為了確定新中國成立后的中美關系路線,美國國務院還于1949年10月6日至8日召開圓桌會議,邀請費正清、鮑大可等著名漢學家和工商界人士、政界人士共同商議對華路線,其中多數主張承認新中國。美國還保持和中國各方力量的接觸,例如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時任中共南京軍管會外事處主任黃華在南京展開溝通,并表示其將“努力使中美關系完善解決”。然而,美國內部反共聲浪日漸洶涌,美國對蘇聯遏制態勢持續強化,致使美國最終并未做出承認新中國的決定,而是采用一種所謂“等待塵埃落定”的政策觀望中國的走向。
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抗美援朝”,中美在朝鮮半島直接的軍事對抗使美國對中國轉而產生了敵意和憎恨感,也使美國正式拋出對華遏制路線。這一時期,美國民眾和精英都對中國產生了負面的看法。此外,新中國推行的“一邊倒”外交政策路線,也讓美國部分政要意識到了中國加入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決心。在美國人看來,中國人和蘇聯人一樣都是“赤色威脅”,是美國的敵人。這種觀點最為典型的代表是盛行于1950年到1954年的麥卡錫主義,在這一以美國反共參議員約瑟夫·雷芒德·麥卡錫命名的反共主義思潮煽動下,美國大量進步人士遭到迫害。美國時任國務卿約翰·杜勒斯也在演講中提及,要對中國共產黨實施孤立和包圍。約翰·肯尼迪上臺后,將中國視為東南亞地區和南亞地區的威脅來源,并通過對越南的軍事干預以及對印度的軍事支持與中國在越南戰爭和中印沖突中展開對抗。1964年中國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使美國人的精神更趨緊張,無理指責中國“藐視人類生命和公認國際道德標準”,有摧毀國際秩序的明確意圖。這種敵意認知在約翰遜政府上臺后持續強化。美國著名民調公司蓋洛普(Gallup)的調查結果顯示,1967年,美國公眾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達到91%。
對華遏制戰略的醞釀及其產生并不偶然,美蘇對峙的國際格局和美國國內反共、反華力量的膨脹共同推動了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生成。由此,美國對華敵意在冷戰期間長期持續,并主導了中美兩國長達二十余年的對峙,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再到肯尼迪政府均對中國奉行貿易禁運、軍事圍堵的“遏制”戰略。
(二)1972—1991:從“敵對”到“接觸”
根據蓋洛普20世紀70年代的數據,1973年,美國受訪公眾中有53%對中國印象積極,而在1972年,這一占比僅有23%。導致美國公眾對中國態度發生轉變的重要變量是中美關系的正常化。伴隨著中蘇關系惡化、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漸趨孤立和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泥潭深陷,中美兩國決策者在這一時期都在謹慎地思考和調整自身的外交路線。這一時期,中美關系正常化和美國對華態度好轉相輔相成。前者為美國人了解中國打開了重要通道,使得美國傳統的以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思維為主導的中國觀有所打破,豐富了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討論,而在后者的促進之下,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開始思考與中國開展交往的可能性。
美國對中國認知轉變的討論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肯尼迪當政時期。此時的美國與蘇聯一度在古巴導彈危機當中陷入核大戰邊緣,同時美國國內左翼思潮的發展沖擊了美國社會賴以運行的自由主義思想根基。美國政府面臨國內外的雙重壓力,在國際社會則表現為實力的相對衰落,使得美國外交政策傳統當中現實主義的一面逐漸占據了對外政策當中的主線。“兩個中國共存論”是這種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的折射。1959年,美國民間學術團體康倫協會(Conlon Association)為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撰寫一份關于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報告,并在美國亞洲政策設計中首次提出了“一中一臺”的方案。1962年,美國著名智庫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開展了以中國研究為主題的項目,并于1967年出版了《世界事務中的美國與中國》叢書,其研究核心是主張“重新審議中國情況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得失”。1963年11月,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甚至提出,美國“期望中國被帶回到國際大家庭中來,與鄰居們欣然和平相處”。這種所謂“遏制但不孤立”的對華戰略思想成為中美之間接觸戰略的雛形。
尼克松政府時期,對華正常化思想正式形成。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事務》雜志撰文提及,“長遠來看,我們不能將中國永遠置身于國際大家庭以外,任其憤怒和仇恨滋長,并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我們沒有足夠的空間讓近10億最具潛力的人民憤怒地生活在孤立之中。”尼克松的上述討論可以被看作是“遏制但不孤立”思想的一種延續。1968年尼克松再次參選總統并獲勝,次年1月就任后,尼克松在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均勢思想運作之下,形成了與中國展開接觸,從而對蘇聯進行制衡的外交路線。1969年7月,尼克松在關島提出“尼克松主義”,將中國視為世界主要的力量中心之一。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訪華,中美關系正常化的破冰歷程由此開始。
從尼克松政府開始,對華接觸(Engagement)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美國戰略界意識到,與中國維系良好的大國關系是全球穩定的基礎,中國能夠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對抗蘇聯的力量。在這一共識指導下,中美之間高頻度的軍事、經貿合作有序展開,共和黨和民主黨精英均對中美關系的和解作出積極回應。1978年12月,卡特政府宣布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美兩國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一個中國”政策開始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石。里根政府時期,中美之間展開了大量軍事合作。美國總統里根1981年簽署的第11號“國家安全決定指令”準許美國國防部對中國出售先進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導彈技術。1983年,里根決定啟動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計劃。而圍繞臺灣問題,中美在里根時期簽署了《八一七公報》,美國承諾將逐步減少對臺軍售直至最終解決。
美國這一時期的對華接觸框架帶有對抗蘇聯的意圖和“改變”中國的期待。正如里根在第140號“國家安全決定指令”所提及的:“美國尋求推動中國保持獨立于蘇聯;鼓勵中國引入市場化力量,持續擴大其同民主國家的聯結;協助中國現代化是基于強大安全和穩定的中國可以是增進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力量。”中美在正常化后形成的“準同盟”關系本質上受中美蘇大三角關系的影響,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又懷有將中國納入世界秩序的意圖,企圖將中國塑造為符合美國民主價值觀的國家。
三、冷戰后美國的中國觀
冷戰的結束標志著國際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化。伴隨著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的解體,兩極體系終結,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國際體系開始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啟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經濟實力迅速增長,加速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美國戰略家普遍預測中國可能會在未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如何與一個日漸融入國際秩序并產生重要影響的中國共處就成為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當中的主要問題。中國學者王緝思曾經指出:“冷戰后的美國對華政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限制中國國力增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又要同中國保持交往和合作。”以冷戰為界,這兩股力量相互交疊、此消彼長,作用至今。從1992年到2010年,美國中國觀總體而言表現為交往與合作為主,限制為輔的路線;然而從2010年開始,美國對中國看法中限制的一面逐漸壓過了合作的一面。
(一)1992—2010:在“搖擺”中“接觸”
不論是克林頓政府的“戰略接觸”,還是小布什政府的“利益攸關方”,抑或是奧巴馬政府初期美國戰略家所提出來的“G2”(兩國集團)思想,從1992年到2010年,美國對華戰略路線在“接觸”和“遏制”的天平之間搖擺。這背后折射出美國中國觀在形成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即美國究竟應以共存還是對立的態度對待中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貫穿在1992年到2010年的三任政府間。
1992年,克林頓上臺之后,適逢冷戰剛剛終結,美國掀起了對華政策的大辯論。在這場辯論中,美國國內形成了“接觸”和“遏制”兩種立場,其中接觸路線的支持力量多于遏制一方。在接觸派看來,遏制路線明顯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時任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認為:“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在將來一定會成為敵人。對中國采取遏制戰略(Containment)可能會導致‘敵意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在應對中國崛起方面,克林頓政府的接觸政策是更好的政策路線。”鑒于這一時期全球化深入發展使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程度進一步加深,美國主流精英不愿意被隔絕于一個快速發展、充滿市場潛力的中國之外,因此反對對華采取遏制戰略。此外,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向世界表明了進一步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也被西方戰略家視為積極信號。權衡之下,克林頓政府最終做出了對華“戰略接觸”
(Strategic Engagement)的決定,并于1998年訪華期間確定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繼承了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融合路線。盡管在克林頓任期內,中美之間有諸多矛盾和摩擦,如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最惠國待遇問題、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等等,但總體而言,每一次危機都因中美兩國落實了有效的危機管控措施而結束,這表明了雙方不愿重走相互敵視老路的意圖。
小布什從競選時期再到上臺初期,新保守主義力量主導了布什政府內部對華觀點,將中國看作是“潛在的競爭對手”。在這種負面觀點的影響下,中美關系在小布什政府初期一度十分緊張,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1年“9·11”事件的爆發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折點,使美國將反恐列為外交政策的優先議程。與大國之間的反恐協作需求增強了美國對華合作的意愿。2005年9月,時任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演講時提出,美國應鼓勵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與“我們一道維護現存國際體系。”面對當時美國有關中國“和平崛起”理念的負面輿論,美國時任國務卿賴斯還回應提出“美國歡迎一個自信、和平、繁榮的中國崛起”。受接觸戰略思想影響,美國先后接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全球反恐問題上尋求與中國的合作,甚至在中美最為敏感的臺灣問題上由小布什總統親自出面明確表態“反對臺獨”,從而推動中美關系進入黃金期。
奧巴馬政府前期,美國戰略家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延續了對華“接觸”路徑,甚至將中國當作一個與美國同等位置的大國來看待,“兩國集團”(下稱G2)共識就是奧巴馬政府初期由一批有影響力的美國戰略家提出的戰略思想。2008年7月,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長弗雷德·伯格斯騰(Fred Bergsten)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展出G2概念,認為中美可以合作形成“領導世界經濟秩序的兩國集團格局”。ヒ此后2009年1月,民主黨資深戰略家、曾任卡特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在《金融時報》發表題為《可能改變世界的兩國集團》一文,明確提出美國應當把中美關系提升至等同于美國與歐洲、日本等主要盟友之間的關系,中美應構筑“全面的伙伴關系”,共同應對從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到朝核問題、印巴沖突等地區性問題。布熱津斯基認為形成“非正式兩國集團”的中美兩國,具有“最非同尋常的潛力,塑造我們共同的未來”。由于布熱津斯基在民主黨內德高望重,并且擔任奧巴馬競選團隊的外交政策總顧問,因此他對G2構想的提倡被認為代表了即將上任的奧巴馬政府的戰略傾向。此外,世界銀行行長、前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等重要政界人士都表態支持中美G2構想。不過部分出于顧慮盟友的反對,奧巴馬上任之后并沒有正式采納G2主張。盡管如此,奧巴馬政府還是明確表示希望能和中國“同舟共濟”,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和其他全球性以及地區性挑戰。美國主流戰略家提出G2構想到奧巴馬表態,表明美國在這一時期對將中國納入國際秩序,并且推動中美兩國共同參與全球事務,為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共同維護國際秩序的意圖。
然而,不論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概念,還是G2構想,美國對華認知本質上受錨定于接觸層面的對沖策略組合所主導:一方面,美國強調對華接觸和融合機制,冀圖中國能受其規訓;另一方面,美國又持續鞏固軍事同盟體系以防范中國崛起。對沖戰略構成理解美國冷戰后對華政策的一條基本線索,影響著這一時期兩國關系的變化。而隨著近年來中國的飛速發展,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疑慮日漸增強,對沖戰略當中防范、牽制的一面顯著上升。
(二)2010年至今:從“接觸”到“競爭”
2010年后,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和美國戰略重心的轉移,美國對華戰略定位的競爭性明顯上升。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具有較為突出的對沖屬性。奧巴馬時期仍然希望能夠“塑造”中國,將中國納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中。因此,當中方提出中美應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之時,奧巴馬政府一度表態積極。2014年11月,奧巴馬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采訪談及中國和地區秩序的關系時,表示美國愿意接受中國成為亞太地區秩序的“主導大國之一”,前提是中國不能將美國排除在亞太之外。不過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疑慮和威脅認知的上升,奧巴馬政府后期對華對沖策略組合中的防范、牽制和制衡等競爭性、強制性的戰略工具的比重有所增加。而以2017年12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布為標志,特朗普政府開始正式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特朗普政府中后期超級鷹派主導對華政策,全面復活冷戰話語體系,將中國視為“比蘇聯更大的威脅”,明確把發動對華新冷戰、擊敗中國作為其對華政策的核心戰略目標。拜登政府相當大程度上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認知,延續并強化了對華全面、長期戰略競爭,但劃了一條底線,即中美不沖突、不對抗,不尋求新冷戰。在過去十幾年中,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戰略意圖形成了嚴重誤判,開始逐步認定中國的戰略意圖就是取代美國,不僅要在亞太地區,而且更是要在全球尋求主導地位,取代美國霸權。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這一認知逐步成為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共識,取代了過去的“舊接觸共識”(OldEngagement Consensus),成為支撐美國對華政策的認知和心理基礎。美國近年來對華戰略競爭框架的產生并非無跡可尋,可被看作是克林頓時期以來美國戰略界對華遏制思路的濫觴,其興起于奧巴馬時期,成型于特朗普上臺以后,并在拜登任期內得到了延續和發展。
早在奧巴馬任期內,美國對華威脅認知就不斷上升,以“中國強硬論”為主要代表的反華論調在美國逐漸興起。以沈大偉、范亞倫為代表的美國部分戰略家認為中國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信心大增,在對外行為上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并且推行“亞洲版門羅主義”,尋求將美國排除在亞太地區之外。奧巴馬也曾經在其回憶錄中認為,這一時期的中國在南海問題、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等等議題上表現出“和此前不同的做法”,甚至有“玩過火”的態勢。2015年,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布萊克威爾和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泰利斯聯合撰寫《修正美國對華大戰略》。在這份對外關系委員會的特別報告中,布萊克威爾和泰利斯指出,美國對華“接觸”戰略不足以規制和塑造中國,主張采取“制衡”,提出美國應該修正對華戰略,更多地強調壓力與競爭。ホ同年,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學者戴維·蘭普頓發表題為“中美關系的臨界點正在向我們走來”的演講,認為美國政策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日益傾向于把中國看成是美國在全球主導權的一個威脅,“中美兩國各自的憂懼比兩國關系正常化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于壓倒我們對雙邊關系寄予的‘希望的臨界點”。在對華疑慮日趨增長的背景下,美國于2015年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過去以接觸為主的對華對沖戰略組合,強調對沖策略組合中的防范、牽制與制衡等戰略工具的比重。マ特朗普上任后,反華論調逐漸主導美國對華輿論界,并最終推動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框架的形成。早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就以“美國優先”為旗號將矛頭對準中國,多次宣稱中國奪走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鼓吹美國制造業回流。2016—2018年,“對華接觸失敗論”成為美國精英界的主流對華認知,其主要觀點認為,中國在市場經濟轉型、政治民主化改革、接受國際規范等方面未達到美國預期,反倒借機實現崛起甚至造成權力轉移,在全球范圍內推行威權體制,威脅美國霸權地位和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因此主張運用“全政府”手段對華進行全面戰略競爭。“對華接觸失敗論”影響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外交路線。在戰略層面,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家防務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等報告出臺為標志,中美關系由奧巴馬時期合作與競爭并存轉向以戰略競爭為主。特別是在2017年12月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首次將中國描述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這標志著美國決策層對華戰略定位正式告別“合作”與“競爭”之間的“搖擺期”,形成了確定的對華戰略競爭框架。ミ在這一框架之下,以特朗普政府國防部長馬蒂斯為代表的傳統地緣鷹派、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經濟民粹主義者和鼓吹人權問題的民主黨人合流,在美國形成了一股反華逆流。
特朗普團隊核心決策成員白宮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國務卿邁克·蓬佩奧以及白宮貿易委員會主席彼得·納瓦羅等反華鷹派均以意識形態視角度量中美關系,夸大渲染中美矛盾、抹黑丑化中國形象,甚至將矛頭直接對準中國的體制和意識形態。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發布《美國對華戰略取向》,標志其正式將新冷戰作為對華政策的核心目標。受上述負面對華認知主導,特朗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并推動中美在經貿、科技和人文領域的脫鉤,成為中美關系的主基調。
拜登上臺以后,盡管在對華路線方面與特朗普有所區分,但總體仍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確立的對華戰略競爭框架。一方面,與特朗普宣揚新冷戰不同,拜登團隊對華態度更為審慎和理性。2021年3月3日,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任內首場外交政策演講,提出中美關系“應該是競爭性的”,“可以是合作性的”,“當必須對抗時則是對抗性的”,“必須基于實力與中國接觸”,意在強調中美關系的主軸是競爭,但并不排除合作的并存。2021年9月21日,拜登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言又表示,“美國并不尋求新冷戰”,減弱了對華表述的沖突性。拜登上任至今,中美兩國高層會晤機制、經貿和人文交流機制有所恢復。2021年以來,中美兩國元首先后舉行了五次通話。拜登在通話中多次重申美國不尋求“新冷戰”的立場,強調中美合作的重要性。2022年2月23日,美國司法部宣布終止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發起的“中國行動計劃”,該計劃要求美國司法部門每年至少提出一至二起針對中國的訴訟,而這一行動的中止可被看作美國在人文交流領域釋放的正面信號。但另一方面,拜登在一定程度上“特”規“拜”隨,繼承了特朗普政府時期對華全面戰略競爭的思想,不愿意放棄對中國的打壓、圍堵。拜登對特朗普路線的延續基于以下兩點原因:其一,拜登團隊仍對中國抱有偏見,奠定了拜登政府對華總體基調。拜登上任后分別任命杰克·沙利文和庫爾特·坎貝爾為國家安全顧問和印太事務協調人,二人曾于2019年在《外交事務》上共同發表文章,指出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應當推出更為強硬的對華路線。モ2022年3月30日,拜登團隊核心成員之一、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國會聽證會中稱,改變中國的行為是浪費時間,并主張采取措施確保美國行業保持競爭力。其二,對華戰略競爭已經成為美國兩黨共識,束縛了拜登政府的認知和政策回調空間。2021年4月21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以21:1的壓倒性優勢通過了《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對中國實施全面“戰略競爭”政策。2021年6月8日,美國參議院以68票贊成、32票反對的結果投票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致力于在技術研發體系、治理模式等方面實現“去中國化”。2022年2月4日,美國眾議院審議通過《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該法案以中國為“戰略對手”,旨在提振美國在科技、教育、經濟、外交等多個領域的競爭力。7月28日,美國參議院又審議通過《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該法案次日在眾議院通過,旨在促進美國半導體行業發展,應對“中國競爭威脅”。在參眾兩院,共和、民主兩黨均形成對華競爭共識的背景下,拜登延續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戰略競爭思想,構筑了全方位規鎖、打壓中國的對華政策。在地緣政治領域,拜登政府把美日澳印四方機制升級為四方峰會(Quad Summit)、與英國和澳大利亞構筑三邊安全聯盟(AUKUS)打造軍事上防范、圍堵中國的“印太”地區網絡;在經濟領域加大對華投資審查,擴大對華出口管制清單以在供應鏈方面“去中國化”;在科技領域采取“小院高墻”策略,對華采取“精準脫鉤”戰略,并以“反制中國‘技術威權主義”等意識形態話術包裹其維護美國科技霸權的目的;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領域,更是大打“人權牌”“民主牌”,刻意將中國描繪為與西方國家對立的“威權國家”和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并以此進行國內和國際的政治動員,試圖在對華全面戰略競爭中壓制中國。
從奧巴馬再到拜登時期,負面性、敵意性的認知元素逐漸主導美國的中國觀。當前,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從期望改變中國的“接觸”思路走向了將中國看作最大威脅的“競爭”思路,以意識形態棱鏡透視中美關系,甚至建構起一種妖魔化、污名化中國并夾雜著美式種族主義的“他者化”(the Othering)極端敘事。受到這種極端敘事的影響,在短短幾年之內,美國民眾對華負面認知也急劇上升。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6月29日發布的民調數據顯示,有82%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較2012的民調結果翻了一倍。
四、結語
從1784年“中國皇后號”首航中國至今,美國一直以來抱持著“改變”中國的傳教士熱忱,試圖按照美國所期望的形象塑造中國,這種美式普世邏輯的價值觀發軔于美國“天定命運”的政治文化,并且塑造了美國外交當中的帝國主義邏輯。美國自詡民主與自由的燈塔,認為自身有義務拯救其他國家,復興人類社會。受這種心態影響,美國在中美關系正常化當中形成了“舊接觸共識”,將中國視作需要“轉變”“整合”“引入”美國主導秩序的“他者”,并由此成為美國兩黨長達40余年對華戰略路線的共同紐帶。然而,這一中國觀本質上存在著“刻舟求劍”的認識論謬誤。在40多年過去之后,如今的中國非但沒有按照美國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反而走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美國很多精英失望了,心態開始失衡,開始認為對華戰略接觸失敗了。現在,美國實際上是從一個極端到了另外一個極端,從最初的“想要改變中國”一下子轉為“視中國為最大的挑戰和威脅”。而這背后也有認知心理學所說的“信念系統的過早閉合”這一機制在起作用。譬如,現在美國相當一部分精英認為,“中國一直對美進行戰略欺騙,表面上談合作共贏,其目標實質是要挑戰、取代美國霸權,而美國現在已經看透了中國的戰略意圖,不會再上中國的當。”這就是典型的“信念系統過早閉合”導致形成的偏見。曾得到特朗普賞識的共和黨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所著的《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一書就集中代表了這種觀點。該書前幾年出版后在美國風靡一時,被很多美國鷹派引為解讀中國戰略意圖的圭臬。無獨有偶,美國“少壯派”中國問題專家、拜登政府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最近也出版了《持久戰:中國取代美國主導秩序的大戰略》一書,斷定中國具有一個長期的逐漸取代美國領導地位與影響力的戰略。盡管該書對中國的戰略意圖做了嚴重誤讀和歪曲,但卻受到美國戰略界、政策界的熱捧。這反映出對中國戰略意圖的這種嚴重誤判和誤讀已經成為美國跨黨派主流共識,也成為支持美國對華全面戰略競爭的邏輯和認知基礎。上述美國近年對華政策變化的認知和心理層面的根源值得關注和深思。
應當看到,中美合作,兩國和世界都會受益;中美對抗,兩國和世界都會遭殃。ル推動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是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回應布林肯對華政策演講時指出,當前美國的世界觀、中國觀、中美關系觀都出現了重大偏差,美方應做出正確抉擇,不要在“三分法”“三點論”上不斷做文章,而是把精力真正放在踐行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上,進而找到中美兩個大國在新時代的正確相處之道。筆者認為,中美之間應當形成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為基礎的“新接觸共識”(New Engagement Consensus),兩國應成為應對共同挑戰和維護全球秩序的兩個穩定支柱,推動全球秩序向著和平穩定繁榮的方向演進。“新接觸共識”要求美國戰略精英摒棄零和思維,采取正和思維,拋棄意識形態和種族主義的狹隘偏見,重建中美之間新的經貿均衡,推動中美關系重回正軌。
在中美戰略競爭中,中國始終是一個“不情愿的對手”。中國反對美方以競爭片面定義中美關系,對霸權競爭毫無興趣。2021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上指出,“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范圍,不搞軍備競賽。中國將繼續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從中國角度看,形成“新接觸共識”需要在看待中美關系時保持開放、理性、審慎的心態。一是拒絕簡單化、靜態化看待美國的中國觀,要認識到美國戰略認知的多元性。就在美國政策界批評對華接觸戰略助長中國權勢、培養了美國的敵人之時,美國前代理助理國務卿董云裳、前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貝德、前駐華大使芮效儉等前政要都曾公開反對“對華接觸失敗論”。2019年7月3日,在美國反華聲浪高漲時,百位美國“接觸派”前政要和學者在《華盛頓郵報》聯名刊登致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公開信,表示“北京并不是必須全方位對抗的經濟敵人或重大國家安全威脅”,“美國把中國當作敵人并使其與全球經濟脫鉤的努力,將破壞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和聲譽,并損害所有國家的經濟利益”。這表明美國精英對華認知并非鐵板一塊,仍存在理性、務實的聲音和力量。二是要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充分發揮人文交流、智庫對話的作用,以最大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推動中美關系良性發展。2022年5月24日,習近平主席在復信美國艾奧瓦州友人時提到,中美兩國人民都是偉大的人民,人民友好既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更為兩國關系發展提供重要基礎。中國人民愿繼續同美國人民一道,加強友好交流,推進互利合作,共同促進兩國人民福祉。要積極通過省州經貿合作、青年人文交流等渠道打開中美兩國良性溝通的通道,增進兩國民眾之間的相互了解,促進友好認知的形成。三是推動中國對外話語的迭代創新,發展出更加柔性、觸動人心的國際敘事,講好中國故事,講好的中國故事。
未來,如果中美兩國能夠踐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就一定能克服當前中美關系遇到的挑戰,推動中美關系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迎來更為美好的中美關系前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新接觸共識”可以為未來幾十年的中美關系發展提供一個總體知識框架。
作者簡介 王棟,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兼智庫中心管理辦公室主任,國際關系學院長聘正教授、博導,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教育部)研究基地執行主任陳涵,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