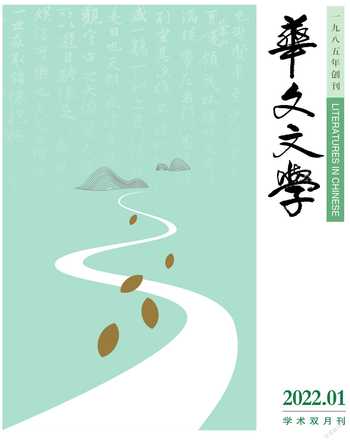“看清楚這個世界上的路”
2022-03-24 08:32:16劉亞群虹影
華文文學
2022年1期
劉亞群 虹影
劉亞群(下稱劉):虹影老師,您好。作為女性主義作家,您曾說女性寫作應進入一個新領域,中國作家需要革自己的命。您所謂的“女性寫作的新領域”具體指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寫作呢?
虹影(下稱虹):女性寫作領域現在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但是作品好像沒有跟上。我們女性寫作者的思想要高于我們的作品這個當然很難,全世界也都是一樣,目前超越伍爾芙和蘇珊·桑塔格的作品還比較少,像波伏娃《第二性》這樣的我們雖然早期也出現過,比如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文學里面有女性身體寫作,但目前現階段沒有特別突出的作品。
劉:閱讀您的作品,我始終有這樣一種感受,那就是您和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們,都執拗地想要去做傳統世俗眼中“男人”做的事,都很“要強”,比如筱月桂和于堇。而您本人也在之前的訪談中對文學史、文學評論、寫小說這些事都由“男人”主宰而“女人”一直處于“弱勢集團”的現象頗有微詞。您自己也說過,您是“女兒身男兒心”。那么您覺得,“女人”拼命地想去做“男人”能做的事,想跟“男人”一樣,這種思維方式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于無形中也落入了男權思維的窠臼?也就是說,它是不是其實還是潛藏著“男人向來比女人強”的內在邏輯和含義?
虹:我覺得人的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是有區分的。比如我知道我是女人,但我的性格以及內在性別卻不是由生理性別決定的,是由我的思想決定的。我的內心像男人一樣堅強。……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名作欣賞(2021年24期)2021-08-30 07:02:24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文學教育(2016年27期)2016-02-28 02:35:09
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4期)2015-06-23 08:50:1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百花洲(2014年4期)2014-04-16 05:52:45
語文知識(2014年7期)2014-02-28 22: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