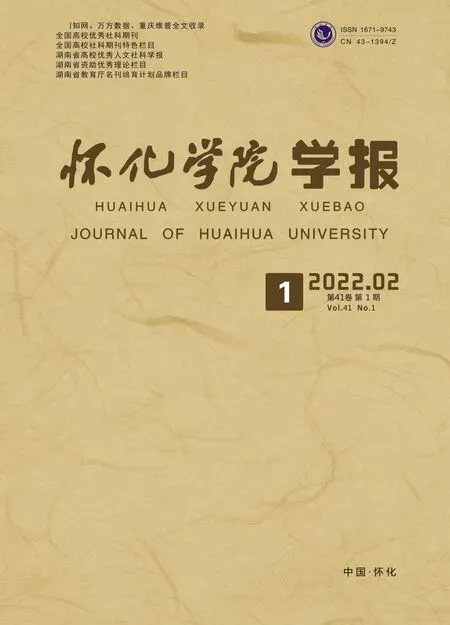基于苗族史詩(shī)《亞魯王》多元文化特征的文化整合研究
劉康凱, 趙 東
(1.巢湖學(xué)院文教學(xué)院,安徽 合肥 238000; 2.貴州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文學(xué)院,貴州 貴陽(yáng) 550022)
史詩(shī)研究專家朝戈金將苗族史詩(shī)《亞魯王》描述為“復(fù)合型史詩(shī)”。他指出:“《亞魯王》的面世,為我們思考‘復(fù)合型史詩(shī)’(跨亞文類) 提供了一個(gè)鮮活的當(dāng)代案例。”[1]復(fù)合型史詩(shī)囊括了北方史詩(shī)和南方史詩(shī)的諸多文化特征,甚至還會(huì)帶有一些西方史詩(shī)的文化特征,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寬廣的文化外延給亞魯王文化研究帶來(lái)一定的難度。史詩(shī)《亞魯王》的文化研究需要從多角度入手,除了史詩(shī)研究常用的母題研究、比較神話學(xué)研究之外,還需運(yùn)用西方人類學(xué)的文化研究觀念和民族志書(shū)寫(xiě)的方式對(duì)史詩(shī)中的文化現(xiàn)象進(jìn)行有針對(duì)性的研究。
鑒于史詩(shī)《亞魯王》文化的復(fù)雜性,對(duì)于史詩(shī)文化的研究可以采取“分”與“合”相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在“分”的基礎(chǔ)上突出“合”的研究。首先是立足于“分”的研究,最終歸結(jié)于“合”的研究。所謂“分”的研究是針對(duì)具體的文化現(xiàn)象分別進(jìn)行個(gè)案分析式的點(diǎn)上的研究,對(duì)史詩(shī)《亞魯王》中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進(jìn)行重點(diǎn)挖掘和分析,從而得出具有一定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的觀點(diǎn)或依據(jù);所謂“合”的研究是指站在跨文化比較的角度進(jìn)行面上的研究,即文化整合研究,通過(guò)搜集整理相關(guān)文獻(xiàn)資料和進(jìn)行跨文化比較,對(duì)史詩(shī)中的主要文化現(xiàn)象進(jìn)行歸納總結(jié)。目前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亞魯王文化的研究成果,點(diǎn)上的成果居多,面上的成果相對(duì)不足,缺乏對(duì)亞魯王文化更為深入的整合式研究。
文化整合研究在西方人類學(xué)理論中并不少見(jiàn),特別是涉及跨文化比較領(lǐng)域的人類學(xué)理論中,帶有鮮明的文化整合色彩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較為成熟。文化人類學(xué)發(fā)展史上出現(xiàn)過(guò)一些著名的文化整合理論,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國(guó)人類學(xué)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論”,法國(guó)神話學(xué)家列維- 施特勞斯的“結(jié)構(gòu)主義神話學(xué)”,瑞士心理學(xué)家榮格的“原型理論”和蘇聯(lián)民間文學(xué)專家普羅普的“母題理論”,等等。這些文化整合研究理論為史詩(shī)《亞魯王》的文化整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參考。面對(duì)苗族史詩(shī)《亞魯王》繁復(fù)多姿的文化現(xiàn)象,還要充分發(fā)揮民族志書(shū)寫(xiě)的長(zhǎng)處,對(duì)史詩(shī)進(jìn)行多視角的文化呈現(xiàn)和表達(dá)。
一、史詩(shī)的稻作文化模式
本尼迪克特將人類文化看成一個(gè)整體的“文化模式”理論是典型的文化整合理論。她認(rèn)為如果把全世界的文化比作一個(gè)圓弧的話,每一種類型的文化出于自身的選擇或者歷史的發(fā)展,終將成為這個(gè)圓弧上的一段[2]。這個(gè)文化之弧規(guī)定了某一種文化類型的性質(zhì),每一種文化類型都是對(duì)于世界某種文化資源的一種選擇,不加選擇的文化類型是無(wú)法獨(dú)立存在的,也無(wú)法傳承。本尼迪克特從行為主義心理學(xué)出發(fā),長(zhǎng)期觀察不同文化的類型,她發(fā)現(xiàn)文化具有地域性的特色,這種文化特性是由于不同類型的文化對(duì)人類共有文化資源的不同選擇和占有而造成的。
亞魯王文化帶有鮮明的中國(guó)南方文化的印記,西部苗族以稻作為主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歷經(jīng)千年傳承而得以保留至今,在社會(huì)功能上和民間信仰層面均有所表達(dá)。史詩(shī)中不斷描繪了遠(yuǎn)古時(shí)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圖景,魚(yú)蝦成群,河汊密布,稻米飄香,是典型的長(zhǎng)江中下游稻作文化現(xiàn)象。稻作文化還孕育出發(fā)達(dá)的商業(yè)意識(shí),史詩(shī)中描寫(xiě)亞魯王支系善于利用山地文化資源,開(kāi)發(fā)礦產(chǎn),興建集市貿(mào)易,稻作文化還積累了豐富的戰(zhàn)爭(zhēng)文化傳統(tǒng),早期的稻作文化區(qū)經(jīng)濟(jì)繁榮,帶來(lái)軍事實(shí)力的強(qiáng)大,這些都是亞魯王文化在長(zhǎng)期的歷史演變過(guò)程中傳承下來(lái)的文化特色。經(jīng)過(guò)筆者的實(shí)地調(diào)研,亞魯王文化的核心地帶,貴州省麻山一帶的苗寨至今仍然保留著稻作文化區(qū)的飲食文化,比如在喪葬儀式上,要不斷用米飯供給亡人,讓亡魂在“返家”途中保持體力。貴州省麻山一帶水資源稀缺,湖泊河流稀少,當(dāng)?shù)孛缛耸终湟曯~(yú)類資源,就算是在很小的河溝中抓到的小魚(yú),也要精心制作成魚(yú)干,以備他日喪葬儀式之用。
亞魯王文化的復(fù)雜性在于,盡管史詩(shī)《亞魯王》反映的大多是南方文化傳統(tǒng),卻也夾雜了一些北方文化。史詩(shī)中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場(chǎng)面的描寫(xiě)和英雄屢經(jīng)挫折不斷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又帶有北方英雄史詩(shī)的文化特征。亞魯王文化中對(duì)動(dòng)植物的描述極其豐富,特別是動(dòng)物的神性表達(dá)帶有北方游牧文化的特征,這也有力地證明了本尼迪克特所說(shuō)的任何一種文化的性質(zhì)都是源自對(duì)人類共有的文化資源的選擇和占有。貴州省麻山一帶土地貧瘠,當(dāng)?shù)刈顬槌R?jiàn)的農(nóng)作物是耐旱的玉米、土豆和麻類,但當(dāng)?shù)厝藢?duì)有限的耕地和匱乏的水資源進(jìn)行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麻山地區(qū)竟然可以找到幸存數(shù)量很少的二十多種農(nóng)作物,而且一半以上農(nóng)作物是北方常見(jiàn)的麥子、小米和各種豆類等。這一方面說(shuō)明亞魯王文化本質(zhì)上是南方文化,但同時(shí)可能在長(zhǎng)期的遷徙過(guò)程中也不斷吸收了北方文化。麻山苗族主要飼養(yǎng)的牲畜有豬、牛和羊,他們對(duì)各種動(dòng)物均有著較為深厚的情感,當(dāng)?shù)厝藝?yán)禁捕殺鳥(niǎo)類,認(rèn)為鳥(niǎo)類是祖先的信使,可以傳遞祖先的信息。亞魯王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對(duì)十二種動(dòng)物的起源和使命均有著細(xì)致的描述,這些描述大多反映出西部苗族的文化歷史傳統(tǒng),也少量夾雜著北方游牧文化的元素。
亞魯王文化有著超常的穩(wěn)定性,既有先秦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禮儀特征,又有三國(guó)和唐宋時(shí)期的制度文化特征,在這樣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下,具有穩(wěn)固文化結(jié)構(gòu)的苗文化禮儀、制度帶有強(qiáng)烈的制約性和傳承性。用文化模式理論來(lái)研究亞魯王文化,可以把苗文化放到數(shù)千年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歷史背景中進(jìn)行考察。文化模式理論的先進(jìn)性在于,它始終保持著文化相對(duì)主義的觀點(diǎn),將文化類型的特色視作文化多樣性的表現(xiàn),而不是以先進(jìn)和落后或者原始和現(xiàn)代等標(biāo)簽來(lái)界定文化類型。文化模式理論的科學(xué)性在于,它堅(jiān)持以行為主義心理學(xué)作為基本研究方法,強(qiáng)調(diào)田野調(diào)查的重要性,在社會(huì)調(diào)研的基礎(chǔ)上對(duì)文化模式中的群體進(jìn)行大量的觀察和研究,針對(duì)調(diào)查中得到的現(xiàn)象和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從而實(shí)現(xiàn)文化整合研究的目的。亞魯王文化作為苗文化的重要代表,通過(guò)對(duì)亞魯王文化進(jìn)行整合研究,不僅可以對(duì)苗文化的特征和類型有整體的把握,同時(shí)還可為研究整個(gè)中華文化,乃至全球文化提供很好的借鑒。
二、史詩(shī)《亞魯王》的神話學(xué)結(jié)構(gòu)
列維-施特勞斯的神話學(xué)理論有兩個(gè)突出的特點(diǎn),一是從潛意識(shí)出發(fā)研究神話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二是神話結(jié)構(gòu)可以折射出特定文化類型的深層文化結(jié)構(gòu)。列維-施特勞斯認(rèn)為,科學(xué)與巫術(shù)需要同一種智力操作,與其說(shuō)二者在性質(zhì)上不同,不如說(shuō)它們只是適用于不同種類的現(xiàn)象。其中一個(gè)大致對(duì)應(yīng)著知覺(jué)和想象的平面;另一個(gè)則是離開(kāi)知覺(jué)和想象的平面。這兩條途徑中的一條緊鄰感性直觀;另一條則遠(yuǎn)離感性直觀。從列維-施特勞斯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神話和儀式對(duì)應(yīng)著的是人類的感性直觀,這種感性直觀導(dǎo)致的并非只是美學(xué)意義上的文化積淀,同時(shí)還蘊(yùn)含著深層次的理性認(rèn)識(shí),雖然神話和儀式在形式上與科學(xué)有很大的差異,但在反映人類文化成就上,卻具有同樣的價(jià)值和意義。列維-施特勞斯的神話結(jié)構(gòu)理論基礎(chǔ)是社會(huì)學(xué)的“問(wèn)題意識(shí)”,即神話的深層結(jié)構(gòu)是為了解決人類早期面對(duì)自然問(wèn)題和社會(huì)問(wèn)題時(shí)的解決方式。他的神話結(jié)構(gòu)解釋方法深受結(jié)構(gòu)主義語(yǔ)言學(xué)的影響,同時(shí)他采取了社會(huì)統(tǒng)計(jì)學(xué)的方式將神話故事的各種元素進(jìn)行排列組合并做出深度闡釋。列維-施特勞斯堅(jiān)信神話是人類理性的心靈表達(dá)而非簡(jiǎn)單的臆想,因此,列維-施特勞斯的結(jié)構(gòu)主義理論是按照嚴(yán)肅的社會(huì)學(xué)統(tǒng)計(jì)和語(yǔ)言學(xué)分類的方式來(lái)研究的。他將神話的不同元素進(jìn)行社會(huì)功能和文化意義的分類排列,然后再將這些元素進(jìn)行整合分析,以獲取某種特定文化類型的整體性特征,列維-施特勞斯的結(jié)構(gòu)主義神話學(xué)研究實(shí)質(zhì)上也是文化整合研究。它的科學(xué)性不僅在于采用的方法具有社會(huì)學(xué)和心理學(xué)的特征,更為重要的是他始終堅(jiān)信神話反映的是人類心靈無(wú)意識(shí)的結(jié)構(gòu),不管神話如何敘述和表達(dá),也不管神話如何隨著歷史發(fā)展演變而產(chǎn)生變化,同一類型神話的基本結(jié)構(gòu)都不會(huì)發(fā)生變化。列維-施特勞斯的后期理論中更加鮮明地反映了他對(duì)于神話的整體性思維,他認(rèn)為個(gè)別神話只能放在神話整體中才能體現(xiàn)神話的真正意義。“所有神話共同表明了事物的總和,這種總和不是任何個(gè)別的、具體的神話所能確切表達(dá)的,這種總和應(yīng)該是所有神話共同表達(dá)的一種必然的、富有詩(shī)意的真理。”[3]
亞魯王文化是上古神話的沃土,西部苗人保留了中華民族上古先民對(duì)自然環(huán)境的神奇想象和人類社會(huì)獨(dú)特的心靈結(jié)構(gòu),研究亞魯王文化的神話現(xiàn)象可以從整體上把握中華民族上古神話認(rèn)識(shí)世界的邏輯。以往的神話學(xué)研究曾傾向于認(rèn)為神話是古代原始思維的產(chǎn)物,對(duì)于現(xiàn)代社會(huì)并沒(méi)有多少社會(huì)功能和學(xué)術(shù)價(jià)值,而亞魯王文化自遠(yuǎn)古走來(lái),傳承至今,融合了不同時(shí)代的文化特征,至今仍然發(fā)揮著重要的社會(huì)功能和精神價(jià)值。首先是“家國(guó)一體、天下一家”的家園文化。亞魯王的神話中流露出天下萬(wàn)物和全人類同宗同源的生態(tài)文化思想。史詩(shī)的“創(chuàng)世”部分對(duì)上古時(shí)代的宇宙觀和人類的家族譜系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描述。史詩(shī)認(rèn)為,宇宙是由早期的若干位女性祖先創(chuàng)造,而且人類擁有共同的文化家園,不僅具有現(xiàn)實(shí)層面的家園,還具有理想化的終極家園。其次是對(duì)于自然界的敬畏之心。神話中對(duì)于動(dòng)植物有著大量詳細(xì)的描述,在史詩(shī)中所有動(dòng)植物皆為祖先,因?yàn)樗鼈兺瑯邮亲嫦鹊膭?chuàng)造,而且它們比人類出現(xiàn)要早。史詩(shī)中對(duì)每一種動(dòng)植物的起源和在世間的使命以及與人類的關(guān)系都有著詳細(xì)的闡述,這個(gè)動(dòng)植物的神話體系十分精密,動(dòng)植物各司其職,與人類共同完成祖先的心愿。最后是生生不息、生死循環(huán)的生死觀和世界不斷復(fù)制繁衍的宇宙觀。亞魯王文化的神話結(jié)構(gòu)中透露出明確的混淆生死界線、生死循環(huán)不止、世界不斷復(fù)制的宇宙觀。按照列維-施特勞斯的結(jié)構(gòu)主義神話學(xué)理論,史詩(shī)《亞魯王》的諸多神話內(nèi)在具有嚴(yán)謹(jǐn)?shù)恼w性特征,這個(gè)整體性特征恰好反映出這個(gè)文化現(xiàn)象的內(nèi)在深層的文化意蘊(yùn)。亞魯王文化的神話學(xué)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反映出上古神話中蘊(yùn)含著至今仍然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的生態(tài)文明思想和家國(guó)同構(gòu)的人類共同體意識(shí)。
三、史詩(shī)文化原型的“模子”意識(shí)
榮格的集體無(wú)意識(shí)理論的核心是原型。追溯原型這個(gè)概念,可以發(fā)現(xiàn)古希伯來(lái)文化和古希臘文化中皆有較為明確的“模子”意識(shí)。史詩(shī)《亞魯王》涉及的文化原型幾乎涵蓋了人類生活和心靈結(jié)構(gòu)的各個(gè)層面,其中和榮格重點(diǎn)分析的文化原型一致的大致如下:誕生原型、復(fù)生原型、死亡原型、權(quán)力原型、巫術(shù)原型、英雄原型、樹(shù)的原型、太陽(yáng)原型、月亮原型、河流原型、火的原型、動(dòng)物原型、武器原型等。然而還有很多榮格沒(méi)有重點(diǎn)分析過(guò)的其他文化原型,比如洪水原型、女性原型、嫉妒原型、靈魂原型、家園原型等。《亞魯王》包含的文化內(nèi)容覆蓋了苗族文化的各個(gè)層面,從社會(huì)生產(chǎn)生活方式到歷史記憶,乃至民間信仰和倫理道德。《亞魯王》以亞魯王的英雄事跡為主線,描述了苗人開(kāi)疆拓土、征戰(zhàn)遷徙、信仰儀式等各方面的內(nèi)容。《亞魯王》中的文化現(xiàn)象十分繁雜,如何透過(guò)這些錯(cuò)綜復(fù)雜的文化現(xiàn)象,找出其背后的內(nèi)在規(guī)律?首要的任務(wù)就是對(duì)文化現(xiàn)象進(jìn)行整合性歸納。榮格的原型理論恰好可以幫助我們透過(guò)現(xiàn)象看本質(zhì)。通過(guò)對(duì)史詩(shī)中各種神話故事和傳奇事件的分析,可以找到亞魯王文化現(xiàn)象背后的那些原型,這對(duì)于我們重新認(rèn)識(shí)亞魯王文化,并將之與異質(zhì)文化進(jìn)行對(duì)比,從而從整體上研究苗族文化的發(fā)展脈絡(lu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jià)值。《亞魯王》的文化原型豐富而多變,如果從上古文化的角度來(lái)看,這些神話原型一再?gòu)?qiáng)調(diào)創(chuàng)造宇宙的始祖大多是女性,后期才出現(xiàn)了幾個(gè)男性的祖神,而這些男性祖神本身就是那些母性祖神的孩子。史詩(shī)神話中的萬(wàn)物之間可以自由溝通,而且動(dòng)植物和自然界的其他無(wú)生命的物質(zhì)與人類同為家人。在亞魯王神話體系中生命是永不停止的循環(huán)往復(fù),生命終止的同時(shí)也是生命的開(kāi)端,亡魂要回到祖先的家園成為新的祖先,同時(shí)祖先們又要?jiǎng)?chuàng)造出新的生命,歷經(jīng)數(shù)千年傳承的文化原型里包含著中華上古時(shí)期先民的智慧和理想。在貴州省麻山一帶的苗人的社會(huì)生活中,各種生活用具中大多可以體現(xiàn)出文化原型的思想:麻山一帶的古代軍事文化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在喪葬儀式中保留著大量軍旅生涯的文化印記;主持喪葬儀式的“東郎”身著象征古代戰(zhàn)袍的青色長(zhǎng)衫,手持古代將軍使用的長(zhǎng)劍,腳下還要踩著一塊當(dāng)?shù)亟凶鳌拌F鏵”的大鐵片,象征古代戰(zhàn)士的鐵鞋。喪葬儀式上還有模仿當(dāng)年作戰(zhàn)的“征糧”環(huán)節(jié),而且每一個(gè)壽終正寢的亡人都要被“封侯拜將”,成為亞魯王旗下的將軍,踏上漫漫征程。喪葬儀式上要不斷地敲擊戰(zhàn)鼓以鼓舞亡魂作戰(zhàn),筆者調(diào)研中發(fā)現(xiàn)有些喪葬儀式上使用的鼓是當(dāng)?shù)厥来鄠鞯墓糯鷳?zhàn)鼓,而在亡魂發(fā)喪之時(shí),扮演成古代戰(zhàn)士的親屬要向四方不斷射箭為亡魂開(kāi)路。這些器物和儀式無(wú)不折射出亞魯王文化的軍事文化原型。
四、史詩(shī)三大母題的文化功能整合
母題概念目前在學(xué)術(shù)界的論述較多,很多專家學(xué)者針對(duì)母題概念提出自己的界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湯姆森在《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xué)》中曾提出的,“一個(gè)母題是一個(gè)故事中最小的,能夠持續(xù)在傳統(tǒng)中的成分”[4]。蘇聯(lián)著名民間故事專家普羅普發(fā)展了湯姆森的母題理論,在他的代表作《故事形態(tài)學(xué)》中他提出了對(duì)母題的功能性分析,并對(duì)傳統(tǒng)民間文學(xué)母題進(jìn)行功能單位的進(jìn)一步劃分。普羅普的母題功能性切分理論大大拓展了民間文學(xué)的研究思路,他將湯姆森的母題索引分類體系進(jìn)一步進(jìn)行功能切分,對(duì)民間文學(xué)的深層內(nèi)涵和故事功能分類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神話學(xué)家陳建憲指出,“母題”在各門(mén)學(xué)科中都被用作一種結(jié)構(gòu)單位,可見(jiàn)這是它的一個(gè)約定俗成的屬性[5]。母題是民間文學(xué)中的一個(gè)可以構(gòu)成文學(xué)框架的基本結(jié)構(gòu)單元,在民間文學(xué)中具有文本生成功能和藝人講演或傳唱時(shí)候的結(jié)構(gòu)文本的功能,這是在任何一種文化現(xiàn)象中都會(huì)存在的基本元素,因此母題分析是民間文學(xué)研究的基本手段之一。普羅普的神話母題研究的前提是任何母題都是來(lái)自生活的邏輯和規(guī)律,而且他認(rèn)為母題研究是一種純粹的形態(tài)研究,和內(nèi)容沒(méi)有太大關(guān)系。因此,普羅普認(rèn)為從母題中可以反推出生活的邏輯。普羅普的想法在今天看起來(lái)有些簡(jiǎn)單,因?yàn)樗治龅哪切┟耖g故事來(lái)自俄羅斯,結(jié)構(gòu)簡(jiǎn)單,類似童話故事。
史詩(shī)《亞魯王》幾乎涵蓋了苗人生產(chǎn)生活和精神信仰的全部,相當(dāng)于苗人的百科全書(shū)。面對(duì)亞魯王文化中盤(pán)根錯(cuò)節(jié)的文化母題,我們要如何從眾多的母題中找出內(nèi)在的結(jié)構(gòu)性元素,對(duì)苗族文化進(jìn)行整合性研究以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在規(guī)律呢?史詩(shī)中最為突出的三大母題,創(chuàng)世母題、遷徙母題和戰(zhàn)爭(zhēng)母題可以統(tǒng)攝整部史詩(shī)的眾多母題,從三大母題入手可以對(duì)史詩(shī)母題進(jìn)行整合性研究。面對(duì)《亞魯王》大母題和小母題融混為一體的現(xiàn)象,就不能像普羅普那樣將母題和內(nèi)容割裂開(kāi)來(lái),簡(jiǎn)單地做出直觀判斷。以史詩(shī)中的洪水母題為例,亞魯王文化中的洪水母題里融合了多種文化元素。史詩(shī)中洪水的起因就涉及苗族的音樂(lè)起源,起初吒牧造的樂(lè)器都不能發(fā)聲,做了很多銅鼓和其他樂(lè)器都是沒(méi)有聲音的,后來(lái)因?yàn)檫改恋膬合眿D波尼岡孃無(wú)意中在月經(jīng)期間坐到銅鼓上并把經(jīng)血流到了銅鼓上,銅鼓竟然就發(fā)出了聲音,于是吒牧就把波尼岡孃殺掉,用她的血來(lái)祭奠他的樂(lè)器,從此銅鼓和其他樂(lè)器都發(fā)出了聲音,于是音樂(lè)就出現(xiàn)了。吒牧把死后的波尼岡孃藏在谷倉(cāng)之中,可是波尼岡孃之死終究還是被她的父親雷神知道了,雷神震怒就降下暴雨毀滅人類,雷神的外甥女波尼虹蓊甩下三只銀簪戳出三個(gè)龍洞,洪水流進(jìn)龍洞里,于是洪水就退去了。洪水之后,螢火蟲(chóng)尋來(lái)火種,蝴蝶尋來(lái)谷種,老鷹找到了新的疆域,所以老鷹獲得在秋天可以到人間捕捉小雞作為食物的特權(quán)。亞魯王文化的洪水神話除了上述故事,尚有其他版本的再造人類的神話傳說(shuō)流傳在民間。比如尚未出版的史詩(shī)《亞魯王》第二部的田野調(diào)查資料中就記載了洪水神話中兄妹成婚繁衍人類的傳說(shuō)。迄今為止,亞魯王文化的洪水神話可能是各種洪水神話再造人類母題中最為復(fù)雜的版本之一,亞魯王文化的豐富性和包容性從這個(gè)案例就可以窺見(jiàn)一斑。在亞魯王文化的洪水神話母題復(fù)雜多變的文化現(xiàn)象背后,還是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內(nèi)在的規(guī)律性。亞魯王文化起源于上古時(shí)代,經(jīng)過(guò)數(shù)千年的演變形成洪水神話母題,亞魯王洪水神話中包含著大量的上古文化信息,甚至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shí)代之前的遠(yuǎn)古文化現(xiàn)象,從神話學(xué)的角度來(lái)看,亞魯王文化保留著一些大洪水時(shí)代的文化信息,可是又融合了一些后世的洪水神話元素,不難看出,亞魯王的洪水神話具有時(shí)代的跨越性。
五、結(jié)語(yǔ)
目前對(duì)于亞魯王文化的研究,從苗文化本身出發(fā)的研究成果是數(shù)量最多、水平最高的。這些以亞魯王文化的個(gè)案分析作為切入點(diǎn)的文化研究成果是開(kāi)展亞魯王文化整合式研究最為重要的基礎(chǔ),正是這些研究成果讓我們更加清晰地了解苗文化的特征和亞魯王文化的內(nèi)涵,給進(jìn)一步深入開(kāi)展亞魯王文化的整合式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針對(duì)亞魯王文化的豐富性,從更為寬廣的學(xué)術(shù)視野出發(fā),通過(guò)民族志書(shū)寫(xiě)和人類學(xué)經(jīng)典理論的綜合運(yùn)用,對(duì)史詩(shī)進(jìn)行整合性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為深入而系統(tǒng)地理解亞魯王文化的原貌。
亞魯王文化在長(zhǎng)期的發(fā)展歷程中出現(xiàn)了變異,“但無(wú)論如何變異,這些變異都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完全不顧及原來(lái)故事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而另編一個(gè)話題”[6]。面對(duì)具有如此豐富而又多元的史詩(shī)文化,在對(duì)亞魯王文化現(xiàn)象進(jìn)行田野調(diào)查之后,有效借鑒西方文化整合理論,合理地利用他山之石,打開(kāi)藏在亞魯王文化背后的文化之玉,是文化整合研究的出發(fā)點(diǎn)。在文化整合研究中,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既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論,迷失本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不能固步自封,陷入文化保守主義的怪圈。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對(duì)苗族史詩(shī)《亞魯王》進(jìn)行文化整合研究,也是符合時(shí)代發(fā)展潮流的做法。
- 懷化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湖南沅陵官話同音字匯
- 我國(guó)融合出版研究20年(2000—2020)
——基于Citespace 與Gephi 的知識(shí)圖譜分析 - 董事會(huì)治理結(jié)構(gòu)對(duì)內(nèi)部控制有效性的影響
- 協(xié)同發(fā)展視角下商業(yè)對(duì)制造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影響分析
——以泉州為例 - 政府補(bǔ)助、高管激勵(lì)與實(shí)質(zhì)性創(chuàng)新
——基于新能源企業(yè)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 - 湖南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現(xiàn)狀、困境及對(duì)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