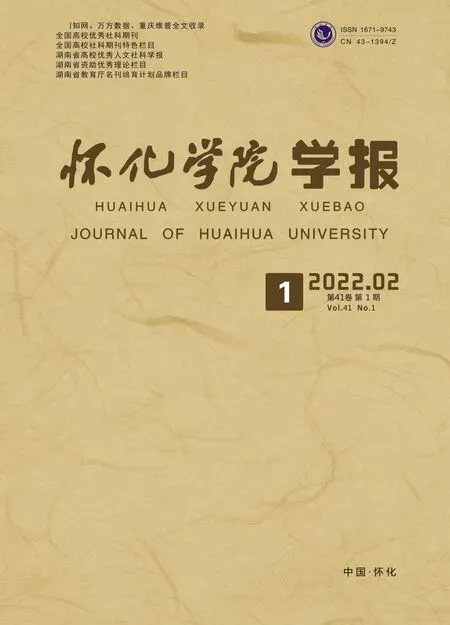清代湘西苗疆邊墻民族貿易探析
侯有德
(吉首大學武陵山區發展研究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一、引言
清代中后期以來,清廷重修苗疆邊墻,并圍繞苗疆邊墻推行一系列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措施,通過對社區土地的法制化建設、調整民族經濟、實施有限開放的民族貿易政策、調整民族婚姻政策、建設非武裝化社區等具體措施來重構湘西苗疆的民族關系。由于清代對民苗之間的婚姻時禁時許,且以禁為主,故民族貿易就成為清代湘西苗疆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徑。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貿易與苗疆邊墻密切相關,帶有深深的“邊墻格局”的印記。
二、民族貿易政策的變遷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參將朱紱在平息鎮竿紅苗之事后,以湖廣總督郭琇為代表的地方官員就針對漢土民與苗民的現實生活需要,提出在苗漢居住地設立集市,并規定“每月三日,聽苗民互市,限時集散”[1]。與此同時,也重申了販賣火藥軍械、漢民迎娶苗婦的禁令。“清朝政府對民、苗每月三日互市異常謹慎,嚴格規定了交易的具體地點、日期,以及市場交易時間的長短,交易物品的種類與范圍等。”[2]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湖廣提督俞益謨在《戒苗條約》中對苗、漢交易問題進行了分析。文曰:
鹽、布二項,爾苗急需。皆因爾性好劫殺,以致無人進來交易,即有轉賣進來的,其價又貴,是以爾苗歷來常受寒冷淡食之苦,殊屬可憐。爾若不劫殺,則漢人進來交易者多,將爾土產,以換鹽、布,豈不兩得其利?爾若守法,可以到乾州五寨司買去,其價更賤[3]。
可見,清康熙年間,民苗之間的鹽、布交易是比較普遍的,民苗交易并未受到限制。雖然俞益謨在《戒苗條約》中將對苗漢貿易的管制歸咎于苗民“性好劫殺”有失公允,但我們可以從中窺見清廷對民苗貿易政策的調整與苗疆社會穩定與否密切相關。換言之,清廷在湘西苗疆貿易政策的調整都以穩定、治理湘西苗疆為最終目的。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時任湖廣總督的郭世隆對民、苗交易提出了“以塘汛為界”的要求。清光緒《湖南通志》卷一百三《名宦志十二》載:
郭世隆,漢軍鑲黃旗人。康熙四十六年,總督湖廣條奏防守紅苗三事。謂:沿邊塘汛周密,惟盛華哨至鎮溪所一帶,山高箐密,難于瞭望,應酌撥鎮竿兵八百名,另設四營分駐,每日派官一員,帶兵五十名游巡。舊日民苗來往,每滋事端,今以塘汛為界:苗除納糧、市易,不得擅入塘汛,民亦不得擅出塘汛,違者治罪。從前漢奸與苗人結親,致勾通為匪,不可究詰。嗣后如有,前事應斷離異[4]。
從上可知,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苗漢邊界塘汛周密,盛華哨至鎮溪所一帶亦有駐兵把守,苗漢通婚被禁,集市貿易成為苗民與漢土民交往的主要途徑。
康熙五十年(1711年),地方官員正式將民間貿易管理起來。傅敏在苗疆巡視時開始在湘西苗疆推行“國家在場”的集市貿易制度。對此,清鄂海在《撫苗錄》中有詳細記載。文曰:
今卑職等公同會議,得中營汛屬之宜都營,前營之箭塘營,右營之西門江,左營之窯頭坡,四處具系民苗出入適中之地,應于各該地方設立集場,每月定以初十、二十五二日,令苗民兩次會集貿易,即著該管百戶與該汛弁目帶領兵丁監督稽查,令民苗集于辰時,散于午時。……民人售賣貨物,亦止須鹽米服食等項,其余硝磺軍器有干禁令者一概不許貨賣[5]。
由此可知,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 官方加強了對集市場址、場期、場時以及趕場人員、交易貨物的管理。官方于民苗交界之地設立集場,規定趕場日期為每月初十、二十五,辰時聚、午時散,由百戶與汛弁領兵丁監督稽查,只允許鹽、米等的交易,禁止火藥、軍械交易。
清雍正五年(1727年) 官方進一步限制了民族貿易的交易內容,嚴禁民苗之間的土地貿易和借貸活動。這一點在傅敏《奏苗疆要務五款》中有詳細記錄。文曰:
請自后除糶糴糧食,買賣布帛,現錢交易,毋庸禁止。民與苗賣產借債,責之郡縣有司。兵與苗賣產借債,責之營協汛弁。自本年為始,許其自首,勒限贖還,犯者照律治罪,失察官弁,嚴加參處[6]。
奏折中規定,民、苗交易內容限于糧食、布帛,交易方式限于現錢,嚴禁“賣產借債”即買賣田產和民間借貸。對于之前有賣產借債行為的民苗,允許自首,從輕或免除處罰。對此后違反此條者,嚴懲不貸。
清雍正七年(1729年),湖廣總督邁柱《條奏苗疆事宜》中對民苗貿易的管制更加細化。文曰:
湖南民人往苗地貿易,令將所置何物,行戶何人,運往何處,報明地方官。給與印照,填注姓名、人數,行知塘汛驗照放行,不得夾帶違禁之物。如官吏、兵役藉端需索,一并查究。苗人至民地貿易,請于苗疆分界之地設立市場,月以三日為期,交易而退,不得越界出入,令各州縣派佐二官監視[7]。
綜上可見,清雍正年間,清廷對參與貿易的漢土民、苗民均有嚴格管制。要求前往苗疆邊墻之外貿易的漢土民填報行程,登記貨物,并辦理證件。對于進入苗疆邊墻以內貿易的苗民只準許在“邊界”市場交易,每月三日,完成交易及時返回邊墻之外,不得越界,全程派官員監察。
清乾隆年間,為有效管控民苗往來,仍允許民苗交易。清乾隆《鳳凰廳志》卷二十《藝文》中有湖南巡撫蔣溥奏請準許民苗交易的記載。原文如下:
民苗宜許其交易。查從前定例苗地不許漢人來往,原以苗性愚頑獷悍,奸人一入其地,貪利魚肉,久之積成仇釁,易至蠢動,是以立法禁止。即楚南永順、永綏等處建城安營,不過以□彈壓,并非為苗人開貿易往來之路。若如□□所奏,許其當官、交易、買產借債,恐奸民毫無顧忌,公然來往,轉得借端欺占,別生事端,殊為不便。應令該撫仍照定例遵行[8]。
當然,清廷對民苗貿易的種種嚴格管制政策也一直延續下來。清乾隆《鳳凰廳志》卷五《疆域》載:
鳳凰廳民苗兼轄,既不欲使民苗私相往來,以杜其勾引之漸。必別為之所,伸之易粟易布,以通有無,則市集之在苗疆,更宜加在意矣!但開集設場,或稱經紀,或號牙行,大約均非善類,藏奸聚匪,啟爭致釁恒出于此,選擇以慎。初稽察以善后享其利勿□其弊……西門江集,城東北四十里。箭塘集,城西北三十里。鳳凰集,城西南六十里。以上三集,系從前通判設立,文武衙門彈壓。永寧哨集,城西南四十里。靖疆營集,城東北六十里。新寨集,城西北六十里。竿子哨集,城東北六十里。以上四集俱系乾隆十九年新設[8]。
由此可知,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鳳凰廳另設永寧哨集、靖疆營集、新寨集、竿子哨集的目的是為了杜絕“民苗私相往來”,以“杜其勾引之漸”。
清乾隆年間,政府官員執行著嚴格的集市管理制度。為了禁止客商販賣私貨,官府加強了對進入苗地貿易客商的管控。一方面,執行嚴格的印票核驗制度,“凡各商販必于所在官司討一印票,以便查驗。如某處某人于某地買某貨至某地發賣,止許寫大地名……所在官司關市驗實放行,若無□票即同私販,貢□□官”[9];另一方面,規定客商至苗地貿易時,由“苗長赴本哨交易,不許販商擅入巢穴與諸苗交通,違者,以軍法從事”[9]。
值得注意的是,相同的貿易政策在湘西苗疆各個地方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明顯差異。鳳凰廳的地方官員多“選擇以慎,稽察以善,后享其利,毋檻其弊”[10],頗有消極應付之意。永綏廳“惟是地方遼闊,村落零星,苗人來城買賣,往返擔延時日。必擇大村寨適中之地,立集場數處以便就近交易,庶貨物流通,民苗兩利云”[11]。可見,治理永綏廳的地方官員出于民、苗便利考慮選址建立集場,態度更為積極。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定番界”,頒布了“苗疆禁例”,明令規定“各省民人無故擅入苗地,及苗人無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來貿易,必取具行戶,鄰右保結,報官給照,令塘汛驗放,始往”[12]。按這一規定,民苗之間交易要受到三重監管,首先要“取具行戶”即到商行領取備辦,然后要“鄰右保結”即鄰里左右做擔保,最后由塘汛官兵勘驗核查無誤后才能通行。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 之間,政府官員一度提議解除對民苗貿易的種種限制。清乾隆《辰州府志》卷十二《備邊考》載:
湖南民苗貿易于雍正七年禁止。凡有往土苗貿易者,務將取置貨物、鋪店報明地方官查明,行戶鄰右保結存案,給以印照,注明人數,令塘汛點驗,始準入。土苗交易殊多不便,后然雍正八年議改市場,民苗定期交易,汛弁官役彈壓稽查,但彼時設立市場未能普遍,且現在各村莊俱有苗人買取什物,原難禁阻,前例已屬虛設,徒滋兵役,籍索無益防維。今民苗既準共互相結姻,凡苗人赴內地貿易似可聽從其便,應請將限定場期、官弁監視交易之例一概停止,俾得貿遷有無,以資生計,將見苗人感皇仁益無涯涘,苗疆風俗日臻淳厚矣[13]!
由此可知,針對清雍正七年以來清廷對民苗貿易設置的重重關卡,部分地方官員提議“凡苗人赴內地貿易似可聽從其便”并要求將“限定場期、官弁監視交易之例一概停止”。
乾嘉民苗起義平息后,建在苗地的集場基本被遷到了民、苗交界處。和琳《善后章程》中就要求在民、苗交界地設立集場,民苗交易僅限于集場之內定期舉行,由官兵監視交易過程,且規定趕場之日,駐守碉樓、哨臺的兵丁“只準一二人趕場”,“卡內亦不過酌令數人趕赴,不許多人遠出,其出外者,仍需迅速趕回,不許逗留,逛久”[14]。
嘉慶元年(1796年),和琳在《善后章程》中重申了限制民苗交易內容即民苗交易限于糶糴糧食和布帛買賣,進而強調了禁止民苗買賣田產和借貸的政令[15]。在《善后六條》中,和琳指出“苗地所需鹽斤,布匹等類,均籍客民負販,就近易買,以資日用。過于禁絕,苗情轉有不便”[16],故而建議“嗣后民苗買賣,應于交界處所擇地設立場市,定期交易,官為彈壓,不準以田畝易換物件,以杜侵占盤剝釁端,則民苗永可相安無擾矣”[16]。
嘉慶五年(1800年),傅鼐在辦理苗疆均田事務時規定:“每逢場期,準令民、苗兩相交易。各卡門務須查明,不準苗人混帶槍械進內,民人及勇丁等與苗人買賣,須皆照時價公平交易,不得欺騙肇釁。倘有滋事者,立即嚴拿重究。”[15]
嘉慶十四年(1809年),傅鼐針對“生苗區”苗民私自在寨內開設集場交易的情況,重申了民苗貿易的定例。對此,清嘉慶《湖南通志》卷六十五《職官九》、道光《鳳凰廳志》卷八《屯防一》、光緒《乾州廳志》中均有記載,原文如下:
現在民苗界址劃分清楚,應申明舊例。漢民仍不許擅入苗地,私為婚姻,以免滋事。惟各處集場,原許民苗按期趕趁,以有易無,應令汛屯員弁親為彈壓,無許市儈侵欺,一切公平互市,交易而散[17]。
可見,清嘉慶年間,仍然嚴格執行著“漢民仍不許擅入苗地,私為婚姻”的禁令,民苗之間的交往仍然主要通過有限的民族貿易來實現。
三、“邊墻格局”與民族貿易
明清修建邊墻客觀上對湘西苗疆的民族分布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隨著圍繞苗疆邊墻一系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政策的推行,逐漸形成了“邊墻格局”。受“邊墻格局”的影響,湘西苗疆的民族貿易特色鮮明。
(一) “邊墻格局”與集場分布
通過對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貿易政策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清廷對湘西苗疆地區民族貿易的管控愈來愈嚴格。這主要有幾方面的原因:其一,清廷治理和開發湘西苗疆之初,苗民與漢土民之間的關系相對緩和,故一度出現準許民苗通婚、民苗自由貿易的局面。乾嘉苗民起義以來,防苗、控苗成為了地方官員治理湘西苗疆的重要目標,苗漢通婚被禁,民苗之間的貿易往來作為民族交往的主要途徑自然備受地方官員關注,從而在交易時間、場地、方式、內容等方面設置層層限制,成了清代未有間斷的,如“戴著鐐銬的舞蹈”一般的民族交往方式。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民族關系緊張的階段,尤以乾嘉年間苗亂為典型,清廷也未禁止民苗之間的民族貿易,而只是針對民族關系的緊張程度對民族貿易的場地、時間、內容、交易方式等相關內容進行適度調整。這主要是因為,苗漢之間的民族貿易是穩定湘西苗疆社會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是滿足民苗現實生活需求的主要途徑,是安撫民苗的有效手段之一。
其實,在湘西苗疆地區形成以依托邊墻為特征的集場之前,民、苗之間的貿易就一直存在,只是以一種相對隱蔽的方式進行著,故未受官方管控。這些集場主要分布在邊墻汛堡、哨卡附近。這一分布格局與明代始修苗疆邊墻和推廣衛所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明代在邊疆地區推廣衛所制度,駐守者們便在此安居下來。他們有著客觀的生產生活需要,各類交易活動也因此在駐屯、汛堡、哨卡附近興盛起來。這類自發興起的“民間集場”最初的交易群體主要是駐守邊墻沿線的屯兵及其家眷,此后,隨著民苗交往的日益頻繁與密切,社會生活需求的增多,集市的擴大和興盛,世居于湘西苗疆的苗民、土民等群體才加入進來,成為民族貿易對象的主要群體之一。這類“民間集場”的形制“實在有些簡陋,多由夯土圍墻圈成,場內或搭草棚或堆亂石,用于雜陳貨物,買賣人或蹲或立叫賣、交易。”[2]然而,這并不影響民苗之間的貿易往來,亦不影響民苗之間民族貿易在穩定苗疆社會以及促進經濟發展與民族文化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
從布局和設置來看,湘西苗疆地區的“民間集場”一般位于“汛堡外城之內或緊鄰汛堡內城,或位于邊墻外部靠近苗人地界一面”[2],旁邊多有瞭望臺、護城壕等防御設施。這主要是基于防范民、苗勾結“構亂”以及苗人趁趕場之機闖入城中劫掠的目的。集場位于汛堡外城之內或鄰近汛堡內城,有利于場內“構亂”之時屯防兵勇很快介入管控。集場設于邊墻外部靠近苗人地界一側主要是為了方便苗民的交易,當然也不妨礙漢土民的積極參與,一些駐防的哨兵屯勇往往會定期趕集,故才有了如前文所述清代“卡內亦不過酌令數人趕赴”以及趕場屯兵“仍需迅速趕回,不許逗留,逛久”[14]的規定。
清嘉慶二年(1797年),乾嘉苗亂平息之后,政府在民苗交界地廣設集場。明代以來,湘西苗疆地區的“民間集場”業已形成沿墻布局的地理分布特征,清代湘西苗疆“官方集場”的地理分布基本上延續了這一特征。其原因有二:第一,也是主要原因,清廷在明邊墻舊址上重修了苗疆邊墻,并圍繞邊墻推行了一系列治理政策,最終形成了“邊墻格局”,民族貿易亦呈現出以邊墻為中心的特征;第二,清廷開發和治理湘西苗疆之時,這些沿著邊墻汛堡、哨卡分布的“民間集場”依然悄然進行著,且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煥發著生機和活力,逐漸引起了官方的重視,被納入官方層面,成為清廷開發和治理湘西苗疆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 “邊墻格局”與民族貿易之禁
在“邊墻格局”的影響下,清代民苗之間以集場交易為核心的民族貿易在重重限制下持續進行著。為了維護湘西苗疆社會的穩定,防止民苗的貿易糾紛,治理湘西苗疆的地方官員不僅嚴格限定了集場交易的地點和場期,而且對交易過程和交易物品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形成了一些“貿易之禁”。
第一,禁止“奸民”“兇苗”欺行霸市,保障貿易公平。嘉慶十年(1805年),湖南巡撫阿林保就在《苗疆經久章程》中提出,在集場附近要派官兵對參與交易的民、苗進行督查,“惟各處集場,原許民、苗按期趕趁,以有易無。應令汛屯員弁親為彈壓,無許市儈侵欺。一切公平互市,交易而散”[18]。
第二,嚴禁田產買賣及民間借貸,嚴禁販賣火藥、軍械。如前文所述,民苗之間的貿易以鹽為貴,以糧食為大宗,兼有布匹、牛、馬、南雜、桐茶油等生產生活用品。民、苗之間嚴禁田產買賣及民間借貸,嚴禁火藥、軍械買賣。清雍正五年(1727年),傅敏在《奏苗疆要務五款》中已言明禁止民苗之間“賣產借債”,即禁止民苗之間的土地買賣和民間借貸行為。清嘉慶元年(1796年),和琳在苗疆《善后章程》 中又重申了相關禁令。清嘉慶五年(1800年),傅鼐在經理苗疆屯田事務時就明令禁止民苗之間的槍械買賣,言明“每逢場期,準令民、苗兩相交易。各卡門務須查明,不準苗人混帶槍械進內,民人及勇丁等與苗人買賣,須皆照時價公平交易,不得欺騙肇釁。倘有滋事者,立即嚴拿重究”[15]。
(三) 邊墻與集場:張力的展現
在以集場交易為中心的民族貿易中,邊墻與集場之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邊墻-集場結構”。“邊墻- 集場結構”展示了清代民族界隔與民族交往之間的內在張力,展現了國家在治理地方社會時剛性政策與柔性政策之間的內在張力。
在“邊墻-集場結構”中,集場成了湘西苗疆苗民與漢土民交易、交往、交流的合法途徑和重要平臺;邊墻的軍事防御與界隔民苗的功能淡化,其作為國家與地方緊張關系的象征符號意義也日趨弱化,并被賦予了新的功能,成為民苗交易交往交流的依托。由此可見,對湘西苗疆邊墻的定義不應只局限在其軍事防御、界分民苗的顯性功能之上,還應把握其在保障邊墻內外不同群體交往交流中的平臺作用,把握“邊墻-集場結構”所反映出的民族界隔與民族交往之間的內在張力。
湘西苗疆邊墻是明清政府為了防“苗亂”、界隔苗民而采取的軍事防御措施,體現了國家在深入治理地方社會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剛性。集場的設置和管理則以在維護地方穩定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滿足邊墻沿線漢土民與苗民現實的生產生活需要為目標,通過對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貿易政策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清廷在集場設置和管理上的靈活多變,亦可窺見國家在深入治理地方社會的過程中所具有的柔性。集場依托邊墻而起,依托邊墻而興,形成了粘連緊密的“邊墻-集場結構”。隨著集場經濟的繁榮,圍繞邊墻而興的民族貿易逐漸興盛,苗疆邊墻逐漸成為了民族交流的平臺,具有了新的功能和意義。因此,“邊墻-集場結構”展現了國家治理湘西苗疆剛性政策與柔性政策之間的內在張力。
四、結語
清代重修苗疆邊墻之后,民族貿易成了苗族與漢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方式和有效途徑。隨著對湘西苗疆管控的日益增強,清廷對苗漢之間的民族貿易的管制也越來越嚴格,具體到集場選址、集市時間、交易內容、交易方式等,事無巨細都有規定,且要求官弁對交易過程進行嚴格監督。為了方便民苗貿易,清代湘西苗疆集場多設在苗疆邊墻碉堡、哨卡以及邊墻沿線村莊。因此,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貿易呈現出緊密圍繞苗疆邊墻的特征,帶有深深的“邊墻格局”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