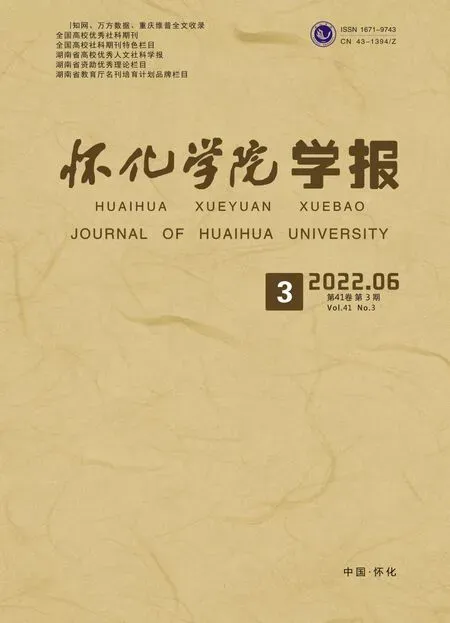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的身體敘事
鄒序桂, 陳保學, 張 斌
(懷化學院體育與健康學院,湖南 懷化 418008)
引言
節事活動是人類生產生活經驗與民俗文化活動得以傳承的重要載體。這個載體孕育的文化內涵、民族信仰、族群記憶、族群認同、精神歸屬等周而復始地被貫穿和強化,在本民族民眾心中根深蒂固。它不僅是各族民眾長久生活的文化模式,也是維系中華民族家國與族群同構的根基所在。以湘、桂、黔苗族聚居地為中心且多民族參與的“四月八”是一項代表性節事活動,因其重要,于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長期以來,每逢農歷四月初八,貴州噴水池、松桃,湘西花垣、鳳凰等地的苗族民眾不約而同地在當地聚集,以隆重的活動形式、直觀的身體敘事演繹著苗族古老的族群記憶。隨著社會發展與時代變遷,盡管各地舉辦“四月八”的活動形式和內容略有差異,但其目的都是為了祭祀先祖、懷念英雄、族群聯歡。湘西苗族“四月八”從紀念英雄反抗暴政的事跡中口傳并發展而來,有著厚重的歷史感與節事的代表性。苗族雖沒有文字,苗族民眾卻在重要的節事活動中通過身體敘說著古老的歷史與文化、時下的祈愿與希望。
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示:全力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發展,保護和傳承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的命運共同體。在此背景下,我們對苗族“四月八”活動中以“身體”為載體敘說的“古老歷史與文化,時下祈愿與希望”進一步深度解讀,有益于“四月八”節事活動的傳承與保護,更有益于苗族文化的創新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本文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通過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獲得翔實資料,并以敘事學為理論指導,綜合歷史學、民族學、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等多學科視角,分析湘西苗族“四月八”活動的身體敘事情節,力求科學、客觀地進行本真性闡釋。同時,圍繞“四月八”節事文化的科學研究、旅游開發、活動參與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一、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身體敘事的表現形式
在湘西苗語中“四月八”也稱“旦太旦臘”,有白天跳花、夜晚跳月之意[1]。因此,湘西苗族“四月八”也有“跳花節”之稱,它是湘西苗族最為隆重的節事活動,是一場融祭祀、舞蹈和娛樂為一體的集體歡騰。正如涂爾干認為“集體歡騰是人類文化創造力的溫床”[2]一樣,身體在場的“四月八”就是一種經典文化創造,既表達著對先祖和英雄的深切懷念,又展現出對愛情和自由的積極追求,這種表達與體現具有典型的身體敘事性。
(一) 巴岱的身體作為媒介,連天接地、通古問今
巴岱是湘西苗語對法師的統稱,掌管宗教教義、巫詞、祭祀禮儀[3]275。巴岱是苗族古老文化的傳承者,掌握一定的醫術與神術,借助祀神、巫術、禮儀來傳播苗族文化。在苗族民眾的內心,巴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古曉今,享有極高的地位和威信,是維系苗族社會同構的重要媒介與紐帶。巴岱日常所做的宗教活動是主持祭祀敬祖儀式,儀式中各種規則與禁忌,處處體現出“齊肅事神明”的正統與莊嚴。這種“地位和威信、正統與莊嚴”主要來自獲得巴岱身份的各種驚險與神奇事跡。
據《湘西文化大辭典》記載,從巴岱弟子到正式成為巴岱法師,須經歷“渡身”“上刀梯”“下火海”等多項考驗。所謂“渡身”是巴岱學徒“出師掌壇”的重要典儀,師傅當眾為弟子舉行“渡身”典儀后,才傳授弟子真正的法術,學成之后另設“法壇”并公開承認弟子為掌壇師[3]345。其中一種進入“發癲”狀態來實現人與鬼、人與神之間的溝通本領,顯得十分神奇。似乎這種“溝通”必須以“道行”高深的人的身體作為媒介,才能打開世俗社會通向神圣世界的大門,籍此增強現實社會的力量[4]。相比“渡身”儀式的神奇而言,巴岱法師“上刀梯”則更為驚險。隨著文化的交流與開放,如今我們在各種媒體上都能見到苗法師赤腳爬上數米高的鋒利刀梯,并在梯頂擺出各種動作的驚險場面。這些或“神奇”或“驚險”的場面,雖然在現代科學面前有些站不住腳,但對于世代深居武陵山腹地的苗族民眾而言卻深信不疑。因為,古往今來,這些場景早已成了根植于苗族民眾的集體記憶。這種集體記憶在“一個由人們構成的聚合體”中存續,并從中汲取力量。巴岱法師做出的各種“神奇”與“驚險”行為軌跡,根深蒂固地在苗族族群中存續,也成了一種維持苗族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考察中我們發現,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中巴岱法師身著道袍,手執法器,做出各種動作,口中念念有詞。他們為什么做這些動作?口中念叨的又是什么內容?為此我們專訪了當地一位姓龍的老巴岱法師,據老法師介紹:“在祭祀的時候,每一個身體動作都在與神圣發生關系,乞求四月八這場活動得到宇宙、天地、神祇的認可。”這一點陸群教授這樣解釋:對于凝視巴岱法師的民眾來說,這種儀式也和世俗發生關系,借助巴岱的身體行為,把天意、神意傳達給世間,湘西巴岱法師所請的神是一位稱作“巴岱扎”的武將,能夠招來千萬“神兵”幫助本寨村民戰勝邪魔鬼怪[5]。基于此,我們認為巴岱的身體可視為一種媒介,通過顫抖、旋轉、舞蹈、吟誦、擊鼓等行為敘事,實現所謂神與凡人的交流,而這種交流在苗族社會里有著某種“合法性”。
(二) 祭祀的身體作為符號,奉谷獻粟、敬祖尊神
祭祀是以線香、水酒和肉類等貢品向神靈奉獻、祈禱的一種敬奉行為,是華夏典禮的一部分。《史記·禮書》曰: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祭祀活動古已有之,而祭祀的對象分為天神、地祇、人神三類,天神稱祀,地祇稱祭,宗廟稱享。發展至今,我國許多祭祀活動早已形成一種文化符號,表達著中華兒女慎終追遠、禮敬先祖、弘揚孝道的傳統觀念。
在苗族文化系統中,祭祀是節事活動的重要內容。除隆重的“四月八”以外,還有鼓藏節、蘆笙節、花山節、趕秋節、蚩尤節、椎牛、過苗年等等,幾乎月月有祭祀。在祭祀過程中,苗族民眾要擺設祭壇,焚香燒紙,奉上酒肉,以表達對先祖和神靈的尊敬。苗族之所以盛行祖先崇拜,源于“萬物有靈”和“靈魂不滅”的原始宗教觀念。《湘西文化大辭典》中記載苗族祭祀的祖先有盤瓠辛女、儺公儺母、阿公阿婆,尊奉的神靈包括蚩尤、亞努、亞宜等。另外,信奉的鬼神也很多,如湘西花垣苗族地區有36 堂神和72 堂鬼[3]311。苗族盛行多重信仰與崇拜,也體現出遠古先民對天體運行、萬物存在和演變的多種臆測。湘西苗族“四月八”祭祀活動十分隆重,數十名巴岱共同主持,苗族民眾要跟隨法師一起拜天、拜地、拜祖先,其目的是乞求風調雨順,村寨平安。祭臺上擺放著黃牛、肥豬、肥羊、酸魚、米酒、糯米粑等。祭祀中焚燒一米多長的高香、敲擊百余張大鼓、吹長號、舉大旗、放煙花、響火銃,場面十分壯觀,正是這種“壯觀”吸引著四面八方的游客前來旅游觀光。祭祀過程祭師與民眾共同身體在場,敬祖與尊神構成共同心理意識,祭師的身體語言以及民眾的參拜動作是一種可以相互理解的話語和行為。歐文·戈夫曼用情境互動理論,將這些互動事件看作是區別于其他社會關系群體的情境互動,使共同在場的參與者之間形成一種微型的、權宜性的互動共同體[6]。身體在場的情境互動,恰恰能夠反映出苗族“四月八”祭祀活動表象背后“更深層、未成文”的那種社會規范。這種借助敬奉先祖與神靈而形成的社會規范,就如同“鄉規民約、祖傳戒律”一樣,在維護和穩定苗族社會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 舞蹈的身體作為記憶,傳史承道、敘事達情
歌舞是苗族的一項重要的身體記憶,在“以舞敘事、以舞傳情”的作用下,舞蹈的首要功能是講述英雄故事,承載歷史記憶。按照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理解,歷史記憶并不是個人直接去回憶事件,只有通過閱讀或聽人講述,或者在紀念活動和節日的場合中,人們聚集在一塊,共同回憶長期分離的群體成員的事跡和成就時,這種記憶才能被間接地激發出來[2]39。苗族人民正是以節事舞蹈為載體,通過舞蹈傳史承道、敘事達情。
明史記載,在祭祀活動中往往伴隨舞蹈,甚至遇喪事時也有跳舞環節[7]。苗族舞蹈種類繁多且功能各異,綜合文獻梳理和田野考察,可以將苗族舞蹈分為祭祀性、戰爭性、敘述性舞蹈三大類。苗族舞蹈一般以樂器、道具、器皿以及使用場所而命名。如蘆笙舞、鼓舞、板凳舞、刀馬舞、花棍舞、夜樂舞、斗角舞、喪葬舞、遷徙舞等等。其名稱已經能夠反映出苗族舞蹈與歷史記憶、文化敘事、藝術審美、祭祀儀式有著復雜多樣的聯系[8]。楊鵑國在《苗族舞蹈與巫文化》中,從文化學角度,對苗族舞蹈在民族歷史、文化心理、審美意識積淀以及文化認同、文化行為、儀式符號表征等方面做了深刻闡述。他指出苗族舞蹈“巫、農耕、山地、少數、無字”的文化境域,使“看上去似乎駁雜紛亂的苗族舞蹈獲得了文化學意義上的統一框架”[9]。苗族舞蹈是一個具有巫、史、自然崇拜、風格各異的符號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苗族舞蹈不僅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根植于苗族民眾的身體,同時也承載著飽受戰亂和多次遷徙的古老歷史。在節事活動中,通過舞蹈的身體敘述著苗族歷史,表達熱愛生活、向往和平、崇尚愛情的祈愿。以鼓舞為例,這種舞蹈在湘西叫跳鼓藏,表演時將牛皮大鼓置于木架上,表演者手拿兩根木棒,一邊擊鼓,一邊跳舞,自娛自樂。鼓舞動作來自生產勞動和日常生活的各種行為,舞蹈風格剛勁、豪放、粗獷,既是對祖先豐功偉績的歌頌與懷念,又是一種敘事達情的身體記憶。這種身體記憶“存在于歡騰時期和日常生活時期之間的明顯空白”[2]44,使苗族民眾在單調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始終保持鮮活的狀態。
(四) 娛樂的身體作為表白,跳花跳月、娛神娛己
“四月八”又稱“跳花節”,也是苗族青年男女“跳花跳月、娛神娛己、表白愛情”的歡樂節日。這個節日起源于苗族一段英雄救美的動人故事。老一輩苗民都認為,很久以前,在湘西鳳凰和貴州松桃交界的龍塘河跳花溝,每年農歷四月初八要舉行隆重的“跳花節”。這天,苗族青年男女都要穿上顏色鮮艷的新裝齊聚跳花場熱舞狂歡、表白愛情。活動分“跳花”和“跳月”兩部分,白天稱“跳花”,各村寨苗民齊聚跳花溝,參加和觀看各種豐富多彩的節目,如蘆笙舞、花鼓舞、跳花舞、盾牌舞、團圓舞、苗歌對唱、獅子跳桌、踏火海、上刀梯、武術表演等。夜晚叫“跳月”,五彩繽紛的煙花炮火照亮星空,在跳花溝的空地上升起一堆篝火,大家圍在一起,載歌載舞集體狂歡。狂歡中苗族成年的小伙子們一邊吹著蘆笙,一邊跳著蘆笙舞,尋找心儀的姑娘。姑娘們則穿上刺繡衣裙,佩戴絢麗奪目的銀飾,等待著意中人的到來。在歡樂的節日氛圍中,苗族阿哥和阿妹約定時間地點,表白心中愛意。找到各自的意中人后,他們一起唱著動情的苗歌,表達心中的濃情蜜意。這種表白愛情的方式是苗族民眾心中的集體認同,是當地苗族青年男女一場美好的相親大會。
然而,這場美好的“相親大會”卻遭到破壞。據說,一次,在“跳花節”當天,一些紈绔官家子弟見到一個個如花似玉的跳花姑娘,心生歹意,前來搶親。搶來的姑娘或用于自己“享用”,或用于向上“進貢”,這種卑劣行徑拆散了許多美好姻緣,糟蹋了許多花樣少女。為了阻止這場災難,鳳凰山下的苗族英雄亞宜率領眾青年歃血盟誓,決定以武力反抗前來“破壞”的官家子弟。不料官家引來大批兵馬前來鎮壓,亞宜與眾后生血戰了幾個晝夜,終究寡不敵眾,被迫向貴州方向轉移,最后同貴陽地區苗族青年英雄亞努戰死沙場[10]。這段民族英雄反抗暴政的故事可歌可泣,從此“四月八”活動中便加入了紀念以亞宜為首的青年英雄環節。也因此,崇尚武藝、英雄救美、捍衛家庭、反抗壓迫成為苗族民眾的一種族群精神。這種精神通過舞蹈的身體記憶不斷被強化,形成一種深刻的歷史記憶,展示出淳樸善良、重情重義的苗家風情。
二、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身體敘事的主要問題
在“經濟搭臺,文化唱戲”的旅游經濟發展策略下,各地以節日為依托發展了一系列旅游產業。旅游產業開發推動了湘西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如“鳳凰- 吉首- 張家界”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旅游線路。然而,隨著“快餐文化”的盛行,人們往往容易忽視對文化的“原生態”和“本真性”的保護。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同樣如此,近年來,隨著經濟旅游的開發,為迎合游客對民俗舞臺效果的過度追求,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的身體敘事功能正在淡化。
(一) 圍繞經濟旅游的開發,活動淡化了敘事性
在敘事學中,身體是符號化的,故事是身體化的[11]。因而,身體和故事是一種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態,按照敘事學的理解,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具有典型的敘事性。“四月八”活動中跳花跳月的舞蹈,一方面表達著苗族阿哥阿妹崇尚自由戀愛的婚姻觀念,另一方面敘說著青年兒女勇于反抗暴政的英雄故事。因此,從歷史學和敘事學角度來解讀“四月八”節事活動,它是一種身體與故事的完美融合,是一種民眾與族群的集體認同。
近年來為了發展經濟旅游,過度追求規模與效益,過分打造和包裝淡化了“四月八”活動的敘事性。據當地民眾說,以前的“四月八”節日是由巴岱組織,村民自覺參加,并無大型舞臺,而是在田間地頭自娛自樂,村民們通過這個節日表達對先祖神靈的敬畏和對民族英雄的懷念,在祭祀儀式結束后,盡情地唱、盡情地跳、歡快而來、盡興而歸,而現如今搞得太“正式”了。這種“正式”雖然看似熱鬧,卻使得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的敘事性逐漸淡化。因為,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旅游經濟是以旅游活動為前提,以商品經濟為基礎,依托現代科學技術,反映旅游活動過程中,游者和旅游經營者之間,按照各種利益而發生經濟交往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12]。在這種利益關系中,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對于旅游開發公司來說,需要“做大做強”并“千方百計”留住遠方游客,充分發掘這場活動背后的經濟價值。因此,經濟旅游的開發在一定層面上提升了苗族民俗活動的社會影響力,卻也對苗族民俗資源的保護與活動敘事的文化意義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二) 追求舞臺效果的突出,使表演失去了鄉土氣息
文化應回歸鄉土。從文化意義說,充滿鄉土氣息的表演,其實更能反映出一種文化屬性的原汁原味。正如費孝通先生言及“中國傳統文化是講平衡和諧,講人己關系,提倡天人合一”[13]的道理一樣。對于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的資源開發而言,我們應該保持“適度”與“和諧”的態度,如果過度追求舞臺效果容易掩蓋或忽略其原本的文化意義。在一項關于苗族節日的產業化問題研究中也提到,一些旅游企業為了打造節日,存在偽民俗、假節日、過度包裝的問題,不僅不能帶來經濟效益,反而勞民傷財,適得其反,損害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真性[14]。
湘西苗族“四月八”自2011年入選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來,在鳳凰古城已經連續舉辦了5 屆規模盛大的“四月八”民族文化節活動。地方政府和文化旅游企業為“四月八”節事活動進行了精心的舞臺包裝,并邀請當紅民族歌唱家宋祖英、陳思思以及著名畫家黃永玉等名人為整場活動增添影響力。活動分為“大祭祖”“贊英雄”“大聯歡”和“跳花”四大篇章,十分隆重而熱鬧。活動中,巴岱法師“上刀梯”“踩犁頭”“下油鍋”等神秘絕技也搬上了舞臺,成了吸引觀眾眼球的節目表演。震撼的場面與豐富多彩的民俗節目,吸引了湘西周邊的群眾,甚至許多國內外游客也前來觀光。相比鳳凰縣城“華麗變身”的文化節日而言,在鳳凰山江鎮馬鞍山跳花坪舉行的“四月八”活動卻表現出一種“原汁原味”的文化傳承。這里“插秧”“犁田”“耍獅子”“苗族武術”等表演雖然缺少縣城的華麗與熱鬧,也不如沱江兩岸“人山人海”的觀眾捧場,卻充滿著鄉土文化氣息,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更為真實的節事記憶的身體表達。雖然鳳凰縣城的“四月八”已經打造成為當地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極大地推動了招商引資和旅游業的發展,但從文化應回歸鄉土的理想思維來看,其表演的鄉土氣息也正在弱化。
(三) 迎合游客觀眾的心理,使祭祀弱化了儀式感
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祭祀文化已經成為各種儀式慶典的重要內容。盡管不同種族、不同人群,祭祀的內容不盡相同,但不論是何種祭祀,都十分講究祭祀的程序化。這套“程序”通常包括設壇、焚香、燒紙、跪拜、誦經,而祭祀的內容無外乎人、鬼、神、畜等,另外配以鑼鼓、嗩吶、鞭炮、法器、祭品,整個過程以法師為中心,嚴格按照流程進行祭祀,其中燒紙跪拜、誦經等許多環節需要多次重復。因此,一套完整的祭祀程序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短則幾小時,多則三五天,甚至更長。比如苗族最大的“椎牛”祭典儀式,歷時長達四天三夜或五天五夜。從“吃牛難,大戶動本錢,小戶賣田莊”的苗諺可以看出,椎牛儀式不僅耗資多,規模大,而且時間長。這一點,湘西花垣、鳳凰、吉首、保靖、古丈、瀘溪等縣市的方志中都有記載。在乾隆十六年《永綏廳志》中關于椎牛儀式有這樣的描述:“每農事畢,十月十一月,饒裕者獨為之,或通寨聚錢為之。預結棚于寨外,先一日殺牛,請苗巫,著長衣,手搖銅鈴,吹竹筒,名曰做米鬼;次日,宰母豬,吹竹筒請神,名曰做雷鬼;第三日,宰雄豬祭享,名做總鬼;第四日,設酒肉各五碗,米餅十二枚,置火床上,燒黃臘,敲竹筒祀祖,名曰報家先。然后集鄰族友,男女少長畢至,鳴鑼鼓放銃,請牛鬼;第五日,棚左右各置一椿,系黑白二牛各一,先讓極尊之親楫四方畢,用槍以刺,余以序進,一人持水隨潑,血不淋于地。牛既仆,視其首之所向以卜休咎,首向其室則歡笑相慶。”[3]341這套祭祀流程包括許愿、備牛、送黃牯、敬家先、享客、講古根、跳鼓舞、行法、除怪、椎牛、送牛、送客等12個環節。
從文化學意義上來講,這種煩瑣的程序代表著莊嚴與神圣,有著很強的儀式感。而從游客觀眾的心理感受來說,深入體驗祭祀的儀式和程序,才能更有一種身體在場的參與感和體驗感,是一種古老的民族記憶和文化感知。而現如今,在祭祀文化和經濟效益的取舍面前,鳳凰苗族“四月八”活動的祭祀環節單方面顧及觀眾的“審美疲勞”而選擇了簡化程序和形式化操作,使得原本莊嚴而神圣的祭祀活動,有虔誠跪拜的、也有隨意行走的、有專注誦經的、更有大聲說笑的……,這種“鬧市化”的場面大大弱化了祭祀的儀式感。據鳳凰旅游開發公司的數據統計,2011年至今,前來參觀“四月八”這場民族文化節的人數正在逐年下降。為此,我們訪談了一些游客,多數認為,祭祀程序的簡化,缺乏一種儀式的莊嚴感和神圣感,游客們因為“看不懂”而產生了不想“回頭看”的念頭。由此可見,要迎合觀眾的心理,更應當注重祭祀的儀式感。
(四) 注重業績的彰顯,節事缺少了娛樂性
在中國廣袤的農村,農歷四月初八,恰逢春耕結束,農閑時節,正是祭祖、踏春賞花、舉辦民間傳統節事的好時節。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更是一場獨具民族特色、內容豐富且充滿娛樂性的節會。有關“四月八”節日狂歡娛樂的記載甚多,如“四月八日,苗鄉節日,一班男女群喜看之,此為苗鄉集會之一種”“是日愛唱歌之人,相約該處,比賽唱歌之優劣”“在旁觀聽之人亦多,贊聲掌聲較為歡騰。老少踏青游樂,或坐或立,或蹲或臥,任其自便。凡有新裝異服,均穿示眾以炫富”[15]等等。可見,傳統少數民族節事活動在發揮祭祀功能的同時,更不乏娛神娛己的娛樂氣氛。在這場娛樂活動中,無論是表演者,還是現場觀眾,身體共同在場的參與性、積極性、娛樂性都非常強。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在當地政府和旅游企業的傾力打造下,如今的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已經成了苗族人民展示民族文化、加強民族團結、促進經濟發展、建設精神文明的綜合性盛會。2012年湘西吉首德夯苗寨舉行的“中國·吉首苗族四月八”活動,吸引了來自貴州銅仁、凱里等地上萬的苗族群眾。近年來,在湘西鳳凰舉辦的苗族“四月八”活動更是迎來了全國各地甚至海外的游客前來觀光。在現代化節日的精心包裝下,苗族“四月八”的規模越來越大,活動所發揮的經濟效益也越來越大。然而,在精心包裝和打造之下,節目變成了過于“正式”的表演,游客更成了專注于表演的觀眾,由此導致節事活動必然缺少參與性、互動性和娛樂性等這些問題,在我們進一步發掘和開發節事旅游資源時應該予以充分的重視和辯證的思考。
三、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文旅開發的幾點建議
鄉村旅游應立足于本土文化,鄉村+文化旅游是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文旅開發的應然選擇。《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 (〔2015〕62 號) 指出:立足當地資源特色和生態環境優勢,深入挖掘鄉村文化內涵……舉辦有地方特色的節慶活動[16]。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不僅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活動中苗族民眾以身體敘事更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和苗家風情。而民俗活動中的身體敘事“有著廣泛的認同性和極強的解釋性,還具有較強的表現力和可感知性”[17]。因此,對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的開發,應充分考慮身體敘事的本土性和本真性。從巴岱法師到祭祀行為,從苗族舞蹈到娛樂狂歡,都體現出苗族人民通過身體語言敘說著古老的歷史與文化,時下的祈愿與希望。然而,在旅游公司的包裝和打造下,盡管活動規模與經濟效益得到充分凸顯,但同時節事活動本身的敘事性和儀式感正在淡化,其文化本身的鄉土氣息和娛樂性也有所缺失。辯證地看,在打造文化品牌、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考慮文化生態的本真性保護。為此,我們提出發掘和開發“四月八”身體敘事的幾點建議。
(一) 既尊重歷史又尊重民俗,對其身體敘事的闡釋既要保持客觀性的態度又要堅守主體性的立場
歷史分為正史和野史,皆為文化的傳承、積累和擴展,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留下的痕跡。所謂正史就是經過官方編修的歷史,一般較為權威可信。而野史,則是正史之外帶有傳說性質的歷史,許多民間傳說和民俗活動往往反映出歷史真實的一面。苗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我國古代典籍中,有關苗族先祖的記載可追溯到原始社會活躍于中原地區的蚩尤部落。商周時期,苗族先民便開始在長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國”,從事稻作農業。苗族早期有著自己的文字,在《苗族古歌》唱詞中,苗族先民因逃避戰爭和追殺,擔心遷徙秘密暴露,不得已焚燒文字,而后失傳。盡管如此,智慧的苗族人民依然通過各種民俗節事活動,包括祭祀、舞蹈、服飾等身體語言記錄著古老的歷史與文明。因此,對少數民族節事活動中身體敘事的理解,既要尊重歷史又要尊重民俗,如此,我們對文化的闡釋才能保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態度和立場。
(二) 既注重效益又注重生態,對其身體敘事的開發既要考慮商品化的包裝又要堅守本真性的內涵
從經濟學角度理解,效益是指項目對國民經濟所做的貢獻,它包括項目本身得到的直接效益和由項目引起的間接效益。要獲得這種直接或間接效益,需要對相關項目進行商品化包裝,以期獲得更好的銷售。然而,從文化學意義來講,少數民族節事活動有著自身的文化形態,這種文化形態需要堅守其本源性和本土性。因此,對于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的身體敘事開發,要辯證來看待,要將其看成一個文化事項,對其開發既要注重經濟效益,又要注重文化生態。在高度社會化、商業化、信息化的當下,對于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的身體敘事開發既要考慮商品化包裝、擴大規模、加強影響,同時也要堅守其文化本真內涵、注重傳承、突出特色。應該按照中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統一,遵循文化發展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一手抓繁榮、一手抓管理,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18]。如此,我們對節事旅游的開發才不至于削足適履,造成尷尬。
(三) 既顧及游客又顧及居民,對其身體敘事的參與既要有對外來的吸引力又要有對本土的凝聚力
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在商業開發之前,是一場族群內部的集體記憶與民眾狂歡,主要功能是族群認同與族國同構,是凝聚苗族人民內部社會關系的社交活動。因此,這場活動從組織者到參與者均為當地苗族土著居民,其目的是增強本民族民眾的凝聚力。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業得到蓬勃發展。現如今各地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大多進行商品化包裝與打造,也增添了許多現代化元素,成了展示各地民族特色的文化名片。如鳳凰苗族“四月八”形成了民俗特色的旅游品牌,綏寧苗族“四月八”成了招商引資的重要平臺,而貴州苗族“四月八”成了表達歷史文化與經貿洽談的綜合盛會。經過打造的“四月八”節事活動成了“文化名片”,雖然增加了許多外來游客,但是許多當地居民由“參與者”變成了“旁觀者”。旁觀者多了,參與者卻少了,缺少參與者的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勢必削弱其自身的內生動力。因此,在“四月八”節事旅游的開發過程中,既要顧及游客,又要顧及居民,其身體敘事的參與既要有對外來人的吸引力又要有對自己人的凝聚力。如此,才能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下“共商、共建、共享”的互利共贏。
四、結語
少數民族節事活動有著豐富的身體敘事內涵。通過探究湘西苗族“四月八”節事活動中的身體敘事,發現巴岱的身體是連天接地、通古問今的重要媒介,祭祀的身體是奉谷獻粟、敬祖尊神的文化符號,舞蹈的身體是傳史承道、敘事達情的身體記憶,娛樂的身體是跳花跳月、娛神娛己的情感表白。近年來,圍繞經濟旅游的開發,湘西苗族“四月八”活動的身體敘事性有所淡化,使其表演失去了鄉土氣息,祭祀弱化了儀式感,也缺少了娛樂性。節事活動作為一項重要的文化載體,關系到中華民族固有的家國同構、族國同構的根基。因此,從堅守文化的主體性立場和本真性內涵出發,對身體敘事的闡釋應該保持客觀性和主體性相統一,對節事的旅游開發要考慮商品包裝和文化堅守相結合。如此,我們對文化本身的闡釋才能堅守“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立場,對節事的旅游開發才能不忘“共商、共建、共享”的初心,在文旅融合和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才更有利于中華民族文化繁榮和當地經濟、文化、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