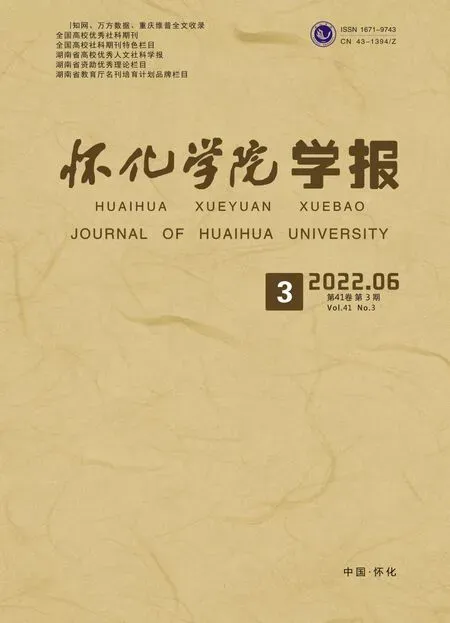家庭生計模式與疫情下跨境婚姻家庭穩(wěn)定性研究
——基于滇東南M 縣的調查
王顧言
(云南民族大學社會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4)
一、問題的提出
自疫情以來,我國對社會進行了嚴格、有效的管制,主要表現(xiàn)在確保合法流動、做到有痕流動、控制聚集規(guī)模等。這些舉措在我國邊境的疫情反復地區(qū),尤其是西南邊境執(zhí)行得尤為嚴格與細致,防控的效果也尤為顯著。但其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同時,也對西南邊境存在的大量跨境事實婚姻家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邊境地區(qū)事實婚姻家庭的穩(wěn)定不僅關乎其自身,更對邊境地區(qū)社會治理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探究特殊防控期間西南地區(qū)跨境婚姻家庭的穩(wěn)定性變化對于落實社會有效治理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一) 國內有關跨境婚姻家庭的研究概述
我國關于跨境婚姻的研究整體上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學術界對于跨境婚姻最初的研究是從其形成機制開始。學界普遍認可的跨境婚姻形成機制主要分為兩類。一是認為跨境婚姻的形成是基于特殊的地理歷史因素,在特定社會環(huán)境的社會群落中產生的[1];二是從邊民互動著手研究跨國婚姻的形成,認為邊民跨國婚姻是邊境地區(qū)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也是兩國邊民在日常生活與非日常生活中頻繁互動交往的結果[2]。第二,學界還從婚姻家庭的角度展開論述。有的從外籍婦女身份認同著手討論其社會適應,呼吁政策關注跨國婦女國籍問題[3],也有學者將跨國婦女及其子女的身份困境問題高度概括為“他者認同與制度排斥”的問題,例如,認為那些無法肯定自我的越南婦女當中必然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拒斥性認同[4]。第三,由于跨境婚姻家庭是跨境婚姻現(xiàn)象的主要社會治理主體,因而其家庭自身的穩(wěn)定性對于研究分析跨境婚姻現(xiàn)象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當前我國關于跨境婚姻家庭穩(wěn)定性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三種觀點。其一,從跨境婚姻締結的自身機制來說,有學者從買賣婚姻出發(fā)評價這種締結方式對家庭穩(wěn)定性造成的影響,認為通過買賣婚姻組成的家庭極不穩(wěn)定,“守不住,養(yǎng)不熟”[5]。其二,從跨境婚姻面臨的社會適應而言,有學者認為基于經濟吸引而嫁進來的越南女性難以適應當?shù)厣鐣菀妆煌饨缫蛩赜绊懀敩F(xiàn)實與理想出現(xiàn)落差,越南女性往往會改嫁或離開[6]。其三,從跨境婚姻面臨的社會制度約束來說,有學者關注到了跨境婚姻家庭的制度保障問題,呼吁政府調整相關政策,以便從根本上解決問題[7]。
縱觀學界對跨境婚姻的相關研究,對跨境婚姻形成機制以及跨境婚姻家庭的研究重點在于從社會結構(無論宏觀、微觀) 的角度考察跨境婚姻(家庭) 這一社會現(xiàn)象以及其連帶問題產生的社會機制。雖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是歸根結底都是一種外部的靜態(tài)視角,沒有認識到跨境婚姻及跨境婚姻家庭間的區(qū)別,忽略了婚姻的分析主體——家庭,因此較難深入這些現(xiàn)象背后的問題本身。當前關于跨境婚姻家庭穩(wěn)定性的研究事實上也重復了我國跨境婚姻研究第一和第二個方面的缺點,依然是從宏觀、外部視角分析相關因素對跨境婚姻家庭穩(wěn)定性的影響,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從這些家庭內部自身的結構、動機等方面來分析這些家庭的穩(wěn)定性。并且更為重要的是,當前關于跨境婚姻穩(wěn)定性的研究中,鮮有關注疫情對家庭穩(wěn)定性的影響。本文嘗試從跨境婚姻家庭的自身結構類型角度出發(fā),分析新冠疫情對跨境婚姻家庭穩(wěn)定性的影響。
本文主要依據身份合法性對不同跨境婚姻家庭進行分類,進而對疫情下不同類型家庭自身穩(wěn)定性的影響進行分析,從而闡明何種結構下的家庭面對新冠疫情管制時其穩(wěn)定性最強,而何種家庭結構下的家庭穩(wěn)定性最為脆弱,容易引發(fā)社會問題。進而在當前我國后疫情時代的現(xiàn)實背景與推進鄉(xiāng)村振興、治理相對貧困的政策背景下,為地方政府治理跨境婚姻提供政策指導。
(二) 田野點概況
滇東南M縣的邊境國界線有近三百公里,M縣的壯族、苗族、瑤族、彝族、傣族和仡佬族都屬于跨境民族,與邊境另一側的居民屬于同源文化民族,相互地域相連,語言相通,文化相同或相似,交往歷史悠久。2019年前,跨境婚姻呈現(xiàn)一種逐年上升的趨勢,2018年甚至多達一千余對,邊境往來走訪頻繁,但由于2021年以來疫情嚴防嚴管,跨境婚姻數(shù)量沒有明顯增長,反而呈現(xiàn)斷崖式下降。公安系統(tǒng)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據顯示,2021年大約只新增幾十個跨境婚姻家庭。據當?shù)毓簿纸y(tǒng)計,縣內目前有近5000 個跨境婚姻家庭,其中進行了合法登記的僅占總數(shù)的4%,外籍人員有近6000 人,無法取得戶口的外籍子女約占外籍人員總數(shù)的5%,即“黑人黑戶”①。
M 縣跨境婚姻的主要特點:(1) 通婚對象以越南人為主,且呈現(xiàn)女方單向的嫁到中國的特點;(2) 分布廣,幾乎全縣域內都有分布;(3) 族內通婚明顯,基本都是同源民族;(4) 女方年齡呈現(xiàn)低齡化趨勢;(5) 女方整體文化水平偏低,基本都是初中以下;(6) “滾雪球”[5]婚姻締結方式,多為熟人親戚介紹,即先嫁入我國邊境的越方女性把身邊的女性介紹到同一個村或鄰村的女方介紹方式。根據調研,M 縣跨境婚姻產生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 地理條件便利,山水相連,沒有明顯的地理分界和地界區(qū)分; (2) 民族之間同源同宗,語言風俗習慣基本一致;(3) 村莊之間通婚歷史悠久;(4) 兩國之間經濟發(fā)展差距大,越南經濟水平與我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差不多,對女方有吸引力,且我國婦女地位較越南高; (5) 兩國國情,越南由于長期戰(zhàn)爭,國內女性數(shù)量比男性多,我國則是男多女少,雙方互補有利于改善人口結構。
由于多數(shù)越南新娘都是通過中間人介紹嫁到中國,所以男女雙方之前具有的感情基礎并不深厚,在組成家庭的初期,男方并不著急外出務工,而是選擇在家中與新婚妻子培養(yǎng)一段時間的感情,待有初步的感情基礎或者子代出生之后才外出務工。在疫情出現(xiàn)以前,邊境地區(qū)對外籍人員的管控并沒有上升到紅線的程度,外籍人員有多種途徑可以獲得收入(外地務工、打零工等),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跨境婚姻家庭在經濟收入層面與本地婚姻家庭無異。而在疫情開始之后,我國嚴格限制外籍人員出入境,對居住在我國境內的外籍人員的監(jiān)管上升成為工作的重點,一方面限制他們的活動范圍,另一方面禁止境外方偷渡國界,將“三非人員”驅逐出境,以至于沒有身份證明的外籍人員想去內地打工已不可能。已構成事實婚姻的境外方配偶只能留在家中從事小規(guī)模的農業(yè)種養(yǎng)殖或做些零工來獲取收入,這極大地減少了家庭的經濟收入。他們那些留在國外的親戚由于是“三非人員”②也被限制入境,跨越邊境的走親訪友是不被允許的,在當?shù)赜泻芏嗫缇郴橐黾彝ヒ虼吮黄确蛛x。長期處于一種家庭不完整狀態(tài),也為家庭埋下了不穩(wěn)定的因素。
二、分析框架
邊境跨境婚姻家庭成員的構成與普通婚姻家庭成員的構成最大的區(qū)別在于,涉外婚姻會牽涉配偶方的境外身份,其次是可能會攜帶外籍非婚生子女入境。跨境方合法身份的有無直接影響跨境婚姻的合法性,也決定著個人的生計方式。生育子女是家庭血脈的延續(xù),而撫育子女則是為家庭和社會培育新的勞動力的過程。子代成為勞動力之后可以為家庭創(chuàng)造經濟價值,使家庭這個三角結構更加穩(wěn)固,但在這之前很長的一段撫育周期,家庭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與金錢。外籍子女在跨境婚姻家庭當中處于一個較為尷尬的地位,非婚生子女不能加入中國國籍,無法享受中國國民待遇,在求學和就業(yè)方面都受到不小的限制。其次,外籍子女同樣需要較長的撫育期才能成為家庭的新勞動力,這樣一來,短時間內邊境婚姻家庭中的合法勞動力往往只有境內方一人。我們在分析跨境婚姻家庭構成中重點關注的是撫育周期尚未結束的家庭,處于這一階段的家庭不僅不能依靠新生勞動力創(chuàng)造收入,反而需要不斷地投入成本。
基于上述原因,邊境跨境婚姻家庭成員構成涉及兩個最核心的因素,一是跨境婚姻配偶方合法身份的有無;二是是否攜帶外籍子女。前者影響家庭的生計分工,后者影響家庭的供養(yǎng)壓力。家庭經濟收入越高,因經濟原因而導致家庭破裂的可能性就能降低。所以根據這兩個核心因素將邊境婚姻家庭區(qū)分為三類:“理想”家庭、“半理想”家庭和“非理想”家庭(見圖1)。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發(fā)生之前,不具有合法身份的越南女性外出務工雖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生計方式上的靈活為其增加了很多勞動機會,家庭的收入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可觀的。疫情到來后,嚴格的管控縮小了她們的可活動范圍,勞動機會與收入也隨之減少,家庭經濟收入主要靠男性外出務工獲得。雖然現(xiàn)實中確實可能存在越南男性娶中國媳婦組成家庭然后留在中國的情況,但在調研走訪過程中遇到的村民、村干部均表示該地近幾十年來沒出現(xiàn)過這個情況,所以不存在家中男主人是外籍人員的情況。故在對邊境婚姻家庭成員做分類的時候,默認家中的經濟支柱是男方,特此說明。

圖1 家庭類型圖
(一) “理想”家庭
“理想”家庭指婚姻雙方都具有合法身份、在我國民政部門進行了婚姻登記、各方面權益受到合法保障的家庭。由于沒有身份的顧慮,男女雙方都可以外出務工,家庭的經濟供養(yǎng)模式是雙線供養(yǎng),婚后生育的子女可以落戶,且待撫育成人后也可以成為勞動力。這類家庭即使伴隨外籍子女的進入,其外籍子女的戶口也有寄托。與我國男性結成家庭后,家庭的經濟供養(yǎng)模式依然是雙線供養(yǎng),外籍子女的存在反而為家庭的收入多提供了一條路徑,家庭分工屬于典型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模式[8]。基于這種考慮,該類家庭構成一個穩(wěn)定的三角結構,家庭的穩(wěn)定性相對較高。
(二) “半理想”家庭
這里說的“半理想”家庭是指女方沒有合法身份,沒有攜帶外籍子女的家庭。后代經親子鑒定確認是親生子女即可落戶中國,將來也可以成長為家庭潛在的勞動力。由于女方身份受限,輕易不會選擇外出務工,所以這種家庭的經濟供養(yǎng)模式多為以男方的單線供養(yǎng)為主、女方靈活就業(yè)的副收入為輔的家庭雙線收入模式。經濟環(huán)境理想的時候勞動機會多,女方的生計方式也較為多樣,可以就近務工也可以外地務工。這類家庭的供養(yǎng)模式看似依靠男性單線供養(yǎng),實際女方靈活就業(yè)獲得的收入與本地一般家庭相差無幾。就算女性選擇在家務農,在經過一個正常的撫育周期后,子代也能成為新的勞動力,從而使得家庭形成一個較穩(wěn)定的三角結構,穩(wěn)定性雖較理想家庭弱,但也能維持基本運轉。
(三) “非理想”家庭
“非理想”家庭是女方沒有合法身份,同時也攜帶了外籍子女入境。家庭潛在勞動力育成需要很長的周期,婚生子與外籍子女同時存在的家庭需要負擔雙重的撫育成本,即使夫妻雙方都有收入,家庭的經濟壓力仍然較“半理想”家庭重。而且由于外籍子女無法在我國落戶,求學就業(yè)等也就無法享受國民待遇,醫(yī)療和社會保障仍舊需要依靠家庭的供養(yǎng)。在非特殊時期,外籍子女可以同母親一樣從事靈活就業(yè)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但在特殊時期外籍子女不僅無法獲得收入,反而需要來自家庭的經濟支持,加重家庭經濟負擔。總而言之,外籍子女是家庭中的不穩(wěn)定因素,極易受環(huán)境的影響進而影響家庭的經濟情況,故此類家庭處于一種低穩(wěn)定狀態(tài)。
三、疫情前后的家庭生計模式變化
在M縣,“理想”家庭僅占跨境婚姻家庭總數(shù)的大約4%,數(shù)量極少且實際上此類家庭與本地婚姻家庭幾乎沒有區(qū)別,可以視作學界一般研究的普通農村家庭。疫情對于此類家庭的影響與本地婚姻家庭一樣,都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因此不在本文重點討論的范圍之內,僅依照分類窮盡原則列舉,但下文不贅述。
(一) “半理想”家庭:雙線收入到單線收入
從M縣公安局登記的外籍子女數(shù)量上看,“半理想”家庭是M 縣跨境婚姻家庭的主要構成類型。經濟環(huán)境較為理想的時候女方既可以跟隨男方一起前往外地靈活就業(yè),也可以留在家中就近務工,同時與長輩一起經營農田。此時家庭經濟來源以男方外出打工收入為主,女性靈活就業(yè)收入為輔,生活水平基本可以與本地一般家庭持平。而在疫情的影響下,她們中的大部分人失去了前往外地打工的機會,被迫在家留守。家庭的經濟壓力主要由男方一人承擔,女方在家中就近打零工或者在自家農田里種植一些作物,對家庭的經濟收入所能起到的輔助性作用下降。疫情后這類家庭的生計模式從之前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農”生計模式轉變?yōu)椋耗蟹酵獬鰟展ぃ彝ソ洕饕獊碓矗?+女方與長輩在家從事農業(yè)(家庭收入次要來源) +業(yè)余從事打零工/黑工(家庭不穩(wěn)定收入來源) - 撫育子代(潛在勞動力的養(yǎng)成)。
從半理想家庭開始,男性的家庭供養(yǎng)的壓力已有所體現(xiàn),疫情爆發(fā)后由于對外籍人員的管控上升到監(jiān)控紅線的程度,絕大多數(shù)老板不愿招收這些非本國籍的工人,導致勞動機會大大減少,女方只好退回農村從事小農經濟。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變成僅靠男方一人支撐,女方通過小農經濟為家庭收入創(chuàng)收成為次要來源,偶爾通過就近“打黑工”補貼家用,即此時家庭收入由原本的雙線收入轉變?yōu)閱尉€收入。
ZLF③:“以前沒有管得那么嚴格,廠老板需要大量招工的時候也不用看你身份證,符合條件就直接上崗了,所以那些越南媳婦就跟著老公去外地打工咯。現(xiàn)在哪里還有老板敢招外國人,他(老板) 也怕被抓嘞。”
QYT④:“有些時候是男的先去廠里做一年活,等環(huán)境都熟悉之后去問老板可不可以帶他媳婦過來(打工),他媳婦沒有身份證的,有些老板不在意這些,他媳婦就一起過去了。以前就是當上面有人來查的時候就讓她們(外籍人員) 找地方躲著,不準出來,現(xiàn)在只有一些膽子很大的老板才敢這樣咯。”
邊境地區(qū)跨境婚姻家庭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情感基礎則是日后慢慢建立和加深的,所以當家庭的經濟情況出現(xiàn)問題時,情感因素在彌補家庭危機中起的作用也不大。比如男方喪失了勞動能力,家庭就失去了經濟來源,經濟危機也會破壞夫妻之間的感情,這些家庭就將會面臨破碎的風險,感情基礎相對較弱的家庭當中女方往往會選擇改嫁。
HXL⑤:“家里男的如果病了或者殘了,不能苦錢(掙錢) 了,就剩一個媳婦(越南媳婦) 在家守著娃娃,一般都守不了好久就走(改嫁) 咯。”
(二) “非理想”家庭:雙線收入到雙線內耗
非理想家庭的生計模式在半理想家庭生計模式的基礎上多出了外籍子女這個不穩(wěn)定項。據統(tǒng)計,M縣外籍子女的母親沒有合法身份,與男方又不構成血緣上的親屬關系,所以無法在中國落戶,年紀小的在當?shù)馗S同齡人完成基本的義務教育后無法正常升學,較早地成了社會閑散人員,其主要生存方式還是依靠家庭供養(yǎng),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外籍子女也更早地成了家庭新生代勞動力。
LJG⑥:“那些外來娃娃(外籍子女) 基本上初中畢業(yè)就出去找活了,不然就是在街上到處閑逛,父母也惱火得很,就把他們打發(fā)出去做活了,多少還能賺點錢回來。”
在疫情爆發(fā)之前,年齡大的外籍子女可以通過在家做農活、打零工或者去外地尋找更多的勞動機會,為家庭減輕經濟壓力。但是疫情爆發(fā)之后,他們面臨著更嚴格的監(jiān)管,被發(fā)現(xiàn)之后所承擔的后果也更嚴重(輕則罰款,重則遣返),喪失了外出工作的機會,在家附近的“黑工”收入極不穩(wěn)定,故而疫情爆發(fā)之后這類家庭由原本雙線供養(yǎng)的家庭生計供養(yǎng)模式轉變?yōu)閱尉€供養(yǎng)、雙線內耗的生計模式。體現(xiàn)在生計模式上表現(xiàn)為:男方外出務工(家庭經濟主要來源) +女方與長輩在家從事農業(yè)(家庭收入次要來源) +業(yè)余從事打零工/黑工(家庭不穩(wěn)定收入來源) - 撫育婚生子(潛在勞動力的養(yǎng)成) - 供養(yǎng)外籍子女(家庭的內耗)。
與婚生子一樣,被攜帶入境的外籍子女消耗同樣的家庭成本,但日后為家庭帶來的經濟收益卻遠低于婚生子,那些婚生子與外籍子女皆有的家庭則更是消耗雙重撫育成本,所以有外籍子女的跨境家庭抗風險能力也就較其他家庭更低。
總而言之,我國對邊境地區(qū)“三非人員”的管控一直存在。在疫情爆發(fā)之前,事實婚姻的存在為這些外籍人員的居留提供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家庭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庇護所,因此在非特殊時期,這種道德合理性可以大于外籍人員本身的制度合法性,為外籍人員就地務工甚至前往內地提供了可行性。但在疫情開始之后,嚴格的邊境管控在原有基礎上更加強調了外籍人員的合法性,使其超越了非特殊時期跨境婚姻為外籍配偶提供的合理性。這些外籍人員的行動被嚴格限制,喪失外出務工機會,多改為在家務農或從事“打黑工”。因此,疫情期間“半理想”家庭與“非理想”家庭均出現(xiàn)了外出勞動力回歸,家庭收入下降的局面。家庭供養(yǎng)模式由之前的雙線收入變?yōu)閱尉€收入加輔助性收入,家庭內耗增加,家庭經濟下降,給跨境婚姻家庭的穩(wěn)定性帶來了影響。
四、疫情對邊境跨境婚姻家庭穩(wěn)定性的影響
家庭穩(wěn)定性和家庭生計模式有著直接的關系。首先,家庭成員的分工間接地區(qū)分了不同的家庭生計模式:夫妻雙方的“雙線供養(yǎng)”,男方一人的“單線供養(yǎng)”。其次,家庭生計模式影響著家庭的經濟收入。最后,家庭的經濟收入高低決定了家庭穩(wěn)定性的高低。疫情爆發(fā)后的內地農村家庭,夫妻雙雙外出務工或者一方留守是家庭的主動選擇,但邊境地區(qū)婚姻家庭的特殊性導致女方的留守往往是被迫的,也就是說這些家庭的生計模式在疫情爆發(fā)后已轉向以“單線供養(yǎng)”為主,家庭的經濟收入明顯受到影響。
基于家庭生計模式差異,疫情導致的家庭整體收入下降對半理想家庭與非理想家庭的穩(wěn)定性均有影響,均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但二者下降的幅度不一,其中非理想家庭下降的幅度更大。
(一) 半理想家庭:經濟危機
邊境地區(qū)男女雙方成家背后的行動邏輯存在差異,男性主要是“家本位”,女性則主要是“錢本位”。在我國傳統(tǒng)價值觀中,男性往往是“先成家,后立業(yè)”。受傳統(tǒng)價值觀的影響,邊境地區(qū)的男性在建立家庭、生育子代后才能安心在外務工。所以那些在本地婚姻市場受到擠壓的男性為了建立家庭,就選擇了向外求偶,與越南媳婦構成家庭。而當?shù)氐脑侥吓栽敢饧薜街袊钪匾脑蚴俏覈慕洕l(fā)展水平高于越南,在這邊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這種男女雙方結婚成家的目的取向不同就造成了價值追求的不同。男性成家后的思考邏輯是“家本位”,基于家庭邏輯做出行動,婚后育有子女培養(yǎng)出一定感情再外出打工;而女性是基于經濟誘惑才嫁過來成家,感情是后來培養(yǎng)的,當下的生計穩(wěn)定則家庭穩(wěn)定,這是出于“錢本位”的個人邏輯。二者的不對等導致對家庭經濟情況做出的選擇也不一致。
疫情爆發(fā)后的半理想家庭,由于女方沒有合法身份喪失了外地的勞動機會,為了補貼家用幾乎都選擇做農活,比如種莊稼、養(yǎng)豬。在當?shù)匾部梢酝ㄟ^給一些工廠打“黑工”獲得收入,只不過風險較大,一旦被警察發(fā)現(xiàn)可能面臨高額罰單甚至遣返回國,家庭經濟收入較疫情以前減少。在這樣的家庭角色分工當中,男性是家中經濟的支柱,女性則是依附者角色,男方穩(wěn)定的收入加上女方來自務農、零工等的輔助收入也能夠維持家庭運轉。但男性一旦喪失勞動能力或者家庭經濟狀況出現(xiàn)問題,后天培養(yǎng)的感情基礎并不牢固,成為家庭不穩(wěn)定的隱患。
(二) 非理想家庭:經濟、情感雙重危機
經濟收入受到家庭生計模式的影響,而外籍子女的有無則是影響家庭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另一變量。實際上,那些有外籍子女的越南媳婦大多是二婚甚至多婚,迎娶她的家庭本身條件就一般,以至于男性很難娶到初婚女子。沒有合法身份的外籍子女從養(yǎng)育到成年所需要的周期較長,成年之后也不能正常打工,即使有婚生子女作為后備合法勞動力,同樣需要漫長的撫育周期。因此,家庭一直處于巨大供養(yǎng)壓力之下,抗風險能力不高。男性承擔撫育與自己沒有血緣關系的子女更多是基于夫妻之間的義務,其中的義務性大于情感性,這種情感偏向在婚生子出生之后可能更加明顯,但是由于家庭經濟還比較穩(wěn)定,這種感情矛盾還不至于上升到家庭矛盾。但疫情導致這類家庭陷入經濟的窘境,卻比半理想家庭還多承擔一份不見回報的供養(yǎng)壓力,久而久之,對非血緣關系的子女的不滿很可能就會上升到夫妻層面的矛盾,從而動搖家庭關系。
LT⑦:“小的嘛就跟著老娘在屋里,大一點的嘛這幾年出不去啦,不敢出,去遠了被警察抓到可能要坐牢嘞,怕人得很,很多老板也不敢要了,所以這幾年陸陸續(xù)續(xù)都回來了,在家?guī)椭P盤地喂喂雞,掙不到錢喲。”
非理想家庭在疫情的影響下家庭功能失能的情況比前兩類家庭都更為嚴重,可以外出務工的勞動力縮減為只有家中男主人一人,但是需要供養(yǎng)的人口數(shù)量沒變,家庭的經濟功能受損。當?shù)卣块T依照政策為這些低收入家庭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即以家庭為單位對他們進行補貼,減輕其經濟壓力,保障家庭的基本運轉,也允許他們正常繳納養(yǎng)老和醫(yī)療保險,也可以得到我國政策的優(yōu)惠,但是大頭依舊需要來自家庭的支撐。外籍子女的成家立業(yè)也是問題,家庭無法進行再生產,沒有新鮮的血液補充進來,加劇了家庭的脆弱性。基于與外籍子女的非血緣關系紐帶建立起來的情感非常容易被外界影響所打破,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夫妻之間的感情,是影響家庭穩(wěn)定性的一大因素。
HXL⑤:“誰愿意養(yǎng)別人的兒子,那不是沒得辦法嗎,自身條件也討不著更好的了,湊合過過日子,就當家里多一個干活吃飯的,成家的事情以后再說。”
彭大松基于云南省7 個貧困縣的調查數(shù)據統(tǒng)計顯示:家庭貧困加劇了婚姻脆弱性。貧困程度越深,家庭收入越低,婚姻穩(wěn)定性越差;個人收入對婚姻穩(wěn)定性有非線性影響。在低收入階段,收入的增加顯著降低離婚風險,在高收入階段,收入的增加推高了離婚風險[9]。疫情給邊境跨境家庭帶來的最大沖擊來自經濟層面,也是影響跨境家庭穩(wěn)定性的直接因素,由于情感因素會受經濟因素的波及,后天培養(yǎng)的家庭情感如果力量薄弱,則會間接成為家庭穩(wěn)定性下降的因素。
五、結語
家庭是社會群體的最小單位。健全和健康的家庭是國家與社會穩(wěn)定、安寧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若家庭出現(xiàn)問題,社會就會有麻煩;若眾多家庭同時出現(xiàn)問題,就可能引起社會動蕩、國家不寧。在疫情下,邊境跨境婚姻家庭中半理想與非理想的家庭由于生計變動的影響,其家庭穩(wěn)定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具體表現(xiàn)為,半理想家庭其生計模式由雙線收入轉變?yōu)閱尉€收入,進而其家庭面臨經濟困境,動搖了以經濟為取向而結合的家庭;非理想家庭則面臨更大的困境,其生計模式由雙線供養(yǎng)轉變?yōu)殡p線消耗,使得其不僅面臨經濟危機,更會導致情感危機,進而危及家庭完整。而這種家庭穩(wěn)定性的削弱,帶來了復雜的社會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家庭的社會化功能和贍養(yǎng)功能的失能以及社會治理成本的提升。
云南邊境線漫長且雙邊多為同源民族,存在大量事實婚姻家庭。一旦放松管理會造成大批邊民涌入,給我國邊境地區(qū)的疫情防控和管理帶來巨大工作壓力,但完全禁止他們入境又會對跨境家庭的穩(wěn)定性造成沖擊。同時,對于已經在我國境內生活且締結事實婚姻的境外人員,其生計問題的落實是保障其婚姻家庭穩(wěn)定的關鍵。
基于多方面的考慮,筆者認為,從完善邊境地區(qū)邊民通婚法規(guī)、跨國婚姻登記制度的角度出發(fā),或許可以改善跨境婚姻家庭人員的身份合法性困境。半理想家庭與非理想家庭的形成受家庭成員身份的合法性影響,跨國婚姻登記制度的完善可以為他們的婚姻提供法律保障,繼而可以為他們的身份進行擔保,便于他們在我國境內合法流動,有助于降低邊境地區(qū)半理想與非理想家庭的數(shù)量。從創(chuàng)新邊境地區(qū)社會管理模式的角度思考對策,對陷入經濟困難的跨境婚姻家庭提供社會幫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因為經濟緊張造成的家庭危機。從半理想家庭開始,家庭經濟供養(yǎng)壓力開始逐漸遞增,尤其在疫情的影響下,不少家庭的經濟收入減少。對受影響程度較大的家庭提供一定的幫扶可以有效地減輕他們面臨的經濟壓力,保證其家庭的穩(wěn)定性。
疫情波及廣大家庭,而邊境的維穩(wěn)從來不只是家庭或政府單方面的事情,它有賴于國家、家庭等多主體的參與。邊境穩(wěn)定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跨境婚姻家庭的穩(wěn)定是邊境穩(wěn)定的基石,家庭的穩(wěn)定是家庭功能維持常態(tài)化運行和社會正常運轉的關鍵。因此,如何在保證防疫大局的前提下,實施更加人性化的邊境治理,真正做到凡邊境之內壯有所用、幼有所養(yǎng),是對當前邊境管理工作的重大考驗。這考驗不僅關系到疫情防控,更關系眾多家庭的完整與穩(wěn)定,關系到社會的和諧。
注釋:
①此處對調查數(shù)據做模糊化處理,下文涉及到相關數(shù)據亦然。
②“三非人員”是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yè)”的人。
③ZLF,男,43 歲,滇東南 M 縣人,訪談時間為 2021年 7月。
④QYT,男,45 歲,滇東南 M 縣人,訪談時間為 2021年 7月。
⑤HXL,男,42 歲,滇東南 M 縣人,訪談時間為 2021年 7月。
⑥LJG,男,53 歲,滇東南 M 縣人,訪談時間為 2021年 7月。
⑦LT,女,50 歲,滇東南 M 縣人,訪談時間為 2021年 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