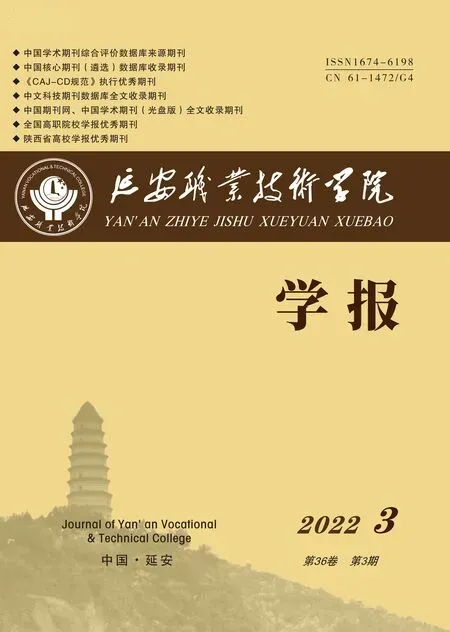《秋燈瑣憶》中的敘事成分淺析
席紫怡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引言
在明清小品文的敘事研究中,《影梅庵憶語》與《浮生六記》一直備受關注,自《影梅庵憶語》伊始,開創了名為“憶語體”的文章體裁,即通過敘事者對過去生活的回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身的人生經歷與思想歷程。我們也可以看到明末清初社會動蕩之際文人在從事文學創作時,從儒家傳統的“文以載道”經世致用的文學創作原則轉變為窗牗之后專注于書寫閨閣生活這一流動過程,并以此了解文人轉入家庭視角的敘事作品中所蘊含的興亡之感,身世之嘆亦或是惆悵之傷,從而去探究該時代大背景下文人生活的另一個切面。
《秋燈瑣憶》便是繼《影梅庵憶語》《香畹樓憶語》《浮生六記》之后的又一“憶語體”散文。文章以主人公“余”即作者蔣坦的視角在妻子亡故后回憶起與妻子生活的點點滴滴構成,在回憶中帶有十分豐富的情感色彩,將閨閣之中的小天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一、《秋燈瑣憶》的敘事學背景與敘事成分類型
(一)中國敘事的傳統與發展
中國文學擁有悠長的敘事傳統,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成熟并衍生出了許多類型。最早的敘事可以濫觴到語言出現之時,由于并沒有文字可供記載,僅僅是簡單的口頭敘事,現如今已難以考證。而這一現象伴隨著文字的出現逐漸轉換為了文本敘事,所敘時間伴隨著文本的保存得以流傳于后世。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可以被稱為“有秩序的記述”最早可追述到殷商時期的甲骨卜辭以及《易》卦爻辭。再到后來的青銅器銘文擁有了詳實的敘事功能,能夠記錄包括時間、地點人物在內的諸多敘事要素,使得敘事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到明清之時,中國敘事文學發展日趨于成熟。敘事主體轉換成為了明顯的標志,由史官敘述的史傳傳統逐漸轉入了小說、散文、戲曲等不同的敘述文體。這主要表現為敘述手法的逐漸成熟,敘事方式的紛繁錯雜,敘事作品的百花齊放。同時,伴隨著戲曲點評的長足發展,使得文人們往往可以通過戲曲點評與小說去深入討論敘事理論,因此進一步加深了敘事文學的繁榮。越來越多的敘事計較也被運用與不同的問題之中,敘事成分的種類逐漸豐富。
“憶語體”的文章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產生的一個支流,它既是敘事文學這顆大樹興盛的一個具體枝節的體現,也是文學中敘事性的生動表現。而《秋燈瑣憶》就是“憶語體”文學的其中一部作品,它在行文之中以無數事件的敘述所構成,以“余”即作者蔣坦第一人稱的視角回顧與妻子從青梅竹馬的相知,到結縭數十載的婚后生活,通過對無數小事件的敘述體現了蔣坦與妻子秋芙的鶼鰈情深,同時也通過種種婚后的事件塑造了妻子秋芙這一典型的女性形象。魏滋伯在《秋燈瑣憶·序》中評價道:“今觀藹卿茂才《秋燈瑣憶》一編,比水繪影梅諸作,情事殊科,詞筆同美。”[4]19-20可見《秋燈瑣憶》在憶語體文章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二)《秋燈瑣憶》敘事成分的分類
對《秋燈瑣憶》中的敘事成分可分為三個類型,分別是敘事角度與敘事時空、敘事模式以及主要的敘事手法。
一個敘事作品的視角往往決定了敘事內容與風格的不同,因而本文將著重探索其敘事視角的作用及作者選擇該視角的原因,進一步探究視角的選擇對文本的影響。由于《秋燈瑣憶》這一作品是作者從現在這一時空回憶過去瑣事組成,回憶往往是無時序無規律的,因而造成了敘事時空的混亂與無序,因而對于敘事時空的探索也納入其中。
作者在《秋燈瑣憶》中對情節脈絡的發展與表現中,大量的運用了古今交錯的敘事模式,通過顯示慘淡結局與過往美好回憶的交替描述,不同的敘事時空也在文中重疊,對于情節脈絡的梳理有助于全面的認識敘述事件的全面以及敘述者的創作意圖,從而進一步發掘背后的內涵。而以事敘人的敘事手法運用,將妻子的形象完整呈現而出,從而使全書情節梗概、事件發展的輪廓更加清晰,對于全書記敘事情的認識也將得到深化。
二、《秋燈瑣憶》的敘事角度與敘事時空
(一)敘事人稱與視角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將敘事人稱與視角總結分別分為了兩類,即敘事人稱分為第三人稱與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分為全知視角與限知視角。[2]43《秋燈瑣憶》文本所采取的正是第一人稱以及全知視角,如石昌渝先生所言:“敘事者毫不掩飾自己在作品中的存在,他不但時時中斷敘述站出來對情節中的人和事加以詮釋和進行評論,而且在敘述時使用感情傾向顯露的語言以表達自己的愛憎……敘事者不但知道任何人物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干什么,而且知道任何人物的內心隱秘。”[2]43《秋燈瑣憶》在這一敘述人稱中以“余”的角度回顧了自己和妻子從青梅竹馬到結為夫婦再到婚后生活的點點滴滴,從“余”這一視角刻畫了妻子秋芙這一生動的女性形象,同時傾注了對妻子濃烈深沉的愛情。采用第一人稱進行敘述,往往會充滿強烈的主觀色彩,同時亦容易將讀者帶入情節之中,與作者一同置身大時代之下的小家庭中,體會微觀角度中的情感與生活。同時,全知視角的采用使得全文穿插在過去與現在,過程與結局之間,充滿了回憶的真實觸感以及前后的因果聯系性。
蔣坦以“道光癸卯閏秋,秋芙來歸。”[1]1519作為開頭,回憶起與妻子結婚的時刻,往往能夠將讀者直接帶入他們二人之間的故事中去,跟隨著文中的敘事主體即“余”,站在他的角度去了解他們夫婦間的那些生活瑣事與成長經歷,這一敘事視角是作者將自身的敘事行為融入到了這一家庭當中,所見之處皆為一戶人家房門內的種種小事。
從作者的敘事視角中可以看到,他始終以一種平等的充滿尊重的角度去看待妻子。他們二人因“夏夜苦熱”在妻子的邀約下可同游理安寺;秋芙夜深口渴欲飲水,然而“瓦铞溫暾,已無余火,欲呼小鬟,皆蒙頭戶間,為趾離召去久矣”,他便“分案上燈置茶灶間,溫蓮子湯一甌飲之”[1]1520;他善于傾聽并欣賞妻子,在妻子看法出奇卻與他相左的時候能嘆“不意秋芙亦能作議論,大奇”[1]1525。這與之前其他“憶語體”作品是有所不同的。《影梅庵憶語》中冒襄始終將董小宛看作他的妾室,在回憶之始也只將其置于附屬地位,在冒襄心中無論是妻子,母親亦或是弟弟的地位都要優于董小宛,自身始終處于這一段關系的高位,直至最后董姬不離不棄直至逝世后才在他心中鑄成偉像。而《浮生六記》中沈復對妻子蕓娘雖愛重,但與蕓娘的故事僅是他人生經歷中的一部分,或者說只屬于《浮生》中的一個篇章。而《秋燈瑣憶》中蔣坦與秋芙原是青梅竹馬,年少情深,兩個家庭亦是門當戶對,他們之間的家庭地位亦是平等的,縱觀全文便可看到他們相知相守,相惜相依的過程,而作者始終以一個丈夫與愛人的眼光看待秋芙,二人之間的地位始終是平等與尊重的。
(二)敘事時空
《秋燈瑣憶》所選的敘述角度是以作者的回憶為主,而由于回憶的飄忽性與創作的間斷性,往往筆下出現的事件處于不同的時空,這些時空有的獨立成立,有的則交織著過去與現在兩種時空,同時蔣坦對于不同事件所傾注的感情也是不一樣的,因而使人感到了時空界限的模糊以及思想情感的跳躍。這些由瑣事構成的不同時空仿若一個個獨立的珠子,由作者對已經發生的事情以一條清晰的回憶線索所穿在了一起,形成了“長線串珠”的結構。
首先是蔣坦在《秋燈瑣憶》中并未直接描寫,但無時無刻都存在的一個當前的時空,全文中的敘述便是在這個時空中完成的,作者身處現在的時空,回憶過去與妻子相處的點點滴滴,并就事感慨。在這個時空中,作者是一個已經經歷所有事情,再回頭看的總結者,同時也是全文情感的締造者即采用了全知視角進行敘述。恰如楊義《中國敘事學》中所說:“結構之所以為結構,就在于它給人物故事以特定形式的時間和空間的安排,使各種敘事成分在某種秩序中獲得恰如其分的編排配置。因此,順序性要素是結構得以成形的要素。敘事結構順序之妙,在于它按照對世界的獨特理解,重新安排了現實世界中的時空順序,從而制造了敘事順序和現實順序的有意味的差異。”[3]61全文并未按照時間順序或敘事情節順序而對文中時空進行有序排列描繪,更多的是由散漫無序的時空一一羅列而出,這與回憶的飄忽無序是極其相似的,作者打亂了原本的現實順序,結合自身的回憶與經歷創造出了文本中的敘事順序。而由作者的回憶線索穿插起來的不同事件,又屬于不同的時空。它們或是新婚之夜兩人的對詩;或是二人同游葛林園時妻子發釵無意落水,或是二人秋時吟詠宋玉《九辯》的共情;或是二人冬日尋梅時蔣坦折一枝梅花簪于妻子發間。這些一個又一個的小時空無疑都充滿了溫存美好的氛圍,這也是能在作者記憶中長存的原因。
同時,這些時空也會存在古今交錯的現象,這往往是因為作者在歷經了一切的事情后,再以回憶視角敘述所經歷的事情之時,過去美好的事情最后走向不同的結局,與當時情境的對比不免值得嘆息。蔣坦在與秋芙尋梅登高之時回憶的景象為:“斜月曖空,遠水渺口,上下千里,一碧無際,相與登補梅亭,瀹茗夜談,意興彌逸。”而很快筆鋒一轉時空回到了現實的“今亭且傾圮,花木荒落,惟口娥有情,尚往來孤山林麓間耳。”[1]1527-1528二者一古一今,過去二人同游的盡興之至到如此的蕭索孤寂,空間交疊,兩相對比之中愈加凸顯當前時空的蕭索。在作者敘述秋芙因屋檐外“巢泥忽傾,墮雛于地”之時為燕子鑄新巢為舊時回憶,而該段敘述在斷尾話鋒一轉將時空放到了當前,并發出“今年燕子復來,故巢猶在,繞屋呢喃,殆猶憶去年護雛人耶?”[1]1528的感嘆。過去現實的時空兩相錯位,懷舊感傷之情溢于言表。
三、《秋燈瑣憶》的情節脈絡
(一)情節脈絡
全書由作者的回憶之線寫就日常瑣事,日常事件紛繁多樣,文章的敘述穿梭于現實與過去之間,時常顯現出一種人生夢幻虛浮,幻滅不可捉摸之情感,這得源于它跳躍的敘事,時空的錯位。作者在敘事舊日之歡的時候時常埋下許多伏筆,與未來慘淡幻滅交相呼應,讓人不勝唏噓。其中情節脈絡的跳躍性,時間的巨大跨度也使得敘述文本具有了縱橫的深度。
在蔣坦憶起自己教秋芙彈琴時,先是敘述了妻子彈琴“既起,指法漸疏,強為理習,乃與彈于夕陽紅半樓上。調弦既久,高不成音,再調則當五徽而絕。”的情境,作者的敘述到此轉折言樓下失火以至“煙霧迷空,窗紙欲黑”,最后嘆曰:“知猝斷之弦,其讖不遠,況五,火數也,應徽而絕,琴其語我乎?”[1]1519整個場景有彈琴為起,琴斷失火而落,最后發出“其讖不遠”的感慨也似乎預示了未來并不圓滿的結局。
同樣,作者由妻子喜愛繪畫牡丹到談及昔日與老友錢、費、嚴、焦等“品葉評花,彌日不倦”,對舊事的懷念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結局“既而錢去楊死,焦嚴諸人各歸故鄉。秋芙亦以鹽米事煩,棄置筆墨”的結局并不圓滿,當作者再執其妻子與眾人共同往日所繪制的牡丹畫扇之時,在贊嘆“精神意態,不減當年”之余也只剩下了“賓朋零落之感”[1]1520。過去的歡樂與如今的蕭索兩相對比,更突顯后來的孤寂。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全書的敘述中,時常將古人詩詞穿插于諸多日常場景之中,或是由眼前之景聯想到某一句詩,或是吟詠詩詞時景象不禁浮現眼前。據統計,全文所引用的詩詞之中,出現最多的當屬元稹的詩,而這些詩又基本皆為悼亡之作。誠如之前所言,文章有一條清晰的線索是作者身處的未來,而由回憶的筆觸,對過去時光的喟嘆都是我們能夠感受到在這條線索中的作者似乎充滿了賓朋散盡的蕭索,孑然一身的孤寂,追憶往事的迷惘。因而這些穿插的詩詞使得作者在敘述往事之時與未來的自己在情感上產生了呼應。
因而作者在回憶與友人暢飲時,呼酒久而不至,詢問妻子才得知床頭無錢,妻子“脫玉釧換酒,酒家不辨真贗,今付質庫,去市遠,故未至耳。”作者即誦元九“泥他沽酒拔金釵”詩,該句出自元稹《遣悲懷》其一,為其悼念妻子之詩,全詩追憶往日與妻子共患難的貧苦生活,對妻子在貧困中對自己的體貼關懷感到喟嘆不已。作者在引用該詩時,便是在經歷未來孤寂的結局之后,對往事的喟嘆,古今交錯之際也擁有一定的隱喻性。因而在這段敘述的末尾才會這樣寫道:“自此而后,蹤跡天涯,云萍聚散,余與秋芙亦以塵事相羈,不能屢為山澤游矣。”[1]1523
作者也才會在看到妻子梳頭時,不光想到當時“初日在梁,影照窗戶,盤盤膩云,光足鑒物”的溫情景象,同時也“因憶微之詩云:‘水晶簾底看梳頭’,古人當日,已先我消受眼福。”[1]1524在文中提及“水晶簾底看梳頭”句出自元稹《離思五首》中的第二首,為元稹悼亡之詩,該詩以桃花掩映的環境起筆,從自己讀書再轉到妻子梳妝,以樂景寫愛情,表達了對妻子的無限思念,以及對往事的悵惘。作者在回憶的敘述中引用該詩,其意味不言而明。
(二)重點情節的描述
作者敘述與妻子自青梅竹馬到結縭的過程也是該文的一個敘事的典型案例。先是開篇闡述了他與妻子兩家為表親,在婚前二人的關系是“繞床弄梅,兩無嫌猜”[1]1524,后回憶起除夕兩家長輩欲結親的情形,作者十分詳細的描寫了妻子秋芙和自己的著裝細節,為:“秋芙衣葵綠衣,余著銀紅繡袍,肩隨額齊,釵帽相傍。”[1]1524這里的細節描寫,正是側面寫出了作者對這段回憶的珍視與愛惜,只有十分重要的事,才會時隔多年仍舊細節都能歷歷在目。而后以時間為序,敘述了兩人往后十五年中的五次相遇,儼然一條有序向前進行的時間線。先是數月后的兩家人聚會,他與秋芙玩鬧中“戲解所系巾,曰:‘以此縛汝,看汝得歸去否?’”[1]1524。再次是數年后去拜見丈人家時“入門見青衣小鬟,擁一粲姝上車而去。俄聞屏間笑聲,乃知出者即為秋芙。”[1]1524在一年后,于熱鬧市間馬車上匆匆一瞥。緊接著下一年在丈人家中“庭遇秋芙,戴貂茸,立蜜梅花下。”只可惜“俄聞銀鉤一聲,無復鴻影。”[1]1524作者詳細的寫出數十年間數次相見的種種細節,層層遞進,雖無寫情之句,卻字里行間皆是情誼。尤其回憶二人結婚之日,通過妻子臉上的酒窩已經“非復舊時豐滿矣”這一細節,才恍然察覺歲月流逝,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之前數次相遇的時間流逝之感。再后來時間一轉到“今去結縭又復十載”[1]時,二人“皆鬢有霜色”[1]1524,時間再一次遞進,一條兩人自幼青梅到相伴一生的時間線便清晰地展現出來。該段的敘事仿若全文內容的一個小縮影,與開篇即從嫁娶那日開始敘述的婚姻生活不同,該段情節沒有婚后生活的半點影子,卻是后面二人幸福美滿生活的“前因”,至此則交代了二人的結緣與傾心,才有了后來婚后的琴瑟和鳴。在這樣的敘事手法的運用之下,交代清楚了全文的因果關系,更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與連貫性。
四、主要敘事手法
全文采用以事寫人的手法,通過對諸多事件的敘述,從而塑造了妻子秋芙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而秋芙的形象塑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作者于日常的點滴的敘事記錄中逐漸積累,通過不同的事件從她身上某一特質,再通過對相似事件重復描寫,層層累加,從而加深讀者對該特質的認知,達成了形象塑造的目的。
清人沈善寶在《名媛詩話》中評價到:“庚戌冬日,余返杭掃墓,關秋芙集諸閨友,宴余于巢園,出所著花蘞,集眾香詞,讀之 覺纏綿哀艷,音節凄清。秋芙年才二十余,豐神秀美,伉儷多才,性耽禪悅。人有金童玉女之目,家擅園林之勝,詩得唱和之樂,而清愁一縷縈繞筆端,殆天賦歟。”[5]729《杭州府志》中亦有對其相同的記載:“關锳,字秋芙,諸生蔣坦室,工詩善倚聲,兼長駢文。嘗學書于魏滋伯,學畫于楊渚白,學琴于李玉峰,鏡檻書林,文彩可想。”[6]2393
在蔣坦筆下的秋芙,是一個體貼的妻子。作者回憶起自己這六年之間的三次生病,秋芙都總是衣不解帶的照顧他,而秋芙體質柔弱,歷經勞瘁之后往往都會病倒,因而作者三次生病,秋芙亦是病了三次。通過妻子對自己三次生病的照顧,使得秋芙體貼細致的形象初具雛形,而作者三次生病,妻子亦是如此的細節描述,則加深妻子體貼細致的形象內涵。
同時蔣坦還通過重復描繪妻子與自己在日常生活極富情趣的小事,逐漸將秋芙極富生活情趣的特質呈現出來。春日桃花被風雨吹落地上之時,她會拾撿花瓣用以為她所吟的詩砌字。秋天月亮明亮時,她會“命雛鬟負琴,放舟兩湖荷芰之間”[1]1521,為丈夫鼓琴作《漢宮秋怨》,佳人景色兩相交融,是作者筆下“四山沉煙,星月在水,琤瑽雜鳴,不知天風聲環佩聲也”[1]1521的愜意舒懷。幾次事件的抒寫之中,將秋芙富有生活情趣的形象深刻呈現而出。
而在對于妻子才慧俱佳的描述中,蔣坦更是著墨良多。從開頭新婚之夜相互對詩,直至“而檐月曖斜,鄰鐘徐動,戶外小鬟已啁啁來促曉妝矣”[1]1520的描寫,將他們二人志趣相投的形象初次展現。而他們入寺聽禪,賞畫時,秋芙“題詩其上”[1]1523;家中長輩“晚年多疴”,二人結壇祝禱時,妻子作“駢儷疏文”[1]1526等諸事,都旨在加深秋芙才慧俱佳的形象。最后在作者回憶自己與妻子在秋日的詩句唱和,通過自己 所作的:“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也瀟瀟。”,以及妻子回復:“是君心緒太無聊,種了芭蕉,又怨芭蕉。”[1]1526兩句詞的比對,徹底坐實了妻子才慧俱佳的形象內涵。
可見全文通過樁樁件件具體事件的敘述,使妻子秋芙的形象不斷累加,從而塑造成為了讀者心中一個有趣的女性形象。故而林語堂先生將秋芙與《浮生六記》中沈復的妻子蕓娘形容為中國古代最可愛的女性。
余論
《秋燈瑣憶》通過對自己與妻子往事的抒寫,呈現了一對夫妻從年少情深到婚姻美滿的故事。其中敘事視角的采用與敘事時空的切換;情節脈絡的梳理與敘事手法的運用,是文學敘事日趨成熟的體現。同時,其以事情塑造人物的手法,塑造了妻子秋芙這一鮮明且具有特點的人物形象,使許多讀者在閱讀之余不禁與她產生共情。最后,作者以回憶敘事的角度,呈現了當時一個大時代背景下的家庭小天地,使人在時代的洪流中,聚焦于一個小的家庭視野,感受普通人生的趣味,而文章中模糊的時空與情感的跳躍更是充滿了人生虛茫,滄海一粟的無限感慨。其中敘事成分的運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憶語體敘事手法的類型,深化了憶語體敘事性研究的蘊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