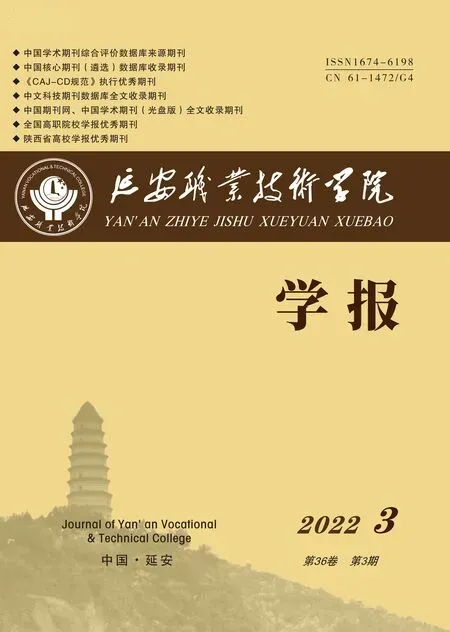走出女性的“荒原”:《美狄亞》與《呼嘯山莊》之“雙性同體”研究
侯夢汐
(安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引言
《美狄亞》是古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歐里庇得斯的經典戲劇,《呼嘯山莊》是十九世紀英國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說,被視為曠世奇書和世界文壇的“斯芬克斯”。兩部作品在文學時空中遙遙相隔,卻均為破解繚繞于荒原的斯芬克斯之謎而保持內在關聯。在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參照下,它們暗合的深層原因指涉了叛逆的女性主義傾向,即女性內心深處因受到社會與文化壓制而產生了憤懣與不滿、沖動與狂野的反叛欲望,跋涉于荒原的孤寂靈魂亟待尋求出路。這里的“荒原”既是相對于文明社會的蠻荒之地,又意味著女性身陷于第二性的性別困境。正如恩格斯指出:“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庭中也掌握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1]52“荒原”的貧瘠可追溯至文明時代的開端即女性地位的開始失落,將女性地位提升至和男性同等的位置,彼此勢均力敵,“荒原”的出口方能通向“雙性同體”的廣闊前景。
在女性主義理論的視域中,“雙性同體”由英國女性主義學者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最早闡釋,提倡的是一種理想的人格狀態,“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腦子里男性勝過女性,在女人的腦子里女性勝過男性。最正常,最適意的境況就是這兩個力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時候。……只有在這種融洽的時候,腦子才變得肥沃而能充分運用所有的官能。”[2]120-121在父權制的國家體系之中,男性群體以或顯或隱的方式壓榨女性權益,女性被壓抑的反抗情緒日益高漲,故而發出女性要與男性相比肩的合理訴求。伍爾夫認為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具備雙性的氣質,所持有的地位和權利均等。“雙性同體”理論在《美狄亞》與《呼嘯山莊》中印證的前提根源于兩性的不平等和對立,呈現出美狄亞和“瘋女人”希刺克厲夫共同的女性“他者”身份處境;構成“雙性同體”的過程中,為了爭取與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像男性一樣展現自己的行動力與創造力,美狄亞與凱瑟琳盡管各自下場和結局不同,卻均由異化自我回歸至主體性本我,經受了“殺死房間里的天使”與“表達自我”兩次冒險的考驗。身居荒原深處的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在女性意識與男權思想的現實博弈中以超性別的心態與立場構筑了兩性獨立完整的人格,提供了相較《美狄亞》更為開放交流而非對抗性的思路,對消解男權中心,實現現代社會雙性文化的和諧構建具有積極意義。
一、溯源:女性“他者”的身份處境
在創世紀之初男女兩性原本是平等的,母系崇拜源于對女性生育的神化與敬畏,伴隨著男性社會性別魅力的施展,父系氏族社會取而代之成為必然。“雙性同體”的提出首先追溯并揭秘了父系社會到父權社會轉變這段前史,女性遭受的歧視與壓迫是階級社會的縮影,女性實為整體中的他者,夫妻關系中的他者,性別中的他者。在女性主義的語境里,波伏娃的《第二性》一針見血地挑明女性的“他者”身份羈絆,二元對立的模式引導著男性將自己標榜為主體,將女性對象化并降格為滿足主體需求的客體——“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則是他者”[3]14,“他者”符號的指代預示著從屬和次要的位置。男性任意虛構了種種關于女性的神話和假定,在這種對于女性的“表彰加冕”和充斥著虛情假意的天使烏托邦中“并不是根據女人本身去解釋女人,而是把女人說成是相對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3]11。根深蒂固的歷史偏見同樣來源于女性對自己的認知,在獨自承受被男性所建構并打壓的苦楚與荒蕪之時,竟不假思索地領受命運的安排,不自覺地放棄了女性的立場,將男權觀念內化為對自身的準確表達,任由被玩味和評判,甚至在對于后代的憧憬中也刻上了男性希冀的印痕,以男性為仿效標準,性別間的權力關系仍作為強有力的壓抑機制在運作,因而女性意識與男權話語不謀而合。
在符合男性作家審美標準的文學寫作世界里,女性通常以“他者”的身份出現,自我的主體性和表達的話語權被剝奪,成為空洞的符號以填充男性的生命體驗、歷史指認與藝術想象。妖魔化女性是將女性他者化的常見策略。歐里庇得斯作為“第一個發現了女人”[4]280的劇作家,塑造了美狄亞這一最早的“惡女人”原型,而被當時很多人稱為患有“厭女癥”或“虐女癥”。戲劇以代言體形式再現美狄亞攜帶“他者”的身份跟隨伊阿宋從異鄉嫁到新的國度,卻遭遇了丈夫的無情背叛。保姆和歌隊輪流上場,講述這位棄婦已做好破釜沉舟的準備,暗自密謀復仇的計劃。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當走入婚姻生活的女性困囿于家庭的狹促空間,受到倫理道德的層層綁束時,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認同與逃離兩種境遇,認同即意味著在家庭中扮演完美妻子和母親的“他者”角色,服侍丈夫和照料孩子是必須履行的職責。美狄亞先前主動拋棄父權之家的舉動,使她注定要脫離夫權之家的庇蔭,懷著對懦弱的男性同盟者的強烈不滿,毅然做出決斷性的悲劇選擇,顛覆“他者”處境以實現身份的重建。
《呼嘯山莊》中幼年希刺克厲夫原是利物浦大街上的流浪兒,被老莊主收養指向了“他者”的身份,也因此受盡羞辱欺壓,與凱瑟琳彼此的愛戀成為唯一的慰藉。兄長辛德雷繼位后利用家庭統治者的優勢加深了橫亙于希刺克厲夫與常人間的鴻溝,不容許他僭越男性主體身份,加劇了他內心的怨恨。而地位的懸殊與相互的誤解使希刺克厲夫遭遇凱瑟琳的背叛,在崩潰與絕望的邊緣不得不出走謀生。穿行于敘事的迷宮,小說引入旁觀者角度,以后顧之勢在外來訪客洛克伍德和管家耐莉間反復切換,冷靜舒緩地回憶“異己”的過往存在和人事浮沉,如抽絲剝繭般逐漸揭開故事的謎團。經年之后希刺克厲夫榮歸故里,神秘陰郁的環境將“他者”命運建基于隱喻男權封閉統治的呼嘯山莊、象征自由的外界和隱喻世俗力量的畫眉山莊三方的強化對比中。置身石楠叢生、蒼莽無邊的荒原之上,干枯低矮的樅樹荊棘與暴雨狂風殊死搏斗,極致的愛恨交織成剛烈粗獷的超自然威力,造就了惡魔般的“瘋女人”。“瘋”向來是對女性正當訴求和真實內心的遮蔽手段,希刺克厲夫的外在形象與內在心理經由女性化渲染,凸顯出從隱忍到迸裂的“他者”力量——高舉復仇的屠刀,不僅掠奪辛德雷的財產,將辛德雷的兒子貶為自己的仆人,還誘騙林頓的妹妹伊莎貝拉結婚以報復凱瑟琳,摧枯拉朽般扭轉了生存局面。
二、考驗:自我異化到本我回歸
走出女性的“荒原”即探尋“雙性同體”的歷程,伍爾夫認為女性必須經歷的第一次冒險是“殺死房間里的天使”——當女性受制于潛意識中既定社會規范的囚籠并行將自覺臣服之際,要敢于抗拒這種無形干擾,破除男權魔咒,如若不將之“殺死”,便會被它“殺傷”成異化的自我。這里的“自我”代表著獨屬于個體的意志和特性,即“人的主體性”。弗洛姆在《孤獨的人:現代社會中的異化》中認為“異化”是一種病態的心理體驗,在異己力量的作用下,人類整體或個體喪失自我,喪失主體性,喪失精神自由,淪為物化人。從原始社會進化至文明社會,異化現象始終存在,凱瑟琳和美狄亞雖所處時代和最終下場不同,卻都曾身陷自我被男權社會異化的淵藪,淪為男性的財產和附屬品。女性必須經歷的第二次冒險為“表達自我”,從以間接的“她”到以直接的“我”來言說是一種坦蕩的性別確認,激活被男性目光長期遮蔽的女性的真實自我,這里的“自我”指女性內心的隱秘悸動和欲望體驗。親身經受冒險之旅的考驗,對深刻內在于其中的男權文化進行揭示、解構與重寫,關注女性的焦點也由“你是什么樣子”轉變為“你可以是什么樣子”。對照文本,一邊是戲劇的內聚焦視角中美狄亞的沉痛控訴,一邊是小說自如穿插宛若囈語的女性獨白,并以噩夢閃回里的凱瑟琳日記為補敘。兩部作品共同審察悲劇女性飽受重壓與戕害的精神層面,從心靈深處開掘出“不忠的美人”的生本能與死本能,召喚讀者在情節的波瀾迭起中與之強烈共情。
在文明最初所設立的秩序中,女性被拋入了邊緣地帶并被忽略,從邊緣實現突圍勢必要與處在中心地位的權威相抗衡,摘掉男性強加于女性身上的角色指稱。美狄亞是妻子,是母親,但首先是她自己。伴隨著女性意識發生的三個階段演變,她以扭曲自我的異化走向了與男權意識徹底決裂又回歸本我的道路。愛的力量促使美狄亞幫助伊阿宋盜取金羊毛,她的欲望與世俗的教條角力,不顧眾叛親離,這正是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征兆。婚后生活表面溫情脈脈,實則危機四伏,自我向著保守和庸俗發生異化,恪守婦德的美狄亞是溫柔賢惠的妻子和母親,她的價值以丈夫認定的標準來評判,曾經的瘋狂和不羈歸于沉寂,原本浮現的女性意識也于庸常的瑣事里逐漸消沉。伊阿宋的追權逐利和見異思遷使得美狄亞開始重新審視界定自己的婚姻,她深知這種幸福是不對勁的,力圖找回本我,獨立的血液在身體流淌,女性意識在復蘇重燃,甚至更加洶涌猛烈。她因絕望而失控,因失控而愈發清醒,決心揭露伊阿宋的薄情與忘恩負義,揭露男性霸權扭曲異化女性的真相,代表向來沉默溫順的女性群體發出怒吼:“在一切有理智、有靈性的生物當中,我們女人算是最不幸的。”“我寧愿提著盾牌打三次仗,也不愿生一次孩子。”[5]136美狄亞不惜以殺死親生兒子為代價向其父復仇,既割斷父子之間的血緣紐帶,沖擊由此確立的男性主導地位,又影射男性的“閹割焦慮”,加深他們被懲罰的威脅與萎靡不振的劇痛,極富戲劇張力。美狄亞積蓄女性智慧和勇氣贏得了兩性硝煙戰爭的勝利,被異化的邊緣女性消解了男性權威中心,以本我的嶄新面貌決絕地叛離男權體系的掌控,美狄亞的哀怨與狠毒、凄楚與瘋狂交織為女性的生命贊歌。
反觀至維多利亞社會,男女結合首先是財產、地位和家族的結合,婚姻的基礎是金錢而非真愛。時代政治的風云照不進女性的閨房,勢單力薄的未婚女孩們指望嫁給富有的男人來獲取幸福。凱瑟琳愛希刺克厲夫——孩子氣的、充滿欲望的本我,卻違背本我的意愿,受權利與地位的誘惑,嫁給了有錢有勢的林敦,沉溺于拜金主義風潮的幻夢,被馴化為畫眉山莊“屋子里的天使”,成為傳統意義上的“好女人”和父權制的犧牲品。希刺克厲夫的東山再起呼喚著凱瑟琳的精神轉變,她痛苦地反思自己的婚姻生活,愈發清醒迫切地尋找久已失落的主體性本我。她始終對希刺克厲夫抱有深刻的眷戀和不舍,訴說自己“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厲夫的悲痛”,“對林敦的愛像樹葉”,而“對希刺克厲夫的愛像巖石”[6]74-75。內心郁積的矛盾促使她在癲狂中只得走向死亡這條唯一的出路。死亡絕非陰陽兩隔,凱瑟琳克服了強大的異己阻力,以鬼魂的姿態回歸本我,長久地游蕩在高地上。
三、愿景:雙性融合的詩意棲居
美狄亞身處兩性尖銳對立的懸崖之巔,從女性意識出發思考女人的命運以及兩性差異,性格中原始的野性和反叛使她又表露出男性的膽識和謀略,這種剛柔并濟、陰陽和諧構成完整的“人的力量”,是“雙性同體”在歷史上的最初身影。“悲劇是以它向我們提出的挑戰而結束的”[7]201,究竟“是以兩性分立來對抗男權主義,號召婦女以女權主義抗爭的強行方式進入男性的社會呢?還是簡單套用生物進化論‘強者生存’的理論模式承認現狀呢?”[8]108-113《美狄亞》所留下的問題在《呼嘯山莊》中得到了回應。“雙性同體”的對話性呼應著由針鋒相對的尖銳抗衡走向開放包容和平等尊重的性別秩序的建立,男女之間秉持“平等”“大同”的思想,將心比心,彼此互補。無論是第一代人凱瑟琳和希刺克厲夫相伴而生的“雙性氣質”,還是小凱瑟琳和哈里頓作為第二代人培養的和諧統一的理想化人格,都表明對父權中心的反撥未必要以女性話語的徹底“翻盤”為目標,事實上任何一方的性別優勢躍居于另一方之上都不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有序與和諧發展。只有男女雙方都具備等同的力量,擁有平等的生存機會和價值權利,形成彼此牽制的性別中立結構,才是歷史進步性和社會積極意義之所在。
《呼嘯山莊》記錄了凱瑟琳的成長史,無論是向打算去利物浦的恩肖先生要一條馬鞭作禮物,還是大膽地反問恩肖先生:“你為什么不能永遠做一個好男人呢,父親?”[6]37言談舉止分明顯現著桀驁不馴的男性特征。凱瑟琳自幼就是性情粗野的姑娘,每日與希刺克厲夫嬉鬧于荒涼的曠野,像野草瘋長,邋遢隨性,狂放不羈,無所畏懼,“我就是希刺克厲夫!”的疾呼昭示出愛情的宣言。確如黑格爾所說:“由于忘我,愛情的主體不是為自己而生存和生活,不是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個人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時也只有在另一個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自己。”[9]327共生乃人世間的最高境界,凱瑟琳與希刺克厲夫的存在填補了對方于閉塞境地中的所有匱乏,他們同盟作戰,在靈魂和精神上保持高度統一性,一如英勇的驍將,一如揚起的馬鞭,將敵人的挑戰當作生命的饋贈,享受自由的至死不休。臨近結尾,小凱瑟琳與哈里頓的和睦相處讓希刺克厲夫仿佛重回自己與凱瑟琳的昔日光陰。呼嘯山莊和畫眉山莊的空間固然有限,但游弋于前世今生的如火激情與似水柔情卻亙古綿長,人性之善喚醒了缺席的良知,難以釋懷的痛苦被療愈,復仇的怨念瓦解為寬容與釋然,希刺克厲夫的雙性氣質在與歷史的和解中達到平衡。“看上去可能像恨的蔑視是由于愛(她與希刺克厲夫兩人像是同一個人)才成為可能的,而看上去可能像暴力的能量也是由于一個未被分裂的自我帶來的安寧(整一性)所導致的。”[10]388希刺克厲夫終以絕食的方式跨越生死結界,與凱瑟琳的鬼魂漫步荒原,返璞歸真,在精神還鄉中實現“雙性同體”的結合,兩性力量平等自由、有機和諧地共生,圓滿了人類自誕生之初最本真的圣潔狀態。
作品中的情愛傳奇與詩意愿景令人慨嘆的同時,其背后也映射了艾米莉·勃朗特飽受壓制的現實境遇和因之而生的獨特風格。伍爾夫的“雙性同體”富于追求人性美好完善的理想主義特色,既是創作的最佳狀態,為寫作主體超越性別困境提供了獨特的實踐途徑,也是消弭性別對立的有效方式,為世界文學的多音齊鳴創造了寶貴的機遇。女性作者在創作過程中走出個體的邊界,進入更多元的公共空間和更廣袤的思想領地,積極與自己頭腦中的男性因素進行對話,形成思想的對流,正所謂“女人像女人那樣寫,但是像一個忘記自己是女人的女人”[2]114。十九世紀中期正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女性作為“第二性”和“失語者”在男權社會里悄無聲息地時刻留心每一個有潛在危險的陷阱,沒有廣泛接觸外界的機會和獲得良好教育的權利。加之英國社會保守的傳統,剛剛興起的女性寫作在菲勒斯文化主導中普遍受到排斥,大多數女性作家在全景式男性視野的審視與框定之下,遵從第三者的角度描摹并過度理想化自己,溫和柔弱的筆觸極力迎合男性看客的興趣。而艾米莉超出了男性理解慣性和期待視野,居于約克郡偏僻荒野的她繼承了凱爾特人的細膩、真摯和浪漫,貧窮的生活和凄慘的童年又賦予了她怪戾脫俗、倔強不羈的性格。一股遒勁粗獷之氣在晦暗的天色中向上升騰,野蠻狂放的典型原始氛圍醞釀著壓抑至極端的爆發和狂風驟雨式的毀滅,鑄就了寓暴烈于不動聲色的哥特式奇觀。兩性氣質的敏感與陣痛演繹著孤魂野鬼的曠世奇戀,是并不突兀的兩種對立因素尋找吸引對方,最后達成和諧原則的體現,符合作者的自主意志,頗具夢魘般的感染與震撼。文學即人學,兩性之間的差異并不能抹殺兩性共同作為“人”的人性之美。只有合體的雙性,方能熔鑄為彼此立足于世的底氣和后盾,共同對抗僵化的罪惡根源,“勇敢地應對撒旦和它所有的軍隊”[6]320,最終獲得精神的解放。
正如柯勒律治所言,偉大的頭腦是雙性同體的。當時勃朗特三姐妹以中性的筆名發表小說,《呼嘯山莊》竟一度被看作是出自男性作家筆下,“在維多利亞小說的文雅背景之上,(它)莊嚴而與眾不同地矗立著,像一個一件消滅了的氏族留下的唯一的紀念碑”。[11]362正是兩性混淆的錯覺使得艾米莉在掌舵者皆為男性的文學滄海中泛起孤舟,傳神地塑造了立體豐滿、有血有肉的圓形人物,以獨立于主流價值觀的姿態和超越單一身份的立場顛覆了傳統的性別定位,在質疑和挑釁的陰霾之下破浪前行,讓雙性融合的自由之聲永久呼嘯于茫茫時空。
結語
當女性察覺到不對勁的時候,正是她成長的開始。在走出女性“荒原”的長途跋涉中,無論是對女性“他者”處境的呈現,還是獨立女性的艱難探索,最終指向并非傳統性別觀念的二元對立,而是達成雙向的交流與互動。面對社會輿論中性別問題一再被重新探討的當下,豐富多元的理解往往來自于兩性之間流動的對話,而非凝固的既往觀念。一方面,男女兩性是共生的,彼此的交流合作促進了生產生活的有序開展,人類作為物種得以健康可持續的綿延生息;另一方面,兩性之間的碰撞與磨合也是女性主義不斷完善其內涵,發揮更多社會作用的動力。以“雙性同體”的視角考察《美狄亞》與《呼嘯山莊》的異同,引出一條從女性的“荒原”中突圍而通向兩性和諧的美學建構之路。只有兩性在不斷博弈中進一步完善自我,尊重彼此,立足于人性提升完善的價值立場,保持寬容接受異己話語的開放態度,才能創造出構建和諧兩性關系的有利條件,在理論的啟發中汲取改變現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