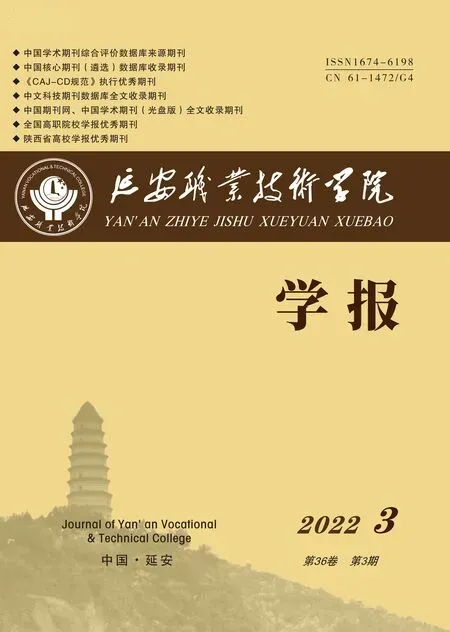子洲縣面花習俗考察
高錦花,郭咪咪,駱夢男
(延安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2018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振興鄉村戰略的二十字方針,內容之一便是“鄉風文明”。我們認為要想構建鄰里守望、誠信重禮、勤儉節約、孝悌友愛的文明鄉村,必須立足于鄉村本身的文化傳統。或者說,鄉村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最可利用并能直接實現轉化的就是民俗文化本身。以子洲面花習俗作為切入點,一方面可以讓人們了解該地的民俗文化的豐富多彩,另一方面則可以通過面花習俗進一步了解其在地方文化體系形成過程中所承擔的構建功能。
子洲縣位于陜北黃土高原腹地,榆林市南緣,1944年由綏德、米脂、橫山和清澗四縣劃撥成立,因紀念烈士李子洲而命名。明弘治本《延安郡志序》中“幅員北控,窮荒絕境,酋虜跳梁,輒烽火連夜”[1]10的記載大體就是當時陜北人文地理環境的真實寫照,同時書中這樣描述綏德、清澗、米脂和葭州一帶的風俗:“(綏德)地近邊垂,俗尚強悍”[1]203;“(清澗)民務農桑,士崇學問”[1]218;“(米脂)務本業,畜牧,尚勇少文”[1]230;“(葭州)人性勇直,好尚武力”[1]239。又清康熙本《延安府志·輿地志·風俗篇》說:“清澗、綏德、葭州、神木、府谷、吳堡近晉,習俗頗儉,且近邊,尚剛武”[2]18這些記載均說明由于自然環境惡劣,溝壑縱橫,土地貧瘠,加之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塑造了陜北人民注重實際、樂觀豁達、淳樸善良、好直尚勇的民族性格。
子洲縣南川一帶(從何家集鎮到淮寧灣鄉)有一種從清代道光年間就已流行的特殊民俗文化現象——捏面花,每逢寒食清明前后,這里家家戶戶都要捏面花,隨著社會發展,面花從清明節浸潤至人生禮儀和其他節日慶典中,構建起一套具有區域特色的符號文化體系,使這里百姓的日常生活被各種人生禮儀和節日儀式文化所包圍。由于在榆林十二縣中具有極強的文化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2012年子洲面花被選入榆林市非物質文化遺產,2013年又被選入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發展成為子洲的一張文化名片。具體在研究過程中,結合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口述史學等多個交叉學科理論,從文化視角去考察這一民俗事項所承載的內在文化價值與意義,在陜北鄉村文化建設中作拋磚引玉之論。
一、子洲面花習俗的歷史淵源
面花主要流行于我國長江以北以面食為主食的地區,其中陜西、山西、山東、河南、寧夏、甘肅等地最為流行。因各地風俗不同,就形成了“面花”、“花饃”、“面塑”、“禮饃”、“花餑餑”等不同叫法,陜北還有些縣域(如米脂)稱之為“燕燕”。至于其來源,在子洲縣有一則婦孺皆知的民間故事:相傳春秋戰國時期,晉獻公之子重耳因驪姬之亂逃往白狄國(今子洲縣懷寧河流域)避難,介子推作為隨行屬臣同重耳在此生活了十二年。重耳復國后,賞“從亡者”,遺漏了介子推,他遂攜母隱居綿山,文公求人心切,下令放火燒山,后在枯柳樹下發現介子推母子的尸體。民眾聽聞后悲痛不已,為緬懷介子推母子,便于清明前后捏制裝飾花鳥等物的“饅頭”(又名“子推饃”)。關于這一習俗,清道光本《清澗縣志·風俗篇》這樣記載:“三月清明,士女插栢葉于鬢,祭墓,戲鞦韆,作饅頭相饋,上綴各蟲鳥形,名為子推。謂晉文焚山,禽鳥爭救子推也。”[3]86文獻中所說點綴蟲鳥形的“饅頭”即今之面花,彼時當地便以此互贈親友。同書《地理志·山川》、《古跡》記載“縣北九十里有懷寧河”[3]58,有城一座,“宋慶歷時修,賜名懷寧,接橫山一帶”[3]71。這足以證明如今盛行于淮寧灣的面花至少在清代已相沿成俗。這是陜北地區面花源于介子推的最早記載和清明節前后民俗主要活動。
當然關于面花的真正起源,以及面花如何由早期單一的清明節祭品發展為其他節日禮儀用物,再發展到人生禮儀的象征物,因文獻缺載,已無從考究,但是可以通過它在社會事實中與何種習俗活動結合在一起,也可揣摩出一些端倪來。功能學派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在《文化論》一書中認為人類有許多物質技術、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都起源于“人類有機的需要”[4]26,他把這種文化不斷發展、社會持續進步的“需要”或推動力稱之為“文化手段迫力”[4]47,所以在他看來:“風俗——一種傳統力量而使社區分子遵守的標準化的行為方式——是能作用的或能發生功能的。”[4]33功能學派核心觀點認為人類諸多文化創造是出于其有機需要,只要我們按照文化要素分析方法,一一析出這些文化要素或文化事項在實際生活中發揮何種功能,與何種社會事實結合在一起,就能知道文化產生的根源,也能探究出文化發展演變的內在邏輯。我們知道,民間習俗的形成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歷史傳統,它傳承發展的動力恰恰源于其在民眾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由于面花具有溝通人際關系、構建禮儀秩序等特性,承載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歷史記憶,培養了人們內在的文化認同感、鄰里守望和互助合作的族群凝聚力,最后自覺形成鄉村道德倫理規范。
二、子洲面花與民俗文化生活互動
從現有資料和民俗活動來看,子洲面花不只作為祭品存在于民俗活動中,而且在一些人生重大禮儀、節日慶典中,均是不可或缺的道具或媒介物,甚至在一些廟會活動中也必不可少。接下來我們從人生禮儀和節日文化兩方面考察面花如何在鄉村社會構建起一個文化場域。
(一)人生儀禮
著名民俗學家鐘敬文說:“人生儀禮是指人在一生中幾個重要環節上所經過的具有一定儀式的行為過程。”[5]156具體包括誕生禮、婚禮和喪禮等,面花可以引導我們探討探尋民眾對生命過程和生命意義的認知和理解。
1.誕生禮
生命的孕育是這個世界上最值得謳歌的事情,新生命的誕生意味著新希望的到來,事關整個宗族(家族或社區)的發展。圍繞新生命的誕生,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著相同的習俗,即整個家族或社區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尤其是在非常重視血脈相續的中國,當一個嬰兒(特指男孩)呱呱墜地會被視為整個家族的頭等大事,必須舉行一系列的儀式活動以示慶賀,有些地方相應的祝福一直持續到孩子滿十二周歲為止。陜北地區,過去由于經濟文化落后,醫療衛生條件較差,嬰兒死亡率較高,所以當一個新生命誕生以后,他周圍便充滿了來自于親朋好友的各種祝福和保佑,直至其長大成人。若所生為女孩,慶賀儀式則相對簡化。
在子洲,生肖是伴隨孩子一生的吉祥物,并通過諧音或生肖本身的寓意而形成大量吉祥用語,如“猴寓侯”、“兔平安”、“馬成功”、“雞同吉”等。因此,在嬰兒誕生前,外祖母就要捏制具有祈福意義的生肖面花。滿月這天,外祖母和舅家等親戚都要送滿月面花前來慶賀,類別主要有魚饃、虎饃和兔饃,數量一般是十至十二個。面花個個形體飽滿,色彩亮麗。當地巧手婆姨薛冬梅①說:“孩子出生后送的面花越大越好,這是希望娃娃們長得大大的、壯壯的。”表達了人們對嬰兒生命力頑強、旺盛的祝福。
核心儀式如下:首先孩子母親將其抱放在炕中間,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孩子胸前系一把五色鎖線(象征陰陽五行),然后請家族中最為年長且最德高望重的女性長輩,將親戚們帶來的魚饃繞孩子放一圈。若是男孩,要在孩子旁邊放象征陽剛之氣的虎饃,寓虎頭虎腦、虎虎生氣;若是女兒,則放一圈代表陰柔機敏的兔饃,寓意將來像兔子一樣靈動可愛。孩子一周歲時,須過周晬。滿月時來過的親友們仍帶魚饃、兔饃前來祝賀,這種慶賀方式一直持續到孩子滿十二周歲為止。民間認為,孩子十二歲以后才“魂全”,此前父母十分注重保護孩子的元魂。十二也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年齡,類似于其他民族的成丁禮或成年禮,陜北地區孩子滿十二后便可解除一些禁忌。
2.婚禮
婚禮是誕生禮之后的又一大事。《禮記·昏義》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6]1416結婚不僅僅意味著成年,也意味著一個年輕人從此正式進入社會人際圈,成為社會正式成員,從此開始承擔撫育子女、奉養父母、養家糊口的各項責任,也要參與宗族或社區重大公共事務的商討和決策,履行修路、筑橋等義務勞動,必要時要有義務出資資助村社和宗族的發展。儒家強調一個人應具備的“修齊治平”的德行修養和治理家國的能力在這一刻起進入實踐層面。因此,婚禮就成為誕生禮后又一項重大禮儀,它既是身份轉變的象征,也是開啟人生新階段的轉折性標志,自然需要盛大的禮儀慶祝。這個過程離不開長輩們的主導,且一定會利用面花傳情達意,將男女青年一步一步順利導入角色。
按照子洲風俗,訂婚后首個清明節男女雙方需互贈面花作為定情信物。男方贈送女方一對蓮花魚兒,其造型為靈巧的魚兒上方馱著盛開的蓮花,寓意女子像蓮花般高潔,如魚兒般聰穎,這應該是陰陽相交、陽往而陰來的古老文化的物化表達②。有些村落送一對大抓髻饃饃③,當地有一句俗語:“抓髻扎起來,婆家不引來?”透露出女方待字閨中、男方急切希望盡快迎娶的心情;女方回贈男方一對大面老虎,象征男子陽剛、威猛、雄壯。
迎親當天有三個展示面花功能的儀節,頗耐人尋味。首先迎親隊伍給女方家帶來10 個長度約為20CM的喜饃,俗名“催妝饃饃”,意為感謝女方母親十月懷胎之辛勞。關于“催妝”習俗,唐人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記載北朝時已有此俗:“北朝婚禮……夫家領百余人挾車,俱呼曰:‘新娘催出來!’齊聲不絕,登車乃止,今之催妝是也。”[7]4直到現在,陜北人均把迎親當天夫家所帶之物稱為“催妝”,可見文化浸潤之深之廣。其次新娘迎娶回來與新郎進入洞房,之后男女雙方盤腿端坐在炕(床)上,由家中女性長輩圍繞二人放一圈俗稱“圍兒女饃饃”的面花,共由兩個大的子推饃和十二個點彩小白饃組成,兩個大的象征夫妻二人,分別裝飾許多同樣材質的小動物;十二個小白饃則寓兒女成群,繞膝承歡。然后夜晚就寢前,新郎母親扮演“送子娘娘”,用搟面杖戳開新房窗戶紙,往里扔2個白饃饃,此即“撂兒女饃饃”,新娘和新郎在屋里各接一個,祈愿新婚夫妻早生貴子。
喜事一過,這些面花及各式饃饃就可饋贈親朋好友。交感巫術理論認為,人只要接觸到某種具有特殊功能的吉祥物,便可擁有同樣的能力。親朋好友吃了這些“饃饃”不僅會沾染喜氣,而且也會具有相應的繁殖力,兒女成群。縱觀誕生禮和婚禮,正如已故歷史學家常金倉所言:“文化因子的聚合分散不僅可以造出錯綜復雜的文化,而且某些能量較大的因子很可能削弱和改變文化某方面的趨向……如果我們看看新幾內亞蒙杜古馬人——這也是一個父權制的部落,就會知道,僅僅因為那里盛行換親制度,就使他們特別重視多生女子,文化因子間的這種相互作用是不能忽略的。”[8]61-62如今子洲當地的婚禮儀式已刪繁就簡,但面花的媒介作用并沒有削弱,陜北其他各縣亦有相同儀式,只是數量、造型上略有差異。
3.喪禮
與人生禮儀相關的另一項重大禮儀就是喪禮。各民族和地區,針對喪禮有不同的儀節和民俗,祭奠用物也有所不同,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在陜北廣大地區,比較普遍的供奉給亡靈的最后獻物也是面花,子洲叫老獻,有的地方如米脂則叫大獻。活著的人通過最后的用物表達對死者的敬意,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生者與死者的正式“分隔”媒介物,其象征意義遠大于其實際價值。當然相較于前兩者,喪禮中的面花造型和顏色搭配更莊重素樸,數量也較少。而且喪禮所需面花亦須請當地面花藝人蒸制,主要有老獻和猴拜相兩種類型。
老獻,也稱老饃、大饃,通身為一個未經裝扮、施彩的圓形大饃。當地老人苗得庫④解釋:“這個大圓形象征混沌宇宙,意味著人從混沌出生,逝去后又回到混沌中去。”這種對宇宙奧秘和生命輪回的直觀體悟通過一個大饃來代替,寓示了生命從無到有、復歸于無的本原狀態,他們對生命過程的理解充滿了哲理,完全是中國傳統道家對生命直覺體悟的哲學觀念,不得不讓人贊嘆大道至簡的民間智慧。老獻使用數量因葬儀不同而不同。如果單埋,蒸半桌老獻,即六個;如果夫妻合葬,則蒸一桌老獻,即十二個。至于猴拜相面花,其造型為猴子坐于大象身上,雙手舉起向前叩拜,取諧音“封侯拜相”,寓意死者到了陰間以后也能封侯拜相,成就另一番功名。
由以上可知,圍繞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人生禮儀,反映了傳統農耕文明狀態下老百姓的生活生產習俗,其中滲透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些核心價值,如孝悌友愛、尊老愛幼、慎終追遠、團結互助等。此外,上述儀式巧妙地將傳統鄉村文明與現代文明完美結合起來,面花的捏制不僅融合了現代手工藝品的手法和技藝,還充分借鑒國內外鄉村文明的優秀成果,實現了鄉村文明的與時俱進和創造性轉化。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說:“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耕讀文明是我們的軟實力,要保留鄉村風貌,堅持傳承文化。”[9]總之,傳統中國社會秩序很大一部分是靠日常禮儀活動來鞏固和維持,而現代鄉村文明的建設除了依靠法治,另一方面在我們看來,還須借助鄉村固有的文化傳統來凝聚人心,進一步整合和提升傳統文化的功能與價值。
(二)節日慶典
節日是中國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載體,透過節日,不僅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物質文化的變遷,也可以看到人們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的變遷軌跡。下文主要通過元宵節、清明節和中元節三個節日考察子洲面花習俗的發展和演變。
1.元宵節
元宵節是中國傳統節日之一,也是一年中第一個滿月之夜,古稱“上元節”、“燈火節”,子洲人在這一天的慶祝活動有轉九曲、鬧秧歌、賞燈逛街等。同時為了祈求神靈福佑,家家戶戶都趕蒸十五面花,其中既有祭獻給天地神靈的大“棗山”,也有贈予親友的小棗山和面雞。
所謂“棗山”,主要是由面和紅棗兩類食材做成“山”狀面花。因是獻神之物,當地巧手婆姨周彩英⑤說:“棗山捏得越大越好,這代表著自己對天地神靈的敬意多,家里的發展也就越紅火。”面必須提前一晚發酵好,藝師先取一部分面團搟成圓形薄餅作底盤,然后取小塊面團搓成多個長條,捏制成回云紋,并在云紋間放大紅棗,這樣一層一層由大到小堆成小山一樣的形狀,通常為五層。 捏制好后的棗山放入一口大鍋中蒸熟,出鍋后由一家之主恭敬擺放在窯洞內或房間的天地神位,全家人都要祭拜,祈求平安順遂。此外,元宵節期間還捏制許多小棗山和面雞以贈親友,由于“雞”和“吉”諧音,寄托捏制者祈望新的一年中親友們身體健康、吉祥如意。所以面花在這一場合不僅成為溝通人與神的媒介,也成為人際關系的黏合劑,培養了人們的文化認同感。
2.清明節
清明節作為中國傳統四大節日之一,在子洲縣南川形成了豐富的民俗文化,這一天也被確定為“面花節”,尤其2013年面花被列為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后,每年都要舉行盛大的活動進行慶祝,屆時媒體記者、地方政府官員都要出席,其影響力和傳播力都遠超附近縣鄉(如米脂和綏德)。文化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經歷文化的聚合分散以后,有些文化因素得到發展并逐漸成為特色鮮明的文化特質,有些文化因素因此而消失,民俗文化尤其如此。
子洲縣南川清明習俗捏面花活動與紀念介子推“割股奉君”傳說有關,人們每逢清明節便捏制“子推饃”進行祭拜。面花節確定以后,面花遂成為子洲新農村文化與文明建設的主要表征。其造型、食材及制作步驟都與“棗山”類似,但顏色更加絢麗奪目,形狀更大,裝飾更加豐富多樣,底盤面團超大,上面盤繞著具有層次感的三圈面條狀裝飾,每圈面條上歇息著眾多活靈活現、形象逼真、施以各色的燕燕雀雀,再以紅棗點綴其間。當心靈手巧的子洲人將面花這一藝術品展現在公眾視野時,也展示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理。隨著民俗文化的發展變遷,民間上墳祭祖,除了擺上象征葷食的豬頭饃和子推饃,還要帶時令新鮮果蔬酒菜。在子洲南川老君殿鎮、何家集鎮一帶,為了攘除不吉、驅除邪氣,清明時還為家人捏面花,為男孩捏制小老虎面花和燕燕雀雀面花;為女孩捏制“小抓髻饃饃”和小花籃面花;為從事耕作不輟的勞動人民捏“大燕背小燕”面花。
整體上北方地區清明節前捏燕燕的民俗活動可以上溯到宋代,《東京夢華錄》說:“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面造棗旗飛燕,柳條串之,插于門楣,謂之子推燕。”[10]129宋代“子推燕”的大小形狀現已無法考證,但我們看到當一種變動不居的文化現象一旦被社會民眾普遍接受,節日文化標志物遂具象化,形成持久而穩定的民族風俗習慣。此外《榆林府志》還記載過西川一帶民眾佩戴柏樹葉趨吉的習俗:“‘清明’,士女插柳毛(白柳芽),柏葉于鬢。”[11]96總之,清明節的各種祭掃文化將活著的和死去的人用共同的文化聯系在了一個共同體中。
3.中元節
農歷七月十五日,道教稱為“中元節”,佛教稱為“盂蘭盆節”,民間稱為“鬼節”。雖難與元宵、清明等節日比肩,但陜北多地照樣將之過得隆重紅火。這一天人們會用新谷做成祭品酬謝先祖,以及各路風師、雨師和雷神等自然神,也包括孤魂野鬼,以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子洲地處陜北腹地,常年干燥少雨,只適合旱作作物生長,產量極低。每逢七月十五日,諸多作物進入成熟期,風調雨順才能保證最后的豐收,善良的子洲人便會通過虔誠儀式表達對天道自然和各路神鬼的敬畏之心,獲其福佑。首先是祭祀谷神和風雨等自然神,屆時農家巧手媳婦用新麥蒸制十二個大面卷,備好香火、黃紙、白紙和酒水,由家中老農帶去田間祭祀。老農將所帶黃、白色紙剪為長條在莊稼根部焚燒,再將酒水灑于田間,焚香插于地中,磕頭祭拜。然后把大面卷掰成小塊分成幾部分,一部分撒向四方,恭請眾神享用,民間謂之“潑散”。其余一部分用來獻祭祖先,方式就是要在經過精心挑選、長勢茁壯的莊稼周圍撒一些,報答他們;一部分隨意撒在外圍,供孤魂野鬼取食,希冀他們毋行搗亂。光緒版《綏德州志》這樣記載這一習俗的:“至‘中元節’,家家皆詣先塋燒紙錢,秋露既零,故祭祖焉。農家晨興,向田間擇禾之長茂者,以五色紙旗掛之,曰‘田幡’。”[11]79只不過現代人用黃白紙取代了明清時的五色紙旗。但當地老農加紅高⑥說:“年輕人都不這么講究了,過去老一輩的人種莊稼時,收成不好的時候才這么做。”
而陜北其他縣域,如與子洲毗鄰的米脂縣高西溝村在這一天則舉行廟會活動,或其他文藝形式如唱戲、說書、扭秧歌等進行慶賀,也有希望家中生意順利或家人生病痊愈而給神許過愿的人家,他們會擺“花貢”酬謝神靈保佑。“花貢”就是各種式樣的面花,數量多寡,造型大小不限,講究的是虔誠。當地的面花傳承人也會通過面花比賽向人們展示技法的嫻熟和技藝的高超,造型別致與花樣翻新的將會受到一定的表彰。所以這里的人們已經把傳統節日變成了一場藝術盛宴,反映了新時代下民眾非凡的藝術想象力和富足和樂的精神面貌。而中元節的源起,應該是中國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將傳統“忠孝”觀念由人道擴展到了天道,構建起人-鬼-神-自然和諧相處的“天人合一”精神世界,將個人納入到祖先與后代以及與神靈為一體的文化體系中,用費孝通先生話說,就是“他們用祖宗和子孫的世代相傳、香火不斷的那種獨特的人生觀為信仰,代替了宗教”。[12]233
綜上可知,節日的最大功能除了娛樂,更重要的是在民俗活動中起到對鄉民價值觀和文化觀的整合與認同,人民生活在一個具有共同祖先或神靈的庇護、擁有共同歷史記憶的社區或村落中,而面花成為勾起人們共同記憶進而產生濃厚親情的一個具象代表。
三、以面花為媒介的鄉村文化體系的構建
通過對子洲面花起源及使用習俗的考察,我們發現該地面花文化已將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精神與當地人們的思想觀念與信仰淬煉為一體,構建起一套以面花為媒介的文化符號體系,維系著人際秩序。它既包括人與神之間的交往,也包括人與鬼魂之間、人與祖先之間,以及晚輩與長輩老人之間的交往。這種交往背后有著鮮明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所崇尚的“施報”特色,即《禮記》所說:“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6]11費孝通先生說:“人的語言、人的行為模式、人的身份等,不是哪一個人創造出來的,而是積在社會里的個人創造,成為社會共同的‘遺產’,是文化的積累。”[13]82-83所以,鄉村文化建設和加強不能單純依靠經濟,重點還得要有一套文化體系和理念。總結起來,有如下方面:
首先是溝通人際關系。凡生命個體都有生老病死,圍繞這個過程,人類社會絕大多數民族都被納入到一個由禮儀生活編織起來的人際網絡之中。在子洲縣這個人際網絡之中,有一條核心主線不容忽視,人們會普遍遵循一種互惠互利原則進行來往。于是在一個世世代代生活共同體中形成贈予-收受-回贈無限循環的人際圈子,老人贈予嬰孩,大人贈予兒童,希望孩子們一生平安順遂,晚輩希望長輩健康長壽,頤養天年;生者送走死者,希望得到死者護佑。然后再將小范圍的家族、宗族、社區的互惠擴大到某個集團、某個群體,某個地區,甚至將這種關系延伸到人與神、祖先和鬼魂之間,這種互惠原則在人類學家利奇看來,“獻祭是人們給神敬獻禮物、貢金或罰金,借以禳除不祥事端,獲得神的福佑的過程。獻祭儀式是互報原則的表現,人給神以禮物,神就得回贈人以好處。通過獻祭儀式,獻祭者在神界與人界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梁,神的能力通過橋梁能夠通達到獻祭者本人。”[14]83此外,研究云南芒市一個傣族村寨的儀式生活專家褚建芳關于清明節上墳儀式(傣語謂“恨隆”)有這樣一段論述:“在這個儀式中,人與人之間、人與自己的祖先之間以及人與野鬼之間,分別發生了不同性質的交換行為。在人與人之間,親屬關系的紐帶把不同家庭的個人聯系在一起,參加儀式和聚餐的各個家戶都帶來一些大米,作為自己的飯費。在人與自己的祖先之間,人們燃放鞭炮,向祖先供獻物品,并跪拜行禮,祈求祖先給予福佑和庇護。在人與野鬼之間,人們施舍給他們一些用生竹葉包好的米飯團,并口頭安撫他們,以免他們因沒有吃的而來搶自己祖先的飯菜。”[15]308對比發現,傣族與子洲縣在文化觀念上很相似,二者具有的共同文化觀念充分說明,在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上,正是相似的文化把各族人民聯結為一個休戚相關的民族共同體。
其次構建起禮儀主導的秩序世界。考察人類社會秩序的構建,至今已有多種類型,有通過法律和規章制度構建起法律至上的早期法治國家,有通過宗教信仰原則構建起神學至上的政教合一國家,中國社會則恰恰構建起禮儀文化特別發達的禮治國家。常金倉先生在研究中國本土文化類型的時候這樣說:“某個文化類型……對于每一代人來說,他們考慮的僅僅是采用什么樣的方法對付眼前面臨的生活問題,而毫不計及采取某種措施對以后的文化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在他們應付生活問題的種種措施中,有些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或者干脆因為時代相傳的習慣,于是在該文化系統中,這些因素得到了優先的發展,從而形成了文化要素發展的不平衡,哪些優先發展起來的因素形成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并常常改變了其他因素的品質,文化類型便漸漸顯示了出來。”[16]中國自古以來,很多生活場景都是通過禮儀活動主導,從而成為中國文化類型形成的關鍵性因子,中國也被稱之為“禮儀之邦”。因而我們看到,中國雖由眾多不同民族構成,但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生活在同質的儀式性生活之中,無論是人生禮儀,還是日常性的節日生活。這些禮儀生活,具有超強的約束力。所以褚建芳說:“這種結構和秩序是以神圣性為特征的,不同神圣等級之間取送往還的施報原則構成了這種結構與秩序的基本特征和動力機制。”[15]314這當中“取送往還”的東西在子洲日常生活中就是面花。我們看到,面花除了食用功能,還有觀賞價值,最關鍵它還是人們生活方式的體現。所以常金倉在《中國古代的禮品交換與商品交換》一文中總結:“禮品交換……它使我們領悟到一個民族商品經濟是否發達不僅僅是個生產力高低、剩余產品是否豐富的問題,它還與該民族的生活方式或文化類型具有密切的關系。”[16]356所以人們更看重的是附著于面花之上的情感溝通價值,而非面花本身,所以常金倉先生又說:“循環往復的禮物饋贈是靠良好的道德維持的,如果某人不守社會公德,那么就會遭到輿論的譴責而陷于孤立,甚至受到嚴厲懲罰。所以道德既是禮物饋贈的保障又是它的產物。”[16]364當代民俗學家蕭放說:“禮儀實踐與民間信仰、地方傳統糅合在一起,共同構建了基層社會的禮俗秩序,有著高度的社會治理價值”,“是踐之于身的行為規范,也是約之于心的道德規范”。[17]83-92
再次具有文化認同功能。所謂認同,其實就是一種心靈的歸屬感。在一些民俗學者和人類學者看來,類似于面花這些地域特征突出的文化現象具有很強的文化認同價值,“民俗是文化共同體建立的基礎,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其中民俗記憶資源的多樣性、多層次性構成認同的不同形態和不同層次。”[18]90-97文化認同,本質是價值認同,對于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們來說,由于擁有共同文化傳統而產生某種歸屬感,人們遵循集體認可的習慣勢力,不遵守者會被視作離經叛道,進而受到某種來自于習慣與習俗的譴責,獲得了日常生活的意義。人生活在這個集體中,就必須接受一套先于他存在的文化體系。也有民俗學者將之稱為“民俗認同”,即“以民俗為核心來構建和與維系多重認同并由此傳承傳統的精神意識與日常行為。因此,關注民俗認同就是在研究認同的構建和民俗的傳承進程中,以民俗傳統本身為主線,記錄和分析一個傳統事項的傳承與演變機制,以及該傳統如何與其他傳統互動而創造新傳統。”其核心是“共享的民俗”,本質上是一個群體所共享的“實踐的民俗”。[19]9-17所以面花所具有的文化認同功能是顯而易見的,圍繞它所構建起來的鄉村文化文明體系,就是當下子洲淮寧河一帶人們的日常,這也是鄉風文明的一部分,即在繼承和弘揚鄉村原有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建設以文化為主導的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生態文明社會。
總之,由于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某種意義上,鄉村社會也是維系和傳承歷史積淀下來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和根本,而民俗文化則是鄉村社會的核心文化,這就決定了鄉風文明建設中以民俗文化鑄魂的重要性。被列入陜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子洲面花以及與此相關的民俗,不僅折射了鄉村文化和文明中蘊含的形神兼備、情景交融的美學追求,也反映了自然經濟生產狀態下人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觀念,更彰顯了以子洲為代表的陜北人民在世世代代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斗爭過程中所形成的樂觀豁達的奮斗精神。當然,我們必須強調并指出,民俗固然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經驗累積和文化傳承,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但民俗中仍然包含一些已經不適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糟粕性的內容,對此要持批判性態度,優良習俗要繼承,陳規陋俗要揚棄,這既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要求,也理應屬于鄉村振興戰略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注釋:
①薛冬梅:女,43歲,子洲縣老君殿鎮人,高中文化,非遺代表,2020年10月10日訪談。
②陰陽相交思想觀念來源:鄭玄在解釋《禮記·昏義》時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第1416頁)蓮花魚是藝術表達形式,其中“蓮花”象征女子,屬陰,“魚兒”象征男子,屬陽。這與中國自古以來的陰陽交感的哲學思想完全吻合。按照靳之林先生研究,他認為民間有許多這樣的藝術作品都指向這一哲學基礎,如“魚戲蓮”“老虎吃南瓜”“獅子滾繡球”“猴吃桃”“老鼠吃白菜”“金雞探蓮花”等。(靳之林《中國民間藝術的哲學基礎》,《美術研究》,1988年第4期。)
③抓髻娃娃是陜北剪紙中最經典的藝術素材之一,造型多種多樣。據靳之林先生考察,抓髻娃娃典型形象是頭梳雙髻(雞),雙手舉雞,肩上雙雞,襟上雙雞,膝上雙雞,腳上雙雞,渾身上下左右都是雞。雞屬陽,抓髻娃娃象征陰陽相合的生命守護神和繁衍之神,寓意多子多孫、子孫綿延。他提出這一觀點之后,學術界所謂生殖崇拜、巫術崇拜等說法,是對靳之林先生理論的進一步闡發。面花中抓髻娃娃的藝術塑造并不多見,子洲縣在男女訂婚時送抓髻娃娃,其文化內涵我們從剪紙藝術可以推斷出二者具有相同的生育文化的哲學思想。而遍布全國各地的抓髻娃娃文化現象,詮釋了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已存在的重視生命、繁衍之神的哲學思想。(靳之林《中國民間藝術的哲學基礎》,《美術研究》,1988年第4期。)
④苗得庫:男,73歲,子洲縣老君殿鎮人,小學文化,非遺代表,2020年10月13日訪談。
⑤周彩英:女,50歲,子洲縣周家儉人,初中文化,非遺代表,2020年10月12日訪談。
⑥加紅高:男,81 歲,子洲縣老君殿鎮人,文盲,非遺代表,2020年10月13日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