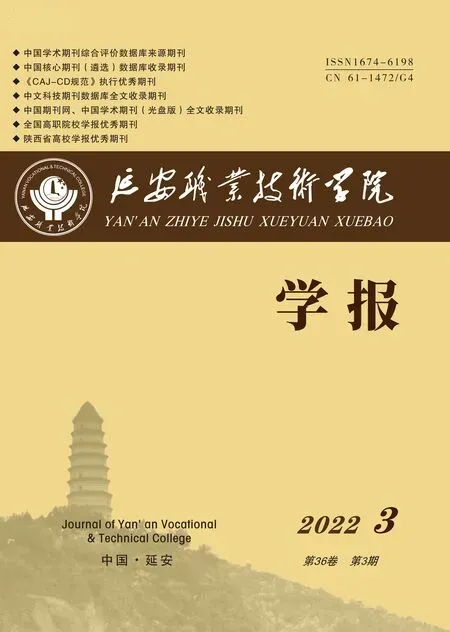淺析陳彥《主角》中的詈語
汪東鋒,劉雨涵
(延安大學 文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詈語,即粗野的罵人話。《說文》中指出:“詈,罵也。從網(wǎng)從言,網(wǎng)罪人會意。”朱俊生在《說文通訓定聲》中解釋道“按,言之觸罪網(wǎng)者也。”不難看出,詈語是通過語言來使對方反感、憤怒、進而達到“罪人”的目的。雖然詈語在日常生活中出現(xiàn)的頻率極高,是人們慣常使用的“工具”,但卻不為主流社會所接受,因其內(nèi)容及形式的特殊性,往往會在正常的語言教學、學術研究中被刻意忽視。而事實上,作為和人們生活緊密相連的詈詞詈語,最能真實直觀地呈現(xiàn)語言背后的文化傳統(tǒng)及社會心理。有很多作家,以使用白話性的詈語為刻畫人物和描繪社會萬象的“利器”,使得文學作品更加“接地氣”,更具人情味兒。陜西籍作家陳彥所寫的《主角》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作為一種語言現(xiàn)象,詈語是音義結合體,以詞,或詞組,或句子的形式呈現(xiàn)。對于詈語研究,目前涉及到的領域包括詈語的本體性研究、語用價值研究、文化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角度的研究等等。本文從詈語語義分類、詈語中蘊含的民俗文化、詈語的功能三個角度分析陳彥的《主角》中詈語的運用。
一、《主角》中的詈語語義類型
詈語又叫罵詈語,由罵意和罵語兩個部分構成,罵意體現(xiàn)的是罵詈者的情緒和情感,罵語是用于罵詈的語言材料。根據(jù)詈語的語義不同,《主角》中的詈語大致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與牲畜、無生命有關的詈語
這一類的詈語是將人和非人界限錯置,將人比作牲畜,降低了他人的人格,將被罵者的某種低劣的品性或品格與動物自身存在的劣根性相聯(lián)系起來,意在指出他人與牲畜“別無二樣”,以達到發(fā)泄憤怒或不滿的目的。如在《主角》中,有這樣的說法:
2.高五福說:“狗賊心還大得很,縣里都看不上了。”[2]477
另外,在作品中,還有一類是以“貨”為詞綴構成的詈語,例如:
3.……他叼著牙刷對胡彩香說:“看你個二蛋貨!”[2]55
4.另一個也不蹲了……“看把你個碎貨能的些。”[2]13
5.“咋不讓人家法院一槍打死算了呢,這個得倒頭瘟病的貨呦。”[2]105
將人比作“貨”,也還是將其劃作非人之類,不屬于人屬的“東西”。實際上是對對方智力、人格的貶低。但“貨”類的詈詞在陜西方言中并不都是用于發(fā)泄不良情緒之用,有很多也用來表示對人不爭氣的惋惜、或表達長輩對晚輩的疼惜之義,比如例⑤,胡秀英面對弟弟因圖一時口實之快被有心人陷害而深陷入獄的遭遇,不由痛罵出“倒頭瘟病的貨”,這其中更多的是對其弟胡三元遭遇的痛惜,而不僅僅是單純的咒死義。由此可見,方言中諸多的詈語現(xiàn)如今詈罵的濃厚色彩已經(jīng)開始慢慢淡化乃至褪色。
(二)與性有關的詈語
從古至今,“性”一直是一個隱晦而神秘的話題,“隱晦”在于它有諸多不可置之于口、公之于眾的內(nèi)容和色彩,而因其時常被人故意隱去不提,故而像一層面紗一樣具有了隔膜一般的神秘感,成為了約定俗成的禁忌。而和“性”有關的詞匯出現(xiàn)在詈語中則表現(xiàn)出人們違反禁忌,給他人施加來自社會的心理壓力,對其造成不快和傷害。和“性”有關的詈語在作品中主要體現(xiàn)在性器官和性行為方面,比如:
6.剛一走進幕簾,立馬猴下身子,就罵將起來:“賊他媽,臺上熱得兩個蛋都快焐熟了。”[2]15
7.“沒本事,混在這行球不頂。”[2]25
(三)與污物有關的詈語
在宋元時期之前,文學作品中與污物有關的詈語還極少,不足加以分類闡明,從宋代開始,由于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勾欄瓦肆成為繁華之所,俗文學開始拔地而起,此類作品大多反映了平頭百姓的日常生活,為了更好地迎合流連此地的熟客,自然不免將粗俗之語越來越多的帶入到作品當中,也就從此開始,詈語開始充滿了市井氣,變得愈發(fā)低俗化。諸如“屄、屁、屎”類的詞語,在明清之際,更是在眾多世俗小說中出現(xiàn),如《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等。這些詈詞經(jīng)歷了百年的變遷,其罵意依然保留至今,并且在方言小說中大放光彩。在《主角》中,如:
8.廖師就罵開了:“放他娘的豬屁,誰說菜難吃了?”[2]113
9.“五、讓他把屄嘴夾緊些。”[2]220
10.姥姥就罵他:“買你娘的屄②,又買摩托呢。……”[2]]781
二、《主角》中詈語蘊涵的文化
《主角》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亮點便是文中大量的陜西方言的運用。方言作為地方文化的載體,以語言為媒介展現(xiàn)出獨特的風土人情和地域色彩。通過對方言的分析,不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地域文化對其形成的影響,更可以從語言的角度揭示文化流變的原因和趨向。由此可見,方言與地域文化是互為表里的。在本書中,作家通過陜西方言向人們呈現(xiàn)出陜西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利用陜西方言塑造了一個又一個鮮活且飽滿的人物形象。在當下的時代背景中“活著”的每一個小人物,從出生之日起便與浸潤了幾代人的文化共生共存,而他們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和“侵蝕”。“詈語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現(xiàn)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4]詈語是最能直接且露骨地呈現(xiàn)一個地方地域文化“俗”的一面,以下主要從三個方面闡述書中涉及到的民俗文化。
(一)詈語反映了男尊女卑的倫理文化
男尊女卑的觀念古之已有,從夏朝開始,隨著男權社會的完全確立,“家天下”的禪位模式徹底顛覆了母系時代。母系社會的日益衰亡,顯而易見的便是女性地位的降低,再加之有小農(nóng)經(jīng)濟這一經(jīng)濟基礎的加持,女性由于自身條件的不足自然而然便成為了家庭和社會的“弱勢群體”。自周朝宗法社會成為體系之后,男尊女卑、男主女從便成為了主流社會的倫理規(guī)范。經(jīng)濟地位的缺失以及封建思想的禁錮,使得女性自身也逐漸承認并主動成為這一思想觀念延續(xù)的“幫兇”。
在陜西方言的詈語中,涉及女性歧視的詞匯有很多,大多和女性長輩有關,如,“賊你媽、賊他媽、操你姥姥”“日你媽”等,也有一些意指女性地位卑賤,瞧不起對方的詈語,如“碎蹄子”“碎婊子”“碎貨”。而且從各類詈語類型來看,相對于男性相關的詈語數(shù)量來說,貶損女性更是占據(jù)上風。從語言表征上來看,陜西地區(qū)男權文化占據(jù)主導地位,女性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極為低下。
(二)詈語折射出陜西的禁忌文化
禁忌語中所蘊含的,是人們出于趨吉避兇的心理而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的規(guī)定性的禁忌文化。這種禁忌性文化體現(xiàn)出人們遵從社會心理和道德的制約,自覺地保持和維護這種帶給社會團體以穩(wěn)定和平衡的規(guī)范。若沖破規(guī)范,則面對的是整個社會群體的集體性施壓,來自心理和精神雙重層面的。過去在陜西,普通百姓的生活也非常困苦,由此導致突破禁忌的文化大行其道,人們常常使用“性”詈語傾瀉了對生活中各種不滿或壓抑的憤怒情緒。《主角》中就有很多“性”詈語,比如“日他媽、屄嘴、皮膪膪貨”,多是與男性生殖器官或與性關系有聯(lián)系的詞語。“性”自始至終都是一個禁忌性的話題,而它在詈語中應用,表明人們以語言為出口進行不良情緒的傾倒和發(fā)泄,實現(xiàn)心理的平衡和欲望的滿足。
(三)詈語旁涉陜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文化
陜西地區(qū)的渭河兩岸有“八百里秦川”的美稱,這是由于經(jīng)過數(shù)千年歲月的累積而形成的肥沃之地。由于土地肥沃、雨水量充足、氣候宜人溫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自然就成了陜西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業(yè)”。生活在陜西地區(qū)的人們世世代代以農(nóng)耕為生,有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生活的動物詞語自然也成為了當?shù)匕傩盏娜粘T掝},甚至變成了陜西方言詈語,其中以牲畜家禽類詈語數(shù)量為多。《主角》中出現(xiàn)的這方面的詈語不多,僅有“牛“”驢日“”狗日“”雞賊”等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
三、《主角》中詈語的功能
(一)具有交際功能
詈語在交際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攻擊”,通過辱罵、訓斥等形式將憤怒的情緒傾瀉出來。而在小說中,很多詈罵情境都是將攻擊與發(fā)泄結合在一起。比如:
舅把牙一咬:“嚼他娘的牙幫骨。不收我姐的娃,你叫他試試。”……“開他媽的個癟葫蘆子!”[2]9
“放心,那些給哈慫領導獻媚的,我都有辦法收拾。”舅把話題一轉,說,“你可得把這娃的事當事。”[2]10
在以上示例可以看出,詈罵的攻擊作用并不是很強烈,更多的是和不滿情緒的發(fā)泄結合在一起。
除了攻擊和發(fā)泄情緒之外,詈語還有諷刺的功能。“罵詈語的諷刺功能就是用罵詈語來嘲笑諷刺對方,這樣的罵詈含蓄、委婉、隱晦,被罵詈的對象要能領會其意旨才能使其產(chǎn)生嘲諷功能,達到諷刺的目的。這樣的罵詈語通常是罵詈者把握了對方心理,罵詈雙方相互熟悉才能出現(xiàn)。”如,小說中,胡彩香給憶秦娥換新買的衣服,因不滿胡三元給憶秦娥的穿著打扮,而說道:“看你那大‘搖婆子’鞋。也真是的,你舅個死嗇皮,連鞋都舍不得給外甥女買一雙。”[2]20這段話看似是胡彩香在嘲諷胡三元眼光落后,土氣,實則其中含有一種“打情罵俏”的情感,借詈罵的形式表達了對“她舅”這個人過于死摳的無奈。另外,在小說中,出現(xiàn)更多的是作者對角色的“嘲諷”,從第三方的角度去審視這個角色,而非產(chǎn)生于人物對話的碰撞,比如,在描寫憶秦娥參加縣劇團的招生考試中,作者寫道“也不知咋的,她的腿也不抖了,心也不亂跳了,就瓜不唧唧地戳上了舞臺。”[2]21“瓜”本是形容人呆傻,但在這句描述中,除了體現(xiàn)她的呆氣,更多的是對第一次面對這樣大場面的一種自然的人物反應。所以,在文學作品中的詈語,它的交際功能是混合的、多樣的,只有這樣,才能將貼近生活的真實的人物和情感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二)具有塑造人物的功能
詈語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其對彰顯人物性格、刻畫人物形象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在小說《主角》當中,詈語的運用無疑是對塑造、刻畫普通老百姓之間爾虞我詐、勾心斗角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在人類溝通交流的過程中,是無法避免強烈的情感對沖的,而在這樣的體驗下,就會迸發(fā)出詈罵語言,這些語言才是人們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正是這樣的共情式的情感特征才能讓作品顯得更加真實,這是正式的交際用語所無法比肩的。也正是有了詈罵的加入,角色的立體感和真實感才會更上一個臺階。小說中,胡三元就是一個“出口成臟”的人,他常常嘴邊離不開的就是“哈慫”“少皮干”這樣的罵語,通過這些具體到語境中的詈語,可以使讀者深入地認識到胡三元這個人物形象的復雜性、立體性。胡三元并不是像他所說的罵語那樣的低俗不堪,而是一個有擔當?shù)哪腥恕_@樣的人物形象如果脫離了詈語的描述,那人物的真實性就會大打折扣。再者,小說中還塑造了一個與胡三元形象完全對立的角色——郝大錘。此人雖然和胡三元同樣喜歡“出口成臟”,但是罵語和罵意卻狠毒許多。比如:
臨走臨走了,他還給易青娥撂了幾句話,“火燒得美美的么,咋想起要唱戲了呢?真是跟你那個爛桿舅一樣,一輩子瞎折騰哩。都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是吧?”[2]175
郝大錘一邊朝排練場外面走,還一邊罵:“你個老皮,見你把個爛大衣一天披來篩去的,我就頭暈。你還嫌我呢,排不成了滾你娘的蛋。”[2]139
顯而易見,通過罵詈,郝大錘來宣泄自己內(nèi)心的不滿和技不如人而帶來的內(nèi)心挫敗感,罵詈中所包含的惡毒詛咒也把“攻擊”這一功能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借此將這一人物的歹毒狠辣、陰險自負的性格特征塑造得飽滿而充沛。
總之,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多角度、全方位反映了民族文化的豐富性、復雜性。方言中的詈語,則是地域俗文化的重要載體,以其獨特的角度,折射出普通民眾的倫理觀念、社會生活。[5]陜西作家陳彥以其細膩獨到的觀察,深刻認識到詈語的俗文化鏡像功能,把陜西詈語運用到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借此塑造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原生態(tài)的陜西地域文化,可謂是一箭雙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國是文明古國、禮儀之邦。漢語歷經(jīng)幾千年的發(fā)展,積淀了發(fā)達的語匯和豐富的語言表達方式。無數(shù)文人墨客,運用漢語鋪錦列繡的辭藻,塑造了鮮活生動的文學形象,傳承了泱泱大國的禮俗文明,化育成為今天人們待人接物的美好風尚。在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新時代,語言文明仍然是傳承和構建文明價值觀的重要工具。毋庸諱言,陳彥《主角》中運用詈語刻畫了生動的人物形象,展現(xiàn)了陜西人千年承襲的民間習俗,這是作品的一個亮點。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作品中這些詈語的書寫與使用,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青少年讀者的語言接受與習得,某種程度上會對社會的語言文明造成一定負面影響。在此,我們呼吁,文學作品如無十分必要,盡量減少或者節(jié)制詈語的使用,盡可能以委婉含蓄的文明語言取代詈語,使文學作品更好地服務文明社會的建設。
注釋:
“尻”當為古漢語書面語用字,意為“屁股”,讀為“kāo”。今現(xiàn)代漢語“尻”也多用于書面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稱“尻”“今俗云溝子是也”。也就是說,“溝子”一詞在清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現(xiàn)在西北方言中指稱人屁股時多用“溝子”一詞,不單說“溝”,也不會說“尻”或“尻子”。據(jù)考察,陜西各地都沒有把屁股稱為“尻”“尻子”的說法。今陜西各地方言多用“溜溝子”“溜溝子貨”“舔溝子”來侮辱人。因此,書中以“尻”“尻子”代替“溝子”疑為作者誤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