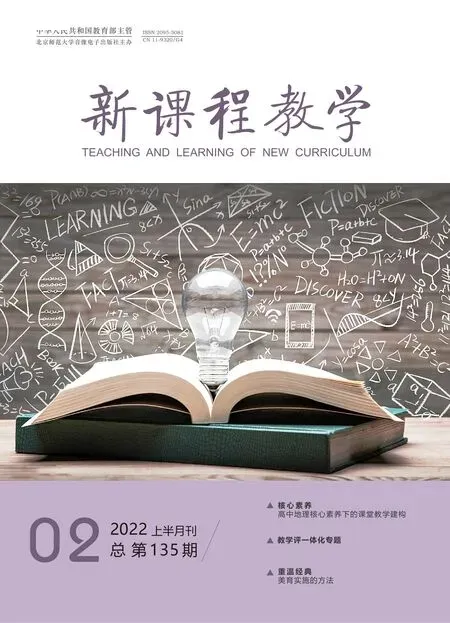論“騷雅”在詩詞審美中的表現形式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新世紀中學 陶 達
“騷雅”這一審美概念在詞論中大概最早出現于南宋初鮦陽居士之《復雅歌詞序》,序謂唐宋以來之歌詞,“韞騷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張直夫為詞序,亦云詞須“靡麗而不失為國風之正,閑雅不失為騷雅之賦”。(周密《浩然齋雅談》)而最早在詩話中使用“騷雅”這一審美概念的,是唐代的白居易,他在《文苑詩格》中說道:“為詩之道,義在裨益,言意皆有所為。為詩不裨益,即需諷諫,依離騷雅。”“騷雅”在其他詩話中亦有所使用,如“……頃之,議論騷雅,相得喜歡。”(《古今詩話》)“騷雅”這一審美概念在詩話中出現極少,既未涉及具體作品,又無具體論述,不便于把握其審美內涵。
白居易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詩人,他主張作詩要聯系政治時事,或揭露,或諷喻。其《讀張籍古樂府》云:“為詩意如何?六義相鋪陳。風雅比興外,未當著空文。”“風雅比興”是六義之精髓,而“美刺”又是“風雅”的精神之所在。白居易把“風雅比興”或“美刺比興”作為最高標準,用來衡量文學史,評價詩作,去偽存真。可見,白居易在創作方法上充分繼承了《離騷》的現實主義傳統和浪漫主義精神。他所說的“依離騷雅”也就是指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是重點就創作方法而言的,詞論中的“騷雅”則是對詩話中“騷雅”內涵的繼承和發展。
古代詞論,大都散見于隨感、漫興的記載之中,顯得零散而不成體系,對“騷雅”這一審美概念沒有作出具體的定義,各個詞評家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騷雅”這一審美概念的內涵,使得我們在借助“騷雅”這一審美概念來鑒賞文學作品時,有了充分的理據。
一、“騷雅”表現在詩詞作品的語言特點上
宋末張炎在其《詞源》中,曾多次使用“騷雅”這一審美概念來評價宋人詞作的語言風格。如他在評價周邦彥詞作的語言特色時說:“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于媚軟中有氣魄,系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惜于意趣并不高遠。所以出奇之語,以白石騷雅句法潤色之,真天機云錦也。”張炎詞論的標準有三,即“意趣高遠”“雅正”“清空”,他對白石詞推崇至極,尤其是白石詞的語言特色和“騷雅”句法。白石詞在語言上的“騷雅”特點,可以從其《暗香》中窺見一斑。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 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一句“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展現給我們的是一片令人神往、讓人傾心而又不堪回首的湖光山色。耿相憶,那曾經與紅顏知己心相映、手相握的地方,如今卻人去樓空、千樹林立,那湖邊的柳條,就像掛滿了縷縷思念,依依不絕,揪人心痛……白石詞的語言,騷雅結合,內涵豐富,充分表現出了語言的無限張力,意蘊深厚,余味無窮。只一個“壓”字,就把雪后湖邊梅花盛開、斗艷群芳、充滿生機、相映成趣的優美景致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白石詞中虛字的運用,使其詞平實穩健,在節奏上跌宕多變、自然完整,涌動著一種不可抗拒的靈動。懷古思今,凄婉哀怨,真乃“以樂景寫哀情之神筆也”。
二、“騷雅”多指詩詞作品的風格
段誠之在《菊軒樂府》《江城子》里云:“月邊漁,雨邊鋤。花底風來,吹亂讀殘書。”前調“樂園牡丹花下酒酣即席賦之”云“歸去不妨簪一朵,人也道,看花來。”況周頤謂之“騷雅俊逸,令人想望風采。”
在評價白石詞風格時,張炎在《詞源》中云:“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琵琶仙》《探春》《八月》《淡黃柳》等曲不唯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如白石早期詞《揚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青青,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余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稍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本詞上片所寫之景,凄楚荒涼,令人感慨愴然,由于戰亂,昔日的名城破敗不堪,黃昏清角,愁滿空城。下片用杜詩抒寫懷古傷今之情,蘊含了對國家興亡的深深嘆息和哀怨。作者運用對比、聯想、想像,用心靈視覺跨越時空,粗筆勾勒,虛實結合,用平實的語言描寫刻畫心理。張炎認為白石詞“清空”“騷雅”,主要是針對白石詞的語言風格來說的,是一個極高的評價。雖然詩詞作品的語言特色、文辭、創作方法和表現技巧都在風格的領屬之下,但在審美活動中它們又屬于不同的審美對象,相互之間不可替代,所以“騷雅”這一審美概念在適用于不同的審美對象時便有了不同的內涵和蘊義。
三、“騷雅”有時也表現為詩詞作品的表現手法
其實,“騷雅”與浪漫主義是息息相通的。一方面是指詩詞作品中多采用香草美人式托物見志的表現手法,另一方面,又指其馳騁自如的想像。清代田同之在《西圃詞說》里曰:“王美元論詞云:‘寧為大雅罪人’,予以為不然。文人之才,何所不寓。大抵比物流連,寄托居多。《國風》《騷》《雅》,同扶名教。即宋玉賦美人,亦猶主文諫之義。良以端之不得,故長言詠嘆,隨旨以托興焉。必欲如柳屯田之‘蘭心蕙性,枕前言下’等言語,不幾風雅掃地乎!”
白石之詞,有的詞以寄寓深遠、托物比興的方式,抒寫自己不屑流俗的思想和家國興亡之感,這與最初鮦陽居士提出的“騷雅”之義如出一轍。陳廷焯談到白石詞時說“姜堯章詞清虛騷雅”,又說“南度以后,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于詞中寄感慨。……感慨時事,發為詩歌,便也力據上游,特不宜說破,只可用作比興體”。(《白雨齋詞話》)宋翔鳳的《樂府余論》則稱“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托比興于長短句寄之”。他們認為,白石詞的寄托比興,亦近騷體,一是指其詞作中香草美人式的托物以見志的表現手法,再則說其馳騁天地、超然物外的想像力。在運用這些表現手法時,白石憑借高超的藝術功底,不落俗套,獨具匠心,別出心裁,既“騷”且“雅”,使其詞格調清新、雋永,耐人尋味。
由于蕭落的人生際遇,以及昏庸國事的困擾,白石心境黯然、觸景神傷。白石吟荷詠梅,更是生動傳神,意內言外,清幽自然,而其中的騷興,又顯得浪漫而典雅。浙派領袖朱彝尊,首倡白石宗風,提出詞要有所寄托的主張:“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于《離騷》變《雅》之義。”
四、“騷雅”亦指詩詞作品文辭的雅潔
蔣兆蘭的《詞說》云:“古文貴潔,詞體尤甚。方望溪所句舉古文中忌用諸語,除麗藻語外,詞中皆忌之。他如頭巾氣語,南北曲中語,世俗習用熟爛典故及經傳中典重字面,皆宜屏除凈盡,務使清虛騷雅,不染一塵,方為比妙。”
文辭騷雅者,如辛棄疾之《祝英臺近》: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喚流鶯聲住?
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更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
該詞婉轉凄涼、情境相生,文辭質樸而不事雕琢,顯得雅潔自然。玉田《詞源》論賦情云:“……如陸雪溪《瑞鶴仙》辛稼軒《祝英臺近》,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蔡嵩云《樂府指迷箋釋》)。
綜上所述,“騷雅”這一審美概念,在詩詞作品的審美運用中已具有悠久的歷史,且可運用于不同的審美對象,適用性較廣。就同一詩詞作品而言,其語言特色、文辭、表現手法及風格都是密切相關的,審美時不能孤立對待。“騷雅”這一審美概念,作為一種鑒賞標準,既可給讀者提供一種審美參照,又能充分調動審美主體再創造的積極性,發揮藝術想象力,體現審美主體的個性,豐富審美對象的內涵,幫助讀者對古代詩詞作品進行藝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