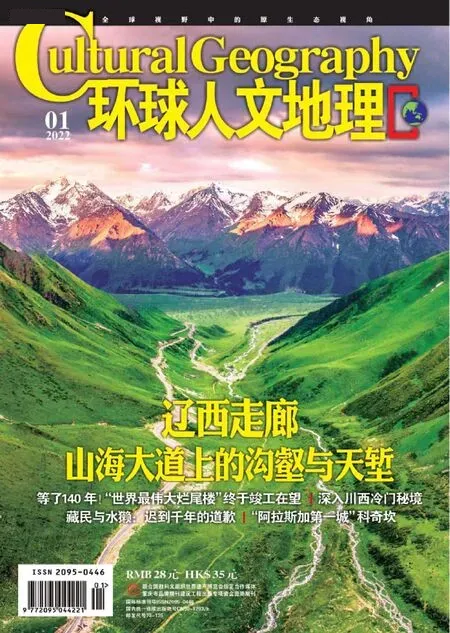東北的大缸
馬如營
作為中國民俗文化的符號,缸的作用不可小覷。詞典上這樣解釋“缸”:盛東西的器物,一般底小口大,有陶、瓷、搪瓷、玻璃等各種質料的。
在一年冷半載的東北,缸是衡量居家的標準,可以上升到品德的高度。即便是現在,隨手推開一戶住平房的東北人家,屋內的水缸、米缸、酒缸、醬缸、酸菜缸、咸菜缸一應俱全,否則會被視為“不過日子人家”,備遭詬病。
邁克爾·麥爾是我哥們兒,這個屬鼠的“美國鬼子”,多年前因為看了我寫的《辜鴻銘先生》和《黃仁宇先生》兩篇隨筆,跑到哈爾濱找我玩。那時候我不太了解這小子底細,況且還是美國人,唯恐“蔣干盜書”案件復發,甚是警覺,畢竟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于是,我傲慢了幾天,就像當年毛姆膜拜辜鴻銘。瓜皮帽下一根羸弱的辮子、山羊胡下的一襲長衫馬褂、瘦若柴雞的辜鴻銘讓英倫海峽的文豪毛姆知道了中國文化的春秋大義。
幾頓觥籌交錯,我便知道了麥爾的名氣大得破了天,我根本不是對手。這小子先在四川做義工——免費教English,爾后去清華學中文,住在大柵欄附近,2013年出版了《再見·老北京》。《東北游記》是他娶了東北媳婦后,因愛成書,頗具好評。
我媽住在山里低矮的板夾泥草房里,這種房子長得不好看,卻冬暖夏涼,睡在火炕上,夜里聽雪折枝,意境深遠,山風洗肺,雜糧果腹,精血蓄銳,我媽說給個縣長都不干。
貓腰進山的時候,正值寒露,滿頭銀發,精神矍鑠的我媽正在腌酸菜。兩口大缸被刷的干干凈凈,擺放在外屋(東北民居燒水做飯房間),那口八仞大鍋盛滿了水,鍋底被柴火熱烈地舔舐,片刻鍋里的水便歡呼起來。
樂觀、探究、隨和是大多美國人不容置否的性格,麥爾饒有興趣地給我媽打下手。剝去老皮、爛幫、蟲蝕的大白菜,浸在沸水里,煮焯后放進大缸。麥爾按照我媽腌酸菜的工藝流程,擺放一層焯好的白菜,撒上一層大粒鹽,再跳入缸內踩實,如此反復,周而復始,不到個把小時,兩口大缸便填滿了,然后在缸上壓一塊碩大的石頭,剩下來的日子,就等白菜在缸里慢慢發酵,三十天之后變成酸菜了。
嚴格意義上說,就東北三省而言,白山黑水,最具風骨的尚屬黑龍江和吉林,說話腔調一致,行事風格相同,尤其氣候,長春和哈爾濱不分伯仲,哈爾濱打個噴嚏,長春人準感冒。但昔日的共和國長子,落魄成“姥姥不愛,舅舅不親”的“外甥”。翻開厚厚的唐詩,僅查閱到一首跟東北有瓜葛作品,而且滿懷怨氣。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或許是關東的風雪過于凜冽,讓詩人卻步于山海關南側的隘口內;或許是關東路阻且長,讓“流人”文化有了古拉格的味道。
漫長的冬季,東北人要與惡劣的自然環境做斗爭,若想頑強地生存下去,就得儲存活命的糧食和蔬菜。沒有冰箱的時代,東北人的大缸對于儲存食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糧食入缸,不生蟲害,防止發霉變質;蔬菜藏缸,保鮮鎖水,吃點取點,細水長流;小燒窖缸,酒醴維醹,口味純正,經久醇香,不輸茅臺、五糧液。當然,盛水是缸的重要使命之一,父親生前總是將家里的缸盛滿水,鮮有半缸水的時候。他說,讓水在缸里自我坐清(過濾),久了雜質自然會沉入缸底,清水浮在上面。后來我想,缸里的水或許就是人生哲學的過程。
正是得益于父親缸里滿水的生活理念,使得我們全家逃過了一場火災之劫。燒薪取暖的林場,1972年冬夜鄰居失火,殃及我家。西北風裹挾著火舌,瞬間吞噬了伐木工人家的夢魘。父親用水瓢從缸里舀出水,潑在棉被上,披在家人身上,破窗魚貫而出。翌日,五戶人家一死四傷,僅有我戶毫發無損。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分門立戶后,家里始終存留一口缸,而且“缸里滿水”,以備不時之需。
缸在中國是有歷史淵源的,山東淄川就有一家“缸文化博物館”。館內,記載渭頭河陶瓷歷史的圖片與幾千件古陶瓷,尤其是“摑貨”——渭頭河大甕系列,讓人大飽眼福。展廳中,最大的大缸直徑為80公分,歷史最悠久的則是清初的窯角大缸,距今已有400多年的歷史。
渭頭河一帶自宋、金便有制陶業。明清時期,渭頭河大黑碗、大紅碗在陶瓷集散地就享有盛名。民國早年,這里的產品開始以大甕為主,并逐漸成為了風靡北方地區的名牌產品。渭頭河大甕品種多樣,底厚壁薄,堅硬敦實,不滲水,經久耐用,行銷中國整個北方地區,長盛不衰。其生產一直使用延續了上千年的原始制作工藝,直至上世紀60年代,牛拉碾、人採泥、手拉坯、泥條盤筑成型、手工剟修、窩窩頭窯燒成等生產工藝仍在沿用。
中外關于“缸”文化的演繹也不勝枚舉,比如我們熟知的“司馬光砸缸”,唐詩人杜牧“窗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缸”。當然,缸里也有齷齪,現代京劇《沙家浜》中壞蛋胡傳魁曾向刁德一吐槽自己的糗事:“遇皇軍追得我暈頭轉向,多虧了阿慶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她那里提壺續水,面不改色,無事一樣,騙走了東洋兵,我才躲過大難一場......”
《地道戰》中鬼子軍曹,被土八路無孔不入的地道驚得寢食不安,弄口大缸置于臥室地下,時不時側耳傾聽是否有挖地道的聲音。
缸最早叫“甕”。《資治通鑒·唐紀·則天皇后天授二年》載: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請君入甕”。
薄迦丘在《十日談》中也對“缸中藏人”做過描述,那個叫佩羅內拉的女人當自己丈夫的面,巧妙地把與其歡愉的男人藏在缸里暗度陳倉,酒莊簡直成了奧革阿斯的牛圈。
文化和經濟是雙引擎,缺一不可。去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著名經濟學家蔡昉在談論振興東北時說,東北經濟就像一口大缸,干貨被淘空了,成了風穴。尤其是人口的流失,讓東北更顯雪上加霜,而專家給出的方子,不一定是振興東北的良藥。
中國老子也說:“天之道,損有余也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
蔡昉進一步解析道,東西部地區千萬不要把勁頭使在爭取項目投資上面,而是在人力資本上面。借助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投資,把貧困地區送入一種自身人力資本所不能維系的增長“穩態”,最終證明都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只有投資教育、健康等增加人力資本的領域,才是根本的出路。
莎士比亞在《尤里烏斯·凱撒》中說,世事起伏跌宕,若能順應潮流,激流勇進,便可成就事業;逆潮流而行,錯過機遇,只能終生蹭蹬。
其實,人類的經濟史就是一部遷移的歷史,從《詩經》到《出埃及記》,到現代經濟增長中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無一例外地揭示了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強烈愿望。誰能保證二十年之后,沒有大災大難的白山黑水不會迎來第三次“闖關東”浪潮呢?
說到底,東北的缸,還是要裝自己的東西。畢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