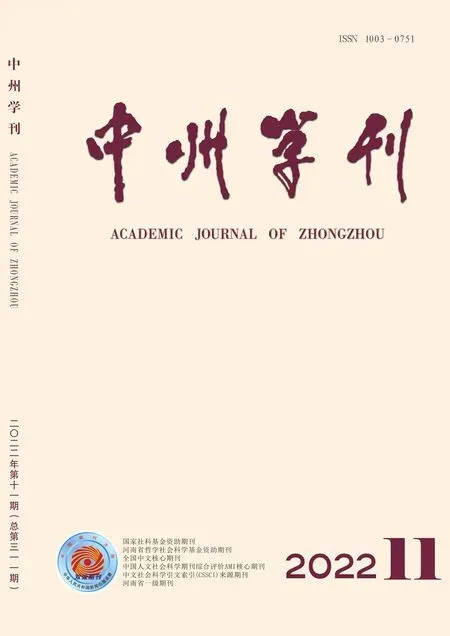杜甫華州去官是棄官還是流放?*
張 起 邱 永 旭
一、問題緣起
華州去官是杜甫人生中的重要關捩,詩人遭遇的苦難無不由此而起。經歷這一事件后,杜甫的詩風也為之一變,由明麗直截變含蓄隱諱,許多事在詩中不能直說,只能寄托遙深,被迫沉郁頓挫。自宋代出現“去官說”后,遞相祖述至于今,影響深遠。比如在學界影響較大的陳貽焮、莫礪鋒,在各自的《杜甫評傳》中也以“棄官說”為圭臬。但筆者越認真讀杜詩,越覺得這種說法令人生疑。此事關涉詩人事君交友、生平出處大節,甚至可以說它影響了詩人后半生的運程,對解讀杜詩至關重要。因此對這一疑案加以考證很有必要。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杜甫華州去官,是因關中饑荒主動請辭,還是肅宗進一步加責免除?到底是棄官,還是罷官?他入隴蜀,是自己的主動選擇,還是被迫流放?從他與肅宗的微妙關系看,筆者更傾向于后者。
華州去官,古今學者幾眾口一詞,認為是他主動棄官。但筆者認為杜甫并非這種人。他很忠君、很重傳統,“奉儒守官”,報效朝廷,是其家族傳統。天寶十三載(754年)杜甫作《進雕賦表》自述“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祖父文采風流,“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天下學士到如今而師之”[1]2172。杜甫家族門風清華,儒學傳家,世代官宦。奉儒守官,成為他一生的追求。傳統道家的逃逸、魏晉名士的個人解脫以及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迂拙,都與他無關,家族傳統中無這些基因。他堅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社會理想,自比“稷與契”,述志詩《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已表明其人生態度。莫礪鋒認為:“就杜甫一生的行事來看,‘奉儒守官’的家庭傳統對他產生的主要影響絕不是‘積極地營謀官職’,而是堅信儒家的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2]如果沒有外力逼迫,他怎會無端辭官?
杜甫華州去官之前的行為已表明,他是一位忠君愛民的詩人。天寶十五載,安祿山攻陷長安,玄宗奔蜀,肅宗靈武接位,杜甫遷家鄜州,北上勤王,途中陷賊軍,困于長安,作《哀江頭》,有“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之語。后來,他冒死竄奔鳳翔,“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如此危境,忠勇的詩人都經歷了,怎會因饑災棄官呢?在華州他作有批評肅宗的《洗兵馬》、描寫戰亂和百姓苦狀的“三吏”“三別”,他怎可因饑荒便棄華州百姓獨自逃荒?杜甫剛到華州,即埋頭工作,作《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代州牧寫《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分析形勢,仇注云“經國有用之文”。這一時期他還有《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寫李嗣業安西兵馬過境討安慶緒,“竟日留觀樂,城池未覺喧”為王師討賊而高興。《夏日嘆》《夏夜嘆》記錄了鄴城三月兵敗后關中久旱無雨的景象,人禍天災,生靈涂炭,滿目蕭條,詩人“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化用陸機《為周夫人贈車騎詩》“對食不能餐,臨觴不能飯”,忠君憂民之狀溢于言表,毫無辭官之志。從其價值觀與道德人品來看,他不可能棄官逃荒。所以,“棄官逃荒說”純屬無稽之談,頗不合詩人家庭傳統、人生理想及為人處世。
翻檢近年研究杜甫的文獻,杜詩研究雖為“顯學”,但相比而言,對于華州去官問題卻鮮少追尋,囿于定說。早期如20世紀80年代鄭文《杜甫為什么棄官》、馮鐘蕓《關于杜甫棄官往秦州緣由新探》,到近年丁啟陣《論杜甫華州棄官的原因》、安志宏《“少陵棄官之秦”探因——關于杜甫棄官流寓秦州的補充意見》、陶成濤《杜甫棄官奔秦州原因再探析》、師海軍《杜甫離職華州西行論稿》均從宋人之說。這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多是就棄官原因分析,未能上升到罷官這一層面。如馮文史料運用非常詳盡,可惜仍在舊說里轉圈子。鄭文既有退隱之志分析,又有罷官猜測,惜無結論,便有些模棱兩可,在文末說明:“由此可見所謂詩人的棄官,并非由于天災饑餓,而是由于人事排斥,本詩自道明甚。以上所舉,理由還不夠充分,證據還不夠切實,請候高明,作進一步之探索。”陶文則把杜甫說成憂懼戰爭而逃亡,將詩圣視為偷生之輩,而無視其忠勇。文中將杜甫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在蜀中所寫的《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中的“不關輕紱冕,但是避風塵”之句,膚淺地理解為字面的“躲避戰爭風塵”,不明白詩人為尊者諱的苦心,說“杜甫擔心叛軍再次攻入潼關,擔心華州再次淪陷,故而提前棄官西逃”。師文是新近的研究成果,卻又回到宋人棄官舊說,進一步分析了“主動辭官”的原因,認為詩人離職華州西行及其在秦州的經歷是去找人,是為了去涼州投奔河西節度使杜鴻漸。這屬于主題先行式寫作,完全不可取。
21世紀初有人提出“華州罷官說”,如閻琦《杜甫華州罷官西行秦州考論》、王勛成《杜甫罷官說》、李宇林《杜甫罷官華州原因探析》、韓成武《解說“罷官亦由人”之“罷官”——對杜甫離開華州任原因的討論》,但在分析原因時,要么牽強附會,要么與棄官原因大同小異。如李文雖然說華州“罷官”,卻認為是因為杜甫身患重病,難以應付繁重的公務而遭“頂頭上司”罷官。韓文認為“罷官”有兩義:一是當事者主動辭掉官職;二是當事者被免除官職。杜甫離職屬前者,是對肅宗政治失望而自己罷自己的官,實際上仍等于“棄官說”。閻文雖認可罷官,卻說詩人是因“荒怠政務”中途擅離職守跑回河南“觸犯職律”而遭遇罷官。這種看法沒有理解詩圣之心,與歷代對詩圣的認知嚴重不符。王文認為杜甫罷官是因為唐代考官制度,秩滿罷官,是“緩解選人多而官闕少這一社會矛盾的一項措施”。這里把杜甫看成普通平民士人,與杜甫家世身份不合。王文看似另辟新路,實際上卻不可取,此時是盛唐而非中晚唐,官路未見堵塞,只有中晚唐科舉放開,平民士人大量出現,才使得進身之路十分擁擠,而朝廷提供的崗位又不能滿足需求。
“罷官說”雖然比“棄官說”有所進步,但仍然未能看清杜甫遭遇流放的真實遭遇。研究杜甫,都知道“華州事件”對解讀詩人后期詩歌的重要性,但對這一事件的認知如果上升不到“流放”的程度,則難以解釋透徹杜詩,難以解釋清楚杜詩前后詩風的重大轉變。不知杜甫遭遇流放,導致今人對其草堂詩的誤解。不少人對詩人經歷喪亂之后,在成都獲得表面平靜生活的詩歌作閑適寫景解讀,完全低估了草堂詩的價值。比如《草堂即事》,就并非寫景詩,其中“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之句埋藏著詩人對朝廷、對君王的深切眷戀。杜甫在草堂詩中大量引用《離騷》《詩經》中的典故,即可知其自比屈子之難。又如肅宗上元二年(761年)杜甫在成都所作《楠樹為風雨所拔嘆》,表面在寫風雨摧拔楠木之景象,實則在寫宮廷斗爭的血雨腥風。“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暗示了詩人對失勢玄宗的同情。讀者如果不知詩人介入的深淺,便不知詩人心中的滴血。《讀杜心解》說“深痛摧埋失色”,嘆楠樹,亦是詩人遭遇流放的自嘆。
二、多種典籍對杜甫華州去官的誤載
關于杜甫華州去官之事,代表性的說法主要有三種:一是仇兆鰲考訂朱鶴齡《杜工部年譜》中所說:“乾元二年己亥,春,自東都回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3]16二是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中所說:“乾元二年己亥(759),公四十八歲。春,自東都歸華州,途中作‘三吏’‘三別’六首。時屬關輔饑饉。遂以七月棄官西去,度隴,赴秦州。”[4]69三是王士菁《杜詩今注》中在《立秋后題》下注:“這首詩約為乾元二年盛夏已過,立秋后辭去華州司功職務,即將前往秦州時所作。”“罷官二句”下注:“這是說去官之意完全由自己決定,心不為形所役。反陶詩之意而用之,以明去官之志。”[5]以上不同時期的說法皆從主動“去官說”,均把“華州事件”簡單化,殊不合詩人的理想抱負。
追本溯源,杜甫華州“棄官說”出自兩《唐書》。《舊唐書》文苑本傳記載:
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征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于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谷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采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6]3193
《新唐書·杜甫傳》記載:
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庭蘭罷宰相。甫上書,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于色,然性失于簡,酷嗜鼓琴,庭蘭托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嘆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畿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7]3588-3589
但兩書均距杜甫生活的時代較遠,不能說最權威,并且兩史杜甫本傳皆有重大缺漏。《舊唐書》言“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谷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文義不連貫,從華州參軍直接跳到寓居成州同谷縣,中間有重要信息脫漏,故意漏言杜甫“寓居成州同谷”之因,似有隱情。《新唐書》則徑直言“關畿饑,輒棄官去”,明確說杜甫為饑荒棄官,去過不受約束的自在日子。比較兩書,《舊唐書》并無“棄官”二字,100多年后編纂的《新唐書》中添加“棄官”二字,讓人殊難理解。危急關頭,一貫為蒼生號寒啼饑的杜甫會拋棄自己一直關心的黎庶,不負責地棄官逃跑,去過“負薪采橡栗自給”的生活?這不僅嚴重違背他“奉儒守官”的家訓,而且與他后來在成都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時展現的儒家情懷相悖。從杜甫一貫的立身行事來看,他不會如此前后人格分裂,“華州逃荒”幾不可能。
追而溯之,《新唐書》的“棄官說”蓋源自宋人王洙《杜工部集〈記〉》介紹杜甫生平時所說的“屬關畿饑亂,棄官之秦州”。“逃荒說”則是王洙根據《舊唐書·肅宗紀》中關中災荒的記載,增補杜甫棄官的原因是“關畿饑亂”。王洙的記載誤導天下人千年,并引起后人對華州之后大量杜詩的誤讀,至今未得到匡正。
三、杜甫華州去官的真相
杜甫華州去官之因是什么?《舊唐書》不便寫出,直接略去;《新唐書》說是“棄官”;杜甫自己也刻意回避。從杜甫自身而言,他具有憂念百姓的情懷和濟蒼生安黎元的抱負,并且這種志向老而彌堅,他無論如何不會坐視人民苦難主動辭官。天寶十四載(755年)他擔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一年后,回奉先省親,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充分表達自己堅定的志向與抱負: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
仇兆鰲注曰:
(第一至八句)此自敘生平大志。公不欲隨世界立功,而必朝圣賢事業,所謂意拙者,在比稷契也。甘契闊,安于意拙;常覬豁,冀成稷契。[8]259
(第九到二十句)此志在得君濟民。欲為稷契,則當下救黎元,而上輔堯舜,此通節大旨。江海之士遺世,公則切于慕君而不忍忘;廊廟之臣尸位,公則根于至性而不敢欺。此作兩形,以解同學之疑。浩歌激烈,正言詠懷之故。明皇初政,幾侔貞觀,迨晚年失德,而遂生亂階。曰“生逢堯舜君”,望其改悟自新,復為令主,惓惓忠愛之誠,與孟子望齊王同意。[8]259-260
(第二十一句到第三十二句)此自傷抱志莫伸。既不能出圖堯舜,又不得退作巢由,亦空負稷契初愿矣。居廊廟者,如螻蟻擬鯨,公深恥而不屑干。游江海者,若巢由隱身,公雖愧而不肯易。仍用雙關,以申上文之意。放歌破愁,欲藉詠懷以遣意。[8]260
杜甫要求自己向稷、契看齊,為了此志,即使落得一生勤苦、一事無成,也不愿轉移志向。雖然他慚愧沒有像許由、巢父飄然世外,但不愿改變節操。所以,杜甫不可能辭官逃跑,其華州去官另有原因,筆者認為是他與肅宗的君臣關系出現了問題而被罷官。《舊唐書》不記去官原因,是受為尊者諱的史傳傳統約束。杜甫自己避而不談,也是在為尊者諱。
綜觀杜詩,杜甫僅在《立秋后題》這一首詩中非常隱晦地提及華州罷官之事: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愿,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這首詩是乾元二年(759年)立秋次日作。杜甫此前所作憂國憂民的《夏日嘆》《夏夜嘆》均無辭官的跡象。立秋次日即言“罷官亦由人”,可見罷官是在立秋日。“節序昨夜隔”,暗示昨日還在官,隔夜就被罷免。“日月不相饒”,除時序更迭外,背后還有日月力量。日月代表著誰,詩人沒有說。他是別有一番痛楚不能說,此乃春秋筆法。我們聯想這一時期李白流放夜郎時所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十》中的“雙懸日月照乾坤”之句,可以推知,日月分別指玄宗和肅宗。“日月不相饒”不能單純解為化用鮑照詩句“日月流邁不相饒”,而是一語雙關,還隱含著鮑照下句“令我愁思怨恨多”,由此可知詩人對罷官多么痛苦不堪。
《杜詩詳注》中朱鶴齡、王嗣奭、仇兆鰲對這首詩的解釋皆失誤,所謂“此詩蓋欲棄官時作”“乃公轉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9]544,均是不解詩人之遭遇。其實杜甫在詩題中直接點明這首詩立秋后作,是別有深意的。古代設官立制、刑殺赦免均要依節序,應四時。《禮記·月令》載:“孟秋之月……用始行戮。……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10]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天有四時,王有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下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11]杜甫在立秋之日被罷官,隱晦地道出肅宗迫不及待地對他秋后算賬。
翻檢杜詩,可以發現杜甫對于涉及自己重要人生關節的詩全有自注,唯獨《立秋后題》這首沒有,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在為尊者諱。這種良苦用心,在其他作品中也有體現。乾元元年(758年)杜甫由長安出華州途中作《題鄭縣亭子》,也在“為尊者諱”,詩中有“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之句。詩人為誰傷神?他苦楚難言,自己的遭遇不可留于“青竹”。又如五年后他在蜀中寫的《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中有“不關輕紱冕,俱是避風塵”之句,談到當年被驅趕出朝、華州罷官時,也是十分含蓄隱諱,完全把責任歸于自己。尤其是“敗亡非赤壁,奔走為黃巾”兩句,既隱含安史之亂,又映射肅宗擅自接位、架空父皇的不孝行為。晚年他在總結性長詩《壯游》中也刻意回避關涉自己人生大節的華州罷官事不記,僅言“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前句暗指詩人當年任左拾遺時激烈批評肅宗的行為;后句暗示華州之難及流放隴蜀的遭遇。擔任左拾遺卻不能進諫,反而被放逐邊荒之地,詩人故意跳過其中的原因與過程不言,只能“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值得注意的是,杜詩中有許多帶“病”字的句子,這往往并非指身體之病,多數情況下應當理解為君臣之病。他所“病”之人,是罷官背后的強大勢力,也就是詩人“為之諱”的唐肅宗。我們從“罷官亦由人”之句可知,杜甫不是簡單貶謫,而是被革職。因政治打擊而直接罷官,懲罰過于嚴重,之后像永貞之變這樣擾亂朝綱的重大政治事件,當事人也僅是被長期貶逐。由此可見,杜甫與肅宗之間的恩怨已超越房琯事件。
四、杜甫與肅宗的君臣關系
杜甫與肅宗的君臣恩怨,我們可結合史料梳理出二人交集的幾個重要時間節點。
一是杜甫與肅宗二人的關系始于天寶十三載(754年)。
《新唐書·杜甫傳》記載:“天寶十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7]3588天寶十三載十月杜甫守選期滿,授河西尉。河西縣屬同州(陜西渭南),為春秋時期游牧部落大荔戎進入洛水建立的戎國之地。這與詩人的正統觀念不合,他并未像一般寒士考選出來那樣去就職,于是再改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杜甫在《官定后戲贈》題下自注:“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左右衛率府參軍為太子武官,掌兵仗羽衛,設倉兵胄三曹參軍,從八品下,官階不高。《新唐書》稱杜甫“胄曹參軍”有誤,《舊唐書》稱“兵曹參軍”是準確的。杜甫在這個崗位履職一年余,有多首與官員交往的詩可以為證。這一年他還得到休假,多次往返奉先(陜西蒲城)探親。從杜甫的《夏日李公見訪》一詩可知,太子曾委派家令李炎去看望杜甫,從中亦可推知杜甫與太子的關系比較密切。
杜甫做了一年率府參軍,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他又從京城赴奉先探家,寫下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筆者細致閱讀杜集,發現杜甫履職一年多后才回奉先探親。不少學者讀書時誤將天寶十三載這年省去,認為天寶十四載杜甫官定后即回奉先探親。如果按今人觀點,至少有11首杜詩無法編年,杜甫北上勤王,而不追玄宗入蜀的行動,也不能準確解釋。
二是至德二載(757年)春,杜甫自長安亡走鳳翔,五月十六日授左拾遺,受到肅宗器重。
錢謙益《錢注杜詩》卷二《述懷》注:
唐授左拾遺誥:“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為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后,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張鎬赍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右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五寸許。今藏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12]
宣義郎,散官銜,從七品下;左拾遺,職事官,從八品上。杜甫由兵曹參軍改左拾遺,屬升遷。左拾遺雖為從八品上,卻是天子近臣,“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于下,忠孝之不聞于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13]。肅宗把如此責任重大的職位交付于杜甫,可見對他充分信任。杜甫左拾遺的任命由中書、門下二省奉皇帝敕詔頒授,比吏部銓選授官更為尊榮。左拾遺為敕授官,由皇帝授予;旨授官由吏部銓選上報,再下旨頒授,人選并非出自皇帝。可見此時肅宗非常器重杜甫,君臣關系融洽。
光復后杜甫回到長安,肅宗曾給予他很大恩遇。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載,“乾元元年戊戌,公四十七歲。任左拾遺。春,賈至、王維、岑參皆在諫省,時畢曜亦在京師,居公之鄰舍。四月,上親享九廟,公得陪祀”[4]68,可謂榮顯。仇兆鰲注:“唐史肅宗還京,在至德二年十月,其親享九廟及祀圜丘,在乾元元年四月。”這種莫大的榮耀給杜甫留下美好記憶,晚年他還在《往在》中述此盛事:“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群公。登階捧玉冊,峨冕耿金鐘。侍祠恧先露,掖垣邇濯龍。”至德二載五月,杜甫作感恩詩《端午日賜衣》,可見君臣之間往來密切。
三是至德二載閏八月初一,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觸怒肅宗,被遣返鄜州省家,君臣關系開始疏遠。
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記載:
至德二載丁酉,公四十六歲。春,陷賊中。在長安時,從贊公、蘇端游。四月,自金光門出,間道竄歸鳳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遺。是月,房琯得罪,公抗疏救之。肅宗怒,詔三司推問,張鎬、韋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薦等四人薦岑參。閏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鳳翔,至邠州,始從李嗣業借得乘馬。歸家臥病數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師。[4]65
乾元元年戊戌,公四十七歲。任左拾遺。……六月,房琯因賀蘭進明譖,貶為邠州刺史。公坐琯黨,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是秋,嘗至藍田縣訪崔興宗、王維。冬末,以事歸東都陸渾莊,嘗遇孟云卿于湖城縣城東。[4]69
《舊唐書·房琯傳》記載:
上由是惡琯。……憲司又奏彈董庭蘭招納貨賄,琯入朝自訴,上叱出之,因歸私第,不敢關預人事。諫議大夫張鎬上疏,言琯大臣,門客受贓,不宜見累。二年五月,貶為太子少師。[6]2076
房琯五月十日被貶為太子少師,杜甫五月十六日授左拾遺。因杜甫與房琯為布衣之交,杜甫向肅宗“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親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甫謝,且稱:‘琯宰相子……酷嗜鼓琴,庭蘭托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污。……’然帝自是不甚省錄”[7]3588。
“墨制”是指皇帝避開中書、門下二省用墨筆親書詔令。肅宗不經外廷蓋印就直接向杜甫下達親自書寫的遣返詔書,說明他對杜甫非常生氣,很有可能在廷上匆匆草就。杜甫對這一突然下達的詔命毫無思想準備,感到茫然失措。但他在被遣送鄜州省家路上作長詩《北征》,仍在憂慮國事、憂君失誤,東坡稱贊“《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3]406。在杜甫看來,只要正義就要堅持進行不妥協的斗爭,但在肅宗看來,這種做法不僅違背圣心,更是站在自己的對立面了。
乾元元年,肅宗出賈至汝州,貶房琯邠州,下除高適太子少詹事,劉秩、嚴武等均被逐。朝中發生這么多大事,不少舊臣受到處理,身為諫官,杜甫感覺自己有諫諍的責任。正如其《題省中院壁》所云:“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他認為,如果諫官無忠言以補天子,便是愧對皇恩。
杜甫初為諫官,便以房琯罷相之事上疏,這觸犯了肅宗內心的禁忌。肅宗先登基再通告玄宗的做法有違儒家血緣倫常,他要借賀蘭進明讒毀房琯之故罷免房琯以平息非議。房琯罷相是肅宗對玄宗舊臣有計劃的清洗,杜甫卻抓住此事上疏力抗,由此得罪肅宗。這并不是杜甫迂腐,而是他看清了肅宗面目后的深思熟慮之舉,是其一貫的忠勇正義的行為。他知道房琯恢復相位已不可能,但他偏要不可為而為之,這并非不合時宜,而是要表明態度,阻止肅宗繼續迫害大臣和上皇。廣德元年(763年),他在《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中仍說“太子即位,揖讓倉卒”,委婉批評太子繼位違背倫常。《舊唐書·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七月“是月甲子(十三日),上即皇帝位于靈武”。《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十五載八月“癸巳(十二日),靈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十六日),上用靈武冊稱上皇,詔稱誥。己亥(十八日),上皇臨軒冊肅宗”。也就是說,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即位靈武,玄宗八月才知情,有一個月的時間天下有二主。杜甫的清醒,正是肅宗懼怕的。因此,在同年閏八月初一,杜甫被肅宗墨制放歸鄜州省家。由此開始,他與肅宗漸行漸遠。從《北征》“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之句看,他內心對皇帝的疏遠感到惶恐不安。
杜甫直言極諫的執著,讓肅宗煩惱,因為這樣對自己清除舊臣、樹立權威不利。當時上皇還健在,舊臣與之多少有瓜葛往來,這是肅宗心病,必須處理。乾元元年杜甫出華州后,同年八月肅宗又將李白流夜郎。當時被處理的官員基本上不是玄宗舊臣,便是永王李璘之人,唯有杜甫出自東宮,但他卻沒有站在肅宗陣營。他去京時作《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殘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他撫今追昔,感慨萬千。時值朝廷用人之際,自己卻遭受貶謫,由此更可看出他內心的無限悲涼。此詩仇注引元人趙汸《杜詩選注》:“公雖遭讒黜,而終不忘君,……豈為一身計耶?”又引清人顧宸《杜詩律注》:“此公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節。曰‘移官豈至尊’,不敢歸怨于君也。當時讒毀,不言自見。”[3]481杜甫一生遵從君臣大義,無只字怨君,只能自嘲“不怪君王,怪我才不合道”。詩人從此以后,再沒有回到長安。
四是至德二載十一月杜甫自鄜州歸京,繼續任左拾遺,至乾元元年六月突然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君臣關系惡化。
杜甫出京前,作《酬孟云卿》,“但恐天河落”之句暗含被貶的原因。是年肅宗處理大批舊臣,筆者推測他又會上疏阻攔。他在朝廷目睹肅宗對上皇不孝的做法,剛到蜀中便以春秋筆法寫下《杜鵑行》,微言大義對肅宗進行含蓄的批評和質疑,可見他立場之鮮明、態度之堅決。
君臣關系是封建時代最重要的政治關系,左遷華州后杜甫也可能托人做過疏通,努力修復君臣關系,但沒有成功。杜甫有《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云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特意注明“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于何事,詩人沒有詳說。杜甫詩集是詩人自編,他在編訂時對自己重要的人生關節,都有“自注”,由此可見“之東都”一定不是小事,如仇兆鰲所言“此公生平事君交友立朝大節也”[3]25。按人之常情推測,當時詩人內心最焦慮的應該是修復自己與皇帝的關系,有《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為證。杜甫在冬至懷念同事及左掖生活,流露出對過去朝中生活的無限眷戀,以及對當前處境的愁悶。懷念同僚在很大程度上是懷念朝廷。此時,杜甫被貶華州已有半年,但君臣關系沒有緩和的跡象。在湖城(河南靈寶)劉顥宅宴上,他醉酒作詩“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款曲”須互通,“艱難”尚努力。他期盼“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但只有“天開地裂”才能溝通長安之路,這實在太難。“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時過境遷,合轍難求,暗喻君臣關系難以修復。但當他從洛陽轉回華州不久,卻被無情地罷官了。估計肅宗得知有人求情后,更為發怒。
乾元元年冬末,他急于往東都見何人?依筆者推測,很可能是高適。劉開揚《高適年譜》記載:
758年,戊戌,肅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復以載為年。高適五十五歲。貶官為太子少詹事,赴洛陽。適后有《同河南李少尹畢員外宅夜飲時洛陽告捷遂作春酒歌》。五月,過睢陽,有《罷職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夏日,在洛陽,有《同群公宿開善寺贈陳十六(章甫)所居》詩。又有《送崔錄事赴宣城》《送桂陽孝廉》,似亦洛陽之作。
759年,己亥,肅宗乾元二。高適五十六歲。五月,出為彭州刺史,有《赴彭州山行之作》。于蜀山中為亂軍劫奪。九月,史思明入洛陽。十月,引兵攻河陽城,李光弼率諸將敗思明將周摯,擒徐璜玉等,思明遁去。十一月,適有《同河南李少尹畢員外宅夜飲時洛陽告捷遂作春酒歌》。又《同鮮于洛陽于畢員外宅觀畫馬歌》,亦是年冬作。至彭州,有《謝上彭州刺史表》。十二月有《贈杜二拾遺》詩,時杜甫初至成都,寓居草堂寺中。[14]
由上可知,杜甫去洛陽時,高適正以太子少詹事的身份分司東都。他有可能是去求高適幫忙,去之前特意寫了《寄高三十五詹事》,中有“時來如宦達,歲晚莫情疏”之語,但從“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來看,他還沒有收到高適的回信,所以他直接去洛陽求見。在洛陽,高適很可能答應幫助他,故乾元二年年底,杜甫一到成都便收到高適的《贈杜二拾遺》,得到物質幫助和精神慰藉,“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外復何言”。這相互形成的鎖鏈,或可解“冬末以事之東都”之謎。當然這僅僅是根據杜甫與高適關系的推測,能否成定論,尚待新材料進一步考論,此處只是拋磚引玉。
五是乾元二年(759年)立秋,杜甫毫無征兆地去官。
杜甫華州去官,后人皆言“公有高蹈之志”,因其與朝廷不合作的態度。但筆者認為,“高蹈之志”與他不符,杜甫不是道家人物,也沒有雜家思想,他是純儒。即便流放秦州,他仍有《蕃劍》述志:“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趠,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是年,貶邠州一年的房琯被召回,“詔褒美之,征拜太子賓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15]。貶巴州的嚴武也在上元元年(760年)遷東川節度使,次年擢成都尹、劍南節度使。可見,肅宗對琯黨的處罰并不嚴,是給了出路的。
但杜甫則不同,這一年他反而徹底失官了。為什么?因為在華州他堅守初衷,仍在含蓄地批評肅宗。如《洗兵馬》作于鄴城大戰前,當時王師已掃清外圍,詩人對未來河清海晏充滿期待。但我們仔細品味相關詩句,可以發現,詩人并不止于“贊”,而是明“頌”暗“刺”,明“贊”暗“諷”。經歷華州之貶,遭受切膚之痛,杜甫已經深知肅宗為人。由“鶴禁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蛇曉”之句,開始轉向“刺”。實際上玄宗自蜀還京后從未有如此待遇,詩中故意這樣描述豈不是“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之句再提房琯事,又是明“贊”暗“諷”。蕭丞相、張子房分別代指房琯、張鎬,二人都有輔宰之才,但都被罷相了。“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之句,更是在諷刺肅宗不明忠直之臣,隨意刑罰。此詩雖然是頌詩,但詩人沒有“空頌”,對肅宗有美有刺。“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與“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形成鮮明對比,揭示肅宗對待大臣的不同態度:肆意賞賜自己人,處理父親舊臣時卻十分殘酷。末句“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表達了對肅宗治國的強烈否定。《錢注杜詩》云:“《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錢謙益感受到了詩人之心,明確指出:“此公一生出處,事君交友之大節,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則以房琯之生平,為唐史抹殺,而肅宗之逆狀,隱而未暴故也。”[16]67肅宗顯然也感受到了《洗兵馬》中詩人的良苦用心,因此很快將其罷官。環視琯黨成員,尤其是朝廷高層,唯有杜甫堅守君臣大體,秉持忠義之氣,容不下破壞人倫秩序的事。所以,稱杜甫是唐代的孔子,稱杜詩是“詩史”,皆是中肯的評價。
六是上元元年(760年)杜甫被流放成都,作三首“杜鵑詩”譴責肅宗。
在蜀地時,杜甫罷官已過數月,仍不能釋懷,作《杜鵑行》,借古蜀神話追記肅宗不盡人子之道: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眾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愿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干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于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教學傳遺風。乃知變化不可窮,豈知苦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12]636
上元二年(761年),杜甫再作《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里,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惟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復何所無,萬事反復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12]116
《錢注杜詩》云:
上元元年七月上皇遷居西內。高力士流巫州,置如仙媛于歸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皇不懌,因不茹葷,辟谷,浸以成疾。詩云“骨肉滿眼身羈孤”,蓋謂此也。移杖之日,上皇驚,欲墜馬數四。高力士躍馬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又令輔國攏馬,護持至西內。故曰“‘雖同君臣有舊禮”,蓋謂此也。[12]117
大歷元年(766年),杜甫在云安(重慶云陽)再作《杜鵑》。此時代宗已即位,努力糾正父親錯誤,撥亂反正,以工部員外郎召還杜甫。《杜鵑》乃是杜甫還京途中寫給代宗的頌詩。杜甫之所以去蜀,是因為他要赴京受職。《年譜》此處說嚴武暴卒后杜甫失去依靠去蜀,完全錯誤。全詩如下: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云安有杜鵑。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馀,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喂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圣賢古法則,付與后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12]168
這三首“杜鵑詩”均采用了“詩史”筆法,深含春秋隱意,以蜀人悲杜鵑啼血,杜宇禪位傳說,托寓上皇與肅宗之間的恩怨。作前兩首時,肅宗在位,杜甫雖在流放中仍堅持批評。他即使遠離政治中心,也心系朝廷,堪稱唐代屈子。最后一首作于代宗時期,詩旨已完全不同。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二,寶應元年(762)建巳月:“甲寅(五日)上皇崩于神龍殿。……丁卯(十八日)上崩。”[16]由此可知,大歷元年的《杜鵑》是寫給代宗的贊美詩。這首詩充分體現了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沉郁頓挫”是一種貴族情懷,“頓挫”即上下有序、尊卑錯落的儒家社會秩序,如“行飛與跪乳,識序與知恩”。詩人此時已獲代宗啟用,正還朝接受郎官,遺憾“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一片忠謹之意。此詩寫于去蜀后病阻云安,不能進京報天子恩遇,正是“頓挫”之詩。可惜,國內學者對“頓挫”的理解存在不小的誤解。
對比前兩首,第三首“杜鵑詩”在贊美代宗的同時,也是在譴責肅宗,一褒一貶,詩人多么深婉頓挫。由此我們大致可以能得出如下邏輯:杜甫疏救房琯是表象,反對肅宗清洗舊臣才是目的。他以疏救房琯表達對玄宗的支持,也就引發對肅宗擅自繼位的質疑。杜甫最重儒家血脈親情,將違背倫常看作“亂源”,在華州他以《洗兵馬》批評肅宗不孝,這些做人原則,無論是杜甫擔任左拾遺期間,還是在華州參軍任上,都是他實現“再使風俗淳”的社會理想所要堅持的。也正因為如此,他才遭到肅宗步步迫害。杜甫憂心如焚的“亂世”,包含兩方面:一是安史之亂,二是人主不盡孝道。百善孝為先,講的是秩序;萬惡淫為首,說的是亂的根源。這兩條肅宗與安祿山都觸犯了。大逆不道與忤逆不孝,皆是違背天下秩序之禍首,這是杜甫終身批判的,所以他自然也不會見容于肅宗。但杜甫又特別尊崇君臣禮義,不能直接譴責皇帝。即使肅宗強逼玄宗退位的事實也不能提,只能將一腔憂憤化為疏救房琯的抗顏直諫。杜甫之心,別人不知,肅宗卻會感知,故有罷官處罰。詩人之苦,“后世罕有知之者”。這就是肅宗對所有“琯黨”都予平反,唯獨不放過杜甫的根本原因。在華州,他“獨立萬端憂”,卻諱言不能述。
五、華州罷官后杜甫遭遇流放
杜甫華州罷官后,他去往何處,為何不能回長安呢?這又是一個關節問題。他不能回去,一如“罷官亦由人”那樣無奈,這是流放,去哪里由不得他,自然未能再回長安。杜甫《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一云:“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其中“因人作遠游”已隱諱道出他遭遇了類似屈原那樣的放逐,這是關乎他日后成為“詩圣”的重要內在因素。
關于流放的去向,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這樣分析:“是時東都殘毀,既不可歸,長安繁侈,又難自存。”并舉杜甫在秦州時所作《寄高岑三十韻》中的詩句“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為證,認為居秦州是因其侄杜佐居東柯,那里雨水充足,“秋禾有收”,“因攜家徙居焉”[4]169。聞氏延續《新唐書》的“辭官逃荒說”,故有“惟秦州得雨”適合居家的認識。這種認識將詩人遭遇放逐簡單化地理解為為了生存,沒有明白“無錢居帝里”乃詩人采用春秋筆法“為尊者諱”。“得雨”,真是秦州有大自然之“雨”嗎?真是為了生存去秦州嗎?這只是字面意思,筆者以為必須回到復雜的政治斗爭中看問題,從君臣關系分析中找到隱含的答案。
杜甫華州罷官后,皇帝為何不讓歸京?原因很簡單,怕他回京生事端,議論自己清洗舊臣、穩定政權的策略。長安不準回,杜甫只能流去秦州,故才有“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之嘆,一種無奈莫可言述。杜甫的流放是被指定去處的,秦州自漢代以來即行役戍邊的苦寒之地,羌戎雜居,杜詩稱其為“天末”,指中原之外,即為天邊,有懲罰之意。他在《秦州雜詩二十首》中形容秦州“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和杜甫一樣被放逐秦州的,還有長安高僧贊上人。二人交往頻繁,相互慰藉。杜甫寫過三首詩送他,其中《宿贊公房》自注“京中大云寺主,謫此安置”,詩人自己又何嘗不是被“謫”呢?仇注引趙汸《杜詩選注》:“贊,亦房相之客,時被謫秦州。”[9]592-593兩相參證,二人均“因人”“因事”去秦州,或為肅宗的統一安排。
到秦州不久,杜甫又被迫前往兩百里外的同谷。他在《別贊上人》中感慨“我生苦飄蕩,何時有終極”,他不愿再流,可肅宗迫害又至,不知何時會停止。他在《發秦州》中說“生事不自謀”,“惘然難久留”,這些奔波都不是自己的本意。在同谷他有《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其中“中原無書歸不得”之語感嘆命運難自主。入蜀也是肅宗的安排,杜甫有《發同谷縣》,“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深含微意。詩人由華州到秦州轉同谷再到蜀中,故言一年“四行役”,離京城越來越遠。誰役使他?詩人沒有說,我們不難推測應是肅宗加害。以上推論可知,華州去官非本愿,秦州流放屬無奈,入蜀也非他自主決定。此時正逢國家多事之秋,用人之際,不反對肅宗的王維、岑參均在數月內得到遷升,杜甫卻一步一步遠離政治中心。由此可見,他與肅宗的君臣關系不是一般糟糕,這是導致他被罷官的根本原因。
后來,杜甫又補京兆府功曹。《舊唐書》載:“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新唐書》載:“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朝廷召補杜甫京兆府功曹在何年?從肅宗對他的態度來看,應在肅宗駕崩后,代宗寶應元年征召。杜甫有《奉寄別馬巴州》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寶應元年(762年)七月杜甫送嚴武至綿州,嚴武還朝任京兆尹,即為他請此官。因吐蕃滋擾,杜甫應召阻滯閬州,無法出川。廣德二年(764年)正月,嚴武再督川,改請節度參謀。杜甫十分欣慰,寫下《奉待嚴大夫》,從“一生襟抱向誰開”之句看,只有嚴武最了解他的志向。
杜甫雖然遭遇流放,歷經苦難,但他始終沒有怨君失志。在同谷,他有“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鳳凰臺》)的號呼,聲明自己不棄理想,不做清流。流放蜀中時,他不怨天尤人,反而詩思壯闊。《贈蜀僧閭丘師兄》中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他對皇恩只有感激,無個人怨悱。在苦難中,他沒有頹廢,從“窮愁一揮淚,相遇即諸昆”“漠漠世界黑,驅車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的詩句中,可見少陵曠懷。
杜甫遭遇罷官流放,千載無人言述,無論錢謙益還是仇兆鰲,或許沒有意識到,或許故意疏忽。我們抽絲剝繭發現其中真相應該是:在古代血緣倫常政治中,人倫忠孝是執政之基,杜甫對于肅宗不敬上皇、違背倫理,及由此引發對肅宗政權合法性的質疑,戳中了肅宗的痛處,導致他受迫害,在所有琯黨平反后,他反而被罷官流放。但《新唐書》與《舊唐書》均為尊者諱言,使“詩圣”之痛苦千古沉冤。
綜上,杜甫華州去官實為“罷官”,再流放隴蜀,直到肅宗駕崩,代宗繼位,他才在嚴武的大力舉薦下得以復官,相當于獲得朝廷正式平反。這期間,杜甫有四年時間無官職,以后又經幕府參謀、蜀中軍功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入朝就職。終因途中消渴病發,被阻夔州,但他仍赤心不改,期待還朝。詩人因糖尿病銷蝕身體,不能還朝履職,最后在一條孤舟中帶著無盡遺憾與憂傷離世。
杜甫的不幸遭遇,成就了他在文學史上的“詩圣”地位。正是因為華州罷官,流放隴蜀,杜甫后半生詩歌轉入春秋筆法的隱諱,成為“詩史”。詩人的不幸遭遇強化了杜甫詩歌的“沉郁頓挫”。這里說一下筆者對“詩史”的理解,“詩史”決非文學史泛解的現實主義詩歌,而是微言大義、春秋筆法,具有四個標準,一是言王事,二是語詞曲折意含褒貶,三是讓亂臣賊子懼,四是為尊者諱。我們理解杜詩中稱為“詩史”的詩,當圍繞這些標準。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華州罷官,隴蜀流放,成就了“詩史”,成就了這位五百年一遇的偉大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