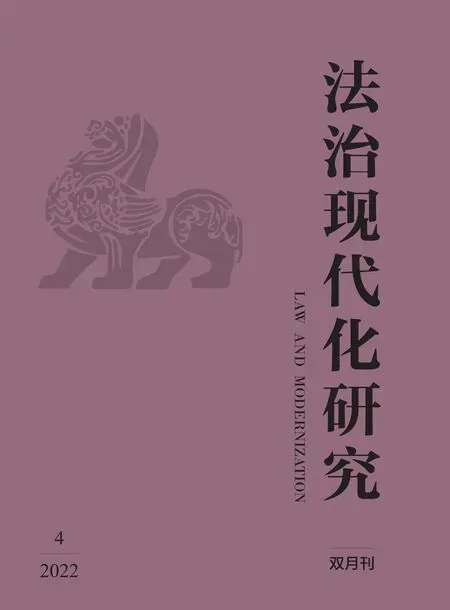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理論批評與實(shí)踐反思
——兼論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決定權(quán)之適用
孔祥穩(wěn)
一、 引 言
在有關(guān)個人信息保護(hù)模式的討論中,經(jīng)由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證立并闡發(fā)的“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是最為重要的理論路徑之一。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以保護(hù)人格自由發(fā)展為目標(biāo),將個人信息保護(hù)置于“人的尊嚴(yán)”視域下,構(gòu)建起以個人控制為中心的保護(hù)體系。這一理論在世界范圍內(nèi)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至今依然在持續(xù)形塑著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個人信息保護(hù)制度,諸如歐盟的《通用數(shù)據(jù)保護(hù)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GDPR)和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個人信息保護(hù)規(guī)則都被認(rèn)為較多地承襲了這一理念。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在我國也得到了學(xué)術(shù)界的高度關(guān)注。一方面,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價(jià)值被充分肯認(rèn)。在公法層面,有觀點(diǎn)提出,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作為一種憲法未列舉基本權(quán)利,適宜作為公法上信息保護(hù)的理論基礎(chǔ);(1)參見姚岳絨:《論信息自決權(quán)作為一項(xiàng)基本權(quán)利在我國的證成》,載《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4期;趙宏:《從信息公開到信息保護(hù):公法上信息權(quán)保護(hù)研究的風(fēng)向流轉(zhuǎn)與核心問題》,載《比較法研究》2017年第2期。在私法層面,亦有觀點(diǎn)認(rèn)為個人信息權(quán)的本質(zhì)就是個人信息自決,并主張確立個人對其信息的自主控制權(quán)。(2)參見王利明:《論個人信息權(quán)的法律保護(hù)——以個人信息權(quán)與隱私權(quán)的界分為中心》,載《現(xiàn)代法學(xué)》2013年第4期;楊立新:《個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權(quán)利——對〈民法總則〉第111條規(guī)定的“個人信息”之解讀》,載《法學(xué)論壇》2018年第1期;王成:《個人信息民法保護(hù)的模式選擇》,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9年第6期。另一方面,對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批評也一直存在。(3)參見劉金瑞:《個人信息與權(quán)利配置——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反思和出路》,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有研究者提出,公法意義上的信息自決權(quán)是“在國家行為領(lǐng)域沒有必要的新主張”,私法上的信息自決權(quán)則是“在私人行為領(lǐng)域危險(xiǎn)的新主張”。(4)楊芳:《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理論及其檢討——兼論個人信息保護(hù)法之保護(hù)客體》,載《比較法研究》2015年第6期。
在實(shí)定法層面,我國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規(guī)定,“個人對其個人信息的處理享有知情權(quán)、決定權(quán),有權(quán)限制或者拒絕他人對其個人信息進(jìn)行處理;法律、行政法規(guī)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學(xué)界對該條文的闡釋不可避免地與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相聯(lián)系,或是認(rèn)為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構(gòu)成決定權(quán)的法理基礎(chǔ),(5)參見龍衛(wèi)球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hù)法釋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200頁。或是提出二者在權(quán)利性質(zhì)、權(quán)利對象、權(quán)利內(nèi)容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應(yīng)作出區(qū)分。(6)參見張新寶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hù)法〉釋義》,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51-352頁。上述理論與實(shí)踐上的分歧表明,系統(tǒng)澄清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相關(guān)理論,并在此基礎(chǔ)上討論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規(guī)定的決定權(quán)應(yīng)如何適用仍有必要。
本文旨在通過對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本源——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人口普查案”的梳理,闡明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本身存在的理論局限,以及在中國法上將其實(shí)定法化面臨的困境。本文試圖證明的是,個人信息自決更傾向于一種維護(hù)個人自主性的抽象理念,而不應(yīng)將其實(shí)證化為個人對其信息享有的控制和支配權(quán)。個人信息保護(hù)涉及復(fù)雜和多樣的法益,試圖用自決理念來實(shí)現(xiàn)統(tǒng)攝并不是可行的路徑。對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決定權(quán)”的解釋應(yīng)當(dāng)尋求更加本土化的方案,為“自決”尋找更加準(zhǔn)確和合理的定位。
二、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證立及其淵源
從理論脈絡(luò)上看,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肇始于德國,但并非德國基本法明確列舉的權(quán)利,而是通過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的判決證立。在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1983年“人口普查案”后,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正式得以確立并產(chǎn)生重大影響。梳理其證立過程及背后的淵源,有助于更準(zhǔn)確地認(rèn)識和把握該項(xiàng)權(quán)利。
(一) “人口普查案”的緣起
1982年3月,德國聯(lián)邦政府公布了《有關(guān)人口、職業(yè)、住宅、工作場所調(diào)查之法律》(即“人口普查法”)。(7)參見BVerfGE 65, 1, Rn. 1.該法第1條至第8條規(guī)定了普查的內(nèi)容和方式,其中第1條規(guī)定了全面實(shí)施人口、職業(yè)、住宅、工作場所等方面的信息普查,第2條至第4條規(guī)定了普查的具體內(nèi)容,(8)該法所規(guī)定的普查內(nèi)容極為廣泛,如僅在人口和職業(yè)項(xiàng)上,就需要統(tǒng)計(jì)姓名、住址、電話、性別、出生日期、家庭情況、宗教、國籍、住所、主要生活費(fèi)用來源、從事營業(yè)活動與否、學(xué)業(yè)、專業(yè)、就業(yè)單位的名稱和地址、上班或上學(xué)時(shí)主要乘坐的交通工具及所耗費(fèi)時(shí)間等信息。第5條至第8條規(guī)定了普查的具體方式。該法第9條規(guī)定了信息的傳輸和二次利用,其中第1款規(guī)定,根據(jù)該法收集的信息可以用來與相關(guān)登記冊比對,校正登記冊所載信息,但不能被用來針對特定個人采取不利益措施;第2款規(guī)定,為合法完成職權(quán)范圍內(nèi)行政任務(wù)之必要,可將信息在各部門間傳輸和使用;第3款規(guī)定,為了區(qū)域計(jì)劃、測量活動、鄉(xiāng)鎮(zhèn)計(jì)劃及環(huán)保等目的,可將信息傳輸給鄉(xiāng)鎮(zhèn)和鄉(xiāng)鎮(zhèn)協(xié)會使用;第4款規(guī)定,為了學(xué)術(shù)目的,可將信息傳輸給相關(guān)公務(wù)人員使用;第5款至第8款規(guī)定了傳輸?shù)木唧w要求。(9)參見BVerfGE 65, 1, Rn. 3-55.
起草法案的聯(lián)邦政府對普查目的作了說明:人口、職業(yè)和工作場所的調(diào)查是普查的核心,居民的人口狀況、居住空間分配以及與人口流動特征相關(guān)的經(jīng)濟(jì)活動信息,是聯(lián)邦、各州、各鄉(xiāng)鎮(zhèn)制定經(jīng)濟(jì)政策必不可少的基礎(chǔ);一些社會組織,如黨派團(tuán)體、行業(yè)組織、學(xué)術(shù)組織也都依賴上述調(diào)查結(jié)果開展工作;進(jìn)一步的統(tǒng)計(jì)或隨機(jī)抽查類工作也需要在上述信息的基礎(chǔ)上展開。同時(shí),這些信息也構(gòu)成許多行政目的的基礎(chǔ)。例如,居民人數(shù)對各州在聯(lián)邦參議院票數(shù)的分配、聯(lián)邦議會選區(qū)的劃分、財(cái)稅分配、鄉(xiāng)鎮(zhèn)議會的規(guī)模等重要事情都具有重大意義。而關(guān)于住宅的調(diào)查統(tǒng)計(jì)反映了特定區(qū)域能夠獲得住宅的情況及結(jié)構(gòu);工作場所的調(diào)查對空間規(guī)劃、區(qū)域規(guī)劃、工作市場政策、交通政策等都具有相當(dāng)價(jià)值。(10)參見BTDrucks. 9/451, S. 7 ff.
憲法訴訟提起人認(rèn)為,該法案侵犯了德國基本法第2條第1款、第1條第1款、第4條第1款、第5條第1款、第13條、第19條第4款規(guī)定的基本權(quán)利,并使得基本法第20條第3款規(guī)定的法治國原則落空,理由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基于基本法第2條第1款和第1條第1款,人口普查應(yīng)遵守匿名要求,所收集的信息應(yīng)確保不能回溯至個人。若匿名無法保障,則相關(guān)信息可能基于其他目的而被任意使用,個人的自決權(quán)可能被剝奪,成為他人意志行使和控制的客體。在現(xiàn)有的技術(shù)水平下,簡單的數(shù)學(xué)方法即可攻克看似牢不可破的匿名化,完成對個人身份的再識別,尤其是當(dāng)前數(shù)據(jù)收集和處理的條件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統(tǒng)計(jì)機(jī)構(gòu)已發(fā)展成為數(shù)據(jù)中心,各級機(jī)關(guān)也建立了包含大量數(shù)據(jù)的資料庫。這導(dǎo)致人口普查信息在相同計(jì)算機(jī)和相同程序下,由相同人員加以處理,就如同其他國家機(jī)關(guān)自己的信息一般。數(shù)據(jù)接收方所掌握的大量數(shù)據(jù)降低了重新識別個人的門檻。這些變化使得建立每個人全面細(xì)致的畫像成為可能,國民將逐漸喪失私領(lǐng)域而成為“透明人”。與此同時(shí),該法對許多特定的重要問題,如信息處理的目的、范圍等保持緘默,不符合聯(lián)邦憲法法院確立的“重要性要求”。該法規(guī)定的信息收集方法缺乏必要性,違反了禁止過度原則。若在匿名、自愿狀態(tài)下可以實(shí)現(xiàn)同樣目的,就不該采用實(shí)名、強(qiáng)迫的方式。
其二,訴訟提起人特別提出,法案第9條存在嚴(yán)重的合憲性問題。其中,第1款規(guī)定可根據(jù)統(tǒng)計(jì)信息矯正登記冊,違反了憲法上權(quán)限分配規(guī)則內(nèi)涵的數(shù)據(jù)分散儲存要求,致使統(tǒng)計(jì)信息與行政執(zhí)法信息相結(jié)合。這可能使得被調(diào)查人因?yàn)樘峁┬畔⒌姆ǘx務(wù)和登記冊校對而陷入必然違法的困境,從而違反了法治原則。第2款至第4款違反了“明確性要求”,因?yàn)槠鋵π畔⒔邮照吆投卫媚康亩贾蛔髁四:?guī)定,難以為公民所理解。第2款和第3款對禁止傳輸?shù)男畔⒅?guī)定也不夠明確。由于使用目的不確定,所有信息都可能單獨(dú)或與其他信息相結(jié)合而造成當(dāng)事人無法預(yù)見的不利益。
其三,人口普查侵犯了基本法第4條第1款的宗教信仰自由,因?yàn)樵摲ㄒ蟮怯涀诮虉F(tuán)體的成員歸屬,同時(shí)也侵犯了基本法第5條第1款的言論自由,因?yàn)檫@一權(quán)利保護(hù)不披露某些事實(shí)的自由。此外還因國家機(jī)關(guān)進(jìn)入房屋或房主被迫開門而侵犯了基本法第13條,即住宅自由。
其四,由于信息收集者的范圍和信息使用目的的模糊性,其實(shí)質(zhì)上剝奪了公民對于“何人,得以在何處,以何種方式,出于何種目的接觸和使用其個人信息”的知情權(quán)。被傳輸?shù)男畔⒃谌找鎻?fù)雜的網(wǎng)絡(luò)中傳輸,難以被控制。這將造成基本法第19條第4款規(guī)定的法律保護(hù)落空,當(dāng)事人難以尋求救濟(jì)。(11)參見BVerfGE 65, 1, Rn. 91-99.
(二) 聯(lián)邦政府的抗辯
在審理過程中,法院向有關(guān)各方及聯(lián)邦和州的數(shù)據(jù)保護(hù)專員提出了人口普查法的立法目的、目的限制原則的憲法意義、基于行政執(zhí)法目的統(tǒng)計(jì)信息披露是否應(yīng)當(dāng)被允許、立法作更細(xì)致規(guī)定的必要性、全民普查與比例原則的兼容性、是否有影響更輕微的執(zhí)行方法、禁止信息傳輸對公共利益的影響等問題。面對訴訟提起人的主張和法院的問題,聯(lián)邦和絕大部分州政府都認(rèn)為人口普查法是合憲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作為最常用的信息來源之一,對于觀察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fàn)顩r,計(jì)劃和準(zhǔn)備相應(yīng)決策、措施和項(xiàng)目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面對復(fù)雜的調(diào)查統(tǒng)計(jì)活動,不可能在法律中對所有目的和方案作出準(zhǔn)確、具體的說明。可以確定的是,人口普查法規(guī)定的調(diào)查內(nèi)容沒有涉及不能侵犯的私領(lǐng)域,相應(yīng)的保護(hù)要求也較之前的同類立法更高。
其二,人口普查法并不侵犯基本法第2條第1款和第1條第1款所規(guī)定的一般人格權(quán)。人格與群體相連,內(nèi)含社會關(guān)聯(lián),這排除了個人對其個人形象所享有的全面自決,國家并不自始被禁止獲取個人信息。立法機(jī)構(gòu)可以權(quán)衡個人保持匿名的利益與公眾的信息利益。但在利益衡量時(shí)必須考慮到,人口普查是國家有計(jì)劃地采取行動的前提條件。根據(jù)基本法第20條第1款和第28條第1款的“社會國家”要求,政府和議會對信息的利益是合憲的。
其三,人口普查法符合比例原則,不構(gòu)成過度侵害。面對錯綜復(fù)雜的問題,立法者擁有裁量空間,司法應(yīng)予尊重。人口普查雖涉及私領(lǐng)域,但影響非常輕微,相關(guān)信息累積起來也不會對私領(lǐng)域造成重大侵害。信息收集通過表格進(jìn)行,并不會形成聯(lián)結(jié),統(tǒng)計(jì)部門的數(shù)據(jù)庫未接入外網(wǎng),也防止了信息被濫用。此外,立法已經(jīng)考慮到技術(shù)變化和國民的信息保護(hù)意識,減少了問題數(shù)量,增加了防范信息濫用的措施。國家機(jī)關(guān)不應(yīng)被假定為一定會濫用信息,而應(yīng)被假定為會遵守信息保護(hù)要求。就可替代性而言,倘若可通過其他手段(如登記冊、健康和養(yǎng)老保險(xiǎn)檔案、土地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庫等)獲取相應(yīng)信息,則可以放棄人口普查。但這些數(shù)據(jù)庫錯誤極多,且使用這些信息的前提是使用同一識別信息,這可能造成更高的風(fēng)險(xiǎn)。另外,基于對信息準(zhǔn)確性、全面性的要求,抽樣、自愿的調(diào)查難以實(shí)現(xiàn)目的,因而人口普查是必要的。
其四,就信息傳輸而言,從基本法中無法得出為特定行政目的所收集的信息永遠(yuǎn)只能與該目標(biāo)聯(lián)結(jié),而不能作他用的要求。統(tǒng)計(jì)信息亦是如此。統(tǒng)計(jì)信息并不只供特定目的使用,而是為未來的規(guī)劃和行動這一整體性目的發(fā)揮作用。這一目的主要受到數(shù)據(jù)保護(hù)法和憲法上一般人格權(quán)的限制。國家的信息行為必須具備一定彈性,若目的限制過于僵硬,會導(dǎo)致國家無法對難以預(yù)見的新問題作及時(shí)反應(yīng);在憲法上,國家合法所得的信息并不始終受到原使用目的之限制,基本法第35條第1款的職務(wù)協(xié)助也可為目的外使用提供形式上的依據(jù),聯(lián)邦數(shù)據(jù)保護(hù)法等法律則可提供更具體的法律依據(jù)。目的限制原則的意義被高估了,聯(lián)邦和各州的信息保護(hù)法已經(jīng)放棄了對目的背離的一般性禁止,而更多通過比例原則來規(guī)范。只有對特別的信息,如公務(wù)秘密等才優(yōu)先適用目的限制原則。
基于此,人口普查法第9條第1款明確規(guī)定了信息傳輸用于更正登記冊這一必要目的,不屬于侵害私人利益的目的背離。第9條第2款至第4款亦如此,第2款規(guī)定了必須基于合法的行政任務(wù)之必要才可傳輸,第3款和第4款明確了二次利用的目的。某些特定信息也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傳輸范圍之外。與此前的立法相比,該法已經(jīng)強(qiáng)化了防止濫用的要求,體現(xiàn)了立法者對比例原則的重視。此外,聯(lián)邦政府還提出,當(dāng)事人具有提供信息的義務(wù)不構(gòu)成強(qiáng)迫自證其罪,法案符合“重要性要求”和法律保留原則,亦不存在影響更輕微的實(shí)施方法。(12)參見BVerfGE 65, 1, Rn. 101-118.
(三) 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的判決
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在確認(rèn)該案的可受理性后,(13)法院提出,盡管人口普查法尚未付諸實(shí)施,調(diào)查統(tǒng)計(jì)尚未開始,但當(dāng)法案執(zhí)行可能對相應(yīng)權(quán)利造成難以彌補(bǔ)的處分時(shí),應(yīng)允許當(dāng)事人在執(zhí)行行為開始前提起訴訟。同時(shí),基于憲法法院的補(bǔ)充定位,應(yīng)要求當(dāng)事人先窮盡其他救濟(jì)途徑,如針對執(zhí)行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但這可能導(dǎo)致憲法法院與行政法院判決相爭論,行政法院的判決之間也可能相互矛盾,影響法律安定性。這不僅不利于減輕憲法法院的負(fù)擔(dān),還可能造成審判壓力,因此應(yīng)允許當(dāng)事人提起憲法訴訟。參見Vgl. BVerfGE 65, 1, Rn. 131-133.先對法案是否侵犯基本法規(guī)定的各項(xiàng)具體基本權(quán)利作出了判斷:首先,提供關(guān)于是否加入宗教團(tuán)體的真實(shí)信息,并不違反基本法第4條第1款規(guī)定的宗教信仰自由。雖然宗教信仰自由保護(hù)消極的信仰自由,即就信仰自由保持沉默之權(quán),但這一權(quán)利可基于法定的統(tǒng)計(jì)調(diào)查要求而被限制。基于完成法定任務(wù)之必要,聯(lián)邦被授權(quán)合法地收集宗教團(tuán)體的成員信息。其次,普查行為未侵犯基本法第13條第1款規(guī)定的住宅不可侵犯,因?yàn)檫@一基本權(quán)利保護(hù)的是空間上的私人領(lǐng)域,其針對的是公共機(jī)構(gòu)違背住宅主人的意愿進(jìn)入或在家中停留的行為。調(diào)查和獲取信息無須進(jìn)入住宅或在住宅內(nèi)停留,并未落入該條的保護(hù)范圍。再次,普查行為也不侵犯基本法第5條第1款規(guī)定的表達(dá)自由,因?yàn)楸磉_(dá)自由所保護(hù)的是意見、態(tài)度、觀點(diǎn),而人口普查所收集的信息只是單純的事實(shí)性信息,并未形成意見。(14)參見BVerfGE 65, 1, Rn. 135-142.
在逐一排除了對信仰自由、住宅自由、表達(dá)自由等基本權(quán)利的侵犯后,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將案件的審查標(biāo)準(zhǔn)鎖定為基本法第2條第1款和第1條第1款共同保障的一般人格權(quán):作為自由社會的一員,得以自由地自決行事的人的價(jià)值和尊嚴(yán),是憲法秩序的核心。基本法第2條第1款和第1條第1款所共同保障的一般人格權(quán)對此提供了保護(hù)。鑒于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和隨之而來的對人格的新威脅,這種保護(hù)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盡管迄今為止,司法先例還未能就一般人格權(quán)的內(nèi)容作出結(jié)論性的限定,但它包括了先例中所指出的“個人有權(quán)自行決定,于何時(shí)、在何種范圍內(nèi)披露個人生活相關(guān)事實(shí)”。(15)參見BVerfGE 65, 1, Rn. 144.
聯(lián)邦憲法法院認(rèn)為,在自動化數(shù)據(jù)處理的背景下,一般人格權(quán)需要受到特別保護(hù)。因?yàn)榻柚詣踊幚砑夹g(shù),與特定個人相關(guān)聯(lián)的信息可以被無限期地儲存,并且無論在何時(shí)何地都可被迅速獲取。此外,在綜合性信息系統(tǒng)建立后,信息之間的結(jié)合可以形成完整的人格圖像,但當(dāng)事人卻無法對其正確性和利用方式進(jìn)行控制,這使得信息經(jīng)由公眾壓力而對個人可能形成的影響仍在以不確定的方式擴(kuò)展。在這個意義上,個人自決不僅包括了對作為或不作為的自由決定,還包括了在事實(shí)層面的選擇可能。如果個人無法掌握與其有關(guān)的何種信息會被如何披露和利用,那么個人在自決權(quán)下享有的作出決定和計(jì)劃的自由就可能受到妨礙。
法院指出,當(dāng)個人無法確定,其與眾不同的行為是否會被隨時(shí)記錄并被長期儲存、使用、傳播時(shí),他就只能選擇減少或不采取相應(yīng)行動以免引人注目。例如,若一個人預(yù)料到其參加集會將被當(dāng)局登記在冊時(shí),他就可能放棄行使基本法第8條和第9條保障的集會權(quán)利。這不僅侵害個人自由發(fā)展的機(jī)會,也損害公共利益,因?yàn)樽杂擅裰鞯纳鐣⒃诠竦男袆雍蛥⑴c能力之上,而自決正是其中的功能要素。由此可見,在現(xiàn)代化的數(shù)據(jù)處理?xiàng)l件下,人格的自由發(fā)展以保護(hù)個人信息不受無限制地收集、儲存、使用和傳輸為前提。基本法第2條第1款和第1條第1款為個人自主決定其個人信息的披露和使用提供了保護(hù)。(16)參見BVerfGE 65, 1, Rn. 145-147.
與此同時(shí),法院也承認(rèn)個人對其信息并不享有絕對的、不受限制的控制權(quán)。因?yàn)槿司哂猩鐣傩裕瑐€體的人格是在社會共同體當(dāng)中形成和發(fā)展的。個人信息亦是社會事實(shí)的寫照,并非當(dāng)事人排他所有。在面對重大的公共利益時(shí),個人必須容忍對其信息自決權(quán)的限制。當(dāng)然,對該權(quán)利的限制必須具備合憲的法律基礎(chǔ),并有明確的限制目的及范圍,以符合憲法規(guī)定的明確性要求。此外,限制還必須符合比例原則。考慮到自動化時(shí)代的風(fēng)險(xiǎn),立法者應(yīng)當(dāng)采取更多組織上和程序上的措施來避免人格權(quán)可能遭受的侵害。(17)參見BVerfGE 65, 1, Rn. 148-149.
法院同時(shí)還指出,國家機(jī)關(guān)信息處理行為的影響不能僅依據(jù)信息的類型而定,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信息的利用方式。在自動化條件下,已經(jīng)不再有“不重要”的信息。信息的敏感程度并不僅取決于它是否涉及隱私。確定信息在個人權(quán)利上的意義,必須要了解其使用背景。只有在信息的利用方式和與其他信息結(jié)合的可能性足夠明確時(shí),才能對信息自決權(quán)的合法限制作出判斷。通常來說,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個人化、以非匿名形式收集的個人信息和一般性的統(tǒng)計(jì)信息。前者須由立法明確信息在特定領(lǐng)域中的使用目的,精確規(guī)定信息的使用方法,確保信息對實(shí)現(xiàn)該目的是適當(dāng)且必要的,貫徹目的限制原則,同時(shí)應(yīng)采取對當(dāng)事人影響最小的手段。后者的使用方式和可能的關(guān)聯(lián)在一開始難以確定,故需要在系統(tǒng)內(nèi)對信息的收集和處理加以限制,如明確信息處理的條件,審查信息收集是否會引發(fā)不當(dāng)?shù)臉?biāo)記和分類、是否可以匿名收集,進(jìn)行有效的外部隔離,實(shí)現(xiàn)信息的保密和盡早匿名化等。若為了行政執(zhí)行目的,而傳輸、使用基于統(tǒng)計(jì)目的收集的非匿名、未經(jīng)統(tǒng)計(jì)處理的個人信息,可能構(gòu)成對信息自決權(quán)的侵犯。(18)參見BVerfGE 65, 1, Rn. 150-164.
法院認(rèn)為,人口普查法規(guī)定的信息收集范圍和收集方式基本符合上述憲法要求(除第2條第8款等少數(shù)條款外),其指向重大公共利益,遵守了規(guī)范明確性要求,同時(shí)也未違反比例原則。但為更好地保護(hù)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還需進(jìn)一步補(bǔ)充程序法上的限制,如澄清和指導(dǎo)義務(wù)、盡早刪除識別因子、建立調(diào)查員回避制度、優(yōu)化調(diào)查表內(nèi)容等。與此相反,該法第9條規(guī)定的信息傳輸和二次利用則存在合憲性問題,將為統(tǒng)計(jì)目的而收集的非匿名數(shù)據(jù)用于行政執(zhí)行的目的,使得個人無法確定信息利用的可能性。為統(tǒng)計(jì)目的收集信息和為執(zhí)法目的收集信息在前提條件、保護(hù)方式上都存在差異,將不相容的二者結(jié)合在一起將構(gòu)成違憲。(19)參見BVerfGE 65, 1, Rn. 165-193.
具體而言,第9條第1款因侵害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而無效,該款允許將普查信息與登記冊信息相比較并更正登記冊,屬于將不相容的東西相結(jié)合,與信息收集的預(yù)期目的不符;其內(nèi)容也不夠明確,公民無法理解其可能造成的影響,同時(shí)會導(dǎo)致禁止不利益利用要求的落空。第9條第2款亦因侵害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而無效,因?yàn)槠淙狈γ鞔_的目的規(guī)定,無法判斷數(shù)據(jù)傳輸是否是在實(shí)現(xiàn)目的的必要范圍內(nèi)進(jìn)行的。第9條第3款第1句同樣未明確信息傳輸?shù)木唧w目的,特別是沒有明確信息僅用于統(tǒng)計(jì)還是也用于實(shí)現(xiàn)具體的行政目的;第2句雖將使用目的限定在統(tǒng)計(jì)處理上,但接收信息的鄉(xiāng)鎮(zhèn)由于任務(wù)、組織等各種原因難以實(shí)現(xiàn)這種目的限定。第9條第4款未侵犯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因?yàn)橐涝摽顐鬏數(shù)男畔⒈仨毐3衷趯W(xué)術(shù)目的范圍內(nèi)利用,而大部分學(xué)術(shù)研究并不需要直接涉及個體的信息,信息接收者一般也不具有補(bǔ)充信息實(shí)現(xiàn)再識別的能力,因此保護(hù)強(qiáng)度已經(jīng)足夠。(20)參見BVerfGE 65, 1, Rn. 196-207.
(四)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規(guī)范基礎(chǔ)與歷史淵源
從上述梳理可見,面對國家的信息收集和利用行為,法院在排除了對于具體自由權(quán)的侵犯后,將審查基準(zhǔn)確定為德國基本法第2條第1款和第1條第1款導(dǎo)出的一般人格權(quán),并將其進(jìn)一步具體化為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基本法第1條第1款是德國憲法秩序的基石,其規(guī)范意旨常被解釋為以下兩點(diǎn):其一,人本身即是目的,不得被視為物或者達(dá)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人被“物化”,那么人的尊嚴(yán)就將喪失;其二,人的自主和自決應(yīng)當(dāng)?shù)玫匠浞肿鹬兀诨緳?quán)行使的正當(dāng)范圍內(nèi),若失去自主決定的機(jī)會,人的尊嚴(yán)亦將喪失。(21)參見李震山:《論資訊自決權(quán)》,載李震山:《人性尊嚴(yán)與人權(quán)保障》,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05-240頁。基本法第2條第1款規(guī)定“在不侵害他人權(quán)利,不違背憲法秩序和道德規(guī)范的前提下,人人享有自由發(fā)展其人格之權(quán)利”,其核心內(nèi)涵是“人格的自由發(fā)展應(yīng)以個人自我形塑為核心,確保個人的意見及行為皆由自己決定,并由自己負(fù)責(zé)”。(22)參見前引,李震山文。在這一內(nèi)涵下,基本法第2條第1款既可以作為具體自由權(quán)的補(bǔ)充,對一般行為自由提供兜底性保護(hù),亦可與第1條第1款相結(jié)合,以“組合基本權(quán)”的形式導(dǎo)出一般人格權(quán)。(23)參見王鍇:《論憲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及其對民法的影響》,載《中國法學(xué)》2017年第3期。其中,第1條第1款發(fā)揮著價(jià)值目標(biāo)的導(dǎo)向功能,并補(bǔ)強(qiáng)一般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力度;第2條第1款作為一般人格權(quán)的存身之所,二者聯(lián)結(jié)形成憲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
事實(shí)上,在“人口普查案”之前,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和德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已在多個案件中完成了從上述兩個條款中導(dǎo)出一般人格權(quán)的解釋學(xué)作業(yè),并將基本法第2條第1款和第1條第1款內(nèi)涵的“自主”和“自決”價(jià)值貫注到一般人格權(quán)當(dāng)中,奠定了其權(quán)利底色。一般人格權(quán)圍繞著“精神的、道德的人”和其“內(nèi)在的空間”而建立。在這個范圍內(nèi),個人得以免遭外在干涉和侵犯,實(shí)現(xiàn)人格的自由發(fā)展。(24)參見陳道英:《從德國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看憲法權(quán)利與民事權(quán)利的協(xié)調(diào)》,載《法學(xué)評論》2011年第5期。從功能上看,一般人格權(quán)為那些不屬于基本法具體自由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但對人格發(fā)展又極為重要的要素提供了保障。(25)參見Bj?rn Ahl:《德國保障IT系統(tǒng)私密性和完整性基本權(quán)利的確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對“在線搜查”作出的判決》,載《法學(xué)》2009年第3期。
德國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發(fā)端于民法。聯(lián)邦最高法院于1954年審理的“讀者來信案”被稱為德國一般人格權(quán)第一案。(26)該案的基本案情是,被告在其出版的雜志上刊登了一篇關(guān)于夏赫特(Hjalmar Schacht)的文章,涉及了夏赫特在納粹時(shí)代的作用。夏赫特委托律師發(fā)函要求更正。但被告在進(jìn)行刪改后,直接將律師函作為“讀者來信”刊發(fā)。律師以人格權(quán)受侵害為由提起訴訟。法院認(rèn)為,任何言論都是發(fā)言者的人格表露,言論是否應(yīng)當(dāng)公開和應(yīng)當(dāng)以何種形式公開,應(yīng)由發(fā)言者自己決定。在何時(shí)以何種形式公開私人的信件或手稿,應(yīng)當(dāng)征得當(dāng)事人同意。未經(jīng)同意修改他人言論可能會呈現(xiàn)錯誤的人格形象,損害人格權(quán)。由于《德國民法典》并無一般人格權(quán)條款,法院借助基本法第2條第1款及第1條第1款導(dǎo)出了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并認(rèn)為其屬于《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規(guī)定的“其他權(quán)利”,侵犯該權(quán)利應(yīng)承擔(dān)損害賠償責(zé)任。BGHZ 13, 334. 該案的兩個中文譯本,參見《“讀者來信”案》,鄧建中譯,載《私法研究》第8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97-401頁;《讀者來信案》,李穎譯,載《私法研究》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281頁。在該案之后,聯(lián)邦憲法法院通過“索拉雅案”等案件認(rèn)可了民法上一般人格權(quán)的證立,(27)該案的基本案情是,被告出版社在其刊物上刊登了一篇關(guān)于波斯國王前妻索拉雅的訪問稿,后發(fā)現(xiàn)內(nèi)容為捏造。報(bào)社以刊發(fā)新報(bào)道和更正啟事的方式作出彌補(bǔ)。索拉雅認(rèn)為其人格權(quán)受到侵害,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則認(rèn)為聯(lián)邦法院的判決侵犯了其新聞自由,于是提起憲法訴訟。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在該案中肯認(rèn)了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對一般人格權(quán)的構(gòu)建,并闡釋了一般人格權(quán)在公法上的效力。聯(lián)邦憲法法院提出,在社會共同體中自由開展的人格及其尊嚴(yán)是基本權(quán)利價(jià)值的核心,應(yīng)享有所有國家權(quán)力的尊重與保護(hù)。個人在私人領(lǐng)域自主地、自我負(fù)責(zé)地作出決定,并希望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唯有原告方可以決定是否以及以何種方式,使公眾得以探究其私生活。”參見BVerfGE 34,269. 案情介紹,參見陳志忠:《個人資料保護(hù)之研究——以個人資訊自決權(quán)為中心》,臺灣地區(qū)“司法院秘書處”發(fā)行2001年版,第33-37頁。并因循“自決”路徑構(gòu)建了公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這一時(shí)期,信息技術(shù)和大眾傳媒飛速發(fā)展,社會關(guān)注、媒體輿論侵入私人領(lǐng)域,對個人形成壓力,影響到個人自由發(fā)展。聯(lián)邦憲法法院在適用一般人格權(quán)作出裁判時(shí),多次提到上述時(shí)代特征,試圖通過強(qiáng)調(diào)“自決”的價(jià)值來維系人格發(fā)展的自由。從權(quán)利發(fā)展脈絡(luò)來看,一般人格權(quán)的構(gòu)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應(yīng)這種復(fù)雜的個人與社會關(guān)系。在有關(guān)個人社會形象維護(hù)的系列案件中,一般人格權(quán)支撐著個人自主決定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展現(xiàn)其人格形象,即具體化為“自我形象權(quán)”;在有關(guān)私人領(lǐng)域的系列案件中,一般人格權(quán)發(fā)揮著保護(hù)個人私人領(lǐng)域的作用,即具體化為“隱私保護(hù)權(quán)”。同時(shí),一般人格權(quán)還可具體化為“自我決定權(quán)”,支撐個人對其事務(wù)的自主決定。(28)參見謝立斌:《中德比較憲法視野下的人格尊嚴(yán)——兼與林來梵教授商榷》,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4期;張翔主編:《德國憲法案例選釋(第2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7-78頁。
可見,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并非橫空出世,其只是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將自決理念應(yīng)用于個人信息處理領(lǐng)域的結(jié)果。確立一項(xiàng)“個人有權(quán)自行決定于何時(shí)、何種范圍內(nèi)公開其個人信息或?qū)€人信息交付利用”的權(quán)利,與此前的判例是一脈相承的。當(dāng)然,“人口普查案”對一般人格權(quán)也有發(fā)展和突破。這在塑造了令人矚目的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同時(shí),也為這一權(quán)利埋下了隱患。
三、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結(jié)構(gòu)性缺陷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核心邏輯可概括為,個人有權(quán)自行決定于何時(shí)、何種范圍內(nèi)公開其個人信息或?qū)€人信息交付利用,以防止國家在自動化條件下無限制地收集、傳輸個人信息,形成對人格自由發(fā)展的威脅。然而,這一理論存在著明顯的結(jié)構(gòu)性缺陷,致使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難以成為一項(xiàng)穩(wěn)定的基本權(quán)利。
(一) 對領(lǐng)域理論的放棄模糊了權(quán)利的保護(hù)范圍
德國法上并無“隱私”概念,判例和學(xué)說通過對一般人格權(quán)的具體化,形成了對私領(lǐng)域的保護(hù)。在“人口普查案”前,法院對私領(lǐng)域的保護(hù)采領(lǐng)域理論。該理論將私領(lǐng)域分為隱秘領(lǐng)域、秘密領(lǐng)域、私人領(lǐng)域三個層次,并給予不同強(qiáng)度的保護(hù)。學(xué)理上多將其比作一個同心圓式的模型,視與中心部分的遠(yuǎn)近,給予區(qū)別保護(hù)。其中,隱秘領(lǐng)域涉及人性尊嚴(yán)的核心,受到絕對保護(hù);其余兩個領(lǐng)域則需要通過利益衡量來判斷是否以及如何提供保護(hù)。(29)也有學(xué)者采四分法,將私人領(lǐng)域分為“絕對受保障的隱秘領(lǐng)域”“在重大公益及比例原則的保護(hù)下可被限制的私人領(lǐng)域”“個人在社會中與他人接觸而形成,在較少的嚴(yán)格保護(hù)下可被干預(yù)的社會領(lǐng)域”“自始面向公眾,不存在秘密保護(hù)的公開領(lǐng)域”四個層次。參見前引,陳志忠書,第79-80頁。盡管該理論也存在界限不夠清晰的問題,但能夠?yàn)榇祟惏讣峁┹^穩(wěn)定的分析框架。
然而,在“人口普查案”中,聯(lián)邦憲法法院提出,綜合化的信息系統(tǒng)可以將個人信息組合起來形成完整的人格圖像,進(jìn)而對人格產(chǎn)生威脅。在自動化的數(shù)據(jù)處理技術(shù)下,已不再有不重要的信息。在對人口普查法具體條文合憲性的判斷中,法院也是在區(qū)分非匿名化涉及人身的信息和一般性統(tǒng)計(jì)信息的基礎(chǔ)上,對信息利用的風(fēng)險(xiǎn)作出判斷。這一立場是對領(lǐng)域理論的實(shí)質(zhì)性放棄,意味著無須再對個人信息進(jìn)行靜態(tài)分層,而應(yīng)轉(zhuǎn)向考慮個人信息的使用方式和可能的結(jié)合來提供保護(hù)。(30)參見王澤鑒:《人格權(quán)法》,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頁。這將帶來兩個方面的影響:第一,擴(kuò)大保護(hù)范圍,將“領(lǐng)域理論”下無法保護(hù)的外層個人信息納入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保護(hù)范疇當(dāng)中;第二,既然不再對個人信息進(jìn)行分層,那也就意味著不再存在絕對不受保護(hù)的私密領(lǐng)域,所有個人信息都可能受到重大公共利益的限制。在后續(xù)的“日記案”中,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放棄了為本歸屬于隱秘領(lǐng)域的日記提供絕對保護(hù),認(rèn)為即便是日記也要受到刑事偵查等重大公益的制約,進(jìn)一步確證了該立場。(31)參見BVerfG, NJW 1990, 563. 參見楊芳:《德國一般人格權(quán)中的隱私保護(hù)——信息自由原則下對“自決”觀念的限制》,載《東方法學(xué)》2016年第6期。
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在20世紀(jì)80年代就已考慮到大量個人信息相互結(jié)合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認(rèn)為“不再有不重要的信息”,應(yīng)當(dāng)說是富有遠(yuǎn)見的。時(shí)至今日,數(shù)據(jù)挖掘、聚合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外部信息的豐富強(qiáng)化了再識別的能力,“看似強(qiáng)大的匿名化”在技術(shù)層面搖搖欲墜,基于匿名化設(shè)計(jì)的個人信息保護(hù)法律機(jī)制也受到?jīng)_擊。(32)參見Paul Ohm. “Broken Promises of Privacy: Responding to the Surprising Failure of Anonymization”, UCLA Law Review. 57, No.6 (2010).這彰顯出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超越時(shí)代的先見。但是,“人口普查案”消解了領(lǐng)域理論分層級保護(hù)的要求,卻沒有為復(fù)雜多樣的個人信息設(shè)定區(qū)別化的保護(hù)密度和保護(hù)方式。在理論上,這未能體現(xiàn)出不同個人信息與人格自由發(fā)展的關(guān)聯(lián)度;在實(shí)踐上,這可能導(dǎo)致個人信息保護(hù)成本的大幅提升。該案判決中,法院對一般統(tǒng)計(jì)信息和特定的、非匿名化人身信息的分類過于簡單,其提出的“結(jié)合可能”則高度個案化和不確定,難以形成穩(wěn)定和可操作的標(biāo)準(zhǔn)。
放棄領(lǐng)域理論帶來的深層次問題是,個人信息保護(hù)所指向的法益愈加模糊不清。在“人口普查案”中,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多次提到1969年的“Mikrozensus案”(亦被稱為“小普查案”)。在這一案件中,德國聯(lián)邦政府同樣因人口普查立法引發(fā)憲法訴訟。聯(lián)邦憲法法院針對1957年的“抽樣調(diào)查法”提出,基本法保障每個人有一個絕對不受侵犯的隱秘領(lǐng)域。強(qiáng)制性的抽樣調(diào)查使人格目錄化,使得個人好像貨架上的物品,從而與人的尊嚴(yán)相抵觸。但是,并非所有信息收集行為都侵犯人的尊嚴(yán)和對私人領(lǐng)域的自決,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其必須忍受國家的調(diào)查。法案規(guī)定的統(tǒng)計(jì)調(diào)查雖涉及一些隱私信息,但并不涉及隱秘領(lǐng)域,同時(shí)匿名化也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是合憲的。(33)參見BVerfGE 27,1. 案情介紹,參見前引,陳志忠書,第42-45頁。
在“小普查案”中,聯(lián)邦憲法法院仍堅(jiān)持領(lǐng)域理論,以個人信息與私領(lǐng)域的關(guān)聯(lián)來確定其對人格的影響。但在“人口普查案”中,法院一方面放棄了國家權(quán)力侵入私領(lǐng)域?qū)θ烁褡杂砂l(fā)展造成影響的論證思路,另一方面卻未能充分說明保護(hù)個人信息免受無限制地收集、儲存、使用和傳輸與人格自由發(fā)展的關(guān)聯(lián)。這使得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雖作為憲法一般人格權(quán)具體化的成果,但卻依然不夠具體,尤其是法院在判決中就個人的社會角色進(jìn)行了論述,似乎是將個人信息保護(hù)問題從“隱私保護(hù)權(quán)”向“自我形象權(quán)”轉(zhuǎn)移,進(jìn)行了理論路徑的更新。那么,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究竟是對隱私保護(hù)范圍的拓展,還是對自我形象決定的數(shù)字化延伸,抑或是完全獨(dú)立于上述兩項(xiàng)一般人格權(quán)的新型一般人格權(quán)?(34)有觀點(diǎn)認(rèn)為,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屬于自我表現(xiàn)權(quán)的范圍。參見前引,謝立斌文。還有觀點(diǎn)認(rèn)為,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并非一般人格權(quán),其性質(zhì)更接近基本法第2條第1款所保護(hù)的一般行為自由。參見前引③,劉金瑞書,第79-85頁。在這一問題上,“人口普查案”可以說是“破而未立”,并沒有給出清晰的答案。
(二) 對侵害行為認(rèn)定寬泛加劇了權(quán)利的不確定性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是一般人格權(quán)在個人信息保護(hù)領(lǐng)域具體化的結(jié)果,這導(dǎo)致其先天帶有一般人格權(quán)的局限。德國憲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以人的尊嚴(yán)和人格的自由發(fā)展為客體,要求他人尊重個人人格自由發(fā)展的空間。但“人格的自由發(fā)展”往往立基于個人內(nèi)心的主觀感受,缺乏穩(wěn)定和客觀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這使得一般人格權(quán)缺乏具體和外在可識別的客體,保護(hù)范圍過于開放而不確定。(35)參見前引,楊芳文。
這一問題在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上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法院在“人口普查案”的判決中舉例指出,當(dāng)一個人預(yù)料到當(dāng)局會記錄他參加集會時(shí),他就會放棄行使基本法第8條和第9條所規(guī)定的集會權(quán)利。但在這一例子中,當(dāng)局的記錄可能產(chǎn)生哪些影響,其對人格自由發(fā)展的威脅有多大,都未得到充分說明。記錄個人信息的部門既可能濫用相關(guān)信息擠壓當(dāng)事人人格發(fā)展空間,也可能什么也不做——此時(shí)真正發(fā)生的只有當(dāng)事人主觀上的擔(dān)憂和恐懼。聯(lián)邦政府在訴訟中就曾主張,在對風(fēng)險(xiǎn)進(jìn)行評估時(shí),不應(yīng)假定國家機(jī)關(guān)必然會濫用信息,而假定其會遵守信息保護(hù)的法定要求,但法院沒有給予回應(yīng)。僅以基本權(quán)利主體“想象的侵害”和“內(nèi)心的擔(dān)憂”,而非現(xiàn)實(shí)侵害或侵害可能性來論證人格自由發(fā)展空間的減損,使該權(quán)利顯得過于主觀和不確定。誠如德國學(xué)者所言,通過一種“即將被監(jiān)控的感覺”來論證侵害的成立,將不會獲得清晰的輪廓。(36)參見[德]弗里德里希·肖赫:《信息社會背景下的信息自決權(quán)》,查云飛、阮爽譯,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5年第6期。
在后續(xù)對人口普查法具體條文的合憲性判斷中,法院認(rèn)定法案第9條第1款至第3款侵犯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所給出的主要理由是信息傳輸和二次利用的目的不夠明確,二次利用可能造成的影響無法判斷。但是,在這一邏輯中,信息的傳輸和二次利用究竟給當(dāng)事人帶來了哪些現(xiàn)實(shí)的不利益未得到充分說明,人格自由發(fā)展面臨的風(fēng)險(xiǎn)在多大程度上會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shí)侵害亦未得到充分度量。將基本權(quán)利的主觀防御權(quán)從防御國家權(quán)力的現(xiàn)實(shí)侵害擴(kuò)張至防御一種不確定和尚未實(shí)證化的風(fēng)險(xiǎn),將很難建立起穩(wěn)定的權(quán)利結(jié)構(gòu)。
傳統(tǒng)上,對基本權(quán)利的干預(yù)是指具備主觀目的性、直接性、法效性、強(qiáng)制性的行為,即國家故意而為的直接限制基本權(quán)利的強(qiáng)制性法律行為。(37)參見張翔:《基本權(quán)利限制問題的思考框架》,載《法學(xué)家》2008年第1期。這一標(biāo)準(zhǔn)隨著基本權(quán)利學(xué)說的發(fā)展而呈現(xiàn)逐漸放寬的態(tài)勢。在德國學(xué)理和實(shí)務(wù)上,已將基本權(quán)利干預(yù)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擴(kuò)展到“凡因國家權(quán)力的作用,而使得個人無法從事原來屬于自由權(quán)保護(hù)領(lǐng)域內(nèi)之行為時(shí),均構(gòu)成基本權(quán)之干預(yù)”,(38)黃清德:《科技定位追蹤監(jiān)視與基本人權(quán)保障》,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73-75頁。即重點(diǎn)關(guān)注國家行為對基本權(quán)利產(chǎn)生的實(shí)際影響。但即便采此種解釋立場,對侵害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認(rèn)定也顯得過于寬泛。即便是國家實(shí)施的最中性的信息行為,只要涉及個人信息處理,都可能因?yàn)楦鞣N可能的后果引發(fā)個人擔(dān)憂,進(jìn)而存在影響公民人格自由發(fā)展的風(fēng)險(xiǎn)。這導(dǎo)向的結(jié)果是,國家的所有信息處理行為都須遵守高密度的法律保留要求,且需要有十分明確、清晰、具體的覆蓋信息處理全生命周期的行為規(guī)則。如此,國家機(jī)關(guān)自主應(yīng)對變化的能力和裁量余地將受到很大限制,可能造成國家在數(shù)字化社會的建構(gòu)面前步履維艱。
(三) 基于個人意志的預(yù)防式控制容易導(dǎo)致保護(hù)過度
在個人信息處理關(guān)系中,個人大多數(shù)時(shí)候面臨的是對信息被濫用風(fēng)險(xiǎn)的恐懼和擔(dān)憂。但是,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卻承襲一般人格權(quán)中的“自決”因素,構(gòu)建了一項(xiàng)帶有明顯積極向度的支配性權(quán)利。以自決理念為中心進(jìn)行法權(quán)結(jié)構(gòu)配置,必定會導(dǎo)致相應(yīng)制度設(shè)計(jì)圍繞信息主體對信息處理活動的控制展開,這實(shí)際上是對不確定的風(fēng)險(xiǎn)采取了高強(qiáng)度的前置防御,容易導(dǎo)致保護(hù)過度。
雖然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不認(rèn)為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是一種不受限制的絕對權(quán),也未強(qiáng)調(diào)其價(jià)值優(yōu)先性,(39)在“索拉雅案”中,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就明確提出,一般人格權(quán)不得全面主張其有優(yōu)先地位。參見前引,陳志忠書,第36頁。但自決理念實(shí)證化的后果往往是實(shí)定法制度設(shè)計(jì)上的“自我控制”與“自決優(yōu)先”。在形式邏輯上,若承認(rèn)信息主體享有“自行決定于何時(shí)、何種范圍內(nèi)公開其個人信息或?qū)€人信息交付利用”的權(quán)利,那獲得個人意志的容許自然就成為個人信息處理的前提條件。于是,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與同意機(jī)制在實(shí)踐中被緊密地捆綁在一起,“自決優(yōu)先”被具體化為“同意優(yōu)先”,能夠體現(xiàn)個人意志的“告知—同意”也就順理成章成為個人信息處理最重要的合法性事由。有研究者將此歸結(jié)為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遭到的誤讀——“人口普查案”判決的重點(diǎn)是對目的限制原則適用性的討論,而非對知情同意原則的強(qiáng)調(diào),但這種誤讀卻是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權(quán)利表達(dá)必然導(dǎo)致的結(jié)果。
這種“同意優(yōu)先”的設(shè)定直接塑造了個人信息保護(hù)秩序的基本面貌: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的常態(tài)不是“普遍允許——可能出現(xiàn)損害時(shí)禁止”,而是“普遍禁止——獲得個人同意后允許”,個人信息的流動由此處于一種高強(qiáng)度的默認(rèn)禁止?fàn)顟B(tài)。(40)參見梅夏英:《在分享和控制之間 數(shù)據(jù)保護(hù)的私法局限和公共秩序構(gòu)建》,載《中外法學(xué)》2019年第4期。然而,在風(fēng)險(xiǎn)和損害尚無法確證的情況下,就對所有的個人信息處理活動采取“控制優(yōu)先”的規(guī)制進(jìn)路,將無可避免地面臨個人信息保護(hù)是否會影響經(jīng)濟(jì)發(fā)展、限制信息流動等拷問。(41)參見楊貝:《個人信息保護(hù)進(jìn)路的倫理審視》,載《法商研究》2021年第6期。盡管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并非絕對權(quán),在獲得個人同意之外尚存在其他例外事由,但這也面臨著一個悖論:在例外事由規(guī)定不充分和不具體時(shí),其依然難以避免以“同意”為核心的制度導(dǎo)向。如GDPR中雖然也規(guī)定了大量的例外情形,但由于權(quán)利條款明確具體,例外條款模糊和不確定,其依然可能對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造成不利影響。(42)參見許可:《數(shù)字經(jīng)濟(jì)視野中的歐盟〈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hù)條例〉》,載《財(cái)經(jīng)法學(xué)》2018年第6期。而當(dāng)例外情形規(guī)定過多時(shí),自決的意義將被大幅削弱。在大部分的信息利用場景都可能滿足例外條件的情況下,自決就很難再作為一種基礎(chǔ)性的原則和要求得到貫徹。
(四) 進(jìn)一步追問:個人信息保護(hù)需要以“自決”為核心嗎
現(xiàn)代信息法律秩序的底層邏輯支持以個人意志為中心的制度建構(gòu)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大型電子數(shù)據(jù)庫出現(xiàn)以前,除隱私之外的個人信息并不被納入法律保護(hù)的范疇,而是一直被置于公共領(lǐng)域自由流通。(43)參見梅夏英:《社會風(fēng)險(xiǎn)控制抑或個人權(quán)益保護(hù)——理解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的兩個維度》,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2年第1期。在電子化技術(shù)廣泛應(yīng)用后,個人信息泄露和被濫用的事件頻發(fā),才凸顯出個人信息保護(hù)的必要性。如果說傳統(tǒng)條件下的個人信息具有更多個人屬性的話,那么當(dāng)下的個人信息更多是作為個體社會活動的數(shù)字反映而存在,具有更強(qiáng)的社會屬性。例如,附著在個人網(wǎng)購記錄之上的除了個人權(quán)益外,還有網(wǎng)絡(luò)平臺基于信息流的商業(yè)利益和行政機(jī)關(guān)執(zhí)法活動需要實(shí)現(xiàn)的公共利益。若承認(rèn)個人有完整的控制權(quán),顯然無法兼顧上述利益。總之,這一時(shí)代的個人信息更多是個人與社會信息系統(tǒng)相互作用的產(chǎn)物,具有較強(qiáng)的涉他性、公共性、動態(tài)性,建立在個人主義觀念下的個人控制模式已無法適應(yīng)當(dāng)下的數(shù)字環(huán)境。(44)參見高富平:《個人信息保護(hù):從個人控制到社會控制》,載《法學(xué)研究》2018年第3期。
更進(jìn)一步而言,個人其信息不僅無法自決,也無須自決。早在1977年德國聯(lián)邦數(shù)據(jù)保護(hù)法出臺后不久,德國學(xué)者就提出,個人信息保護(hù)的客體是四類具體利益:知悉個人信息被處理的利益、個人信息正確和完整的利益、個人信息處理須符合特定目的的利益以及隱私利益。(45)參見楊芳:《個人信息保護(hù)法保護(hù)客體之辨——兼論個人信息保護(hù)法和民法適用上之關(guān)系》,載《比較法研究》2017年第5期。我國學(xué)界也對個人信息保護(hù)中不同層次的法益作出了界分。如有觀點(diǎn)指出,為了防止因個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或利用而產(chǎn)生的侵害人格尊嚴(yán)、妨礙人格自由、損害人格權(quán)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等風(fēng)險(xiǎn),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自然人對其個人信息具有防御性或保護(hù)性利益。(46)參見程嘯:《民法典編纂視野下的個人信息保護(hù)》,載《中國法學(xué)》2019年第4期。這實(shí)際上是將個人信息權(quán)益作為保護(hù)人身權(quán)、財(cái)產(chǎn)權(quán)等實(shí)體權(quán)益的前置性權(quán)益,建立了一個雙層結(jié)構(gòu)。有學(xué)者將這種結(jié)構(gòu)概括為個人信息保護(hù)的“本權(quán)權(quán)益”和“保護(hù)‘本權(quán)權(quán)益’的權(quán)利”,并指出本權(quán)權(quán)益包括人格尊嚴(yán)、人身財(cái)產(chǎn)安全、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護(hù)本權(quán)權(quán)益的權(quán)利則包括作為支配性權(quán)利的同意和作為救濟(jì)性權(quán)利的刪除等。(47)參見張新寶:《論個人信息權(quán)益的構(gòu)造》,載《中外法學(xué)》2021年第5期。
雖然學(xué)界就個人信息權(quán)利束的公私法屬性還有不同觀點(diǎn),但上述研究中對個人信息權(quán)益的分層解剖是切中肯綮的。個人信息保護(hù)法并不保護(hù)個人對其信息的控制,包括決定權(quán)在內(nèi)的各種個人信息權(quán)并非目的性、實(shí)體性的法益,而只是個人對抗信息處理者的工具性權(quán)利。(48)參見王錫鋅:《國家保護(hù)視野中的個人信息權(quán)利束》,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2021年第11期。從嚴(yán)格意義上說,在“人口普查案”中,“自決”也并非一項(xiàng)獨(dú)立的實(shí)體權(quán)利,而是維護(hù)“人格自由發(fā)展”這一權(quán)利的前置要求。被認(rèn)定違憲的人口普查法第9條第1款至第3款是關(guān)于信息傳輸和二次利用的規(guī)定,法院所擔(dān)心的是無限制的個人信息傳輸會讓國家過度掌握公民人格圖像,公民無法獲知其信息的利用情況,最終導(dǎo)致人的自主性喪失。
因此,與其說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意在保護(hù)個人對其信息處理活動的“自決”,毋寧說該權(quán)利是在保護(hù)個人在數(shù)字化時(shí)代人格自由發(fā)展的“自主”,這也是德國憲法一般人格權(quán)的題中之義。需注意,保障人格自主的方式多種多樣,賦予個人決定權(quán)僅是其中一種成本較高、效果不一定理想的方式而已。認(rèn)為“要避免個人淪為他人可操控的信息客體,從而失去作為主體的參與可能,就必須賦予個人對其信息的支配權(quán)”,(49)趙宏:《告知同意在政府履職行為中的適用與限制》,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2年第2期。是一種事實(shí)判斷上的錯誤和權(quán)利安排上的錯配,“人口普查案”判決最核心的癥結(jié)也正在于此。
那么,是否有必要承認(rèn)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在工具性權(quán)利層面的地位,以這一權(quán)利來概括和統(tǒng)合個人信息權(quán)利束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其一,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并不能夠很好地總結(jié)個人信息保護(hù)所涉及的各類法益,反而會因“自決”價(jià)值的凸顯而遮蔽個人信息保護(hù)的本來面目。其二,“自決”的權(quán)利表達(dá)難免導(dǎo)向個人控制式的權(quán)利配置,引發(fā)前述一系列問題。可資參考的例子是,盡管歐盟受個人信息自決理念影響較大,但在起草《歐盟基本權(quán)利憲章》時(shí),采用信息自決權(quán)概念的建議最終被否決,其中一個理由便是擔(dān)心這種定位會產(chǎn)生個人對信息處理具有絕對決定權(quán)的誤解。(50)參見王錫鋅:《個人信息國家保護(hù)義務(wù)及展開》,載《中國法學(xué)》2021年第1期。德國有學(xué)者亦曾提出用“限制信息他決”取代“信息自決”的主張,因?yàn)樾畔⒅黧w在處理個人信息方面擁有發(fā)言權(quán),但并不總是有最終決定權(quán)。個人信息權(quán)益只是個人信息處理中要考慮的諸多因素之一,且其可能也不一定會高于信息處理者或第三方的利益。(51)參見Winfried Veil. The GDPR: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On the Structural Shortcomings of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 Data Protection Law, in: NVwZ 10 (2018), S. 686-696.
此外還必須要說明的是,個人信息自決的理念實(shí)際上與德國和歐陸法系的法文化傳統(tǒng)緊密相連。在德國法上,這一權(quán)利有著德國民法和憲法上眾多一般人格權(quán)判例的支撐和法文化的長期浸潤,屬于“觀念基礎(chǔ)與制度脈絡(luò)先于實(shí)證法”。(52)參見姚佳:《個人信息主體的權(quán)利體系——基于數(shù)字時(shí)代個體權(quán)利的多維觀察》,載《華東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2年第2期。這是德國基本法將人性尊嚴(yán)奉為圭臬前提下的特殊成果,并因?yàn)榈聡ㄎ幕跉W洲的強(qiáng)大影響力而被歐盟所接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并不具備復(fù)制這一權(quán)利的基礎(chǔ)和必要。
四、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實(shí)證反思
在論及憲法位階的環(huán)境權(quán)時(shí),曾有觀點(diǎn)一針見血地指出:“傳統(tǒng)環(huán)境權(quán)論者以法律中心主義、自然法意味以及絕對主義,來面對一個富有高度科技背景,決策風(fēng)險(xiǎn)與利益沖突的問題,自然導(dǎo)致水土不服的現(xiàn)象。尤其是論者以憲法位階的環(huán)境權(quán)延伸到私權(quán)意義的環(huán)境權(quán),更有小頭扣大帽而不知所向的困難。”(53)葉俊榮:《憲法位階的環(huán)境權(quán)——從擁有環(huán)境到參與環(huán)境決策》,載葉俊榮:《環(huán)境政策與法律》,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6-27頁。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亦是如此。如果忽視了信息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而以“自決”作為個人信息保護(hù)法律制度設(shè)計(jì)的基點(diǎn),極易陷入個人信息保護(hù)的困境。由于我國公法和私法上都存在接納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主張,因此本部分將結(jié)合現(xiàn)行法規(guī)范對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實(shí)定法表達(dá)展開討論。
(一)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公法困境
我國公法領(lǐng)域的個人信息保護(hù)研究起步相對較晚,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憲法隱私權(quán)的建構(gòu)上。個人信息保護(hù)議題興起后,學(xué)界對個人信息保護(hù)的法權(quán)基礎(chǔ)應(yīng)上升至憲法位階并形成共識,但在具體路徑上存在“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和“國家保護(hù)義務(wù)”等不同立場。在個人自決權(quán)的支持者看來,相較于憲法隱私權(quán)等理論進(jìn)路,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經(jīng)由德國司法判例和法教義學(xué)的長期形塑,表現(xiàn)出定位明確、意涵清晰、價(jià)值多元、體系開放等諸多優(yōu)勢”,更宜成為公法上個人信息保護(hù)的基礎(chǔ)。(54)參見前引①,趙宏文。在實(shí)定法上,可通過對我國憲法第33條第3款“人權(quán)條款”和第38條“人格尊嚴(yán)條款”的解釋導(dǎo)出這一權(quán)利。(55)參見趙宏:《信息自決權(quán)在我國的保護(hù)現(xiàn)狀及其立法趨勢前瞻》,載《中國法律評論》2017年第1期;前引①,姚岳絨文。但是,這一理論進(jìn)路既不符合公法上個人信息保護(hù)的客觀實(shí)際,也與實(shí)定法體系無法契合。
首先,公法上并不存在一般性的自我決定空間。在現(xiàn)代信息條件下,國家機(jī)關(guān)處理個人信息的主要目的在于增進(jìn)公共福祉,實(shí)現(xiàn)公共利益。這種公共價(jià)值判斷通常由立法形成,個人意志無法對其形成制約。事實(shí)上,國家機(jī)關(guān)行為的單方性、強(qiáng)制性正是公法活動最突出的特點(diǎn),信息主體無論同意與否,都必須遵從法秩序的安排。這決定了法定職權(quán)是國家機(jī)關(guān)處理個人信息最主要的合法性基礎(chǔ)。國家機(jī)關(guān)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是否具備合法性,應(yīng)當(dāng)以該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權(quán)限和程序?yàn)闃?biāo)準(zhǔn),而非以行為是否背離信息主體的意志為標(biāo)準(zhǔn)。在公法領(lǐng)域確立一項(xiàng)“自我決定”的權(quán)利,并不具備實(shí)現(xiàn)條件。盡管可以將基于公共利益的個人信息處理解釋為對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限制,但這意味著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可能基于各種法定事由而遭到廣泛的限制,這些限制甚至已經(jīng)掏空了權(quán)利本身,很難說這樣的權(quán)利還有什么實(shí)際意義。
有觀點(diǎn)認(rèn)為,國家機(jī)關(guān)處理個人信息具有多元的合法性基礎(chǔ),其中包括作為意定基礎(chǔ)的個人同意,“取得個人同意”是與“為履行法定職責(zé)所必需”相并列的一項(xiàng)獨(dú)立合法性基礎(chǔ)。(56)參見彭錞:《論國家機(jī)關(guān)處理個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礎(chǔ)》,載《比較法研究》2022年第1期。然而,與私法領(lǐng)域不同,國家機(jī)關(guān)在沒有法定依據(jù)的情況下,不能隨意增加公民權(quán)益或減損公民義務(wù)。若承認(rèn)同意可作為獨(dú)立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一方面可能造成國家機(jī)關(guān)在履行法定職權(quán)所必需的范圍之外,依據(jù)當(dāng)事人同意過度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的問題——盡管可適用正當(dāng)、必要等基本原則進(jìn)行規(guī)范,但基于原則的規(guī)范密度顯然要低很多;另一方面由于國家機(jī)關(guān)和個人之間具有高度的不對等關(guān)系,很難確保個人同意是否足夠真實(shí)和自由。(57)參見Article 29 Working Party Guidelines on consent under Regulation 2016/679 (As last Revised and Adopted on 10 April 2018), pp.6-7.因此,同意不應(yīng)成為國家機(jī)關(guān)處理個人信息時(shí)的一項(xiàng)獨(dú)立的合法性基礎(chǔ)。
其次,國家機(jī)關(guān)在處理個人信息的法律關(guān)系中,無須通過抽象出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來提供保護(hù)。個人信息保護(hù)法草案三審時(shí),在第1條增加了“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的表述,立法機(jī)關(guān)對此的解釋是“我國憲法規(guī)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公民的人格尊嚴(yán)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hù)。制定實(shí)施本法對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嚴(yán)和其他權(quán)益具有重要意義”。(58)《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hù)法(草案)〉審議結(jié)果的報(bào)告》,載楊合慶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hù)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201頁。這蘊(yùn)含兩層意思:第一,個人信息保護(hù)的法權(quán)基礎(chǔ)應(yīng)上升至憲法位階;第二,個人信息保護(hù)涉及棲身于不同憲法規(guī)范的多種法益。這具體表現(xiàn)為以人格尊嚴(yán)條款為中心,連接通信自由與通信秘密等多項(xiàng)基本權(quán)利的一個權(quán)利群。對此提供保護(hù)有兩條路徑:一是直接訴諸人格尊嚴(yán)、通信秘密等具體基本權(quán)利的直接保護(hù);二是在此基礎(chǔ)上構(gòu)建一項(xiàng)權(quán)利束式的“個人信息權(quán)”或“個人信息受保護(hù)權(quán)”,形成對實(shí)體性基本權(quán)利的統(tǒng)合和前置性防御,以解決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無法落入傳統(tǒng)基本權(quán)利保護(hù)范疇的問題。而無論選取以上哪一條路徑,都無須訴諸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
以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作為憲法上個人信息保護(hù)的基礎(chǔ),既不必要,也缺乏規(guī)范支撐。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支持者多將人權(quán)條款和人格尊嚴(yán)條款作為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依據(jù),但卻未能充分證成。論者僅提出,憲法第33條第3款可作為未列舉基本權(quán)利的存身之所,第38條則可參照德國基本法第1條第1款的精神和內(nèi)涵進(jìn)行擴(kuò)張解釋,但這種簡單化的闡釋存在著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國憲法第38條與德國基本法第1條第1款在性質(zhì)、內(nèi)涵等方面并不相同。在性質(zhì)上,憲法第38條究竟屬于憲法基本原則,還是憲法層面的一般人格權(quán),抑或是一項(xiàng)具體的基本權(quán)利,尚有較大爭議;(59)參見林來梵:《人的尊嚴(yán)與人格尊嚴(yán)——兼論中國憲法第38條的解釋方案》,載《浙江社會科學(xué)》2008年第3期;前引,謝立斌文;鄭賢君:《憲法“人格尊嚴(yán)”條款的規(guī)范地位之辨》,載《中國法學(xué)》2012年第2期。在內(nèi)涵上,“人的尊嚴(yán)”與“人格尊嚴(yán)”也存在著本質(zhì)性差別,(60)參見前引,王鍇文。尤其是我國憲法第38條的規(guī)范表達(dá)強(qiáng)調(diào)人格尊嚴(yán)“不受侵犯”,體現(xiàn)出更多的防御色彩,從中恐怕難以導(dǎo)出在交互關(guān)系中的支配性權(quán)利。第二,憲法第33條第3款和第38條在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證成中是什么關(guān)系,亦需進(jìn)一步說明。尤其是德國法上的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乃基本法第2條第1款和第1條第1款共同導(dǎo)出的一般人格權(quán)之具體化,我國憲法第33條和第38條卻難以復(fù)制這種聯(lián)結(jié),如論者主張,將憲法第38條往德國基本法第1條第1款的方向解釋,那更為概括的憲法第33條又發(fā)揮何種作用?在未解決上述問題的情況下,直接移植德國法上的基本權(quán)利,恐非科學(xué)和規(guī)范的解釋路徑。
(二)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私法困境
基本權(quán)利具有防御權(quán)、受益權(quán)和客觀價(jià)值秩序三重功能。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首要功能是對抗公權(quán)力不法侵害的主觀防御功能。在受益權(quán)方面,有觀點(diǎn)認(rèn)為信息權(quán)利的保障無須國家積極給付;(61)參見趙宏:《〈民法典〉時(shí)代個人信息權(quán)的國家保護(hù)義務(wù)》,載《經(jīng)貿(mào)法律評論》2021年第1期。但也有觀點(diǎn)指出,信息主體應(yīng)有知悉他人如何利用個人信息及個人信息正確與否的權(quán)利,這屬于積極請求給付的功能。(62)參見前引,李震山文。最后,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具有客觀價(jià)值秩序功能,國家須落實(shí)制度性保障、組織與程序保障,同時(shí)還要承擔(dān)避免第三方侵害的國家保護(hù)義務(wù)。但是,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本是對抗國家機(jī)關(guān)單方、強(qiáng)制性信息處理行為而設(shè)計(jì),將其擴(kuò)展到私人間,可能會引發(fā)信息關(guān)系的緊張。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的判例也較少涉及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間接第三人效力和私法中的保護(hù)義務(wù)。(63)參見前引,肖赫文。
從理論和制度的發(fā)展脈絡(luò)來看,自決理念一度對我國私法層面的個人信息保護(hù)產(chǎn)生較大影響。該理論的支持者多主張,個人信息保護(hù)的客體是作為民事權(quán)利的個人信息權(quán),而個人信息權(quán)主要是指對個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決定。(64)參見前引②,王利明文;前引②,王成文。有學(xué)者明確提出,個人信息權(quán)是指自然人依法對其本人的個人身份信息所享有的支配并排除他人侵害的人格權(quán),是排他的自我支配權(quán)和絕對權(quán),其權(quán)利要求是自然人對于自己的個人信息自我占有、自我控制、自我支配,他人不得非法干涉,不得非法侵害。(65)參見前引②,楊立新文。在實(shí)定法上,早期的個人信息保護(hù)立法,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關(guān)于加強(qiáng)網(wǎng)絡(luò)信息保護(hù)的決定》和網(wǎng)絡(luò)安全法都高度重視“同意”在個人信息處理中的地位,體現(xiàn)了較強(qiáng)的“自決”理念。
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之所以在私法上產(chǎn)生重要影響,原因在于其權(quán)利話語符合我國個人信息保護(hù)特定階段的需求。數(shù)字時(shí)代到來后,私法領(lǐng)域頻繁出現(xiàn)的個人信息泄露與被濫用引發(fā)了高度關(guān)注,傳統(tǒng)上間接、零散的立法進(jìn)路不足以應(yīng)對現(xiàn)實(shí)需要,(66)參見王錫鋅、彭錞:《個人信息保護(hù)法律體系的憲法基礎(chǔ)》,載《清華法學(xué)》2021年第3期。通過配置一種強(qiáng)力的民事權(quán)利來強(qiáng)化個人控制成為重要的理論依托。在論者看來,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維護(hù)者,由個人對其信息進(jìn)行自我管理,是成本最小、效果最佳的選擇。(67)參見前引②,王利明文。但是,這一路徑未充分重視個人信息的公共性和社會性,而只關(guān)注了信息主體這一單向維度,既可能過度限制信息的流動和利用,也難以實(shí)現(xiàn)對個人信息背后實(shí)體利益的有效保護(hù)。
一方面,個人信息自決的理念將導(dǎo)致過高的制度成本。基于自決理念構(gòu)建的個人信息保護(hù)機(jī)制必然為信息主體設(shè)置強(qiáng)有力的控制系統(tǒng),通過強(qiáng)化個人支配力來確保個人意志的實(shí)現(xiàn)。這些控制機(jī)制包括在事前以“告知—同意”作為個人信息處理的主要原則,在事中和事后配置強(qiáng)大的控制性權(quán)利束。但在私法領(lǐng)域,個人信息處理者與信息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雖不平等,卻可以通過其他手段實(shí)現(xiàn)部分緩解。同時(shí),私法領(lǐng)域的個人信息絕大多數(shù)是基于信息主體與信息處理者的數(shù)字化交互行為產(chǎn)生,是個人自愿選擇的結(jié)果,而非信息處理者主導(dǎo)的強(qiáng)制行為。將信息主體的單方意志作為信息處理的原則性要求,忽略了信息關(guān)系的雙向性,將導(dǎo)致利益分配上的失衡。最典型的表現(xiàn)是,集中體現(xiàn)個人控制理念的“告知—同意”往往以“全有或全無”的方式適用,(68)參見萬方:《隱私政策中的告知同意原則及其異化》,載《法律科學(xué)》2019年第2期。不僅增加了信息處理者的制度成本,影響信息的聚合和利用,也增加了信息主體的時(shí)間成本、通信成本以及使用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成本。(69)參見任龍龍:《論同意不是個人信息處理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載《政治與法律》2016年第1期。對歐盟GDPR的考察就指出,高強(qiáng)度的控制權(quán)“增大了數(shù)據(jù)聚合成本,且人格尊嚴(yán)利益的開放性、抽象性與主觀性特征使得企業(yè)在權(quán)衡個人控制價(jià)值與數(shù)據(jù)流動價(jià)值時(shí)限于高度的合規(guī)不確定桎梏,造成數(shù)據(jù)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與挖掘不足的‘反公地悲劇’困境”。(70)謝堯雯:《個人信息保護(hù)制度“個人控制”模式的立法選擇》,載《青海社會科學(xué)》2021年第4期。
另一方面,私法層面的個人信息自決呈現(xiàn)出保護(hù)不足的問題,這既是因?yàn)樾畔⒅黧w與信息處理者的實(shí)力不均衡,更是因?yàn)閭€人理性和意志無法真正回應(yīng)個人信息保護(hù)復(fù)雜的風(fēng)險(xiǎn)面向。尤其是在大數(shù)據(jù)環(huán)境下,“建立在算法基礎(chǔ)上的數(shù)據(jù)流通具有隱匿性和隨意性的特點(diǎn),難以為用戶知曉和追蹤”,(71)參見前引,梅夏英文。個人基于有限理性判斷和控制風(fēng)險(xiǎn)的能力趨弱,風(fēng)險(xiǎn)預(yù)防更多需要依靠國家履行基本權(quán)利保護(hù)義務(wù),設(shè)定公共執(zhí)法機(jī)制來實(shí)現(xiàn)。例如,“告知—同意”機(jī)制就長期面臨著個人認(rèn)知能力有限,無法對風(fēng)險(xiǎn)進(jìn)行全面有效的評估,無法真正行使拒絕權(quán)等問題。(72)參見呂炳斌:《個人信息保護(hù)的“同意”困境及其出路》,載《法商研究》2021年第2期。在比較法上,大量立法都在強(qiáng)化對“告知—同意”的公法約束,如GDPR更重視確保當(dāng)事人同意的真實(shí)和有效,我國個人信息保護(hù)法則規(guī)定了大量的單獨(dú)同意要求。學(xué)界也主張,應(yīng)將“告知—同意”視為一項(xiàng)具體要求,而非基本原則。(73)參見韓旭至:《個人信息保護(hù)中告知同意的困境與出路——兼論〈個人信息保護(hù)法(草案)〉相關(guān)條款》,載《經(jīng)貿(mào)法律評論》2021年第1期。上述轉(zhuǎn)變展示出,基于自決理念的“告知—同意”已難以為繼,新的“告知—同意”不再以維護(hù)個人意志為中心,而是更接近于一個帶有公法屬性的風(fēng)險(xiǎn)防范機(jī)制,旨在讓信息主體了解、判斷并對抗個人信息處理帶來的風(fēng)險(xiǎn)。
或許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民法典并未完全采納個人信息自決的理念。首先,民法典無論是在總則編還是在人格權(quán)編,都未采納“個人信息權(quán)”的概念,而是將個人信息作為一種法益予以保護(hù);其次,民法典第1035條雖承襲了網(wǎng)絡(luò)安全法的規(guī)定,依然將“告知—同意”作為個人信息處理的唯一合法性基礎(chǔ),但在第1036條確立了基于正當(dāng)事由的免責(zé)事項(xiàng);再次,民法典第1037條雖然確立了查閱、復(fù)制、更正、刪除等權(quán)利,但均有“依法”等條件限定,表明上述權(quán)利并非廣泛的絕對權(quán)。總之,從民法典的規(guī)范中亦無法解釋出個人信息自決的意旨。
五、 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決定權(quán)”的性質(zhì)及內(nèi)涵
我國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規(guī)定,個人對其個人信息的處理享有決定權(quán),有權(quán)限制或者拒絕他人對其個人信息進(jìn)行處理。這一權(quán)利的設(shè)置將無可避免地引發(fā)“決定權(quán)”與“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關(guān)系的討論。準(zhǔn)確厘定決定權(quán)的屬性與地位,對于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的實(shí)施有著重要意義。
(一) 決定權(quán)的定位與性質(zhì)
前已述及,一種以個人意志為中心的、廣泛的、實(shí)體性的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在中國法上缺乏事實(shí)和規(guī)范支撐,在公法和私法層面都不能作為個人信息保護(hù)的基礎(chǔ)。剖析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的立法思路,亦可看出該法第44條設(shè)置的“決定權(quán)”并非對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繼受,二者有著本質(zhì)性區(qū)別。首先,在個人信息保護(hù)的目標(biāo)上,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確立了“保護(hù)個人信息權(quán)益”“規(guī)范個人信息處理活動”和“促進(jìn)個人信息合理利用”三重立法目的,并未將保護(hù)個人信息權(quán)益作為唯一目標(biāo)。這體現(xiàn)出立法平衡個人信息權(quán)益保護(hù)與信息利用的包容態(tài)度和靈活思維。其次,在個人信息保護(hù)的手段上,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確立了行政規(guī)制和私人救濟(jì)并行的模式,并對行政規(guī)制有較多著墨。(74)參見孔祥穩(wěn):《論個人信息保護(hù)的行政規(guī)制路徑》,載《行政法學(xué)研究》2022年第1期。這表明立法并未將強(qiáng)化個人的控制權(quán)作為主要的保護(hù)手段,自然也就無須設(shè)定廣泛的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立基于上述立法思路,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規(guī)定的決定權(quán)與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應(yīng)屬于“形似而神非”,其屬性和內(nèi)涵應(yīng)從以下幾個維度把握。
第一,決定權(quán)是一種工具性權(quán)利。按照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的規(guī)定,個人僅對其個人信息的處理而非對個人信息享有決定權(quán)。由此可認(rèn)為,該條賦予信息主體的并非一種近似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信息控制和支配權(quán),而是一種矯正信息處理者與信息主體失衡關(guān)系的工具性權(quán)利。(75)參見程嘯:《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35-336頁。從司法實(shí)踐來看,在個人信息保護(hù)法頒布實(shí)施前,(76)由于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生效時(shí)間較短,目前尚未能從公開途徑檢索到以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決定權(quán)作為裁判依據(jù)的案件。多地法院曾基于“告知—同意”的要求認(rèn)可個人對其信息享有自主決定權(quán),但卻未將決定權(quán)視為一種獨(dú)立的實(shí)體性法益。侵犯決定權(quán)但未造成其他實(shí)際侵害后果的,通常僅承擔(dān)賠禮道歉的責(zé)任。(77)參見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qū)人民法院(2016)粵0304民初24741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終8911號民事判決書、北京互聯(lián)網(wǎng)法院(2019)京0491民初16142號民事判決書等。基于工具性權(quán)利的屬性,決定權(quán)雖在理論上貫穿個人信息處理的全周期,但卻并非在所有場景下均可適用。因?yàn)閺膫€人信息保護(hù)法的規(guī)定出發(fā),對個人信息實(shí)體法益的保護(hù)存在多種方式,有的可通過當(dāng)事人行使決定權(quán)等權(quán)利來實(shí)現(xiàn);有的則是通過法律法規(guī)為信息處理者設(shè)定公法義務(wù),強(qiáng)化對信息處理行為的直接規(guī)制而實(shí)現(xiàn)。從實(shí)踐來看,決定權(quán)通常是在信息主體對信息處理行為具有法秩序允許或合意產(chǎn)生的自主選擇空間時(shí)適用,如對于信息處理目的、方式等方面的選擇和決定。
第二,決定權(quán)是一種概括性權(quán)利。在體系結(jié)構(gòu)上,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位于該法第四章的章首;在權(quán)利內(nèi)容上,“知情”和“決定”是工具性權(quán)利束價(jià)值功能的集中表達(dá)——通過保障個人的知情和參與來確保個人對信息處理者形成有效的監(jiān)督制衡,從而保護(hù)個人信息背后的實(shí)體法益。知情權(quán)和決定權(quán)由此成為“個人在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中的基礎(chǔ)性、概括性權(quán)利”,(78)參見前引,楊合慶書,第113頁。對個人信息權(quán)利束上的其他權(quán)利發(fā)揮著統(tǒng)率作用。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四章所規(guī)定的權(quán)利束也因此形成一個多層次結(jié)構(gòu),即以知情權(quán)和決定權(quán)統(tǒng)率其他工具性權(quán)利,并通過對知情權(quán)和決定權(quán)的保障促進(jìn)個人信息實(shí)體法益的保護(hù)。(79)在這個意義上,知情權(quán)和決定權(quán)因?yàn)轶w現(xiàn)了程序參與和個人自主的價(jià)值,與個人信息實(shí)體權(quán)益關(guān)聯(lián)較緊密,也可被視為目的表征較強(qiáng)的工具性權(quán)利。基于概括性權(quán)利的屬性,當(dāng)存在已型式化的具體權(quán)利時(shí),應(yīng)當(dāng)優(yōu)先適用具體權(quán)利,如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四章明確規(guī)定的可攜帶權(quán)、更正補(bǔ)充權(quán)以及刪除權(quán),以及從個人信息保護(hù)法條文中可析出的同意權(quán)、撤回同意權(quán)、選擇權(quán)、拒絕權(quán)等。當(dāng)不存在相應(yīng)的具體化權(quán)利時(shí),可適用一般性的決定權(quán),并依托具體領(lǐng)域的立法或司法裁判對決定權(quán)進(jìn)行具體化,以彌補(bǔ)已型式化的各項(xiàng)具體權(quán)利之缺失。
第三,決定權(quán)是一種消極防御性權(quán)利。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44條對決定權(quán)的權(quán)能作出了限定——“有權(quán)限制或者拒絕他人對其個人信息進(jìn)行處理”,這通常被理解為決定權(quán)的消極防御功能。但如前所言,在交互性的個人信息處理關(guān)系中,無論是限制、拒絕還是退出個人信息處理活動,其實(shí)質(zhì)都是信息主體對信息處理活動施加的主動性影響,體現(xiàn)出一定的積極面向。這增加了決定權(quán)性質(zhì)的復(fù)雜性。決定權(quán)究竟是消極權(quán)利還是積極權(quán)利,需要從目的和手段兩個維度入手作出界分。(80)參見萬方:《算法告知義務(wù)在知情權(quán)體系中的適用》,載《政法論壇》2021年第6期。就對本權(quán)權(quán)益的保護(hù)而言,決定權(quán)是消極的、防御式的;就實(shí)現(xiàn)這種保護(hù)的手段和方式而言,決定權(quán)體現(xiàn)出一定的積極性——這也被學(xué)者稱為“進(jìn)攻性權(quán)能”。(81)參見前引,王錫鋅文。決定權(quán)的這一結(jié)構(gòu)并不改變其作為消極權(quán)利的屬性。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消極權(quán)利與積極權(quán)利被侵犯時(shí),權(quán)利主體均可行使積極的權(quán)利保護(hù)請求權(quán),因此權(quán)利保護(hù)請求權(quán)不是判斷一項(xiàng)權(quán)利積極或消極的關(guān)鍵,積極權(quán)利與消極權(quán)利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是其本權(quán)請求權(quán)的屬性。(82)參見周剛志:《論“消極權(quán)利”與“積極權(quán)利”——中國憲法權(quán)利性質(zhì)之實(shí)證分析》,載《法學(xué)評論》2015年第3期。
第四,決定權(quán)是一種框架性權(quán)利。決定權(quán)并不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先定的、絕對的權(quán)利,而是一種框架性權(quán)利。框架性權(quán)利與其他類型權(quán)利的核心差別在于,侵犯框架性權(quán)利的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不作先行推定,而需要通過權(quán)衡他人的相關(guān)權(quán)利方可得出結(jié)論。(83)參見薛軍:《揭開“一般人格權(quán)”的面紗——兼論比較法研究中的“體系意識”》,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5期。這意味著在適用決定權(quán)時(shí),必須將信息主體的利益與他人利益、社會利益進(jìn)行綜合考量,尤其應(yīng)當(dāng)通過利益衡量協(xié)調(diào)好個人信息權(quán)益的保護(hù)與個人信息合理利用的關(guān)系。這也符合學(xué)界所提出的應(yīng)當(dāng)在特定的場景和過程中確定工具性權(quán)益適用方案的主張。(84)參見丁曉東:《個人信息權(quán)利的反思與重塑 論個人信息保護(hù)的適用前提與法益基礎(chǔ)》,載《中外法學(xué)》2020年第2期。
(二) 決定權(quán)在公法層面和私法層面的具體化
在公法層面和私法層面的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中,信息主體所具有的工具性權(quán)利并不相同。即便是同一工具性權(quán)利,對公權(quán)處理者和私人處理者的要求也存在差別。(85)參見前引,王錫鋅、彭錞文。個人信息保護(hù)法在這方面存在疏漏:該法第二章第三節(jié)并未對國家機(jī)關(guān)作為信息處理者時(shí),信息主體所享有的權(quán)利束作出任何特別規(guī)定,但第四章中的部分權(quán)利顯然是無法在公私法領(lǐng)域統(tǒng)一適用的——如第45條第3款所規(guī)定的可攜權(quán)就難以在國家機(jī)關(guān)之間適用。這意味著各項(xiàng)工具性權(quán)利需經(jīng)過整體性考察,依其性質(zhì)決定在公法上和私法上的適用方式,決定權(quán)亦是如此。
在國家機(jī)關(guān)作為個人信息處理者時(shí),由于缺乏意思自治的空間,決定權(quán)的適用空間自然較小。有研究就指出,“‘同意’在行政機(jī)關(guān)處理個人信息活動中不具備普遍性、獨(dú)立性、決定性、根本性的特征,只是特定場景下的程序要素”。(86)王錫鋅:《行政機(jī)關(guān)處理個人信息活動的合法性分析框架》,載《比較法研究》2022年第3期。除個人信息保護(hù)法已作出明確規(guī)定的更正、補(bǔ)充、刪除等權(quán)利外,決定權(quán)在公法上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為個人對信息處理方式的選擇權(quán)和拒絕權(quán)。
其一,個人在自動化決策程序中的選擇權(quán)和拒絕權(quán)。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24條第3款規(guī)定,“通過自動化決策方式作出對個人權(quán)益有重大影響的決定,個人有權(quán)要求個人信息處理者予以說明,并有權(quán)拒絕個人信息處理者僅通過自動化決策的方式作出決定”。這表明在行政自動化決策中,個人有權(quán)拒絕信息處理者僅通過自動化決策的方式作出決定,從而要求人工做出決定。其二,與前一情形近似,在當(dāng)前部分行政活動中,行政機(jī)關(guān)通常會設(shè)置電子化、數(shù)字化的辦理程序,如通過App辦理駕照的申領(lǐng)、更換等。在此類活動中,個人有權(quán)拒絕電子化的辦理方式,選擇到現(xiàn)場等傳統(tǒng)方式和程序。這實(shí)質(zhì)上是對個人信息處理方式的選擇和決定。其三,個人有權(quán)決定是否公開自己的個人信息。個人信息保護(hù)法第25條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15條、第32條對此作出了規(guī)定。
在私主體作為個人信息處理者時(shí),信息主體應(yīng)在符合權(quán)利行使條件的情況下,優(yōu)先行使個人信息權(quán)利束上已型式化的各項(xiàng)具體權(quán)利。在不具備已型式化的具體權(quán)利需要直接適用一般性的決定權(quán)時(shí),應(yīng)當(dāng)堅(jiān)持決定權(quán)消極權(quán)利和框架性權(quán)利的定位。首先,信息主體不應(yīng)尋求對信息處理活動的積極干預(yù)和支配,無權(quán)在一般意義上要求信息處理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處理個人信息。實(shí)踐中已出現(xiàn)類似問題,如國家網(wǎng)信辦《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服務(wù)算法推薦管理規(guī)定(征求意見稿)》第15條規(guī)定,“算法推薦服務(wù)提供者應(yīng)當(dāng)向用戶提供選擇、修改或者刪除用于算法推薦服務(wù)的用戶標(biāo)簽的功能”,其中修改功能已超出了消極防御的范圍,賦予了用戶實(shí)現(xiàn)除防御侵害之外的意志之權(quán)利。這可能帶來過高的成本。其次,當(dāng)事人并不享有廣泛的決定權(quán),而僅可在法秩序允許的自治空間內(nèi)行使決定權(quán)。通常來說,當(dāng)事人可行使決定權(quán)的情形一般是信息處理行為存在風(fēng)險(xiǎn)的情況下,由信息主體自主進(jìn)行風(fēng)險(xiǎn)判斷,或是選擇控制、防止風(fēng)險(xiǎn),拒絕相應(yīng)個人信息處理活動;或是選擇接受風(fēng)險(xiǎn)及其可能帶來的有利和不利后果。如“微信讀書案”的判決就用戶同意所展示,“在這個幾乎各種生活軌跡均被記錄并刻畫的數(shù)字時(shí)代,用戶應(yīng)享有通過經(jīng)營個人信息而自主建立信息化‘人設(shè)’的自由,也應(yīng)享有拒絕建立信息化‘人設(shè)’的自由”。(87)參見北京互聯(lián)網(wǎng)法院(2019)京0491民初16142號民事判決書。再次,決定權(quán)的行使應(yīng)符合“禁止權(quán)利濫用”這一原則的要求,防止出現(xiàn)背離立法目的、帶有主觀惡意的行權(quán),如通過決定權(quán)的行使故意侵害他人利益等。最后,決定權(quán)并非絕對性權(quán)利,其行使需要經(jīng)過充分的利益衡量,在個人信息利益與信息利用帶來的商業(yè)利益、社會利益中間進(jìn)行取舍判斷。
六、 結(jié) 語
“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濫觴于德國法的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旨在保護(hù)人格發(fā)展的自由,防止個人在數(shù)字化系統(tǒng)面前失去主體性。然而,落入“自決”窠臼的法權(quán)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卻因信息環(huán)境的復(fù)雜性和個人理性的有限性而窒礙難行。“自決”概念固然具有強(qiáng)烈的價(jià)值感召力,但卻無法成為一勞永逸地解決個人信息保護(hù)問題的終極答案。對個人信息自決權(quán)的解剖應(yīng)當(dāng)肯認(rèn)“自主”之價(jià)值,通過立體化的個人信息保護(hù)機(jī)制化解數(shù)字技術(shù)帶來的憂懼,同時(shí)亦應(yīng)拋卻對“自決”的執(zhí)念,為信息處理關(guān)系中的個人意志尋找恰如其分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