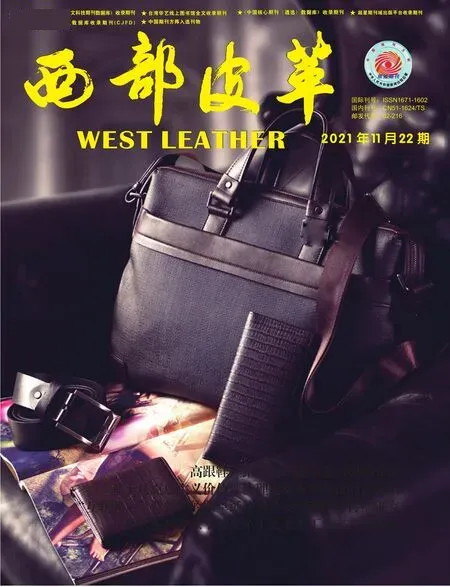現代刺繡藝術中的文化驅因分析
——以徐州刺繡為例
王艷,馮博文,王慧靈
(江蘇師范大學,江蘇 徐州 221116)
前言
明代著名詩人和詩書畫家王士性先生曾經在《廣志繹》中這樣評價明代蘇人“聰慧好古,又善操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俗之雅者,則天下四方之人隨而雅之;以為俗者,則四方隨而俗之”。此處的“雅”即指吳地精神文化的最大特征。在其深刻影響之下,蘇州地區所形成的社會時尚和精神追求輻射影響了當地的刺繡藝術風格,成就了蘇繡的一大特色[1]。同樣的,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徐州地區的特點,必然是南秀北雄。在長久的文化浸染中,現代徐州刺繡文化總體呈現出雄秀結合,粗中有細、細中有粗的地方特點。
筆者通過訪談、參觀與調研,以徐州刺繡為例,對徐州地方刺繡的文化驅因進行了梳理,最終發現:刺繡藝術與當地文化有著密切關聯。
1 文化驅動著針法的發展
想要自己繡出一副好的中國刺繡藝術作品,必然需要了解針法的基礎知識。一般來說,刺繡針主要分為四種,分別是十字繡針、常用刺繡針、書簽針和珠針,繡針的選擇是要結合刺繡作品的面料品質,使用的線的粗細來進行的。選擇了合適的繡針后,就需要知道如何繡,也就是明確針法。任何一副傳統刺繡藝術作品,它歸根結底是在畫面上的一種視覺形象呈現。而構成一副傳統刺繡藝術畫面最基本的視覺形象要素就是“點線面”。
基礎初始針法刺繡藝術作為中國傳統現代刺繡的一種造型藝術表現手段,通過基礎初始針法的各種基本單元針的線和織法針跡的排列組合,它就已經可以直接用來塑造無窮無盡的傳統刺繡形象,例如,打籽的平繡籽是棉花種子中的一個籽,平繡的一個籽是短針和一根直針等。
每種基本單元針的線和織法通過針跡的不斷排列延續重復陳列,它所產生的線就是表現韻律美的基礎線條,不斷地在其中重復著一個根本基礎初始點。而每種針法的連續不斷排列就直接形成了對刺繡畫面的各種視覺形象表現。除此之外,每種針法的基本結構及表現效果也側重于表現某一類的造型特征,譬如打籽繡以表現點見長,滾針以表現線見長,齊針以表現面見長[2]。
針法的表現方法是靈活多變的,從構成的視角去觀察針法,不難發現,針法的使用原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實都是在面料上的穿針引線,主要是通過直行、環繞、打結這3 種方式演變成各種各樣的針法類型。任何一種針法都能通過單元針跡的陳列組成點線面,但在具體運用上,需要結合物象特征選擇適宜的針法來表現,靈活運用各種針法組合構造繡面,才能將刺繡藝術更好地呈現出來[3]。
針法的表現手段各異,但不同流派或不同地域的刺繡,還是有著自己顯著特色的。諸如蘇繡,在明朝康熙時期便逐漸形成了“精,細,雅,潔”的一種藝術風格,它的針法基本表現形式有將近二十種。不過蘇繡中普遍使用的針法還是直繡中的直針、纏針,以及盤針所包含的切針、接針和滾針。蘇繡作為傳承我國悠久歷史的一種刺繡,具有特殊的藝術價值,它靠著自身獨有的藝術歷史性和文化底蘊在當下的經濟社會中占領高地,而現代蘇繡繡法在各種類型蘇繡針法作品設計中的合理的運用更加充分展示了蘇繡所特有的藝術感染力。蘇繡一開始是被人們當作裝飾品來使用的,因而針法就會更加地注重美觀性和實用性。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人們觀念的更新,蘇繡作品逐漸地被人們當作是一種有極高欣賞價值的藝術作品看待,這就要求設計師們能夠緊跟時代步伐,來滿足時代藝術發展新的要求不斷創新新的針法形式來順應這樣的藝術賞析性。蘇州繡娘鄒英姿發明并已申請國家專利的“滴滴針法”,能夠使刺繡作品更具靈氣,似畫非畫,如蘇繡作品《煙雨》(見圖1)就大量使用了這種針法,提高了作品的通透感和觀賞度。可見繡品的地域性與功能性影響著它的針法。

圖1 《煙雨》
徐州的城市風格素有“南秀北雄”之說,南方人氣質偏溫婉,刺繡的針法也就更加精細;而北方人則偏粗獷豪邁,刺繡針法就更加豪氣大方。徐州刺繡的針法中和了兩方特色,既有微細之處,又見磅礴之勢。
一席地的席建勛先生在繼承傳統繡法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新的繡法:彭松繡法(見圖2),此處的“彭”既有“彭城”之意,蘊含著深刻的地域文化內涵,又表達著繡法深意。它區別于其它繡法最大的一點,便是不緊貼在繡布上面,停留在繡布上面的兩三毫米之處,這樣便能織造出一種蓬松感和立體感,使徐州刺繡“粗中有細”,特別適合繡樹葉、云彩一類的小物件,能夠彌補北方刺繡過于粗獷的不足。

圖2 《錦繡彭城之山水云龍》局部
2 文化影響著題材的選擇
地區文化對刺繡影響最直接、最明顯的一個方面就是表現題材。絲線難認,針法難辨,相比之下,題材內容一覽無余,較容易窺見刺繡藝術中的文化驅因。
唐宋時期,經濟、文化相對繁榮的吳地孕育了欣賞性繡品的涌現與發展,文人優秀的書畫作品促使“繡畫”“繡書法”流行起來[1]。同樣的,湘繡受楚地文化的影響也頗深。1972 年長沙馬王堆漢墓考古挖掘發現出土的漢代民族刺繡中包含了具有大量崇拜古代中國天上地下神仙的民間宗教文化題材,而天、地、冥三界觀念的形式與楚國文化有非常深刻的聯系。因此可見,湘繡中那些圍繞中國大自然的刻畫以及人物形象的藝術描繪基本都緣起于楚漢文化[4]。
藝術來源于生活,優秀的刺繡作品必然離不開人民的日常生活。徐州現代刺繡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內容和創作題材一直在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發生變化。現代徐州刺繡年頭不久,但滲透其中的徐州文化是深入且全面的。千年文明史,千年建城史,古城徐州風景秀麗,遺跡眾多,文化多元,多彩而又絢麗的文化基因融入了每個徐州人的骨血當中,在徐州本土刺繡的內容題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多次獲大獎的系列作品《錦繡彭城》(圖3—5)。徐州山水形勝,大運河進入江蘇后蜿蜒綿亙,繞城而過,古黃河穿城南北,與云龍山遙相呼應。往日徐州,煤炭和灰布滿城區;今日徐州,青山綠湖環城繞。《錦繡彭城之山水云龍》(圖3)以云龍山、云龍湖為設計基調,加入城市縮影,以城市的中軸線進行圖形設計構思,體現徐州城市山水歷史文化和現代城市歷史變遷,以刺繡表現錦繡,以錦繡表現徐州繁花似錦。“千古龍飛地,一代帝王鄉”,歷史上的徐州是個金戈鐵馬、英雄人才輩出的地方,如今的徐州商賈云集,經濟飛速發展。《錦繡彭城之秋風戲馬》(圖4)選取徐州第一勝跡——項羽閱兵的“戲馬臺”與現代蘇寧廣場兩大建筑,于方寸繡布之上,形成了“知往鑒今”之勢,訴說彭城人文故事。徐州“五省通衢”,占據重要地理位置,《錦繡彭城之馭風漢行》(圖5)以時間為軸線,以交通為主題,把漢代車馬出行與今日高鐵飛馳及代表徐州新八景之一的和平大橋相結合,表現了今日徐州的輝煌成就,喻意徐州發展吐故納新。

圖3 《錦繡彭城之山水云龍》

圖4 《錦繡彭城之秋風戲馬》

圖5 《錦繡彭城之馭風漢行》
3 文化與藝術表現密不可分
藝術表現的方式和手段多種多樣,而之于刺繡,主要的兩個藝術表現的方面就是配色與構圖。構圖決定了一副刺繡作品的基底,色彩則是在基底之上,豐富和延展出刺繡的完貌。
由于市場需求,徐州刺繡的內容題材早已十分的廣泛,覆蓋生活的各個方面。而選材的不同,必然影響著刺繡的整體取色,除了最基本的內容題材,傳統文化的基因,也會影響刺繡色調的走向。
揚州刺繡的主色調偏淡雅脫俗,是因為揚州歷史上眾多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批文玩字畫,而許多刺繡作品都會以這些文墨作為底稿,最終的選色上也會遵從字墨一貫的淡雅。但徐州有所不同,兩漢文化、軍事文化、宗教文化等,共同鑄就了徐州文化的輝煌。文化現象的多樣性需要將其升華到理念認知,才可以總結出它最本土的特色。這也造就了徐州刺繡作品配色的多樣。徐州是有著數千年的文明史和建城史,擁有非常厚重的歷史文化遺存,但真正延續至今而且實際作用于今天生活的,有兩樣東西:一是幾千年來不斷增長的知識和技術,二是幾千年來反復思索的問題以及由此形成的觀念[5]。綜合來看,徐州文化具有北方之韻、融合之美、雄壯之氣三大鮮明特色,形成以北方文化,尤其是齊魯文化為底蘊,以抗爭精神、英雄主義為主干,以南北兼具、四方融合為靈魂的特色地域文化[6]。地域文化的融合兼并,也造就了徐州刺繡作品配色的多樣。正如席建勛老師所言,徐州刺繡色彩上最大的特點便是雅俗共賞,因此在配色上,它既有氣吞山河的壯烈,又有不諳世事的清新淡雅,兼具南北特色,不受限于世俗傳統定義的南秀北雄,獨樹一幟。
構圖是繪畫的基底,不同的構圖方式會給觀者帶來不一樣的觀賞體驗。在繪畫創作中,構圖對作品的畫面效果至關重要,它不僅會影響畫面的視覺感受,還可以與作品的主題思想情感進行密切的聯系[7]。構圖多用于繪畫藝術之中,但前文提到,刺繡作品是先有畫好的底稿再用針線覆蓋。因此,構圖的理念同樣適用于刺繡中。構圖的元素與當地傳統文化以及民俗風俗息息相關。哈薩克刺繡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傳統的哈薩克刺繡圖案中,大多是自然界中的各種動植物、林中的飛禽走獸以及生活中到處所見的各種圖案等,這些生活中的經典圖案是刺繡中最常見的構圖元素[8]。徐州刺繡也是如此,在徐州刺繡作品中,出現最多的元素便是徐州具有代表性的戲馬臺,云龍山和云龍湖,以及代表兩漢文化的龍形玉佩。這些標志性符號都源于徐州深厚的歷史文化。基于歷史元素,徐州刺繡也與時代共頻,如今佇立于徐州市中心的蘇寧塔,也已是徐州刺繡的常用元素。除了元素的選用,徐州刺繡整體的構圖還講究“留白”,就像字畫一樣,刺繡的繡面也求一個“度”,而非要求“滿”,恰當的留白往往能賦予作品更精妙的美感。席建勛老師在做刺繡中一貫秉承著減法原則。可見,刺繡留白在徐州刺繡中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的。
4 文化是藝術創新的基礎
唐朝時期,沿海城市東臺因為常年長期遭受自然災害和少數民族戰亂等各種因素嚴重影響,存在各種民族宗教信仰及各種具有宗教性的祭祀習俗活動,信女為了充分表示自己信仰藏傳佛教的虔誠,剪下秀發,在絲絹上分別刺繡觀音或如來,朝夕叩頭,頂禮膜拜,發繡由此而來。東臺的發繡文化深受東臺佛教文化和當地少數漢族傳統民俗文化的深深影響,寄托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在漫長的發展歷史里,東臺發繡與東臺地區的民俗文化聯系漸漸緊密,“胎毛繡”“結發繡”等既飽含人文價值,又于精細作品中體現了其藝術價值[9]。由此可見,東臺地區發繡藝術的更新換代,正是在其本土地域文化的驅因下,在群眾不斷豐富的民族情感需求中進行的,其中所蘊涵的文化意蘊也因此深厚。
在徐州刺繡中,同樣有著因地域文化進行的藝術創新。在《錦繡彭城》系列作品中,銀杏葉是三幅作品的點睛之筆。邳州出土的《漢畫象石》顯示銀杏種植歷史十分久遠,最早可追溯到漢代,截至今天,邳州仍存在十余棵千年古銀杏,最老的一顆銀杏在白馬寺村,樹齡近1500 年。《邳志補古跡》就曾提到過它,“一在白馬寺,亦有銀杏(一株),頗奇古”。“十月下邳邑,金葉滿城堆。一畦秋風至,樹樹黃蝶飛。”無銀杏,不邳州。正因為這個濃厚的地方特色,席建勛先生在創作《錦繡彭城》時不走尋常路,大膽進行了藝術創新。人們現在看到的《錦繡彭城之山水云龍》中的銀杏葉并非全是穿針引線而來,落在最下面的那一片是真的銀杏葉。金葉滿城,翩翩落于錦繡之上,透露著金秋彭城之意境,象征著繡者對這片土地的誠摯熱愛。
5 總結
刺繡是一種有著悠遠歷史、厚重文化與創新特性的中華傳統藝術,有著非常深遠的文化內涵。現代徐州刺繡還處在發展期,知名度、推廣度和成熟度都比不上四大名繡,但是徐州刺繡背后的文化驅因是飽滿而深厚的。刺繡文化中幾千年的藝術內涵,徐州地區世世代代的地域特色和民俗文化,都在徐州刺繡的傳承和演變中得以窺見,不斷促進其針法的發展,影響著題材的選擇,賦予藝術表現與藝術創新源源不斷的生命力。
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一地一精髓,一域一特色,當代刺繡藝術在把握時代變化的前提下,博采眾長、兼收并蓄,正在憑借其優越獨特的傳承性、民族性和創新性,不斷煥發出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