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研究所,我的港灣
李 玫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2021年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建院七十周年的光榮之年,我所供職的音樂研究所是建院初期最早成立的幾個研究所之一。如今接到邀約撰文回顧我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淵源故事,榮幸之時,自己學術成長之路上的許多往事也如舊電影般涌上心頭。
在書中遙望音樂研究所
1978年,當我收到第一份大學錄取通知書時,滿腦子想的都是學音樂,當演奏家,因此,我放棄了中文專業的就讀資格,直到1982年才正式開始音樂專業的學習,這意味著我為自己選擇了一條音樂人生的道路。雖然懷著當演奏家的愿望進入大學校園,但音樂理論課程卻讓我更感興趣。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上大學前,我讀過豐子愷先生的《近世十大音樂家》和卡爾·聶夫的《西洋音樂史》,我甚至記得在70年代最普遍的露天電影院等待電影開始之前,借著黃昏微弱的光線努力閱讀五線譜譜例,想感受那個旋律的一個瞬間。因為沒有聽過那些杰出的作品,從當時的閱讀中我只是抽象地知道了西方音樂史的輪廓,并且感覺到音樂史的寫法與其他文體截然不同,這是作者對豐富的音樂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后形成的定論。1982年年底,沈知白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綱要》出版,當時定價六毛,這是我讀到的第一本關于中國古代音樂史的著作。但既然是綱要,當然就不是音樂史寫作的完成式。如賀綠汀先生在前言中所言:“這是一本提綱式的講稿……似乎還遠未完成。”這本約7 萬字篇幅的薄冊子,讀起來意猶未盡,特別是作者對一些史實只是簡單介紹,讓我更想知其究竟。當時我們還開設了中國古代音樂史課程,所用的教材是音樂研究所的吳釗、劉東升兩位老師合著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略》。這本“史略”也讓我更想知道“詳”,于是,開始啃起楊蔭瀏先生的經典之作——厚厚的,上、下兩冊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就這樣,我在書海的漫游中知道了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楊先生這部厚重的經典之作,在勾勒每個歷史階段的音樂事件和學術意義時,有幾乎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關于各時代人們在樂律學領域的探索,對古人的得失成敗,分析深入。對于這部分的書寫,體現出樂律學的學科特點,它所具有的嚴謹性和對讀者的知識結構的高要求,激起了我對樂律學的極大興趣。幸運的是,在那個“科學的春天”到來的年代,音樂研究所幾位前輩學者陸續出版了自己一輩子的學術結晶,隨著楊先生1981年出版了《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繆天瑞先生也于1983年出版了《律學》(增訂版),這使我的學習熱情立刻找到了具體的落腳點,花了許多時間鉆研律學。
由于在大學讀書期間對音樂理論的興趣,我對音樂生涯的想象已經不只是當一名演奏家,而在畢業時又正面臨著國家的經濟改革,全社會的關鍵詞是“責任制”,體現在藝術領域就是藝術團體經營的“雙軌制”和流行于全國的“走穴”演出,這與我自幼心目中的演奏家形象大相徑庭。這些原因讓我放棄了以音樂表演為生的理想,選擇了去《新疆藝術》雜志社當編輯。
在新疆得天獨厚的音樂文化環境中開始學術試步
我所供職的《新疆藝術》期刊當時有個立刊主導綱領,就是把這個刊物辦成“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陣地,所以,我每日閱讀稿件多涉此論域。地處新疆這個古代絲路必經之地,豐富的文化遺跡給藝術家們提供了豐富的創作靈感,也給文史哲各領域的學者們提出了許多研究命題,產生了豐富的藝術作品和研究成果。而我在這個藝術和學術的氛圍中,在研讀學習古代音樂史和一些絲路文化研究的論著過程中,有一個強烈的心得,那就是“文化西來說”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創作和研究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大量的研究著力于勾勒文化東漸的規模、內容以及對當時中原文化的影響。這讓我產生了一個疑惑:文化交流在客觀上應該是雙向的,為什么只探討文化西來而沒有反向流播?于是,我用從楊先生的《史稿》中學習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圖像資料、史料和文學作品信息中的蛛絲馬跡來尋找材料,并將它們建立起邏輯聯系,寫成了《古箏西漸探微》。在這篇文章中,我還運用從繆先生《律學》中學到的知識做了一段古箏上運律實踐的分析。有朋友讀過后說:“我認識每一個字,但說的什么一概不懂。”我聽了心里不免有點得意,以為這表明我的寫作已經有了“高深”的學術性。雖然今天想來還是比較幼稚,但我當時的確有著強烈主觀意愿要從音研所前輩的學術敘事中學習研究方法。

1987年夏,考察庫車地區石窟,此為在克孜爾石窟前的荒地上與新疆學者霍旭初、維吾爾族石窟保管員合影

1992年夏,在塔什庫爾干的田野工作途中,和塔吉克族牧民一起等待河對岸的牧民騎馬接我們過河
1987年夏,我因工作項目需要,跑遍了新疆南部的石窟和吐魯番地區的石窟,此外,還于1986年、1988年兩次前往莫高窟朝圣般地細細考查了幾乎所有的石窟,后來就很少有機會再進行如此完整、系統的觀摩了,因為莫高窟出于保護措施,有些洞窟已不再開放。這些經歷,最后形成了兩篇音樂圖像學研究論文:《新疆石窟壁畫中的漢風樂器》《箜篌變異形態考辨 ——新疆諸石窟壁畫中的箜篌種種》,并分別發表于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主辦的《中國音樂學》1991年和1994年的第4 期,至今還常被各地相關專業的研究生導師作為范文用來指導學生,《箜篌變異形態考辨——新疆諸石窟壁畫中的箜篌種種》這篇文章還被收入《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箜篌”條目的參考資料中,其英文版還于2014年發表在國際英文期刊Music In Art
上。在做編輯工作的7年中,我在內地和香港地區的報刊雜志上發表了數十篇學術論文和藝術評論文章。就這樣,我在音樂研究所學術前輩的引領下,向著學術之路蹣跚前行。1988年,我和新疆的作曲家周吉、邵光琛先生合作創作了古箏獨奏曲《木卡姆散序與舞曲》,這個作品以鮮明的風格及其獨創性,成為問世以來被演奏最多的作品之一,并被收入進多本古箏曲集。已故學者席臻貫曾撰文評價此作品“在學術上有著獨特的分量,可謂藝術與學術氤氳醇化為一爐”(《音樂愛好者》1990年第6 期),認為此作品有著學術性之負載。很顯然,這樣的發展方向是我從對音樂研究所前輩的學習中漸漸形成的。
第一次走近音樂研究所

1990年夏,中國樂器國際比賽獲業余古箏組一等獎,圖為獲獎后的演出照

中圖:1997年,在福建永定客家土樓了解當地民俗

右圖:鄉間行,與惠安女成了姐妹
在音樂研究所比我年長的學者中,我對黃翔鵬先生是陌生的,甚至連先生的模樣都記不起來了,但他的學術道路對我的影響卻是深刻而長久的。記得1991年我報考音樂研究所的研究生時,為了免除重復進京參考的路費,研究所專門為我在初試期間安排了復試環節的面試,那是我和黃先生唯一一次面對面的接觸。那時,恭王府顯得破敗凋零,遠沒有今天的王府氣派,但卻是全國各地學者心目中最欽慕的地方。我在一個光線昏暗的小屋里,心情興奮地等待著,當郭乃安先生、黃翔鵬先生及其他幾位所里的前輩依次入場時,我心中的興奮達到極點。現在想來,也在問自己,為什么當時不是考生應該有的緊張忐忑,而只有興奮呢?其實原因也很簡單,我得到了一次與大師們對話的機會,為什么要讓那沒用的情緒干擾到我呢!在面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們對我這位年輕后學的寬厚態度。他們讓我談談為什么要報考音樂學專業,我問我可以說得長些嗎?他們說,你隨便說。于是,我從幼兒時的會唱歌說到“文革”中無學可上,掰著手指學識譜;從做了張古箏學《漁舟唱晚》到放棄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一門心思想當演奏家;從對敦煌壁畫南北朝畫風的著迷,到對音樂圖像學產生興趣;最終,回到了我對“中立音”問題的困惑……我漫無邊際地說呀說,前輩們靜靜地聽呀聽,沒人打斷我的“信天游”。按照考試要求,我被要求彈奏一首樂曲。為了這次學術對話的機會,我準備了技術難度不高,卻具有史學意義的客家箏曲《出水蓮》。由于擔心被質疑演奏能力,我還準備了另一首難度較高的作品。不過這首《出水蓮》果然引起了黃先生等“考官”對歷史上客家民系遷徙在音樂史中留下的痕跡的感慨。音研所不以演奏技術判斷人的音樂修養,沒有人要求我表演技巧,客家箏曲中所透露出的中原聲韻和南國滋味才是理論家們更在意的。
這次考試終因英文成績而敗北,沒過多久,周吉捎來了黃先生的鼓勵:李玫很不錯,不要氣餒,再來!那次考試我還有另一個收獲。黃先生托我給新疆音協秘書長帶去他的論文集《傳統是一條河流》,我回到烏魯木齊后,和秘書長說這本書先借我看看吧,從此書就歸我了。以今天出版裝幀的標準來看,這本書的紙張、印刷和裝訂都太粗糙了,但它卻帶給我豐富的學術營養,書中所涉及的許多學術議題,成為后來我關注的重要論域。
從私淑弟子到嫡傳弟子
樂律學是音樂學的基礎,也是音樂研究所學術傳統的核心,這從楊蔭瀏、黃翔鵬先生的學術論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雖然不是音研所前輩的入室“嫡系”弟子,但從愿望到行動都是以研習樂律學理論為重,所以我把自己定位為音樂研究所的私淑弟子,通過認真研讀眾前輩的論著,私淑諸人。在我的學術研究道路上,由于音樂實踐的原因,我從一開始就確立了以“中立音”現象研究作為目標,并且把楊蔭瀏、繆天瑞、黃翔鵬先生的相關研究以及階段性結論作為對這個論題研究的起點。

2013年,在伊斯坦布爾參加國際音樂圖像學會議,擔任會議主持人
在全面尋找有關“中立音”現象研究既有成果的過程中,我看到了趙宋光先生在這方面的元理論表述。他深刻而清晰地闡述了在音樂流動中“中立音”形成的數理本質,這是在以往的研究表述中從未見過的一種思辨方式和陳述方式,它和中學時代我們得到的數理化三科思辨論證的訓練是一致的。這很吸引我!毫無疑問,我做了趙先生的學生,開始系統地學習趙先生的音樂形態學理論。為了揭開普遍存在于中國廣大區域的“中立音”現象之迷,在趙先生的啟發下,我將目光投向更久遠的歷史深處。匈奴、鮮卑、羯、氐、羌以及他們的先民在中國大地上馳騁縱橫的歷史陳跡與含“中立音”音調的地域分布必然有著不簡單的關系。以樂律學理論為基礎,用樂律學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作為研究抓手,我開始細心地對“中立音”現象進行形態學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從而實現了“中立音”現象理論解釋的原定目標。趙宋光先生于20世紀60年代在音研所的工作經歷及研究成果的積累,不僅為我后來的學術道路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學術任務,也實現了我作為音研所弟子的愿望。

李玫:《“中立音”音律現象的研究》《中國傳統樂律學》《東西方樂律學研究及發展歷程》
趙先生在音研所工作期間,有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即關于中國古代音樂理論“燕樂二十八調”的內在結構闡釋。他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在音樂研究所的整體學術氛圍中是那樣的渾然一體,他和楊蔭瀏先生有同有異的理論方法和實踐特征如同前后相繼并不斷生長的音樂研究所學術之樹上的繁枝茂葉,各顯風華,但都根植于厚重的中國學術傳統中,也都具有近現代科學發展給人文學科打上的烙印。趙先生在音研所工作時期的成果《燕樂二十八調的來龍去脈》(1964年4月油印本)集合為音樂研究所學術成就的一部分,這個成果成為20 多年后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燕樂二十八調”大條目的基礎。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在建所伊始,就集結了全國最頂尖的學者,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學科布局,樂律學是學科理論的基礎,目光聚焦在活生生的音樂實踐中,同時又投向久遠的歷史源頭,觀察每一種音樂事項形成的來龍去脈,這種學術風格包含著即時性和歷時性的雙重視角,形成了音樂研究所特征鮮明的學術傳統。前輩們的學術論著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學術影響力,很多議題的結論或觀點是所里前輩們在長期的探索實踐中形成的共識,而且呈不斷發展的趨勢,并沒有一論定終生。比如楊蔭瀏先生在生命末年,仍有文章反思自己數十年前的結論,修正過去自己曾經發表的觀點;繆天瑞先生的《律學》經三次修訂和增訂,還在不斷打磨;黃翔鵬先生筆耕勤勉,除了在三部論文集和一本《樂問》中討論豐富的中國傳統音樂問題外,還用一本《中國傳統音樂一百八十調譜例集》對自己的理論進行實證研究。我徜徉在這條學術之河中,不斷成長、成熟,承蒙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各位前輩、學長的關愛,2000年獲得博士學位后,我就來到音樂研究所工作,從此我的學術小船終于駛入向往已久的港灣。
在音樂研究所工作的前十年,我出版了《東西方樂律學研究及發展歷程》和《中國傳統律學》,這兩部新著不僅努力改善了此領域原有成果中學理表達方面的不足,還提升了方法論意識及分析手段,增添了許多過去同類著作中沒有的內容,特別是一直圍繞著樂學實踐來談律學問題,使長期以來律學研究的冰冷面孔變得生動而富有現實意義。樂律學前輩趙宋光先生在《東西方樂律學研究及發展歷程》一書的“序”中指出:“利用信息時代的傳媒,利用國際文化交流的嶄新渠道,獲取了許多前所未知的史料,進一步拓寬視野。這是我幾十年來做不到的。這令我在通讀這部書稿時由衷涌起陣陣感激之情。”
在楊先生和趙先生的“燕樂二十八調”研究的基礎上,我展開了進一步的研究,終于在經歷了15年的冷板凳后,出版了《“燕樂二十八調”文獻通考》。這項工作是對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繼承與超越,彌補、修正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這樣的自我表述并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學術研究和學術史發展應該做的,因為我有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因為科技信息技術的發展,讓我有幸得到了更為豐富的資訊,看到了更多的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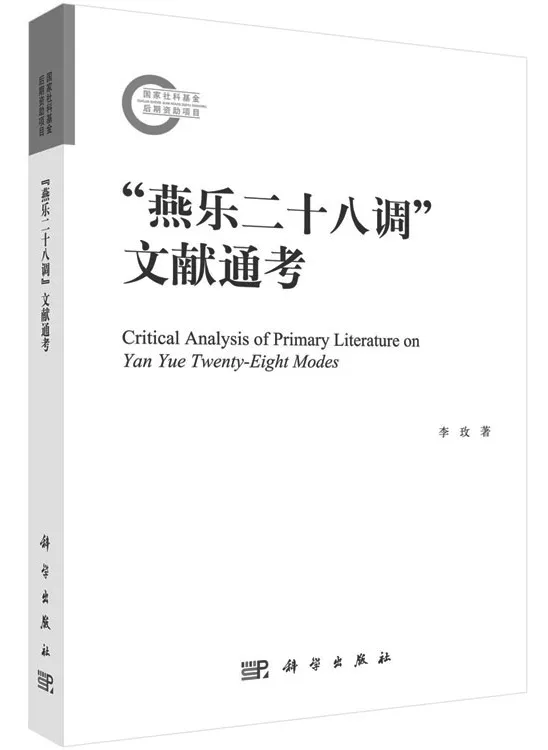
李玫:《“燕樂二十八調”文獻通考》
在音研所這個港灣感受到的學術熏陶和激勵,令我在學術的道路上能夠心無旁鶩,時刻準備著在一個新的議題上再次出發。有同事看著我這些年所關注的領域以及所有的學術表達,很感慨地說:“你真正繼承了音研所的學術傳統。”我聽了這樣的評價,如同獲得一枚榮譽很高的獎章般高興。
我沒有機會親身感受楊先生、黃先生討論學術時的狀態,但在趙宋光先生身上卻可以看到,無論身體多么孱弱,一旦論及學術問題,他的生命之光就燃燒起來。在音樂研究所這20年的學術生涯中,我對王國維用宋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所寓意的學者境界有了漸行漸深的體會,而且這體會帶給我真正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