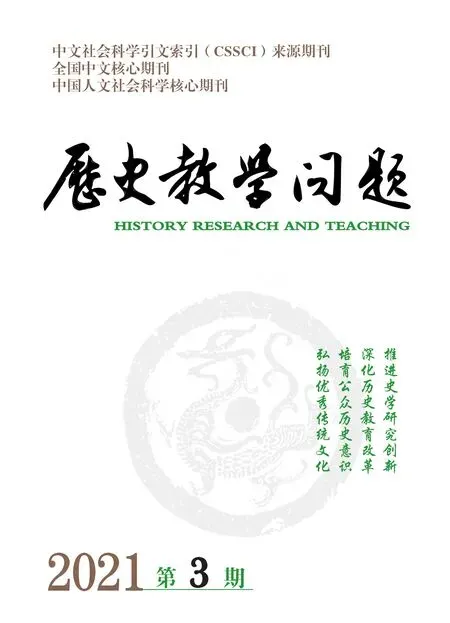大變局時代的世界史研究
俞 金 堯
更好地觀察和認識世界,從來都是中國的世界歷史研究的一個基本任務。從近代中國人開眼看世界起,世界歷史這個領域就引起人們的關注,體現出世界史這門學問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新中國成立以來,世界歷史專業的發展、壯大,與時代的進程關系更加密切。“世界歷史”發展成為“一級學科”,就是在中國成為具有全球影響的世界大國的背景下實現的。可以說,世界歷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是時代的產物,是時代造就了世界史專業。而世界史專業的發展,也與時代同步。
當今世界處在“大變局”的時代。2017 年12 月28 日,習近平在接見回國參加2017 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時發表講話,首次公開、明確地提出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他要求使節們“正確認識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
如今,這個關于世界格局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的判斷,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廣泛共識。2020 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發表的公報兩次講到“大變局”,不僅重申了“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指出,“全黨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事實上,并非只是中國人認識到世界處在巨變之中,國際社會也普遍認識到世界格局正在發生的大變遷。2019 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一年一度的外交使節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說,國際秩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破壞,這可能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這種動蕩中最重要的是一種轉變,地緣政治和戰略的重組。他說,西方可能正在經歷對世界霸權的終結,此外還有新勢力的出現,而我們或許長期低估了其影響,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當然還有俄羅斯,還有正在崛起的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正在成為經濟和政治大國。他還說,隨著西方時代的結束,歐洲也將消失,世界將圍繞著兩個主要焦點:美國和中國。如果歐洲不能作為一個整體發揮作用,那么,歐洲就只能在這兩大力量之間進行選擇。
盡管馬克龍沒有使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一個確切的說法,但是,他對世界格局發生大變遷的認識是十分明確的。他是站在法國和歐洲的角度看到了世界格局正在經歷的大變遷:可能正在經歷西方對世界霸權的終結。世界局面已經發生了改變,新勢力已經出現。馬克龍所講的這些新勢力,正是我們所說的新興的市場經濟共同體中的主要國家。
除了馬克龍的講話,世界格局發生巨變的最明顯的事實,就是近幾年美國陸陸續續地退出許多國際組織:如2017 年6 月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2017 年10 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 年5 月退出伊核問題全面協議;2018 年6 月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等。這些組織是聯合國的重要組織,這些協議則是在聯合國主導下達成的全球性協議。美國頻頻“退群”行為說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形成的世界格局,以及自20 世紀80、90年代以來由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可見,當今世界進入大變局時代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而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加速了世界格局的變遷。尤其是中國率先控制新冠疫情,實現經濟恢復性增長,2020 年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2.3%的增長率,經濟總量超過了100 萬億元。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一個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和比重,加速了變遷的趨勢。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世界格局快速變化所包含的風險,國家和地區間的競爭、西方國家對于正在崛起的新興經濟體的圍堵和打壓,使得世界所面臨的風險急劇增長。世界大變局究竟會走向何方?世界近代以來的歷史上經歷過的變局,是否可以為今天經歷著變局的人類提供有意義的借鑒?大變局是否能夠向正在邁向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中國提供有力的條件和機會?這些問題是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要考慮的問題。盡管大變局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但“百年未有”這個前綴,決定了“大變局”也是一個歷史問題。這就給世界史研究這個具有高度時代特征的專業提出了新的任務:世界歷史研究究竟如何滿足時代的要求,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
這個問題當然不易回答,因為大變局不僅僅是一個長期的趨勢,更是一個復雜而廣泛的變遷過程。不過,世界史研究如何回答時代的問題,以及在大變局時代如何做世界史研究,還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我在此有幾點想法:首先是要轉變觀念,把歷史研究與現實需要相結合,帶著現實關懷去研究歷史。
歷史研究中一直存在兩種取向,一種是做單純的歷史研究,盡量與現實無關;另一種是結合現實問題進行研究,所謂“古為今用”就是這個意思。然而,事實上,前一種取向壓倒后一種取向,并且或多或少存在著對后一種取向的“鄙視鏈”。結果,歷史學者大多不夠關注現實,而把那些需要從歷史的視角進行理解和闡釋的現實問題,留給了現狀研究。例如,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主要集中在國際問題研究方向上。在出版方面,以“大變局”為主題的文集已不在少數,從有關文論來看,國際問題專家偶爾也追溯一下世界大變局的歷史,但他們所做的工作終究不是世界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學者對如此重大的題材投入不足,“古為今用”的意識顯然還不夠敏銳。
當然,歷史學者最近也開始介入這個問題的研究,例如,在2019 年12 月,《光明日報》編輯部與貴陽孔學堂文化傳播中心舉辦了“多學科視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壇。在這個會議上,有一些歷史學者對于當前的世界變局提出了歷史學的認識;2020 年10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優勢學科“歐美近現代史學科”的歷史學者與上海世界史學界的同仁們,在上海師范大學光啟中心舉行了“大變局之際的世界史研究”學術會議,就大變局與世界歷史研究的關系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世界歷史》編輯部在2020 年第6 期就“世界史視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表了一組“筆談”文章;現在,《歷史教學問題》編輯部又專門組織這次以大變局為主題的“筆談”,等等。這些活動表明,“大變局”與世界歷史的關系正在進入世界歷史學者的視野,世界歷史研究的時代性在“大變局”這個問題上開始得到顯現,我們期待從世界歷史視角更加深刻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思想和觀點將會逐步呈現出來。
世界歷史研究者的這種轉變很有必要,因為“大變局”不僅僅是當前正在發生的事情,更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世界面臨”與“百年未有”并提,表明了這場“大變局”不僅僅是一個現實課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它在世界歷史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位置。事實上,在明確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前,習近平在有關講話和文件中,曾經提到過世界正在經歷的巨大變遷是“近代以來”、“數百年以來”未有的變局,這樣的時間限定表明,我們要深刻理解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大變局,必定要它放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來認識。如果缺乏歷史學專業所提供的足夠的時間深度,我們很難認識大變局的真正意義。
第二是世界史工作者有責任為社會提供認識現實世界所需的歷史觀和思維方式。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的整體性聯系空前緊密,中國已經成為這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現實世界與它的歷史發展過程不可分離,可以說,現實世界就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其中包含了歷史的邏輯和必然性。世界、歷史和現實這三者不可分割的關系,使得世界歷史專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它能夠為社會提供深刻理解當今世界格局及其發展趨勢的觀念和思維方式。
習近平多次講到過“歷史思維”的重要性,他把歷史思維當作治國理政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其實,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上來講,歷史思維也具有獨特的價值。例如,對于歷史大趨勢的認識,把全球化放在15、16 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中,我們很容易看清,全球化是在一個長期的、不斷加深的歷史過程,這個趨勢不會因為當前出現一點波折而被打斷,更不用說會出現倒退。現在,媒體和社會上的一些人往往把當前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波折,說成是“逆全球化”,這可能是因為缺乏歷史深度、不能把握歷史趨勢而得出的看法。從長期的歷史趨勢來看,全球化不可阻擋。所謂“逆全球化”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全球化的路徑選擇。歷史進程的延續性在全球化的歷史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這個認識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對待全球化在當前面臨的困境,有助于我們以淡定的心態等待全球化新階段的到來。另一方面,歷史的思維也需要我們以變遷的眼光看待現實世界。例如對概念的認識,大體上,抽象的概念或觀念具有穩定性和同一性,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個概念可以一直延續下來,至今仍被人們廣泛引用,不過,它的內涵可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平等”“民主”“資本主義”等概念就是這樣。這些概念我們一直在廣泛使用,但是,自從它們出現以來,內涵多有變化,它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意涵。準確理解它們的內涵,需要把它們放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厘清它們的變遷,是世界歷史從業人員的責任,我們應該為社會提供現實所需的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思維。
第三是要繼續進行宏觀歷史研究,構建新的宏大敘事。
“世界歷史”就其本義而言就是關于“普遍的”歷史,是具有普遍意義的通史,也是在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歷史知識體系。對于人類的歷史進行總體的概括和敘述,就是這個學科的存在依據和價值所在。“世界歷史”就是一種宏大的歷史。
人類對于自己的歷史有一個總體的認識,是一種內在的需要。“世界歷史”,或以任何其他名義出現的關于人類發展總體進程的歷史,是從來就有的,只不過這種歷史編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形式罷了。《圣經》和歷史上的基督教理論家為古代和中世紀的人們提供了具有基督教性質的關于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到近代,在理想主義、樂觀主義和進步思想的支配下,人們又構建了具有啟蒙特點的宏大歷史,這種歷史給予身處現代的人們認識自己的時代和預見未來的信心,是一種直線式發展、不斷進步的大敘事。最近幾十年,隨著后現代思潮的泛濫,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已經失去了往日的風采,它被解構,或者正在被解構。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開始疏遠宏大敘事,轉而關注微觀研究,微觀史研究一時成為史學的風尚。以至一些人認為,歷史研究現在處在“碎片化”狀態。
歷史研究中有沒有“碎片化”,這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因為微觀的歷史研究與研究“碎片”不是一回事。有一些“碎片”的研究與研究中出現“碎片化”的趨勢,又是一回事。微觀史研究的興起是史學發展的結果,某種程度上,是對啟蒙運動以來所構建的宏大敘事的修正,甚至反動。在這里,對于具有“現代性”的宏大歷史的批判,并不意味著對宏大歷史的否定。事實上,充分的微觀史研究也具有重構新的宏大歷史的價值,而好的微觀史研究總是與宏觀歷史進程相得益彰,互為補充。因此,微觀與宏觀的歷史研究本來就不是互相否定和對立的關系。令人遺憾的是,在現實當中,雙方因為互相誤解而使微觀史研究與宏大敘事割裂開來,的確是一個事實,這大體上就是歷史研究當前面臨的困境之一。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說,宏大歷史敘事是人類的一種內在的需要。我們可以解構或修正不適應時代需要的宏大歷史,甚至重新構建一個符合我們這個時代要求的世界歷史體系,而不是在解構了過去的宏大敘事以后,就不再需要新的世界歷史大敘事了。以為微觀的歷史研究可以取代大歷史,這種想法與那些一講微觀史研究就想到“碎片化”的人,犯了同樣的毛病。后現代主義和新文化史高舉的是“多樣性”的旗幟,宏大敘事應當包括在“多樣性”之中,而且應當是眾多樣式的歷史研究中最有魅力、最能滿足人們內心需求的一種。所以,歷史學在經歷了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新文化史的洗禮以后,應該呼喚新的宏大敘事。
回到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主題,關于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如何進行我們的世界歷史研究,這個主題本身就包含了對歷史進行宏大敘事的要求。“世界歷史”的本質特征就是對人類歷史進行宏觀建構,揭示宏大趨勢,敘述大進程是這個專業的使命。倘若不是這樣,“世界歷史”的意義在那里?世界史工作者又能如何解答大變革時代給我們提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