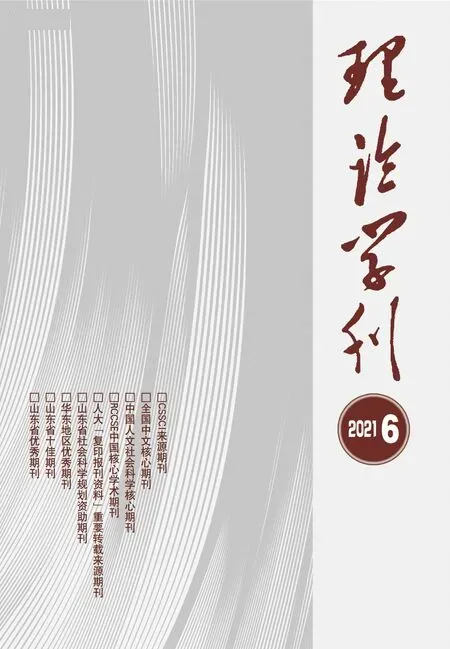政策變遷的動力機制:基于政策動力學的理論解釋
楊志軍
(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一、引言:政策變遷研究的重要性
相較于政治變遷、經濟變遷和社會變遷等理論的發展,政策變遷在當前學術界的受重視程度還有待提高,仍具有極大的探索空間。
首先,政策變遷是政策科學研究的核心詞匯。政策科學創立者拉斯韋爾指出:“我們應該意識到政策過程本身是一個適合的研究對象,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需要提高決策的理性程度。”(1)H.D.Lasswell.The Policy Orientation,in Lerner and Lasswell,ed.,Policy Scienc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Metho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5.正是從決策到終結的周期性循環,才產生了基于政策過程的變遷行為。從拉斯韋爾初創政策階段論再到薩巴蒂爾等匯集政策過程論,都在揭示政策過程周期性變遷的規律和特點。
其次,政策變遷是比較公共政策研究的重點議題。拉斯韋爾和德羅爾都想將政策科學發展成為一門全科性的綜合社會科學,然而在實踐中政策卻逐漸成為彌合政治與行政“二分”的手段。這種情形打消了政策科學試圖成為社會科學“母”科學的設想,其應用性和分析性使得比較公共政策學開始興盛,實證與后實證政策科學相結合,探究了不同國家的政策變遷議題。
再次,政策變遷的內生規律與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等相似。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遷的本質是追求公平、公正、均衡和可持續,讓人類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實現這些目標需要相對主義目光和長期視野,必須正視“均衡—不均衡—均衡”規律。政策變遷與之相類似,國家建設走的就是一條從原初狀態的均衡到現代化進程的不均衡再到終極目標實現的均衡的道路。
最后,政策變遷的外部效應經常是非常規的社會沖突。政策變遷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從而產生外部效應。例如,鄰避設施建設的負外部性容易產生地方政府非常規政策變遷行為,反映出政府治理缺陷,也會造成一定的經濟社會影響。政策變遷的正當性本身就來自于民眾的信任,而地方政府治理如果損害了這種信任,勢必就會消耗掉政策的效力,帶來社會沖突。
政策變遷的范圍和所產生的影響雖然不如政治和經濟變遷,但是業已成為與政治變遷和經濟變遷等相對應的常量。政策變遷在線性生成邏輯上立足于政策過程全周期循環規律,在散性相關邏輯上則與國家、市場和社會緊密相關,前提是探究其動力機制,即政策變遷是什么、何以發生以及如何發生。這是公共政策研究中關于政策過程及其變遷的本源性知識,也是找到核心解釋機制的必由之路。
二、政策變遷的原因和形式
政策變遷是指當前政策被其他政策所取代或者一種既定政策的改變過程,其意義為:不論是受到外在條件還是內在因素的影響,很少有政策能夠一直維持當初被采納時的形式,恰恰相反,政策在制定之后就處于持續不斷的變動狀態。政策變遷的方式是新政策的采用和現存政策的修正或廢止,有人將其概括為“演化路徑”(2)J.J.Stewart,D.M.Hedge,and J.P.Lester.Public Polic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3rd).MA: Cengage Learning,2007.,具體有:(1)現有政策的漸進改變;(2)特定政策領域內新法規的制定;(3)選舉之后的重大政策轉變(3)James E.Anderson.Public Policy-Making:An Introduction(Fifth Edi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3,p.171.。豪格伍德和彼得斯根據政策變遷的程度,將其劃分為四種形式:政策維持(Maintenance)、政策接續(Succession)、政策創新(Innovation)、政策終結(Termination)(4)Hogwood,W.Brian and Peters,B.Guy.Policy Dynamics.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1983,p.25.。這些形式不僅在實踐中極具解釋力,在學術領域也沿用至今。在這里,需要探討政策變遷何以發生和如何發生、以及本部分的主題——政策變遷的原因和形式。
政策變遷為什么會發生?一是為了擴大政府的治理功能。從現代官僚制建立以適應工業化需求,特別是受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思想影響和應對周期性經濟或金融危機以來,政府治理無論是在職能上還是規模上都呈擴大趨勢。這種趨勢一方面來自于應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需要建立高度專業化和部門化的政府治理體系,另一方面則來自于政府體系運行發揮治理作用亦需要連續的政策體系和大量的政策依據。換言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有效率的政府治理體系,而政府治理功能的發揮需要依靠專門政策以解決各式各樣的實際問題,即以政策合法性體現治理合法性。二是為了解決當前政策的效果不彰。政策變遷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政策執行與決策預期之間出現了偏差。政策執行中出現的諸如象征性執行、選擇性執行甚至扭曲性執行的問題,固然與下級政府的意愿和能力相關,但更重要的是與決策環節的關門模式以及不了解實情的“辦公室決策”(不重視和不善于調查研究)等問題相連。因此,只有科學決策得到有效執行,才能保障政策效果,而當二者出現背離時,必須通過政策更新等方式,尋求政策改變。三是為了避免政策快速終結。政策之所以終結,一方面是因為政策方案不合理,如流浪漢及精神病人的強制收容政策,另一方面則因為政策一經發布,反對聲音居多,如建設避鄰設施項目的相關政策。如若一項政策從決策到執行都沒有問題,僅僅是效果不彰,那么就不必予以終結,可以通過政策補丁和更新的方式來實現小幅調整。政策無序終結會造成決策權威喪失,經濟損失不可小覷,因此建立接續式和平穩性的常規政策變遷形態很有必要。
政策變遷的形式如何生成和比較?按照前述劃分,政策維持是指原有公共政策維持不變;政策接續是指對原有公共政策作漸進調整,變動幅度不大;政策創新是指在特定政策領域制定一項全新的法律或計劃,以取代舊的政策;政策終結是指終止或廢除原有政策,代之以新的政策。歸類來看,政策變遷只有兩種類型:一是政策的修正調整,二是政策的終止實施。與政策變遷所呈現的規律一樣,既有激進的突發的甚至是臨機性的間斷性(非連續性)變遷,也有均衡的連續性變遷——漸進調適、有方向性以及有限范圍的改變(5)Starkie,D.Policy Changes,Configurations and Catastrophes.Policy and Politics,1984,12(1),pp.71-74.。在上述四種形式兩兩對比的基本關系中,政策維持與接續為一組,政策創新與終結為一組。政策終結意味著現行的政策被其他政策直接加以取代,是一種直線型政策變遷形式;將某些過去的舊政策并入新政策當中,以強化新政策的內涵,則可以有政策接續、政策更新、政策補丁等形式,是一種強化型政策變遷;將某項政策或計劃分成兩種或多種以上的內涵(機構或政策)屬政策創新,是一種分離型政策變遷(6)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13年版,第477—478頁。。目前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于直線和分離型的政策創新和終結,而對強化型的政策維持和接續的關注不夠。究其原因在于,地方治理活動往往呈現出較強的變動性和創新性以響應中央的指令、戰略和規劃,而中央政策則常以穩定的和可持續的狀態出現,例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長期科技政策等。實際上,政策創新在各級政府治理實踐中并不常見,相比較而言,政策試點更符合中國地方政府治理創新的實踐邏輯。正因為如此,物以稀為貴,一旦有政府治理創新或政策創新出現,社會輿論就會非常重視,從而形成“注意力經濟”,連研究者自身也不例外。所以,政府治理要維持體系穩定性,就會更加注重政策維持,以政策接續來體現創新,以政策終結來響應指令。在實際情況中,政策維持與接續遠比政策創新與終結更為普遍。
那么,政策變遷為什么會出現上述四種形式?首先,從人類本性上來說,每個人都摻雜著感性和理性因素,不是某一單一體,而是二者混合體。從感性(非理性)因素來看,人們喜歡驚險、刺激和挑戰,厭惡平淡、寂寞和退縮,但是在理性上則相反,人們更喜歡安全。政策尤其如此,所有的政策行為都是一個理性綜合體(7)A.Somitm,S.Peterson.Human Nature and Public Polic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NY: Palgrave MacMillan,2003.。就政策決策而言,人類經歷了從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漸進理性的演變過程,在不斷走向可預測、平穩和可持續。這一點與國家治理的系統性、復雜性、模糊性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極其相似。由于國家治理牽一發而動全身,是一個系統工程,創新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因此更需要平穩接續和漸進調適。其次,從漸進主義決策觀點出發,厭惡風險是龐大的政府類公共組織的共同特征,而不同形式的創新均具有風險。在政策制定、執行、評估、終結所構成的直線型政策變遷過程中,雖然我們常用“創造”“誕生”“創新”等名詞來形容新政策的提出,但實際上新政策在政策議程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大部分的政策制定都是以政策接續的方式出現(8)Hogwood,B.W.,and Peters,B.G.The Dynamics of Policy Change: Policy Succession.Policy Sciences,1982(14),pp.225-245.。這既是實踐中的情形,也是政策過程循環周期論所得出的結論。
在政策變遷與政治變遷、經濟變遷、社會變遷、文化變遷同等重要的前提下,如果說揭示“為什么會產生政策變遷”是在解釋其條件和背景,那么分析四種政策變遷的形式就是在展現其樣貌。原因的揭示重點在于其內外結合的條件,形式的描繪重點在于其不同的風格,于是我們有必要追問:政策變遷的動力機制是什么?政策變遷動力機制在學理上隸屬于“政策動力學(Policy Dynamics)”的解釋范疇,最早來自于輿論學的傳播動力途徑,后續被運用到比較公共政策領域,最近則是二者的結合,從而形成了議程動力(9)Frank R.Baumgartner and Bryan D.Jones.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2nd e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輿論動力(10)Mary Layton Atkinson,K.Elizabeth Coggins,James A.Stimson,and Frank R.Baumgartner.Three Models of Opinion Dyna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信息動力(11)Frank R.Baumgartner and Bryan D.Jones.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Problem Definition and the Course of Public Policy in Americ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等研究。依據政策動力學前沿理論和政策周期循環論的觀點,本文認為,政策過程順時針和全周期演進,在與外部沖突、沖擊和影響相結合中產生了三大變遷機制:直接觸發機制、常規運行機制、核心穩定機制,分別對應于選舉、議程設置和偏好。
三、選舉是政策變遷的直接觸發機制
選舉的意義何在?西方國家中政府的政策重點反映了政黨競爭在選舉中提出的正式計劃。克林格曼等人認為,承諾與績效之間的一致性是所謂“民主”的核心(12)Klingemann,H.D.,Hofferbert,R.I.,and Budge,I.Parties,Policies,and Democracy.Boulder,CO: Westview,1994.。選舉被用來指稱民主,并被當成民主的必備要件,從熊彼特到薩托利,都認為民主的實質就是“競爭性選舉”,從而把“競爭性選舉”作為劃分有無民主的根本標準(13)[美]薩托利:《民主新論》,馮克利、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頁。。熊彼特認為:“民主方式是為達成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在此安排下,個人在爭取人民選票的競爭中獲得決定權。”(14)[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吳良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69頁。達爾推進了一步,將一個以政治商討、競爭性選舉和多元精英為特征的政體視為現代民主的唯一模式(15)[美]羅伯特·達爾:《民主及其批評者》,曹海軍、佟德志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5頁。。亨廷頓也表達了相同的旨趣,即“如果用普選的方式產生最高決策者是民主的實質,那么民主化過程的關鍵點就是用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通過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16)[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7頁。。由此可見選舉對于西式民主的重要性。這些活在20世紀的西方學者還認為,以發達的民主制度、成熟的競爭性選舉等為基礎的多元主義,必須依賴高度發達的所謂公民社會才能夠實現政治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20世紀以來,選舉由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武器逐漸成為西方國家傳播自由價值觀的手段。如果追求自由是天賦人權,投票選舉產生最高國家領導人以及各層級行政長官是在踐行這些權利,那么選舉產生政府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回到為民服務和高效行政上來,但事實上,西方國家選舉在形與神、表與里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背離,并沒有解決權利自由和高效治理之間的矛盾。不論是從西方媒體所揭露出的事實還是從可觀察到的視角來看,西方國家政黨競爭性選舉通過廣泛政治動員(一般是4年一次)稀釋和轉移國內矛盾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而這一現象的本質就是,其只停留在通過綱領和口號的宣揚傳播來對外輸出以偏概全的自由價值觀,而對于真正關系到公民福祉的行政作為以及高效治理卻避而不談或束手無策。選舉要么被民意裹挾,要么被民粹利用,成為政黨之間追逐選票以求獲得勝利的工具。因此,打破以選舉論民主、以選舉講政策的局限,需要采取不偏不倚、執兩用中的哲學思維,即既要將選舉作為一種長期運行的實體機制和一項存在廣泛政治效應的客觀事實,也要清醒認識到選舉只是民主的要素,不是唯一,也不是全部。選舉的自由價值一方面被廣為贊頌,另一方面又屢遭詬病,如何做到實質性民主和程序性民主的統一,才是問題的本真所在。政策變遷對此提供了有力的新視角,作出了新的解釋,這在以往很少被發掘。
首先,國家治理重在實效。選舉機制及其功能在目標導向上是要實現實質性民主和程序性民主的統一,從而在機制橋接上為國家順利且正當地實現政策變遷提供機會,是一種直接觸發機制。西方選舉表面上宣揚全社會最廣泛的政治情緒,實質上則是要建構國家議程,實現某種注意力轉移。所以,政黨競爭性選舉要想在政策綱領和治理行動上有所作為,就必須實實在在地將實質和形式(程序)兩個民主的內涵統一起來。同時,如果選舉不能用政策變遷來進行機制橋接,那么就會陷入自由價值一直被詬病而實際治理效果一直未達成的窠臼;如果政策變遷不能用選舉來進行內涵充實,那么這些以各種各樣、各式各類政策作為手段或根據的國家治理行為就缺乏一種正當性來源。
其次,從確保“人民當家做主”的實質性民主和實現“民主過程”的相關制度、機制和規則的程序性民主兩種形式相統一的角度來看,選舉之于政策變遷并作用于國家治理的意義就在于成功地實現了公眾注意力轉移。因為選舉是一場最廣泛的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有可能凝聚共識,也有可能撕裂共識。從負值和正值相抵消,亦即從“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角度,選舉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并被廣泛使用,就在于凝聚共識,最大程度地避免共識撕裂的危險,如有(共識撕裂)發生則需要重新聚合共識,這是選舉的正向功能。在程序性民主上,政黨之間在綱領、政策上相互較量,形成某種注意力轉移。愷撒的物歸愷撒,上帝的物歸上帝,注意力轉移分開了所謂的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使民眾具有更強的辨識和反思能力,從而提高國家文明程度。但在注意力轉移過程中,最根本的還是要把一種消極的負面的注意力轉移到積極的正面的注意力上來,在不同政黨的綱領輪換和政策變遷中體現人民意志,這才是選舉民主的根本價值。
最后,政黨之間的選舉較量也會形成一種注意力轉移運動,這種注意力轉移通常是黨派的、跨國的以及動態的。具體而言,以一國中兩個政黨A和B為例,如果政黨A對某個問題具有優勢,便更喜歡談論這個問題,希望獲得主動權,然而政黨B并不能因為政黨A占得先機而選擇放棄重視這個問題。這種在政黨競爭運動中發生的政策注意力轉移,往往傳遞出非常明顯的政治立場,美國總統大選中1964年巴里·戈德沃特的慘敗和1980年羅納德·里根的成功就是例子。
如果把這種注意力轉移放置到政策變遷過程中,那么政黨該如何在選舉環境或政策制定中發揮作用?許多理論已經指出,政黨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們“擁有”的那些問題上(17)John R.Petrocik.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With a 1980 Case Stud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6(40),pp.825-850.,從而產生了三大原則,即支配性原則、分散性原則以及融合性原則。其中,支配性原則表明,如果一個政黨在給定問題上相對于另一政黨具有優勢,則應將注意力集中在這點上,如果雙方都沒有優勢,那么分散性原則就會建議雙方都應該避免討論。但是,如果雙方都不愿意或者不需要討論當前的重要問題,那么融合性原則會出現嗎?此時,各政黨需要聚合到選民所在地,看各自在多元流程中的表現。首先,各方是否成功地將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他們有優勢的問題上,取決于他們面對問題時所展現出來的勇氣和智慧。其次,媒體更對政黨之間的沖突感興趣,有的時候選民看到的只是媒體的偏好,而并不能準確和及時地知曉政黨的傾向。再次,權力制衡架構對于選舉的注意力轉移功能亦有影響。有學者對丹麥議程項目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議會反對派的成員可以把他們的問題集中在那些最可能使現任政府難堪的議題上,因為媒體和民眾都有興趣看到黨派混戰(18)Green-Pedersen,C.,and Mortensen,P.B.Who Sets the Agenda and Who Responds to It in the Danish Parliament? A New Model of Issue Competition and Agenda-Setting.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009(49),pp.257-281.。還有學者研究了1960年至2000年《紐約時報》關于總統競選活動的約10286個新聞報道,發現競選最受關注的四個議題分別是種族、社會保障、稅收和支出、國防和國家安全,總統候選人必須高度重視這些議題(19)Sigelman,L.,and Buell,E.H.,Jr.Avoidance or Engagement? Issue Convergence in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1960-2000.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4(48),pp.650-661.。這表明注意力轉移的機制還是政策及其變遷。
選舉所帶來的注意力轉移運動已成為一種常態,而注意力轉移的焦點是調動國民情緒,傳達某種意識形態。政治科學對此研究有限,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科學家關心選舉太過于“科學”,主要將注意力放在了理解人們如何在特定的選舉中投票以及影響其行為的心理因素上(例如關于投票的大樣本調查、實驗分析等)。注意力轉移運動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立場,比較公共政策專家擅長運用社會科學方法來測度這種變化,例如通過“政策情緒”來測度為什么一部分老百姓支持政黨A而不是B,以及這種一貫的支持或反對及搖擺不定的支持立場如何形成注意力轉移等(20)Stimson,J.A.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Moods,Cycles,and Swings (2nd ed.).Boulder,CO: Westview,1999.。不管是政治科學還是比較公共政策學,都發現政黨意識形態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重大變化,并且這種變化有可能是在走向趨同,同時這種變化也關系到主要西方國家政治立場的走向。這或許意味著在多元主義歷史文化中所孕育的政治思潮有可能走向提升政治整合力的統合主義路徑,尤其是這種統合主義路徑在其他一些國家還起到了促進政治發展的作用。
總而言之,在議題和時間兩個維度上,注意力轉移都應納入對政策變遷的總體理解之中。更全面的考慮要素應該是選舉轉變、與選舉無關的信息動態、制度設計和針對特定問題的解決方案等。如果某個議題一開始沒有與單個政黨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那么就需要分析注意力分配、備選方案選擇以及政策議程設置等政策變遷因素,而不是只關注問題的呈現情況。政黨之間在不同問題上的分歧恰恰是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作為一種常態而存在的。這種分歧可以被激活,也可以被關閉,還可以開展政策辯論,這樣就需要將選舉之于政策變遷并作用于國家治理的意義作為民主價值與治理效能的關系變量進行重新評估。這種評估必須面對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倡導民主價值和實際治理效能之間存在的二律背反困境,評估的關鍵是選舉機制及其過程和功能所展現的實質——注意力轉移運動如何形成政策變遷及其效果。
四、議程設置是政策變遷的常規推動機制
選舉是政策變遷的直接觸發機制,但是不能期望選舉機制包含所有任期內出現的問題,議程設置才是政策變遷過程中最常規的運行機制。1972年,科布和埃爾德一起提出了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21)Cobb,R.W.,and Elder,C.D.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Agenda-Building.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2.,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正式提出了“媒體議程→公眾議程→政策議程”的議程設置模式(22)Maxwell E.McCombs and Donald L.Shaw.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2(2),pp.176-187.。隨著互聯網和新興社交媒體的出現及蓬勃發展,議程設置的混合交互模式越來越明顯,但在很多學者看來,媒體議程依然重要,正如伯納德·科恩所言:“媒體無法告訴我們該怎么想,但是他們可以告訴我們要怎么想。”(23)Cohen,B.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近十多年來,議程設置在理論與實踐的融合度上得到很大提升,開始轉而探討政策問題與政治爭議之間的關系。這一點可以溯源到“主權在民”形式(24)Schattschneider,E.E.The Semi-Sovereign People.NY: Holt,Rinehart & Winston,1960.以及權力的“兩種面孔”(25)Bachrach,P.,and Baratz,M.The Two Faces of Powe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2(56),pp.947-952.,到了20世紀晚期才聚焦到政策議程的新形式上。金登的多源流框架(26)Kingdon,J.W.Agendas,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MA: Little,Brown,1984.、鮑姆加特納和瓊斯的間斷—均衡理論(27)Frank R.Baumgartner.,and Bryan D.Jones.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2nd e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等紛紛指向議程設置始于政府議程空間稀缺的假設,即決策機構注意力稀缺是理解高度動態的決策過程的關鍵。作為政策變遷的初始環節,議程設置是一個完整的前決策過程,包括從問題出現到問題界定、篩選再到議程設置過程,其實質是注意力分配,意味著既要對注意力稀缺保持警惕,又要對注意力飽和作出選擇,還要對注意力轉移進行回應。
第一,對注意力稀缺保持警惕。注意力稀缺即為資源稀缺,意味著政府應該對社會資源最大程度地發揮效用。面對有限而非完全的理性決策瓶頸,政府既無法掌握完備信息,又無法具備“一統”能力,還面臨著資源稀缺,所以就要對注意力稀缺這個現實保持警覺。這是理解議程設置作為政策變遷常規變量的前提。
第二,對注意力飽和作出選擇。政府核心決策者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有很多,注意力分配決定著決策者為何選擇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那個問題。面對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問題,為什么有些決策者會這樣做,而其他人卻不這樣做,這就意味著注意力會時刻面臨飽和的情形。在注意力飽和之下,決策者獲取的信息以及選擇處理信息的方式,是議程設置作為政策變遷常規變量的核心。
第三,對注意力轉移進行回應。常規流程是議程設置的基礎,由新信息而產生注意力轉移卻是議程設置的魅力。與常規流程不同,新信息機制是議程設置的另一重要因素。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8—2009年的經濟和財政危機,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最初不愿意采取大規模的經濟干預措施,因為為銀行紓困顯然不屬于任何政黨的政治綱領,但最終整個西方國家都采取了此辦法,這就證明不斷變化著的信息流對政策變遷具有重要價值。
議程設置作為一種注意力分配過程,其稀缺、飽和以及轉移三者之間存在強相關,注意力稀缺或飽和均會產生轉移。注意力稀缺不代表沒有注意力,只是需要在合適的時間制造注意力,決策的注意力從能源轉向醫療保健、移民、經濟再到戰爭、氣候變化或人權,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外部環境和國際局勢的影響。當注意力稀缺或飽和時,就要極力避免問題的嚴重程度和解決方案的效率要求同時出現,因為政策方案不能同時關注速度和質量。注意力轉移很多時候由問題的性質決定,而問題則來自于媒體報道、公眾不滿和現實世界的變化(比如失業率或通貨膨脹率)等,政府官員對這些問題始終處于監控狀態,常常以指標、焦點事件、危機和符號以及社會反饋來判斷。在這些因素所顯示的問題嚴重性面前,注意力即使再飽和也會發生轉移,而在其他時候,例如沒有嚴重的經濟衰退,議程設置對注意力的稀缺或飽和則具有更大的容納空間。所以,不同情形下三者的關聯度解釋是不一樣的。
在注意力稀缺、飽和以及轉移三種情形之下,議程設置的關鍵還在于問題進入政府議程的渠道,亦即如何“讓問題成為問題”。政策過程的每個階段都具有形成注意力的規則,而在議程設置階段則要更強一些。“讓問題成為問題”與注意力飽和緊密相關,一個負責任的、透明的和有所作為的政府須時刻保持對注意力稀缺的警覺,處于飽和反而是常態。在問題出現擁擠和摩擦的時候,政府注意力如何從飽和中解脫出來并轉移到必須解決的重大議題上,就需要根據公共事項的優先順序來決定。優先事項的排序方式有兩種,也就是科布和埃爾德所指稱的系統(公眾關切)議程和政府(正式機構)議程。一個社會問題只有在擴散到更廣泛的公眾那里的時候才可能成為系統議程,這被看作是“外部創生模式”或“外部嵌入法”;而由有規律和規則的議會政治演化而來,或由政府公共預算常規操作流程構成并被優先考慮的社會問題,則屬于“內部創生模式”或“先期排序法”。“內部創生的反面是純動員模式,外部創生的反面則是聯合模式,二者若有交叉,則是多源流模式”(28)Peter.J.May.Reconsidering Policy Design: Policy and Public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1991,11(2),p.187-206.。這些議程設置模式最終都指向政策議程建立,因為這些不同模式都必須遵循政策議程的演進邏輯,即一般社會問題成為重大公共問題再到成為政策問題。傳媒議程、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三種模式在議程設置中本是一種順向遞進關系,但是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新興社交媒體及網絡平臺廣泛出現,議題變得更加具有流動性,議程設置模式也逐漸演變為并列平行關系,從而動搖了政策議程建立的傳統根基。但是動搖絕非撼動,政策議程在問題進入政府議程渠道上長期占據主導地位這一點并沒有改變,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習慣于使用政策議程設置或建立,而將傳媒和公眾兩種議程看作演進的過程或者催化工具(29)楊志軍、支廣東:《完全還是有限:政策議程建立的型構條件與耦合機理——基于“關鍵個人”變量的新多源流模型解釋》,《中國行政管理》2020年第12期。。
在更強調制度和法律作用的政治體系中,議程設置的主體經常是政府議程,只是出現政府議程的渠道不同。在美國,總統演講、法案介紹和國會聽證會往往會讓某些社會問題出現在政府議程上,而在許多議會制民主國家,行政演講和議會質詢才會發揮這樣的作用。比起政府議程的法律和預算形式(后期階段),行政演講、政策辯論、公民論壇(早期階段)等往往可以讓公共優先事項產生變化(30)Jones,B.D.,Baumgartner,F.R.,Breunig,C.,Wlezien,C.,Soroka,S.,Foucault,M.,A.Fran?ois,C.Green-Pedersen,P.John,C.Koski,P.B.Mortensen,F.Varone,and Walgrave,S.A general Empirical Law for Public Budge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53),pp.855-873.,議程設置雖然經常以政府議程形式出現,但是系統議程在很多時候也很管用,因為要響應不斷變化的信息輸入,政府議程表現出更大的“粘性”和對變化的抵抗力(31)Jones,B.D.,and Baumgartner,F.R.The Politics of Attention: How Government Prioritizes Problem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議程設置指向問題產生的不確定性。垃圾桶模型最早意識到并試圖破解“決策活動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但就像打靶原理所揭示的道理那樣,用移動的托手去射擊移動的靶子很難成功,因為至少要保證托手的穩固。經過改進后的多源流模型,不僅將四源流調整為問題、政策和政治三個源流,而且用“政策之窗”替代決策的機會,成為決策活動是否成功的關鍵。但看似精密的機器實則并不精細,面臨著“源流的獨立性問題、動態變化的結構性框架孱弱”兩大病癥。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以預知將要發生的事情,就像他們無法精確界定政策問題產生的范圍和精準制定解決方案一樣。當議程容納和設置空間不足時,首要問題便是“我的優先事項是什么”。在特定的政治結構下,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議程設置特點及其規律,兩黨或多黨競爭選舉的國家在收集信息方面有著優勢,因為這些國家有更活躍的社會組織網絡,包括由政務官組成的政黨(這些官員急于了解選民所想)。而在一些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政策議程則具有強烈的國家自主性,在強體制的推動下形成決策“內輸入”。因此,系統議程和政府議程并不是單一地發揮作用,政策議程的建立邏輯也不是單線條的,而是相互融合、多元互動的結果,具有相當程度的可觀察性,而這也增加了比較公共政策議程研究的多樣性。
五、偏好是政策變遷的核心穩定機制
西方學者開展比較公共政策議程分析時發現,政策偏好具有一致性(32)Frank R.Baumgartner,Bryan D.Jones.John Wilkerson,Comparative Studies of Policy Dynam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1,44(8),p.963.。政策主題(公共優先事項)排序的差異深層次地反映出政策偏好的穩定性。比較公共政策研究將偏好、制度和信息作為政策變遷的三大變量,而偏好和制度比信息的作用更受關注。選舉會導致決策偏好發生變化,當選舉結果決定執政聯盟的命運時,一系列新的政策偏好就會產生,從而將政策偏好轉化為決策能動性。制度既是穩定的,又是變化的,穩定的制度會被修正推翻,也會被固化定型。在選舉替代和否決權使用的西方政治體系中,制度反而容易被型構,新信息也經常會促使政府采取冒險行動,唯有政策偏好是內生且穩固的,這與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由差異邁向統一以及二者并存原理相類似。因此可以說,任何政治行動者都會有政策偏好,并且隨時準備將這種偏好最大化,構成政策變遷的核心穩定機制。
首先,偏好來自于理性。政策偏好是一種試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理性假設的產物,政策制定者會選擇最符合自己偏好的方案,而不是改變自身的偏好。赫伯特·西蒙指出,不同的學者對理性假設會有不同的理解,但對其實現政治目標最大化的作用則普遍認同。在強理性選擇形式下,擁有完備信息的理性行為者具有無限的認知能力;在弱理性選擇形式中,信息是不完整的,行為人只是“盡力而為”地利用現有信息作出最恰當的決定。如果偏好驅動行為是以一種最完備信息來達成交互的,那么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這些信息從何而來,那些不能接收所有信息輸入以及不能投入所有時間的政治行為人又是如何會對新信息產生敏感的,以及他們是否能改變競爭對手對這種信息機制問題的解釋等問題(33)Simon,Herbert A.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47.。這意味著行為者對信息進行處理和回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策變遷最終是在特定制度環境下進行集體決策的產物。組織處理信息不僅受個體行為人認知能力和溝通方式的影響,還受到法律、規則、程序等正式硬制度的制約,以及習俗、觀念、道德等非正式軟制度的影響,這種影響是觀點如何聚合以產生集體決策的原因(34)Jones,B.D.Politic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Choi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沒有人否認政治領袖對其周圍世界變化所作出的反應,但是有關偏好的知識論和制度設計論最能夠解釋政策變遷。傳統上將并非由選舉引起的偏好改變因素歸納為“外來沖擊”,這種外來沖擊對傳入信息的響應是不平穩的,規模是不成比例的或難以預測的。
其次,偏好不可測量。在倡議聯盟框架解釋范疇中,偏好類似于政策體系和不同聯盟所擁有的深層核心信仰,不可動搖也不可更改。這一點又可與彼得·霍爾提出的政策范式變遷三層次論相結合,即第一層次的政策變遷是指政策工具的水平或參數調整變化,第二層次的政策變遷強調在總體政策目標不變的情況下政策工具發生改變,第三層次的政策變遷是指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標均發生了改變(35)Peter Hall.Policy Paradigms.Social Learning,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s Policy-Making in Britain.Comparative Politics,1993,25(3).。而只有第三層次的政策變遷才是根本性變遷,被稱為政策范式轉移。政策范式的變遷往往意味著政策發生巨大的變革,而要出現這種變革非常之難。意外事件對政策決策的影響要比現有規定對政策決策的影響更加突出,成功的政府部門會根據不斷變化的信息模式(包括反對派和公眾如何應對這些變化)調整公共事項的優先次序,畢竟解決問題才是決策的必要條件,而解決問題的方案又是在等待問題的過程中準備完成的。最初研究政策動力的方法是將長時段的注意力集中在各種政策問題上,然后審查注意力的模式,最近的政策動力機制則包含了比較政治研究中通常缺少的一些東西:不斷變化的政策注意力主題。例如,有人試圖通過從一個時期到下一個時期的法律的數量來解釋立法效率,從而揭示出偏好是政府行動最穩固的基因,也是政府信仰中最為核心的因素,但是卻很難去測量(36)Lapinski,J.S.Policy Substance and Performance in American lawmaking,1877-1994.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52),pp.235-251.。當偏好作為一種深層核心信仰成為政策變遷的核心穩定機制時,其不可測量性要求時刻關注政策議程設置的常規性注意力變化,從中發掘出偏好的形成規律。
最后,制度有助于解釋偏好既定情況下跨國間的政策產出。政策偏好一旦形成極易制度化,政策動力途徑假設制度變量有助于解釋特定政策領域內的產出差異(不同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產生不同的政策變遷模式),還強調制度與那些賦予否決權的規則一起構成決策阻力的來源。決策阻力還可能源于議題競爭,因為議題相互競爭體現的是政策偏好之間的競爭。政策動力途徑認為偏好或制度所造成的阻力是相對而非絕對的,粘滑動力學(stick-slip dynamics)將制度摩擦分為兩個部分:粘性(stickiness)和滑移(slippage)。如果摩擦從來沒有被克服過,那就是堵塞,而不是摩擦;摩擦可以通過更強的力量來克服,當它被克服時,滑移就會產生。就像我們描述政策變遷一樣,不論是研究者還是普通公眾往往對諸如創新這樣的劇烈政策變遷有濃厚興趣,并且最好是劇烈政策變遷在沒有任何大的前兆和變化預期下發生(類似于“一鳴驚人”)。再者,僵持和堵塞與摩擦不一樣,摩擦是一個更完整的想法,因為它兼顧了變革的阻力以及克服變革障礙時的突然變化。從間斷—均衡理論的觀點來看,政策變遷的間斷和均衡是同一過程的兩個并行部分,摩擦、粘性等概念是政策變遷和制度設計的自變量而不是條件變量。
上述情形意味著僅僅假設由政策主題的注意力變化產生政策變遷是不夠的,政策變遷在維持偏好穩定的情形下,取決于政治制度中的摩擦或阻力水平。由這些制度摩擦所產生的政策間斷強弱及其影響又有不同,相對于制度摩擦水平較低的國家,制度摩擦較高的國家發生政策變遷的幾率較大,但政策間斷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頻繁,因為制度摩擦通常會延遲政策調整的效果。政府永遠關注一個政策主題是不現實的,議題本身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尤其是在網絡社會,公民可以期望也可以討論需要政府解決哪些重要社會問題。選舉機制使得人們認為政府在獲得政黨任命權后只是簡單地執行其意識形態及政策,政府始終面臨著許多缺乏明確解決方案的困境,但也必須開展治理行動。
因此,選舉機制不能解決選舉時期內出現的問題,因為問題往往會被提前設置,選舉中的問題只能納入下個議事日程。對一個問題的回應可能會與其他問題的解決存在相互矛盾的關系,例如美國槍支問題得不到解決的根本原因在于控槍與公民防衛權和自由權相抵觸。隨著反對派將注意力集中在擬解決方案的缺陷上或那些不是執政政府優先考慮的問題上,這些缺陷或問題就會成為在野派攻擊執政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的理由,再加上權力制衡因素,很多時候這些攻擊會使得政治格局發生變化(如彈劾總統生效)(37)Frank R.Baumgartner and Bryan D.Jones.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Problem Definition and the Course of Public Policy in Americ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如果說政策變遷動力機制涉及“何以產生”的解釋,那么政策變遷的形式則是對其樣態進行描繪。單線條地解釋每種形式產生的動力是可行的,但更有意義的是在原因和形式基礎上對產生政策變遷的動力機制作維度探索。基于此,本文對公共政策學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啟示:
第一,選舉作為傳統變量需要重新審視。正如土地之于農業、市場之于工業的重要性一樣,皇權之于專制統治、政黨之于民主治理同樣重要。在倡導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坐標系和方向標上,西方政黨競爭的選舉體系和機制缺陷明顯卻依然高歌猛進,不得不讓我們思考選舉的驅動力、影響力問題。選舉作為驅動政策變遷的傳統力量,很多時候跟不上新信息的出現或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卻是產生和推動政策變遷的重要因素。
第二,信息機制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信息機制在注意力運動中呈現,也在議程設置中發揮作用,信息的入口是問題的出現、界定和篩選,出口則是建立政策議程。這在橫向的跨國性比較議程研究中已經得到證實,不同點在于信息機制會有優勢和劣勢之分。多元主義政治體系在議程設置上具備信息獲取優勢,但并不具有信息處理的優勢。所以,信息機制不在于政治體系的制衡和治理體系的多元化,而在于重視新信息并及時給予回應和解決。
第三,大多數政策過程都是間斷的平衡。政治決策者一般都會設置危機閾值,如重大突發事件或其他公共安全的死亡人數等。在面對重大公共危機的時候,不是決策的過程而是決策的速度決定政策質量。面對危機的公共決策以及由此產生的政策變遷相較于常規化政策變遷,肯定是一種間斷,但卻不是間斷與均衡,而是均衡中的間斷以及間斷之后的均衡。雖然不同治理結構下的治理能力有差異,但并沒有改變治理連續性本質,這種能力差異來源于不同治理結構的注意力轉移速度。
第四,政策變遷研究的學科融合大于分野。比較政治學和比較公共政策學對政策變遷的貢獻,主要來自于以政治學者身份從事比較公共政策研究的學者。在政策過程理論學派(38)Weible C M,Sabatier P A.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Fourth Edition).New York: Westview Press,2017.中,多源流、倡議聯盟、間斷平衡、制度分析與發展、政策網絡、政策反饋以及政策創新與擴散,屬于實證性政策科學范式,而政策敘事、話語分析等則屬于后實證政策科學。不同方法和面向依然能夠匯聚為政策過程理論,相互融合、取長補短,足以證明學科融合既是進步之源,又是未來之勢。
拉斯韋爾在《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中提出的“5W2H分析法”,對政策變遷研究啟發頗大。一種基于條件和類型分析之后的動力探尋,給本文定下了主基調。“政策動力學”不僅有利于我們理解政策過程理論的國際化和實證性,而且對探尋當今世界大國治理所應該具備的“理性預期”具有相當意義。目前在政策變遷研究中,除了政策過程理論的解釋、應用、比較、修正和創新之外,還有一項是針對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信息處理上的機制與過程研究(39)Samuel G.Workman,Bryan D.Jones,Ashley E.Jochim.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olicy Dynamics.Policy Studies Journal,2009,37(1),pp.75-92.,未來的熱點和創見也可能來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