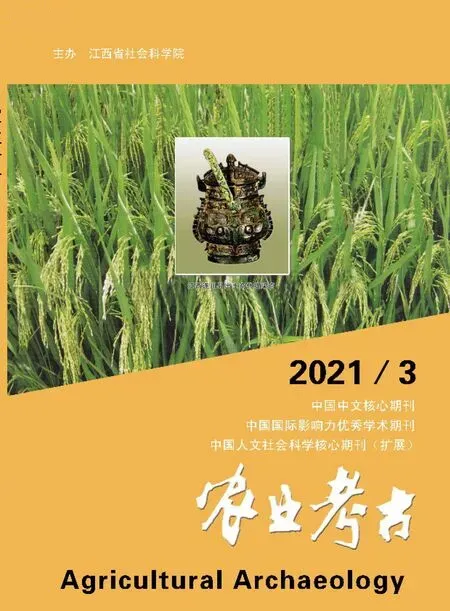興屯實邊:清末川邊農業墾殖研究(1903-1911)*
王海兵
光緒二十四年(1898),寇松接替埃爾金就任印度總督后,極力在亞洲實行反俄政策。為了將西藏納入英國勢力范圍,成為英印屏障,排除俄國對西藏的影響,寇松打算在中印之間建立緩沖地帶。光緒二十九年(1903),寇松提出宗主權(Suzerainty)問題,將中國稱為西藏的“中介”“宗主國”等[1]。寇松的對藏政策導致后來英印政府對西藏的軍事行動。同年(1903)五月,乘日俄戰爭之機,榮赫鵬率遠征軍入侵西藏,并于光緒三十年(1904)六月二十二日進抵拉薩,七月二十八日以武力逼迫西藏噶丹赤巴簽訂《拉薩條約》。為了挽救西南邊疆危局,清廷分別在川邊與西藏實行新政,其中農業墾殖是川邊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學界對清末川邊屯墾引發的生態環境、墾牧爭地以及屯墾的實施過程等問題已有不同側面的探討,而在川邊屯墾的整體性、制約因素等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本文主要利用清末川邊檔案資料,并參證其他相關史料,擬對川邊農業墾殖問題做進一步梳理、論述。
一、清末川邊墾務的初創(1903-1905)
光緒二十九年(1903)七月十五日上諭:“有人奏,川、藏危急,請簡員督辦川邊,因墾為屯,因商開礦等語,著錫良查看情形,妥籌具奏。”四川總督錫良遵旨查議川邊屯墾等事宜后認為,“大抵藏之急務,固非屯墾、商礦所能解其危迫”[2](P365)。但迫于清廷壓力,錫良決定先在巴塘試辦墾務。“查巴塘氣候比爐邊、里塘一帶為溫和,地勢亦較平衍,似宜于巴塘一處先將墾事籌維舉辦,商礦各務兼可次第講究。查土司地面,歸化已久,平日原極輸誠,惟其生性終屬愚頑,一旦開墾其地,必非所愿,規畫自屬不易”[3](P1-2)。同年十二月,四川礦務局派員會同巴塘糧務委員吳錫珍及巴塘都司吳以忠試辦墾務[3](P2)。據吳錫珍等人查勘,巴塘可開墾水旱地共計50600余畝[4]。吳錫珍認為:“開墾之政有二:就可墾之地,官自募民耕之,酌收獲之豐歉,定租賦之多寡,數歲之后,著為定額,是曰官墾;募民之稍有資力者,或一、二人自認一段,或數十人分認一段,墾成許其永為己業,三年之后,按地肥瘠升科納糧,是曰民墾。巴塘僻在荒徼,與內地不同,民墾尚難猝辦,自宜先就官墾入手,俟著有成效,民之趨利者,自望而爭赴,則由官墾而民墾,無難愈推愈廣矣。”[5](P9)
光緒三十年(1904),據吳錫珍、吳以忠稱,開辦巴塘墾務,“正土司羅進寶、副土司郭宗札保暨丁林寺堪布傲拉扎巴等投具切結前來。該正、副土司樂從其事,均無異言。惟丁林寺堪布等結稱所管地方,除牧放牛馬草場以外,并無可墾之荒山荒地,因恃其俗僧之眾,顯系狡展。查巴塘地面,俗稱三曲宗。正土司為第一曲宗,副土司為第二曲宗,丁林喇嘛寺為第三曲宗。該三曲宗正、副土司既遵開辦,有其二不患無其一,盡可次第辦理”[5](P12)。為此,吳錫珍等人擬定了開辦巴塘墾務辦法,主要內容有:1.根據巴塘“節候冷暖、地勢高下”不同,擬“在巴塘迤西二十里茶樹山一帶先行開辦,墾畢一處,推廣別處”。2.“巴塘漢夷雜處,土著系屬蠻民,漢民則多半客籍,且習于經商,未必皆諳農務。所有招雇農夫一節,必須求諸異地”[5](P12)。3.所招墾夫每名每月給工食銀3兩,墾夫每10人配伙夫1名,伙夫每人月給工資銀2兩7錢,專管背水、采薪、煮飯等事[5](P12)。4.每10名墾夫選1人為墾長,“如軍營什長之類,仍責其隨同眾人一律操作”,墾長從開工之日起,每名月給工食銀3兩8錢。5.在當時83名巴塘防兵中酌撥二三十名從事開墾,每名每月酌給津貼銀1兩5錢[5](P13)。所墾土地由士兵經營,“將來墾成之后,兵餉即由此出,是亦古屯田之遺意也”[6]。6.擬在茶樹山“先行擇地蓋造房屋兩三區,將來聚人既多,占地必廣,即為漸成村落地步。所有木匠、泥匠,即在巴塘雇募,工食按時價照給”[5](P13)。
《拉薩條約》簽訂后,為了“挽利權而資抵御”,清廷于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任命鳳全為駐藏幫辦大臣,委“所有西藏各邊,東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帶,著鳳全認真經理”[7](P117)。又因“章谷實為霍爾適中要隘,上至德格,下至革什撤,為進藏北路。其全境近接三瞻所屬仁達地方,距道塢不遠,尤川、藏出入之要津”[2](P425),于是錫良奏請將章谷土司之地按照懋功五屯成案,特設屯員,改為爐霍屯,兼管朱窩、麻書、孔撒、白利及東谷諸土司[2](P425-426)。鳳全將屯墾、練兵視為經營川邊藏區的首要措施。光緒三十年,赴藏途中的鳳全對打箭爐至巴塘沿線的墾務情況做了調查。據鳳全稱,“隨處查勘,冰霜荊棘,滿目荒寒。惟爐屬之阿梁壩、東俄洛等處天氣稍和,地勢平坦,番民墾成熟田不少。里塘一帶,磽確尤甚,殊少可耕之地。巴塘氣候稍為和煦,近臺數十里,土尚膏腴,前經督臣錫良飭派該臺糧員試用知縣吳錫珍、駐防都司漳臘營參將吳以忠試辦開墾,一年以來,計開成熟地三百余畝。原稟查勘可開荒地甚多,奴才連日逐處履勘,沙石參半,其實可耕而易成者,不過五六千畝”[5](P38)。鳳全認為,巴塘墾務開辦,“一年間,約可成田一千余畝,逐年擴充,成效當不只此數。將來以歲入之租,養防邊之勇,一勞永逸,計孰便于此者”[5](P38)。就在鳳全計劃擴大墾務之際,卻遭到了當地政教系統的抗阻。鳳全“派勇彈壓,經過丁零寺門外,喇嘛即放槍傷勇,此二月二十一日事也。厥后焚燒墾場,糾結日眾”[2](P477)。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鳳全被殺,墾夫或死或逃,開辦一年多時間且已粗具規模的巴塘墾務遭到重創。
二、改土歸流時期川邊墾殖的拓展(1906-1911)
“巴塘事變”發生后,四川總督錫良、成都將軍綽哈布派四川提督馬維騏、建昌道員趙爾豐會同辦理墾務。光緒三十一年六月,趙爾豐被任命為爐邊善后督辦。光緒三十二年,錫良派趙淵赴巴塘辦理善后,與趙爾豐籌商,“整理屯務,鞏固邊庭”[2](P593)。攻克桑披寺后,清廷于光緒三十二年任命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首先在康南地區進行改土歸流,廢除土司及其統治系統,改設漢官,管理地方百姓及錢糧訴訟等事宜。巴塘全境“凡種地者,無論漢、蠻、僧、俗皆應納正糧。何謂之糧?民收為租,官收為糧也”[5](P96)。改土歸流后,“凡在巴塘全境喇嘛寺院,皆屬大皇上地土。凡喇嘛無論自種、佃種之地,皆應與百姓一律按等完糧,不得以廟地稍有歧異”,“查抄丁林寺、正副土司及各匪首逆產,由官招人佃種。其糧皆五成上納,不在三等之例”[5](P97)。同時,“巴塘及鄉間荒地甚多,自三十二年起,皆歸官招墾,無論漢、蠻、僧、俗皆準到官府承領執照,方準耕種。如由官日給工食者,其地墾熟,并所出稞麥一概歸官;第二年若能自備口食,官只借給籽種,照準五成納糧外,再將籽種還官,平出平入,不取利息,第三年后即照章按等完糧。其自備口食開墾者,第一年免其納糧,第二年后,即照章按等完糧。惟此項墾田,作為官佃,準其世世耕種”[5](P97-98)。
改土歸流為川邊農業墾殖的拓展奠定了基礎。中國歷代王朝經略邊疆,大多主張以民實邊、移民屯墾。“竊維體國經野,為致治之良圖;興屯實邊,實保疆之至計”[5](P921),而且“墾草創邑,辟地植谷,為富民之本計”,“總之,守邊之本,足兵足食;諸侯之寶,土地民人。墾務不舉,則無食無人,而兵亦無由練”[5](P924)。由此可見,屯墾關系到駐軍糧食保障和邊防之穩定。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趙爾豐向清廷奏陳邊務應辦事宜,陳述了興學、通商、開礦、屯墾、練兵、設官六事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認為必須同時并舉。趙爾豐的經邊計劃得到清廷的批準,并在財政極其緊張的情況下,撥給專款支持川邊屯墾[5](P118-125)。
為吸引民眾赴川邊開墾,趙爾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墊給墾民路費、口糧。清廷“于打箭爐設立招待所,于各處開墾地面設監墾所,凡內地民人前往邊地認墾,由原籍地方官取具妥保,按日墊給口糧”[5](P122)。墾民到打箭爐后,“酌定撥往何處開墾,按照所至之地,計日發給口糧。邊地寒冷,并給氈衣褲一套。到屯之后,由監墾所給與構造廬舍之資及農具、籽種、耕牛,并仍按旬發給口糧,以收獲新糧之日為度”[5](P123),“出關口糧川資,每名每日省九七平銀一錢,十五歲至六歲減半,再小者不給,并給予路票”[3](P12),“綜計由原籍及招待所、監墾所前后墊口糧、什物共銀若干,令其于正糧之外,分年帶繳,繳清之日即發給印照,作為該墾戶業產”[5](P123)。2.修建墾房。川省農民“肯于應招赴邊者,大都貧苦佃戶,自無寸土之人,農具、廬舍令其自備,斷難集事”,“若再不為籌備耕具居處,勢必觀望裹足,則墾務萬無能興之日”[5](P120)。“查邊地一望荒涼,往往數十百里不見煙戶,墾夫無處棲止,若概令自構廬舍,實屬力有不逮。現擬變通辦法,準由各處委員借領公款,代造蠻式墾房,撥給墾夫居住”[5](P467)。若“有平坦寬廣之地可墾數百畝,則于適中之處修造廬舍。仿照內地街市建法,起初時,接連建屋十余間,俾佃戶毗連而居,各耕地畝,可以守望相助。以后漸次推廣,作為場市。如只可墾地二三十畝之處,一二佃戶即可耕種;其建房,但求避水患可也”[5](P180-181)。墾房應照“蠻房”式樣建造,由墾夫分年繳還造房官價[5](P468)。
在屯墾政策的引導下,墾民的招募取得一定成效。蓬州知州戴賡唐的招墾“辦法甚善,所招之人,視別邑為多”,共招募了97名墾丁,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蓬州起程,赴川邊開墾[3](P15-16)。據打箭爐廳統計,光緒三十一年三月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四川各縣墾夫出關人數為119丁、48口,共計167人,主要赴巴塘、鄉城等地屯墾[8](P27-28)。光緒三十四年(1908),據趙爾豐云,“照得關外改土歸流,開辦之初,以墾荒為急務。自光緒三十二年招墾以來,出關墾夫已過數百名”[3](P22)。同年(1908),趙爾豐致電武文源稱,在各縣招募的800名墾夫內,有眷屬者370余人,皆由各縣領單陸續發往墾區。“先至者分發:定鄉二百名,稻城二百名,巴安二百名,河口二百名,留二百名開墾東俄洛。宜札飭明正土司遵辦照料”,“分發各縣之墾夫,仰該丞派妥員分批送至河口,由河口送至理化,再由理化委員分送至各處,沿途不準騷擾”[5](P278)。宣統二年(1910),趙爾豐在示諭內地農民到察隅開墾時云,“照得關外巴塘、里塘上年改土歸流,因見其土地肥美,無人耕種,本大臣就地出示招人開墾,今已三年。各處招徠之人,已有一千多名了”[5](P666)。光緒三十四年,趙爾豐招墾夫200名,于爐霍縣仁達溝及沿河兩岸擇地開墾[9](P97)。在甘孜縣設治之初,趙爾豐“擬招夫千人于此開墾,分置玉隆縣”,當時甘孜縣墾夫已至百人[9](P145)。至于川邊各縣墾民的具體數字,由于資料缺乏,已難以精確統計。據劉贊廷估計,改土歸流時期,出關之墾夫共1723名,有眷屬者600余人,分發康定、雅江、稻城、定鄉、巴安、鹽井、道孚、爐霍、甘孜等縣開墾。至宣統三年擬續招墾夫2000名,開辟金沙江以西各縣[10](P91)。
兵屯亦是川邊屯墾的重要組成部分。趙爾豐認為,“安巴、安藏,不外移民政策,然絕不可遽言遷民”[5](P187),“惟藏地奧阻,無論藏民不能容納,即川民亦不肯遷移,斷難操之過急。惟有寓遷民于兵”[10](P157)。為達到兵民合一之目的,趙爾豐“招募三營,皆有家室,略加訓練,率帶出關。到彼即預行屯田、畜牧、開礦諸法,使見有利可圖,然后招其眷屬續往,化出關之兵為民,復招關內之民為兵,循環漸漬,不但兵無戍邊之苦,而風聲所樹,乃可徐施移民之策”[5](P187-188)。為了讓駐康士兵安心屯戍,趙爾豐鼓勵家無妻室的士兵與藏族婦女通婚。光緒三十三年,趙爾豐詢問代統領吳俁,“我兵仍思歸否?娶婦之風如何?凡娶婦者,必撥地與種,俾有以養,如何能為持久之計?籌復”[5](P110)。據劉贊廷稱,川邊士兵中“配有夷女為妻者,由公家每月發給青稞一斗,生有二女者,一人一斗為津貼。有愿隨營開墾者,所得之地,系為己有。三年后,除納官糧之外,免去一切雜差”[10](P145)。
趙爾豐還鼓勵藏民就地墾荒。改土歸流前,川邊藏民“向不準私自開墾,須向土司領地,準給者方能耕種,名為官地。不準私相買賣,并可隨意奪回。凡種一地,納糧之外,支差幾至百倍,不勝其煩。是以荒地雖多,百姓皆不愿領種”。改土歸流后,清廷宣布“免去各項差徭,從前已開之地,準其永遠管業;其未開之地,任人開墾,三年始報升科,亦準永遠承種,發給地照為憑”[5](P458)。宣統二年,據稻城委員冷家驥稟告,稻城東路、北路以及松堆村等地15村215戶藏民,共墾荒地252畝。稻城藏族墾民由墾地所在各村村長管理,“不得另舉墾首、墾目”,“各村荒地,即由各村招貧民開墾……每月每人須墾一畝,少亦必及半畝,乃能準借口糧”,“俟墾地出產,由村長向墾夫收回,交還官倉”。“所墾之地,耕種三年,不納官糧。自第四年起,下種一斗者,納官糧一斗,或一斗二升”[5](P797-798)。
清末川邊墾務較有成效的是鄉城、巴塘、河口(雅江)、爐霍等縣。鄉城“所屬以二郎河為產糧之區,沿河兩岸南北二百余里悉為田,土質肥饒,氣候溫和,每年兩季”[9](P749)。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鄉城墾田已至2000余畝,主要集中在上鄉城之元根、正斗、火竹鄉,中鄉城之宜士、頂中巴,下鄉城之巴坡及上中下三蕊窩等地[9](P750)。光緒三十二年(1906)二月至光緒三十三年四月這段時間內,巴塘地區新到墾夫200余名,共開地391畝2分[5](P405)。至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九 月 ,巴 塘 “ 茶 樹山、底塘宮、載石垌,蠻房三所,現已一律告竣,所需鍋灶器具,陸續置用。該茨荔隴已開一百八十余畝,底塘宮已開三十余畝,載石垌已開八十余畝,共計墾成熟地三百畝之譜。又載石垌水槽,計已開成五十余畝”[8](P25)。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至宣統元年(1909)五月底,巴塘地區共開墾熟地600畝[5](P405)。宣統二年(1910),據巴塘糧員稱,“附臺一帶地方,氣候溫和,居民稠密,凡可耕之處,早經開辟”[5](P742)。宣統二年,據河口委員喬聯沅匯報,河口28村尚有可墾之地一千五六百畝,其中鐘中堂村多系漢人,“歷年開墾殆遍,荒地亦屬無多”,噶拉村附近可墾荒地“近年已陸續為漢民指墾 ”[5](P722)。爐 霍 屯 于 光 緒 三 十 年(1904) 改 土 歸流,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元年春,爐霍屯陸續認墾者36戶,共認墾地644畝,至宣統元年四月已墾成熟地304畝[5](P345)。
隨著土地的開墾,地權問題隨之出現。清末川邊墾地大致分為官地和民地。光緒三十四年,趙爾豐下令“將一切新墾之地,不分漢蠻,招佃耕種”[5](P179)。還清墾費是墾民承耕官地的前提,“官墾之地,以資遣農夫出關,合計墾費每畝約銀十五兩。如佃戶力能繳還官費,由地方官稟明,給予執照,作為民業”[5](P181)。同時,墾民“仍按年按照征糧章程納糧。其地仍為官地,不準私自買賣,以杜弊端”[5](P468)。若墾夫“力不能承耕者,令其專墾荒地”,由地方官按月發給口糧[10](P92)。除來自內地的墾民外,“如防營兵勇娶有家室者,蠻民有家室而無恒產者,果其勤而耐勞,均準承佃官地,耕種納糧”[5](P180)。民地系由佃戶自費開墾之地,“官墾時,擇上地而墾之。旁有余地,即令佃戶于農隙之時,就近自行開墾”,所墾之地“準作為民業,三年之后,由官勘丈,發給地契,按畝計科,每畝年納糧一克”[5](P181)。
三、農作物和農業技術在川邊的推廣
改土歸流前,“康人所種之谷不及十類,以青稞為大宗,各處均種,其余有不種之處,然谷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康人不食菜,故不學為圃,雖河口、道塢、甘孜、巴塘、乍丫有種菜者,皆駐臺漢塘兵所為,無塘兵之處仍無菜”[11](P114)。川邊改流后,趙爾豐認為“關外蠻民多種稞麥,內地之人漸次出關,宜兼種包谷、黃豆、高粱、小米各項為漢人習慣之食,免再由關內運米,致耗庫款”[5](P181)。此外,趙爾豐還派人“由川購菜種分發各屬,令其試種,并通令各屬勸民種黃豆以作菜焉”[11](P114-115)。隨著墾殖的推進,川邊各縣陸續設立農事試驗場等農業改良機構,雜糧、蔬菜、瓜果等新型農作物在川邊得到推廣種植。
宣統元年(1909),登科委員喇世俊稱,“登科蠻民尚知力田。惟囿于方域,青稞、豆、麥而外,更無所出。且耕作多未得法,非有以提倡之,農務難望起色”。為此,喇世俊“擬就舊有菜園量為擴充,周圍環以墻垣,內修土房三間,以為場丁了望棲止之所。并置糞坑,置備農器,外建大門一座,榜曰‘登科農事試驗場’”,又“托人在甘孜、章谷、道塢、爐城一帶,采買各樣雜糧、菜蔬、果木等種,一俟明年春暖,及時播種,令五路農民來場參觀研究種植之法”[5](P496)。登科農事試驗場設立后,喇世俊“于樹藝培植之法,反復開導,其間稍有知識者漸悟夙昔耕種之未善。昨集各路紳民,陳列試驗場所產雜糧,人人為之色喜”[5](P818)。為了進一步改良種法,喇世俊于宣統二年十月稟請趙爾豐在登科設立農事改良所。農事改良所的主要職能包括“講求樹藝培植之法”選擇良種、改良農器等[5](P819)。
同普農業試驗場于宣統三年(1911)成立。同普委員張以誠稱,同普“夷民尚知力田,惟稞麥、豌豆數種而已。且種植向未得法,除一犁之外,別無農具,禾同草生,成為壅田,無人提倡農務,難望起色”,遂建農業試驗場一處,并“托人在雅安、滎經采購各種雜糧、菜蔬、花草,俟待回時,教民播種”[5](P888)。德格自改流 設治 后 成 立農業 試驗場,“于更慶村腳小河邊,開墾試驗場地塊,將發到各色種子,如法播種。并買添胡豆、黃豆、豌豆、高粱、小麥、洋芋及各種瓜菜等種,如法試種,加用肥料,引水灌溉”[8](P20)。此外,康北的爐霍、瞻化等縣亦設有農業試驗場,種植南瓜、茄子、白菜等蔬菜和一些豆類作物。
在康南地區,巴塘“近時所種之菜蔌,緣經憲臺調集內地墾夫,以內地藝蔬之法,行于遐陬,而官商軍民人等,始有菜可購,而佐盤飧”。當時巴塘所種之內地蔬菜有白菜、蔥苗、四季豆、蕓香菜、辣子等[8](P20)。巴塘在清末設立農事試驗場后,“凡內地花果于此教種,應有盡有”[9](P873)。宣統元年(1909),理化廳同知李克謙稱,“去歲通判到臺接管時,見此地雖寒,可種菜蔬。由省中寄購籽種各色,飭署內跟役并分給民兵試種,蓬勃秀榮無異內地所產。嗣經再三研究,則因霜雪不時,于種糧不甚相宜,除菜蔬外,最便于種桑……擬就營官壩辟一農業試驗場,由關內購運桑秧兩萬株,于開春雨水節前如法栽植,桑之下仍種菜蔬及洋芋等類,以開風氣而辟利源”[5](P390)。宣統二年,冷家驥稟請設立定鄉農牧研究會[5](P727)。雅江“自設治以后,漢人來此居住,皆由內地自帶菜蔬花仔圃種家養”[9](P544)。
內地農具亦不斷輸送到川邊。據傅嵩炑言,“康人不效法耕稼之事,榛狉自封,只知畜牧!迄今牧者多,耕者少,而所種之谷不過荍麥與豆,其山高水冷不產百谷之處無論矣!而能產之處,如巴塘、雜瑜產稻、谷,種之者亦鮮,耒耜仍如神農之法,斲木揉木為之;犁則二牛一具,具不系于牛項而系于牛角;又不糞”[11](P112)。趙爾豐認為“關外農器皆不適用,必須官為制造”[5](P467)。宣統三年(1911)二月,同普委員“由爐城購制鐵犁板五具回局,發交五路村長收存官寨,凡有百姓開荒者,均準借用,損壞不令賠償”[5](P973)。由于受到內地墾民耕種方法的影響,巴塘一帶的“土人漸亦學之,碎石除草,亦有鐮鋤之具”[9](P872)。
荒地的開墾促進了川邊水利設施的修建。巴塘糧務委員吳錫珍認為,“惟取水之法不一,必須因地制宜,地勢高則挖溝以引水,地勢低則開槽以進水。總之開通水源,以資灌溉,系墾務中第一緊要”[3](P9)。光緒三十四年(1908) 至宣統元年(1909),康定地區共修建灌田水渠長6389丈,其中新開渠993丈,其余“皆就廢渠故道修補擴充,寬四五尺或三四尺不等,淺深各就地勢,渠岸修筑均極堅實”。渠名為“永濟渠”,分為喇嘛寺、松林坪、磨西面、大杉樹四段。近渠一帶,有數戶播種稻谷,“居然有收”[5](P316-317)。
四、清末川邊農業墾殖的制約因素
川邊荒地雖多,但實能墾熟之地則非常有限,屯墾受到高寒和灌溉不便等條件的制約。宣統二年(1910),里塘糧員稱,“遵即查勘本臺四境各村,遍覓荒地。惟是地方高燥,春夏風雹極多;只東南一帶,較為溫和;西北及中央秋冬以后,類皆積雪彌漫,不出五谷。是以歷年招募關內墾夫,皆是送往巴塘、鄉城、稻壩等處,誠以試辦,難收效果,得不償失”[5](P728)。據德格委員萬里恩報告,“德格全境除作慶、格多、玉隆、巴烏、新多、上甲喜等處地勢高寒,只可畜牧,不能耕種……只有傍大小金沙江之絨壩岔、雜壩、卡生渡、汪波得、夜郎、熱登、崗拖、白椏及絨松、公丫、更慶、歌澤等寨,地氣較為溫暖”[5](P743)。巴塘“天氣燥熱,每屆春秋時節,晴多雨少,且數十里以內,山勢環繞,半屬磽確沙石,其間有平坦地壩,均經土司頻年開墾播種稞麥,所余山坡土凸,及稍為平坦之處,尤苦于無水灌溉,恐墾種亦難期收獲”[3](P9)。宣統二年,據定鄉委員調查,上鄉城、下鄉城、火竹鄉等處可墾荒地1320畝,“其余荒地雖多,或缺水,或瘠薄,據各墾夫聲稱,均不可墾”[5](P681)。
清末川邊的社會環境亦不利于屯墾的開展。川邊民眾缺乏重農意識,畜牧業在川邊占據重要地位。“照得關外蠻民,大都專事畜牧,雖平疇沃壤之地,亦曠而不耕,皆作為草場”[5](P436)。宣統元年(1909),趙爾豐在向度支部呈送的墾務暫行章程中稱,“關外蠻民游牧者多,耕種者少,兼之土司不準民間私自開墾,是以各處皆有荒地”[5](P467)。對于此種民俗,任乃強認為:“西康之番族受數千年逐水草張天幕之遺傳與訓練,遂以游牧為樂……雖有沃壤,亦棄不用……觀其良田荒棄之多,農作受限制之嚴,農民差徭之重,與農人子女規避吃莊房而樂為僧侶之狀,可以知其賤農矣。若牧民則甚自由,差徭亦輕。”[12](P25)
內地百姓根深蒂固的鄉土情結使得墾民的招募相當困難。光緒三十二年(1906),據蓬州知州戴賡唐稱,“蓋安土重遷,我國民久成習慣。舉田園親族而去之,時人既無此遠志;無田園產業之人,即去未必愿墾,墾者又未能必去;即或能墾又愿去矣,人數又不甚多;千里投荒,不免道遠勢孤之懼,只身異地,易起去而復返之心。其他種種下情,尤難悉數”[3](P16)。同時,川邊迥異于內地的自然環境和農作物出產,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民眾裹足不前。川邊“崇巒峻嶺,處處皆山,自打箭爐而外以至里塘,地寒雪早,遇有陸地,只產稞麥,更無水田可種稻谷”[3](P1)。光緒二十九年,據錫良奏稱,“竊查徼外,地非不廣,而樹藝不生、草木不長者恒多;間有可耕,僅產稞麥。非番屬之甘于荒棄也,冰雪彌望,風沙蔽天,盛夏猶寒,弗利稼穡。故蜀民最勤于農事,寧遠適秦、黔而不來墾辟,知其猶石田而無所獲也,今招募之亦必不至。若集商股,更無應者”[2](P365)。趙爾豐亦云,“川地偏暖,關外嚴寒,五月披裘,六月大雪,天時與內地迥殊。故言及出關,官商兵民無一情愿”[5](P120)。
由內地招募的墾民經常由于各種原因逃散。宣統三年(1911),據陸軍軍官張宣調查,“近年來,巴塘、定鄉一帶已由四川各州縣資遣農民出關”,但“未及一載,半已逃亡”[13]。這對墾務造成很大影響。總括起來,墾民逃亡的主要原因有:1.沿途土司的阻擾。光緒三十三年(1907),鹽源縣墾民500余人擬至鄉城屯墾,當行至瓜別土司地界時,“該處土司知民等要來鄉城,遂不放行,估逼民等與伊種地”,并帶人打散墾民,“搶去牛、馬、物件、農器、籽種等項”,剩余的墾民行至木里土司地界,土司“令人引民等由山僻小路而行,行至深山窮谷,引路人不知去向”。至鄉城地界時,墾民只剩180人,“其余七八十人落后的,均被木里土司攔回,不準前進”[5](P151-152)。2.川邊氣候和飲食不適。一些墾民因“吃慣大米,關外出產只有小麥、青稞、荍子、包谷各項,無有米吃,大家就嫌其地方苦寒,故出關之后,又有仍回原籍者”[5](P666)。3.官府給予墾民的補貼未能全部兌現。“農夫出關時,初議每名日給銀壹錢伍分,及抵關外,僅月給青稞二斗,約值銀壹兩貳錢有奇”[13]。4.墾民無法償還“公家所貸與之籽種等類”[13]。5.墾務官員的苛虐迫使一部分墾民逃亡。光緒三十四年,據墾夫張祿明云:“伊系四川樂至縣人,于前年應我帥招夫,隨帶妻子三人,分發至正斗村開墾,已開成熟田十余畝,已可安家,再不愿他往。乃因今年七月所領墾糧內有朽糧,而吳委員不但不承認發有朽糧,反謂墾夫聚眾滋擾……事后又恐吳統領拿辦問罪,以致渙散,無法制止。下鄉城墾夫逃往云南或稻壩,亦有逃往鹽井者,中鄉城墾夫逃往理化或巴安等處。我等逃往固頂寺,暫避其難。”[5](P279)另據宣統元年的一份報告稱,墾民到達關外屯墾地點后,“力耕苦作,稍怠則鞭笞立至,欲去則關隘綦嚴,困苦顛連,不堪言狀。川員每過其地,則環泣哀鳴,求在季帥(即趙爾豐)前代為恩懇”[14](P212)。
在前赴川邊的墾民中,無業游民、老弱病殘占有很大比例。據巴塘糧員陳廉稱,“接爐王丞來電,言資陽送來墾夫五十名”,但來到巴塘報到的只有老弱婦孺共22名,其中1名逃走,在剩下的21名中,“年富而力弱者紛紛以素昧農業,不知墾務,請給假另圖改業為詞。究其始招之由,半屬無賴流氓,在籍為煙債所迫,借關外為逋逃藪。既有川資可領,又有行館可投,借墾夫之名而來,非真欲來此開墾者也”[5](P398)。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陳廉建議,“嗣后有送墾夫出關者,必查其有無嗜好,是否農民,取具本地紳民鋪保。或仿行營招募兵勇之例,填造箕斗清冊,遞送爐城,再由爐丞詳加考驗,果諳習農業,再行按站發給到里口糧,以免沿途逃逸、改名他適之弊”[5](P399)。趙爾豐亦云,“墾夫則十有九病,屢集屢散”[5](P199)。宣統元年,卸管巴塘糧員兼知縣董濤指出,“出關墾夫老弱病疲十居七八,懶惰性成,久在洞鑒之中。或相率偷竊,或領糧私逃,甚有充清道夫亦不勝任者”[5](P405)。
清末川邊屯墾還存在效率低、成本高、招佃難、風險大等問題。巴塘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開辦墾務,“迄今三年,出關墾夫不下數百名,新墾之地不過數百畝,但所耗川資、口糧、農器及一切費用,曷可勝計”[5](P398)。巴塘“各村蠻民稀少,性又依戀鄉土,再三招徠,均不愿來巴佃種。本地漢夷百姓多種有三曲宗官地,兼小貿為生。加以近日差務繁多,實在無力承佃墾地。其外來漢民類皆游惰之徒,為數亦不甚眾,一經佃領墾地,必借領籽種、口食,方能承佃,稍不如意,輒相逃亡,所領籽種、口食即歸糧員墊賠。故,巴塘墾務匪特開地無多,深以為憂;即開成地畝,所苦無人耕佃,尤為可慮”[5](P405)。一些地方官對待墾務的態度亦十分消極。趙爾豐“曾設專員管理墾務,墾戶逃后,責令賠償。后因事權不一,歸并地方官兼辦,事同一律,故委員視招募墾夫為畏途,墾務之無起色,是亦原因”[13]。
清末川邊墾殖遭遇的困境也與制度等原因有密切關系。任乃強在論及清末川邊墾殖時認為:“移民不必由政府以令教強制,但宜將邊地景況、內地危機廣為宣傳,使齊民覺悟,志愿徙邊,則其開墾乃成定業。昔趙爾豐劃撥巨款,自湖北、四川招募墾夫,應募之人中途聞邊地苦寒,逃者什九。其到墾地者,遽使開墾,種種非法,一年無收,又俱惶恐逃去。巨款虛糜,徒為世戒,可為鑒矣。”[12](P292)與清廷主導的川邊移民屯墾相比,基督教會在爐霍、康定、道孚、巴塘等地屯墾政策的成功主要歸因于 “所用之墾民多屬漢番混血種”[12](P255)。土司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川邊改土歸流后,“雖然土司們的土地已經交付到政府的手里,但政府不曾以一種管業的形式分劃給享有土地的人民,使他們得有長期保障;雖然土司們被逐了,但趙氏不能有徹底的辦法使土司們與土地長期斷絕關系”[15](P341)。辛亥革命爆發后,政權鼎革,土司、頭人等復辟,重新把持地權,墾民陸續被逐,部分墾地逐漸拋荒。
五、結語
綜上所述,清末川邊農業墾殖大致分為初創與拓展兩個階段,歷時八年之久。由于諸多因素的制約作用,清末進入川邊的墾民數量以及所墾田地均相當有限。在屯墾實施過程中與當地民眾存在資源競爭等問題。清廷對川邊墾牧關系的認知也存在偏頗,一味強調墾殖,而忽視對川邊畜牧業的經營。即便如此,清末川邊墾殖也還是促進了當地農業改良和社會進步,對于維護國家統一、鞏固西南邊防起到了積極作用,其影響是長期而深遠的。來自內地的墾民攜帶新式農具、耕作技術及種子等,引發了川邊農業生產的革新。農事試驗場的開辦,使得蔬菜、雜糧等農作物在川邊得到推廣,導致川邊地區較為單一的農作物結構發生變化,豐富了民眾的日常飲食。同時,清末川邊各地的農事試驗場也成為民國時期西康農事試驗場的前身,奠定了川邊現代化農業的基礎。隨著農業墾殖的實行,墾民進入川邊各地安家立業,其中有泥、瓦、木、石、金、銀、銅、鐵等各種匠人[5](P278-279),他們創設木匠鋪、鐵匠鋪、裁縫店、理發店以及金銀作坊、小飯店等,川邊社會呈現出一番新氣象,內地的土地制度、社會習俗和文化傳統等也隨之向西傳播,推動了川邊地區多民族共居局面的形成和經濟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