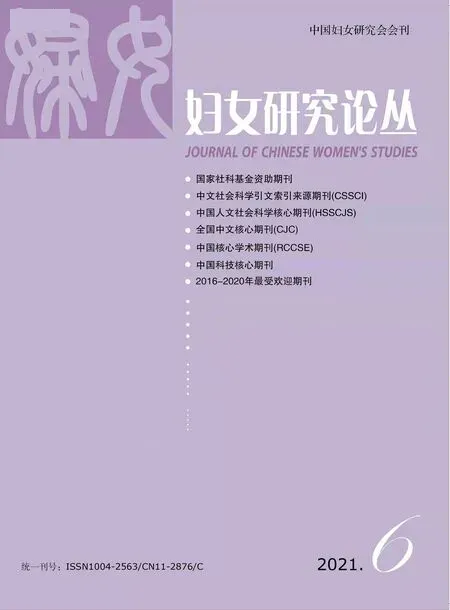外發工廠婦女的勞動生活困境與應對:一個零工經濟與性別融合的分析*
丁 瑜 梁家恩
(1.中山大學 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廣東 廣州 510275;2.廣州市花都區鄉村振興發展中心,廣東 廣州 510800)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本文作者之一的姑姑進入位于其粵西家鄉的一家外發工廠打工。在此之前她常向作者表達想去城市務工卻被家庭安排“拖后腿”的無奈。進廠之后,她的言談中多了很多新事和新詞,不再只關注家長里短。外發工廠這種“新鮮”設置讓很多像姑姑這樣的農村婦女多了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她們的家庭內部分工和關系也隨之發生改變。作者假期回家時,聽到了更多關于婦女打工的事情,比如她們以“臨時工”的身份加班,每個小時只有大概5元的加班費;她們的話語中多了“開心”、“QC”(質控員)、“經濟獨立”、“穿衣風格”、“身體護理”這樣的表達,與以往相比,話語重心發生了從“家庭事務”到“自我生活”的明顯轉移;她們要在車間里和管理人員“斗智斗勇”;她們既渴望上班,又累得不想去工作。男性村民無一例外地贊揚工廠的建立,認為這是在照顧農村人,老板是“好人”,而婦女本身卻對進廠勞動秉持兩面的、矛盾的看法。這激發了作者對外發工廠和對鄉村婦女在里面打工的好奇——外發工廠到底是怎樣的?婦女在其中打工有什么想法和體驗?
隨著非正式就業、產業區域轉移、遠距離外包等勞動用工和生產模式的出現[1],勞動力市場逐漸形成彈性機制,工資、雇傭關系、工作制度和勞動技能等變得更加多樣、靈活[1][2][3]。自2010年以來,全球代工產業最發達的中國珠三角地區囿于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的高成本,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廣東省內較偏遠的區域輸出[2]。這在某種程度上給生活在這一區域的人們,尤其是像作者姑姑這樣的留守女性,帶來了更多就業機會。這批經歷過外出打工又因家庭照料和戶籍制度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女性重新回到全球生產鏈條中。
近年來,隨著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政策的推行,各種扶貧工作模式如家庭代工、扶貧車間、村鎮工廠應運而生。無論是資本自發遷移、市場自發驅動的外發工廠等平臺,還是由國家力量主導,社區、社會資源等多方參與的各類減貧策略,都在客觀上迎合了農村留守女性就近就業的需求,因勞動密集性強、就業距離短和勞動形式靈活等多種特征,吸納和動員了較多的農村女性參與[4]。
作為脫貧攻堅短板的農村婦女就業問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議題,學者從不同視角研究“離土不離鄉”的就業形式對婦女的意義[2][4][5][6],豐富了我們對其就業狀況的認識。但過往的研究也時時提醒我們,當女性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社會建設或者全球化生產中時,各種隱形的設置可能會給女性帶來一些限制[7][8][9]。
隨著田野工作的逐漸深入我們發現,婦女在工廠勞動和家庭生活之間分身乏術,固有性別理念和家庭分工使得她們在繁重疲憊的工作之余仍要兼顧家庭事務;彈性而不穩定的訂單,加上近距離就業,使得女工看似擁有了“高度彈性化的工作時間”,實則沒有選擇權利,身體和時間不斷地被納入由訂單牽動的生產體系中。
我們比較容易看到農村婦女就近零散就業帶來的生活空間拓展、擺脫繁重勞作和獲得經濟權的外溢效果,但是這種看似“雙贏”的局面恰恰遮掩了背后的困境。對最新研究進行梳理,我們發現在零工經濟的研究中,學者多關注平臺勞動,對傳統勞動內容加新用工方式這樣“半新不舊”的勞動形式較少探究,即使關注也缺乏性別敏感度。在鄉村振興、婦女減貧的相關研究中,對留守婦女生產生活中的壓力、限制和她們做出的應對的討論依然不足;創新的減貧舉措也可能制造出性別困境,而這些問題仍未能得到充分探討,有些政策、措施缺乏性別意識與設計[4]。這兩方面研究的交織凸顯了性別分析的重要性——將以扶貧車間、發包代工等鄉村兼職短工方式開展的農村女性就業納入靈活就業的彈性工作制研究視野,讓我們更好地看到就近留守女性身處的勞動情景及其受到的限制和束縛;重視性別分析的婦女減貧研究能幫我們看到這些困境的性別特性,以及婦女在其中的主體性。我們希冀這樣的結合能更好地回應以下問題:留守婦女在外發工廠中有何勞動體驗?她們從勞動中能獲得什么?她們會面對什么風險與困難?是如何應對的?她們的經驗與城市中的男性零工經驗有何不同?
二、留守婦女就業之路:在零工經濟視角下重新審視
農村留守婦女的主要就業形式是非正規就業。基于家庭照料等限制,她們往往選擇就近彈性就業或兼業,具體工作形式多種多樣,有“客廳即工廠”的就業狀態[10]、由家戶加工發展而來的家庭代工[3]、因服裝產業而發展起來的合作生產隊[5]等。學者就不同類型的平臺對婦女就業的意義展開了討論,多數研究都認為它們有助于婦女在多方面獲益。
第一,這些平臺讓婦女的務工距離更短[4],使得她們能夠以較低的交通與時間成本參與生產。多數平臺都有較為靈活的工作形式,為女性務工帶來了更多空間便利,減輕了一些心理顧慮[4]。
第二,這些平臺往往是本地人員基于政策、資本流動等多方面關系設立的,動員的多是附近村民,形成以熟人網絡為基礎的擴散就業[6]。這樣的人際網絡使工廠、車間的管理更人性化,較能適應鄉村生活特性[2]。
第三,有學者認為,農村婦女的就業與傳統性別角色、家庭和社會關系等多有沖突,兼職和非正式就業本身就是婦女嘗試在家庭和工作角色之間尋求平衡的一種途徑。它回應了傳統性別角色對婦女的期待,滿足了婦女兼顧生產與家庭的需求[2][11]。
第四,留守婦女再就業可以增加家庭經濟收入[4],提升家庭生活質量,獲得家人尊重,在處理與夫家關系時提高在家庭中的話語權[2];同時,兼業生產收入是留守婦女承擔家庭重任之后的主要收入,留守婦女可以自主決定消費方式,提升自信[12]。人際交往格局的變化與圈子的拓寬也是婦女就近就業帶來的一個突出改變[6]。
與上述文獻所提到的勞動模式相似,本文中外發工廠的婦女勞動內容屬于傳統勞動范疇,勞動組織形式卻發生了一些變化:她們既不像以往那樣集體進駐工廠成為流水線工人,也不通過互聯網平臺接單,而是從工廠直接攬活,按需生產、按件計薪,或者就近應聘于臨時性、一過性的活計,工作具有即時性,不簽署正式或長期的用工合同。這屬于零工的形式,但與被稱為“新零工經濟”[13]的基于數字平臺勞動參與的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的勞動情境與方式不盡相同,也不屬于強調臨時性、項目性,參與者有特定技能、獨立自主的自由職業者的“傳統零工經濟”[13]。
有高技術門檻的高技能新生代勞動者并未成為中國零工經濟的主流,真正的大流是與之“相反”的低技能勞動者。零工經濟臨時性、非全職、彈性等特征導致了工作不連續、不穩定的脆弱性,缺乏保障[14][15]使身在其中的勞動者面臨諸多風險,低技術門檻行業的低技能工人只能靠在場服務加以應對[16]。研究顯示,技術能力與工作復雜程度越低的勞動者自主程度越低,可替代性與受控性越高,工資依賴越高,勞動者的競爭力就越弱,零工體驗也越負面[14][16][17]。農村留守婦女承擔的外包生產工作如釘珠、制作箱包零件、車縫,甚至是按次從事的清潔、拔草工作等,幾乎沒有技術門檻,婦女們也因為沒有其他就業出路而不得不去找這樣的工作機會,不斷接單以補貼生計,同時兼顧家庭照料。但她們經常面臨的情況是:訂單量不穩定,閑忙兩極,工資收入低,工作時間不規律,沒有福利保障。
傳統勞動理論對工人明知被剝削還全力投入的情境有非常充分的闡釋[18],既有研究大致將勞動動機歸為兩方面:一是由于勞動力市場結構轉變被迫選擇零散就業,勞動者并沒有追求自由自主、提升薪酬水平與擴大交際的就業目標;二是在別無他法之下的臨時性、補救性選擇,因缺乏其他賺錢途徑而不得不以此為補貼方式,勞動者并未有長期從業的打算[19][20]。工人處于勞資二元對立下的控制—屈服關系中,呈現出被動而妥協的形象,反抗意識被逐漸消解。近年來,關于平臺經濟中的勞動過程也受到學界關注,主要探討工人與機器間日益復雜的關系[21]。消費者體驗與評價的納入,使勞動關系拓展至三元,給予勞動者一定自主空間的同時對其產生了新的控制與支配[22]。
這些研究有助于我們察覺低技能屬性的彈性就業對勞動者的束縛。因此,當我們把鄉村婦女彈性就業或兼業工作放置在零工經濟的視野下時,就不難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何充滿臨時性、過渡性色彩的零工經濟到了農村婦女身上,就成為她們的有益出路?外發工廠的勞動婦女與其他零工經濟下的勞動者一樣,都處于資本的高度控制之下,雖然勞動關系不盡相同,但“虛假自由”[23]如出一轍,扶貧項目中的勞動婦女也面臨相似困境。借助零工經濟的視角,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留守婦女在生產生活中所受的限制。
但現有的零工經濟文獻中,“勞動者”多作為職業或階層分類的身份屬性被談及,對主體性的分析也多立足于勞資二元或勞消資三元的抗衡中,未能與更多社會維度結合,也沒有拓展至工作場所以外的地方[24],因而對結構性制約的分析不夠全面。接單勞動的留守婦女一方面屬于零工的范疇,另一方面屬于城鄉二分背景下拆分型勞動體制與父權制家庭安排的“無聲的順應者”,她們身上既有勞動者的特性,又有鄉村女性、留守妻母的性別身份屬性,如果我們單純用零工經濟理論來分析闡述她們的勞動過程、動機和體驗,不考察這些屬性及其身處的社會環境的影響,還是難以描繪她們的體驗并理解其主體性。
在女性主義的批判與推進下,勞動理論學者開始關注勞動以外的場所如家庭、性別刻板印象、日常性別實踐等對勞動關系和生產過程的影響[25](PP18-31)。這類研究的主要任務集中于兩點:一是性別如何從家庭和社會介入了勞動過程;二是性別如何塑造工人的主體性,從而使其產生應對或反抗。接下來將就此展開敘述。
有學者帶著性別視角去分析勞動過程,比如工廠怎樣塑造等級化、差異化、城鄉二元的性別形象以控制女性勞動力[26][27][28][29]。有學者開始關注各類鄉村婦女就業實踐中性別與就業在復雜社會經濟情境中的相互交織作用,比如,一些婦女就業平臺并不具備明確的性別意識,但在實際中契合了農村地區家庭的兩性分工以及農村婦女渴望通過工廠增收以改變自身家庭地位和家庭生計的需求,從而在扶貧工作中的性別意識方面具有意外性與外溢性[4]。有些扶貧車間給孩子們提供免費晚餐與寫作業的地方,解決了婦女的后顧之憂,這些設置可能是婦女們在其他企業里所不能擁有的“特殊待遇”[6]。
但同時,這些措施反映的正是婦女需要兼顧家庭照顧和社會化生產的現實。看起來溫情脈脈的親緣用工,又何嘗不是運用熟人網絡背后的“忍讓文化”使婦女面對更多的兩難呢?婦女在“離土不離鄉”的留守情境下,就近就業時會面臨更多的因性別身份帶來的限制與負擔[7]。她們有多重責任與壓力,家庭照料使其不斷向市場妥協,成為“不易反抗”的“廉價勞動力”[6]。李小云曾敏銳地指出,婦女減貧實踐可能引發賦權異化,比如婦女賺錢回家之后因家庭權力關系而將錢全部交由丈夫管理,或者用于購置夫家物品,因此我們不能只看到利好的方面,還應探索適合婦女性別特性的勞動內容與扶貧配置[12]。
目前大多數關于婦女減貧的實踐與研究都比較缺乏這樣的性別敏感度,對就業實踐對于婦女的影響缺乏細致洞察和多維度、綜合性的考慮,只看到表面效益,較少對其背后所存在的問題和挑戰進行探討,這樣的模糊處理不利于鄉村產業化更好地支持留守婦女群體,還可能會讓婦女陷入更大、更隱性的困境。
有學者分析了性別化的層級形成過程,比如不同的女性氣質與性別想象如何塑造了不同的勞動實踐[30],姐妹情誼如何拓展形成特定的婦女團體[31]。近年來有更多的學者開始探究性別化的主體性,比如,在主流性別期待與性別角色分配下,一些男性勞動者為了養家糊口的家庭責任忍受就業歧視,在與支配性男性氣質不符的情況下,他們可能出現性別氣質焦慮[32]及對子女愧疚、感覺自己無用的情感負擔[33],進而創造出多種策略構建不同于主流的男性氣質[33][34],弱化由遷移、就業帶來的城鄉和性別不平等。鄉村婦女面對彈性就業中的困境,也逐步發展出自己減負和應對風險的辦法,比如轉移家務照料負擔和“插忙工”[35]。
除了個體的應對,婦女有可能在日常雜事與自身需要的驅動下抱團,在這個過程中逐步走出小家庭,建立起更豐富的自我認知與團體感,在日常生活中雖艱難但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36][37]。比如,一些城中村婦女在日常生活中從自己最關注的事務出發,組織、動員其他婦女形成具有社群感的小團體,共同改善與維護自己生活的環境,并逐步從個體層面拓展到社區,開始關懷村中的其他人群,這種婦女團體的發展具有十分鮮明的性別特性[36]。我們在外發工廠的婦女中也看到了這樣的趨勢。婦女在父權制家庭體系與生產平臺的嚴苛控制中如何應對?她們因工作形成的新業緣群體能帶給她們什么?她們的經驗與我們較為熟知的城市男性零工有何不同?對于這些我們還需要加深了解。這些經驗對我們的研究乃至日常實踐來說尤為重要,是聯結理論解釋與實踐行動的通路。
基于此,本文呈現農村婦女在零工經濟下的選擇、生產故事與風險應對策略。一是為當下的零工經濟勞動過程討論增加更多的維度,包括性別與鄉村父權制家庭觀念影響下的勞動動機、過程與體驗,以更好地理解農村婦女所處的結構性環境;二是重新剖析在資本控制下逐漸淡化乃至消解的主體意愿,將過往研究中單純聚焦在“勞動者”身份上的扁平認知拓展到融入性別身份與團體互助的立體圖景中,推進對婦女主體性的理解;三是以一種更辯證的眼光看待婦女作為勞動力參與生產鏈條,防止利用婦女弱勢,以擠壓其生活空間、犧牲性別平等的長期發展為代價的方式提升經濟收益。
三、田野點與研究方法
本文的田野點位于廣東省茂名化州市H鎮。化州地處粵西,為茂名市代管的縣級市,是典型的農業與勞動力輸出大縣。H鎮位于化州西部,主要經濟來源是農業種植,一直有大量人口外出前往珠三角地區打工。2011年以后,該地開始出現外發工廠,本研究中的D廠是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承接來自珠三角及海外市場的訂單,主要從事皮包生產及服裝加工。工廠吸引了當地大量留守婦女加入,生產旺盛時期到廠上班的員工達300多人,疫情前穩定上班的有150多人(1)該數目截至2020年2月末。該廠訂單來源和消費者群體主要在國外,受疫情影響,2020年4月開始沒有了訂單,工廠停止生產,眾多女工選擇到城市謀求發展機會,因此女工數量大幅度下降。。
作者通過家人接觸到了更多接單勞動婦女,她們都是附近村民,每日騎電動車、摩托車往返于家庭和車間。我們遇到的絕大部分是“40”“50”年齡段,有媽媽、媳婦、妻子三重身份的婦女,她們都是比較“能干”的,是留守婦女勞動力的主體。工廠只有在特別忙碌時才會考慮招募較為年長者,因此平時基本沒有老年婦女。事實上,中壯年婦女都為自己能在廠里找到工作而感到慶幸。D廠對應聘者沒有特別的技能要求,主要就是“勤奮”。有的婦女有規定工作時長,可以領取勤工獎和假期補貼;有的沒有硬性上班時數,多數都是兼業生產。從薪酬計算方式來看,有論件、論時計酬兩種。她們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大部分靠的是鄰里社區的社會網絡,少部分靠的是親戚關系。
我們主要通過訪談了解婦女的個人及家庭狀況,打工經歷,進廠打工及不同工種選擇的原因,日常生產生活安排,就近就業對生活、經濟、社交的影響,等等。同時,通過熟人介紹我們認識了工廠管理人員,了解了工廠的運作和市場生產邏輯。我們共訪談了15名婦女、2名男工和2名管理人員,文中均采用化名。為了深入體驗婦女的工作生活,作者在2020年2-3月以“臨時工”身份進入D廠勞動,在閑暇時拜訪婦女們的家,了解其居住環境、家庭安排、生活狀態、成員關系等,有了直觀的感受和鮮活的體悟。
四、資本與父權合謀下接單婦女的三重困境
1.彈性工作的迷思:“隱形”的圍墻
留守婦女選擇就近就業的首要考慮是不用和家人分居兩地,可以兼顧工作與家務。婦女進廠時可以選擇當“長期工”或“臨時工”,但實際上這兩種形式都屬于非正規就業,都不在國家勞工權益保障體系內,只是D廠內部的叫法。“長期工”上班時間相對固定,有特定的獎勵機制,比如每月工作天數達28天以上且沒有遲到記錄,就能獲得100元全勤獎(2)這個金額對于當地的婦女來說不少,因為如果按時薪來計算,D廠內大多數婦女每小時僅能獲得7元報酬。,這樣的設置是為了鼓勵婦女盡量多地投入生產。“臨時工”可以擁有更自由的上班時間,可以請假照料家務,加班計時工資比長期工高。玉梅告訴我們,大多數婦女都想做“臨時工”,畢竟,婦女留守的職責是照料家庭或“成為前陣生產的后盾”。
但在D廠的實踐中,彈性工作時間意味著根據訂單情況被安排,隨時待命。當家庭需要和工廠生產重疊時,婦女基本無法獲得工廠的理解與體恤,個體生活必須讓位于生產進度。麗姐曾講過一件事:
入廠的時候,大家都說上班時間那么自由,那就是既可以照顧家里的事情,又可以揾點(賺點)收入。但實際上走動一點都不行。趕貨的時候,我們(生產)線有個婦女,她的兒子還在讀小學,老家只有家公幫忙照顧小孩。她兒子晚上從學校回到家就想找媽媽,打電話叫媽媽回家,她準備寫請假條回家。張總不批準,那個婦女就一直哭,她兒子也在電話里跟著一起哭。張總就罵:“有什么好哭的呢?趕完貨落班(下班)再回去。”
為了贏得生存空間,外發工廠“瘋狂”用工,它們不分工序多少,不考慮盈利空間高低,有單就接,這樣的結果是整個廠全年都處于忙碌的趕貨節奏中。婦女們訴說根本沒有淡季和忙季:“哪有什么不忙的時候?幾乎一年365日天天都加班。”
D廠主要加工國外訂單,而國際市場本身就充滿著不穩定性。國際采購商為壓低成本不斷地在全球尋找最廉價的生產者,貿易公司與當地制造業間的伙伴關系也變得脆弱起來,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從工廠的角度看,利潤高低主要取決于工人生產效率的高低。D廠是典型的勞動力密集型非精工型經濟,它回應市場不穩定的壓力主要靠廉價勞工,而非熟練技術工與持續的技術創新。它一方面通過品質管理維護重點客戶,另一方面通過低價接單與競爭工廠“自相殘殺”。
為保生產,每當婦女請假,工廠都會讓她們先趕貨,所謂的零散、自由無從說起。為了拿到每月100元的全勤獎,婦女一個月只能請假一次,“生存文化”讓她們別無選擇,“兼業”變“主業”。婦女們常提及“請假難”的事:
每次向組長請假都好難的,即使最后簽名了,還是要提很多次的。(珍姐)
家里種了點田,我那時候也做了臨時工,就想請假回去種田。我和組長說,組長怎么也不肯簽名,我就去找主管,主管也不肯簽名……說是臨時工,但一到請假就很麻煩……(玉梅)
“就近”與“彈性”并沒有為婦女帶來更多的家庭照料時間,反而成了工廠的用工策略。比如,D廠每月只放假一天,且時間不固定,要隨工廠需要“彈性安排”:
(放假一般)二十幾號,說不準,有時候遲點。發工資時,看趕不趕貨。如果貨不是很緊,就放一日假給大家逛街,要看貨期的。農村這些婦女就是每日都被困在那里,連日用品都買不了。(阿梅)
在這里上班很忙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時候放假,大多數時候都需要加班,一年365日,都沒有想到哪些時候不用加班的。訂單很多,做完這一批,下一批又開始了,感覺喘氣的時間都沒有,就又要開始干活了。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是個非正規廠,上班時間比正規廠還多,有時候還需要通宵加班。(麗姐)
婦女作為生產線的最末端,身體和時間不斷被納入由訂單牽動的生產體系中。但也有另一種極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訂單量急劇減少,工廠關門,婦女被解雇,她們一下連出賣勞動力的機會都沒有了。最新的研究也揭示了這種非正規就業的“超不穩定性”[38]。因為年齡、性別等門檻,她們無法尋求其他工作機會,很多人只好無奈地回家了。
2.親緣用工中的控制與隱忍
在偏遠鄉村的外發工廠,主要管理人員往往也來自附近村莊。一些研究顯示,雇主和工人間的關系更多是基于鄉誼和親情的互動,管理一般比較人性化,彈性放假和請假規定也似乎契合鄉誼生活圖景[2],但我們在調研中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與其他研究發現類似,婦女在出現問題和沖突時往往會礙于情面而選擇忍讓,避免矛盾激化。比如,車間管理者一方面要讓生產的皮革制品能達到采購方的質量檢測標準,另一方面又要滿足訂單數量的要求,婦女們有時會夾在“質”和“量”、本廠管理人員和采購方質檢人員中間難以平衡。此時,她們會采取“隱忍”或接受“責備”的方式來避免沖突和矛盾。本文作者之一在工廠時看到一個典型的情景。一批皮包由于趕工出現了質量問題,流水線上的阿姚把它們歸到“次品”的類別中,而D廠質控員認為這些產品應該歸到合格品里,就把它們撿出來移到“合格品”框內。后來,采購方質控員因這些“問題”皮包拒絕采購這批貨品。工廠管理者張總非常生氣,責備阿姚不仔細檢查產品。阿姚既委屈又生氣,忍不住發火,一邊將制包的原材料扔得四處飛散,一邊說道:“我叫不扔進去的,她們那些管理叫扔進去。假QC看得過眼,真QC能看得過去嗎?”其他婦女在一旁默不作聲。事后阿姚責備婦女們什么事情都忍著,阿梅回應她:
黃蜂和蜂王斗,你能斗得過嗎?你去斗他們,不就是讓別人來蟄你嗎?她是主管,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你不出聲就是了。而且有矛盾始終是不好的。我們很難做,工廠有要求,QC又有要求,兩頭都不能得罪。廠里頭大家又熟口熟面,沒有人想有矛盾,即使有委屈,自己忍忍就算了。
親緣用工模式中管理者利用留守婦女文化水平不高且維權意識不強的特點,通常并不為她們提供“五險一金”的法定保障。熟人關系下,遇到自身利益受損的情況,她們一般也不會向工廠索要賠償。若提出辭職,工廠會拒付一個月的工資,婦女也只會自認倒霉,不會繼續追究。
D廠實行“早七晚六”制度,對工人進行嚴格的管理。婦女們除了中午吃飯的時間外,沒有其他休息時間,每天工作長達10小時以上。工廠有“十不準”,比如嚴格遵守上班時間,未經許可不得離開工作崗位;不準無故曠工,請假需組長簽名,組長請假需主管、總經理簽名;生產線上不準吃東西;不準玩手機、打鬧、嬉笑;不準聊與工作無關的事;等等。雖然有這些規定,但是每到下午或晚上婦女們覺得紀律控制開始松懈的時候,就會三三兩兩地聊天,組長會點名提醒,有時候甚至直接罵人。英姐形容組長“罵人很厲害”“人還沒有到車間,聲音就先到”。苛刻而細微的工廠管理貫穿于每位女工的日常生產,直接作用于其身體,電子監察也發揮著作用。管理人員說過:“下次就在廁所安裝監控,大家就不敢去廁所玩手機,上廁所都那么久。”
婦女們會抓住工廠非正規就業這個點來抱怨:
如果說它是正規廠,錢也不多;如果(說它)不是正規廠,又管的那么嚴格,還趕過正規廠。(麗姐)
更多時候,她們會以沉默,即“不管它”來回應這些不合理現象。身體的慢性疼痛也成為一種常見反應。如凱博文(Arthur Kleinman)[39]所說,慢性疼痛是人類表達痛苦的形式,也是個體抵抗真實生活經驗的具體過程。D廠的留守女工每天勞動時長達10小時以上,訂單密集時通宵達旦加班也是常事。高強度工作下,加之飲食清淡又缺乏營養,許多婦女都出現了身體疼痛的毛病。
婦女概念中的合理與否,很大程度上和她們的接受與忍耐程度相關,這又與其對自身的性別定位相關,冬梅的評論很典型:
我們這把年紀出去好難揾工(找工作)的,又老,不要說45歲,40歲出去打工都沒有人要了。這個廠就不一樣了……50幾歲的婦女不知道有多少……我們這把年紀可以揾到工(找到工作)都偷笑了。
3.工廠和家庭:責任兩頭擔
在如此的勞動強度下,婦女本身已經疲憊不堪,但她們除了工人身份,還是母親、媳婦和妻子。調查時我們問當地村民對于D廠落地當地的看法,男性村民無一例外地說,“很好呀,婦女不用兩頭走了,可以照顧家里,又可以揾(賺)錢”“這個老板這樣做很好,非常照顧農村人”。但當我們問婦女“如果可以選擇,你想在家務工還是在外面務工”時,她們則表達了不一樣的想法:
如果可以,肯定想出去打工。在外面,自己一個人,生活又規律,吃飯又規律,中午又可以午睡。晚上只要洗完自己的衣服就可以睡了。在家里,下班之后不能丟開家里的事情,什么都得弄弄。在家里工作比在外面忙多了。(阿鳳)
外出務工的話,婦女不能直接處理家庭事務,無法兼顧賺錢與養家,因此一般而言,只需全神貫注做好工作,寄錢回家就好;而就近就業的婦女就在家門口干活,并不能擺脫家務。在問及如何處理家務時,她們的答案是類似的,即擠壓自己的休息時間:
早上早早起來,煮好飯。有時候早上要澆菜,有時候晚上澆菜。如果是夏天還好,早上起來天還很亮,晚上回去也還能看到路。如果是冬天,要打手電筒去澆菜。你不種點東西不行,哪有時間去買菜?而且能省一分是一分。(阿鳳)
走了很多人,大家嫌工作辛苦,沒日沒夜地做。中午半個小時就打兩次卡,下班打卡,吃完飯打卡,半個小時有多長,也沒有時間睡午覺。有時候困到站著都能睡著。比如阿材的老婆,家里沒有老人家可以幫忙,又要煮飯、澆菜、喂雞,她說她半夜12點才睡,有時候站著都睡著了。下班的時候又不能休息,想著家里的活沒干完都睡不著。(阿紅)
表面的互利共贏背后是一種斷裂,婦女不得不犧牲個人休息時間以“兼顧”性別化的照料義務和經濟需求,但也只能賺取微薄的薪水。阿梅說這種勞動方式不是婦女的“自由選擇”,而是在沒有轉圜余地的情況下不得不走的謀生之道:
如果可以,誰想拿那一點工資,又那么辛苦,實在是沒有辦法,正常班才5塊一個鐘,晚上加班也就是多2塊。過年那些出去打工的婦女說好像在家里工作也不錯,也有兩三千(元)一個月,我就會反問:“你們愿意回來做嗎?”實在是無奈才選擇這樣的方式的。
每到過年,看到別的婦女從城市務工回來,阿梅都羨慕不已。她非常清楚自己婚后就再也沒有機會外出務工了:家里事情太多,除了種菜和糧食,還要養蠶和照顧老人。每當和家人溝通外出務工的事,得到的回應都是“出去打工啰,整個家都不要了”。阿梅覺得很困惑:
家怎么就變成了我的呢?家公照顧也怎么成了我的呢?過年的時候,家公把被單、褲子都弄臟了,我就去處理了。一家人都在那里吃飯,就沒有一個人記得家公沒有吃飯。我就說,你們每個人只顧得自己吃好,不要老豆(爸爸)了。在家那么多年,照顧完細佬仔(小孩子)讀書,就照顧家婆。現在家婆走了,又要伺候家公。每次想出去打工,我老公就罵我,老豆不要了,扔了算了……根本就不能放開手。
要料理家務、照顧家人,還要處理村里人情往來、節日祭拜等事宜,婦女們只能利用早上七點前和晚上八點后的時間,其余時間都用于生產,來回奔波,分身乏術,疲憊不堪,一肩挑起兩副重擔。在訪談的最后,我們會詢問這些婦女是否愿意繼續在D廠干活,她們無一例外地表示,“不想到這個廠上班了”,“目前的情況比以前在城市打工累多了”。表面上就近靈活就業能使婦女取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實則是她們跌跌撞撞、戰戰兢兢之下的自我擠壓和犧牲,背后的邏輯是固化和加劇的性別秩序。
五、姐妹情誼中的婦女主體生成
拆分型勞動體制重塑了人口的流動和分布,農村空心化,婦女在村里“無所事事”。以前外出務工使婦女與原有鄉村生活脫節,與村里人事疏離,與丈夫情感疏遠,處于一種“懸浮”的狀態。能在家門口賺點錢或許是有益出路,也是她們最初進廠打工的目的,事實上卻收入微薄。代工生產隱性地利用了就近零散就業女性的弱勢來實現利益最大化,讓她們陷入了更多的限制和更大的困境。
故事的這一面看起來無奈且悲情,但當我們將這些婦女與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型零工經濟下的勞動者相比較的時候,還是能發覺一絲差異——婦女們以一種充滿了鮮明性別色彩的方式為自己開創了一隙空間,形成了支撐力量。高度發達的平臺與大數據技術造成了“被算法困住”的打工人[40],騎手、司機們必須遵循緊密的訂單時間,就像孤軍奮戰的一個個原子,孤立而缺乏歸屬感;D廠的婦女則像一個蜂群,雖然來自不同村落,卻因共同話題如工作、孩子、家庭等形成了新的業緣關系,打破了以往血緣、地緣人際交往格局的束縛,實現了信息共享和情感支持。
新情誼如同一塊石子投入平靜生活的水面,激起圈圈漣漪,婦女們互相交流、幫助、鼓勵,討論出一些應對困難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明晰了自己想通過勞動獲得什么,又可以得到什么。這是她們的直接收獲。婦女群體的形成也恰恰是她們應對困境的獨特策略,兩者互為因果。
1.在群體分享中應對困境
收入的增加讓婦女們的日常聊天多了話題,她們開始使用和分享那些會帶來“美”的體驗的產品。有些工友喜歡涂護手霜,其他人耳濡目染也開始用。過年后D廠開工,阿玲讓作者陪她去買內衣,說是工友介紹的,穿起來很舒服,就是有點貴,要四五十元一件,但想著橫豎都是自己穿,就買了。
在日常聊天與分享中,工友群體具有了一定的“黏性”,有助婦女獲得自己的生活空間,防止“夫權”的步步侵蝕,也使婦女有了傾訴之處。阿鳳自從在D廠工作后,社交圈擴大,網絡社交媒體使用愈加頻繁,下班后也常和工友通過手機聯系。丈夫看到她玩手機,非常好奇甚至警惕,當他覺得無法掌控她社交情況的時候,就會表達不滿。有一次他當著作者的面“投訴”阿鳳“玩手機的時候偷偷摸摸,也不知道外面是不是有人了,如果我發現,就打斷她的腳”。對此,阿鳳憤怒回應:
干什么都管,和工友聊個微信也管,我自己不能有點隱私和空間嗎?那我不玩手機,把手機給你管好了。你那么想把我管死,不要讓我去工作好了,你有能力讓我不去工作嗎?靠你自己一個人能撐起整個家嗎?
阿鳳的丈夫聽到這些,便沉默了。婦女有了抵御的盔甲和更多討價還價的空間,她們在一起聊家事、出主意,發泄不滿、互相安慰。
婦女們還想出了家務分攤的辦法來應對重負。開始賺錢之后她們就有了一些家務代際轉移的底氣,比如要求其他家庭成員,尤其是婆婆承擔部分家務:
每天七點就要上班,五點醒來都干不完家里的事。我出去賺錢,那家里的事,家婆就會幫忙弄弄,小孩子回到家里就做飯給他吃。其他事她也會幫忙打點。(麗姐)
除了在女性之間轉移,她們也開始將家務讓男性分攤,沖擊農村原有的性別分工。尤其是年末,丈夫們從外地回家過年,恰好碰上D廠最忙碌的時節,婦女們幾乎每天都在趕貨,她們就集體性地要求丈夫做家務。阿萍頗為驕傲地說:
以前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做,我老公的衣服也要我洗,但上班之后有時候回家很晚,他也會洗自己的衣服了。大家都這樣做,他也就沒有什么怨言了。
一些女性開始拒絕再從事需投入大量時間但收成受天氣等眾多因素影響、經濟效益低的繁重農作生產:
誰還想耕那兩畝田,日日曬,又辛苦,有時候做生做死都沒什么產出。但家公家婆又講閑話,說你閑在家里干什么呢?鄰舍閑話也多,你如果在家里,不干點農活、種點田,都會被人說。但是入廠打工就不同啦,平時家里買肉、柴米油鹽的錢都是我賺的。以前說我不干農活懶,現在一年有一萬(元)收入,不多,但是家里要點什么我都能出,就沒有人敢說什么了。(梅姐)
更有利的是,婦女們在一起會互相幫忙,比如誰家的孩子需要接送,有空的就去幫忙,誰家的農活要幫助,大家也會一起“快手快腳做完”,能解燃眉之急。雖然大家都忙忙碌碌,但互相交換一下信息,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2.姐妹情誼作為一種策略
上班使婦女有了自己的社交,是對“無聊”和“空洞”的生活的一種抵御。像阿玉所說,“大家都是工友,知根知底,溝通也多點,也有多點共同話題”。閑聊能提供一種強大動力,日復一日,從交換信息、產生對抗困難的方法到讓婦女因相互理解而抱團、互助,充滿凝聚力。婦女們常被說愛“八卦”,工作時“八”,吃飯時“八”,下班后就算在微信上也要“八”,還因為愛“吹水”(類似于“侃大山”的意思)而被管理層不斷批評。“八卦”在粵語中是一個非常性別化的詞,幾乎成了嘮叨中年婦女的代名詞,充滿了雞毛蒜皮、家長里短、好事饒舌的意味,但就是這樣的一種性別特性,成為婦女獨特的力量來源。
有時她們聊做工的話題,比如應對上面的管理,如何偷懶、請假、車縫某個部件;更多的時候她們會聊生活上的事,比如孩子教育、家庭關系與婚姻。一些難以對他人訴說的事,在同齡的工友這里就能自然道來。阿紅曾說:
你剛剛見的那個婦女很慘,她老公很大只(健碩),像阿明那么牛高馬大,但是他什么都不干,每天就是去打桌球。每次她老婆發工資的時候,他就去搶、去打她。她老公很沒有用,自己沒去工作,又常打老婆。我們平時聽她說,都覺得她好可憐,她一邊說、一邊哭。大家買東西吃也會分給她,她也喜歡分東西給我們吃,但是我們都不要,我們都知道她好凄涼,知道她的錢在發工資的時候會全被老公搶走,我們都看不過眼,大家都給她出意見。
生活的環境讓她們難以接觸到“家暴”的概念,但她們依靠自己的經驗和共情能力給工友提供安慰和建議。很多“不知道向誰說,別人又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會向工友說,大家都能理解”(冬梅)。基于工友身份而建立的親密和信任感,使得她們愿意分享。她們建立起姐妹情誼,產生替代性情感支持,也逐步認識到了自己的愛好與需求:
平時農村都是靜悄悄的。晚上加班晚回來又黑又怕,村里好安靜的。和工友聊聊沒有那么無聊,我們經常微信打電話談些好玩的,最近大家都喜歡分享跳舞視頻,大家都在房間里跳跳,活動身體,人就活起來了。(阿鳳)
工作中與工余的交流從提供新信息到改變生活態度,這是更重要的“再造”——在這些看起來“有的沒的”、無關緊要的瑣碎交流中,朦朦朧朧地,婦女們開始有了自我察覺,開始思考自己與周遭環境的關系,重新理解自己過往的生活與家庭關系,主體性逐漸凸顯。這并非源于她們有怎樣的性別覺悟,只是尋找到了以群體力量應對困難的方法。她們的關系始于車間,聊天的話題從最日常、直接的生產出發,延伸到共同的鄉村生活里,培養出共同的興趣,在勞動之外通過跳舞、美食、鄉俗瑣事進行聯結,再外擴到有關婦女共同的處境、利益,并在此中意識到留守女性共同的難題,比如缺乏交際、夫妻關系疏離、夫家壓力、鄰里矛盾、孤獨育兒,乃至家庭暴力。分享使她們意識到某些經驗具有共性,某些辦法能幫助他人,互相透露不僅不會暴露弱點,反而有強壯內心的作用。婦女樂于分享、擅于情感的特性使她們的關系超出了工友,情同姐妹。
在我們的田野中,婦女談及最多、最在意的就是工友間的聯結與情誼,這是一份“額外”的收獲,亦是吸引她們在困境中堅持的一股隱性的力量。她們非常珍惜這種惺惺相惜,會為了與工友相聚那一時一刻的歡樂去打這份苦工:
大家上班好開心的。雖然說很累很辛苦,但有時候也挺有趣的,斗斗嘴,吵吵架,一些不開心的事很快就過了……你拿我開玩笑,我拿你開玩笑,大家都好像姐妹那樣。(阿梅)
阿榮的女兒說,她從未見過母親有那么開心的時候,她甚至會帶上零食,和工友邊吃邊聊。以前她不理解為何母親“一把年紀了還執意要出去干活”,但在疫情封閉期間目睹了日常生活中父親對母親每每的冷言惡語相對和一貫的忽視,她“以一個女人而不是女兒的身份”開始明白了母親出去工作的愉悅,“現在她終于可以自己花自己的錢,出去之后和認識的那些姐妹們一起很開心的樣子”,哪怕只出去一天“也是開心自由的”。
這種能自我決策的獨立感和姐妹們在一起的群體感讓她們忍受工作中的困苦,堅持了下來。我們不能忽視女工在生產中的遭遇,但也無法忽略這些讓女性變化的閃光點。城市中的平臺工作者在資本控制下淡化、消解的主體性,在這些鄉村外發工廠的勞動婦女身上得到了彰顯,性別特性鮮明的姐妹情誼給我們帶來了啟發——想婦女之所想,充分運用日常生活與交流的累積力量,把團體營造作為一種激發主體性的策略,從點滴中提升婦女的自我意識。
六、總結與反思
不可否認,近距離的彈性就業對留守女性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借助零工經濟的視角,融合性別、城鄉、父權制家庭文化等多維度分析,我們能看到鄉村背景下傳統性別規范給婦女勞動帶來的困境與限制。D廠在H鎮的開設意味著偏遠農村已與全球經濟體系緊密聯系在一起,將留守女性作為“剩余勞動力”納入全球生產鏈條之中。接踵而來的訂單、停不下來的生產線,牽引著車間運作,安排著婦女的生活。密集的生產時間、無處不在的監控、嚴苛的管理人員,外加訂單的緊迫性和對采購商高質量的要求,催生婦女高強度勞動。零工式生產并不意味著松懈管控,鄉村環境中的親緣用工模式未能給婦女帶來良性的管理體驗。同時,因為女工們都住在附近,工廠可以以彈性工作為理由毫無顧忌地安排加班。無論是“長期工”還是“臨時工”,實際都是打零散工,不分晝夜地生產,所謂的彈性制度只體現在隨時隨意加班的“彈性”上。表面上看婦女似乎可以對自己的工作生活擁有“自主權”,實際上,由于留守和就近,她們并不能減少家庭照料,而是愈加工作和家庭責任“兩肩挑”,長期缺乏休息,造成心理的壓力和身體的疲憊。
留守婦女以就近零散就業的形式參與生產,肩負經濟發展的“神圣使命”,同時仍要承擔為母為妻的“道德義務”[10]。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勞動形式在推動女性走向社會的同時,也維持了社會性別差異,加劇了社會性別不平等。因此,我們認為當下應關注的重點不是婦女能否進入勞動力市場,而是她們如何同時挑起了勞動力市場中的生產功能與家庭中的再生產功能[10]。
這些研究發現提醒我們,如果只停留在個體層面,不能顧及婦女的實際境況、需要和性別特點,對她們所處的社會環境與結構性限制考慮不周,就容易僅在表面上將婦女納入發展的思路中,即只是在扶貧或鄉村振興項目前綴了個“婦女”的帽子,實際上卻并未深入,也難以通盤考慮婦女的需求,這是很多婦女減貧項目的通病[12]。我們需要思考為何在車間工作的群體大部分是女性,而不是覺得車間生產能滿足女性的顧家和生產需求,因此便具有性別外溢效果。具有性別敏感性的扶貧策略,要基于經驗,深入思考是什么結構性因素導致了婦女的處境,背后存在怎樣的社會與文化困境,將婦女與其他群體聯系起來考慮[41]。
資本、父權式家庭觀念與農村生活環境一方面合力對婦女產生壓迫,但同時,生產要求下生活習慣的改變也給婦女制造了松動的機會。婦女們利用生產安排上的緊湊、經濟上的改善調整家務分工,調節家務數量,分攤照料事宜,爭取更多個人空間,抓住話語權,發展個人愛好。共同的經歷與境遇讓婦女發展出了很好的社交關系和姐妹般的情誼。我們發現,群體的存在與其帶來的正面感受是婦女到D廠勞動的一大動力,即便零散勞動使得她們的生活變得細碎而辛苦,但因為它創造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群體感,所以她們堅持了下來。持續工作、經濟收入、交往擴大、自我改變扣合在一起形成因果循環鏈條。增加收入不是婦女工作動機的全部,它其實是生活方式、人際交往與自我認知改變的一把“扳手”,婦女只要自己手中有一點點閑錢,就更容易跳出原有的生活圈層,開始審視自我與環境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加深自我察覺,從而為建立工友群體積攢了意識上的能量;群體又為她們解決生活生產諸事提供了實踐上的能量,使這個鏈條動起來。婦女的性別身份在與工廠、夫家和鄉村生活的來回切磋、對抗中得到重塑和凸顯。
在零工經濟普遍發展的當下,從零工經濟的角度分析鄉村婦女的就近就業,包括勞動形式、雇傭關系、勞動權益保障等,突破了此前研究中對鄉村婦女勞動類型的關注,有助于我們看到婦女面臨的困境與限制;疊加勞動中的性別問題、家庭問題等多重矛盾,能推進我們對婦女處境的立體化認識。婦女在就業中形成的半職業社會關系對原有的家庭關系、性別關系都產生了影響,這是與城市男性零工不同的經驗。也許因為男性情感外露較少、隱忍要強的“性別腳本”限制,個體間缺乏聯結和正式制度支持;為了生活、養家而吃苦受罪,也是男性氣質的彰顯,因此他們只能獨自默默忍受。這也是本文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啟示——女性的一些性別化特性也許并不一定是限制,它可以被運用在婦女群體的動員和形成上,以集體的力量面對個人困境。因此,培育婦女的個人主體性與社群主體性[41],引導婦女團體的發生與成長,應是一項長期的努力。
女性賦權和女性反貧困是長遠的議題,避免婦女減貧路徑帶來的消極意義值得關注,設計有性別意識的扶貧政策尤為必要。本文側重在提出問題、呈現現狀與引發思考,研究也未涉及介入和實踐,未能在“如何做”這點上展開,但這應是將來研究和實踐的重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