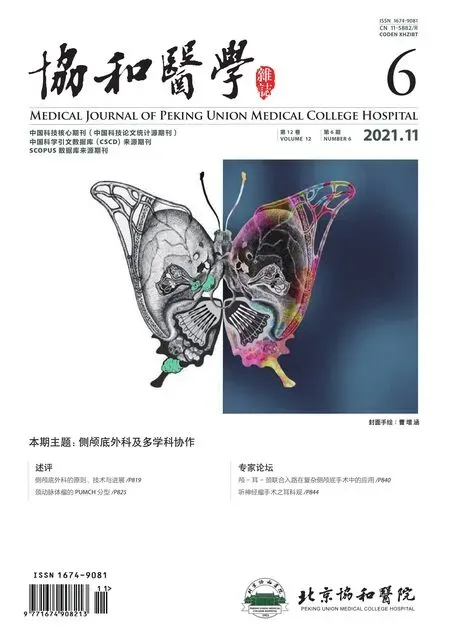數字醫生與平行醫療:從醫療知識自動化到系統化智能醫學
王飛躍
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復雜系統管理與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190
自人類歷史有記錄以來,醫療和智能就是我們生存與發展永恒的主題,二者相互促進、密切關聯,由此衍生出哲學、科學和今日形形色色的各種技術。追根溯源,西方現代醫學、哲學、科學和人工智能等學科和領域,同孕于古希臘文明,共生于文藝復興,成熟于近代和當代的科學技術。此外,自人工智能研究正式成為一個較為獨立的科學領域起,其在醫療中的應用是研發的核心主題。20世紀80年代,人工智能由于專家系統技術而有了歷史上的第一個“中興”時期,而醫學領域正是專家系統的主要用武之地,由此產生了著名醫用專家系統如MYCIN、DENDRAL、INTERNIST、CADUCEUS等[1]。
事實上,人工智能目前的“復興”也是基于20世紀40年代維納、McCulloch和Pitts等人對生物生理和人類大腦的研究,其所歸納形成的“循環因果(circular causality)”和人工神經元網絡模型正是今日大數據因果革命和深度學習的思想及理論基礎[2-3]。更為重要和有趣的是,引導未來人工智能和智能科技進一步深入發展的知識自動化理念與方法的正式提出,也是源自1987年《首都醫學院學報》對美國人工智能專家費根鮑姆在1986年第五屆世界醫學信息科學大會上所作報告題目之“誤譯”:把自主知識的英文 “AutoKnowledge”翻譯成“知識自動化”[4]。我們應該慶幸這一“正確”的誤譯,不但把知識自動化的歷史提前了20余年,且讓我們從新的角度反思:為何幾乎是智能醫學領域最需要的醫學知識自動化,其研發反而嚴重滯后,其配套的基礎設施至今依然是不成規模、難以流程化的“碎片”“孤島”式系統?
回顧西方現代醫學的發展,醫護工作者和相應學科的“專業分工”是其科學化的關鍵一步。然而,醫療的專業分工能夠達到今日的高效和可靠程度,各類醫用機器的引入功不可沒。特別是在醫用機器人引入之后,“人機分工”己成大局,并進一步成為“專業分工”真正有效、可信的基礎和保障。人機分工之后,盡管醫學信息化得到了深入和普及,但為了實現醫學自動化的需求,我們必須進一步考慮并引入“虛實分工”,利用智能科技和云端資源,推動醫學智能化,反過來以此確保醫學自動化的成熟、可靠、可信以及普及應用,進而提升人機分工的水平[5-7]。
我們認為,從“專業分工”到“人機分工”,再到“虛實分工”,是智慧醫療發展的必由之路,而虛實分工的關鍵與核心是引入數字人醫生或數字醫護工作者,以及相應的虛實互動平行智能醫學體系,其本質上是通過虛實分離實現醫療知識自動化的過程(圖1)。這樣做的目的,首先是強化生物人醫生在整個醫療體系中的核心與指導作用;其次是減少醫護人員和患者家庭不必要的工作量與負擔,平衡生物人醫生、機器人醫生和數字人醫生之間的關系,有效地從醫學小數據中生產出醫學大數據,進而從中提煉出針對具體患者病情及場景的“醫學智數據(smart data)”;最后,以可持續的方式,實現“6S”的新一代智慧醫療體系,即基于虛實互動的平行健康、平行藥物、平行醫學、平行醫療、平行醫院,實現人類健康系統在物理空間中的安全(Safety)、在信息空間里的安全(Security)、生態的可持續性發展(Sustainability)、個性化優化(Sensitivity)、全面服務(Service)和深度智慧(Smartness)[5-7]。

圖1 數字醫生與智慧醫療的虛實分工
本文將就新一代智慧醫療系統進行初步討論,以期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共同推進智能醫學和智慧醫療的深入發展與應用。
1 智能醫學研究現狀與問題
以圖像處理為主的疾病診斷智能化是目前智能醫學研發的絕對主流[2,7-9],熱點依然是精度和可靠性問題,深度學習和對抗生成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工具。隨著深度神經網絡構造的不斷演化、算法的不斷提高和圖像數據庫的不斷擴大,精度將成為非主要問題,特別是相對生物人醫生水平而言。然而,依據現代算法的水平,可靠性和穩定性問題依然難以獨立解決,人機混合的方式不但可以解決可靠性和穩定性問題,且可顯著提高醫療圖像識別的精度。綜合考慮法律、倫理和人性化,人機混合智能和視覺推理方法應是疾病診斷智能化研究的主要方向。平行醫學圖像處理和計算知識視覺方法[8-10]是沿此思路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醫學圖像處理方式,可以方便地將醫護人員的行為模式、醫療診斷流程和面向患者的可視化工程等涉及人的環節納入基于圖像的診斷過程。
以語言文本分析為主的疾病咨詢智能化是人工智能醫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且日益受到關注的方向,語言交互和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是其主要方法和工具,已在智能導診和心理咨詢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實際上,這一方向的工作不但涉及人工智能的核心技術NLP和正在興起的腦機接口與人機交互,且與剛剛起步的敘事醫學[5-7]、患者健康數據的有效利用及進一步提升息息相關,是改善醫療效率和醫患關系的重要手段和創新途徑,十分值得關注和投入。
疾病預測與干預智能化和疾病治療與醫學服務智能化是智能醫學研究的2個重要領域,但難度相對較大,且很難靠智能算法單獨解決,必須有醫學知識和專家的深度介入。在預測和干預方面,主要方法是較為傳統的醫學信息檢索、信號處理、大數據分析與模型預測,以及新興的知識圖譜方法。在治療和服務方面,主要手段是NLP、人機交互、醫用機器人、機器學習和增強現實等。
人工智能在衛生健康管理智能化領域的研究正在引起廣泛關注,且在引入NLP、社會計算、機器學習、知識圖譜、機器人過程自動化等方法與技術后,取得了顯著成果[7]。另一個相對被忽略但十分重要的方向是人工智能在健康及醫學教育方面的應用。盡管中外許多創業公司和跨國企業已大力開展醫學教科書和論文的知識圖譜構建,但相關教學與示教應用仍然滯后,應引起關注。人工智能在健康、醫學、醫療教育和管理方面的應用極其重要,也是智能科技易真正發揮效益的地方,但利益沖突和體制慣性是其相對落后的重要原因。
總之,盡管近年來人工智能在醫學領域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在數據質量、監管與評估、成果轉化與商業化、法規與倫理等方面依然存在諸多問題和挑戰。宏觀上看,目前研究涉及的醫學知識和醫療流程并不深入,人和社會因素考慮不足,在本質上難以整體處理醫學所面臨的科學性、人文性、社會性交融的復雜問題,必須集跨學科醫學、復雜性醫學和系統化智能醫學為一體,在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基礎上,創立新一代的智慧醫療。結合平行智能方法,沿此方向的一些初步研討可見文獻[5-10]。
2 智慧醫療:學科交叉、復雜性科學與系統智能科技
被稱為西方“現代醫學之父”的奧斯勒曾言:“行醫是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藝術。”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點破了醫學的本質:醫學,特別是醫療,僅有科學還不夠,人們必須同時面對醫學的科學性、人文性和社會性,以及這些屬性共同糾纏所產生的不定性(Uncertainty)、多樣性(Diversity)、復雜性(Complexity),即UDC。智慧醫療的歷史使命就是利用智能科技創出一條新路,化UDC為保障人類生命健康的AFC能力,即針對各種疾病處理的靈捷(Agility)、向具體醫療任務聚焦(Focus)、向健康目標收斂(Convergence)的能力。為此,我們必須融跨學科醫學、復雜性醫學和系統智能醫學為一體,集生物人醫生、機器人醫生、數字人醫生于一身,開創醫學發展新的歷史階段。
為何采取這一途徑?源頭即是醫學問題的復雜性和當前已經出現的一些難題。人類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努力,從宗教或經驗式的傳統醫學啟航,終于使現代醫學成為現代科學的核心之一,特別是在基因信息學和分子生物學的推動下,正向集防御(Preventive)、主動(Proactive)、精準(Precision)和個性化(Personalized)為一體的“P4”醫學邁進。然而,在醫學的科學進程中,技術至上的思潮涌現,甚至愈演愈烈,致使有些地方的醫療實踐嚴重偏離醫學的人文和社會屬性,特別是對不斷重復的LUC(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現象視而不見。這些問題充分表明,醫學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只能回答可否做到,但依然無法真正回答需要做什么的問題。這就是必須融合復雜性科學、系統化智能科技和交叉學科方法構建智慧醫療的根本原因。
針對醫學科學屬性中的還原困境和循環困境,醫學人文屬性中價值的主觀性、效果的心理性和應用的有界性,醫學社會屬性中發展的資本性、倫理性和一致性等一系列主要問題,除現行的方法與實踐外,新一代智慧醫療應考慮下列研究課題:(1)基于復雜性科學的復雜性醫學;(2)基于交叉學科的跨學科醫學;(3)基于系統工程的系統智能醫學或元體系智能醫學。
總之,復雜性醫學的目標是利用復雜性科學的研究,將復雜性任務交給虛擬的人工系統解決,而醫學工作者的工作必須盡可能簡單化,最終希望人僅處理高心智卻“簡單”的人文性和社會性任務。跨學科醫學的任務是建設新的醫學基礎設施,培養新的醫學范式和醫療文化,實現交叉學科醫學知識自動化,其目的依然是減輕醫生和患者的負擔,提高醫療效益。系統智能醫學希望利用數據智能和智能科技,通過人機結合虛實平行的方式,將復雜性醫學和跨學科醫學的理念、方法、技術、流程付諸實踐,成為可信、可靠、易用、高效的分布式自主自動化醫療組織和系統,變革現行醫學和健康體系,更多更好地服務人類。
3 平行醫療和平行醫院體系
所謂平行醫療,就是利用平行系統和平行智能方法研究與醫學相關問題的方法與體系,主要由基于人工社會(artificial societies)+計算實驗(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平行執行(parallel execution),即ACP方法的醫療流程和平行醫學框架平臺組成。目前風行的“數字孿生”是平行系統的簡單例子,而元宇宙是平行系統較復雜的情況。首先,需要構建與實際現行的醫學研究和醫學服務對應的人工或虛擬醫學研究步驟和醫學服務過程模型,即將其軟件化定義或數字化孿生。一般而言,一個或多個實際醫學系統(實際系統)可以對應于一個或多個人工醫學系統(人工系統),一是完成醫學醫療模型的形式化和知識表示,二是將模型的功能從傳統的分析轉化為數據生成。在人工系統的基礎上,開展醫學的計算實驗,將具體問題的“小數據”,通過這一實驗過程和對抗生成等方法變成“大數據”,再利用機器學習和各種人工智能方法凝練出針對具體問題的精準知識,即“智數據”。醫學的最終任務是解決患者的問題,因此,還需要在人工系統和計算實驗的基礎上實施平行執行:實際醫療系統與對應的人工醫療系統各行一步,然后交換其結果并進行比較,根據差別進行虛實反饋,實現虛實閉環,如此反復進行,利用虛實平行互動,形成虛實之間的雙反饋和雙閉環醫療系統。
平行醫學的基本思路為:利用虛實的相互作用,由“單一世界”轉變成“多重世界”,完成對實際醫療過程的管理與控制,包括對有關醫學人員的培訓和系統學習,對相關醫學決策和行為的實驗與評估,使過去“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方式升華為科學化、系統化、精細化水平的科學管理,并能夠以可計算、可實驗、可驗證的方式不斷改善、不斷提高。
平行醫學系統的基本框架主要由實際醫學系統和人工醫學系統所構成的平行系統,以及學習與培訓、實驗與評估、管理與控制3個功能平臺組成(圖2)。利用平行系統的虛實互動和平行驅動,對虛實之間的行為進行交換、對比和分析,完成對各自未來狀況的借鑒、預估和優化,相應地調節各自的運行管理與控制方式,實現相關人員和算法的學習與培訓、相關決策和行為的實驗與評估、相關過程與服務的管理與控制。

圖2 平行醫療系統的基本框架
盡管在科學上已取得了許多重大進展,但醫學在本質上還是一門實驗學科,依然按照“吃一塹,長一智”的方式進化發展。在一定意義下,平行醫學就是利用信息和智能技術,把在物理世界的“吃一塹”,換成在知識虛擬世界的“吃一塹”,把在虛擬世界認知上的“長一智”,換成在物理世界實踐上的“長一智”,特別是虛擬的“吃一塹”可以通過知識自動化和數字人醫生的形式大范圍地快速進行實驗,把醫學的“小數據”變成“大數據”,再凝練成“智數據”,實現低成本、高效益、廣智慧。目前,平行系統和平行智能的方法已在軍事、國防、經濟、制造、教育等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5-10],并在痛風、皮膚、眼科、手術、制藥和醫學圖像等方面開始了一系列的探討[5-10],有待進一步開展更加深入細致的系統化研究與實踐。
顯然,針對平行醫療技術,現存的醫院管理與服務體系也應進行相應的變革,其關鍵是引入數字人醫生的理念和方法,實現醫療服務的知識自動化。因此,醫院本身也必須虛實一體,將目前的醫院信息系統進一步數字化、平行化和智慧化。此外,醫院之間也應形成一種新型的合作關系,在“孤島”和保護隱私的前提下,實現共同提高、共享服務。聯邦醫院體系就是面向這一方向的一種新的技術[5]。其核心就是利用區塊鏈和DAO技術,以及面向人類的編程(HOP)和操作系統(HOOS),特別是引入數字人的數字人格與相應人類性格的適配算法,通過共識算法和聯邦控制實現聯邦數據,進而由智能合約和聯邦管理實現聯邦服務和聯邦智能,構成智慧醫院體系,走向真正集預防、主動、精準、個性化于一體的平行系統智能健康與醫療,即“P5”醫療。
4 展望
畢寶德(Peabody,1881—1927)是西方現代醫學史上的傳奇醫生,他的傳世名言是:“臨床醫生的一個基本品質就是人道精神,因為照顧好患者的秘訣就在照顧的過程之中(One of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of the clinician is interest in humanity,for the secret of the care of the patient is in caring for the patient)”。一百多年前,正是畢寶德幫助洛克菲勒基金會制定了創立北京協和醫學院和醫院的決策和規劃。為了使“照顧好患者”從一門藝術成為一門科學,從而更好地救助患者,畢寶德引領美國醫院和醫學院發起從傳統向近代科學變革的運動,在醫院中引入實驗室探索和案例研究制度,推動醫生從傳統匠人轉為研究型學者。彼時正值傳統醫學向現代醫學過渡的關鍵時期。他不但在哈佛醫學院和波士頓城市醫院推行并實踐其理念,還力推將其納入北京協和醫學院和醫院的建設方案和實施之中,認為“協和不但在人員、設備和設制上屬世界一流,而且其選擇和照顧患者的方法、醫護人員學習與交流的方式尤具特色,可與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醫學院在科學醫療前沿攜手共進”[11]。
一百年后的今天,醫學科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畢寶德 “照顧好患者”的信念依然是醫學的起源和目標。在巨大的科技進步之后,人們發現我們必須綜合考慮醫學的科技性、人文性和社會性,否則將無法“照顧好患者”。這正是以人工智能和智能科技為基礎的智慧醫療的歷史使命和動力:從復雜性科學、多學科交叉和組織系統化智能的角度,統籌人類健康的科學、人文、社會等屬性,不但推動從“P4”至“P5”的精確智能醫療進程,還要加速實現“6S”的新一代人類智慧健康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