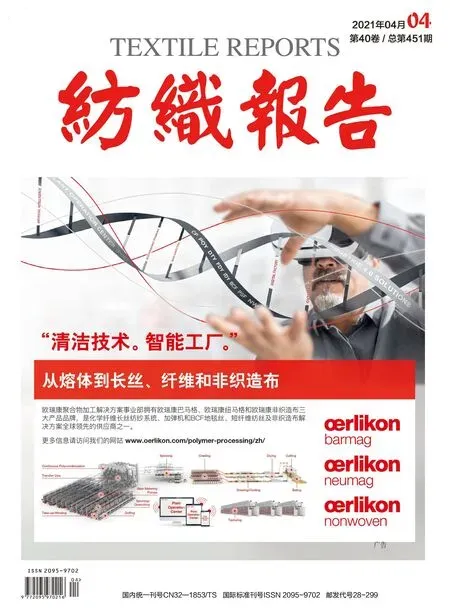唐代兒童服飾文化與形制特征
劉 歡
(嶺南師范學院 美術與設計學院,廣東 湛江 524000)
在中國古代繪畫中,以兒童為入畫題材有著悠久的歷史,根據畫像可以推測出古代兒童服飾特征與文化,為當代兒童服飾設計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在兩宋時期,嬰戲題材較為豐富,而唐代以前的圖像不多,從唐代開始清晰易辨。畫像中呈現的服飾一方面反映了開放經濟影響下成人對孩童的成長與關懷,另一方面蘊含了當時的宗教思想。描繪孩童的畫家有張萱,雖然在唐代還未形成獨立的兒童繪畫,但張萱畫孩童既有童稚形貌,又有活潑神采,從宋摹本的張萱《搗練圖》中可窺見一斑。
1 唐代兒童服飾的文化屬性
通過梳理唐代兒童圖像發現,唐代兒童服飾大體上呈現簡潔、實用的特征,同時受胡服的影響,唐代兒童服飾獨具特色,唐代經濟的發達、意識的覺醒促進了唐人對兒童的包容及人性化、至美至善的成長觀,在服裝上則更多體現其合理、科學的功能性和美觀裝飾作用。唐代兒童服飾的審美趣味及其受到的影響出發,本研究認為唐代兒童服飾受到3種文化的重要影響,分別是儒家文化、胡風和佛教的影響。
首先,以儒家文化為基礎。李唐立國之后,延續了隋代的科舉制度,打破了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度,對后世中華文化影響極深。儒家的興盛使得對孝行的提倡再次成為社會的普遍認識。“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兒童成為社會關注的對象,也反映在唐代詩歌中。據統計,《全唐詩》收錄了73首兒童詩,包括“兒童自己創作的詩、描寫兒童的詩、寄贈兒童的詩”等[1]。如白居易的“繞池閑步看魚游,正值兒童弄釣舟”、賈島的“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都是千古名句。此外,還出現了天才兒童詩人,如晏殊八歲就被譽為神童,《新唐書》載:“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唐代美術考古實物中豐富的兒童圖像及其反映出的服飾文化,正是在唐代儒家文化流行的背景下,人們追求“子孫昌盛”和重視兒童教育社會現實的縮影。
其次,胡風的浸潤。唐代,開疆拓土版圖達到了歷史巔峰,在唐朝統治下,有很多胡人把“胡風”帶入了長安,帶入了唐代社會。尤其是在盛唐文化中,以“胡風”為審美的社會尺度,在長安街頭流行胡食、胡服、胡語、胡坐等,上層統治階級使用“葡萄美酒夜光杯”,李白筆下有“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當安歸”。胡服、胡妝在社會中廣泛流行,元稹寫道“女為胡婦學胡妝”,對社會習俗影響深遠。在這種背景下,兒童服飾也受到了胡風的浸潤。如前文提到的兒童所穿的皮靴就是來自胡風,童子的披帛更是受到印度的影響。敦煌莫高窟第361窟中唐時期化生童子的腰鼓是來自西域諸國的樂器。莫高窟第12窟中晚唐時期化生童子的服飾是“交領窄袖”的胡服,其抱持的“篳篥”等樂器也是來自西域地區。《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引《樂府雜錄》云:“篳篥者,本龜茲國樂也,亦名悲篥,有類于笳也。”
最后,佛教的影響。童子與蓮的組合受佛教的影響較大,亦體現了唐代人賦予兒童服飾的寓意,并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較多例子表明,佛教石窟壁畫是唐代兒童服飾圖像的重要載體,表明二者之間的關聯。如敦煌壁畫中,兒童圖像非常豐富。又如在佛教故事繪畫中,童子本身就是“化生童子”和“誕生佛”內容繪制所必需的題材。在唐代“凈土宗”流行的背景下,在壁畫或絹畫描繪的佛國世界里,童子形象又是千變萬化的佛國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童子們或披帛舞蹈,或攀登蓮花;或雙手合十,虔誠禮佛;或演奏胡樂,令人陶醉。佛教的悲憫之心和童子的天真無邪形成了對應,影響了石窟觀賞者的宗教體驗。
總之,唐代兒童服飾呈現出以上3種文化的綜合影響,形成了獨具魅力的兼容并蓄的藝術特色,成為中華服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人們深入了解中國古代悠久燦爛的文化、實施“文化自信”戰略、為當代兒童服飾設計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2 唐代兒童服飾形制
通過唐代兒童圖像及相關文獻資料的分析,可窺見中國唐代兒童服飾的基本形態。唐代兒童服飾形制包括首飾、帽子、圍涎、披帛、襁褓、兜肚、裲襠、圓領袍衫、短衫、襦裙服等,既滿足了兒童身體發育的需求,簡潔、實用,又體現了多民族服飾文化融合的影響,款式上豐富多彩且獨具特點。
2.1 飾品
頭部、身體各部位佩戴的裝飾品,大致可以分為首飾、帽子、圍涎、披帛,具有實用功能或裝飾功能。瓔珞和虎頭帽可作為唐代兒童飾品的代表,在考古資料中時有發現。現有的兒童圖像資料顯示,唐代兒童佩戴的首飾主要有項圈、手鐲、腳鐲、長命鎖和項鏈等[2]。項圈有金屬素圈,另在兒童和女性之中廣為流行的是鑲飾珠寶的瓔珞。纓絡,即瓔珞,可佩戴在不同部位,戴在脖子上的叫“瓔”,戴在手臂、小腿等處的叫“珞”,源于佛像頸脖間的裝飾。在敦煌莫高窟第361窟中唐時期的伽陵頻迦伎樂與化生童子畫像中,人首鳥身的伽陵頻迦頭梳發髻,半身赤裸,張開翅膀,身上佩戴瓔珞,雙手作舉高狀態,敲擊圓形銅鈸,而右側上方童子亦全身佩戴瓔珞,有項飾、胸飾、臂釧和腕釧,童子腰間一鼓,畫像呈現出精致、豐富多彩的唐代菩薩裝飾風格。同時,唐代兒童有佩戴長命鎖的習俗,是對子女健康長壽、驅邪消災的祈愿,展現了唐人對孩童的關懷呵護。
帽子在唐代時期已成為中原漢族傳統的兒童服飾之一,具有御寒的功能性和裝飾性。唐代兒童所戴帽式均無帽沿,有多種帽式,如尖頂、圓頂瓜皮帽及虎頭帽。在揚州唐城和1978年常州勞動路分別出土了兩名手抱球且頭戴圓頂瓜皮帽式的童子俑,童子手上均抱有一圓球作戲耍狀態。西安韓森寨唐墓出土的嬰兒俑頭戴虎頭帽,此帽源于佛教中的護法天王形象,可見虎頭帽是一種廣受唐代兒童喜愛的帽式,亦可窺見唐人借神靈來庇佑兒童健康成長。虎的形象具有豐富的民俗意蘊,形象威武又憨態可愛,既可辟邪鎮宅,又可祈福保佑,虎頭帽傾注了唐代成人對兒童的深情呵護,又寄予了對兒童茁壯成長的祝福。亦有學者認為,唐墓中的虎頭襁褓俑、童子雜技俑、童子洗澡俑都屬于戲弄俑,是唐代生活豐富多彩的表現[3]。
圍涎也叫“圍嘴”,最早可追溯至漢代,是嬰幼兒服飾中最常見的一種功能性強的服飾品。西漢揚雄所著《方言校箋》卷四提及“繄袼”一詞,晉代郭璞標注:“即小兒涎衣也。”[4]圍涎早期以實用功能為主,至唐代以造型多樣、實用美觀并存,圍涎上的裝飾紋樣變化豐富,題材多樣,不僅給人們帶來視覺上的愉悅和精神上的享受,亦有較強的文化傳遞和風俗體現,為當代設計留下了珍貴的參考資料。據資料分析,唐代圍涎紋樣裝飾有單一或重復的幾何形、植物形、動物形和人物形,色彩大膽,對比性強。初唐第329窟西龕外側中的化生童子,下方童子頸部戴橙色圍涎,繡有裝飾花樣,右手抓握蓮莖,左手則隨意朝下,雙腳穿同色柔靴,左腳懸空,右腳踩蓮,畫面生機勃勃,突顯孩童天真可愛的性格。晚唐第173窟化生童子畫像中,有一赤裸上身、肩部飾披帛、下身著褲的蓮花童子形象,即化生童子。在佛教中,化生是生命的誕生方式之一,指無所依托,借業力而生。童子與蓮的畫面組合,或手持蓮花、或腳踏蓮花、或處于蓮花之上,蓮花是佛教的象征,是兒童純真圣潔的象征,是對新生命的祝福和對往生者的輪回。
2.2 服飾
古代“衣”的服裝形制,一般指上衣或上下相連的款式,唐代兒童所著襁褓、兜肚、裲襠、圓領袍衫、短衫、襦裙服等皆屬童衣范疇。嬰兒從一出生便穿襁褓,是唐代育兒習俗。“襁”指背嬰兒用的布幅或寬帶,長一尺二寸至二尺,寬度為八寸左右。“褓”指用以包裹小兒的被子,襁褓嬰兒也指未滿周歲的孩兒。在畫圣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畫面第三段《釋迦牟尼降生圖》畫面中,可看到凈飯王懷抱的嬰兒清晰而完整的襁褓形象,畫面以佛教題材表現人物形態和服飾。在西安韓森寨唐墓出土的長約10 cm的嬰兒陶俑中亦有發現,此嬰兒俑頭戴虎頭形帽子,身著一層寬帶圓領襁褓,身前系成蝴蝶結狀于中間,嬰兒睜著雙眼安靜地被包裹在襁褓中。經梳理可知,唐代襁褓是具有保暖功能和人性化的服裝形制,將嬰兒包裹在襁褓中,可使其產生安全感并易入睡,促進嬰兒身體的生長,還可使得腿部保持平直生長,保證身體健康,亦有學者把此俑歸納為戲弄俑,認為是多姿多彩的唐人生活的體現。
兜肚,即“肚兜”,是一種貼身穿著、護住胸部至腹部的布塊,具有保溫、護腹、裹肚的實用功能,用一條或兩條帶子系在脖子上,從腰處將兩條帶子系于后背。基于成熟的唐代絲織工藝技術,肚兜不但品種多樣且繡有精美的圖案。最早發現的唐代兒童所著兜肚畫像,是在湖南長沙出土的童子執蓮紋執壺中,壺上繪有面龐豐滿、活潑可愛的童子腰圍兜肚,童子手持一支蓮花,多條彩帶繞臂部隨風飄揚。唐代兒童所著兜肚形狀多樣,有圓形、半圓形、方形和菱形,肩部分有帶和無帶系連,雖有形態之別,但都只見前身裁片而無后身裁片,穿時后背裸露,僅以細帶系之。與兜肚形制接近的還有裲襠,類似現代的背心、馬甲,前后各有一裁片,兩者的區別在于兜肚為貼身穿著,裲襠貼身穿或穿在貼身衣物外層皆可。法國吉美國立東方美術館館藏的唐蓮花化生童子圖[5],畫面中七童子分別露出生殖器站在蓮花臺上,其中,六童子上身穿裲襠衫,而另一童子則赤裸身體,這就是卵生而非胎生的超自然“蓮花生”。在敦煌壁畫第126窟的方形覆斗藻井中亦出現蓮花童子的形象,兩孩童身穿白色裲襠衫在中心方井舉手并舞,蓮花環繞童子,童子貼身衣物、褲子顏色與蓮花相呼應,共五色。卷草紋、聯珠紋、龜背紋、魚鱗紋等環繞藻井四周,形成清新典雅的藻井。童子與蓮的組合明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并增添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唐代,不同年齡段的孩童穿著略有差異,如4歲以內的幼童活潑好動,著裝較為隨意,有時直接赤裸上身,或只穿下裝,或只穿貼身衣物。當孩童逐漸長大時,穿戴呈現大人服裝的特征,即縮小版的成人服裝,服飾形制有交領袍、圓領袍、短衫和襦裙服等。其中,男童穿圓領袍、交領袍、短衫,女童則多穿襦裙服。受唐代成人女性穿男裝的影響,亦有女童穿男童袍服的現象。袍服的袖身多為窄袖,增強了兒童活動的便捷性,帶有人性關愛的情懷。圓領袍的服飾形制為圓型領子、窄身袖子、衣身長及腰,下著褲裝和衣身及膝蓋處上下,衣側開衩,屬上衣下裳連屬的深衣制。在何家村孔雀紋銀方盒畫像中發現,右側童子穿著交領花紋短袍,袍邊裝飾細帶,下穿簡單褲子;左側童子穿著素色短款上衣,下著短褲,雙手上舉,身后一只小狗(古人稱為猧)。畫面所繪的是兩童子與猧共同玩耍的場景,兒童的衣著較為華麗,應該是出自貴族家庭,可見是對貴族兒童日常生活的一種描述。在長安南里王村韋氏家族墓墓室東壁北側宴飲圖中,右側童子穿著圓領窄袖長袍,左側童子穿著短上衣,下著褲裝,右臂彎曲上舉,意欲撲蝶。另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在《祭小侄女寄文》中道:“侄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襜文褓,堂前階下,日里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6]其中,“襜”指短衣,“繡襜文褓”指穿繡花的短衣襁褓。
在兒童竹馬游戲的圖像資料中,穿著袍服游戲的兒童較為常見,如在莫高窟晚唐第9窟西側出現了身穿赤色為主、花飾袍服的兒童,顯得充滿活力。在敦煌佛爺廟灣36號墓中也出現了一名兒童上身著紅白圓領短袖衣,下身全裸騎竹馬嬉戲,身旁婦人則身著紅袍白裙的圖像,這些均說明唐代兒童穿著袍服廣為盛行。在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38窟的《仕女童子圖》中,仕女懷中的幼童身穿黑綠色花卉點綴的襦裙服,仕女身邊的兩個幼童亦穿著同色襦裙服,一起游玩嬉戲,展現了歡樂氣氛。兒童與仕女一同出現在畫像中的資料較為常見,兩者相處融洽、親密無間,從服飾上看,該形象為當時貴族家庭婦女,其服飾與孩童服飾色彩呼應,孩童身上的花色圖案與貴婦身上的素衣繁簡對比,協調其中,表現了貴婦憐愛子女之情。以上圖像中兒童所著服飾與成人服飾形制相同,男童均為圓領、交領窄袖袍;女童則多穿襦裙裝,亦有穿胡服、男童服飾的現象,如在畫家張萱《搗藥圖》(宋代摹本)中有一名臉型、身形圓胖,上身穿著桔黃大翻領胡服,下身穿著白色長褲的小女孩在練習穿梭,畫面充滿活潑的生活氣息,由此可見,唐代女性著胡服、穿男裝的服飾形制已然在兒童服飾中轉化,也正是受到了唐代包容、開放的社會風尚影響。
褲子的形制在唐代盛行受胡服的影響較為明顯,其中,以背帶褲為特色的服飾形制簡潔、方便,實用功能性顯著,褲腰上裝有挎肩背帶的褲子,背帶可滿足兒童成長中身體的發育需求,褲口緊窄。目前發現唐代畫像中身著背帶褲的童子較多,如在敦煌莫高窟第119窟《七童子采花圖》中繪有7名身穿赤紅、綠色及黑色服飾的孩童,穿著窄身袍服、短衫及不同長度的褲子形制。在丁卯橋童子文三足銀壺中,兩名童子身著寬松背帶褲,背帶短,褲子腰線高,褲身遮住胸腹部,壺底部裝飾一層浮雕狀的蓮瓣紋飾。新疆阿斯塔納唐墓出土中發現身穿背帶波斯間色豎條紋褲子的孩童圖像,小腳褲口式樣,腳穿紅色靴子,左邊童子右手高舉,左手抱猧子,這種間色條紋窄口褲從波斯傳入新疆至中原內地,并在女性和兒童間流行。從以上畫像中的兒童形象來看,唐代兒童不論性別,多穿長褲且褲筒舒適,夏季的褲子是長及膝處的短褲,春秋冬褲則長及腳部。在敦煌壁畫中亦發現了許多赤裸身體和穿短褲的孩童,如晚唐第196窟南壁《阿彌陀經變》中,正是數名上身穿著短袖衫、圓領袍衫和交領窄袖袍衫,下身穿著中褲、長褲的孩童在戲水嬉鬧,或騎欄桿,或伸手拉水中其他童子,或扶欄桿,畫面純真,充滿童趣。再比如,盛唐第148窟《藥師經變》中見3名童子在水中游玩,下方右側童子身著背帶長褲、腳欲踩荷葉,左側童子和上方童子下身均穿著綠色短褲,共同嬉鬧,畫面充滿生機。在敦煌壁畫中,可發現兒童較喜愛戲水。無拘無束是孩童的天性,從中也可看出唐代成人健康、寬容的孩童成長觀,這與當時的經濟發展促進了社會風尚的變化有很大關系。這種變化反映在兒童服飾上,則體現為輕松、簡便、舒適、灑脫。
3 結語
對繪畫、器物及紡織物中的兒童畫像進行研究是一項長遠而有意義的工作,分析古代兒童家庭的關系、宗教的象征意義及兒童生活游戲等,可窺見中國古代不同歷史階段的兒童服飾,亦是一種研究嘗試。本研究對唐代兒童服飾進行綜合研究,力圖發掘唐代兒童圖像中所體現的服飾及裝飾品特征,探究其服飾的基本形態特征,為中國古代兒童服飾文化增添一抹重要的色彩。通過對唐代兒童圖像的梳理,可窺見唐代兒童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的背景,發掘這些圖像中所體現的兒童服飾面貌及唐人的育兒觀。一方面,受成人服飾形制的影響,唐代兒童服飾在造型、面料、圖案、色彩及工藝裝飾上,一定程度地借鑒了成人服飾的特點,尤其是在禮制嚴謹的場合;又因年齡、生理特征、心理特征、生活環境等特殊性以及唐代開放進步的文化,影響了成人對孩童成長觀念包容的態度,其服飾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種人性關懷和呵護。如根據其自身生長特點進行調整,具有兒童服飾特有的功能屬性,唐代兒童服飾有著與成人服飾相同又不同的發展規律和特征。同時,在唐代多民族文化習俗的碰撞、大環境相融合的影響下,各民族兒童服飾的交流與融合反映了一種社會文化和對兒童的關愛以及傳遞美好生活的狀態。此外,漢至唐代認為的兒童是狹義上處于低齡的孩子,男子二十“及冠”和女子十五“及笄”是古人對“兒童”的界定。“兒童”的稱謂,多使用“小兒”或“童子”,為將研究明確化,本研究中兒童的年齡范疇定為0到12歲。畫像中兒童形象的確定可根據畫面的主題場景、人物組合、道具搭配、發型與身體比例等推測。由于“重男輕女”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加上相當多的兒童圖像性別區分不明顯,兒童圖像以男童造型為主,因此,本研究側重于解讀男童服飾。結合唐代兒童的生活背景,如宗教思想、家庭觀念和兒童游戲,并借鑒唐詩中對兒童及服飾的描述,對唐代兒童服飾及特點進行相對全面、系統的考證分析,對唐代兒童的首飾、帽子、圍涎、披帛、襁褓、兜肚、裲襠、圓領袍衫、短衫、襦裙服等進行具體探究,從中領略唐代兒童服飾的多民族雜糅特征,對當代童裝設計及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西方的兒童史研究走過了近50年的歷程,其兒童服飾文化亦有較長的歷史。我國古代兒童服飾文化的研究則少之又少,現有對服飾的研究以成人服飾為主,面向兒童服飾的研究尚待拓展。唐代兒童圖像實物的大量出土,為研究兒童服飾文化帶來了新的機會,同時也對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受畫像清晰度和敦煌壁畫等文物保護的限制,加上兒童題材的繪畫尺寸一般較小,往往居于畫面一隅,不易發現,對唐代兒童服飾具體紋樣的研究存在一定難度,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