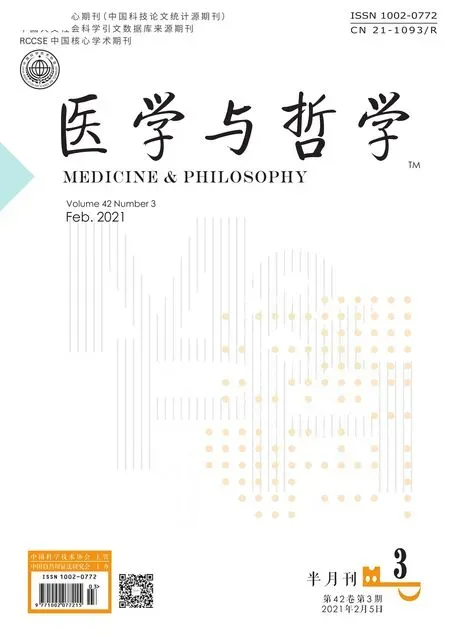從淳于意與華佗醫案比較觀漢代醫事*
于 凌
漢代是中醫理論體系構建成形的關鍵時期,盡管其年代久遠,可資利用的醫案文獻少之又少,史籍中關于名醫醫案的文獻研究價值及中醫學術貢獻值得關注。淳于意與華佗分別是西漢初期與東漢末年的名醫,他們沒有明確留下自己的醫學著作,但他們的臨證思維與實踐經歷已保留在部分史料中。筆者以《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淳于意的診籍[1]和散落在《三國志·魏書·方技傳》的華佗醫案[2]為研究對象,通過對二人在正史中行醫記錄的比較,梳理兩批醫案的特色,在醫案概況、病因認識、病種分科、診斷技術、治法運用、醫學倫理等方面比較兩批醫案的異同,以冀能從中找尋到中醫理論形成初期的某些學術認知規律,并力圖從局部管窺漢代醫學及醫術的發展概貌(《后漢書·方技列傳》的華佗醫案與《三國志》中華佗醫案基本雷同;《中藏經》等相傳為華佗之作的書籍,一則成書年代及其真偽尚存疑惑,二則行文風格與上述正史書籍大相徑庭,因此本文暫不納入討論)。
1 簡況梳理
《史記》載有25例內容翔實的醫案(謂之“診籍”),每案均對患者的姓名、職業、性別、病名、癥狀、脈象脈理、發病原因、診療過程詳細記錄。診籍草創了中醫傳統病案的基本范式,是中醫醫案形成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古典文獻。《史記》中關于醫學理論及術語等方面的記載非常專業,很有可能是參考了當時格式已基本定型的醫療檔案后,進行文學化的加工而形成。因此診籍不僅是一個個可讀性很強的生動醫學故事,更有可能是專業性很強的病歷記錄。相較而言,在《三國志》與《后漢書》中記載華佗行醫生涯中的17例(剔除重復)生動醫案,盡管年代更晚,但和診籍醫案相比則粗陋得多,沒有相對固定的行文格式或醫案要素羅列,內容側重在歌頌或神化華佗的高超醫術,而醫學理論及實踐的具體而專業的內容則相對簡略,整體內容更加藝術化和生活化,學術色彩并不濃厚,也有一些讓人難以信服或中醫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上述差異或許與兩位醫生的生活經歷(淳于意多在廟堂行醫而華佗常游歷于民間)有關,或許與西漢鼎盛時期文檔管理有效及東漢末年兵連禍結造成文獻缺失有關,或許與司馬遷、陳壽及班固等不同作者寫史的風格不同、目的不同有關。
從患者性別及年齡分布看,診籍有18例男性,7例女性。除“齊王中子”有可能是幼兒,其余均集中于成年階段。而華佗醫案中14例為男性,3例為女性。患者年齡除1例是2歲患兒,其余皆為成年。因此,在對患者一般信息的收集上,兩批醫案大同小異,都未對個案中的性別或年齡因素作特殊強調或分析,說明漢代在年齡對疾病的影響方面尚未過多關注。至于現代醫案比較關注的職業因素,兩批醫案多從姓名中帶出職業稱謂,但也很難看出是醫者基于職業對疾病影響的考慮。關于患者的身份或地位,診籍中有3例是明確的奴、侍者類階層,20例明確是政府官員或貴族階級,另有2例身份不明。而華佗醫案則更傾向于對普通百姓的診治,與疾病相關的社會信息缺失較多。
關于預后,25例診籍醫案中,治愈15例,死亡10例,且患者死亡之前,淳于意均對不良后果做出了準確預判。華佗醫案治愈12例,死亡5例(均準確預判)。限于當時的社會條件和醫療水平,這已屬于難能可貴,我們無法以現代的眼光對其苛求太多。
2 兩批醫案的主要內容
2.1 病因認識
淳于意醫案的病因類別,外感病因9例(風、寒、濕、熱等邪氣),各種不良生活習慣7例(如汗出伏地、過勞、臥開口及食而不漱、好持重、飽食而疾走、服石等),房勞因素7例(反映當時社會對房勞與健康關系的重視),嗜酒因素5例(與患者多為貴族階級,有奢侈的生活條件有關),情志因素3例(憂、怒、郁等),外傷1例(墮馬僵石上)。華佗醫案在病因方面的交代多闕如,僅部分醫案涉及外感(府吏兄尋、李延并案)、外傷(督郵徐毅針刺誤傷案)或蟲毒(彭城夫人案)、嗜酒(鹽瀆嚴昕案)、房勞(督郵頓子獻案)、飲食(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案)等因素,其余病案則對病因語焉不詳。可見,漢代醫學已可初見中醫病因理論早期大體分類的端倪。后世較為成熟的中醫病因分類始于宋代陳無擇的三因分類,而上述醫案對于病因的大體分類與之相比,在外感病因方面大體相似,但在內傷病因方面尚有較大分歧,如沒有比較確切地從情志、飲食或勞逸等方面進行梳理,對于生活方式不良的病因也比較分散,但同時卻非常重視房勞和嗜酒因素(并未像后世一樣把房勞歸入勞逸一類,把飲酒歸為飲食內傷一類)。另外對于后世較為重視的病理產物性致病因素(如痰飲、瘀血等)則沒有提及,而是作為了整個病理過程的中間環節。從現在中醫病因病機理論的框架看,病理產物性致病因素不列入病因而是作為病機概念,更加符合臨床實際,也更加能理順理論體系上的邏輯關系。對這個問題重新界定有助于中醫病因病機理論的完善。另外,把誘因當作病因的習慣也在漢代醫案中基本形成。
2.2 病種分科
若依后世中醫分科的標準,診籍醫案除婦產科2例(難產、閉經),外科1例(肺傷),兒科1例(齊王中子病氣鬲案)、寄生蟲1例,齒科1例(齲齒),其他均屬于內科病證,分別是(內)疽、涌疝、熱氣病、風癉、肺消癉、遺積瘕、迥風、風厥、氣疝、熱厥、內關之病等,多數從原文病名無法推斷相當于現代何病,但主癥多集中于發熱類、暈厥類、虛損類、疼痛類及飲食、二便、出汗、四肢運動等方面的異常。說明診籍致病涉獵廣泛,也提示當時社會沒有明確的疾病分科診療意識。
華佗醫案涉及內科11例(除部分頭痛等癥狀外,其余病證表述不明確者居多);外科3例(外傷、蟲獸傷、手術各1例);婦科2例(均為胎死腹中);兒科1例(下利)。華佗醫案的語言沒有太過晦澀的醫學術語,也基本不提病名,只是偶爾簡要敘述主要癥狀,甚至很多醫案連主癥都沒有。
兩批醫案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多數疾苦和當時的醫學發展水平。此外,淳于意長于內科,而華佗擅于外科的傳說憑據也若隱若現。
2.3 診斷技術
診籍中有大量的扁鵲脈法的傳承記載,包括很多更早時期脈學著作的引文,診病當時脈法的運用及淳于意本人對診脈技法及臨床意義的理解。以齊侍御史成案為例,“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于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后五日而臃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臃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從文中可知以下幾點:首先,雖然多數關于脈學、脈法的論述和后世歷代通行的脈學理論及實踐有較大出入,但可以看出在漢代中期,學院派的脈學理論已經較為成熟且自成體系,為何未能傳承下來可能與過于復雜、操作空間較小,不利于流傳等因素有關;其次,淳于意的脈學技能并非憑空出現,也是得益于更早的脈學文獻在當時社會的流行,更早的脈學文獻我們已經無法見到,因此診籍就成為了珍貴的二次文獻;第三,漢代的脈學理論我們現在無法完全破解其醫學含義或操作規范,但從文中可知當時的脈學理論中已經有了脈的形、勢、度等方面的具體規定,脈象變化已經與體內的臟腑、經絡、形體、氣血等狀態建立了密切聯系,與各種病理改變、病證分類等內容有了大致的對應關系;第四,脈診方面在當時已經是判斷病因、分析病機、標定病位、推測病勢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們尚無法通過診籍中這些碎片化的脈法內容構筑一個完整而實用的脈學理論,但診籍中的脈學文獻的價值可略見一斑。
除脈診外,淳于意的色診方法也很有特點,如在齊丞相舍人奴案中,提到“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臟,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在齊王黃姬兄黃長卿案中提到“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干,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在齊中郎破石案中提到“色又乘之”[1]的色診脈診互參法。
反觀華佗醫案,如李將軍妻病案,甘陵相夫人有妊案等都敘述了華佗診脈技能幾乎出神入化,但由于具體方法及醫學解釋上沒有記載,使得華佗醫案中的脈法蒙上了傳說的色彩而失去了醫學價值上的研究意義。
2.4 治法運用
診籍中的內治法涉及到了火齊湯(6例醫案均有涉及,綜合分析可知火齊湯或為當時運用較為廣泛的治療下焦實熱病變的類方)、下氣湯(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案中用于清熱瀉火)、柔湯(齊王黃姬兄黃長卿案中用于治療腎痹,即腎系外感濕邪所致的腰脅痛不可俯仰)、藥酒(濟北王病案中治療寒濕內侵所致的風厥胸滿、菑川王美人案中治療難產)等湯劑及芫花(臨菑氾里女子薄吾案中治療寄生蟲)等藥物。外治法主要涉及刺法(濟北王阿母案、菑川王兩案中均用于泄熱)、灸法(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案中用于治療寒客膀胱、齊中大夫病齲齒中使用)、苦參漱口(齊中大夫病齲齒)、寒水拊頭(菑川王案)等。
華佗醫案中,內治法有湯劑有丸散,治法提到過汗法、下法,具體方藥提及四物女苑丸(東陽陳叔山小男案中治療虛寒),蒜(治療某病咽塞)等,其中四物女苑丸可視為四物湯的前身,對后世方劑學產生重要影響[3];外治法有針刺(曹操苦頭風眩案、李將軍妻病難產案),手術(某腹疾案),溫湯漬手(彭城夫人蠆螫其手案)。另有1例情志療法(某郡守篤病久案),通過激怒病人達到治療目的的另類療法。
兩批醫案的治法各有千秋,淳于意的醫案中常有兩到三種治法綜合運用,如內外治并用,針藥融合等,而華佗醫案的治法較為簡略且單一。從病證與治法的對應性來看,淳于意的醫案中的治法更加貼合后世通行的主流醫學理論與實踐方法,如清熱法、活血法、溫中法、散寒法等,盡管具體方藥不得而知,但治療理念與后世臨床一脈相承。反觀華佗醫案中的治法,不可解釋或沒有解釋的地方更多,如用活血法治療虛寒證。另辟蹊徑的治法也更多,如情志療法,手術或外治法等。這些或許是淳于意代表了當時學院派的做法,而華佗更像是民間醫生做派的又一例證。
此外,治法的細節(如何選藥,如何取穴,如何手術等)我們無法得知,但兩批醫案中表露出來的治則治法理念非常值得后世傳承與發揚。
2.5 醫學倫理
醫學倫理的問題古今中外皆有,從不會因為年代古遠便顯得淺薄。越缺少技術支撐的年代,對人心、人情的關懷越發顯得重要。漢代的醫學倫理內容雖然遠未達到后世的理論高度,但醫案中處處流露出臨床中醫患雙方不得不面對的倫理問題和漢代醫生的處理方式。
關于知情同意:淳于意在診斷齊國侍御史成的頭痛時感到了疾病的兇險,便“即出,獨告成弟昌”,可見自古以來中國的醫者就早早在隱瞞與知情的倫理爭論上選擇了前者,或許對患者本人的某種權益不能做到盡善盡美的尊重,但是對患者的疾病進展或生命質量都力爭最大限度的維護,說明在古代名醫心里,當生命與法理相悖時,醫者多選擇更加重視生命的價值。基于這種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醫學倫理特點,我們無法照搬西方的醫學倫理范式,也無法做到重視病人知情權大于重視生命本身。
關于臨床決策:華佗醫案中曾記載:“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無論是多么高明的醫生,治不治和如何治的選擇權始終是掌握在患者手里的。同出于漢代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中確立患者為本的治病理念,率先提出了“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的英明論斷,不但具有歷史意義,而且至今仍然有其現實價值[4]。這種理念在華佗本案中得以充分體現。
關于臨終關懷:診籍在齊章武里曹山跗病案中提出 “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此種決定體現了淳于意樸素的臨終關懷思想。我國的傳統文化非常忌諱談論死亡,但診籍中已有如此明確的處理方式,似乎與普遍的民眾習俗或文化特征不符。這恰恰是診籍這個傳統醫案范式之作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所在。承認死亡,才能在治療無效的前提下實施臨終關懷。承認醫治對某些瀕死患者來說是無效的客觀現實, 通過對他們提供舒適的照料來替代衛生資源的無謂消耗, 它實質上體現了對患者及大多數人真正的人道主義精神[5]。
3 討論
3.1 兩批醫案的異同
異中之同:“診籍”出現于西漢,華佗醫案散見與東漢末年。前者更周詳,也更貼近于真實的醫療狀況,后者多少帶有了一些傳說或傳奇的意味。兩批醫案在對醫生的評價,醫生的職責,病證譜系的呈現,診斷技術及治法種類的記述等內容大體一致。兩批醫案在成書年代、行文風格等方面存在差異,但總體上勾勒了西漢到三國時期醫學發展的風貌。
同中之異:兩批醫案展現了官方與民間兩個不同類型醫學的雙重形式。前者對于醫學內容本身及醫學相關內容的記述反映了官方規范(有相對固定的格式、要素、立論依據、操作說明、結果呈現等內容),呈現出醫學學術工作或政府檔案管理的雙重需求;而后者則凸顯了民間醫學的一種隨意性(形式不拘一格,內容略于實證而感情色彩濃厚),折射出民眾對名醫垂問人間疾苦,不計功名利祿的美好形象的渴望。
3.2 兩批醫案的醫學啟示
合而觀之,我們可從兩批醫案感知漢代醫學理論與臨床實踐的成熟度。首先,在醫療技術水平低下的年代,對疾病預后的判斷是醫生的重要工作內容,也是評價醫生水平的重要指征,無論是官方抑或民間,對于技術高超的名醫一律懷有尊崇敬畏之心與渴求之意。其次,對于病因的認識和后世病因理論相比,更加簡化而欠于邏輯內涵,但同時也沒有后世那種病因病機相混淆而導致的無謂復雜化的傾向。再次,雖然兩批醫案所處的年代對疾病本質的認識比較粗淺,但對癥狀本身、癥狀與病因的對應關系,癥狀的產生發展機理等方面的醫學解釋已經作了大量嘗試,并且部分病證的解釋和分類對今天的中醫學術內涵乃至臨床應對也具有啟示。最后,漢代的診斷和治療手段與后世中醫臨床的種種診療技術大相徑庭,在后世中醫的發展過程中,規范與簡化(便于操作與評價)是發展主線,由此也犧牲了很多有效但另類的診療技術,兩批醫案在診斷與治療方法上的特殊內容是今天中醫理論與臨床技術提升的重要內容。
3.3 兩批醫案的人文價值
在史書中記載的醫案不同于醫案專著里的醫案。后者非常注重醫學本身的客觀性,而史書中的醫案,由于作者的知識背景與創作目的都有特殊性,因此選案未必完備或客觀,而且記錄過程也非常容易忽視醫學的問題而專注于社會、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問題。因此兩批醫案較后世醫案專著而言,具備了更多更廣泛的人文價值和社會現實意義,對上述文中提到的知情同意或臨終關懷等人文理念,似與西方醫學倫理學的某些觀點異曲同工,但同時又蘊含了中國傳統醫案中“以人為本”的文化特征,值得當今社會重新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