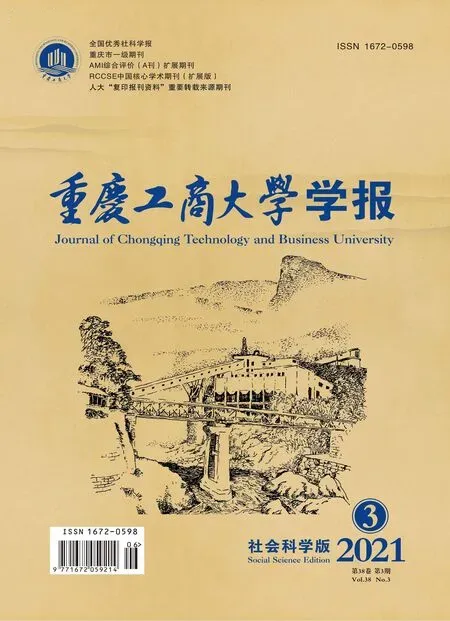勞動解放的中國起點:“五四”勞工話語的建構與轉換*
王金玉
(南京林業(yè)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京 210037)
1918 年11月16日,當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前為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中國15萬勞工而歡呼,喊出“勞工神圣”的口號時,他并沒有意識到這一口號將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歷史效應,但是,有一點是明顯的,那就是,從此以后,“勞工神圣”的口號迅速傳播開來,不僅使勞工話語進入公共話語空間,而且成為“五四運動”(1)關于“五四運動”,有廣義和狹義的概念,本文取廣義的概念,主要指1915年《新青年》創(chuàng)刊至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期的主導性話語,其內(nèi)涵也越來越具體化,其結果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隨著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轉向馬克思主義,原先“勞工神圣”的抽象性話語就被勞動階級的解放話語所取代,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中國開天辟地的新紀元也從此開始。
一、“五四”時期勞工話語的建構
勞工話語迅速占據(jù)公共話語的顯要位置,成為“五四”知識分子關注的重要話題,絕非偶然。
勞工話語成為公共話語的核心話語有著深厚的時代和現(xiàn)實基礎。從時代特征看,由資產(chǎn)階級開啟的世界性的民主潮流,隨著資本主義世界自身矛盾的激化而進一步向前發(fā)展,其特征是不斷高漲的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深入。十月革命的勝利一方面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由理論向實踐的飛躍,從而決定性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發(fā)展方向,同樣深刻地影響著苦苦思索中華民族命運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促使他們關注生活在中國最底層的工農(nóng)大眾。從鴉片戰(zhàn)爭到1919年,中國的產(chǎn)業(yè)工人已達到二百萬人左右。他們?nèi)藬?shù)雖不算多,但他們受壓迫深重,經(jīng)濟地位十分低下,更談不上什么政治權利。由于生存狀態(tài)的惡劣,自發(fā)的工人罷工運動不斷暴發(fā),1914—1919年,“中國工人的自發(fā)斗爭更加高漲,在五年多的時間內(nèi),罷工即達一百多次”。與此同時,農(nóng)村失地農(nóng)民也不斷增加,階級矛盾也在不斷激化。[1]66-67所有這些,構成了勞工話語的時代背景和現(xiàn)實基礎。
“五四運動”本身的特點對于勞工話語形塑的意義。新文化運動的一大特征是平民性。新文化運動倡導文學革命,其最大的功績是文字革命,由文言文改白話文,而白話文彰顯的首先是平民性。陳獨秀1917年2月1日在《新青年》二卷六號上發(fā)表的《文學革命論》一文,凸顯了其平民(階級)的性質(zhì)。在文中,陳獨秀主張推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在他看來,這三種文學“蓋與吾阿諛夸張?zhí)搨斡亻熤畤裥裕橐蚬=裼镄抡危瑒莶坏貌桓镄卤P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使吾人不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2]20正如有學者指出,“新文化運動發(fā)動的語言文學革命,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國語運動,而呈現(xiàn)為文化之階級革命。”從這個角度,新文化運動具有現(xiàn)代“知識人與社會精英之代際競爭之色彩”,換言之,新文化運動的話語體現(xiàn)了新的平民階級的訴求,現(xiàn)代新興知識分子是這些階級的代表。新文化運動的初衷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即認為,民主共和的失敗是由于民眾還沒有覺醒,要改造“國民性”,首先要讓民眾有知識有文化,“這就需要語言之易認易學,文學之淺俗易懂”[3]62-63。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通過辦報刊、組織各種社團等重要活動來倡導其理念。新文化運動中出現(xiàn)的各種社團,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強調(diào)工學結合,倡導勞動習慣,打破勞動階級與智識階級的劃分。而所有這些活動對于知識分子與勞動階級的結合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無政府主義思潮對于勞動話語建構的意義。“五四運動”中傳播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特別是影響很大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對于促進知識分子的勞工意識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流行著各種思潮或話語,主要有自由主義,文化本位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在不同的話語體系中,對于勞工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比如,在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話語中,勞工問題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與政治無關。如蔡元培1920年9月在為英國人克卡樸著、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作序時,如此介紹克卡樸所闡述的英國工團主義的概念:第一,工人階級只能通過“自助和自己組織團體”而自救,與政治無關;第二,工人階級只能通過“工界所組織之工業(yè)性質(zhì)的團體”而不是政治組織而戰(zhàn)勝資本家;第三,工人首先是一個作工的人,如礦工、工程師等,然后才是一個“國民”。工團主義的產(chǎn)生是“許多不著名的人之種種意見相合成的,他的發(fā)生是出乎自然的。 ”在他看來,中國的勞工問題,當務之急就是“工人教育問題”。像英國、美國等國一樣,知識分子參與進去,組織工人學習各種科學知識,組織各種演講、文藝活動等,傳播社會主義協(xié)作觀念。[2]441這時的蔡元培受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五四運動”中,無政府主義是影響很大的思潮。“五四運動”期間,吳稚暉、李石曾等無政府主義者1918年初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個以“勞動”命名的《勞動》月刊雜志。雖然該雜志創(chuàng)辦時間不長,總共發(fā)行了五期,1919年7月停刊,但其影響不能低估。《勞動》雜志大力宣傳“勞動主義”,也宣傳十月革命勝利的積極意義。同時,這份雜志“還第一次向中國人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意義。對工讀主義、勤工儉學以及世界各國的工人運動也有廣泛的宣傳和介紹。”[4]581盡管這些宣傳帶有較為濃厚的無政府主義性質(zhì),但是,在當時特定的背景下,對于激發(fā)人們對勞動、勞工問題的關注,對于勞動話語的形塑與轉向,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從勞工神圣到工農(nóng)革命:勞工話語的問題域轉換
自從蔡元培提出“勞工神圣”的口號后,勞工問題成為“五四”知識分子關注的核心。1920年之前,關于勞工的話題主要圍繞工資、勞動條件、工人教育等具體問題展開。1919年2月,李大釗在《晨報》上發(fā)表《勞動教育問題》一文,一方面強調(diào)勞工運動作為新文明要素的意義,另一方面強調(diào)不僅要重視勞工的物質(zhì)方面,更要重視勞工的知識教育。他認為,工人們除了“物的欲望(而外),尚有靈的要求。”他認為,如今的勞工階級“已竟?jié)u漸覺醒”。他們不僅要求經(jīng)濟上和政治上的權利,還要求有更多受教育、學習知識的權利。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洲的勞工受教育的條件有了改善,“歐洲工人生活改善而后,必有新文明萌發(fā)于其中。像我們這教育不昌、知識貧弱的國民,勞工補助教育機關,尤是必要之必要。”[5]161-163同一時期,李大釗在《晨報》上發(fā)表《青年與農(nóng)村》一文,希望青年知識分子到農(nóng)村去,幫助農(nóng)民階級提高思想覺悟,在中國,農(nóng)民是勞工階級中最大多數(shù)的成員,“要想把現(xiàn)代的新文明,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 ,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 。”他認為,俄國十月革命是勞動階級的革命。對于中國來說,農(nóng)民就是“大多數(shù)的勞工階級”。“他們?nèi)羰遣唤夥牛褪俏覀儑袢w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5]179-180他號召青年到農(nóng)村去,“一面勞作,一面和勞作的伴侶在笑語間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識階級加入了勞動團體,那勞工團體就有了光明”,廣大的農(nóng)村是“民主主義的沃土”。[5]182-183另一方面,李大釗又非常關注中國不斷壯大的工人階級隊伍,關注工人階級的聯(lián)合和團結問題。1919年3月9日,他在《每周評論》第十二號上發(fā)表《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一文中寫道,唐山煤廠八九千人,“竟沒有一個工人組織的團體”,沒有實現(xiàn)有組織的聯(lián)合,任由資本家階級的剝削和壓迫。[5]1921919年3月,李大釗在《晨報》上發(fā)表《現(xiàn)代青年活動的方向》一文,系統(tǒng)闡釋了他的勞動倫理觀。他認為,勞動應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 最好莫過于尊重勞動。”勞動不僅創(chuàng)造了財富,也創(chuàng)造了快樂,“ 一切樂境, 都可由勞動得來, 一切苦境, 都可由勞動解脫。”勞動是最好消遣,“免苦的好法子, 就是勞動。這叫作尊勞主義。”然而,現(xiàn)代社會不僅不尊重勞動,而且剝削他人的勞動,勞動者因此成為“最苦痛最悲慘的人”。他希望青年人尊重勞動,到勞動階級中去,關心他們的疾苦。[5]196-198
陳獨秀在《告北京勞動界》(1919年12月1日《晨報》)一文中,將“勞動界”定位為“絕對沒有財產(chǎn)全靠勞力吃飯的人而言”,如那些“沒有財產(chǎn)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鐵工、車夫……”等,這些人“合成一個無產(chǎn)的勞動階級”。這似乎是按照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概念來定義的。陳獨秀認為,西方的工人運動正熱火朝天,而中國勞動界的主要任務是提高工人階級覺悟,“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處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這境遇的覺悟。”[6]50-51
然而,隨著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fā),中國知識分子對十月革命、中國現(xiàn)實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不斷深化,再加上他們對“五四運動”中的各種試驗及其失敗的深切體悟,特別是“工讀互助團”從成立到失敗的短暫體驗,從1919年底到1920年初,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發(fā)生了實質(zhì)性的變化,體現(xiàn)在勞動話語上,則是由“勞工神圣”的一般性話語向階級專政的革命話語轉變。到了1920年代,勞動話語的內(nèi)涵不僅更加具體化,而且發(fā)生了實質(zhì)性的變化。
在蔡元培“勞工神圣”的概念中,“勞工”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正如他所說的, “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yè),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動。所以農(nóng)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fā)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圣!”[2]426蔡元培“勞工神圣”話語的喊出當然不是偶然的。其直接誘因似乎是表達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華工英勇精神的敬意,對勞工價值的禮贊。然而,本質(zhì)上是對一種新的時代潮流和時代精神的頌揚。這種時代精神已經(jīng)從十月革命的勝利中迸發(fā)出來,只不過,中國知識分子對其的認識還需要一個過程。而這一過程也正是“勞工神圣”話語從初期的模糊性、抽象性到1920年初成為清晰的勞工階級的革命話語的過程,與此相應的是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在艱難的選擇中轉向馬克思主義。
1920年下半年起,一批向工人階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相繼出現(xiàn)。如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出版的刊物有“新時代”;《勞動界》(廣州、上海、北京等地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伙友》(上海工商友誼會的刊物);《勞動周刊》《工人周刊》《山東勞動周刊》《武漢勞動周報》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及其分部的機關刊物。1920年8月15日,李漢俊在《勞動界》第1冊《為什么要印這個報?——〈勞動界〉發(fā)刊詞》中指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經(jīng)是最苦的,而我們中國的工人比外國的工人還要苦。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為外國工人略微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中國工人不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 我們印這個報,就是要教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了,或者將來要苦得比現(xiàn)在好一點。”[2]6921920年11月28日,李達在《勞動界》第16冊發(fā)表《勞動者與社會主義》一文,回答了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他說,社會主義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廣義的社會問題就是全部的社會制度,而狹義的社會問題就是由產(chǎn)業(yè)制度生發(fā)出來的勞動問題。而“勞動問題就是資本制度發(fā)達的結果產(chǎn)生出來的東西”,而現(xiàn)時代最大的勞動問題就是勞動者爭取自由平等的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就是“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就是勞動問題,而“勞動問題就是勞動者自身死活的問題,勞動者自己非有覺悟不可”[2]703-704。
1920前后,李大釗、惲代英、蔡和森、陳獨秀等一批知識分子與無政府主義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紛紛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勞動話語也從此有了更具體、更激進的內(nèi)容。與此同時,“五四運動”的內(nèi)涵也大大擴大。1920年4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七卷五號上發(fā)表《什么是新文化運動》,對“新文化運動”作了與初期相比非常擴大的理解,由文化擴展到社會、政治甚至戰(zhàn)爭等許多方面。“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zhàn)爭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運動底朋友不是敵人。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chǎn)業(yè)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xiàn)實政治底羈絆。”[6]128陳獨秀明確地將新文化運動與勞工階級覺悟的提高聯(lián)系了起來,推動了知識分子與勞工階級的聯(lián)合。至此,我們看到,與初期“不談政治”的文學革命相比,此時的新文化運動正在朝著一個新的方向發(fā)展,即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結合,向著一個開天辟地的新時代發(fā)展的趨勢。
三、勞動話語的轉換與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主體自覺
從“勞工神圣”概念的提出,勞工話語進入公共話語,到這一話語轉變?yōu)楣まr(nóng)階級解放話語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理智自覺的認識過程。這種自覺體現(xiàn)在對十月革命的認識的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認識的深化等方面,這里,主要以李大釗為例。
“五四運動”中的先進知識分子對十月革命偉大意義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最初,中國輿論界對十月革命的反映是“一塌糊涂之亂狀”。[1]135最早以獨到的眼光看到俄國十月革命劃時代意義的是李大釗。1918年7月1日,李大釗在《言治》季刊(第三冊)發(fā)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在文中,李大釗寫道,“不知法蘭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紀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國家主義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會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時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質(zhì)自異,故迥非可同日而語者。”[5]56不久,李大釗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fā)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論文。在前一篇文章中,李大釗贊揚十月革命是庶民的勝利,是勞動階級對資產(chǎn)階級的勝利,是新紀元的開始,“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zhàn)勝。”[5]101在后一篇文章中,李大釗進一步認為,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廿世紀新潮流的勝利。”[1]105他深刻地揭示了俄國十月革命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它開創(chuàng)了勞工階級革命的新時代。由此,在1919年新年伊始,李大釗熱情歡呼新紀元的到來,“這個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這樣一個新紀元的到來,“勞工階級要聯(lián)合他們?nèi)澜绲耐饕粋€合理的生產(chǎn)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5]128-129與此同時,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也逐漸深化。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發(fā)表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表明他在理論上已經(jīng)成為一個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文中,李大釗將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稱為“以勞動為本位”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這種經(jīng)濟學“把社會主義的經(jīng)濟組織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與從來的個人主義經(jīng)濟學截然分立, 而獨樹一幟, 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才成一個獨立的系統(tǒng), 故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的鼻祖不能不推馬克思。”他認為,馬克思的經(jīng)濟理論、歷史理論、社會主義理論是不可分割的三個部分,其中,“階級斗爭說恰如一條金線, 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lián)絡起來。”[5]232他認為,《共產(chǎn)黨宣言》號召勞動階級聯(lián)合起來,“大家才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xiàn), 離開人民本身, 是萬萬做不到的, 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5]248在這里,我們看到,李大釗在思想方法論上持一種相互聯(lián)系的整體主義思想方法。這種方法在他與胡適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中也凸顯出來。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同時也是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劃清界限的過程,如關于“問題與主義”之爭,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斗爭等。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發(fā)生在1919年7—9月,以胡適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評論》上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為起點,其實質(zhì)是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論戰(zhàn)。胡適以杜威的實驗主義或實用主義(pragmatism)為基礎,強調(diào)從具體問題入手介入社會,“主義”只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工具。“我并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2]295李大釗則認為,問題與主義不可分離,這是因為,社會問題是社會大多數(shù)人的問題,要靠大家想辦法解決,而只有“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地成為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5]304。藍公武則從理想與現(xiàn)實的沖突、問題的不同性質(zhì)、看問題的主觀差異等角度,回應了問題與主義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有的問題只需要具體的方法就可以解決,然而,“若是一種廣泛的含有無數(shù)理想的分子的——即為尚未試驗實行的方法——問題,并且一般人民,對于他全無反省,尚不能成為問題時候,恐怕具體的方法,也不過等于空談,決沒有什么效果可言的么!”而且,問題本身是否重要,與人的主觀認知有關,“故所以吾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根據(jù),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便成了問題,才能采納吾們的方法”[2]529-530。
通過爭論,進一步促進了先進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覺,促進了他們與勞動階級的緊密聯(lián)系。正如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周策縱分析的,盡管胡適等自由主義者提出了“多研究些問題”的建議,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必須正視的最嚴重問題是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而自由主義者并沒有提出任何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而在此之后,自由主義者大多躲入書齋,而不少提倡“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則“開始走進工人和農(nóng)民群體,以研究他們的生活狀況”。1919年秋,毛澤東在長沙組織“問題研究會”,從事政治、經(jīng)濟、教育、勞工等問題,并將主義與問題結合起來,如“如何聯(lián)合民眾、社會主義能否實行”,等等。[7]231-232在實際的社會實踐中,毛澤東深切體會到了工農(nóng)聯(lián)合進行社會革命的必要性。正如1920年1月他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fā)言》中所說的,關于解決社會問題的主張有改造(即革命)和改良兩種方法,他主張“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所進行的“勞農(nóng)主義”。[8]2
前文已經(jīng)指出,早些時候,無政府主義在促進知識分子與勞工階級的結合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無政府主義由于反對一切權威而必然具有空想性質(zhì),當勞工話語已經(jīng)由一般性的話語轉向勞工階級的革命話語時,無政府主義的危害性也就顯現(xiàn)出來。因此,“五四運動”后期,批判無政府主義,揭示其空想性質(zhì)就變得十分重要。1920年,施存統(tǒng)在《我們底大敵,究竟是誰呢?》一文中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權力和權威,在他們看來,俄國革命后還存在著專制,但是,我們要問,“他底專制,還是紳士階級底專制呢?還是勞動階級底專制呢?”我們還要問,“在這全世界未起革命底時候,能夠實行全截革命么?倘使俄國把政府廢除,他現(xiàn)在還能夠存在么?而且革命究竟有沒有半截全截的分別呢?”[2]693施存統(tǒng)正確區(qū)分了革命的階段性與最終目的之間的關系,揭示了無政府主義的空想性質(zhì)。陳獨秀在《答區(qū)聲白的信》中,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系統(tǒng)的分析和批判,指出,“我們應覺悟,我們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會制度,否則什么個人的道德、新村運動,都必然是無效果的;因此我們應該覺悟,非個人逃出社會以外,決沒有絕對的自由,決不能實現(xiàn)無政府主義”[6]293-294。
陳獨秀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八卷一號上發(fā)表的《談政治》一文清楚地表達了他關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思想,批判無政府主義對一切權力和權威的否定。他認為,不能籠統(tǒng)地反對強權,而是要看強權(國家、政治等)用來做什么。勞動階級要獲得解放,“只有被壓迫的生產(chǎn)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chǎn)階級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將財產(chǎn)私有、工銀勞動等制度廢去,將過去不平等的經(jīng)濟狀況除去。”[6]158不如此,民主“必然永遠是資產(chǎn)階級專有物,也就是資產(chǎn)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6]163
這一時期,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勞動階級的看法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看到了勞動階級自身所蘊涵著的巨大的能動性潛力。朱執(zhí)信在《野心家和勞動階級 》(1920年3月《建設》二卷二號)一文中,批駁關于野心家煽動工農(nóng)革命的觀點,尖銳指出,有人說,除非有野心家煽動,否則中國的階級斗爭不會是什么大問題,但是,勞動階級如果“沒有能力 ,就無從煽動。有了能力,不要等煽動,也會爆發(fā)。說不成吃緊問題,卻拿沒有野心家煽動做條件,未免太輕視了勞動運動了”[2]525-526。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革命家之一,朱執(zhí)信十分清楚地認識了民眾自身所蘊含的革命力量。1920年5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上發(fā)表《勞動者底覺悟》一文,他認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因為,人類從吃的到穿的都是“做工的人”生產(chǎn)和創(chuàng)造的,他們是社會的基礎,是“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社會的改變最重要的是勞動者的覺悟。[6]135-136強調(diào)對勞動者的教育,啟發(fā)其覺悟。1920年9月,陳獨秀發(fā)表《談政治》一文(《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揭露了資產(chǎn)階級將民主作為其護身符,“若不經(jīng)過階級戰(zhàn)爭,若不經(jīng)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chǎn)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chǎn)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因此,必須“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chǎn)階級)的國家”。[6]163-1641921年6月7日,陳獨秀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份理論刊物《共產(chǎn)黨》月刊(非公開發(fā)行)第五號上發(fā)表《告勞動》一文,他認為,勞動者的問題不是枝節(jié)所能解決的,首先要提高勞動者的“階級的覺悟”,強調(diào)要“把各地方各行業(yè)的勞動組織成一個階級”,形成反抗資產(chǎn)階級的反抗力量。強調(diào)要采取革命的手段,“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 只有各地方各行業(yè)的勞動都有了階級覺悟, 大家聯(lián)合起來, 用革命的手段去組織勞動階級的國家、 政府、 國會、 省議會、 縣議會去解決勞動自身的困苦”[6]284-285。
“五四”先進知識分子還充分意識到了建立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1920年8月,蔡和森在給寫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問題致毛澤東同志的兩封信》中堅定地強調(diào)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重要性。他認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有四種利器:建立政黨,黨是運動的“發(fā)動者,領袖者,先鋒者,作戰(zhàn)部,為無產(chǎn)階級運動的神經(jīng)中樞。”[2]772“有人以為中國無階級,我不承認。只因小工小農(nóng)不識不知,以窮乏慘苦歸之命,一旦階級覺悟發(fā)生,其氣焰不減于西歐東歐。”[2]726
總之,“五四”勞工話語的建構與轉換是多種因素形塑的結果,而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中國革命的新紀元真正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