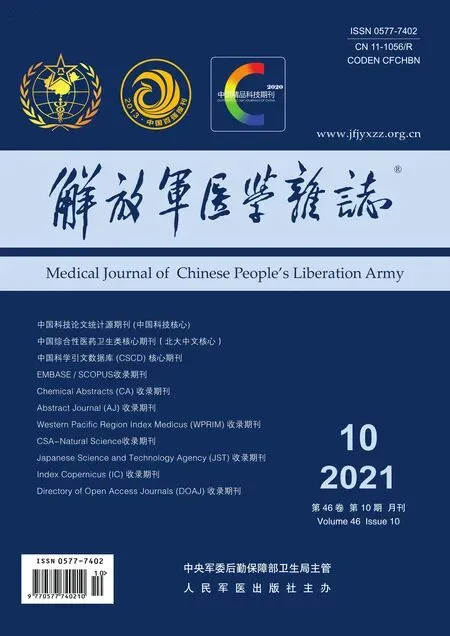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甲狀腺炎的臨床特點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楊子仲,張國慶,秦博宇,張靜,孫瓊,李彬琦,焦順昌*
1南開大學醫學院,天津 300071;2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腫瘤內科,北京 100853;3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內分泌科,北京 100853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是一類新型抗腫瘤藥物,主要通過阻斷程序性死亡受體1(PD-1)/程序性死亡配體1(PD-L1)等信號通路來增強人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既往研究證實,免疫治療較傳統療法緩解率更高,生存獲益更大[1]。目前,ICI已廣泛應用于肺癌、泌尿上皮癌及消化道腫瘤等的治療。一般認為,免疫治療具有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國外有研究報道,嚴重的免疫相關不良反應(irAE)發生率僅為0.5%~13.0%[2]。然而,由于ICI影響自身免疫的特點,其造成的不良反應形式多樣,可累及多種組織器官。目前,關于irAE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肺[3]、心臟[4]、腦[5]等主要臟器,對于ICI所致的免疫相關甲狀腺炎(immune-related thyroiditis,irT)關注甚少。免疫治療的甲狀腺損傷主要包括免疫相關性甲亢和免疫相關性甲減。在既往的藥物臨床試驗報道中,irT的發生率較其他irAE略高,其臨床表現與對應的原發性甲狀腺疾病類似[6]。而藥物性甲狀腺損害嚴重影響患者,尤其是長期生存患者的生活質量。嚴重甲狀腺毒性會造成免疫治療推遲和中止,使患者再次暴露在腫瘤進展的風險之中。同時CheckMate141的亞組分析也顯示亞洲人群免疫相關內分泌不良反應的發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7],但國內目前尚未見多藥物、多癌種中irT發生特點的回顧性研究。本研究對在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接受免疫治療的惡性腫瘤患者irT的發生情況和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對免疫治療不良反應的預防和管理提供經驗。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于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腫瘤內科住院接受ICI治療的惡性腫瘤患者312例進行回顧性分析。本研究經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倫理委員會批準(S2018-092-01),所有患者在開始接受ICI治療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免疫相關甲亢和甲減的診斷標準參考2020年版美國國家綜合癌癥網絡(NCCN)的免疫相關毒性管理指南[8]。甲狀腺功能正常型甲狀腺炎的診斷參考2019年版英國國家衛生與臨床優化研究所(NICE)甲狀腺疾病的評估和管理指南[9]:甲狀腺彌漫腫大伴甲狀腺球蛋白抗體(TGAb)、甲狀腺過氧化物酶抗體(TPOAb)升高,而血清游離三碘甲腺原氨酸(FT3)、游離四碘甲腺原氨酸(FT4)、促甲狀腺素(TSH)水平正常,并排除可能造成甲狀腺腫大及疼痛的其他疾病。納入標準為:(1)患有經病理學確診的惡性實體腫瘤;(2)接受過至少2個周期規范的ICI治療;(3)具有可分析的臨床病歷資料。排除標準:(1)合并甲狀腺疾病、接受過甲狀腺手術或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2)ICI治療開始前存在FT3、FT4、TSH水平異常;(3)可證實為毒性甲狀腺腫所致的甲狀腺功能異常;(4)所患惡性腫瘤為甲狀腺癌或甲狀腺轉移癌;(5)同時接受免疫細胞治療;(6)接受過甲狀腺區放療。最終排除26例,共納入286例。
1.2 方法
1.2.1 資料收集 通過電子病歷系統收集所有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ICI治療開始時的年齡、性別、身高、體重、腫瘤來源,既往接受的抗腫瘤治療史,所用的ICI類型等。所有患者均通過每2個周期(相當于5~6周)ICI治療后評估甲狀腺功能(包括血清FT3、FT4、TSH水平),對于懷疑甲狀腺損傷者進行甲狀腺超聲及甲狀腺自身抗體(TGAb、TPOAb)檢測。T3、T4、TSH、TPOAb、TGAb均通過電化學發光法(羅氏Cobase 601化學發光儀)檢測;甲狀腺彩色超聲檢查由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介入超聲科進行。
1.2.2 irT的分類 根據甲狀腺功能將甲狀腺損傷分為以下5類[10]。(1)臨床甲亢型:FT3或FT4水平升高、TSH正常或低于正常;(2)亞臨床甲亢型:FT3、FT4正常,但TSH水平低于正常,且無典型癥狀;(3)臨床甲減型:FT3或FT4水平減低,TSH水平正常或高于正常;(4)亞臨床甲減型:FT3、FT4正常,但TSH高于正常,且無典型癥狀;(5)甲狀腺激素正常的甲狀腺炎:FT3、FT4正常,但存在甲狀腺腫大等臨床表現及甲狀腺自身抗體陽性,可伴有超聲下甲狀腺形態異常,符合甲狀腺炎的表現。
1.2.3 irT的嚴重程度 irT的嚴重程度分級參考美國癌癥中心不良事件報告術語(CTCAE5.0)進行,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分為5級[11]。1級:僅為臨床或診斷所見,無需治療;2級:具有輕度的臨床癥狀,需要局部或非侵入性治療,日常活動輕度受限;3級:嚴重或者具重要醫學意義但不會立即危及生命,導致住院或者延長住院時間或致殘;自理性日常生活活動受限;4級:危及生命,需要緊急治療;5級:AE相關的死亡。如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出現多次irT,則按照嚴重程度等級最高的一次進行分析。
1.2.4 患者分組 根據患者是否發生irT將患者分為irT組(n=83)與非irT組(n=203)。再將irT組患者根據甲狀腺功能異常情況分為甲亢組(n=28)、甲減組(n=48)及甲狀腺功能正常的甲狀腺炎組(n=7)三個亞組;根據irT的嚴重程度分為輕癥組(CTCAE分級1–2級,n=76)與重癥組(CTCAE分級3級及以上,n=7)兩個亞組。
1.2.5 指標分析 比較irT組與非irT組患者的基線臨床資料(包括年齡等一般情況、腫瘤的來源及治療史、基線甲狀腺激素水平)的差異,再對irT組患者甲狀腺損傷的分型、嚴重程度分級、甲狀腺激素水平、合并癥等臨床特征進行統計描述;對比分析不同嚴重程度、不同臨床分型irT亞組患者的發生時間,所用的ICI藥物種類,甲狀腺自身抗體(TPOAb、TGAb)水平的特點和差異,并分析irT患者的轉歸情況。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2.0和R 4.02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表示,irT組與非irT組基線甲狀腺激素水平的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甲狀腺自身抗體等非正態計量資料以M(Q1,Q3)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概率法校正;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不同亞組中irT發生的時間差異;甲狀腺自身抗體TGAb與TPOAb的相關性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P<0.05(雙側)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一般資料比較 在所有納入的患者中,男性(n=214)多于女性(n=72),接受ICI治療的患者平均年齡為57.9(20~85)歲。納入患者的原發腫瘤種類較多,主要包括非小細胞肺癌(n=110)、食管鱗癌(n=39)及胃癌(n=22),但也納入了部分纖維肉瘤、血管肉瘤等少見惡性腫瘤患者,多數患者在接受ICI治療前曾接受過手術、化療、放療或分子靶向等治療。在應用的ICI藥物類型方面,入組患者主要接受PD-1免疫治療,其中應用最多的四種藥物為帕博利珠單抗(n=75)、信迪利單抗(n=65)、特瑞普利單抗(n=59)、納武利尤單抗(n=51),也有少數患者參加臨床試驗而接受PD-L1或聯合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蛋白4(CTLA-4)抗體進行免疫治療。
286例患者中,83例治療后出現了irT,發生率為29.0%。對兩組患者進行對比發現,不同性別患者irT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67),irT組患者年齡低于非irT組(P=0.033)。在腫瘤的來源方面,兩組中不同癌種irT的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14)。在既往治療史方面,接受過放療的患者irT發生率明顯高于非放療患者(P=0.023),而既往接受過化療、手術及靶向治療對于irT的發生無明顯影響。總體上,不同ICI藥物irT的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28)。在基線甲狀腺激素水平上,兩組患者治療前FT3、FT4、TSH水平均在正常范圍內,用藥前兩組FT3及FT4水平相近,irT組基線TSH水平稍高于非irT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68)(表1)。

表1 免疫相關甲狀腺炎(irT)組與非irT組免疫治療患者的一般資料、ICI藥物類型及基線甲狀腺激素水平比較Tab.1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data, type of ICI drugs and baseline level of thyroid hormone between the patients in irT and non-irT group

(續 表)
2.2 irT的臨床特征 甲狀腺不良反應主要表現為甲狀腺功能的亢進和減退,其中表現為甲亢者11例,亞臨床甲亢者17例,甲減者29例,亞臨床甲減者19例,另有7例患者出現一過性甲狀腺疼痛不適及自身抗體陽性,但T3、T4、TSH水平持續正常,考慮為甲狀腺激素正常的甲狀腺炎。76例(91.6%)患者為1或2級的輕度不良反應,乏力、甲狀腺疼痛是常見的臨床表現,僅6例發生嚴重影響生活的3級不良反應,1例患者出現意識障礙、水腫及合并其他嚴重不良反應,考慮為甲減危象(4級)。發生臨床型甲亢的患者,病程中最高FT3和FT4平均值分別為8.871 pmol/L、28.43 pmol/L;而甲減患者的甲狀腺激素變化則較為明顯,病程中最低FT3、FT4平均值為2.748 pmol/L、9.471 pmol/L。32例(38.6%)irT患者在發生甲狀腺不良反應的同時合并其他免疫損傷,包括免疫相關的間質性肺炎、自身免疫性肝損傷、心肌炎以及免疫性腸炎等。多數irT患者不需臨床干預,11例甲亢患者中6例接受了低碘飲食治療,2例需加用抗甲狀腺藥物治療。29例甲減患者中,有12例接受了甲狀腺素替代治療,發生甲減危象的1例患者接受了糖皮質激素治療(表2)。

表2 免疫相關甲狀腺炎(irT)的臨床特征Tab.2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mmune related thyroiditis
2.3 irT患者發生甲狀腺功能異常的時間特點 患者從第一次接受ICI藥物治療到出現甲狀腺功能異常的中位時間為92(36,170) d,但存在較大個體差異,最長者可達591 d,最短者僅3 d。其中甲減型irT發生的中位時間為120 d(95%CI 56.9~183.1),甲亢型irT為52 d(95%CI 41.9~60.1),甲亢型irT發生的中位時間明顯早于甲減型(P=0.015,圖1A)。CTCAE分級1級、2級與3級及以上irT發生的中位時間分別為76 d(95%CI 33.2~118.8)、100 d(95%CI 82.4~117.6)、92 d(95%CI 0~197.2),不同嚴重程度患者的中位發生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93,圖1B)。值得注意的是,最初診斷為甲亢的28例患者中,有7例(25%)隨病程發展為甲狀腺素水平降低,并最終出現甲減(圖1C),其病程類似伴有一過性甲亢的橋本甲狀腺炎。這些患者甲亢期TSH達到最低值的中位時間為53(27,55) d,甲減期TSH達到最高值的中位時間為179(125,216) d,從甲亢期到甲減期的轉化過程持續125(100,161) d,7例患者中有5例患者在甲減期接受了甲狀腺素替代治療。

圖1 免疫相關甲狀腺炎發生的時間特點Fig.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currence time of immune related thyroiditis
2.4 不同ICI所致irT的發生情況比較 為了對比應用不同種類ICI藥物的患者間irT發生情況的差異,本研究選取了四種應用較多的ICI進行對比,結果見表3。四種藥物的irT發生率和總體發生率相接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79),其中發生率最低的是納武利尤單抗(21.6%),最高的是特瑞普利單抗(35.6%)。在需要臨床干預的2–4級不良反應方面,特瑞普利單抗的發生率略高于其他藥物(20.3%vs. 11.9%,P=0.134)。不同藥物的中位irT時間差距也較大,最短的為信迪利單抗(55.5 d),最長的為帕博利珠單抗(154 d)。

表3 不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所致免疫相關甲狀腺炎(irT)的發生情況比較Tab.3 Comparison of the immune related thyroiditis induc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2.5 irT患者的TGAb和TPOAb抗體水平及甲狀腺超聲表現 在發生了irT的83例患者中,78例檢測了血TPOAb及TGAb水平,其中26例(33.3%)存在甲狀腺抗體水平異常,包括TGAb異常23例(29.5%),T P O A b 異 常1 4 例(1 2.8%),同 時 異 常 者1 1 例(14.1%)。TGAb與TPOAb水平呈正相關(r=0.464,P<0.001)。從分型上看,發生甲亢和甲減的患者,其TGAb[16.8(15.0,32.0) U/mlvs. 15.5(15.1,47.4) U/ml,P=0.495]和TPOAb[30.4(28.1,51.6) U/mlvs. 33.6(28.0,54.9) U/ml,P=0.592]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甲狀腺抗體與不良反應嚴重程度的關系上,發生3–4級irT者TGAb[251.7(100.6,310.2) U/mlvs. 15.2(14.0,27.8) U/ml,P<0.001]和TPOAb[350.1(53.1,500.0) U/mlvs. 30.7(<26.0,46.3) U/ml,P<0.001]水平較發生1–2級irT者明顯升高。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7例發生嚴重甲狀腺損傷者的TGAb水平均異常升高。83例irT患者甲狀腺B超中僅有5例出現明顯異常,irT的超聲表現類似橋本甲狀腺炎(圖2),主要包括累及雙側的甲狀腺密度不均、彌漫性低回聲伴有較豐富的血流信號(n=5)及甲狀腺體積增大(n=2)。

圖2 免疫相關甲狀腺炎(irT)的超聲影像Fig.2 The ultrasound imaging of immune related thyroiditis (irT)
2.6 irT患者的轉歸情況 甲狀腺不良反應的轉歸情況見表4。總體上irT患者的預后良好,7例甲亢、10例甲減患者癥狀完全恢復,7例甲亢和11例甲減患者甲狀腺激素恢復正常水平,但TSH自身抗體異常多持續存在;因irT影響免疫治療者少見,僅1例甲亢和2例甲減患者因irT而中斷過ICI用藥;治療后好轉的10例患者中,有3例在隨后的ICI治療中再次出現甲減癥狀,但復發的嚴重等級均不高于首次發生的等級。

表4 免疫相關甲狀腺炎(irT)患者的轉歸情況(例)Tab.4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immune related thyroiditis (n)
3 討 論
i rT 是免疫治療中一類獨特的現象,早在CheckMate 037研究[12]中就報道了納武利尤單抗引起的內分泌不良反應。而ICI發明之前,腫瘤患者發生藥物相關甲狀腺炎則相對罕見,主要由干擾素、白細胞介素-2(IL-2)及酪氨酸激酶抑制藥引起[13]。國內進行的ORIENT-1[14]、POLARIS-02[15]等臨床試驗中也有甲狀腺損傷的報道,然而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比較不同藥物irT的發生率,很少報道irT發生的影響因素及臨床特點。而對免疫治療患者的甲狀腺不良反應發生情況進行回顧性分析,有助于理解免疫相關甲狀腺毒性的機制,提高免疫治療的安全性。
魏芬芬等[16]對38例患者的回顧性分析結果提示,免疫治療患者irT的發生率為42.37%,較本研究(29.0%)高。盡管結果存在差異,但均明顯高于藥物臨床試驗Meta分析所報道的irT發生率(4.8%~23.9%)[13],提示真實世界中患者irT發生率可能被低估。本研究發現多種腫瘤的免疫治療中均可發生irT,包括縱隔纖維肉瘤等罕見惡性腫瘤,此類疾病可用方案有限且對治療常不敏感,如因irT停藥將對患者造成更嚴重的影響,故在罕見腫瘤治療中更應注意預防irT等不良反應的發生。本研究結果顯示年齡是irT的危險因素,而Mizuno等[17]和Fukihara等[18]對免疫相關肝炎、肺炎的研究均提示發生irAE的患者較非irAE患者年齡更小,這可能與低齡者對ICI藥物更加敏感有關,年輕患者在獲得更好療效的同時也可能面臨更高的irAE風險。
盡管本研究納入的患者未接受過可能直接損傷甲狀腺的頸部放療,但其中接受過其他部位放療的患者irT的發生率仍高于未接受過放療者,提示非甲狀腺區放療也可能增加甲狀腺免疫不良反應的發生風險,放療對irT的影響可能與射線引發的炎癥提高細胞因子水平、增強抗原呈遞有關,其具體機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irT起病時多為輕癥甲狀腺功能異常且缺乏典型癥狀,故患者極少因irT主動就診,而對irT進行預防性低碘飲食、免疫調節并及時開始甲狀腺替代治療可減輕癥狀、保護甲狀腺功能,故irT的早期發現尤為重要。目前,我國免疫治療常以日間治療等短期住院的方式進行,系統復查較為困難。因而筆者建議接受ICI治療者均應監測T3、T4、TSH水平,對疑似irT的患者可增加TGAb、TPOAb及甲狀腺超聲檢查以輔助早期診斷和干預,尤其對于甲減型的irT,未經干預時可能出現嚴重的甲狀腺激素水平減低并引發甲減危象,具有潛在的致命性,更值得臨床關注。對于影響生活的嚴重甲狀腺毒癥及甲減,NCCN指南推薦暫停ICI治療直至癥狀緩解[7],本研究中7例重癥患者在接受治療后irT均得到了控制,僅3例暫時中止了免疫治療。因此,irT多不影響免疫治療計劃,但病情嚴重者需及時應用藥物控制癥狀。
部分irT的臨床經過類似于橋本甲狀腺炎,表現為甲狀腺免疫破壞所致的一過性甲狀腺毒癥和繼發性甲減[19]。然而,原發性橋本甲狀腺炎一過性甲亢的發生率很低(約5%)[20],而本研究中irT發生一過性甲亢的比例則較高,首診為甲亢或亞臨床甲亢的28例患者中7例(25%)后期出現了繼發性甲減。在甲狀腺功能變化的時間特點上,本研究中irT患者甲亢期較橋本甲狀腺炎稍短,TSH達到最低值的中位時間僅53 d,而轉化過程則相對較慢,可達125 d,與國外的相關研究結果一致[21],提示對初診為甲亢的irT應長期監測其甲狀腺功能變化;對于irT抗甲狀腺藥物的應用需謹慎,病情穩定后應及時停藥,避免造成嚴重的繼發性甲減。
本研究對比了四種臨床常用的PD-1抗體,發現irT的發生率差異并不明顯,提示這四種PD-1 ICI在甲狀腺毒性方面的安全性相近。但隨著免疫治療藥物的不斷豐富,PD-L1、CTLA-4、Tim-3抗體等新的ICI的應用也給irT的管理帶來了挑戰。既往研究認為,免疫檢查點CTLA-4在橋本甲狀腺炎的發生中起關鍵作用[22],國外研究也提示聯合應用CTLA-4和PD-1制劑較PD-1單藥的irT發生風險更高[23],但是目前國內CTLA-4類ICI獲批較晚,針對CTLA-4抑制劑所致irT的報道也較少。本研究由于樣本量的限制,并未觀察到PD-1/PD-L1單藥與聯合CTLA-4藥物治療irT的發生率存在統計學差異,因此,CTLA-4抗體引發irT的特點是否與PD-1抗體有所區別,仍有待進一步大樣本研究。
TGAb和TPOAb廣泛應用于免疫性甲狀腺損傷的診斷中。Inaba等[23]曾證實,需要持續治療的irT相對于一過性irT其TGAb水平更高。Kimbara等[24]則發現,治療前甲狀腺抗體基礎水平升高是納武利尤單抗引發irT的危險因素。本研究發現重癥irT的自身抗體水平明顯高于輕癥irT,提示抗體水平高者可能存在更大的風險,更值得臨床關注。在TGAb和TPOAb的比較中,既往研究認為TPOAb在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炎的診斷中具有更好的效能。而在本研究中,盡管兩者的表達水平明顯相關,但irT患者TGAb的陽性率更高。3–4級的irT全部伴有TGAb升高,而TPO的陽性率僅為71.4%,提示與其他甲狀腺疾病相比,ICI所致的甲狀腺毒性中TGAb可能起著更重要的作用[25]。然而,本研究目前只檢測了發生irT患者的抗體水平,其診斷價值仍有待進一步驗證。甲狀腺超聲檢查在irT中陽性率較低且缺乏特異性,但對于甲狀腺功能正常或處于甲狀腺功能轉化期而存在癥狀的患者,超聲檢測可能起到提示作用,未來的研究可以著眼于結合CT、甲狀腺核素掃描等放射檢查方法以早期發現irT的影像學特征。
綜上所述,本研究通過分析ICI治療后患者發生甲狀腺不良反應的特點,發現年齡小、放療史可能增加irT的發生風險;甲亢型irT患者存在向甲減轉化的可能,其演變較非ICI藥物性甲狀腺炎更快;重癥irT患者的TGAb和TPOAb水平明顯高于輕癥患者,且TGAb的異常更加明顯。在臨床工作中,盡管多數甲狀腺毒性并不影響ICI治療的進行,但對甲狀腺功能進行定期監測和及時干預,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預防嚴重不良反應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