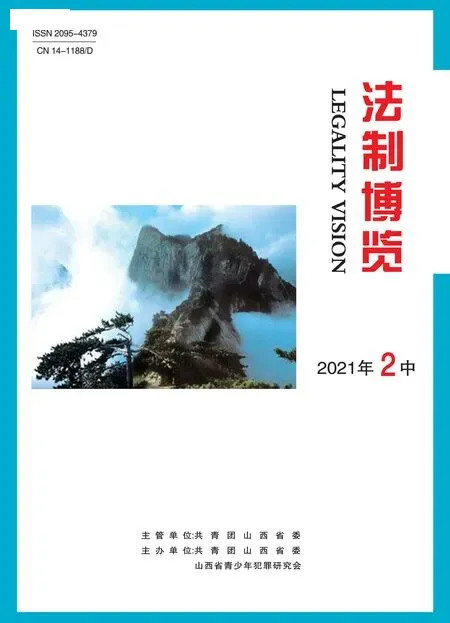法官的調查取證權研究
鮑玥萌
(海城市人民法院,遼寧 海城 114200)
法官在哪種情況下具備調查取證權,會對于案件真相的了解產生直接的影響,也會對于實體正義產生一定的影響。以實際運作來說,則時常形成了對于某方當事者的幫助,所以又和法官之中的程序正義產生了明顯的沖突性。另外,證據主要是由當事者加以收集,或是法官進行收集,通常被判斷為職權主義和當事者主義二者之間實施區分的關鍵標志。以調查取證權本身來說,不管是在實務之中,抑或是在理論之中,都難以合理處置程序主義以及實體主義二者之間的平衡問題,因而容易陷入至這方面的困境之中。因此說,值得對于民事訴訟中的法官調查取證權進行進一步的論證。
一、兩難處境之中的調查取證權
(一)調查取證權的實體正義之維
在我國2002年所頒布的《證據規定》之中,限制了法院的調查取證,而在實務之中則體現出了此種限制損傷到了實體公正,如認為在限制調查取證權之后,會產生諸多的消極問題,當事者在訴訟中會更易說謊話。不服事實認定已然成為當事者不服從判決的重要因素之一,還有法官認為由于當前當事者的法律意識較為淡薄,在取證方面也較為困難,這樣則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法官的調查取證權,不利于保護當事者的權益[1]。該種對于限制調查取證權的判斷以及批判,也獲得了我國學術界的廣泛響應。李浩則認為,此種限縮所產生的后果會使得法官對發現事實真相方面產生消極影響。而肖建華認為,在證據規定之中徹底否決了法官職權調查,導致法官失去了發現案件事實的條件,致使產生審判權缺位的情況。上方評論內容是針對《證據規定》的,但在最新的《民事訴訟法解釋》之中,對于調查取證權的界定,對比于《證據規定》之中的內容,還不存在本質方面的變化,在立場方面更是具備一致性,所以上方批評內容就算用在當下也較為適用。
(二)調查取證權的程序正義之維
調查取證權不單單在實體正義維度方面受到批評,在程序正義維度方面也是一樣。張衛平認為,在最新的《民事訴訟法解釋》之中,對于法官調查取證權予以了限制,在民事訴訟體制層面雖說獲得了一定的進步,然還不是十分完善,因此其強調只需留下對程序事項的調查取證權,針對可能損傷到我國的利益等方面,就無需具備這一權利,這主要是由于法官的調查取證會虛化當事者的處分權以及辯論權,導致裁判失去中立性[2]。再者,法官還難以保障自身所調取的相應證據是絕對具備真實性的,所以也難以確保案件具備真實性。會損傷到我國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情況通常需由刑事訴訟來加以解決,所以不處在民事訴訟的范圍,在上方批判原因之中,關鍵點在于中立問題。
在實務之中,法官調查取證權的主要運作形式,能夠劃分為事實調查及證據收集模式,以及庭外證據收集模式。以庭外證據收集模式來說,則是法官了解某一證據處在特定性的證據源范圍之內,進而就會對于向個人,或是單位的取證產生影響。而事實調查及證據收集模式,則是指法官通常并不根據某一確定的證據實施收集,在案件事實未能了解的情況之下,先去案件現場開展走訪調查工作,在此期間試圖發現真相,并認真的收集相關的線索。本質目的在于探明事實真相,但不管是上述哪個模式,均很難滿足于程序正義之中的相關標準及要求。
二、德日語境之下的調查取證權
(一)辯證主義之下的調查取證權
在德國法之中不存在和中國法絕對一致的法官調查取證定義,意思較為接近的術語則為法官證據提出以及證據調查,而這為法官所具備的重要職權。德國法之中的證據調查和中國的調查取證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其是指法官根據之前對于相應的證據方法實施判斷及審核的一種行為,以表層的意思來分析,即為提取證據,而以深層次內涵來說,則主要指的是法官對于證據方法的感知,并在此期間提取證據的一種行為。在德國法之中,證據主要包括證據方法,證據資料以及證據原因[3]。以證據方法來說,其主要指的是實際的人或物,通過其的幫助而加以證明,更為精準的來分析,則為傳遞或是觀點的重要載體,主要涵蓋鑒定人,勘驗物以及證人等。證據資料主要指的是證據調查的最終結果,對于證據方式實施調查而獲知的信息。證據原因則主要指的是證據資料以及辯論期間被認作為事實的內容。概括來說,證據方法與證據提出之間相對應,而證據資料與法官判斷方面相對應,證據原因則和法官心證方面相對應。
(二)修正辯證主義之下的調查取證權
為提高訴訟效率,盡快發現案件真相,在當前的德國民事訴訟中,雖說在整體方面上堅持辯證主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也具備著許多修正內容,這主要是指運用修正辯證主義,表現在內容與修正辯證主義之原則,法院能夠在不經過當事人申請的情況之下,為職權證據進行調查。一方面在當事人未能夠提出有效的證據方法時,那么則能夠將此證據方法引至訴訟之中,如職權勘驗。另一方面對此種證據方法命令以及證據調查和辯證主義的證據調查實施對比,發現和修正辯論主義的職權證據調查所存在的不同則通常表現在第一層次上,這主要是指法院能夠根據職權提出證據方法,不需要當事者加以舉證,但通常來說,法官須先以釋明權的運用,對于當事者提出建議,讓其能夠提出證據申請,唯有在懷疑可能會違反實際義務的情況之下,才會應用職權證據調查[4]。
(三)否定主義之下的調查取證權
對于一些程序事項來說,在德國法之中法官能夠依據職權加以審查,進而則能夠形成辯證主義的一種例外體現。上述事項通常牽扯到合法性要件方面的內容,許多觀點均認為法官能夠為了自由證明,可不進行嚴格證明,這主要指的是不受到證據調查程序以及法定證據方法方面的約束,而這主要是由于自由證明傾向證明的迅速性、簡潔性,防范產生訴訟拖延的情況。自由證明的主要方法,為立法人員假定的是對于證人的調查補充或利用電子郵件以及電話等形式來開展補充調查工作,而調查的主體則為鑒定人[5]。除卻在事實提出方面上充分按照辯證主義理論加以踐行,在其他方面上的處理則和辯證主義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所以則能夠被作為辯證主義的局部否定。
在德國法中,法院有權基于構成裁判基礎的證據以及事實實施收集這一原則,此原則和辯證主義原則之間處在對立狀態,其核心內容在于法院應依據職權來衡量當事者未能夠主張的一些事實內容。再者,當事者無爭議的某些事實,法院能夠不當作裁判資料,法院能夠以職權調查證據,通俗來講就是法院能夠為證據調查以及職權事實調查。
總而言之,以民事訴訟中的法官調查取證權來分析,嘗試將法官在證據以及事實方面上的權力回歸至司法權之本質層面上,此種論證途徑強調于程序的理性化以及細致化,滿足于現階段程序主義以及實體主義的迫切要求,同時也利于應對法院當前所面臨的困境,并且在理論層面上,這種論證也嘗試確定我國法官調查取證權,在對比法的參照定位之下來體現的缺陷以及特殊性,強調于解除一些對于職權主義以及辯證主義的錯誤性認知,以及偏差性想象,從而為民事審判的革新提供重要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