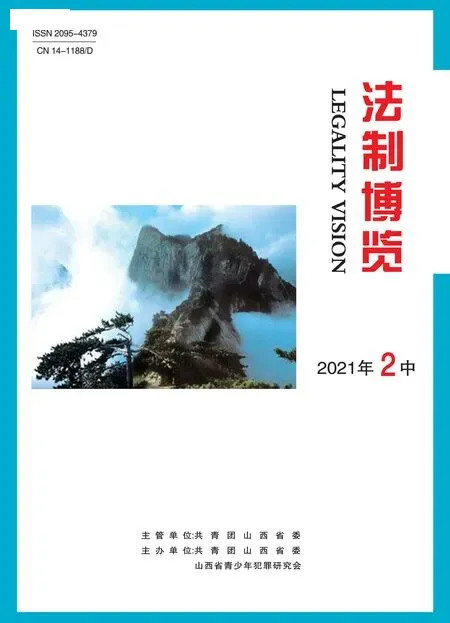信用制度體系獨立化的法理學探究
梁文青
(寧夏大學,寧夏 銀川 750001)
一、信用與信用權的理論溯源
(一)信用的起源
首先是道德上的信用起源。人無信而不立,信用在道德上最先體現出來,人類的在發展的過程中離不開分工合作,在共同的勞動以及相互協助的過程中產生了相互之間的信任,道德上的信用由此而生。同時,信用又體現為一種美德,表現為一個人可被他人信賴以及普遍的責任承諾[1]。其次是經濟上的信用起源,交易是支撐市場存在的基礎,而交易的成功與失敗必然造成交易雙方的利益或者損失,為了減少這種損失,交易主體在交易前必然會計算對方的信用,信用越高則風險越小,信用越小則風險越大。具體在經濟上的信用包括,授信人對受信人的信任、信貸償付在時間上的滯后性以及受信人的清償能力。信任作為信用的核心因素,在交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王立明教授也曾表示信用是主體在社會中與其經濟能力相適應的經濟評價[2]。最后還有法律上的信用起源,信用在羅馬法中被創造出來用于民事主體制度,喪失信用的主體意味著其被剝奪了某種資格,這也意味著,信用與主體權利的得失密切相關,喪失信用就要承擔其帶來的法律負擔。在古代的德國,信用出現在交易的誓約中,交易主體常常要求對方以“誠實”作誓,在到后來為了得到更加可靠的保證,在誓約中加入了“信用”一詞,以確保誓約的履行的確保[3]。
(二)信用權的概念及性質
首先從信用權的產生與發展來看,信用最早在羅馬法中就有出現,但是卻沒有確定的概念,它的保護常常依附于名譽權,但是羅馬法通過對失信者的懲戒來保護信用權方式,也體現了羅馬法對于名譽權益的確認。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加重視信用的利用保護,信用慢慢脫離名譽權,成為一項獨立的權利,最早規定信用權的法律是《智利民法典》,但是真正地使得信用權走向世界的是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它在其中明確地規定“捏造或者傳播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言論使他人的信用受損,或者影響到他人的職業發展以及其他不利影響,即使不知道其為虛假,但應當知道的,也應該負賠償責任”。從此,大陸法系的國家也紛紛效仿,設立信用權,即使未明確的規定在民法中,也通過其他立法規定了對信用權的保護。其次是我國信用權的概念。我國的理論界對于信用權的定義依舊眾說紛紜,信用要獨立成為一項權利,首先需要明確“權利”的概念。雖然在法學元理論、元概念中對于“權利”概念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權利”在法學中的核心地位[4]。因此,信用要想成為一項權利,必然需要符合權利概念。
二、信用權獨立化的法律性質
(一)信用權的權利屬性
人格權說中此前有較大的爭議,民法典的頒布,將信用權益的內容規定在人格權編的體系下,賦予了信用人格權性質,成為與人身關系不可分的權利,其伴隨著這人身關系的變化而產生,當信用受到侵害時,主體有權利排除妨害,其作為一項權益,規定在名譽權與榮譽權的章節中,是為了避免信用權邏輯視角的轉化帶來的問題,未來信用所涉及的權利形態還存在極大的爭議,民法典巧妙地避開爭議的同時,填補了信用在自然人領域的立法空白,這是符合當前信用權發展要求的解決方法。在無形財產說中信用權作為一項權利,具有可支配性,最重要的是其具有財產性,可以為主體帶來財產利益。吳漢東教授就曾表示:信用不是一種人格利益,而因歸為無形財產的范疇。在我國民商合一的體系下,信用權的財產性質體現得更加明顯,商事主體的信用水平由多維度的因素組成,不僅需要通過信用權保護自己的信用水平,還用來換取現實的經濟利益,例如企業融資、企業經營這些企業在經營中所打造出的商譽。
(二)信用獨立成權的要素分析
信用權的主體。一項權利在法律上存在其本身必須具有普遍意義,因此信用要成為一項獨立權利,就要具備主體上的特質。從民法典的規定中,可以明確的是信用規范所適用的主體與名譽權以及榮譽權相一致,但是,就一般主體還是自然人,還需要分析論證。首先是個別信用,道德規范角度的“信用”源于自然人個體之間的誠信。人無信而不立,“誠信”最早所適用的對象是私主體之間,隨著商業文明的誕生,個人更加重視自身的信譽,并且私主體之間的交往需要與個體的信用相掛鉤,此時個別信用發展成為普遍信用,凡是主體皆需要信用。其次是商事信用,對于商事主體來說,交易成本至關重要,其最重要的判斷因素就是信用,良好的信用意味著較低的風險,關系到一個商事交易的成敗,商事主體在社會中的不斷實踐積累獲得信譽,與自身相結合形成了商主體復雜的商譽,證實了商事信用主體的普遍性。權利客體是什么?權利的客體是“權利的附著物和界定對象”。商事信用逐漸成了社會主體之間交易依賴的重要形式,銀行選擇將資金放貸給信用評級較高的私人以及商事主體,通過對未來信用的期待獲得利益,通過總結發現信用評價與信用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聯系,在商事主體中,企業往往通過更加專業的第三方,對象則是票據、債券、股權等,投資方基于對融資方的信用評價,從而達成交易,這對于當今世界資本市場來說十分重要。雖然信用的對象難以概括地表達,但是對于信用評價作為媒介將信用的客體可以概括為利益。
三、信用制度體系建立中的影響
(一)“信用”規范之調適利益的分析
通過上文的分析,信用利益不僅僅是人格利益,還有經濟利益,民法典將“信用”中所包含的人格與財產相剝離,人格利益被納入名譽予以保護。本文認為可以考慮運用《民法典》第998條的規彌補信用制度體系。該條文將人格權利益的具體損害責任分為兩類,一類是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另一類是除此以外的其他人格權,同時對第二類人格權的責任承擔方式提供解決路徑。有學者認為考慮行為人的職業、社會身份、社會影響范圍等,是為了更加具體保護人格權中的經濟利益,否則,如果只為了確認精神利益,則不需要如此區分。當民事主體在受到錯誤的信用評價時,不僅僅可以要求評價機構恢復信用,給予精神撫慰,還可以要求評價機構作出相應的經濟損害賠償,這也為專業機構在進行行為評價時更加專業提供激勵。由此可見,將《民法典》的此款規定與信用制度規范相結合,為信用利益的保護提供了法律基礎,使得信用主體在受到侵害時能夠得到完整的損害賠償。
(二)“信用”規范之社會評價的分析
信用之前被經濟學領域所運用,雖然逐漸被法學界法學納入其中,但在實踐領域依舊沒有脫離“信貸”中的債權和債務關系,《民法典》頒布之后,信用所包含的主體明顯不止于此,信用評價在實踐中所表現的社會評價,該如何確定?當前涉信社會評價有兩種表現形式,第一封閉式的社會評價,這類社會評價機構具有權威性和專業性,但是主體受到嚴格的限制,這類社會評價具有固定的標準和格式,所得信用評價具有封閉性。第二開放式的社會評價,涉信社會評價的主體往往是專業機構以外的社會主體,這類社會評價往往評價標準不一、評價主體較多、評價內容復雜,因此如何對此類社會評價進行適用顯得尤為重要。本文認為通過《民法典》中的“誠信”原則能夠對涉信“社會評價”提供價值導向。以具體案件為例,某省將拒服兵役中的個人作為失信人,納入了失信人懲戒名單,給予了不良的信用記錄,并通過媒體對其行為進行了曝光,案件的當事人認為此行為侵犯了其信用,請求信用修復。在此事件中對受罰主體的行為進行判斷,首先他明顯違反了《憲法》第55條關于服兵役是每個公民義務的規定,其次他拒絕履行憲法義務的行為是最大“失信”行為,但是利用《民法典》信用的規定,顯然不足以認定責任,對于違反憲法的行為,對其責任的承擔難以形成解釋,對此類型就應該以《民法典》第一條與《憲法》相結合,同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誠信”原則為共同的指引,實現對本案例中行為責任的合法合理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