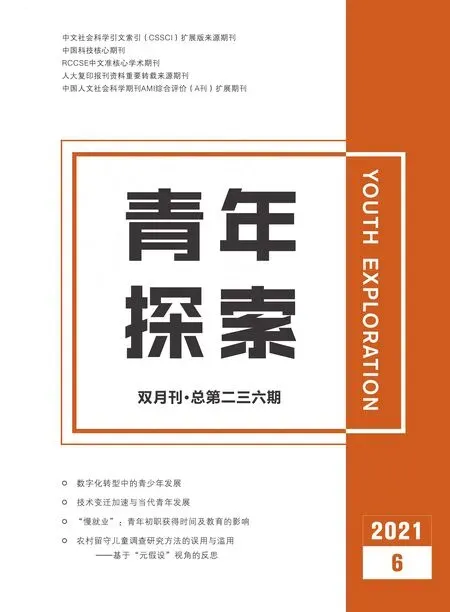農(nóng)村留守兒童調(diào)查研究方法的誤用與濫用
——基于“元假設(shè)”視角的反思
■羅國(guó)芬 馬春冉
一、問(wèn)題的提出
潘綏銘等學(xué)者認(rèn)為,“元假設(shè)”在社會(huì)調(diào)查研究中往往是“未明言、甚至未能意識(shí)到的”,但它又是一切社會(huì)調(diào)查問(wèn)卷設(shè)計(jì)的基礎(chǔ)與靈魂。比如,調(diào)查某個(gè)現(xiàn)象(包括定義該現(xiàn)象、確定其時(shí)空范圍)、提出某個(gè)定義、甚至問(wèn)卷中的每個(gè)提問(wèn)、每一個(gè)字都是“元假設(shè)”。可以說(shuō),“元假設(shè)”是隱藏在調(diào)查研究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的,尤其是在設(shè)計(jì)問(wèn)卷時(shí)非常突出。沒(méi)有“元假設(shè)”這一工具,研究者就無(wú)法設(shè)計(jì)問(wèn)卷;沒(méi)有“元假設(shè)”這種理論認(rèn)識(shí),研究者就無(wú)法解釋好自己的調(diào)查結(jié)果[1]。
從20世紀(jì)90年代后期迄今,學(xué)術(shù)界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群體有過(guò)大量的調(diào)查研究。譚深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研究的文獻(xiàn)進(jìn)行概括,歸納為“問(wèn)題視角”和“比較視角”[2],分別指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問(wèn)題”表現(xiàn)的總體探討和該群體與對(duì)照組“非留守兒童”的比較分析。不過(guò),不管是從“問(wèn)題視角”還是“比較視角”研究農(nóng)村留守兒童,其研究范式都屬于實(shí)證主義范式,其采用的方法基本都是調(diào)查研究法。
在以往關(guān)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問(wèn)題的大量社會(huì)調(diào)查成果中,研究者往往有一些未明言、甚至未能意識(shí)到的“元假設(shè)”在指導(dǎo)自己的研究。比如,從定義來(lái)講,相關(guān)研究中往往下意識(shí)地認(rèn)為,“父母雙方或一方流動(dòng)到其他地區(qū)”之后,農(nóng)村留守兒童會(huì)被留在“戶(hù)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在一起[3],2013年以前,教育部“全國(guó)中小學(xué)學(xué)籍信息管理系統(tǒng)”對(duì)中小學(xué)生是否為留守兒童的統(tǒng)計(jì),將學(xué)齡段“父母外出務(wù)工三個(gè)月以上,由其他親屬監(jiān)護(hù)并留在戶(hù)籍所在地家鄉(xiāng)接受義務(wù)教育的子女”分為三類(lèi):非留守兒童、單親留守兒童、雙親留守兒童。在這一定義中,“家鄉(xiāng)”究竟是指某個(gè)自然村、行政村,還是所在鄉(xiāng)鎮(zhèn)、所在縣?子女留守在“家鄉(xiāng)”或“戶(hù)籍所在地”農(nóng)村具體所指何為,并不太清晰。而從“元假設(shè)”角度思考的話(huà),民工潮興起以后,農(nóng)民工通婚圈在地域上已超出本地鄉(xiāng)村情況下,托養(yǎng)在外公外婆家的“留守兒童”可能就被排除在“留守兒童”的范疇之外了(其戶(hù)籍地與實(shí)際生活地不在一個(gè)地方)。類(lèi)似的“元假設(shè)”還有很多,這些“元假設(shè)”可能不一定符合農(nóng)村留守兒童群體的實(shí)際情況。而基于那些不正確的“元假設(shè)”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規(guī)范”的調(diào)查研究,可能得出片面的、甚至錯(cuò)誤的研究結(jié)論。因此,在以往農(nóng)村留守兒童研究綜述文章之外,本文對(duì)大量農(nóng)村留守兒童研究文獻(xiàn)進(jìn)行梳理,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調(diào)查研究中隱藏的一些“元假設(shè)”問(wèn)題進(jìn)行深入考察。
二、農(nóng)村留守兒童問(wèn)題調(diào)查研究中的常見(jiàn)“元假設(shè)”
“元假設(shè)”在調(diào)查研究中往往是研究者所“未明言、甚至未能意識(shí)到的”,因此,對(duì)某領(lǐng)域、某問(wèn)題的社會(huì)調(diào)查研究中的“元假設(shè)”進(jìn)行研究,就只能從已發(fā)表的論文和研究報(bào)告中依據(jù)研究者關(guān)于其調(diào)查工具(問(wèn)卷)的選用和調(diào)查方法的具體描述進(jìn)行“逆推”,從中識(shí)別、歸納出作者在調(diào)查研究中所潛藏的“元假設(shè)”。
從以往以農(nóng)村留守兒童為調(diào)查對(duì)象的研究成果來(lái)看,其采用問(wèn)卷調(diào)查這一研究手段時(shí)的慣用方法及其背后的“元假設(shè)”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點(diǎn):
(一)關(guān)于分布的“元假設(shè)”:農(nóng)村留守兒童往往生活在較為偏僻、落后的鄉(xiāng)村地區(qū)
研究者尋找農(nóng)村留守兒童做調(diào)查對(duì)象,主要途徑有:一是“社區(qū)調(diào)查法”,通過(guò)調(diào)查偏遠(yuǎn)鄉(xiāng)村里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及社區(qū)狀況來(lái)進(jìn)行研究,如葉敬忠等對(duì)北京市延慶縣珍珠泉鄉(xiāng)八畝地村留守兒童的調(diào)研[4]、姜又春對(duì)湖南省潭村的民族志調(diào)查[5],但使用此法的研究文獻(xiàn)極少;二是“學(xué)校進(jìn)入法”,通過(guò)農(nóng)村地區(qū)的中小學(xué)校直接進(jìn)入班級(jí),再把所調(diào)查班級(jí)的學(xué)生區(qū)分成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比較研究,使用此進(jìn)入法接觸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文獻(xiàn)極多,不贅述。不管通過(guò)哪種方法接近調(diào)查對(duì)象,大多數(shù)研究者往往都是把我國(guó)中、西部地區(qū)選擇外出務(wù)工人員較多的縣市、鄉(xiāng)鎮(zhèn)的行政村、自然村或當(dāng)?shù)氐膶W(xué)校作為首選調(diào)查地點(diǎn),再直接調(diào)查農(nóng)村留守兒童或其對(duì)照組。
(二)關(guān)于對(duì)照組的“元假設(shè)”:農(nóng)村留守兒童生活、就讀于農(nóng)村地區(qū),非農(nóng)戶(hù)口兒童不會(huì)生活、就讀于農(nóng)村地區(qū)
確定調(diào)查區(qū)域后,研究者往往在農(nóng)村中、小學(xué)調(diào)研時(shí),把學(xué)校、班級(jí)的學(xué)生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區(qū)分成“農(nóng)村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兩類(lèi)。比如,2014年底,“上學(xué)路上”公益組織對(duì)我國(guó)六省市農(nóng)村地區(qū)的留守兒童進(jìn)行問(wèn)卷調(diào)查[6]。該調(diào)查通過(guò)詢(xún)問(wèn)家人外出打工情況判斷被調(diào)查的學(xué)生是否為留守兒童以及留守的類(lèi)型。如將選擇“無(wú)人外出”“哥哥或姐姐外出”的判斷為非留守兒童;選擇“父親外出”“母親外出”“父母都外出”的則被判斷為農(nóng)村留守兒童。類(lèi)似處理背后的“元假設(shè)”認(rèn)為非農(nóng)戶(hù)口的孩子不會(huì)生活、就讀于農(nóng)村地區(qū)。故而在所調(diào)查的農(nóng)村中、小學(xué)學(xué)校的學(xué)生中,并未對(duì)“非農(nóng)”、異地隨遷的孩子進(jìn)行剔除。
(三)關(guān)于“缺陷型”家庭結(jié)構(gòu)的“元假設(shè)”:“親子分離”的“缺陷型”家庭結(jié)構(gòu)是本質(zhì)性的、不受外力所影響的、是不變的
據(jù)此“元假設(shè)”,研究者往往依據(jù)一段時(shí)間(三四個(gè)月或半年、甚至一年)以來(lái)至調(diào)查時(shí)點(diǎn)是否處于“親子分離”狀態(tài)來(lái)區(qū)分“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即如果調(diào)查時(shí)點(diǎn)與父母親住在農(nóng)村,就是“非留守兒童”,如果父母親雙方或一方外出,則界定為“留守兒童”。在此分類(lèi)基礎(chǔ)上,依據(jù)一次性橫斷面研究模型,將“留守”家庭結(jié)構(gòu)視為是一個(gè)外生變量(即認(rèn)為家庭結(jié)構(gòu)變量是不受其它變量所影響的),在此基礎(chǔ)上討論“親子分離”的“缺陷型”家庭結(jié)構(gòu)對(duì)留守兒童的負(fù)面影響。
(四)關(guān)于“非留守兒童”家庭祖輩作用的“元假設(shè)”:“非留守兒童”家庭祖輩不參與撫育、教養(yǎng)。只有“農(nóng)村留守兒童”家庭由于父母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而主要依賴(lài)祖輩監(jiān)護(hù),受祖輩學(xué)歷低、溺愛(ài)孫輩等的影響大
對(duì)此“元假設(shè)”,有的研究者學(xué)理上未必能夠認(rèn)同,但從絕大多數(shù)研究者提出“留守兒童-祖輩監(jiān)護(hù)”“非留守兒童-父母監(jiān)護(hù)”的簡(jiǎn)單二元對(duì)立模式,或按“父親外出、母親外出、雙親外出”或“單親監(jiān)護(hù)、祖輩監(jiān)護(hù)、上代監(jiān)護(hù)、自我監(jiān)護(hù)”等標(biāo)準(zhǔn)把留守兒童分為三類(lèi)或四類(lèi),但對(duì)“非留守兒童”則基本上不再分類(lèi)的研究習(xí)慣來(lái)看,這樣的“元假設(shè)”確實(shí)存在。
(五)關(guān)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父母作用的“元假設(shè)”: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不在孩子身邊的父母對(duì)孩子的教育、成長(zhǎng)沒(méi)有什么影響力
據(jù)此“元假設(shè)”,研究者往往只關(guān)注目前留守兒童是由誰(shuí)管教(如父母中未外出的一方、祖輩、親友鄰居、教師或其他代養(yǎng)人員等),調(diào)查問(wèn)卷中常測(cè)量代養(yǎng)人員的教管態(tài)度(是否“重養(yǎng)輕教”、是否忽視教管等)、文化程度(是否能夠輔導(dǎo)孩子功課)和健康狀況等,其預(yù)設(shè)是代養(yǎng)人員的教管態(tài)度、文化程度和健康狀況等可能對(duì)孩子的學(xué)業(yè)、道德品質(zhì)、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表現(xiàn)有(通常是負(fù)面)影響,但對(duì)外出的父母雙方或一方的教育、支持作用不太關(guān)注。
以上這些“元假設(shè)”是筆者在長(zhǎng)期研究農(nóng)村留守兒童問(wèn)題的過(guò)程中,依據(jù)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調(diào)查研究文獻(xiàn)的廣泛了解、歸納總結(jié)而成的。這些“元假設(shè)”是既往文獻(xiàn)中大多數(shù)研究者較流行的一些研究習(xí)慣,但不表明每個(gè)研究者都存在這樣的問(wèn)題。
三、農(nóng)村留守兒童調(diào)查研究中常見(jiàn)“元假設(shè)”的問(wèn)題辨析
通過(guò)常年的農(nóng)村社會(huì)生活調(diào)查與體驗(yàn),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的“元假設(shè)”大都是有問(wèn)題的。簡(jiǎn)單陳述理由如下:
(一)針對(duì)關(guān)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分布的“元假設(shè)”的辨析
從一般研究者的“元假設(shè)”來(lái)看,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隨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的父母進(jìn)城,一般就讀于城市學(xué)校,而農(nóng)村留守兒童是被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的父母“留守”在農(nóng)村的,他們一般應(yīng)該是就讀于農(nóng)村學(xué)校。但從官方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來(lái)看,“農(nóng)民工隨遷子女進(jìn)城就讀、農(nóng)村留守兒童留守農(nóng)村”這樣的“元假設(shè)”有很大的問(wèn)題。
1.“隨遷子女”并非都是“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而“農(nóng)民工隨遷子女”并非全部“進(jìn)城”就讀
2013年以來(lái),教育部教育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中同時(shí)統(tǒng)計(jì)了義務(wù)教育階段所有隨遷子女的數(shù)量以及其中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的數(shù)量。據(jù)此,可以計(jì)算出2013~2020年非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主要包括城→鄉(xiāng)、城→城遷移人員的隨遷子女)的數(shù)量。如表1所示,全國(guó)2013~2020年在校小學(xué)生、初中生中,非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的隨遷子女的數(shù)量都是逐年攀升,2013年“非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校小學(xué)生、初中生分別為255.96萬(wàn)人、80.5萬(wàn)人,之后逐年上升,到2020年“非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校小學(xué)生、初中生分別達(dá)到412.75萬(wàn)人、157.40萬(wàn)人,占小學(xué)階段、初中階段隨遷子女總數(shù)的28.51%和28.50%,說(shuō)明“隨遷子女”中盡管有71.5%左右的兒童屬于“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但畢竟還有將近三成的隨遷兒童是“非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的隨遷子女,“隨遷子女”不能隨意與“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劃等號(hào)。

表1 2013~2020年義務(wù)教育階段“非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的數(shù)量 (單位:人)
此外,很多人印象中農(nóng)民工隨遷子女似乎都是進(jìn)城了,但數(shù)據(jù)顯示卻不盡然。以農(nóng)民工人數(shù)、農(nóng)村留守兒童人數(shù)眾多的人口大省湖南省為例。根據(jù)《湖南教育事業(yè)統(tǒng)計(jì)年鑒2009》相關(guān)數(shù)據(jù)①之所以選用該數(shù)據(jù)是因?yàn)橹挥性撃觇b中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隨遷兒童等在市、鎮(zhèn)、鄉(xiāng)的詳細(xì)分布有細(xì)致統(tǒng)計(jì),但全國(guó)性教育統(tǒng)計(jì)年鑒中沒(méi)有做這樣細(xì)致的區(qū)分。且湖南省一直是人口流出大省,也是農(nóng)村留守兒童大省。湖南省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分布情況大體也能反映中西部地區(qū)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分布狀況。分析發(fā)現(xiàn),2009年,在湖南省初中學(xué)校就讀的農(nóng)民工隨遷子女中,只有59.64%就讀于城市初中學(xué)校。有超四成的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是在鎮(zhèn)區(qū)、農(nóng)村的初中學(xué)校就讀。其中就讀于農(nóng)村初中學(xué)校的隨遷子女比重達(dá)7.93%[7]59。
2.農(nóng)村留守兒童并非全部留守“鄉(xiāng)村”
“農(nóng)村留守兒童”究竟分布在哪里?實(shí)際情況與有些研究者甚至社會(huì)公眾認(rèn)知中認(rèn)為“農(nóng)村留守兒童”主要集中于“偏僻鄉(xiāng)村、偏僻學(xué)校”想象不太一致。實(shí)際上,在縣域范圍內(nèi),由于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基本上都集中于縣城與中心集鎮(zhèn)等地,使得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而小有財(cái)力的家庭往往把留守兒童送到當(dāng)?shù)亟逃|(zhì)量居于前列的學(xué)校就讀,使得農(nóng)村區(qū)域內(nèi),有不少留守兒童已在縣城、中心集鎮(zhèn)就讀,“文字上移”[8-9]。以留守兒童數(shù)量居于全國(guó)前列的湖南省為例,根據(jù)可以清晰分辨留守兒童就讀區(qū)域的新近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來(lái)看,2009年,湖南省農(nóng)村留守兒童初中生有811148人,其中,就讀于縣鎮(zhèn)的農(nóng)村留守初中生有395530人,就讀于鄉(xiāng)村的農(nóng)村留守初中生有415618人。該年湖南省農(nóng)村留守初中生就讀于縣鎮(zhèn)的約四成九,就讀于農(nóng)村的約五成一[7]。
以上湖南省的數(shù)據(jù)表明,義務(wù)教育階段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子女有四成左右并非在城市學(xué)校就讀,將近一半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并非在農(nóng)村學(xué)校就讀。一些學(xué)者在其他省份的研究也早已揭示城鎮(zhèn)學(xué)校里存在“農(nóng)村留守兒童”廣泛就讀的現(xiàn)象[10-12]。在這樣的留守兒童分布背景下,如果抱著“偏僻鄉(xiāng)村農(nóng)民工子女”的“元假設(shè)”去尋找研究對(duì)象,就只會(huì)選擇性地看到“偏僻鄉(xiāng)村、偏僻學(xué)校”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而會(huì)忽略掉在縣鎮(zhèn)就讀的大批“農(nóng)村留守兒童”了。另外,在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相對(duì)落后的“省(自治區(qū))—縣(區(qū))—鄉(xiāng)(鎮(zhèn))—村/或一般及偏下的中小學(xué)校”抽樣(包括一些跨省、跨市縣的調(diào)查,其農(nóng)村留守兒童樣本的區(qū)域選擇往往雷同,存在類(lèi)似的樣本“選擇性偏差”問(wèn)題),同一地點(diǎn)的“留守兒童”同質(zhì)性較強(qiáng),甚至其與“非留守兒童”的同質(zhì)性也很強(qiáng)。如王誼2013年在陜北佳縣2所小學(xué)的調(diào)查表明,分班級(jí)來(lái)看,小學(xué)7個(gè)班和初中4個(gè)班的學(xué)生中,無(wú)論哪個(gè)班其留守、非留守兒童之間的學(xué)習(xí)成績(jī)均沒(méi)有顯著差異[13]。在這一“元假設(shè)”下開(kāi)展的調(diào)查研究也就難以體現(xiàn)留守兒童內(nèi)部的層次性、差異性。而對(duì)“偏僻鄉(xiāng)村、偏僻學(xué)校”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發(fā)展?fàn)顩r問(wèn)題的描述,自然也難以代表更廣泛意義上一般農(nóng)村留守兒童群體的實(shí)況了。
(二)針對(duì)關(guān)于對(duì)照組“農(nóng)村非留守兒童”的“元假設(shè)”的辨析
農(nóng)村留守兒童首先必須是農(nóng)村人口。在“農(nóng)村人口”的定義上,有按行政區(qū)域劃分的“鄉(xiāng)村人口”和按照戶(hù)籍性質(zhì)劃分的“農(nóng)業(yè)人口”兩種情況①直到最近幾年來(lái),由于戶(hù)籍制度的改革,全國(guó)大部分省區(qū)都取消了農(nóng)業(yè)戶(hù)口與非農(nóng)業(yè)戶(hù)口的區(qū)分,統(tǒng)一登記為居民戶(hù)口,在此情況下農(nóng)村人口主要是指行政區(qū)域意義上。。
按照行政區(qū)域,全國(guó)被劃分為“市”“鎮(zhèn)”“縣”三種類(lèi)型。在統(tǒng)計(jì)上,“縣”通常被認(rèn)為是“鄉(xiāng)村地區(qū)”。按照這一劃分標(biāo)準(zhǔn),所謂農(nóng)村人口是指經(jīng)常居住在縣級(jí)地區(qū)的人口。而按照戶(hù)口登記制度,中國(guó)人口的戶(hù)籍性質(zhì)分為“農(nóng)業(yè)戶(hù)口”與“非農(nóng)業(yè)戶(hù)口”兩種類(lèi)型。由于居住地(城市或鄉(xiāng)村)與勞動(dòng)性質(zhì)或戶(hù)口性質(zhì)(農(nóng)業(yè)或非農(nóng)業(yè))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鄉(xiāng)村人口”與“農(nóng)業(yè)人口”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重疊,但兩種口徑之間也有明顯的差異。盡管中國(guó)的“鄉(xiāng)村人口”大多是農(nóng)業(yè)人口,但“農(nóng)業(yè)(戶(hù)籍)人口”中不少并不居住在鄉(xiāng)村。
在城鄉(xiāng)二元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我國(guó)城市與鄉(xiāng)村有空間分異,而在城市與鄉(xiāng)村各自的空間中,又有城市人口(非農(nóng)戶(hù)籍)與農(nóng)村人口(農(nóng)業(yè)戶(hù)籍)之別。眾所周知,工作、生活在城市區(qū)域的人口,未必是“非農(nóng)戶(hù)口”。同樣的,工作、生活在“農(nóng)村”區(qū)域的人口也未必是“農(nóng)業(yè)戶(hù)口”。
因此,在縣鎮(zhèn)的中、小學(xué)里,從戶(hù)口角度看主要包含三類(lèi)人,外縣市戶(hù)籍的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隨遷兒童、本地非農(nóng)業(yè)戶(hù)口在讀兒童和本縣農(nóng)業(yè)戶(hù)口在讀兒童(包括“農(nóng)村留守兒童”與“農(nóng)村非留守兒童”)。在農(nóng)村的中、小學(xué)里,從戶(hù)口角度看也會(huì)包含這三類(lèi)人,學(xué)校存在非農(nóng)戶(hù)籍學(xué)生、縣外市內(nèi)、省內(nèi)市外甚至省外戶(hù)籍學(xué)生以及本地農(nóng)村戶(hù)籍學(xué)生的情況并不奇怪,只是不同類(lèi)別學(xué)生的比重在各個(gè)學(xué)校略有不同而已。同樣,“農(nóng)村留守兒童”既可能生活、就讀于農(nóng)村學(xué)校,也可能就讀于縣鎮(zhèn)學(xué)校[14]。
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研究,需要明確調(diào)查對(duì)象是否符合“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特征,另外,也需要尋找與之具有可比性的對(duì)照組“農(nóng)村非留守兒童”。所以,考慮到農(nóng)村留守學(xué)生的對(duì)照組要具有可比性,因此,通過(guò)學(xué)校途徑接觸到調(diào)查對(duì)象時(shí),不應(yīng)把除了農(nóng)村留守兒童之外的學(xué)生統(tǒng)一歸之為“非留守兒童”。但從已經(jīng)發(fā)表的研究成果來(lái)看,數(shù)據(jù)分析之前就對(duì)學(xué)校中屬于非農(nóng)戶(hù)口的城鎮(zhèn)學(xué)生,以及外縣市戶(hù)籍(不論城鄉(xiāng))的流動(dòng)兒童/隨遷兒童做必要剔除的,卻是鳳毛麟角。
在調(diào)查農(nóng)村學(xué)校兒童中,除了農(nóng)村留守兒童和其他農(nóng)村兒童之外,還有一部分學(xué)齡階段的在校生屬于隨遷子女(當(dāng)然包括農(nóng)民工隨遷子女)。“非留守兒童”是一個(gè)龐雜、內(nèi)部差異甚大的群體。因此,在農(nóng)村學(xué)校進(jìn)行調(diào)查時(shí),把農(nóng)村留守兒童之外的其他在校生都視作“非留守兒童”,可能會(huì)把部分非農(nóng)戶(hù)口兒童、隨遷子女(因各種原因產(chǎn)生的隨遷子女,也包括農(nóng)民工隨遷子女)等全部納入“非留守兒童”,就會(huì)人為加大“非留守兒童”群體的內(nèi)部異質(zhì)性。要避免人為加大這種“非留守兒童”群體的內(nèi)部異質(zhì)性,就需要在研究開(kāi)始前,把與農(nóng)村留守兒童可比性不太高的非農(nóng)戶(hù)口兒童、隨遷子女(含農(nóng)民工隨遷子女)等從“非留守兒童”群體中剔除出去,剩下農(nóng)村留守兒童與較為純粹的農(nóng)村“非留守兒童”,才好進(jìn)行比較。但是,很可惜的是,在大量的研究文獻(xiàn)中,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調(diào)查對(duì)象進(jìn)行過(guò)類(lèi)似剔除處理的研究屈指可數(shù)。
(三)針對(duì)關(guān)于“缺陷型”家庭結(jié)構(gòu)的“元假設(shè)”的辨析
以往關(guān)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研究,研究者往往依據(jù)一段時(shí)間以來(lái)至今是否處于“親子分離”狀態(tài)來(lái)區(qū)分“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再討論“親子分離”的“缺陷型”家庭結(jié)構(gòu)對(duì)留守兒童的負(fù)面影響。這些研究大部分都屬于橫斷面研究,對(duì)于家庭結(jié)構(gòu)變量的研究方式,以往研究者普遍將家庭結(jié)構(gòu)視為是一個(gè)外生變量,認(rèn)為其是不受其它變量所影響的,把“親子分離”的“缺陷型”家庭結(jié)構(gòu)看作是本質(zhì)性的、不受外力所影響的、是不變的。
將家庭結(jié)構(gòu)設(shè)定為外生變量,是假定家庭結(jié)構(gòu)本身是不受其它變量影響的。但家庭結(jié)構(gòu)狀態(tài)由親子分離回到親子團(tuán)聚,說(shuō)明其家庭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是受內(nèi)在因素所影響的。家庭結(jié)構(gòu)在實(shí)質(zhì)上是內(nèi)生變量,是會(huì)受到其它變量所影響的或與其它變量之間具有關(guān)聯(lián)影響。Hao 等指出家庭結(jié)構(gòu)的變遷可能具有潛在自我選擇因素存在[15],且家庭結(jié)構(gòu)變量可能是某些因素(未測(cè)量)所造成的果(主要是內(nèi)生變量)。在家庭結(jié)構(gòu)的改變上,如果僅僅將家庭結(jié)構(gòu)視為外生變量,便可能會(huì)產(chǎn)生因果說(shuō)明上的內(nèi)生性偏誤。例如:測(cè)量過(guò)程中忽視父母健康狀況、心理狀態(tài)、婚姻滿(mǎn)意度等維度,而這些未測(cè)量的變量也可能對(duì)于家庭結(jié)構(gòu)或者子女的表現(xiàn)產(chǎn)生影響,因而使家庭結(jié)構(gòu)的影響系數(shù)產(chǎn)生估計(jì)偏誤。
(四)針對(duì)關(guān)于“非留守兒童”家庭祖輩作用的“元假設(shè)”的辨析
以往對(duì)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家庭結(jié)構(gòu)的研究分析主要是從兩個(gè)方向進(jìn)行的。首先,把農(nóng)村留守兒童根據(jù)父母親外出的不同情形而分成“單親外出”和“雙親外出”兩大類(lèi),其中“單親外出”又可以細(xì)分為“父親外出”和“母親外出”兩小類(lèi)[16]。其次,則是把農(nóng)村留守兒童根據(jù)目前與誰(shuí)同住而分成與母親在一起、與母親和其他家庭成員在一起、與父親在一起、與父親和其他家庭成員在一起、隔代家庭、單身留守、其他類(lèi)型等多種形式[3]。或者,簡(jiǎn)化分類(lèi),如楊菊華等根據(jù)兒童的居住安排,將留守兒童區(qū)分為與父親留守、與母親留守、無(wú)父母留守三類(lèi)[17]。有的研究者把父母親外出方式與農(nóng)村留守兒童目前與誰(shuí)同住兩個(gè)分類(lèi)標(biāo)準(zhǔn)混用,把父親外出打工對(duì)應(yīng)母親監(jiān)護(hù),母親外出打工對(duì)應(yīng)父親監(jiān)護(hù),這樣的處理方式有可能忽略了父母一方外出打工時(shí)留守兒童實(shí)際監(jiān)護(hù)情況下的內(nèi)部差異[18]。
上述兩種探討農(nóng)村留守兒童家庭結(jié)構(gòu)的研究方向是有一定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比如,“母親外出”或“父親外出”的情況下,一般仍有父母中的一方“留守”農(nóng)村。但值得注意的是,依照父母外出情況進(jìn)行的分類(lèi)與依照目前同住成員的情況進(jìn)行的分類(lèi),其詳盡程度是不一樣的。從父母親外出方式來(lái)看,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進(jìn)行“二分類(lèi)”(雙親或單親外出)或“三分類(lèi)”(雙親外出、父親外出、母親外出)顯得簡(jiǎn)潔、清晰,而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依據(jù)居住方式分類(lèi)則有多種類(lèi)別,較為繁瑣,如將“父母都外出”再細(xì)分為“單獨(dú)居住”“祖父母”“其他人”三種居住類(lèi)型,將“僅父/母親外出”再細(xì)分為“單獨(dú)與母/父親”“母/父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兩種居住類(lèi)型。
因此,基于比較視角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研究,往往傾向于依據(jù)父母外出狀況對(duì)留守兒童群體進(jìn)行“二分類(lèi)”或“三分類(lèi)”來(lái)探討留守兒童群體內(nèi)部不同“子群”與“非留守兒童”的群體差異。但由于這種“二分類(lèi)”或“三分類(lèi)”方式忽略了留守兒童實(shí)際居住的家庭環(huán)境的情況(如“父親外出”的話(huà),兒童可能是與母親同住,也可能是與母親、祖輩同住,也可能是其他方式),因此,不同的家庭結(jié)構(gòu)形式(家庭成員居住情況)對(duì)兒童的影響可能難以通過(guò)外出情況的“二分類(lèi)”或“三分類(lèi)”方式進(jìn)行恰當(dāng)?shù)娜后w比較。而有的研究者不把單親外出的兒童視作留守兒童,而僅把雙親外出的兒童視作留守兒童[19-20],這樣處理把“留守兒童”類(lèi)型單一化,但明顯又加大了“非留守兒童”群體的異質(zhì)性。
從實(shí)際同住的家庭成員的角度來(lái)看,農(nóng)村留守兒童中,除了“祖輩監(jiān)護(hù)”的兒童之外,還有相當(dāng)數(shù)量是與父、母親中的一方及祖輩共同生活的。絕大多數(shù)研究者提出“留守兒童-祖輩監(jiān)護(hù)、非留守兒童-父母監(jiān)護(hù)”的二元對(duì)立模式,或把留守兒童按“父親外出、母親外出、雙親外出”或“單親監(jiān)護(hù)、祖輩監(jiān)護(hù)、上代監(jiān)護(hù)、自我監(jiān)護(hù)”等標(biāo)準(zhǔn)分為三類(lèi)或四類(lèi),但根據(jù)周福林對(duì)我國(guó)第五次全國(guó)人口普查0.95‰的抽樣數(shù)據(jù)的分析結(jié)果,無(wú)論是留守還是非留守家庭,其家庭結(jié)構(gòu)均是多種多樣的[3]。一般研究者以為“非留守兒童”既然父母留在農(nóng)村,那么理所當(dāng)然是由父母撫育,所以對(duì)“非留守兒童”基本上不再按撫養(yǎng)者的不同情況做進(jìn)一步的分類(lèi)。一些研究者使用“農(nóng)村留守兒童=父母雙方外出(或父、母一方外出)”與“(農(nóng)村)非留守兒童=父母雙方均不外出”的二元對(duì)立模式來(lái)思考問(wèn)題,如謝妮等把“非留守兒童”定義為是指與父母雙親共同生活的兒童[21],也有研究者按照父母是否遷移和家庭所在地形式對(duì)家庭、兒童進(jìn)行分類(lèi)(包括農(nóng)村完整家庭兒童、農(nóng)村留守兒童等),并認(rèn)為留守兒童是“不與父母同住”的,與留守兒童相對(duì)應(yīng)的“非留守兒童”被命名為“完整家庭兒童”[22],這些研究對(duì)“非留守兒童”進(jìn)行界定背后的“元假設(shè)”是這一群體“與父母同住”。因此,在相關(guān)研究中,往往將留守家庭的家庭結(jié)構(gòu)簡(jiǎn)化為“二分類(lèi)”或“三分類(lèi)”,將非留守兒童的家庭結(jié)構(gòu)看作是鐵板一塊的,忽略了非留守家庭祖輩參與撫育的作用。
但實(shí)際上,祖輩協(xié)助子女撫養(yǎng)孫輩,在中國(guó)歷史上是較為常見(jiàn)的[23]。祖輩是農(nóng)村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撫育網(wǎng)絡(luò)”的重要組成部分。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所謂“非留守兒童”中也有相當(dāng)數(shù)量是與祖輩生活在一起的。“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比較問(wèn)題不能簡(jiǎn)化成留守兒童的“祖輩撫養(yǎng)”與非留守兒童的“父母撫養(yǎng)”的比較問(wèn)題,即使是父母“雙雙外出”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在非留守兒童中同樣有大量祖輩協(xié)助照顧、教養(yǎng)的情形。
以筆者在湖南省寧鄉(xiāng)縣所做的調(diào)查為例,數(shù)據(jù)顯示,僅與父母在家的兒童占調(diào)查學(xué)校農(nóng)村孩子總數(shù)的33.4%,與父母/祖輩在家的兒童則占27.5%。現(xiàn)況為“非留守兒童”的農(nóng)村兒童中,有將近一半(45.3%)是和父母/祖輩在一起。“非留守兒童”中也有較大比例的家庭是有祖輩參與生活的[7]75-76。當(dāng)然,這并不表示其一定是大家庭式的結(jié)構(gòu)。因?yàn)椋问缴献孑呌锌赡芤呀?jīng)與其子女分家,但為了照顧孫子女,在實(shí)際居處中還是像一個(gè)家庭一樣開(kāi)展日常生活。
Goldberg-Glen等的相關(guān)研究把隔代家庭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隔代家庭是指父母完全放棄承擔(dān)孩子教養(yǎng)責(zé)任,而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承擔(dān)全部的養(yǎng)育責(zé)任的家庭。廣義隔代家庭則泛指祖父母任何一方或雙方與第三代有共處的時(shí)間,承擔(dān)某些撫育責(zé)任[24]。筆者對(duì)湖南寧鄉(xiāng)農(nóng)村“非留守兒童”家庭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不少家庭也需要依靠祖輩來(lái)輔助孩子教育,算得上是“廣義隔代家庭”。現(xiàn)況為“農(nóng)村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中,都有不小的比例需要借助隔代教育資源。這與落合惠美子等在2004年對(duì)中、日、韓等6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育兒援助系統(tǒng)調(diào)查[25]中發(fā)現(xiàn)中國(guó)“來(lái)自祖父母等親屬的育兒幫助是6個(gè)地區(qū)中最多、最全面的”的結(jié)論是相符的。1949年以后的“人口政策”和“戶(hù)籍制度”等政策間接地促成了廣義的隔代撫育成為我國(guó)主要的撫育形式之一。農(nóng)村代際、親屬之間的育兒援助更是“人口紅利”時(shí)代的禮物[26]。
張帆等通過(guò)分析具有全國(guó)代表性的初中學(xué)生樣本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代際居住安排會(huì)顯著影響青少年的學(xué)業(yè)表現(xiàn),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與祖輩同住)家庭的學(xué)生的學(xué)業(yè)表現(xiàn)要優(yōu)于兩代核心家庭的學(xué)生。同時(shí),與祖輩同住的效應(yīng)受到家庭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地位和家庭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節(jié),來(lái)自較低階層或非雙親家庭的學(xué)生從與祖輩同住中獲益更多。與祖輩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過(guò)加強(qiáng)親子間的家庭社會(huì)資本這一機(jī)制作用于學(xué)生的學(xué)業(yè)表現(xiàn)[27]。因此,從學(xué)業(yè)表現(xiàn)來(lái)看,祖輩的育兒援助對(duì)青少年表現(xiàn)是具有正向作用的。留守兒童研究中不少研究者把祖輩撫育當(dāng)成留守兒童表現(xiàn)不佳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其研究結(jié)論值得商榷。
另外,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家庭里,同住的對(duì)象往往也反映農(nóng)民工家庭里選擇誰(shuí)作為農(nóng)民工外出期間主要照顧留守兒童的一種選擇順序。依據(jù)歷年來(lái)全國(guó)各地大量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各地留守兒童同住者的比例基本上是:與父母一方同住>與爺爺奶奶同住>與外公外婆同住>與叔伯同住>與姑舅姨同住>與鄰居、其他親屬和朋友同住。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主要照顧者的分布在各地大體上都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各種調(diào)查所顯示的結(jié)果是留守兒童同住者的分布狀況,雖并不直接說(shuō)明農(nóng)民工家庭留守兒童照顧者的優(yōu)先選擇價(jià)值觀念,但這種分布狀況無(wú)疑也是這一價(jià)值觀念作用的最終結(jié)果(參見(jiàn)圖1)。

圖1 漢人父系親屬結(jié)構(gòu)下留守兒童撫育的差序選擇[28]
從圖1中可以看出,在兒童“留守”時(shí),農(nóng)民工家庭的安排首先是選擇留守兒童父母中的一方來(lái)照顧。如果父母雙方都要外出,則選擇爺爺奶奶照顧。如果爺爺奶奶因?yàn)檫^(guò)世或健康狀況不佳、距離學(xué)校較遠(yuǎn)等原因不能照顧留守兒童,則選擇外公外婆。如果祖輩都不能照顧,則選擇叔伯、姑舅姨等。前述親戚均無(wú)法或沒(méi)有能力照顧的話(huà),最后才是由鄰居或其他親屬、朋友來(lái)照顧。這個(gè)留守兒童照顧者的差序選擇并非觀念調(diào)查的結(jié)果,而是根據(jù)現(xiàn)實(shí)的照顧者這一最終結(jié)果的現(xiàn)況倒推出來(lái)的,基本上能夠表現(xiàn)出農(nóng)民工家庭的一種大致思路。這種兒童照顧者的選擇結(jié)果說(shuō)到底是漢族父系家庭制度及男女分工安排之下的一種直觀表現(xiàn),即留守兒童的照顧主要以父系家庭為主,主要為母親照顧或爺爺奶奶照顧,其次才是外公外婆照顧或其他親屬照顧。這樣的安排被某些研究人員形容成打工父母的“不負(fù)責(zé)任”,這種指責(zé)顯然是遠(yuǎn)離事實(shí)的。
(五)針對(duì)關(guān)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父母作用的“元假設(shè)”的辨析
就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家庭生活環(huán)境狀況而言,一些學(xué)者徑直稱(chēng)之為“家庭缺失”[29]、“父母缺失”[30]等。京華時(shí)報(bào)所刊發(fā)的楊耕身題為《惟“共同生活”能解救留守兒童》[31]的文章,被眾多媒體冠以《中國(guó)“留守兒童”達(dá)6100萬(wàn)被稱(chēng)父母雙全的孤兒》的題名廣泛轉(zhuǎn)載,文中直接稱(chēng)呼“留守兒童”為“父母雙全的孤兒”。那么,不在孩子身邊的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的父母對(duì)孩子的教育、成長(zhǎng)有沒(méi)有影響力?以往,研究者往往在研究中只關(guān)注留守兒童日常生活是由誰(shuí)管教、照顧,調(diào)查問(wèn)卷中常測(cè)量代養(yǎng)人員的教管態(tài)度、文化程度和健康狀況等,潛臺(tái)詞是代養(yǎng)人員的教管態(tài)度、文化程度和健康狀況等可能對(duì)孩子的學(xué)業(yè)、道德品質(zhì)、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表現(xiàn)產(chǎn)生影響。但即使上述影響確實(shí)存在,也不代表外出的父母雙方或一方的教育、支持作用不重要/不顯著,可能只是一般研究者在調(diào)查時(shí)對(duì)這一部分根本沒(méi)有設(shè)計(jì)調(diào)查問(wèn)題,根本沒(méi)有辦法體現(xiàn)外出父母的“不在場(chǎng)他者”的影響力。理由如下:
第一,從客觀方面來(lái)看,在這種“親子分離”的家庭模式下,除了極少數(shù)所謂“自我監(jiān)護(hù)”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之外,絕大部分農(nóng)村留守兒童是生活在一定的“家庭”(如隔代家庭、“假性單親家庭”、寄養(yǎng)家庭等)之中的,況且依據(jù)學(xué)界的定義和大眾的認(rèn)知,這些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父母也都還健在。
第二,從主觀認(rèn)同方面來(lái)看,這些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家庭主觀認(rèn)同邊界往往也包括那些與自己處于分離狀態(tài)的父母在內(nèi)。從留守兒童的家庭自我認(rèn)同意識(shí)來(lái)看,雖然其父母暫時(shí)不在身邊,但留守兒童還是把外出的父母視作家庭成員[32],有的留守兒童并不把日常照顧他的祖輩或其他人視作家庭成員。
第三,從撫養(yǎng)、管教的角度來(lái)看,即使是在外的父/母中的一方或父母雙親,也不是完全不管孩子的生活與成長(zhǎng)。這些兒童的父母在外務(wù)工、經(jīng)商期間,通過(guò)書(shū)信、電話(huà)、匯款、回家過(guò)年過(guò)節(jié)等多種方式了解、關(guān)心子女的成長(zhǎng),一出去就杳無(wú)音訊的父母絕對(duì)是少之又少的。
第四,即使是父母不在身邊,這些兒童的代養(yǎng)人、教師等通過(guò)諸如“打電話(huà)告訴你爸爸媽媽”“把你送到城里去”“等你爸爸媽媽回來(lái)……”等諸如此類(lèi)的話(huà)語(yǔ),讓農(nóng)村留守兒童心目中勾畫(huà)出一個(gè)父母的形象、想象到父母管教的要求等,這些實(shí)際上也是父母角色的間接管教作用。
從以上這些情況來(lái)看,絕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其生活起居和日常管教既不是缺失“家庭”,也不是缺失“父母”。實(shí)際上,根據(jù)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表明,父母對(duì)子女的影響可以通過(guò)文化資本來(lái)達(dá)成[33]。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不在孩子身邊的父母對(duì)孩子的教育、成長(zhǎng)也可以通過(guò)家校合作、營(yíng)造家庭認(rèn)同與凝聚力、提供學(xué)習(xí)的物質(zhì)資源等手段發(fā)揮“不在場(chǎng)他者”的影響力。可見(jiàn),從留守兒童的主體視角來(lái)看,外出父母作為“不在場(chǎng)的他者”,其教育、支持、鼓勵(lì)等方面的作用都不容小覷。
至于斷言留守兒童是不是“父母雙全的孤兒”,更需要認(rèn)真察看其日常照護(hù)情況。根據(jù)以往的大量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留守兒童中的絕大部分都在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父母中在鄉(xiāng)一方的照顧之下。真正缺乏任何成年人照管的“留守兒童”是少之又少的。據(jù)段成榮等的推算數(shù)據(jù),46.74%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父母都外出,在這些孩子中,與祖父母一起居住的占農(nóng)村留守兒童總數(shù)的32.67%。與母親或母親、祖父母居住的占36.39%,與父親或父親、祖父母居住的占16.87%,與其他人一起居住的占10.7%。而只有3.37%(約205.7萬(wàn)人)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是單獨(dú)居住的[34]。而且,即便是單獨(dú)居住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其實(shí)際起居生活也是有人照管的。由于超過(guò)九成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是與祖輩、父母中的一方或其他人居住在一起,并由他們照管的,可見(jiàn),從實(shí)際居住情況來(lái)看,直呼留守兒童為“父母雙全的孤兒”,這并不符合農(nóng)村絕大部分留守兒童的實(shí)際情況,同時(shí)也是一種標(biāo)簽化、甚至“污名化”留守兒童的說(shuō)法[35]。
四、研究結(jié)論
在以往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研究中,依托調(diào)查問(wèn)卷進(jìn)行研究是絕大部分研究者的共同選擇。但依據(jù)“元假設(shè)”的理論,這些調(diào)查問(wèn)卷中的問(wèn)題設(shè)定,往往都是研究者(而且往往是目前居住于城市的研究者,如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研究生等)對(duì)于農(nóng)村兒童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先入為主的猜測(cè)與假設(shè)。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進(jìn)行問(wèn)卷調(diào)查,在認(rèn)識(shí)論層次上就是研究者依賴(lài)問(wèn)卷提問(wèn)“人為地、預(yù)設(shè)地去剪裁生活”。而問(wèn)卷調(diào)查的“人為預(yù)設(shè)”這個(gè)根本的局限性可能更需要研究者的高度警惕,以免過(guò)度“裁剪生活”而使研究結(jié)果背離現(xiàn)實(shí)。另一方面,沒(méi)有寫(xiě)進(jìn)問(wèn)卷的問(wèn)題,也是研究者舍棄掉的“假設(shè)”。這樣的割舍是否恰當(dāng),需要從“元假設(shè)”角度多進(jìn)行思考。
本研究基于對(duì)以往大量農(nóng)村留守兒童調(diào)查研究成果中,依據(jù)研究者關(guān)于其調(diào)查工具(問(wèn)卷)的選用和調(diào)查方法的具體描述進(jìn)行“逆推”,歸納、發(fā)掘出研究者在農(nóng)村留守兒童相關(guān)問(wèn)題的調(diào)查研究所潛藏的關(guān)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分布、對(duì)照組“農(nóng)村非留守兒童”、“缺陷型”家庭結(jié)構(gòu)、“非留守兒童”家庭祖輩作用、“農(nóng)村留守兒童”父母作用等五個(gè)方面的“元假設(shè)”,并對(duì)這五大“元假設(shè)”存在的問(wèn)題進(jìn)行深入論證,主要結(jié)論是:
一是農(nóng)村留守兒童分布方面,近半數(shù)的義務(wù)教育學(xué)齡段農(nóng)村留守兒童在城鎮(zhèn)學(xué)校就讀。在已經(jīng)發(fā)布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研究報(bào)告中,研究者鮮有把在縣城就讀的農(nóng)村留守孩子納入研究視野,而熱衷于到較為偏僻、落后的鄉(xiāng)村地區(qū)去尋找農(nóng)村留守兒童作為調(diào)查對(duì)象,忽略城鎮(zhèn)學(xué)校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這將使相關(guān)調(diào)查研究出現(xiàn)樣本選擇性偏差。
二是關(guān)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對(duì)照組方面,不僅“農(nóng)村留守兒童”生活、就讀于農(nóng)村地區(qū),非農(nóng)戶(hù)口的孩子也有不少生活、就讀于農(nóng)村地區(qū)。在農(nóng)村學(xué)校進(jìn)行調(diào)查,從對(duì)照組的可比性角度來(lái)說(shuō),需要對(duì)其中就讀的“非農(nóng)戶(hù)口”的孩子以及外地過(guò)來(lái)的隨遷兒童等進(jìn)行剔除,不能把“農(nóng)村留守兒童”以外的龐雜的多種類(lèi)型的其他兒童全歸為“非留守兒童”群體作為對(duì)照組。“(農(nóng)村)非留守兒童=父母雙方均不外出”的理解其實(shí)偏差很大。不管用嚴(yán)格的方式定義“農(nóng)村留守兒童”(雙親均外出才算),還是寬松定義“農(nóng)村留守兒童”(父母一方外出也算),剩下的“非留守兒童”并不等于“父母雙方均不外出”,因?yàn)椤胺橇羰貎和钡募彝ヒ部赡苁菃斡H家庭,或其他類(lèi)型的家庭。甚至,“非留守兒童”的家庭也可能是父母一方或雙方均有外出,只不過(guò)其外出時(shí)間沒(méi)有達(dá)到累計(jì)六個(gè)月(或連續(xù)三個(gè)月、連續(xù)六個(gè)月等)這一研究者所認(rèn)定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時(shí)間標(biāo)準(zhǔn)而被劃入“非留守兒童”群體中去。
三是關(guān)于“缺陷型”家庭結(jié)構(gòu)方面,“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群體里其實(shí)也都可能存在不同的家庭結(jié)構(gòu)差異,而其中某些類(lèi)型的家庭結(jié)構(gòu)(如單親、“繼親家庭”結(jié)構(gòu))對(duì)兒童某些方面表現(xiàn)的負(fù)面影響是早已被其他很多研究成果所證實(shí)的。比如,Beller等的研究表明,“繼親家庭”所產(chǎn)生的影響,與“原生雙親”或因離婚等所產(chǎn)生的“單親”影響有所差異。盡管“繼親家庭”其形式上“雙親”健全,但由于“繼親”這種特殊形式,其對(duì)子女的教育等也有一定的負(fù)面影響[36]。不宜把“親子分離”的“缺陷型”家庭結(jié)構(gòu)看作是本質(zhì)性的、不受外力所影響的、是不變的。一次性橫斷面研究模型難以反映“留守”家庭結(jié)構(gòu)作為內(nèi)生變量同時(shí)還受其它變量所影響這一情況,需要在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中討論家庭結(jié)構(gòu)的變遷以及與“親子分離”伴生的影響問(wèn)題。
四是關(guān)于家庭祖輩作用方面,以父母外出與不外出為標(biāo)準(zhǔn)推出的“留守—非留守”的二分法或三分法忽視了影響兒童表現(xiàn)的家庭結(jié)構(gòu)要素,不僅僅是其與父母或其中一方的分離,還應(yīng)該包括當(dāng)前與誰(shuí)住在一起、受誰(shuí)照顧與管束。研究者提出“留守兒童-祖輩監(jiān)護(hù)、非留守兒童-父母監(jiān)護(hù)”的二元對(duì)立模式,或把留守兒童按“父親外出、母親外出、雙親外出”或“單親監(jiān)護(hù)、祖輩監(jiān)護(hù)、上代監(jiān)護(hù)、自我監(jiān)護(hù)”等標(biāo)準(zhǔn)分為三類(lèi)或四類(lèi),已充分注意到農(nóng)村留守兒童家庭中的祖輩作用。但祖輩參與孫輩撫育活動(dòng),是當(dāng)前中國(guó)社會(huì)的普遍現(xiàn)象。“非留守兒童”家庭的祖輩多數(shù)也在參與撫育、教養(yǎng)。“農(nóng)村留守兒童”研究中,對(duì)對(duì)照組“非留守兒童”家庭的祖輩是如何參與并發(fā)揮作用也需要納入調(diào)查。
五是關(guān)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父母作用方面,父母是孩子成長(zhǎng)的“重要他者”,農(nóng)村留守兒童不是“父母缺失的孤兒”,也不是“家庭缺失的兒童”。隨著社會(huì)生活的變遷,由于各種原因,無(wú)論是從家庭自我認(rèn)同意識(shí)的角度還是實(shí)際居住的角度,“住在一起的不一定是一家人,不住在一起的未必不是一家人”也逐步成為農(nóng)村居民家庭生活、居住中一種常見(jiàn)的現(xiàn)象,尤其是在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日常生活中更是如此[32]。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的父母即使不在孩子身邊,也能通過(guò)社會(huì)資本、財(cái)務(wù)資本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對(duì)孩子的教育、成長(zhǎng)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力,學(xué)界不能對(duì)此視而不見(jiàn)。
本研究是潘綏銘等人提出問(wèn)卷調(diào)查中的“元假設(shè)”這一理論以來(lái)首次將其應(yīng)用于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調(diào)查研究文獻(xiàn)的評(píng)述,指出相關(guān)研究中較為普遍存在的五大錯(cuò)誤的“元假設(shè)”。誤判農(nóng)村生活現(xiàn)實(shí)會(huì)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調(diào)查研究的設(shè)計(jì)、調(diào)查對(duì)象的選擇、調(diào)查工具的使用等造成影響,最終可能會(huì)影響到研究結(jié)論的準(zhǔn)確性以及對(duì)農(nóng)村留守兒童問(wèn)題的準(zhǔn)確判斷與分析。因此,學(xué)界有必要對(duì)現(xiàn)有“農(nóng)村留守兒童問(wèn)題”現(xiàn)狀描述和群體差異的研究成果保持高度的警惕[37],尤其要檢討其概念界定、對(duì)照組選取等多方面做法背后的“元假設(shè)”是否與農(nóng)村社會(huì)生活現(xiàn)況吻合。今后的研究,也需要對(duì)這一類(lèi)“元假設(shè)”誤區(qū)做出改進(jìn),以使相關(guān)研究結(jié)論更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