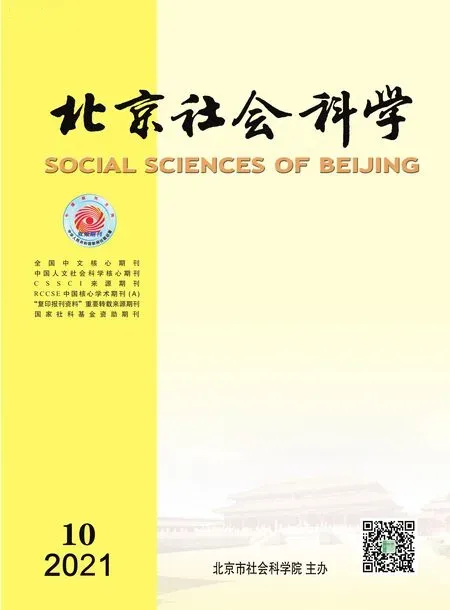婚禮親迎中的告廟禮研究
田 琛 關長龍
一、引言
在儒家傳統觀念中,婚禮并不只是婚姻主體個人之間的事,更聯結著兩個家族的世代傳承。《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1]上事宗廟、下繼后世即成為婚禮最根本之禮義所在。也正因此,在整個婚姻儀式的進程中,祖廟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男家必須先受命于廟然后行事,女家也要在祖廟中受禮,以表達尊敬、慎重之意:“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皆主人筵幾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1]
然而,由于禮經記載不詳,關于婚禮中男女兩家告廟的具體時間與儀程細節,一直存在爭議。親迎作為婚禮六禮中的最后一個儀節,新婿往迎前是否告祭先祖,自漢以來歷代禮學家亦各有觀點,官修禮典之儀注也各依時代及婚主身份階層而相異。就士庶婚禮來看,唐敦煌書儀中有豐富的親迎告祖相關資料可供考察;至宋代,朱熹等一批家禮撰著者依據各自對于禮俗的取舍而厘定親迎告祖的時間與具體儀程;明清以降,民間婚禮親迎則多遵《家禮》。本文將在厘清古禮儀注的基礎上,考察歷代親迎告祖儀程的傳承與變遷,探究親迎告祖儀式的根本禮義所在,以為當代婚禮重建提供可資信賴的參考資源。
二、親迎告廟禮輯說
《儀禮·士昏禮》親迎一節中,對男女兩家親迎前所需的陳設做了詳細說明。其中男家設鼎、洗、酒饌等,皆為新婦抵達后成禮時所用;女家則與前五禮一樣,強調要為祖神布席:“筵于戶西,西上,右幾”[2]。因此從禮經文本來看,親迎似只有女家告廟,而男家并沒有相關儀注可依。就古禮親迎前男家是否需要告廟,歷代一直有不同觀點。
(一)男家不必告廟說
認為男家親迎無需告廟的,以《白虎通》、《儀禮》賈疏為代表。對于男家不告廟的理由,又各有不同。《白虎通》言:“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3]就是說,親迎時婚姻尚不算正式成立,因此不應告廟而叨擾先祖。賈公彥則認為,女子嫁人,是以“先祖遺體”赴外族,而男家只是娶婦入室,輕重不同,女家禮本應重于男家,故女告而男不告:
父禮女者,以先祖遺體許人以適他族,婦人外成,故重之而用醴,復在廟告先祖也。男子直取婦入室,無不反之,故輕之而用酒,在寢。知醮子亦不在廟者,若在廟,以禮筵于戶西右幾布神位,今不言,故在寢可知也。[4]
案此二說,《白虎通》偏于男家而言,賈疏則偏于女家而言,卻皆有其不通之處。《白虎通》言“不必安”故而男家不告祖,但若從女家角度而言,新婦同樣是要待成婦禮之后才可算正式安定于男家,為何女家嫁女需告廟,而男家娶婦卻不告?另一方面,賈公彥認為女子出嫁離開便不再返回,因此女家所行儀式應當比男家更為隆重,但對男家而言,婚禮更是事宗廟、繼后世的大事。對女家而言是本族血統的外流,對男家而言則是外族血統的滲入,兩者于禮并無輕重之分。
由于《白虎通》與賈疏對后世影響較大,清儒中亦不乏持此意見者。如劉沅《儀禮恒解》,就是據前二者又加以演繹,認為不僅男家不告,即便女家也沒有專門的告祖之儀:
但設坐依神而臨其禮即是告,非別有奠酒、瘞幣之儀也。壻家來迎并無筵于廟之文,蓋納吉請期兩番命卜于廟門,則齋戒以告鬼神之義已備,故親迎不必更行告廟之儀也。[5]
劉沅此說,實際上是從另一角度解讀了“告”的含義:于女家而言,“告”即布神席供先祖憑依而觀禮;于男家而言,“告”則是在納吉、請期時卜于廟門,即為“告鬼神之義已備”。依此,則不僅親迎前無需告廟,在婚禮的整個六禮儀程中,男女兩家都不再需要舉行傳統意義上完整的“告祖”儀式。
此外,學者舒大剛等認為,貴族階層雖有在親迎前告廟的做法,但“告廟之禮的重點和意義在于舉辦大事之前‘將行’,并非為婚姻所專設”,因此男家親迎前是否舉行告祖儀式,并不影響婚禮的合法性。[6]
(二)男家亦需告廟說
與《白虎通》、賈公彥等不同,孔穎達、胡培翚等則認為,古禮親迎男家亦需告廟。論證思路主要有二:一是從《儀禮》與《禮記》的經注文本出發,首先論證婚禮六禮男女兩家皆當告廟,次而以親迎為六禮之一,則亦當有告廟之儀;二是以《左傳》等史料為據,明確古禮親迎逆婦前確有告廟之事實。
《儀禮·士昏禮》及《禮記》中的相關儀注,主要有以下四條:
第一條,《儀禮·士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7]
此條下鄭注云:“用昕,使者;用昏,壻也”;賈疏:“‘用昕,使者’,謂男氏使向女家納釆、問名、納吉、納征、請期五者皆用昕……云‘用昏,壻也’者,謂親迎時也”。[7]據此,則“凡行事”是囊括了婚禮自納采至親迎六禮而言的通例。胡培翚①、黃以周②等認為,“受諸禰廟”即指在禰廟中受命于先祖,因此婚禮不僅親迎前應告廟,實際上六禮皆需有相應的告祖儀式。
第二條,《儀禮·士昏禮·記》:某有先人之禮。[4]
鄭珍提出,婚禮男家致禮于女家,禮辭皆曰“某有先人之禮”,既然禮自“先人”而來,則男家必先告于廟,自先祖處受禮。③
第三條,《禮記·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8]
此條下鄭注云:“告于君也。”[8]孔穎達疏《左傳》昭公元年(前541)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而迎公孫段氏時援引鄭注,言“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9],以證逆婦告廟之儀。
第四條,《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10]
孔穎達疏《詩經·齊風·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一句時,援引此條,認為“娶妻自有告廟之法”[11],并結合《士昏禮》中女家納采儀注,認為“其后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于廟”[11]。毛奇齡則提出親迎逆婦依禮需“娶則告迎,入則謁至”,而此條“齋戒以告鬼神”,即是指男家親迎前告祖往迎之禮[12]。
以《左傳》為憑者,主要在以下兩條:
第一條,隱公八年(前715)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先配而后祖”: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13]
關于鄭忽先配后祖的行為,杜預將“配”釋為親迎逆婦,“祖”釋為親迎前的告廟之儀,所謂“先配而后祖”,就是說鄭忽未告廟受命而先逆婦媯:“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后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歸而后告廟,故曰先配而后祖。”[13]
第二條,昭公元年(前541),楚公子圍娶公孫段氏,“告莊共之廟而來”: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幾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9]
公子圍奉君命聘于鄭國,聘禮結束后,欲率眾入城迎娶公孫段氏。鄭子產擔心其趁機作亂,便希望他逆婦于城外。公子圍不從,命大宰伯州犂駁之,稱自己是依禮告莊、共之廟而來,亦當依禮而受女于廟,不應在野外成禮。案莊王為公子圍之祖,共王為其父,因此其稱“告于莊、共之廟而來”,亦即是告于祖禰之廟而來。孔穎達于此解釋道:“聘禮,臣奉君命聘于鄰國,猶尚釋幣于廟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幾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9]
(三)小結
綜上所述,結合《詩經·齊風·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句、《禮記·曲禮》“齋戒以告鬼神”條及《左傳》楚公子圍告莊共之廟等經注文本來看,婚禮需告廟這一點,應是毋庸置疑的。產生分歧的關鍵點,在于究竟應在六禮中的哪一禮告,是否當在親迎前告,抑或是六禮皆告的問題上。筆者認為,除去后人注解中或有去古已遠而不解其義的部分,《儀禮·士昏禮》經文中所言“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一條,可看做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自漢以來,對于“受諸禰廟”一句的爭議主要在于兩點,一是此句是否就六禮而言,亦即親迎是否在其所指范圍之內;二是是否兼論男女兩家之儀。首先,這一句在“記”之第一條,上承“士昏禮”之總括;“用昏昕”之言,也是結合前五禮“用昕”與親迎“用昏”一并指示的,故應當視為婚禮六禮之通例。其次,禮經省文,若每一具體儀節都只孤立于條文內考量,則未詳之處甚多。納采至請期五禮皆立文于女家而不提男家儀節,且女家六禮皆布神席而受禮于廟,男家祖禰卻概無涉及,即使顯然必須由男家卜于廟的納吉禮,也沒有提及相關的告廟儀式。基于此,以男女家儀節互文為解更合經義,而不應簡單地以禮經不言就認為男家沒有相應儀節。要言之,“受諸禰廟”一句,當以兼論男女兩家六禮之通例而言。再具體到親迎逆婦前的告祖之儀,《左傳》中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乃行之記載,則可看做信史。
此外,從婚禮的基本禮義而言,親迎告廟也有其不可省簡的理由。在儒家的傳統婚禮中非常重視家廟。這是因為,供奉先祖的家廟象征著神圣的“家族意志”。納采問名后須“歸卜于廟”,得吉兆方可定婚姻,就是對此最直接的體現。甚至可以說,在整個婚禮向前推進的過程中,先祖作為家族意志的象征,并不只是作為旁觀者在場而已,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重要選擇的決策者與行事命令的發出者。親迎作為六禮的最后一個亦是最為重要的環節,新人將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相接”,從此作為共同主體,成為家族成長鏈條中的一環,肩負起上事宗廟、下繼后世的責任。在直面這些即將到來的重大變化時,新人無疑是忐忑而惶恐的。從這一意義上而言,新人亦需要通過神圣而莊重的告祖儀式,建立起與先祖、家族的溝通與融合,感受家族的認同與庇護,從而獲得身心上的安頓。
還需注意的是,上揭毛奇齡、舒大剛等人亦提及親迎中的“告出”“告返”之禮。案廣義的告廟當有“大中小”三種形態,其小者即以言語告之,若日常小事或出行歸家的告出、告返等;其中者則以香物告奠,小、中之告廟皆不必請神降臨獻祭;其大者則行降神獻祭分胙的完整祭儀。就禮義而言,新郞親迎逆婦,臨行前與返回時的告出、告返是通禮,可以不必專為揭出強調,而文獻所載的親迎“告廟”之禮,亦即本文所探討的親迎告廟禮,則是在告出、告返之外,為親迎所專行的告廟祈安之禮,二者在禮義與禮節輕重上皆有區別。
三、親迎告廟禮的踐行沿革
(一)唐以前之事例

另一方面,傳世文獻中有關唐以前親迎告祖的記錄,除了上文提及的《左傳》隱公八年與昭公元年二則之外,還有《漢書》元始四年(4)平帝納孝平王皇后一則:
(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15]
此條中記錄了“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但未明示此為六禮中具體哪一個儀節的告廟。楊樹達推測“‘待吉月日’者,蓋已請期而告于宗廟也”[16],亦即為親迎前的告廟。案兩漢時期《儀禮》長期在禮學中處于主導地位,不僅立于學官,兩漢禮制亦是“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17]。漢平帝納后時親迎前的告廟之儀,應當也是推自《士昏禮》而加繁所成。綜合前引先秦至兩漢的幾則史料來看,或可推測,古禮所謂親迎告廟,并非限定于親迎當日舉行,而是在親迎事宜既定后到親迎前的時間段內,擇日將親迎之事告于祖禰即可。
(二)唐代親迎告廟之儀注
唐以來,由于官修禮典的系統化及民間書儀的豐富,婚禮各儀節儀注更加明確。唐《開元禮》中規定了自天子至品官的婚儀,其中親迎前告廟儀節的設置如下(表1):

表1 《開元禮》親迎告廟儀注[18]
天子及太子,親迎前告廟并非在親迎當日,而是需要特擇一日行之。這一做法也合于漢以前所見的事例。親王以下至品官,親迎告廟安排在親迎當日的黎明時分,而醮子往迎依禮是在黃昏時,兩個儀節之間實際上是有相當一段時間間隔的。需注意的是,親王納妃只注妃父告廟、公主降嫁只注婿父告廟,亦即除天子與皇太子外,皇室成員無論男女,親迎當日皆無謁祖之儀,品官婚則男女兩家都需告廟。此外,《開元禮》中還注明“無廟者告于正寢”,肯定了告祖儀式不限于在祖禰之廟中舉行,這也可看做是對《儀禮》經文中男家告祖醮子在寢而不在廟的一種解釋。
唐代民間婚禮的告祖儀式,則可從敦煌書儀中窺其一斑。《大唐吉兇書儀》(S1725)中所載初唐禮俗,在醮子往迎前有“啟祭先人”之儀:
成禮法,先須啟祭先人,祭法:在于中庭近西置席,安祭盤,祭人執酒盞曰:“敬啟云考妣之靈:(長子、小兒)甲某乙年已成立,某氏不遣,眷成婚媾,擇卜良辰,禮就朝吉,設祭家庭,眾肴備具,伏愿尚饗!卑者再拜。”婿父在庭前,面向南坐,兒面向北立,父告子:“自往迎汝妻,承奉宗廟。”子答曰:“維,不敢辭。”再拜如出。[19]
與《開元禮》不同,《大唐吉兇書儀》所載“成禮法”,告祖與醮子往迎兩個儀節的連接顯然要更加緊密。這或許是由婚者身份、等級不同造成的,抑或民間婚禮在實際操作中為行簡便,而將“親迎告廟”與新婿臨行前的“告出”之禮合二為一了。遺憾的是《大唐吉兇書儀》中只記錄了男家告祖之儀,未見女家儀注。結合杜友晉《新定書儀鏡》(P2619④)與張敖《新集吉兇書儀》(P2646)等書儀中所錄嫁娶祭文來看,男女兩家祭文的結構內容基本一致,儀程也應類同。以《新定書儀鏡》所載嫁娶祭文為例:
男家祭文:維年月日朔,某謹薦少牢之奠(亦云清酌),敢昭告于祖考(考妣)之靈,某子某乙、年已成冠,禮有納聘,宗繼先嗣,與某氏結姻,克用今日吉辰,不敢自專,謹以啟告,伏愿聽許,伏惟尚饗。某等再拜!
女家祭文:維年月日,某謹薦少牢之奠(清酌),敢昭告于祖(考妣)之靈,第某女年及初笄,禮適某氏,五禮已畢,克今日吉辰,不敢自專,謹以啟告,伏愿聽許,伏惟尚饗。某等再拜![20]
祭文的主要內容是昭告祖先親迎的具體事宜,即某年月日、家中第幾子(女)將與某氏成禮。祭文中在報告完親迎事宜后,特言“不敢自專,謹以啟告”,直觀地表達了在親迎之事上對家族先祖意志的尊重。這也是在儀程設計上,應將親迎告廟設置在親迎當天所有儀程開始前的原因。
(三)宋元時期親迎告廟之流變
宋《政和五禮新儀》中所列自天子納后至庶人娶婦的告廟儀節如下(表2):
《政和五禮新儀》所定婚儀大體沿襲《開元禮》,在親迎告祖這一儀節上,又更加清晰。自皇太子以下至品官,男女兩家親迎前都要祭告先祖,太子及帝姬是提前擇日而告,其他則是在親迎當日黎明告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政和五禮新儀》中設有“庶人婚儀”,這是庶人禮第一次被納入到官方禮制體系中。從表2可以看出,庶人親迎告祖之儀,與品官以上仍有區別:即男家言“再拜而告”,女家卻不明言“告廟”,只說“受禮”。然既受禮于先祖,則亦當有告祖之儀。

表2 《政和五禮新儀》親迎告廟儀注[21]
另一方面,為了滿足士庶階層對禮的追求,兩宋時期還涌現了一批以司馬光、程頤、朱熹等為代表的家禮撰著者。他們以古禮為本,并結合時俗,試圖制定出更具有廣泛適用性的婚儀規范。就婚禮告廟的具體時間與儀程,自司馬光《書儀》、程頤《婚禮》到呂祖謙《家范》、朱熹《家禮》,亦根據制定者對古禮與時俗的理解而各有取舍,表3即為諸書告祖儀節整理輯錄。

表3 宋代私修禮書所載婚禮告廟儀注[22]
從表3可以看出,四人分別對婚禮中的告祖儀程做了不同的設計。歸納而言,親迎當日告祖時間節點的設置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整個親迎儀式啟動前(男女兩家各自告祖);第二個,婿抵達女家后(婿見女氏先祖);第三個,婦抵達男家后(新人共拜男家先祖)。三個時間節點告祖的意義,各有側重:親迎儀式啟動前的告廟,是行事前的祈安之祭;婿見女家先祖,是受女謝祖之禮;婦至男家共拜祖禰,據司馬光言,則是以時人“拜先靈”之俗代替古禮三月廟見的成婦之禮⑦。其中第一個為古禮,第二、三個則是時人所行之俗禮,四人在古禮與時俗之間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調和。筆者認為,朱熹的安排要更為合宜。唯需補充的是,盡管《家禮》“昏禮”篇中沒有專門提及,但據其“祠堂”篇中“出入必告”之制[23],親迎當日新婿為逆婦而出入家宅時,亦當向先祖行告出、告返之禮。
朱熹《家禮》厘定的親迎告廟儀程,對宋元以后所行婚禮習俗有很大影響。考察宋元時期流行的民間日用類書,可以發現其中婚禮儀注多依《家禮》。但同時也應當注意到,在作為理想儀程規范的儀注之外,類書中“祝文致語”等更偏重于實際運用的禮辭集錦篇目,卻多不見親迎前的告廟祝文,只收錄新人共拜先祖神祇的“拜堂致語”。結合《東京夢華錄》與《夢粱錄》中嫁娶儀節的記載⑧,可知民間婚禮在實際操作中也有同樣的儀節簡省的情況。
(四)明清時期親迎告廟之儀注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國之初即下令“民間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禮》”[24],此后朱棣在永樂(1403-1424)年間又“頒《文公家禮》于天下”[25]。《明集禮》中,品官以上告祖婚儀大體沿襲唐宋之制,庶人婚則主要遵循朱熹《家禮》,將《明集禮》與《政和五禮新儀》中庶人親迎告祖儀節進行對比,可以發現《明集禮》不再采用后者女家“受禮于禰位前”的描述,而是依據朱熹《家禮》,明確規定了女家主人須“告于祠堂”(表4)。

表4 《明集禮》親迎告廟儀注[26]
至清代,由于民族文化與禮儀傳統的不同,情況則又有改變。從《清通禮》所定婚儀來看,皇室成員中,只有皇帝大婚時需在親迎前一日告廟,此外皇子、公主、親王等皆未言及告廟。品官士庶婚禮,則采取了《白虎通》等對《士昏禮》的解讀,女家需“告于廟”或“告于寢”,男家只言“醮子”而未明言“告廟”(表5)。
清代民間婚禮親迎告廟的實際情況,亦可從流行于民間的日用類書來考察。分別刊行于雍正、乾隆年間的《家禮會通》與《酬世錦囊》中,均載有親迎告祖之儀節。從二書所載親迎儀節來看,皆遵循《家禮》之原則,男女兩家分別在醮子、戒女前告祖(表6)。

表6 《家禮會通》與《酬世錦囊》所載親迎告廟儀注[28]
可以認為,正如《家禮》對《明集禮》產生的影響,《家禮》自明初以來,不僅被納入官方禮制,也由于政府的認可與推崇,在民間得到了廣泛的普及;而《家禮》中親迎告祖儀節的設計理念,對后世民間婚禮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⑨。
四、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明確,男女兩家在親迎前告廟確為自先秦起即被奉行的古禮。漢唐以降,在官民的禮典儀注和禮儀實踐中,根據婚姻主體的身份不同,親迎告廟的具體時間也或有不同。具體來說,天子及皇族,多在親迎前期特擇一日告廟,品官庶人則在親迎當天黎明告廟。此外民間亦有在子女臨行前告祖的情況,此應視為是將親迎專有的告廟儀式與“告出”之通禮合并而行。此外,司馬光、朱熹等宋代家禮撰著者,依據各自對禮俗的理解與取舍,對親迎告祖儀節做了不同的設計。朱熹《家禮》厘定男女兩家各自在親迎儀程開始前告祖,將當時已被混淆的親迎告廟與告出告返之儀又重新區分開來,并對明清乃至近當代民間親迎禮俗產生了深遠影響。
盡管形式名目不同,自先秦以來親迎告廟儀式事實上一直延續發展著。在當代許多地區,雖然家廟、祠堂等傳統祭祖設施已經衰沒,但仍保留著新婚之日向廳堂中供奉的先祖牌位祭拜,甚至專程赴先祖墓地祭告的習俗。對于親迎告祖的重視,從儒家傳統文化基因的角度看,婚姻關系著兩個家族的聯結與傳承,因此在傳統婚禮中,家族意志自然而然地被擺在更為重要的位置,新人通過與家族精神的溝通與融合尋求庇佑,從而獲得身心安頓。另一方面,這也是由婚禮作為人生過渡禮儀的神圣性所決定的。過渡禮儀往往通過一系列神圣的器物、語言及行為等構建一個神圣時空,以引導儀式主體完成人生角色的轉變,幫助其順利過渡到即將到來的人生新階段。就婚禮而言,目的在于通過一整套“敬慎重正”的儀式⑩,幫助新人確立正確的家庭倫理觀念,這對游移于古今中西而取舍失據的當代婚禮儀式重建無疑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注釋:
① 《儀禮正義》:“昕,陽始也。昏,陰終也。受讀如受命文考之受,謂命于禰廟,然后行事也,蓋據壻家言之。”見(清)胡培翚.儀禮正義[M].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203-204.
② 《禮書通故》:“本《記》言‘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昏謂親迎時,昕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五者,說見賈疏。受諸禰廟即告廟也。”見(清)黃以周.禮書通故[M].中華書局,2007:246.
③ 《儀禮私箋》:“男家當遣使醮子及使者反命之時,亦必于廟之戶西設筵右幾以依神,使若祖父臨之,然后行事決矣。如此則兩家于六禮,直以祖父臨之,不止于一告,使祖父知有此事而已。故其致辭并稱‘某有先人之禮’,言此禮由先人非由已也明乎。”見(清)鄭珍.儀禮私箋[C]//.《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9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5.
④ 寫卷P2619,原定名《殘書儀》,譚蟬雪據P3849等校驗,認為P2619實為京兆杜友晉《新定書儀鏡》,是盛唐之作。參見譚蟬雪.敦煌婚姻文化[M].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28.
⑤ 《政和五禮新儀》庶人昏儀“親迎”節中,言女家“主人受禮如請期儀”;“納成請期”節中,則言“主人受禮如納吉之儀”;“納吉”節中,言“主人受禮如納采之儀”。亦即自納采以下,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女家主人受禮之儀皆同于納采。考庶人昏儀“納采”節:“掌事者設禰位于廳事,南向,主人受禮于神位前,迎媒氏于門外。”見(宋)鄭居中等撰.政和五禮新儀[C]//.中華禮藏·禮制卷(總制之屬第3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1108.
⑥ 呂祖謙《家范》只記親迎前一日陳設與親迎當日儀注,故此表內未錄其前五禮及親迎后之告廟儀程。
⑦ 司馬光在新人共拜影堂一節后注曰:“古無此禮,今謂之‘拜先靈’,亦不可廢也。” 其后又曰:“古有三月廟見之禮,今已拜先靈,更不行。”見(宋)司馬光.司馬氏書儀[C]//.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儒藏(精華編第73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062、1065.
⑧ 《東京夢華錄》載北宋婚儀,未提及親迎前告廟之儀,只在新婦至男家后,新人要一同參拜家廟:“婿于床前請新婦出……至家廟前參拜。”見(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C]//.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31;至南宋《夢粱錄》,則不僅要參拜家廟,還要拜堂次家神及在場諸親:“參拜堂次諸家神及家廟,行參諸親之禮。”見(宋)吳自牧.夢粱錄[C]//.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306.
⑨ 明清地方志中所載冠婚喪儀,大多合于《家禮》,直言“遵文公家禮”者亦不在少數。關于《家禮》對明清以來民間禮儀的影響,亦可參照楊志剛.《朱子家禮》:民間通用禮[J].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4):40-46.
⑩ 《禮記·昏義》:“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M].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1980:1680-1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