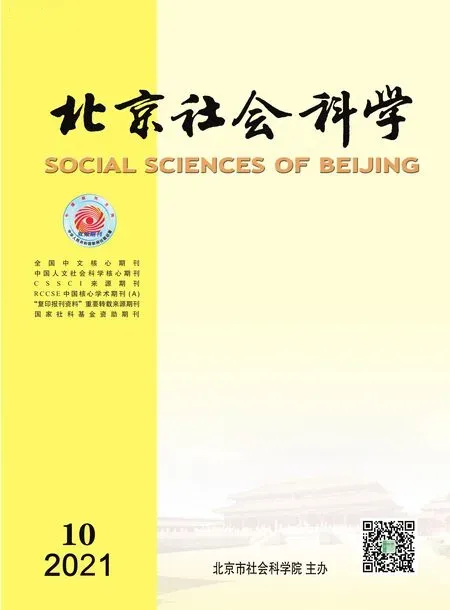論王績文學史地位的升格及價值建構
龔 艷
一、引言
王績以《野望》一詩千古留名,王夫之贊曰:“天成風韻,不容淺人竊之。”[1]聞一多稱該詩“不愧是初唐的第一首好詩”。[2]王績是初唐的重要詩人,現在看來似無疑義。然而,王績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被認同。兩《唐書》將王績列入《隱逸傳》,便是明證。這種局面直至高棅的《唐詩品匯》選錄王績詩才被打破。其后,“詩必盛唐”的詩學觀及建設“新文學”的思潮共同完成了對王績詩學價值的建構,王績的文學史地位遂得以確立下來。這背后傳達的,是一個詩人的價值始終與時代意識相維系,詩人只有符合時代的需要才能被文學史接納,而文學史也在主動建構出一個符合時代意識的詩人。以王績為個案,可以審視其他作家在文學史上的接受問題,亦能窺見作家與文學史之間進行的雙向互動。這有助于豐富我們對文學史、作家、作品這三者之間相互關系的認識。
二、隱節既高:王績隱士人格的凸顯與詩學價值的掩弊
王績詩在唐代并沒有獲得普遍的價值認同,唐代文人欣賞的是王績作為隱士的精神志趣。王績的詩作由其友人呂才蒐輯成編,并為之作序。呂才在序傳中娓娓敘述王績的仕隱經歷以及“縱意琴酒”的風流韻事,對其詩文只字未評。時隔百余年,陸淳閱覽王績的文集后,為突出王績“樂天之君子”的形象而將文集里的“有為之詞”大幅刪減。二者皆為王績的文集作序傳,卻不關注其詩文,不是很可怪嗎?這說明,他們對隱士王績的認可遠大于對詩人王績的認可。這種認識在唐代其他文人身上亦能得到證明,審察唐人稱引王績的詩文,可見唐人對王績的接受多集中在隱士形象的層面,如白居易贊賞王績的隱行,其《九日醉吟》云:“無過學王績,唯以醉為鄉。”[3]柳宗元向往王績的東皋之隱,其《游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云:“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皋耕。”[4]劉禹錫在《王公神道碑》中評價王績:“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5]劉禹錫之言充分證實了王績在兩百年間都以高尚的隱士聞名。《舊唐書》將王績列入《隱逸傳》,是對王績隱士身份的蓋棺定論。王績的隱士身份在歷史定格的背后,顯示的是唐代主流文人群體對王績詩的輕忽。由此可以說,在唐代文人眼中,王績的身份主要是一位隱士,而不是詩人。
到了宋代,王績的隱士形象進一步向士人群體滲透,而其詩的價值仍處于被遮蔽的狀態。隨著意識形態領域內儒釋道三教的融合,隱逸成為宋代時代精神中被普遍推崇的價值觀念之一。王績的隱士形象引起宋人的普遍注意,其中的代表便是蘇軾。他在詩作中多次稱賞王績的隱逸之行,甚至將其與陶淵明并舉,如其詩《和陶歸園田居》云:“斜川追淵明,東皋友王績。”[6]蘇軾不僅欣賞陶淵明的隱者高行,對陶淵明的詩作亦不遺余力地贊美。蘇軾雖欣賞王績,卻未逸出隱逸的范疇,如“且向東皋伴王績,未遑南越吊終軍”[7](《會飲有美堂答周開祖湖上見寄》),“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8](《次韻朱光庭初夏》)。蘇軾在《書東皋子傳后》中盛贊王績的風雅逸趣,對其詩文不置可否。從此可以看出,蘇軾主要接受的是王績作為隱士的一面,而非其詩作所具有的審美內涵。蘇軾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宋代主流文人群體對王績詩的態度,翻檢宋人述及王績的話語,王績大多是以隱士的面貌而出現,王禹偁云:“伯倫酒德,披文見意。王績醉鄉,含章遁世。”[9](《著作佐郎贈國子博士鞠君墓碣銘》)劉克莊:“王績何曾醉?劉蕡本不風。”[10](《再和四首》)我們看到,宋人對王績的接受仍停留于隱士形象的層面,這背后體現的是宋人對王績詩作本體價值的忽視。
概而言之,王績在唐宋時期以隱名顯世,其詩名不顯。唐宋文人雖然在詩文中流露出對王績的欣賞,但立足點在隱逸的范疇之內。陶淵明最初亦被視作隱士,至其詩獲得廣泛認同后,詩人便成為他的第一屬性。王績亦如此,其詩學價值未獲得唐宋主流價值觀念的認同,隱士便是他的第一身份。至其詩學價值逐漸得到認可后,王績的隱士身份遂開始受到質疑,如四庫館臣云:“《新唐書》列之于《隱逸傳》,所未喻也。”[11]在后來的文學史中,王績亦被當作初唐的重要詩人進行書寫。王績的隱士形象被建構與解構的過程,其實就是王績的詩學價值被發現與構建的過程,而這一過程需要依靠學術思潮的加持來完成。
三、肇啟盛唐:“詩必盛唐”的學術思潮與王績詩學價值的構建
南宋嚴羽提出以盛唐詩為宗的理論主張,再經由明代復古思潮的推動,盛唐詩逐步成為詩學領域的典范,如宇文所安所言:“以盛唐詩為正統的觀念時不時受到謹慎地限定或激烈地反對,但它始終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認識,其他見解都圍繞著它做文章。”[12]誠然,在盛唐詩成為詩學領域的權威后,之后的詩學主張或是“詩必盛唐”的理論產物,或是對此的延伸與反撥,基本都是“圍繞著它做文章”。在這一學術背景下,明清文人挖掘出王績詩與盛唐詩的詩學共性,視其為盛唐之音的先聲,帶來王績在文學史上的關鍵轉變。
高棅《唐詩品匯》選錄王績詩若干,將其列于“正始”,是王績進入詩學批評領域的關鍵。《唐詩品匯》之前的唐詩選本甚少選王績詩。可見的如元代楊士宏《唐音》選錄了一首王績詩,并歸于“遺響”。較之于《唐音》,王績在《唐詩品匯》中的詩學地位有了明顯提升。《唐詩品匯》五言古詩類選王績《古意》《田家》,五言絕句類選王績《過酒家二首》,五言律詩類選王績《野望》,五言排律類選王績《贈學仙者》。從數量而言,王績詩一共入選六首;從詩體上說,所選詩涉及王績所作五古、五絕、五律、五排;從定位上而論,所選王績詩全部歸于“正始”之列。由此可見,高棅已經開始重視王績的詩學價值。
王績詩之所以得到高棅的重視,是因為高棅具有建立在詩歌本體價值上的發展意識。高棅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唐詩發展的各個階段,而是著重于把握唐詩各個階段之間的縱向聯系。因此,初唐詩作為盛唐詩發展的起始階段也具有了關鍵意義。我們看到,高棅在楊士宏《唐音》的基礎上有意加大了初唐詩在唐詩史上的權重。首先,《唐音》的“始音”部分僅選王、楊、盧、駱四家詩,而高棅增錄了大量初唐詩人;其次,高棅將“始音”之名易為“正始”,“正”字之冠顯示出高棅對初唐詩格走向盛唐正格的肯定。[13]王績詩作為初唐風格的組成部分受到高棅的重視在情理之中,但更重要的是,王績詩與盛唐詩具有某些詩學共性。從高棅選錄的王績詩可見出,高棅正是發現了王績詩具有與盛唐詩相似的詩體特征,才有意識地突出了王績的詩學地位。如高棅所選《野望》一詩,已初具唐律的詩體特征,可視作“唐代五律的開新之作”;[14]《過酒家》一詩“渾是上繼嗣宗、淵明,下啟王維、李白的”。[15]由此見出,選錄王績詩是高棅建立以盛唐詩為中心的唐詩發展體系的結果。高棅選錄王績詩的意義之一在于將其引入詩學批評領域。《唐詩品匯》在后世基本成為士人必讀的唐詩選本,如胡應麟云:“至明高廷禮《品匯》而始備,《正聲》而始精,習唐詩者必熟二書,始無他歧之惑。”[16]自《唐詩品匯》出,明代幾部重要的唐詩選本如《唐詩選》《唐詩歸》《唐詩鏡》皆收錄王績詩作,使得王績在詩學領域的地位日益穩固。意義之二在于高棅將王績置入唐詩發展史上的“正始”之位,奠定了后人構建王績詩學價值的基礎。后人延續了高棅的詩學邏輯,在詩律和詩風上發現王績詩對盛唐詩的貢獻,從而完成其詩學價值的建構。
楊慎將律詩上溯至王績,指出其詩乃“沈、宋之先鞭”,“詩律又盛”成為明清文人肯定王績詩學價值的重要方面。前人往往將律詩的成型歸功于沈、宋,楊慎則認為王績在沈、宋之前已開唐律之先聲。楊慎明確指出王績在律詩上的肇啟之功,其評曰:“王無功,隋人,入唐,隱節既高,詩律又盛,蓋王、楊、盧、駱之濫觴,陳、杜、沈、宋之先鞭也。”[17]楊慎所謂的“陳、杜、沈、宋之先鞭”,正是著眼于王績在律詩發展進程中起到的承啟作用。首先從七律來講,王績的《北山》已基本符合七言律的詩體特征,該詩云:“舊知山里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游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云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18]前六句在屬對上基本符合七言律的要求,只不過后兩句雜以五言。楊慎將此詩視為“七言律之濫觴”,確為中的之論。其后的學者亦認識到這一點,王夫之直言“七言律詩應當以此為祖”:“如此首前四句,句里字外俱有引曳騫飛之勢,不似盛唐后人促促作轅下駒也。故七言律詩亦當以此為祖,乃得不墮李頎、許渾一派惡詩中。”[19]趙翼亦認為該詩:“皆七言屬對,絕似七律,惟篇末雜以五言二句耳。”[20]再者,王績的《野望》一詩幾乎已是成熟的五言律詩,被普遍視為唐代五言律詩的開山之作。舊題李攀龍《唐詩選》承繼《唐詩品匯》而來,[21]不過在《唐詩品匯》的基礎上做了一番嚴格篩選。其結果是王績的《野望》不僅被保留,且位于五言律詩開卷第一首,緊鄰其后的是楊炯、王勃、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等人。《野望》的詩體價值亦得到清人的肯認:王夫之《唐詩評選》五言律詩選錄《野望》并評之“天成風韻,不容淺人竊之”,[22]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認為《野望》“五言律,前此失嚴者多,應以此章為首”,[23]姚鼐《今體詩鈔》亦列《野望》為五言今體詩開卷第一首。由此可以看出,王績的“詩律又盛”獲得了明清文人的普遍認同。楊慎通過建立王績與沈、宋的詩學線索,打通了王績詩與盛唐詩的聯系,從而將王績在唐詩發展歷程中的位置具體化。王績肇啟唐律,促進律詩在沈、宋等人手中定型,最終迎來盛唐詩的高潮,這便是王績詩學價值得以生成的理論邏輯。
何良俊則指出王績詩呈現出勁挺、真率的面貌,直與盛唐詩的氣息相通。其《四友齋叢說》對王績詩如此評價:
唐時隱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為第一。蓋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于性情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24]
何良俊以“盡洗鉛華”評價王績詩,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王績詩擺脫辭藻的浮華,具有“質而不俗”的詩歌風貌。唐初詩壇彌漫著堆砌辭藻之風,如聞一多先生言:“唐初是個大規模征集辭藻的時期……連詩的制造也是應屬于那個范圍里的。”[25]王績卻掙脫時習,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子,其《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為》一詩:“映巖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26]語言素樸自然、清新明快,而韻味自顯,甚至“有點盛唐山水詩的氣味”。[27]黃汝亨覽其詩文后,曰:“吾輩凈眼讀一過,甚為爽然勝讀《鵩鳥賦》遠矣。”[28]曹荃讀其詩,亦覺“如吸風飲露,疏快宜人”。[28]所謂的“爽然”“疏快”正是王績詩質樸無華的體現,而這種藝術特質直接與之后的審美風尚相接。“四杰”與陳子昂等人在創作中掃除雕琢風氣,而回歸內容的充實便是印證。二是王績詩抒發真情、興寄深遠,呈現出遒勁的詩歌風貌。這一點可以參考何良俊對王績的另一段論述: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無功《古意》、李伯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于氣運哉?唐人詩如王無功《山中言志》……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后人,便有許多緣飾。[29]
首先,何良俊以“勁挺”“激昂”“真率”等詞語來評價王績詩,表明王績詩的風貌已經超越了初唐而與盛唐詩的氣息相通。再者,所謂的“尚在陳子昂之前”,則點明了王績的詩學史意義。陳子昂提出的興寄與風骨,為盛唐詩做好了思想上的準備。而王績詩在此之前就已隱含興寄與風骨的創作特征,如高出《黃刻東皋子集序》認為其詩“喻旨目前,高寄象外,閑適自得,興遠理微”,[30]《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其詩“《石竹詠》《贈薛收詩》,皆風骨遒上”。[31]如果我們認同陳子昂是促進盛唐詩到來的關鍵人物,那么“王績—陳子昂—盛唐詩”的邏輯關系就可以打通,王績對盛唐詩的肇啟之功也可以落實。只要盛唐詩的核心地位存在,這種邏輯關系便能夠成立。如清人吳喬言:“王績《野望》詩,陳拾遺之前旌也。”[32]《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古意》六首,亦陳、張感遇之先導。”[33]皆通過構建王績與陳子昂的承接關系,來確立王績的詩學價值。由此可見,王績的詩學價值取決于其詩對盛唐詩的先導作用,而王績的詩學地位則是由他在盛唐詩發展進程中所處的具體位置來明確的。
王績從隱士形象到作為肇啟盛唐之音的關鍵詩人為世人肯定,其在文學史上地位的轉變正傳達出主流學術思潮對作家價值的融入與建構。明清文人對王績詩學價值的構建主要沿著兩條線索:第一是發掘王績詩對肇啟盛唐詩所起的作用,這體現在王績詩在詩體和風貌上促進了盛唐詩的形成;第二是通過串聯王績詩與盛唐詩的詩學線索將其在詩學史上的位置具體化,這體現在王績揚沈、宋之先鞭,啟陳子昂之濫觴。總之,王績詩的價值是依靠其詩與盛唐詩的詩學共性來獲得。四庫館臣云:“(王績詩)能滌初唐俳偶板滯之習,置之開元、天寶間弗能別也。”[34]這是官方在以盛唐詩作為審美參照的前提下,對王績詩給予的高度肯定。可以說,明清文人在“詩必盛唐”的學術思潮的影響下,以盛唐詩的價值標準對王績的詩學價值進行了建構,從而使得王績完成了其文學史地位的關鍵轉變。
四、反抗宮體:建設“新文學”與王績文學史地位的奠定
明清文人將王績詩引入詩學批評領域,明確其對盛唐詩所做的貢獻,無疑促進了王績文學史地位的提高。然而,王績在初唐詩壇的重要性并沒有體現在早期的文學史書寫中。早期的大多數文學史著作對王績的著墨皆極其有限,對其人其詩皆不作過多評價。茲舉王夢曾《中國文學史》(1914)為例,他專設一節探討古今體詩格之成立,論及除王績以外的多位初唐詩人,將唐代詩格之始成歸于“四杰,陳、杜、沈、宋整齊之功也”。[35]這說明在早期文學史家的眼中,王績的詩學地位尚不足以在文學史中留下重要筆墨。客觀而言,王績的文學史地位雖有所提高,但其對盛唐詩的貢獻始終難與陳、杜、沈、宋等人比并。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1928)是王績在文學史發展歷程中的又一轉捩點。在《白話文學史》中,胡適將王績作為初唐的重點詩人進行論述,將其視為七世紀中出現的“三五個白話大詩人”之一,大大提升了王績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僅如此,他還改變了此前文學史著作中突出書寫“四杰”的模式,將“四杰”作為“王績”的附論。可見,王績在文學史中由之前的一筆帶過轉變為專門的論述,由初唐無足輕重的詩人一躍變為最值得書寫的詩人之一。胡適云:“開元天寶的文學只是少年時期,體裁大解放了,而內容頗淺薄,不過是酒徒與自命為隱逸之士的詩而已。以政治上的長期太平而論,人稱為‘盛唐’;以文學論,最盛之世其實不在這個時期。”[36]顯然,胡適不認同以盛唐詩為標準的價值觀念。那么,胡適是如何對王績的詩學價值進行重建的呢?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以“白話”作為文學史書寫的核心內容和價值標準,試圖沖破傳統的文學史觀以建立新的文學觀念,是王績詩完成價值重構的關鍵。新文化運動以來,傳統的文學觀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評與挑戰,“整理國故”“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幾乎成為學界的主流話語。胡適開創性地提出“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理論主張,成為王績詩進行價值重判的契機。首先,胡適以“白話”作為文學史書寫的核心內容,意味著評定作家的價值標準發生了根本變化。胡適所謂的“白話”指的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不加粉飾的話”以及“明白曉暢的話”。[37]從這樣的價值標準出發,王績就不再是盛唐之音的肇啟者,而是陶淵明的繼承者,因此被視為文學史上的“白話大詩人”之一。其次,在文化運動的時代語境下,胡適認為王績詩具有反抗宮體的精神內涵,這與倡導革命的胡適在精神上產生了共鳴。《白話文學史》的寫作目的不在于文學史本身,其牽系的是作者對傳統價值觀的反抗以及追求進步的革命意識。[38]胡適所構建的白話文學是為了與“傳統的死文學”相對立,宮體詩作為“死文學”陣營的一員必然成為胡適的革命對象。因此,胡適不會建構王績詩與盛唐詩的聯系,而是將王績上溯至陶淵明,尋求二者在反抗宮體上的一致性。審視胡適對王績的評價,他將王績視作陶淵明的同盟,如王績“有點像陶潛,他的詩也有點像陶潛”,[39]他的詩“似是從陶潛出來的,也富有嘲諷的意味”。[40]陶潛是胡適最推崇的詩人之一,其原因在于陶潛的詩具有極強的革命性,如胡適所云:“陶潛的詩在六朝文學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一切辭賦化、駢偶化、古典化的惡習氣都掃除的干干凈凈。”[41]王績在宮體籠罩的詩壇獨樹一幟,所謂的“有點像陶潛”指的是王績詩與陶淵明詩共有的革命意味,傳達的正是胡適對王績反抗宮體的革命精神的肯定。由此觀之,無論是從王績詩的白話特點而言,還是就王績反抗宮體傳統的進步意義而言,胡適將王績提升至文學史上的顯要位置都具有必然性。在建設新文學的語境下,這是符合時代需要的結果。因此,王績被視為陶淵明在初唐的繼承者,成為文學史上必不可少的詩人之一。
無論是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還是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都深深影響了其后文學史的寫作。隨著新文化運動的不斷深入,傳統文學史觀逐步被取代,胡適及其《白話文學史》所代表的文學進化觀念為文學史家普遍認同。余冠英先生在論及文學革命后文學史的寫作通例時斷言:“以影響重大論自然該首推胡適之白話文學史,這本書表現文學革命以后的新觀念并指出中國文學史上的主要通例,實為劃時代的著作。”[42]胡適創建的文學史書寫范式以及倡導的文學觀念對文學史的寫作格局都造成了重大影響。經過胡適對王績詩學價值的建構以及對其革命精神的凸顯,之后的文學史著作幾乎都肯定了王績在初唐詩壇的重要性,尤其強調王績在反抗宮體上具有的進步意義。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1931)認為王績“因崇拜阮陶而使他的作風超脫齊梁而復于魏、晉”;[43]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認為王績對詩壇的重大貢獻是在梁、陳風格籠罩之時以澹遠糾正濃艷,并贊賞王績其人“行事甚類陶淵明”;[44]譚正璧《新編中國文學史》(1936)則云王績詩“甚者或可比擬陶淵明”;[45]陳子展《唐代文學史》(1944)認為“王績的人格和詩格都深受陶潛的影響”,其詩能突破“當時體”的桎梏。[46]可見,這一時期的文學史家們基本延續了胡適的思路,將王績視作陶淵明的繼承者,大力贊揚王績對當時詩壇的反抗。其中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1941)專列一節論述“王績與王梵志”,對王績的書寫最為典型:
他的作品在當日的詩壇,卻又是最革命的了。如果在潘岳陸機以后,覺得陶潛作品出現的可貴,那末在齊梁陳隋的宮體詩以后,有王績的作品,也是一樣的可貴。在藝術的價值上,王績雖比不上陶潛,然在其作品的情調與對當日的詩風的反抗,卻是一致的。在這一點,王績在初唐詩壇的地位,是存在著不可搖動的重要性……他卻完全洗盡了宮體詩的脂粉氣息,充分地表現了他個人的生活和情感……這些詩是陶淵明的承繼者,也就是王維、孟浩然作品的先聲。如《野望》一首,完全是唐律的格調,比起徐陵、庾信們的詩篇來,不要說內容是全異其趣,就是在聲律體裁方面,也更為進步更為成熟了。[47]
劉大杰認為王績的可貴之處在于對時風進行了“反抗”和“革命”,因而其地位在初唐詩壇具有“不可搖動”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劉大杰還指出了王績詩上承陶淵明,下啟王、孟一派,在詩史上具有嗣晉開唐的重要意義。這一見解融攝了明清以來學者們對王績的認識,體現出更為通達和進步的理論意識。經過胡適及之后的文學史家對王績詩學價值的建構與闡釋,王績基本奠定了其在初唐詩壇不可撼動的重要地位。
強調王績對宮體詩的反抗,并突出其文學史地位,是時代主流文化思潮下文學史寫作的必然選擇。胡適將王績溯源至陶淵明,對其反抗宮體傳統的詩學價值進行挖掘與構建,實則是建設“新文學”的策略之一。當時學界的主流思潮是建設“新文學”,打破傳統的文學觀念,作為“死”的、“僵硬”的宮體詩必然成為革除的對象。王績的白話詩作為宮體詩的對立面,不僅符合“新文學”的審美標準,而且具有反抗傳統的精神內核。因此,強調王績的詩學價值就是彰顯“新文學”的價值,亦是強調文學革命的進步意義。與其說是他們選擇了王績,倒不如說是時代選擇了王績。可以說,王績文學史地位的升格是學者們以新理念重寫文學史的結果,亦是合乎時代意識以及順應文學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五、結語
一個作家的價值由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價值構成,這兩者并不處于完全一致的價值系統。王績的文學價值是有限的,相比起陶淵明和盛唐諸人,王績并沒有為詩歌的藝術世界增添多少創新的內容,這也是其詩在唐宋時期未獲得認可的主要原因。就文學史價值而言,他為掃除宮體詩的障礙做出了貢獻,又在詩體未純之時開盛唐先聲,其價值不言而喻。明代以后文人正是從文學史的視角審視王績的詩學意義,從而完成其詩學價值的建構。
王績的詩學價值是順應學術思潮的發展和適應時代的思想需要被構建而出的。王績詩的文本內容是恒定的,而其是否具有價值就在于能否與時代的價值觀念相融合。王績起初詩名不顯,原因在于其詩不符合唐宋詩學的主流價值標準。在“詩必盛唐”的學術思潮的影響下,明清文人以盛唐詩的價值標準審視王績詩,發現并建構出王績詩肇啟盛唐之音的詩學價值。當文學革命成為時代的主流思想意識時,王績又成為“新文學”的代表并被融入反抗宮體的革命內涵。王績詩學價值被構建的過程,其實就是后人不斷將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注入其中的過程。從此可以看到,文學史具有能動性,會主動吸收和容納符合文學史發展規律的因素,同時亦會摒棄沒有融入于文學史發展歷程的作品。到底是作家和作品構成了文學史的內容,還是文學史發明和構建了作家及作品,這其中主客關系的互動和轉化值得我們反復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