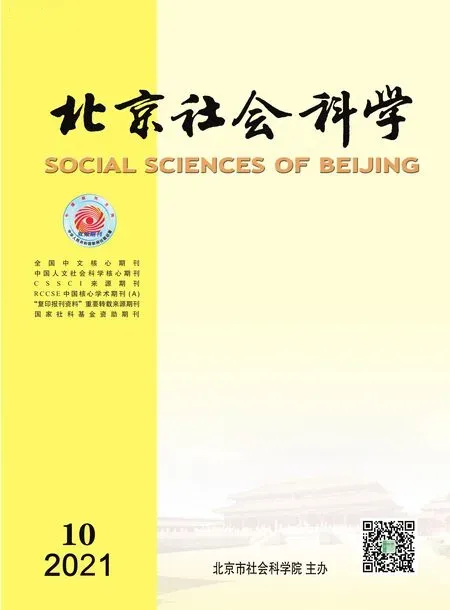生命歷程視角下鄉城遷移老年人的市民化
——基于甘肅省天祝縣的調查
切 排 余吉玲
一、引言
生命歷程理論主要探討社會事件、歷史進程、文化變遷與個體成長和發展軌跡的互動關系。個體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存在,而是嵌入在形形色色的社會關系之中,并與時空、社會制度、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相互影響。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如成年、結婚、生子、就業、遷移、退休等)受社會文化的塑造,社會制度、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影響人們的人格和行為。[1]特別的歷史事件,構成生命歷程的轉折點,造成個體生命軌跡的延續或斷裂。[2]然而個體不是被動地、機械地受社會文化的規范與制約,而是會根據社會情境能動性地改變人生命運。生命歷程理論,強調的是社會結構和個人選擇在時間作用下的相互影響。[3]它的意義在于借助“時間”這個關鍵概念將微觀個體發展與宏觀社會文化環境有機統一起來。生命歷程理論對移民的研究,旨在探討“遷移”的人生經歷對個體生命軌跡產生的重要影響,研究個體如何通過調適與再建構以適應和融入新的地域空間、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以及社會文化;社會結構反過來如何形塑個體。[4]對老年群體的研究,主要考察重大的生命事件、早期人生經歷積累對老年異化、社會地位不平等,[5]晚年生活質量以及身體健康的影響。[6]個體早年的人生經歷和生命事件會影響晚年的遷移行為,老年人生命歷程中的遷移行為受具體社會文化環境影響。[7]
國內利用生命歷程理論范式考察時代變遷、政治變革以及重大社會事件對特定人群、特定生活領域的影響,如“文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包產到戶”、改革開放、允許農民進城等特殊的歷史事件和劇烈的社會變遷造就了處于特定時代人們的獨特命運。在人口大流動時代,從生命歷程理論的視角考察流動對農民工群體社會行為產生的影響。[8-9]還有研究考察兒童期留守經歷或隨父母遷移對新生代農民工成年早期重大生活事件的影響。[10]遷入城市對農民工個體生命軌跡、身份認同、社會角色及其家庭結構、規模與家庭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利用生命歷程范式分析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流入城市、市民化等重要事件對進城農村老年人人生軌跡的影響。
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劇了鄉—城間、城—城間的人口流動,流動的形式呈現出個體流動、家庭流動、旅游流動與邊界流動共存。[11]出于老人養老方便或照顧孩子的需要,在城市有穩定收入或住所的年輕人將老人接到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加速了老年人口流動。除此之外,在人口老齡化影響下,老年流動人口的數量和比例呈上升趨勢,[12]表現出鄉—城、城—城、鄉—城—鄉等流動類型。與主動進城的青壯年不同,老人以協助子女、跟隨子女的角色被動從熟悉的社會環境脫域進入陌生的社會。流入城市的農村老人因缺乏城市積累、難以獲得流入地社會支持而處于空間、體制和文化的邊緣。[13]具體表現為,個體特征上,隨著年齡的逐漸老去,老年人的身體機能、認知能力逐漸下降,加之農村老人受教育程度低,難以適應數字化、信息化的城市生活方式,面臨語言、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融入困境。制度環境方面,受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制約,流動老年人享受不到流入城市的社會保障,更多的是依附子女、家庭養老,這就導致老年人認為自己增加了家庭支出,給子女帶來了壓力。因而定居的意愿和城市融入水平低,在城鄉之間頻繁地兩棲流動。城—城之間流動的老年人,多為退休者,相比農村流動老人文化程度高,是攜帶經濟資本、人力資本而流動,能夠較快的融入當地文化,適應當地生活方式,因而長期定居的意愿較強。[14]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流動老年人的群體特征更加異質多元。除隨遷等被動型流動外,出現了以享受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旅游、選擇適宜養老的城市等主動型流動。流動的距離有跨省、跨市縣、甚至跨國流動等。學者結合“流動”“老年”的雙重特征定量分析老年流動人口的群體特征,并主要考察流入大城市的老年人市民化問題。本文以甘肅省天祝縣為例,以從農村、牧區流入縣城的老年人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為何流動?如何調適因遷移引起的家庭結構、家庭關系、代際供養方式的變化?作為生命歷程中重要的生命事件,流動以及市民化給老年人的生命軌跡帶來哪些影響?
家庭是老年流動人口活動的主要場域,進入城市的老人以“原子化”的方式分散地嵌入在不同的家庭中。而在天祝縣城北新區的保障性住房小區內,生活著大量來自各個鄉鎮的農村老人。在這些小區隨處可見提著小馬扎、顫顫巍巍的老人,他們聚集在一起或曬太陽或閑聊或打牌。如此多的農村老人集中生活在城市小區的現象較為特別。筆者選取其中的Z和L兩個安置小區,于2020年8月和2021年1月兩次深入這兩個小區以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的形式開展調研。探討老年人何以進城,進城之后何以生存,他們對未來生活有怎樣的期盼。對于流動在外的人而言,年老的時候回歸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是國人的普遍追求。“落葉歸根”反映出一種尋根情結,它是對故土思念的回饋,更是為漂泊的靈魂找到一個歸宿。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牧區的老人在生命歷程的后期被裹挾進城鎮化的潮流,加入到鄉—城流動的大軍中。在城市無法就業的老人如何改變生存策略以支撐城市消費型的生活?老人的市民化意愿與能力之間是否存在矛盾與張力?老人如何適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關系、新的文化以及新的身份?落根城市的老年人是否過上了體面的生活?本文借助生命歷程理論,探討從農村脫嵌的老人嵌入城鎮以后如何生存,他們的晚年生活何以安放。
二、脫嵌農村/牧區,落根縣城的歷程
農民、牧民離開原來生活的農村、牧區進入城鎮,可視為其生產生活的空間場域、社會關系網絡從農村/牧區到城鎮的脫嵌與再嵌入過程,農牧民在這一過程中面臨新的身份再造,以實現對城市社會的自我歸屬、自我認同。伴隨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出于對城市更美好更現代生活的向往以及地方政府有力推動,城鎮成為農村人生活的目的地,“農村”“農民”“牧民”成為他們急于擺脫的“標簽”。大城市高昂的房價與生活成本將缺乏資本的農牧民拒斥在外。處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縣城,因為相對較低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以及相同的生活方式、人居環境和文化觀念等,滿足了農牧民市民化的需求。“小城市相當于一個磁石吸引周邊鄉村的人口”。[15]農牧民將務工的積蓄用來在縣城買房定居。在縣城買房定居者已從鄉村精英擴展至大部分草根民眾。在照顧孫子、看病方便、提高晚年生活質量等多重原因的推動下,老年人也被裹挾進縣城,在其晚年的時候成為“城里人”。進入縣城的農牧民面臨著就業機會沒有增多,收入未能提高,支出卻大幅度增加的現實困境,為了維持一家人在縣城的高額開支,年輕人又不得不跨縣、跨省打工,留老人與孩子在縣城,成為縣城新型的留守群體。那么,現實根基不穩,未來不確定的老人何以進城?
(一)主動選擇
1.陪讀者
“工業化和農業的現代化提高了教育和其他技能的回報。結果導致父母的行為從生育很多的孩子變為對每個孩子進行更多的投資。”[16]教育是最為重要的投資之一。隨著農村中小學校的撤并重組、教育結構的優化以及農牧民教育觀念的轉變,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優質的教育,不少農村家庭選擇從小學開始就將孩子轉入縣城或大城市的學校,因為孩子太小,在城市求學生活無法自理,需要家長照料孩子的生活和輔導監督學習,因而在我國產生了陪讀現象。陪讀現象的產生是政策制度、家庭、個體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農村家庭應對城鎮化、家庭流動、農村教育改革而基于家庭成員的角色和身份進行的理性決策。教育是一項長期的、不確定性的風險投資,陪讀無疑進一步增加了教育投資及風險,然而,對于沒有權力背景或資本積累的農村家庭來說,教育仍然是改變子代命運,實現家庭軌跡上升的可能渠道。在天祝縣,大體上有以下幾類陪讀類型,一是父母雙方在縣城邊打工邊照顧子女上學。其次是父母一方,多為母親專職照顧孩子上學,另一方仍在農村從事種植或養殖,或跨縣、跨省外出務工。第三種是父母雙方在外地打工,孩子由爺爺奶奶照顧。在牧區,父母繼續從事放牧,爺爺奶奶進城照顧孫子的現象較為普遍。不管是何種類型的陪讀,都是每個家庭在生存策略之下基于家庭經濟狀況、資源稟賦以及家庭成員所掌握的資本作出的理性選擇。陪讀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首要的是在縣城租房或買房。Z和L兩個小區有廉租房、公租房、經濟適用房等多種房源,能夠滿足不同家庭的梯度需求。一些人認為保障性住房沒有房產證,租住比較可靠。Z和L兩個小區供出租的房子為小套,面積為50-60平方米,租金加上物業費等其他各項開支,一年需8000元左右。如果購買房子定居縣城,需20-30萬元。不少家庭舉債或貸款買房,為了償還借款或貸款,年輕人外出打工,將老人和孩子留在縣城,由老人負責陪讀。陪伴一個孩子從小學到高中畢業,需要十幾年的時間,十幾年生活在縣城,促進了老年人市民化。
2.跟隨子女者
受我國傳統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從農村脫域進城的老年人并未納入城鎮社會保障服務體系,依附于家庭的養老模式仍發揮主導作用,出于子女方便照料的理性選擇,老人被動地跟隨子女進城。另外,經過幾十年人口流動的演變發展,青年一代的價值理念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進入城市的目的和訴求日益多元化,增加經濟收入不再是進入城市的主要目標,追求自我發展、提升個體能力,最終扎根城市進而成為城里人是青年一代的終極目標。在人口大流動時代,流動的趨勢、類型、模式以及結構漸趨多元復雜,舉家遷移的家庭逐漸增多。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獲得親情支持,減少了因離散帶來的痛苦。老人跟隨子女進城,幫忙照料孫子,確保年輕人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增強整個家庭立足城市的能力。
“子女們進城了,我們沒辦法也跟著來,人家打工去了,孫子沒人看,再者我們在農村也不方便,尤其身體有病需要照顧,跟著子女們他們照顧起來方便。”(男,藏族,60歲)
3.提高晚年生活質量者
費孝通指出,親子關系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是極為基本的,任何社會總是以這種社會關系為基礎構成它最基本的群體。[17]西方社會的親子關系是甲代撫育乙代,乙代撫育丙代,依此一代一代接力撫育的“接力模式”。在中國是親子反饋模式,即父母撫育子女長大,年老的時候子女贍養父母,回報父母的恩情。從長期社會實踐看,無論何種親子關系模式,家庭成員之間的取舍給予須遵循均衡原則以保證社會經濟共同體長期維持下去。[18]在傳統的小農經濟社會,“養兒防老”是農民家庭成員之間取予均衡的實踐模式,兒子繼承家庭財產,負責贍養父母。在人口流動的時代,子代進城與留守在農村的父代長期分離,沖擊傳統的供養模式,農村空巢老人逐漸增多,老人從子女處獲得的經濟和情感反饋日趨減少,但在農村社會福利保障還不健全的現實下,依靠子女供養仍然是主要的養老方式。為了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質量,年輕人更加方便的照顧老人,一些家庭給老人在縣城買房子,這種現象大多出現在子女在縣城或其他城市有穩定工作的家庭。父母年輕的時候為了子女的教育耗盡了財力、物力,等到父母老了,子女盡可能的反哺父母,讓父母安度晚年。
“我兒子在縣城上班,為了方便照顧我和老伴兒,在縣城給我們買了房子,以前他回一次家需要2個小時,路也不好走,現在10分鐘就到了。”(女 藏族 67歲)
“我的兩個孩子都大學畢業,工作穩定收入也不錯。當時為了他們上學農村老家的房子從沒翻修過,家里的羊全都賣掉了。他們兩個工作以后給我在縣城買了房子。”(男,藏族,58歲)
(二)被動適應
1.精準扶貧戶與易地扶貧搬遷
根據調研,精準扶貧戶家庭出資1萬元就可以在安置點購買一套安置房。筆者調研的對象共有3個安置點,分別為松山鎮、縣城新區的Z和L小區,各個村子采取抓鬮的方式決定安置點,并根據家庭人口數量的多少決定所分房子的大小,三口人家會分到60平米左右的房子,五口之家的大家庭會分到80平米左右的。
“有些家庭是為了兒子結婚,現在結婚女方都會要求男方在縣城買房。有些家庭是為了小孩在縣城上學選擇搬到縣城。”(男,藏族,58歲)
即使沒有個體化的訴求,對于花1萬元就可以在縣城購買一套房子這樣的優惠政策,幾乎沒有家庭可以拒絕。如果選擇接受優惠政策定居縣城,農村老家的房子、圈舍就會被推掉,土地流轉給農業合作社種植高原藜麥。
天祝縣城周邊的東莊村因為土地都是旱地,地陡靠天吃飯,收入微薄等原因,除養殖戶外,當地政府將單純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戶易地搬遷。
“我們村子里的人大部分搬遷到了縣城,L小區安置了50多戶,Z小區安置了30多戶,農村的老房子被推掉了,土地被流轉種植藜麥。”(男,藏族,73歲)
2.生態移民
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天祝段面積為4390平方公里,占全縣國土面積的61.4%,其中,核心區860平方公里,緩沖區683平方公里,實驗區2297平方公里,外圍保護地帶550平方公里。核心區共居住農牧民群眾59戶217人。為了減少對生態環境的人為影響,天祝縣將位于生態核心區的農牧民進行整體搬遷,并出臺相關的優惠政策確保生態移民“搬得出、穩得住、留得下”。住房方面,為減輕搬遷群眾新建或購置住房負擔,確保群眾搬遷后有房可住,對于搬遷至Z和L小區的住戶每戶補助5萬元的購房資金。就業方面,對符合條件的搬遷群眾根據需求,優先安排農村公益性崗位,對自愿轉為城鎮戶口的,可規定安排城鎮公益性崗位,實現搬遷群眾轉產轉業,確保群眾搬遷后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對搬遷群眾特別是遷入縣城的群眾開展就業技能培訓及就業指導。
“政府組織18-45歲的農牧民參加培訓,培訓的項目有電焊、維修、廚師、運輸等。但是農牧民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有限。”(男,藏族,58歲)
無論是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崗位還是組織的技能培訓,都有年齡的限制,因而將老年人排除在外。根據調研,生態移民戶雖然舉家搬遷至縣城,但是戶口并未遷移,只能享受農村戶口所應享有的保障性政策。
3.失地農民
城鎮化快速發展表現為城鎮空間擴張以及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從事非農產業。城鎮空間的擴張使周邊農村被動卷入城鎮場域,農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進行城鎮化建設,從而產生了失地農民。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全國各個層面的城鎮得到了迅速發展和擴張,連接都市圈與鄉村的縣域在規模擴張中吸納了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的農民,生計方式、職業、社會網絡、價值理念發生了根本性變革,經歷劇烈時代變遷的農民在變革與適應中尋找身份歸屬。調研中遇到一部分來自天祝縣寬溝村的村民,他們的宅基地和土地被征用建設工業園區,失去土地和宅基地的村民被安置在Z和L小區。寬溝工業園區共有23家工廠,主要生產碳化硅、瓷磚等。據村民反映,這些企業在解決本地就業方面貢獻不大。一些外地老板都是自帶工人,不用當地勞動力。另外,企業效益低下,經常發生停工現象,有時不能按時支付工人工資,導致本地勞動力也不愿意到這些廠子打工。
易地扶貧搬遷、生態移民以及失地農民的市民化是政府主導的“政策型”或被動型市民化,而非農民自愿選擇的行為。這種類型的市民化最明顯的特征為農牧民舉家進入縣城,家庭中老年人不得不跟隨進入縣城。農村老人的居住空間、社會關系由農村轉向城市,由熟人社會進入陌生的、異質的社會,社會交往方式發生改變,需要重新建構社會網絡。在Z和L兩個安置小區,移民交往的對象仍然是來自全縣各個地方的農牧民,相似的生活環境,相同的生命歷程,使他們在新的生存空間形成了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群體,社會交往傾向于“內卷化”,社會網絡沒有得到實質性擴展,農牧民社會地位未能上升,身份未發生轉變。老年人因自身能力不足,很難實現再社會化,他們進城即意味著失業,面對比農村消費高出許多的縣城,老人何以生存?
三、落根城鎮,生存如何
農牧區老年人在城鎮生活的現狀與早期人生經歷、個體與城鎮社會的互動經歷有關。老年人與城鎮社會互動的歷程與時代背景緊密相連,在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時代,農牧區老人與城鎮的往來主要體現在以趕集的方式與城鎮實現經濟交換;在城鎮化加速發展的人口大流動時代,老年人在城鄉之間頻繁流動,與城市的交往延伸至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后來在家庭、政策等多種因素驅動下老人長期生活、定居在縣城,此時老人已走到生命歷程的后期,與過去農村生活的縱向比較以及與城鎮其他人的生活橫向比較后發現,遷移影響老人生命軌跡的波動。戴維斯(Davis)將個體生命軌跡方向劃分為上升、水平或下降的形式。調研發現,“農村—城鎮”空間轉換和“農牧民-非農非牧”身份轉變引起進城農村老人生命曲線上下波動起伏。城市完善的基礎設施,優美的居住環境,看病就醫方便等是促使老人生命軌跡上升的有利支持因素。收入未增加,消費迅速增加是導致生命曲線下降的不利因素。在相同的時代背景、政策制度影響下,因個體能力、家庭資源積累不同,其生命軌跡的方向不同。子女在縣城有穩定工作的老人,依靠代際供養不但生活有保障,并且實現了與子女團聚,生命軌跡得以向上起伏。身體患有疾病、子女外出打工的老人,成為縣城新型貧困群體、邊緣群體和留守群體,生命軌跡向下波動。
(一)具有“鄉村性”的城市活方式
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所示,“城市人口的絕大部分來自早期生活模式尚存的鄉村,這種情況強化了俗民社會的歷史影響。我們不可能在城里人和鄉下人的個性類型之間發現突變的、斷裂的變化”。[19]絕大多數農村老人早期生活經歷過貧困,艱辛苦難的過往記憶、體驗與當下的能力缺失規制了老人的消費行為,只能實踐勤儉節約的生活慣習規避未來生活的風險。常年生活在農村的老年人,形成了與農村文明相對應的生活方式、價值理念、角色意識與行動邏輯。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特征的農村文化在老人身上表現得根深蒂固,他們雖然居住在城市,卻保留了農村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費理念,因而難以適應以消費為主要特征的城市生活。在城市消費高幾乎是進入城市的所有老年人的心聲。
“在縣城,吃的、喝的、用的都要拿錢買,水電費、暖氣費、物業費……農村人就不該上樓。”(男,藏族,69歲)
為了應付這些日常費用,老人們盡可能的縮減衣食住行方面的開支。衣著方面,他們仍然保留農村人的風格,有人穿著布鞋,老奶奶們戴著當地農村婦女們常戴的頭巾,老爺爺們戴著很過時的帽子。很多老人抽的煙是農家自產的煙葉子。由此可見,進入縣城的農村老人只是實現了身體所處空間的物理性轉移,消費觀念、行為模式和文化心理打上了深深的農村文化烙印,在自身能力不足的約束下,難以發生轉換。訪談期間,遇到一位有退休金的老人,雖然退休金每月只有2400元,而且這些退休金要養活他和老伴兒兩個人,但老人在衣著方面明顯比來自農村的老人洋氣。
(二)處于城市邊緣,是新型的貧困群體、邊緣群體和留守群體
隨著年齡的老去,老年人身體機能、認知能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逐漸下降,“相伴而生的各種疾病風險的增加與可預期的負面生活事件(如喪偶等)是老人陷入貧困的主要促動力”。[5]楊菊華將老年人貧困分為經濟貧困與社會貧困兩種不同程度的貧困。經濟貧困主要指收入不能維持支出。社會貧困主要包括生活質量低下、身體不健康以及精神孤獨等。老年群體致貧因素多、貧困率高,農村老人更容易陷入經濟貧困與社會貧困中。[20]城市的老人因為有退休金和醫療、養老等社保從而可以有效地規避生活中可能出現的風險。進城的農村老人面臨收入未增加,消費卻迅速增加的困難。在農村60-70歲左右的老人尚且能繼續經營農業,依靠土地收入維持生計,進入城市即意味著失業,只能依附子女、家庭養老,晚年生活質量與子女生活狀況、子女是否愿意承擔贍養責任緊密相關。由于進入縣城的老人仍是農村戶口,因而不能享受城市社會保障服務,每月120元的養老金是大部分老人的依靠。依靠農村收入維持城市消費型的生活難免陷入“捉襟見肘”的境地,雖然老人飲食清淡、穿衣簡樸,日常消費并不高,但是“養樓養病”卻是老人難以應付的主要支出。
“與收廢品者討價還價”“怕浪費電不敢看電視”“為了節約水費,到小區附近的小河提水。”“冬天如果是陰天不敢出來,怕感冒了還要花錢買藥……”
我們所遇到的這些貧困個體,反映出進城農村老人的群體性貧困。雖然老年人進入城市的理由千差萬別,但進入城市后幾乎是同質性的個體。相同的農村背景,在城市沒有穩定收入來源的同樣困境,使老人不可避免地陷入貧困,成為縣城新型的貧困群體和邊緣群體。訪談中遇到的H先生戲稱他們小區是“難民區”,住的都是沒有收入來源,身體又有各種疾病的老年人。
除此之外,在人口流動加速和核心家庭增加的趨勢下,年輕一代攜帶自己的子女跨縣、跨省打工,留老人在縣城獨自生活。老人即使進了城也難以擺脫留守之痛,成為新的留守群體。外出務工的家庭通常將有限的家庭資源投入到子女教育與撫養中,擠壓了對老人的贍養支持。老人從子女處獲得的經濟支持、日常照料、情感慰藉等很有限。有些家庭外出務工時選擇將子女留給老人照顧,老人以陪讀的方式繼續從事再生產活動,繁重的家務勞動、教育孫子的壓力,往往導致老人健康水平下降。
(三)居住空間區隔化,復制農村的文化模式
桑德斯(Saunders D.)將鄉村移民構成的城市飛地稱為“落腳城市”,這些地區與城市中心區隔,處于城市的邊緣與底層,是貧窮、暴力、犯罪的集聚地,同時充滿希望與活力。“落腳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經濟與文化的盛地,也可能是暴力沖突的爆發地。究竟會走向哪條路,取決于當局為移民人口提供哪些權利與資源”。[21]甘斯(Gans)將攜帶傳統文化進入城市的鄉村移民定義為“都市鄉民”。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普遍存在過度城市化或城市化與工業化不協調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產生了大量生活在城市從事“非農”職業,但價值觀念、身份沒有成功轉型的“都市鄉民”。[22]Z和L安置區由鄉村移民構成,在空間上與縣城中心區隔,仿佛是嵌入城市的一塊飛地,這些特征與“落腳城市”類似。對于當下生活在城市中的老人來說,縣城中心的喧囂嘈雜、人來車往,清晨牦牛廣場的轉經聲,傍晚廣場上的鍋莊舞仿佛都與他們無關,這些碎片化的日常文化景象成為區隔城里人與農村人的“顯性符號”。被分散安置到不同的小區,需要重新構建社會關系網絡,鄉村移民在城市空間中所建構的社會關系網具有熟人社會與陌生異質社會相互交織的特征。
“我們村搬來了13戶,散居在一個小區,平時不會打電話聯系,也不會串門。鄰里之間彼此不認識、不往來互動。一起曬太陽聊天的也不認識,今天認識了,明天又忘記了。”(女,藏族,70歲)
聚集在一起閑聊的老人雖然彼此不認識,但相互之間很友好、經常相聊甚歡,喜歡分享家事、私事,缺乏隱私觀念,難守秘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相處的方式是農村文化模式的復制,因而少有城市人的冷漠、多疑。筆者作為一個外來者,跟相遇的老人訪談時,他們表現的很友好,不會懷疑、排斥或拒絕。
(四)生活方式的改變引起家庭關系緊張
城市與農村居住空間的格局分布不同,農村是庭院式的,擴大家庭中的幾代人生活在一個院子,依據輩分、權利居住在不同的房間,不同房間的空間距離較大,是相對單獨和私密化的活動空間,如果家庭關系緊張還可“分灶”,即“分灶不分家”。而城市空間緊湊,幾代人共享一個空間,日常生活中瑣碎的矛盾往往被激化。流入城市空間中的農村人,需要拋棄生成于農業社會的種種習俗,建構與城市文化相對應的生活方式,然而,傳統鄉土文化對老人的影響根深蒂固,他們習得城市的生活習慣需要時間,經過長時間的傳統與現代、新舊價值觀念的碰撞與融合,老人才會實現他們的城市化。舉家搬遷至縣城的有些家庭,因無力購買第二套房產,只好幾代人生活在一起。老年人與子女生活在一起,因經濟拮據、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不同,產生了許多矛盾,導致家庭關系緊張。
“年輕人喜歡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我們老人喜歡吃軟一點、清淡一點的,吃不到一起,總是招年輕人嫌。”(男,藏族,71歲)
另外,與老人不在一起住的年輕人,平時在外地打工,過年回來時將自己的孩子接走,留下老人孤獨過節,享受不到一家人團聚在一起的喜悅。
(五)單調的閑暇時間,匱乏的精神文化生活
城市退休老人的晚年生活豐富多彩,老人有更多的時間去國內外旅游,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繼續深造,諸如學習畫畫、樂器、棋藝等。在城市的公園我們也能看到老年人豐富多元的業余活動,吹長笛的、拉二胡的、跳健身操的、打太極的、舞劍的等等。總之,老人退休以后把大部分時間放在鍛煉身體和陶冶情操上,通過參與各類活動結交新的朋友,保持愉悅心情。根據筆者調研期間的觀察,天祝縣的Z和L兩個小區,幾乎所有老人的閑暇時間以閑聊、曬太陽、散步或打牌的形式度過。參與打牌的也是生活相對富余的少數人,一些老人認為就算一天輸掉2元錢,一個月也要60元,沒有必要增加額外的花費。老人們拿的都是老年機,通訊工具僅限于與親朋好友的聯絡。很少有人拿智能機,更談不上利用網絡交友、瀏覽新聞,充實豐富業余生活,或掌握外界信息接受新事物。有些老人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非常模糊地了解到抖音、快手等新式傳媒軟件。例如訪談中遇到一位76歲的老爺爺說,“快手上說我們的養老金要漲呢”,至于什么是快手卻說不清楚。趙旭東認為,“網絡時代特征之一是去中心化,即網絡通達之地,也就意味著信息的共享,再無需通過中心向邊緣反饋信息,無處不中心是一種現實的日常”。[23]筆者在縣城發放問卷的時候,遇到一位女老板正以網絡直播的方式銷售衣服。直播中使用的是“親、小姐姐們”等網絡語言。其實不只是城鎮,網絡直播、拍攝抖音或快手短視頻等在農村日漸興起,成為農產品銷售、獲得收入或娛樂的新型手段。而進入城市的農村老年人仍然處在信息社會的邊緣,是數字網絡時代的邊際人,對當下流行的通訊媒介感到陌生。老人在同質化的社會網絡中,能夠獲取的信息資源、文化資源非常有限。除此之外,社區很少組織一些志愿活動或公益類活動,老人獲得社會層面的支持非常有限。兩個小區缺乏健身設施器材,缺少關于民族團結、和諧鄰里、文明有禮的宣傳標語、展板等。
(六)能力不足導致對未來生活充滿不確定的擔憂
各行各業的人集聚在城市的萬花筒,在異質、多元、陌生、流動、分層的城市社會中,擁有財富、權力、資源與聲望的人位居社會頂層,相對地,缺乏各類資本與資源積累的群體掙扎在底層社會。失業又缺乏社會保障的進城農村老人無疑是城市社會的弱勢群體,生計極其脆弱、不穩定。老人們對城市生活的期盼和現實能力不足之間存在很大的張力。
“城里好是確實好,平時看病方便,有錢了出去什么東西都能買到。也不用干農活,輕松、干凈,尤其冬天呆在有暖氣的房子暖和。但在城市生活花銷太大,一年的水電費、物業費、暖氣費、天然氣費等各種費用加起來需要8000元左右。還要日常生活呀,我前天買了兩根蔥10元。辣椒一斤10元,油菜5元。肉就更不用說了,一斤大肉26元,我們哪能吃得起。”(女,藏族,72歲)
對于沒有退休金、沒有工作,依靠農村收入供養城市日常生活的老人而言,生活難免陷入困境。大部分老人選擇了依靠兒女的傳統養老方式。如果子女有穩定工作,定期給老人一定數額的生活費,其晚年生活就會相對富余。對于大部分打工家庭,因為還要養活自己的一家人,在生活的重壓之下,供養老人的能力有限,老人從子女處得到的金錢、物質、情感支持難以確保生活的穩定,對何以安度晚年生活充滿不確定性的擔憂。
四、何以扎根城市
(一)渴望城—鄉兩棲生存的邊際人
帕克(Park)認為,邊際人是新舊文化的混血兒,他們既不愿意與傳統文化割裂,也融不進所處新環境的新文化,處于兩種社會、文化的邊緣,兩種文化在其身上從未完全緊密交融。在人口大流動時代,我們將那些從農村流向城市或跨省、跨國流動并且還未還融進城市文化、融進流入國文化,在經濟收入、社會身份方面處在底層的人稱為邊際人或邊緣人。鄉—城流動人口從農牧區脫域,嵌入城市工作,仍然從事依靠體力的職業,較低的收入、缺乏穩定性的工作,城市居民的排斥等使得鄉—城流動人口處于社會底層,他們對城市充滿矛盾、復雜的情感,既渴望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定居城市,又恐懼缺少在城市立足的能力,長期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和漂泊,形成既不想返回農村又融不進城市的鄉城邊際人。攜帶鄉土文化的老年人進入城市后,將農村文化移植在城市的土壤,在城市空間中成長起來的文化,是傳統與現代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而形成的新型移民文化。作為文化實踐主體的老年人是處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邊際人。
進入城市的農村老人期盼一種過渡性的生活,希望能夠在城鄉之間自由往返。在享受到城市文明的方便、快捷、舒適之后,即便在城市生活面臨能力不足、未來如何不確定的困境,大部分老人并不想徹底回歸農村,而是渴望擁有自主選擇生活場域的權力,希望在城鄉之間自由往返。
“要是我們還能回農村就好了,夏天的時候可以種一些菜,養豬養雞……冬天的時候我們回到縣城過冬。”(女,藏族,57歲)
這是年齡不太大,擁有一定勞動能力,身體沒有疾病的老人們的心聲。中小城鎮與鄉土聯系緊密,大部分難以在大城市實現扎根的農村人會選擇定居在家鄉的中小城鎮,實現就地市民化。但中小城鎮因自身經濟發展乏力的制約,可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又因財力不足等原因,難以提供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資源有限的現實情境下,應賦予鄉村移民自由選擇的權力,允許他們將農村作為社會安全網,將經營農業作為增強立足城市能力的策略。如果強制推進城鎮化,斷掉進城失敗者的后路,會讓大部分人陷入新的貧困,造成資源的浪費。在我們的調研中,發現大部分主動進城者,選擇將農村作為退路,作為落根城市的過渡和規避在城市生活風險的保障,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對未來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生活的擔憂與焦慮。
(二)回不去的故鄉,離不開的城市
對于因政策被動卷入城鎮的老人,故鄉已經不存在。從他們選擇將城市作為最后歸宿的場域起,就意味著和過去、和農村的徹底斷裂。老人在身份轉型與扎根城市的過程中,需要依附于家庭、政府與社會。“養樓養病”是老人在城市日常生存實踐中面臨的最大障礙。進城老人首要依靠的是子女,對他們來說傳統的養老模式仍然發揮著主導作用。子女們在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壓力之下,將有限的家庭資源、財力投入到自己小家庭發展之上,導致傳統養老模式的功能逐漸弱化。政府需探索建立適合農村進城者的養老機制,根據老年人在城市生活的現狀相應地提高補助。除此之外,將更多的藥物納入報銷范圍內,減輕老年人生活壓力。調研中,許多老人反映日常生活消費他們尚且能勉強應付,但是常年吃藥使原本貧困的生活雪上加霜、不堪重負。一生在農村、牧區辛苦勞作的老人,身體難免會出現疾病。
“我經常腿疼,要天天吃藥。而且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吃飯總是被噎住,不管吃什么都噎,稀飯也是,沒閑錢到醫院去檢查。”(男,土族,77歲)
來自朵什鄉南沖村的72歲老奶奶,因兒子不幸去世,兒媳婦帶著孫子改嫁等家庭變故的原因而一個人住在縣城,她說自己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雖然慢性病醫藥費可報銷70%,但每月300元的醫藥費無疑是讓她最發愁的事。除醫藥費外,物業費和暖氣費是城市家庭支出的大頭。對于獨自生活在縣城的老人,政府在“養樓養病”這兩項費用方面給予一定的補償,減輕老年人生活壓力。除此之外,強化社會養老的功能,“完善社區養老服務設施建設,提高養老服務供給的能力和質量,提供方便快捷的多層次、多樣化的養老服務”。[24]天祝新區社區養老院已建成但還沒有投入使用,應盡快完善硬件設施與相關規章制度,加快投入使用的進度。
(三)完善老年人社會支持網絡,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
在農村尚可自給自足的老人,進入城市即為失業者,成為失能或半失能者。沒有收入來源,子女不在身邊的老人是城市中的新型貧困群體、留守群體、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即便在縣城生活面臨著一些難題,不少老人滿意城市生活。經過老人們的艱難的轉型,他們子孫后代立足城市的根基將會更加牢固。因此,需要激發社會養老功能,完善社會支持網絡,為老人提供物質與情感支持,協助他們立足城市。社區多組織志愿者服務或公益類活動,在滿足老年人意愿訴求方面提供支持。營造民族團結的文化氛圍,協助小區物業美化安置小區居住環境,打造環境優美、公共服務配套完善、民族團結、文明和諧的小區,讓老人在高品質的小區找到歸屬感,提升融入城市的能力。另外,針對老年人閑暇生活單調的現狀,動員社區居委會組織開展一些文娛活動,如象棋比賽、廣場舞大賽、歌詠、詩朗誦等,豐富老年人業余生活,促進鄰里之間交流互動,創造和諧安居的幸福社區。[25]
五、結論
中西部地區的縣城城鎮化由政策拉動,工業化滯后于人口遷移,由此產生了許多隱性失業的貧困群體。在天祝縣,年輕的女性以導購、飯店酒店服務員為業,月收入2000元左右;中年婦女、男性勞動力一般在建筑工地就業或在“釣魚臺”以打零工的方式維持生活。“釣魚臺”是當地群眾對勞務市場的俗稱,形象地反應出其就業不穩的現狀。政策性推動及追求優質教育資源等主導因素加速了縣城城鎮化,驅使農民家庭將縣城作為生活的歸宿。個體的生命史與時代發展背景密切相連,在一定程度上,社會變遷塑造個人發展軌跡,處于城鎮化加速發展時代的農村老人,在生命歷程的后期以主動或被動的形式進入城市,面臨生活方式、價值理念、身份的轉型。此時的他們已不能通過再社會化掌握城市生存的本領,面對遠高于農村消費的城市日常生活,進入城市的老人們產生了焦慮、恐慌、擔憂的心理。
本文以生命歷程理論為指導,研究老人進城的原因、在城市生活的現狀,思考如何賦能以支撐老人的城市生活。研究發現,進入縣城的農村老人目前只是在居住空間方面實現了市民化,消費觀念、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打下了深深的農村文化烙印。居住的區隔化和交往群體的同質性在他們之間形成了一個亞文化圈,進一步拉大了與城市居民的社會距離。他們是擺脫了土地與草原居住在城市的鄉民,并且將農村的生存方式移植到城市。因戶口未遷移,進城老人依靠農村收入維持城市生活,處于城市底層,是新型的貧困群體。由于子女外出到其他城市務工,老人即使進城也難以擺脫留守的處境。正因為老年人進城以后對家庭貢獻有限,養老依附于子女,導致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社會地位下降,缺少決策權與發言權。除此之外,老人在城市業余生活單調,精神文化生活極其匱乏。從家庭、社會獲得物質和精神支持較少,內心難免孤獨。老人們內心深處喜歡城市的生活,只是受困于自身能力不足,遂產生了矛盾、茫然、苦悶的情緒,符合城市邊際人的特征。
落根縣城的老人,雖在城市日常生活中面臨諸多的現實困境,是城市融入的過渡群體。但老人認為通過忍受暫時的貧困可換來家庭長遠的發展。我們看到,Z和L小區所處的社區正處于成長發展期,農村移民的子女將來會享受到更多更便捷更優質的文化資源、教育資源以及醫療服務資源。隨著政策制度的完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以及鄉城移民后代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權力資本的積累,他們將在職業、經濟收入、身份認同方面實現完全市民化,最終真正扎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