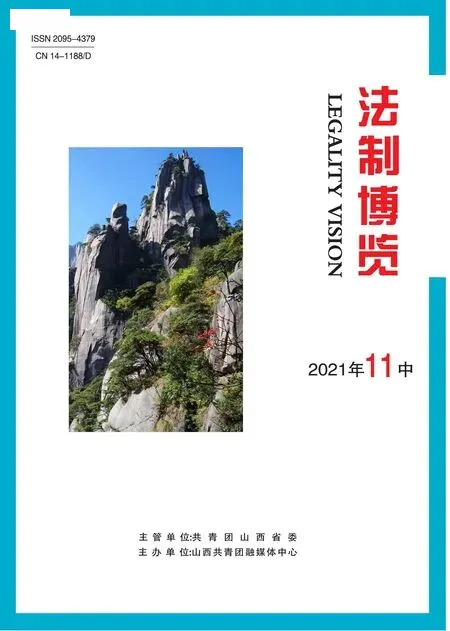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的法律規(guī)制探索
謝璐陽
(西北政法大學,陜西 西安 710063)
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發(fā)展改變了傳統(tǒng)的交易方式,拓寬了商業(yè)活動的渠道。然而,揭開技術變革的繁榮表象,探究競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大數(shù)據(jù)在成為經濟新引擎的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交易雙方地位的不對等。經營者為了攫取最大利潤,利用算法技術這只“無形的手”收集用戶信息并操控價格,以此對消費者進行定點“突破”[1]。近年來,我國網(wǎng)絡平臺頻繁曝出大數(shù)據(jù)“殺熟”事件。多個領域的電子商務經營者均存在疑似大數(shù)據(jù)“殺熟”現(xiàn)象,以及部分旅游平臺具有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2021年2月,反壟斷委員會印發(fā)《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對適用《反壟斷法》規(guī)制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作出指引。然而,實踐中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實施效果卻不如人意,“殺熟”現(xiàn)象仍大行其道。隨著算法技術在各行各業(yè)的普及,殺熟行為如何界定和有效規(guī)制、有關價格的規(guī)定和消費者保護的法律體系如何完善等問題,已然成為當下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一、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之概述
經營者實施“殺熟”行為一般遵循如下路徑:第一步,最大限度獲取用戶信息以形成數(shù)據(jù)優(yōu)勢。經營者獲取的用戶信息包括個人信息和行為信息。行為信息是用戶在網(wǎng)絡平臺進行瀏覽行為時留下的痕跡,包括交易記錄、搜索記錄、訪問記錄等[2]。目前,對于用戶信息處理后形成的數(shù)據(jù)的歸屬尚未形成定論,實踐中一般默認由經營者對數(shù)據(jù)進行事實占有并有權使用,用戶無法知曉和控制其數(shù)據(jù)的利用,從而處于信息的弱勢地位。
第二步,利用大數(shù)據(jù)分析技術進行精準“畫像”。對于經營者而言,收集或獲取用戶數(shù)據(jù)信息僅僅是手段,通過對數(shù)據(jù)信息的挖掘、分析,實現(xiàn)對用戶的精準“畫像”,并據(jù)此實施“精準營銷”的策略和“千人千面”的定價才是其真正目的[3]。通過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對消費者進行具體分析,根據(jù)其消費心理和行為特征,采用指向明確的營銷策略,從而實現(xiàn)對不同消費者群體強有效、高回報的營銷。
第三步,在有效隔離的情況下實施差異化定價。該步驟是基于網(wǎng)絡交易的特點而實施的。在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下,屏幕的界限構成了區(qū)隔屏障,消費者之間難以進行有效信息溝通,無從獲知此時的“明碼標價”是否為“明碼同價”。在此基礎上,商家充分利用其對消費者的“非對稱性”信息優(yōu)勢,恣意對用戶實施“殺熟”行為。
價格歧視這一概念來源于經濟學相關理論。技術的發(fā)展使得經營者能夠在收集用戶的數(shù)據(jù)信息的基礎上,借助于算法精確分析用戶的支付意愿,從而使得一級價格歧視變成了可能,即大數(shù)據(jù)“殺熟”是一種典型的一級價格歧視行為,實踐中可以借鑒經濟學的相關定義來界定法學上大數(shù)據(jù)價格歧視的表現(xiàn)形式,以區(qū)分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和合理的差異化定價。[4]
二、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的法律規(guī)制困境
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損害消費者利益、破壞正常價格機制和競爭秩序、對數(shù)據(jù)利用和商業(yè)倫理帶來不良導向,因此應當予以法律規(guī)制。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格法》《電子商務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規(guī)范對此問題均有涉及,但實踐中對于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的判定和規(guī)制仍存在諸多困境。
(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適用之障礙
大數(shù)據(jù)“殺熟”首先損害到的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該行為對消費者知情權、公平交易權的侵害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有關消費者權利的規(guī)定適配性最高,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給予消費者以救濟應當是最直接的途徑。然而,相關規(guī)定的模糊使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尚不能成為規(guī)制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的有效途徑[5]。
其一,消費者公平交易權的規(guī)定。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條規(guī)定來判斷是否侵犯消費者公平交易權的關鍵在于認定經營者定價是否“合理”。然而并未對“價格合理”的認定給出標準,與之相關的《價格法》則將定價的權利較大程度地授予經營者,這導致“價格合理”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其二,消費者知情權的規(guī)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guī)定了經營者的明碼標價義務。然而,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的外在表現(xiàn)是對不同的消費者“明碼”標示不同價格,法條中對價格的表述較為模糊,適用時對“真實價格”“明碼標價”沒有明確的判定標準,難以認定“殺熟”的差異化定價違反了該條的規(guī)定。
(二)《反壟斷法》適用之局限
首先,對于《反壟斷法》規(guī)制的價格歧視行為中“交易相對人”的認定。一般而言,大數(shù)據(jù)殺熟發(fā)生在商家與消費者之間,而《反壟斷法》中規(guī)定的“價格歧視”主要調整的是經營者之間的法律關系。
其次,對于“沒有正當理由”的判定。《反壟斷法》第十七條在認定“價格歧視”行為時采取“合理原則”,要求經營者實施該價格歧視行為“沒有正當理由”,但卻并未對其含義作出解釋。在實踐中,何為正當理由須由法官具體考量——交易風險、經濟效率等都可能成為經營者抗辯的正當理由——這也進一步削弱了《反壟斷法》規(guī)制的力度。
最后,《反壟斷法》中“經營者市場支配地位”認定困難。在復雜的互聯(lián)網(wǎng)市場環(huán)境中,該地位的認定所涉及“相關市場”“市場份額”的界定更為艱巨,且技術發(fā)展使得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也具備實施殺熟行為的能力。《指南》明確:基于大數(shù)據(jù)和算法,根據(jù)交易相對人的支付能力、消費偏好、使用習慣等,實行差異性交易價格或者其他交易條件、差異性算法、規(guī)則等,可能構成差別待遇,屬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6]。這一細化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與《反壟斷法》第十七條價格歧視行為構成要件的差異。
(三)“個人信息保護”相關規(guī)定適用之困境
大數(shù)據(jù)在激發(fā)了市場經濟的同時,也衍生出許多傳統(tǒng)法律規(guī)范無法解決的問題,尤其是數(shù)據(jù)信息的歸屬和利用。我國雖未出臺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但《網(wǎng)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均有涉及個人信息保護的條款,明確規(guī)定了網(wǎng)絡運營者在收集、利用用戶或者消費者個人信息時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和知情同意的原則,《民法典》中也有對個人信息從權利確認到侵權救濟的詳細規(guī)定。然而,“個人信息保護”規(guī)則在規(guī)制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時卻捉襟見肘,“知情同意”與“公開透明”原則的適用存在困難[7]。
由于消費者對于價格歧視存在抵觸情緒,故經營者不會在消費者“知情同意”后實施價格歧視,即便實際存在價格歧視行為,經營者也不會使其“公開透明”。而追溯到數(shù)據(jù)的收集和使用階段,由于數(shù)據(jù)采集技術的隱蔽性,消費者難以判斷經營者是否在自己“知情同意”的范圍之內收集數(shù)據(jù)。即便是經營者遵循合法途徑收集用戶信息,且由于目前對于經營者對用戶信息及處理后形成的大數(shù)據(jù)在何種程度上享有權利尚無定論,經營者在何種范圍內有權合法使用數(shù)據(jù),仍有待進一步明晰。
(四)其他法律法規(guī)適用之爭議
我國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了規(guī)制網(wǎng)絡經濟的基本法律——《電子商務法》,其中第十八條第一款為規(guī)范經營者基于收集、分析消費者數(shù)據(jù)以實施定價的行為提供了依據(jù)。但“消費者特征”的合理界定依然成為適用層面的難題。2020年文旅部發(fā)布的《規(guī)定》首次明確不得利用大數(shù)據(jù)等技術手段,對不同特征的旅游者就同一產品或服務在相同條件下設定差異化價格,但該文件的適用范圍之局限導致其不能夠對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價格歧視行為進行廣泛的規(guī)制。
此外,消費者在遭遇“大數(shù)據(jù)殺熟”時存在舉證方面的困難。這進一步加劇了相關法律在適用中的困難。綜上所述,現(xiàn)有的諸多法律雖然對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的規(guī)制作出了一定指引,但其在適用時存在的問題削弱了消費者維權救濟的可能性。
三、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法律規(guī)制之完善
對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的法律規(guī)制需要慎重考量,完善并充分發(fā)揮現(xiàn)有法律調控空間、形成多方合力協(xié)作規(guī)制價格歧視,是有效規(guī)制不法行為、促進大數(shù)據(jù)經濟健康發(fā)展的重要途徑。
(一)完善并發(fā)掘現(xiàn)有法律調控空間
1.《電子商務法》
作為《規(guī)定》的上位法,《電子商務法》應當進一步明晰其對大數(shù)據(jù)價格歧視行為的判斷標準及法律責任,為《規(guī)定》的相關內容提供指引和依據(jù)。
如何認定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屬于“向消費者提供針對其個人特征的商品或服務的搜索結果”,該行為的認定可具體為三個要件:第一,平臺經營者收集、分析了消費者消費能力、消費習慣等具有個人特征的數(shù)據(jù);第二,經營者利用數(shù)據(jù)定制了針對其個人特征的商品或服務的價格;第三,經營者對不同消費者提供了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商品或服務價格的選項。在證明責任的分配上,消費者僅須提供初步證據(jù)證明存在不合理的價格變動,由經營者舉證證明其價格變動具有正當理由,不屬于“利用消費者數(shù)據(jù)定制的針對其個人特征的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同時,賦予平臺以監(jiān)管責任,通過監(jiān)測或經舉報發(fā)現(xiàn)商家存在異常價格變動的,應當及時固定證據(jù)并聯(lián)絡商家查明情況,協(xié)助消費者維護合法權益。
2.《價格法》及相關規(guī)定
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是對不同的消費者呈現(xiàn)相同商品的不同價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消費者知情權、公平交易權的適用困境也在于此,即此種價格生成機制和呈現(xiàn)方式是否合理。相關部門可以轉換思路,從規(guī)范經營者的價格行為入手,正向規(guī)定經營者在價格營銷中的定價行為。這一思路必然涉及對“正常”價格的認定。對此可以借鑒英國《物價標示規(guī)則》合理時間的合理性判斷,美國的同業(yè)同商品當前售價對比規(guī)則,日本《關于〈贈品標注法〉上關于不當價格標注的觀點》中相關商品和交易條件的可比性判斷等國外的相關規(guī)定。通過對概念和規(guī)則進行細化,為《價格法》調整市場中價格標示不規(guī)范的行為消除障礙。
3.“個人信息保護”的相關規(guī)則
從個人信息保護的角度來看,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認定的關鍵在于數(shù)據(jù)利用行為的正當性判斷,對此可以在經營者告知義務中增加算法或算法用途說明的要求,滿足消費者對差異化定價的知情權。若經營者違反此義務而實施數(shù)據(jù)的利用行為,則可推定經營者對數(shù)據(jù)進行了不正當?shù)睦茫M者可依據(j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知情權的有關規(guī)定進行救濟,由經營者對其數(shù)據(jù)利用行為的正當性進行舉證說明。《電子商務法》第十七條也明示了經營者的信息披露義務和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保障義務,這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路徑相重合,可與信息保護相關規(guī)則形成呼應和補充,對交易活動中的不當信息利用行為進行規(guī)制。
(二)加強多方主體的綜合協(xié)同治理
算法監(jiān)管的實質是矯正信息的不對稱性,大數(shù)據(jù)技術作為經營者營利的工具,其使用過程具有隱蔽性,消費者個人難以判斷經營者是否落實了法律規(guī)定的“告知義務”。在商業(yè)利益的驅動下,依靠企業(yè)的自我審查又難以保證公正性。因此,引入第三方監(jiān)督及追責制度,通過他律性機制與自律性機制的結合對大數(shù)據(jù)殺熟行為形成有效約束十分必要。
自律性機制主要為行業(yè)協(xié)會的內部管理,具體可以通過制定行業(yè)定價浮動標準、規(guī)范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運用以及建立相應的懲戒機制等措施加強自我約束。他律性規(guī)制主要體現(xiàn)為政府主導的外部監(jiān)管。從我國現(xiàn)行法律法規(guī)來看,各級價格管理部門應當依據(jù)《價格法》的有關規(guī)定對經營者的定價行為進行監(jiān)測和管理,市場監(jiān)督管理部門可以根據(jù)《電子商務法》《反壟斷法》等規(guī)定對經營者不當?shù)亩▋r行為進行監(jiān)管。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認識到,法律的懲戒和有關機構的監(jiān)管都晚于問題的產生,各平臺作為能夠最早且最直接發(fā)現(xiàn)問題的主體,應當擔負起技術責任和社會責任,主動利用其技術和信息優(yōu)勢,通過對經營者的價格設定采取各種監(jiān)督、控制措施,確保經營者能夠合理使用用戶數(shù)據(jù)并實施正當?shù)慕洜I行為,從而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