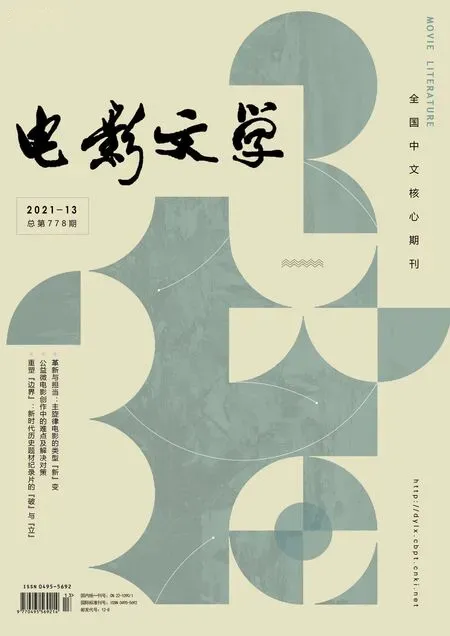“三一律”結構下的懸疑電影《狙擊電話亭》
趙婷婷 史麗芳(華北理工大學輕工學院,河北 唐山 063000)
《狙擊電話亭》是一部短小精悍的美國懸疑片,雖然電影的宣傳點是驚悚,但從觀影效果來看,影片的精彩點不在內容的驚悚,而是導演和編劇在短短的81分鐘內,用一個僅占方寸空間的電話亭和極少的演員,展現一個被狙擊手威脅為人質的男人身上發生的故事。電影比舞臺劇可以多重發揮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將時間和空間無限拉長,通過可移動的攝影機,打破固定空間,擴大時間容量。但是這部電影卻沒有運用這種方法,反倒是運用舞臺劇中的經典理論“三一律”完成了超乎想象的戲劇沖突。可以說此片是戲劇經典定律“三一律”在電影上嫁接的典范之作。本文就從“三一律”方面,探討導演和編劇如何在表達人性主題的同時帶給觀眾更大的戲劇震撼。
一、單一場景的敘事,使情節更加緊湊
在進行影片分析之前,我們必須先對“三一律”有所了解。“三一律”是西方戲劇結構理論之一,亦稱“三整一律”,是一種關于戲劇結構的規則。先由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戲劇理論家琴提奧提出,后由法國新古典主義戲劇家確定和推行。它要求戲劇創作在時間、地點和情節三者之間保持一致性。要求一出戲所敘述的故事發生在一天(一晝夜)之內,地點在一個場景,情節服從于一個主題。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理論家布瓦洛把它解釋為“要用一地、一天內完成的一個故事從開頭直到末尾維持著舞臺充實”。
如要遵循“三一律”的創作原則,在整個影片中就必須使用單一場景的敘事模式。單一場景的敘事發生在一個限定空間內,場景的單一決定了創作者無法利用時空的自由轉換來推動情節的發展,無法通過外界的幫助實現敘事,而只能依靠故事本身的推動力。這樣就更加考驗創作者對于故事情節張力的表達。成功的單一場景電影往往是通過新奇的故事和強烈緊湊的情節取勝。本部影片作為“三一律”的典范,將故事情節的安排做到極致,通過故事情節本身的曲折性和新奇性來吸引觀眾。
影片選擇曼哈頓街區即將要拆除的一個電話亭作為敘事的場景地,選擇電話亭是因為創作者可以通過電話將不同的時空和人物連接起來,拓展單一場景受限的時空,讓故事情節的發展更加合理和緊湊,情節所產生的沖突也更加扣人心弦。
情節沖突一就是主人公斯圖接起一通無法放下的電話。影片開場就是斯圖在游刃有余處理各種工作事務,周游在各方勢力之中,塑造的是一個精英公關的形象。直到他進入到這個電話亭打給一個叫潘的女孩之后,他很自然地接起了電話亭中響起的另一通電話,從此噩夢開始。一開始斯圖用他以往的經驗,想恐嚇這個陌生人,離開電話亭。可是狙擊手射擊了一個亭邊的機器人,警告了斯圖離開電話亭的后果。
導演和編劇設計電話亭為第一個沖突,即將整部影片的場景固定下來,也為以后的故事情節發展做了鋪墊。比如:為什么狙擊手會選擇斯圖作為目標?為什么斯圖明明有移動電話還要來這個電話亭打電話?狙擊手最后真的會殺了斯圖嗎?斯圖還有可能走出電話亭嗎?這樣的單一場景設計將觀眾的眼光全部聚焦在故事本身的具體走向上,讓觀眾時刻關注在與電話亭變故有關的人物身上,而不是場景的變換上。
情節沖突二是狙擊手射殺了想將斯圖拉出電話亭的男人。斯圖無休止地占用電話亭,惹怒了街邊的妓女——他影響了她們的生意。她們命令男人必須把斯圖拉出來,斯圖對這些人表現得非常暴躁和輕視。男人越來越生氣,砸了電話亭的玻璃,試圖將斯圖拉出電話亭。狙擊手不停地問“是否需要幫助”,斯圖在最后關頭回答了“YES”,之后這個男人被射殺,倒在大街上。這個情節沖突使得事情完全脫離了斯圖的想象,變得完全不可控,事態進一步惡化,原本只是斯圖和狙擊手的對決,可是現在第三方勢力警察來到了現場,他們在聽到妓女的證詞后,想要讓斯圖投降走出電話亭。
情節沖突三是斯圖的妻子凱利和出軌對象潘看到各大電視臺的現場報道之后來到現場,斯圖無奈之下向媒體暴露自己的真實面目。狙擊手以妻子凱利和潘為威脅,要求他在所有的媒體面前承認自己的出軌和虛偽,在經過無數的掙扎之后,他照做了,聲淚俱下地懺悔,使得整部電影的情節達到了高潮,所有電話亭前的人和站在影片之外的觀眾真實地感受到主人公斯圖懺悔時的真誠和無助。
在這樣狹窄的電話亭中,導演和編劇用三個情節沖突,一步步將情節推進,故事走向慢慢超出主人公和觀眾的想象,在不斷的意外之中,觀眾慢慢走入影片的節奏。在單一場景中,單純利用故事情節沖突來延續故事的發展和吸引觀眾的好奇心,的確是精彩絕倫的情節設計。
二、視聽語言與封閉空間結合重構影視時空,造就緊迫感
“三一律”的“時間、地點、情節的一致性”,雖然會使整部影片的情節非常緊湊,抓住觀眾的眼光,可是它對時空的限制意味著故事細節不夠豐富。為了使得電影故事情節更加引人入勝,導演一方面遵守著“三一律”;另一方面又大量使用能展現電影細節的視聽語言,豐富影片的內容。
電影的視聽語言,即影像元素與聲音元素,它們分別通過對受眾產生視覺與聽覺刺激,來敘事造型。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而一部成功的電影必然做到音畫統一、視聽合一。
電影《狙擊電話亭》中首先選擇一個封閉狹小的空間,構建整個故事情節。封閉空間往往是導演將人物內心和現實建立聯系的一種途徑,在封閉的空間中,人的生理和心理處于一種極限的狀態。在這樣的環境中,外界和內在的矛盾沖突會更加突出,因為人此時處于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中,只能憑借內心潛在的自我去對抗所有的突發情況。
影片中主人公從進入電話亭開始就陷入了封閉空間的恐怖和絕望之中,在此期間他面對的既有外部妓女的打擾,又有狙擊手對妻子凱利和出軌對象潘性命的威脅。在狙擊手一槍打穿電話亭玻璃,子彈從斯圖耳邊飛過的時候,主人公斯圖已經確定他無法從這個電話亭中走出,除非他能夠向這個世界直接宣告他的真面目。是否走出封閉空間就成為主人公斯圖是否化解自己內心矛盾的標志。其間面對無論是想拉出他的男子還是后來到現場的警察,斯圖都沒有放棄對真實自我的保留和保護,因為這是他最后的尊嚴,所以他始終沒有走出電話亭一步,可在他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以后,他面對著所有的媒體,徹底地暴露了他的真面目,然后以求死的心情走出電話亭:無所謂狙擊手是否會射殺自己。這樣封閉空間就完成了一個導演設定的特定象征符號的作用:一個從偽善走向誠實面對自我的過程。
電影使用了純粹的聲音來達到對主人公斯圖和觀眾的震懾。聲音是電影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電影中的聲音不僅可以塑造人物、推動劇情,還可以增加觀眾對影片故意“留白”的想象。狙擊手出現伊始就一直是以聲音的形式存在,直到影片的最后才出現他的容貌。狙擊手的聲音冷靜而神秘,有著掌控一切的自信和對眾生的蔑視,特別是邪魅的笑聲,讓主人公斯圖和觀眾毛骨悚然。這樣的處理,讓主人公斯圖一步步走入狙擊手的陷阱,也讓觀眾時刻沉浸在狙擊手的安排中。這種看不見的危機更能加強神秘與恐懼感。狙擊手的聲音不只是一個恐怖的狙擊手形象的外化,也是一個如同上帝一般的心靈拷問者的存在:他不斷逼迫主人公斯圖面對真實的自我。
影片為了突破單一場景的限制,營造懸念,出現了大量高層建筑的鏡頭,使影像情緒非常緊張與壓抑。高層建筑是電話亭的外圍,電話亭內的緊張氛圍主要通過主人公和狙擊手的對話營造。四周的高層建筑圍繞著電話亭,是封閉空間之外的大封閉空間,本身就有一種壓抑感,導演又運用特寫鏡頭,將高聳的建筑和建筑上無數窗口作為威脅主人公的一個個槍口,潛在危險成為這些高層鏡頭的特點,也成為感染觀眾情緒的有力場景。
通過這三方面,影片將戲劇理論的“三一律”和現代電影成熟的視聽語言技術結合在一起,使影片產生了新的連貫時間,也使影片的空間無限擴大,在時空的重構中,影片的壓迫感增強,不僅是對主人公的壓迫,也是對觀眾的壓迫。
三、“狙擊手”和觀眾共同構成局外人視角呈現人性的偽善和懦弱
電影以局外人的視角展示場景和人物,可以在具體事件上提供給觀眾新的感受和認識。在《狙擊電話亭》中狙擊手和觀眾都算局外人,影片內外的視角將理性和感性交融在一起,讓觀眾在體驗影片刺激的同時,又能深刻體會劇中人物的喜怒哀樂。
狙擊手為何能夠作為影片的局外人存在呢?狙擊手雖然在影片中是主人公斯圖的掌控者,是存在于影片中的人物,但是從狙擊手的自我描述中,他其實更像是一個觀察者,觀察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再選擇其中惡行滿貫的人進行懲罰。在懲罰過程中,他時刻看著被懲罰者的表現,他是能夠隨時改變主人公行動軌跡的特殊局外人。
觀眾是一個天然的局外人,在單一的場景中,觀眾作為電話亭外的圍觀者,隨時留意著亭內可能發生的狀況,并跟隨主人公的情緒。在影片中,觀眾跟隨鏡頭的轉換來觀察和預測主人公斯圖可能會有的結局。觀眾這個局外人身份,更像是上帝視角,能全面地看清事情的現狀,卻無法實質參與到事情本身。比如在影片的最后,觀眾為主人公斯圖拿著槍走出電話亭而動容,達到共情的時候,只能站在場外默默注視,不能有任何行動。
這種影片內外雙重局外人的視角,除了能將故事的主線清晰地展現出來,還能站在局外看清影片想表達的關于人性的主題,這也是導演和編劇獨具匠心之處,用故意“疏離”影片的方式站在所有情節和人物之外去體察電影更加宏大的主題。
主人公斯圖所代表的就是用偽裝和欺騙的方式,看似游刃有余地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群人,他們極盡虛偽,道貌岸然,可他們的生活中滿是謊言:他出軌一個年輕的想出名的女子,借口是會給她介紹更多的人認識,卻將妻子蒙在鼓里;用以后的報酬期許,哄騙一個年輕的孩子給他免費工作,每次利用完就一走了之。
狙擊手用殘酷的方式逼迫他公布自己的行為,站在影片之外的觀眾,也在用道德的意念,期盼他用誠實實現自我救贖。這兩個局外人才是整個影片看得最真實和清楚的。人本身是有很多人性缺陷的,但我們依然需要誠實面對懦弱膽小的自己,面對已經很糟糕的生活,這才是解脫和前進。
電影《狙擊電話亭》以“三一律”為準,將單一的場景、人物和情節放在短短的時間內,構建一個封閉空間下的恐懼故事,在有限的時空中,使用電影的視聽語言擴展了時空,讓觀眾感受到更為緊湊和有壓迫感的劇情和氛圍。同時讓觀眾站在局外人的視角,更理性地看待人性問題。不論是劇情設計還是鏡頭運用,都稱得上是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