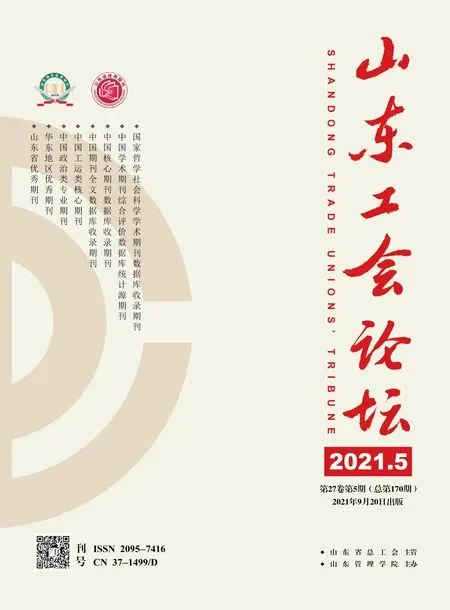家庭互動模式代際傳遞與社會工作介入研究
——基于魯北濱州市部分家庭的案例分析
邱 珊
(齊魯師范學(xué)院 歷史與社會發(fā)展學(xué)院,山東 濟南 250002)
社會學(xué)研究發(fā)現(xiàn),家庭互動模式存在顯著的代際傳遞性。從現(xiàn)代意義上看,伴隨社會的發(fā)展,現(xiàn)代公民家庭經(jīng)歷了不同程度的變化與革新,在家庭結(jié)構(gòu)、家庭信仰、生活方式、家族觀念等方面都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傳統(tǒng)單一的家庭互動模式被現(xiàn)代多樣化的溝通所替代,家庭互動模式呈現(xiàn)出多元分化的趨勢。廣義上,我們可將這種多元家庭互動模式歸納為兩大類,即積極的家庭互動模式與消極的家庭互動模式。積極的家庭互動模式也稱為良性家庭互動模式,這種家庭互動模式一旦進入代際傳遞,就會形成良性循環(huán),對家庭功能的正常發(fā)揮起到正向積極的作用;相反,消極的家庭互動模式即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一旦出現(xiàn)在代際間傳遞中,就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huán),致使每一代人原生家庭中的問題在無休止的代際疊加中發(fā)生裂變,進而嚴重影響正常家庭功能的發(fā)揮。鑒于此,我們選擇消極或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作為研究視點,通過社會工作的介入,嘗試通過個體視角的自我認知提升與自我賦能,以及系統(tǒng)化視角的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法、模仿與社會學(xué)習(xí)等社會工作方法的介入,力圖解決不良家庭互動模式在代際傳遞中的消極影響,降低代際間的輻射效應(yīng),推進現(xiàn)代家庭的和諧構(gòu)建。
一、問題呈現(xiàn):家庭互動模式代際傳遞的顯著性與內(nèi)卷化
(一)典型性樣本選擇
濱州市地處魯北平原,是山東省下轄地級市,地處黃河三角洲腹地,總面積9400 余平方千米,人口400 萬。從濱州市的歷史沿革來看,它幾乎沿襲并參與了中國社會史上每一次的社會變遷與變革運動。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年來,濱州市積極探索自身發(fā)展優(yōu)勢,在深入挖掘現(xiàn)有資源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突破性發(fā)展,無論在城市文化事業(yè)、醫(yī)療衛(wèi)生、基礎(chǔ)設(shè)施、社會保障等宏觀層面,還是在社區(qū)建設(shè)、家庭建設(shè)等中微觀層面,濱州市作為中國城市發(fā)展的一個縮影,都具有較高的研究代表性與典型性。
為了研究的順利開展,課題組選擇了濱州市部分職工家庭作為典型案例進行追蹤調(diào)查,其中家庭成員中有退休人員的家庭占比60%。之所以選擇部分退休職工家庭作為典型案例,是因為:一是從縱向時間軸上看,退休職工家庭普遍表現(xiàn)為兩代或兩代以上成員的家庭結(jié)構(gòu)。這種家庭結(jié)構(gòu)適用于對代際傳遞問題的縱向研究。二是從家庭結(jié)構(gòu)橫向比較上看,與農(nóng)村家庭互動模式相比較,城市家庭互動模式發(fā)生時間更早并且內(nèi)容更廣泛地受到社會變革的影響,家庭成員交往互動形式更趨于多樣化、多元化。因此,鑒于研究意義顯著性的考慮,我們選擇了濱州市部分退休職工家庭作為研究樣本,對其進行了廣泛的取樣與個案追蹤。
(二)代際傳遞外在表征顯著性
遺傳學(xué)、行為學(xué)臨床研究發(fā)現(xiàn),兒童心理及社會性素質(zhì),基本是通過后天觀察、模仿、互動、反復(fù)體驗而習(xí)得的。原生家庭中家庭成員的互動方式、親密關(guān)系、教育方式等社會性情感或態(tài)度,往往對兒童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就是家庭模型的代際傳遞現(xiàn)象。家庭互動模式作為家庭模型的一個表象與重要屬類,在顯著性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見圖1)。

圖1 家庭互動模式對家庭成員的影響
課題組成員通過對濱州市部分職工家庭所做的調(diào)查研究以及個案追蹤,發(fā)現(xiàn)在缺乏民主、溝通互動僵化的家庭結(jié)構(gòu)中,家庭成員更多地表現(xiàn)為對其他家庭成員的憎恨與排斥,同時家庭成員間情感反應(yīng)更為消極與淡漠、成員間也缺乏互動的動機,在面對生活困境的處理上則傾向于拒絕、排斥其他家庭成員的幫助。在這種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下成長起來的孩子,成年后自身在處理婚姻、家庭問題時更多的顯得無所適從,同時有更大的概率面臨與原生家庭相類似的問題。
作為某事業(yè)單位一名退休人員,案主L 女士退休之后仍然延續(xù)了與丈夫長期分居的生活方式。L 女士來自一個嚴謹而又傳統(tǒng)的家庭,祖籍浙江,當年父親作為知識青年分配到濱州市工作。L 女士大專畢業(yè)后與父親同事的兒子組建家庭,并育有一個女兒,女兒現(xiàn)年31 歲,已經(jīng)參加工作。L 女士與丈夫自組建家庭起感情一直不好,兩人個性鮮明,有各自的追求,尤其對生活有著不同的理念,婚后角色調(diào)整失敗,感情始終無法磨合,在女兒小學(xué)畢業(yè)后二人便開始分居生活,夫妻二人各自居住一套住房,偶爾相聚也總是不歡而散。女兒在這種聚少離多并充滿了沖突、不安與矛盾的家庭中生活了31 年,并始終單身。訪談中談到擇偶觀這個問題時,女兒沒有任何猶豫地給訪談?wù)卟恍家活櫟幕卮稹皼]想過”“不想找”,當提及對將來婚姻的憧憬時,女兒黯然地回答“不敢想”“沒有信心”。我們在對其他家庭進行訪談時,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即長期生活在父母婚姻不幸的家庭中的孩子,更易對婚姻產(chǎn)生排斥或恐懼心理,或者即使已經(jīng)組建家庭,也更易面臨婚姻生活長期不和諧的困境。顯而易見,家庭互動模式在代際間的傳遞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而不良家庭互動模式在這一研究背景下則成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三)內(nèi)卷化①
從社會學(xué)的角度看,內(nèi)卷化更類似是一種“內(nèi)耗”,即自我耗竭或自我殆盡。不良家庭互動模式的內(nèi)卷化是由長期的家庭互動模式代際傳遞造成的,每一代人在潛移默化地認同或模仿著原生家庭互動方式與行為規(guī)范的同時,往往以更加激進的方式自我卷入,這種不斷的簡單重復(fù)再復(fù)制,導(dǎo)致每一代人無形之中都在推動或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研究發(fā)現(xiàn),代際傳遞的發(fā)生往往不止于或者不限于對原生家庭的模仿或復(fù)制,很大程度上代際傳遞會擴大原生家庭的某些特征,這種良性循環(huán)或惡性循環(huán)間接反映了社會學(xué)意義上的“馬太效應(yīng)”。因此,內(nèi)卷化的出現(xiàn)從另一個側(cè)面加重了問題的發(fā)生。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少數(shù)在專制、閉塞、不良互動模式的家庭中成長的孩子也會察覺到自己的問題,并反思這些問題與早年生活經(jīng)歷的關(guān)系,通過自我成長、環(huán)境改變等方式進行自我治愈,盡力避免將自己曾經(jīng)體驗過的不良互動方式再次復(fù)制到自己孩子身上。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與這種不良家庭互動模式相比,在良性互動的家庭關(guān)系中成長起來的孩子,成年后家庭幸福、事業(yè)成功的概率更高,更易培育起家庭成員間的“承諾”關(guān)系,發(fā)展出和諧的家庭關(guān)系并構(gòu)建起良好的人際環(huán)境。
二、承諾與互動: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下情感性依戀的破壞
不良家庭互動模式對家庭建設(shè)以及家庭成員的發(fā)展、家庭功能的正常發(fā)揮造成的不利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歸根結(jié)底,這種影響可以歸結(jié)為對家庭成員間情感性依戀(Lawler &Yoon,1996)[1]的破壞,而家庭中的情感性依戀是以一種“承諾”的方式體現(xiàn)的,即不良家庭互動模式最終導(dǎo)致的結(jié)果本質(zhì)上表現(xiàn)為家庭成員間“承諾”的撕裂。
承諾是對關(guān)系的一種情感性依戀或者對關(guān)系主體的一種喜愛情感。如上文所述,家庭互動模式出現(xiàn)問題,實質(zhì)上是家庭成員對彼此“承諾”的破壞。Lawler 等學(xué)者在關(guān)系凝聚力理論(theory of relational cohesion)中闡明,承諾這一行為不僅包括單方面的贈予、持續(xù)保持與特定對象的交換等表征,同時承諾行為會伴隨家庭結(jié)構(gòu)的變化而變化[2]。“承諾”如同家庭成員之間的一種隱性契約,當家庭互動模式出現(xiàn)了問題,人們之間的“承諾”便隨之坍塌,甚而家庭結(jié)構(gòu)被迫瓦解。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角度看,“承諾”的作用是降低關(guān)系的不確定性,保障家庭成員互動的穩(wěn)定性,實現(xiàn)家庭功能。因此,需要從不良家庭互動模式這一表象性的問題著手,由外而內(nèi)地重構(gòu)家庭成員“承諾”關(guān)系,最終從根本上實現(xiàn)家庭互動模式的良性化運轉(zhuǎn)與代際傳遞(見圖2)。

圖2 承諾與互動:社會交換理論對家庭內(nèi)部關(guān)系聯(lián)接與互動的解析
三、個體取向:自我賦能與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代際傳遞的阻斷與改良
降低不良家庭互動模式在代際間的傳遞或者實現(xiàn)在代際傳遞間的改良,是針對“傳遞”這一特殊現(xiàn)象所進行的內(nèi)部重構(gòu)。家庭成員中的每一個人,既是不良家庭互動模式的識別者,也是阻斷者,成員通過意識覺醒、自我提升,積極、開放、理性地發(fā)現(xiàn)問題,改善固有的家庭互動模式,是阻斷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代際傳播的前提與基礎(chǔ)。這種自我重構(gòu)更近似于一種認知導(dǎo)向的自我提升,一種對良性家庭互動模式的積極模仿或?qū)W習(xí),這無疑對家庭中的每個成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每一位家庭成員坦誠、開放地審視自身的問題,通過自我認知的提升進行交往方式的自我重構(gòu)。
(一)認知導(dǎo)向的自我提升與理性關(guān)懷
認知行為理論認為人的行為取決于人對社會情景的知覺與加工過程,問題行為往往源自認知的缺失或認知失調(diào)(cognitive dissonance)②。如何解釋社會事物的過程,如何理解家庭互動關(guān)系中所呈現(xiàn)的冷漠、矛盾、孤立等不良互動問題,如何看待不良家庭互動模式這一表象問題,是認知的重要內(nèi)容,即問題的解決首先取決于案主是否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通過每一位家庭成員對認知失調(diào)的積極調(diào)整,理性地看待家庭互動中的問題,確定家庭成員在家庭關(guān)系中恰當?shù)慕巧ㄎ唬歉纳萍彝セ幽J降年P(guān)鍵,也是阻斷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代際傳遞的前提。
在對濱州市個案訪談的整理中,案主H 先生的回答引人深思。“她不搭理我,我也懶得理她,大小事基本不商量。可能吧(我的家庭有矛盾),不過這事沒什么好聊的”,“多少年了,傳統(tǒng)中國家庭不都這樣嗎?沒什么需要改進的……”。顯然,即使案主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后,仍然不愿意正視問題。案主H 先生作為認知主體,其原有的生活經(jīng)驗、價值觀、情感狀態(tài)、認知偏差、隱含人格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均可作為影響因子,導(dǎo)致H 先生最終在其個體認知領(lǐng)域始終對不良家庭互動給家庭帶來的困境這個議題存在著排斥與回避。可見,家庭成員能否客觀、理性、坦誠地看待不良家庭互動問題是決策的前提與關(guān)鍵(見圖3)。

圖3 案主H 先生“家庭互動”認知系統(tǒng)
客觀、理性認知的形成除了認知主體自身原因外,還受到認知對象的特征、認知情境因素的影響。在此案例中,家庭互動模式作為認知對象是一個抽象的存在,而家庭成員卻是真實地存在于家庭情境中,因此案主對家庭互動模仿的認知泛化到了家庭成員身上,通過對家庭成員的態(tài)度反映出案主對不良家庭互動的漠視。而作為認知情境因素,無論空間距離還是環(huán)境因素在此案例中均屬于非顯著性要素,在對不良家庭互動的解釋力方面,均讓位于認知主體要素。
(二)角色獲得與社會化
以個體取向阻斷不良家庭互動模式的傳遞,或者改進原有家庭互動模式,案主的角色獲得與再社會化是自我賦能與自我提升的另一個重要途徑。角色的概念最早由社會學(xué)家斯麥爾(Simmel,1920)提出③。萊維(Levy,1952)在著作《社會結(jié)構(gòu)》中將角色界定為“由特定社會結(jié)構(gòu)來分化的社會地位”[3],紐克姆(Newcomb,1961)則強調(diào)“角色是個人作為一定地位占有者所做的行為”[4],彼得爾(Biddle,1979)在《角色理論:期望、同一性和行為》中提出“角色是一定背景中一個人或多個人的行為特定”[5]。可見,角色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概念,不同的學(xué)者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強調(diào)了角色的一個側(cè)面。
角色是人們對特定位置上的人所產(chǎn)生的一種行為期待與價值規(guī)范。角色和社會化相應(yīng)而生。通過社會化的過程,人們得以獲得一種新的社會角色,而當人們承擔(dān)某一特定角色時,再社會化也正在發(fā)生。每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在不同階段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旦角色無法順利地過渡或者轉(zhuǎn)變,便會引起角色沖突。家庭作為一個角色扮演的特殊情境,對家庭成員有著不同的角色定位,夫妻、父母、子女不同的角色規(guī)范使家庭成員之間形成了彼此不同的角色期待。然而,在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作用下,家庭成員易催生出非理性的角色期待,或者家庭成員自身沒有完成角色過渡,導(dǎo)致家庭成員時常表現(xiàn)出不同程度的角色沖突。
在對不良互動家庭的訪談中,我們發(fā)現(xiàn)部分案主的潛在思維方式是:我婚前(或做父母前)就是這樣的(比如懶散、依賴、低責(zé)任感等),現(xiàn)在結(jié)婚了(或成為父親或母親了)仍然表現(xiàn)出原來的狀態(tài)是理所當然的。案主看似正確的言論中,實則把“角色轉(zhuǎn)變”完全拋在命題之外。研究發(fā)現(xiàn),從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中走出來的家庭成員,在婚姻前后或成為父母角色后,都會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出角色轉(zhuǎn)變的失誤或角色沖突,或者對夫妻角色、父母角色存在不恰當?shù)慕巧诖瑢?dǎo)致自身社會化的停滯,這種角色轉(zhuǎn)變的失敗又加劇了不良家庭互動問題的程度,引起惡性循環(huán)。
另外,在自我建構(gòu)的過程中還需要避免家庭成員的責(zé)任分散或社會墮化(social loafing)心理的產(chǎn)生。相對于獨立的個體成員,家庭更趨向于一種小群體的建構(gòu)。不良家庭互動方式帶來的是個體對群體的不信任、家庭低效度的交往以及較低的認同感,這種群體關(guān)系成為社會墮化發(fā)生的天然土壤。在這種“混水摸魚”式的社會墮化作用下,責(zé)任分散在所難免,每個人趨于推諉、回避自身的問題,放大其他家庭成員的錯誤,難以正視家庭的問題,導(dǎo)致家庭成員間彼此逃避、漠視、低反應(yīng)度的家庭互動模式。
四、系統(tǒng)化取向:社會工作介入與有效代際傳遞
如果將通過自我賦能和自我提升來阻斷或者改進不良家庭互動模式歸為個體取向,那么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法以及模仿與社會學(xué)習(xí)等社會工作視角的介入則更趨向于系統(tǒng)取向(見圖4)。

圖4 良性家庭互動模式構(gòu)建的策略體系
(一)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與家庭互動
20 世紀60 年代,美國家庭治療大師薩爾瓦多·米紐秦(Salvador Minuchin)創(chuàng)建了結(jié)構(gòu)式家庭治療模式,以重建家庭結(jié)構(gòu)、改變相應(yīng)的家庭規(guī)則作為治療原則,旨在將僵化的、模糊的家庭系統(tǒng)界限變得清晰,并具有滲透性以及應(yīng)對變遷的彈性,治療方法與切入點即設(shè)法改變維持家庭問題或癥狀的不良家庭互動模式。
1.“承諾”的重構(gòu)
解決當下的問題,是實現(xiàn)有效代際傳遞的前提。通過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法的介入,重構(gòu)家庭成員間的“承諾”,實現(xiàn)良性互動以及有效的代際傳遞。承諾作為家庭成員之間一種信任關(guān)系,是引起家庭良性互動的根源與基礎(chǔ)。在高承諾的家庭,成員之間存在高信任的關(guān)系。在不同承諾程度的家庭中,對同樣的一個問題,不同家庭成員的反應(yīng)方式或理解方式也常常存在較大的差異。研究中,對“配偶下班后比往常晚了1 個小時還沒有到家,打電話打不通”情景的設(shè)置,案主A 回答“肯定又和狐朋狗友喝酒(或打牌、唱歌等娛樂)去了”。同樣的情景,來自另外一個家庭的案主B 回答“估計堵車了,再等等吧”。顯然,案主A 和案主B 在配偶晚到家又“失聯(lián)”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家庭成員之間不同程度的信任或承諾關(guān)系。當然,案主A 和B 之所以作出如此迥然的回答,體現(xiàn)了家庭交往中的一種日常,案主A 對配偶的刻板印象與其配偶日常生活中的低責(zé)任感、低尊重以及不良溝通行事方式相干,案主A 配偶的自身行為也難逃其咎。可見,承諾是一種雙向關(guān)聯(lián),單純地提醒或要求案主A 去信任對方顯然是不合理的。
“承諾”作為一種特殊的關(guān)系,有較強的穩(wěn)固性,即承諾關(guān)系的存在能在很大程度上讓關(guān)系趨于穩(wěn)固,并且難以打破。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承諾”也有一定的脆弱性,即承諾關(guān)系一旦確認打破了,將不易重構(gòu)或者重構(gòu)的過程需要家庭成員“打破方”加倍努力的付出。所以,“承諾”的重構(gòu)不是某一個家庭成員努力的結(jié)果,需要所有家庭成員在日常態(tài)系中正視問題,重視問題,尤其是承諾關(guān)系的“打破方”更要“小心翼翼”地通過自我意識的提升、高責(zé)任感、改善溝通方式等,在生活情景中逐漸扭轉(zhuǎn)家庭成員對關(guān)系“打破方”的不良印象。
2.進入和順應(yīng)家庭:“情景”焦點
結(jié)構(gòu)取向往往以“情景”作為焦點,強調(diào)環(huán)境與人的相互影響,而非單純個人的內(nèi)在動力。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方法立足還原真實的家庭互動模式,個人的問題也必須在家庭場景中才能夠如實展現(xiàn)。作為研究背景同時又是研究手段,家庭“情景”對于整個研究過程有著特殊的意義。首先,還原真實的家庭互動模式是研究初期遇到的一個難題。即使先前通過社區(qū)工作人員的引薦或者社區(qū)調(diào)查,我們已經(jīng)初步選定了“問題”家庭,但當真正進入這些家庭后,家庭成員潛意識的“配合性”仍然讓研究成員難以觀察到真實的情景。因此,需要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或熟識,選擇半?yún)⑴c式觀察研究方法,才能使研究逐漸得以展開。其次,作為研究手段,家庭是我們介入的環(huán)境同時也是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問題來自家庭,解決問題也要回歸家庭情景。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方法的“情景”焦點,與家庭互動議題有著天然的連接,為改善不良家庭互動模式這一問題提供了基礎(chǔ)與保障。因此,為了了解家庭的交往方式,社會工作者僅僅客觀地旁觀是不夠的,社會工作者更應(yīng)是一個積極的角色,通過參與式的干預(yù),使家庭原有的交往方式在短時間內(nèi)顯露出現(xiàn),并且通過考察家庭改變交往方式的彈性,探索演練新的交往方式。
3.勾畫家庭結(jié)構(gòu):家庭次系統(tǒng)與“邊界”
家庭是存在“邊界”的。“邊界”的存在讓家庭呈現(xiàn)一定的規(guī)則,降低家庭成員互動的不確定性。家庭可以看作一個系統(tǒng),每一個成員可以作為一個個體,也可以和其他成員形成“聯(lián)盟”式的次系統(tǒng),個體、次系統(tǒng)之間存在界限。“邊界”規(guī)定著次系統(tǒng)的功能,確定了家庭中的權(quán)力集體,從而決定了家庭結(jié)構(gòu)。當一個次系統(tǒng)家庭成員侵犯或者占據(jù)了另一個次系統(tǒng)時,家庭的結(jié)構(gòu)便出現(xiàn)了問題,并通過不良的家庭互動模式呈現(xiàn)出來。
作為一個家庭,如果成員之間沒有形成特有的“邊界”,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闖入一個次系統(tǒng),那么在分工或結(jié)構(gòu)上就會出現(xiàn)混亂,家庭功能就無法正常發(fā)揮。然而,當家庭次系統(tǒng)之間的“邊界”缺乏滲透性或彈性、界限過于僵化時,次系統(tǒng)之間處于完全隔離的狀態(tài),家庭功能同樣難以正常發(fā)揮。因此,家庭次系統(tǒng)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界限以及界限的滲透性,確保父母次系統(tǒng)與兒女次系統(tǒng)的適度隔離是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法比較關(guān)注的問題。
4.典型病態(tài)家庭結(jié)構(gòu):疏離與聯(lián)合對抗
糾纏和疏離易導(dǎo)致家庭中某些成員間結(jié)成聯(lián)盟,當沖突發(fā)生時,結(jié)成聯(lián)盟的成員會沒來由地一味維護本聯(lián)盟的成員,與其他成員相對疏遠或?qū)αⅰ0钢鱄 先生在得知我們的研究項目后,主動通過社區(qū)工作人員聯(lián)系上了我們。H 先生是當?shù)匾患覈衅髽I(yè)的退休技術(shù)人員,和同樣在該企業(yè)退休的妻子、28 歲的兒子、82 歲的岳母生活在一起。岳母有自己的老年生活,對H 先生一家的問題從不過問也不干涉。通過初次會面,我們了解到H 先生和兒子之間存在溝通困難的問題,無論H 先生如何主動和兒子交流甚至示好,兒子均置之不理。在家里,兒子唯一溝通的對象就是母親。按照初次會面的約定時間,H 先生一家三口來到訪談室,在落座的剎那,兒子不假思索地和母親坐在一起,形成了H 先生和母子之間隔離的家庭結(jié)構(gòu)。這種不良的家庭結(jié)構(gòu)不僅展示出了家庭的問題,同時也是造成家庭成員互動問題的原因之一。為此,需要按照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法,通過重新勾畫家庭結(jié)構(gòu),改變家庭看法與家庭成員價值觀,明晰家庭界限,推進家庭問題的解決。
現(xiàn)實生活中,所有的家庭均要面對生活中的壓力與困擾,當外界環(huán)境或家庭內(nèi)部產(chǎn)生變化時,結(jié)構(gòu)功能正常的家庭能夠做出調(diào)整,以適應(yīng)這種變化,而功能失調(diào)的家庭往往固守原有的家庭結(jié)構(gòu)或已經(jīng)失效的交往互動方式,形成病態(tài)的家庭結(jié)構(gòu)。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方法以其對“家庭互動”相關(guān)議題關(guān)注的自身優(yōu)勢介入問題家庭,通過對家庭結(jié)構(gòu),尤其是家庭溝通方式等多方面的分析、解剖、重構(gòu),達到最大化家庭功能、構(gòu)建和諧家庭的目的。以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的視角介入家庭互動模式代際傳遞,能夠?qū)⒉涣蓟幽J酱H傳遞問題止于原生家庭,即通過對“當下”問題的介入、治療,從而完成家庭互動模式良性代際傳遞的使命。
(二)社區(qū)內(nèi)模仿與社會學(xué)習(xí)
如果將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法看作針對家庭問題的一整套內(nèi)部治療體系,那么社區(qū)內(nèi)模仿與社會學(xué)習(xí)則更接近于外部環(huán)境的取向。從另一個角度看,積極模仿與學(xué)習(xí)良性家庭互動模式也是自我建構(gòu)的一部分。模仿(imitation)是強化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之一。模仿是習(xí)得的,是主動效仿他人言行的社會心理現(xiàn)象,而模仿反應(yīng)是一種社會泛化現(xiàn)象。班杜拉(Bandura,1977)的社會學(xué)習(xí)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6]更進一步地說明了環(huán)境對于改變個人行為的重要意義。班杜拉認為,家庭成員互動行為,很大程度上受到來自個人和環(huán)境兩方面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交互決定論得以充分展示(見圖5)。因此,在環(huán)境中樹立典型,模仿、學(xué)習(xí)良性的社會互動模式,成為家庭成員從外界獲得改善的突破口。

圖5 交互決定論④:行為并非終極輸出端,而是個人和環(huán)境相互作用的要素
社區(qū)作為社會系統(tǒng)的一個子系統(tǒng),是居民生活最密切的外界環(huán)境。社區(qū)既區(qū)別于宏觀的社會環(huán)境,又是一個微縮版的小社會,社區(qū)居民彼此熟識,鄰里街坊間存在較高參照性與信任性。對于家庭互動模式這一議題,我們發(fā)現(xiàn)在社區(qū)內(nèi)部,通過搜集素材、積極案例的正向引導(dǎo)、樹立典型等方式對于改進不良家庭互動有著顯著的效果。
XM 社區(qū)是濱州市2003 組建的社區(qū),雖然社區(qū)成立的時間比較晚,但是共同的生活環(huán)境、相似的生活軌跡,使共處于社區(qū)氛圍下的居民對彼此街坊鄰里比較熟識。XM 社區(qū)自2016年開始每年評選“社區(qū)五好家庭”,評價涉及公民道德、社區(qū)美德、和諧家庭構(gòu)建等多個方面,能夠當選的家庭無論在社會影響、家庭氛圍、家庭成員個人的發(fā)展等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典型。將這些被選家庭作為典型素材進行案例整理總結(jié),我們發(fā)現(xiàn)與相對抽象的教材類案例相比,發(fā)生在案主身邊、發(fā)生在本社區(qū)的案例對案主更具說服力與影響力。除了社區(qū)內(nèi)這些正面典型的積極影響外,反面典型也能夠?qū)Π钢髌鸬骄训淖饔谩R虼耍茉焐鐓^(qū)內(nèi)正面典型,激發(fā)社區(qū)居民積極模仿與社會學(xué)習(xí),是改善家庭問題的另一個重要途徑。
五、結(jié)語
良性家庭互動模式代際間的傳遞這一邏輯的成立基于一個假設(shè),即當前家庭互動模式的改善能夠引起代際間的良性循環(huán)。研究從個體化取向的自我識別、自我提升到結(jié)構(gòu)家庭治療、社會學(xué)習(xí)系統(tǒng)性的分析,使實現(xiàn)家庭互動模式代際間的良性傳遞這一議題成為可能,為改善不良家庭互動模式代際傳遞問題做了理論與實踐上的探索。
研究歷時三年,跨越濱州市5 個社區(qū)近20 個家庭,隨機抽樣和個案研究同時進行。由于涉及對某個案主家庭的長時間追蹤調(diào)查,因此樣本數(shù)量受到一定的限制,影響了研究結(jié)論的深度和信度,需要今后繼續(xù)跟蹤研究。社會變遷、社會轉(zhuǎn)型以不可扭轉(zhuǎn)之勢對處于大環(huán)境中的家庭帶來日益廣泛并日漸深入的影響,家庭面對突如其來的變遷,其自身的應(yīng)對力、彈性體系都在經(jīng)受著各種各樣的考驗。家庭互動模式是家庭問題最顯著的體現(xiàn),家庭成員潛意識中對家庭互動模式的默許或認可,使原生家庭互動模式作為一種參照物式的存在于代際間傳遞中不斷地被效仿、浸染甚至復(fù)制。因此,在社會轉(zhuǎn)型加速的今天,如何通過社會工作的介入改善家庭互動模式,形成應(yīng)對家庭變遷諸多問題的天然屏障,推進代際傳遞中良性循環(huán)的實現(xiàn),對于構(gòu)建和諧家庭進而推進和諧社區(qū)、和諧社會建設(shè)均有著深遠的意義。
注釋
①內(nèi)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xué)家吉爾次(Clifford Geertz)著作《農(nóng)業(yè)內(nèi)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tài)變化過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fā)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停滯不前或者無法轉(zhuǎn)化成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xiàn)象。
②認知失調(diào)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最初由社會心理學(xué)家費斯廷格于1957 年闡明并完成理論架構(gòu),認為當各認知因素之間出現(xiàn)“非配合性”(non-fitting)關(guān)系時,認知主體變會產(chǎn)生認知失調(diào)。
③角色理論的解釋力高度依賴于角色這一概念的澄清,“角色”“角色扮演” 概念最早出現(xiàn)在德國社會學(xué)家斯麥爾(Georg Simmel)的相關(guān)論述中。
④班杜拉(Bandura)交互決定論認為個人自身因素與行為同環(huán)境因素是交互作用的關(guān)系,行為受到個人和環(huán)境兩方面因素的影響。行為并非終極輸出端,行為是對個人和環(huán)境發(fā)生作用的一個因素。